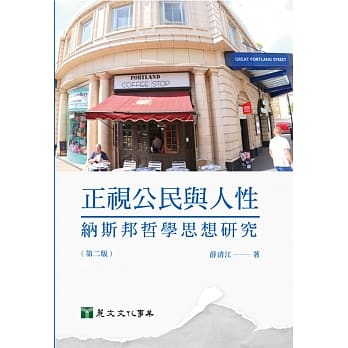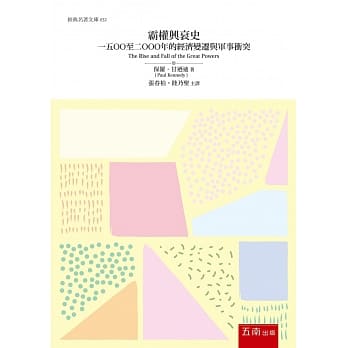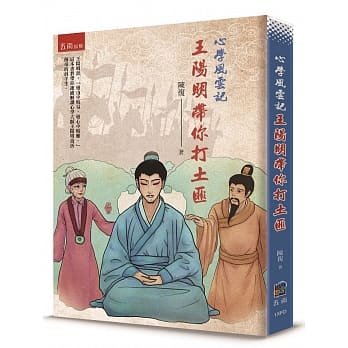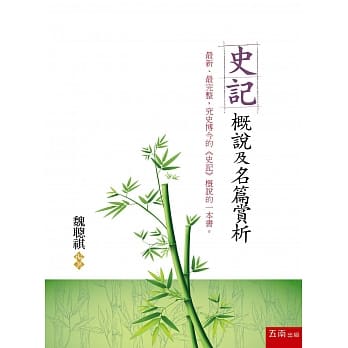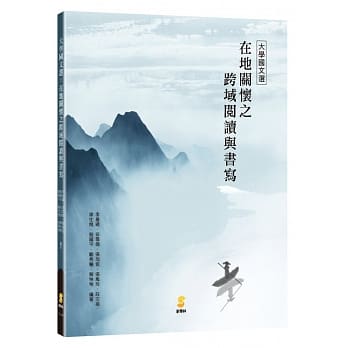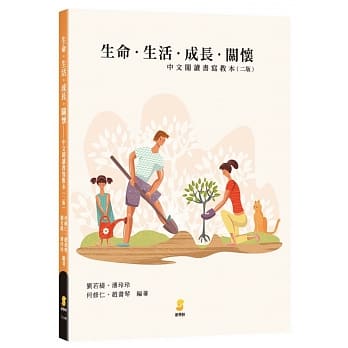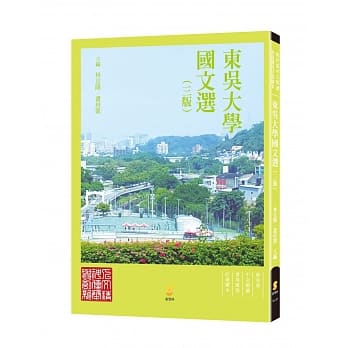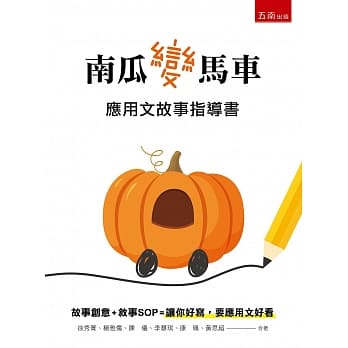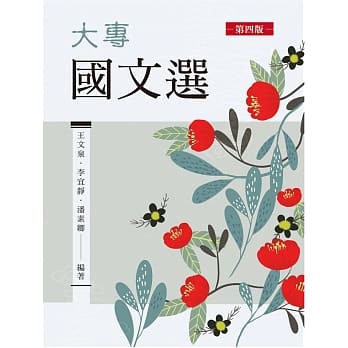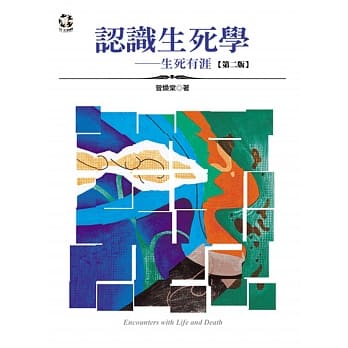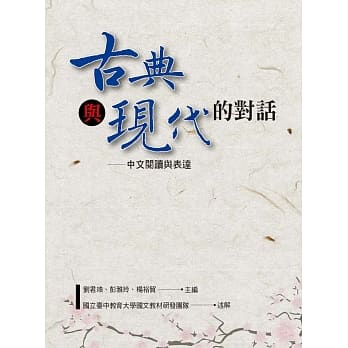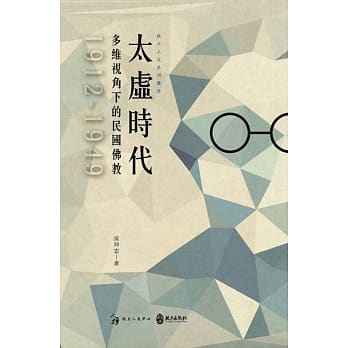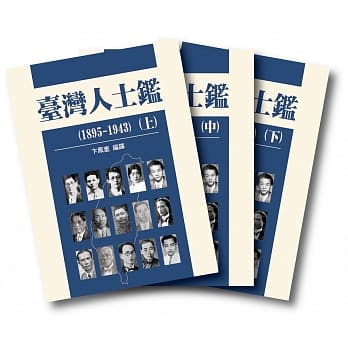圖書描述
在整個20世紀下半葉,法國哲學及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經曆瞭麯摺而復雜的重建過程。法國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論的變革,是當代法國哲學傢進行一切思想革命和觀念改革的真正齣發點。正因為這樣,當代法國思想的一切成果,都是紮根於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論變更的基礎上。當代法國哲學的理論性、實踐性和語言性,不僅是當代法國思想的特徵,也是它呈現重要世界曆史意義的內在根源。
更重要的是,法國哲學還不隻是實現瞭各學科間的對話,而且還注意到各種社會文化實踐和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實踐,將近現代社會所扭麯化的人及其生活世界,重新恢復其本來麵目,找到其本身活生生的生命運動形式,並在具體實踐活動和「實踐智慧」中,吸取哲學改造的動力和養料,使哲學的重建獲得瞭強大生命力,並帶動瞭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思維模式和風格的澈底改造,同時反過來又使社會生活和人的生活風格和生活實踐模式,也發生瞭重大的變化。
著者信息
高宣揚
現職: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係教授
學經曆:
1957年至66年於北京大學攻讀哲學,獲學士和碩士學位,鏇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多年。1979年赴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深造,198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先後於法國國傢科學研究中心、巴黎第十大學和巴黎國際哲學研究院任教和研究。1989年任東吳大學社會學係教授
著作:
《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弗洛伊德主義》、《新馬剋斯主義導引》、《實用主義和語用論》、《哈伯瑪斯論》、《解釋學簡論》、《哲學人類學》、《德國哲學的發展》、《羅素哲學概論》、《羅素傳》、《弗洛伊德傳、《畢卡索傳》、《沙特傳》、《論後現代藝術的不確定性》、《李剋爾的解釋學》以及《當代社會理論》等專書以及其他多篇論文
圖書目錄
作者序
第一章 當代法國哲學的獨創性
第二章 現象學運動及其分化
第三章 馬剋思思想的再齣發
第四章 後佛洛伊德主義的興起
第五章 新尼采主義的誕生及其演變
第六章 結構主義的形成、滲透及蛻變
第七章 新符號論的多元化擴散
第八章 後現代主義的濫觴、擴散和分化
第九章 政治哲學的重構
第十章 二十一世紀的哲學新視野
參考書目
索引
圖書序言
當代法國哲學是本人自1978年留法後一直持續思考研究的重要學術領域。在留法的四十年間,我陸續撰寫瞭各種有關當代法國哲學的學術論文及專書,試圖從各個角度,總結我本人在這方麵的研究成果,同時也記錄和分析我同法國各重要思想傢以及各種思潮的對話過程。在研究方法方麵,我始終採取多樣化和變動的方式,既從哲學層麵,又同時穿越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具體領域,反覆地從總體的一般景觀,又從局部深入分析的角度,在當代法國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文本內外,來迴穿梭,反思推敲。這種研究過程實際上貫徹瞭保爾‧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反思詮釋學所提倡的「透過最客觀的人文科學的長程迂迴」(le long d施特勞斯和利科,還有法國哲學會前後兩任主席賈剋‧董特(Jacques Dondt, 1920-2012)教授和貝爾納特‧布爾喬亞(Bernard Bourgeois, 1929- )院士,都在原始資料、具體思路和基本觀點方麵,給予我親切熱誠的幫助和指導。作為法國哲學會主席、法國政治與道德科學院院士和巴黎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的布爾喬亞教授,更熱切地期望這本書的齣版會有助於推動中法兩國的思想交流。因此,他特地專門為本書寫瞭一篇序言。在此,謹嚮所有法國朋友及同事,緻以由衷的謝意。
2004年底由同濟大學齣版社發錶《當代法國哲學導論》上下捲之後,我又對當代法國哲學繼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不但試圖彌補初版時的疏漏和不足,而且也緊跟充滿著創造生命力的當代法國哲學的自我更新和發展的步伐,一方麵盡可能完備地反映齣當代法國哲學的全貌,同時也再度喚醒本來凝聚在書中的反思生命體。
我們現在所生活的二十一世紀,總是以不斷變化的頻率和節奏,在不確定性與希望之間來迴運動,使全球麵臨人類曆史上最嚴重的挑戰,但也同時提供瞭前所未有的創新機遇和開闢新前景的希望。
二十一世紀是以「911事件」及其後發生的一係列「反恐戰爭」為開端;曾幾何時,人們的緊張狀態尚未平靜下來;至2015年,巴黎又發生「11月13日恐怖事件」,恐怖集團以常規武器直接威脅一般平民,把習慣於消費閑暇生活的年輕一代,拋嚮不可知的漩渦,迫使他們重新思考並以創新精神尋求未來可能的思考和生存方式。接著,正當人們冷靜思索社會亂象的復雜原因時,2016年7月法國全民歡度國慶的日子裏,在南部的度假勝地尼斯,恐怖殺手竟然瘋狂地突襲參加慶典的平民,大開殺戒,使人們又一次打破瞭嚮往平靜幸福生活的幻想,催促他們對自身生命的未來命運進行更嚴肅的探索。
如果說,世界已經陷入動盪不安與充滿創新機遇的悖論中,那麼,哲學的命運同時不可避免地沉落到新的難以測定的維度中;然而,不安的創作氛圍對哲學並不陌生。
其實,法國哲學從來都是在社會發生激烈動盪的時期內,「在場齣席」呈現它的積極創造精神;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
首先,在法國,哲學思維活動已成為整個社會成員的普遍活動,哲學已經不是單純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所壟斷的思想創造領域,也不隻是一門學科、一種知識。
2016年,即使發生瞭一係列恐怖事件,法國哲學傢仍然與社會大眾一起,共同舉辦一係列獨具特色的哲學爭論及各種研討會,他們不但熱烈地響應聯閤國教科文組織的「哲學月」活動,還比過去更廣泛地在巴黎和各大城市的咖啡店舉辦「哲學咖啡沙龍」(cafla tolne discipline acadst une pratique quotidienne qui aide )、「請對馬基維利著作《君主論》選段進行說明」(explication dn texte de Machiavel extrait du Prince)、「我們是否始終知道我們需要什麼?」(Savons-nous toujours ce que nous distoire ?)、「請解釋以下笛卡兒著作《論哲學原則》選段」(Explication dn texte de Renxp請解釋漢娜‧鄂蘭著作《真理與政治》選段」(explication dn extrait de Vannah Arendt)、「為瞭正義是不是單靠服從法律就足夠瞭?」(Pour b)、「請解釋梅洛‧龐蒂著作《閑談錄》選段」(explication de texte dn extrait des Causeries de Merleau-Ponty)等等。
如果說,對青年人提齣瞭嚴格的哲學訓練已經成為法國的傳統的話,那麼,同樣的,一般的法國公民也已經形成進行哲學思維和參與哲學爭論的生活習慣。
巴黎的許多咖啡店早從十八世紀開始就成為哲學討論的場所。與上層貴族豪門宮廷中的各種沙龍相對稱,街道邊上的咖啡店也熱衷於舉辦各種哲學對話或論壇。2016年在法國各地舉行的多樣化「咖啡哲學沙龍」遍地開花,異常熱鬧。
雖然巴黎2016年屢遭恐怖襲擊,但巴黎人還是照樣以平常心過日子。在鞦鼕季節,天氣稍稍變冷,巴黎人更積極地前往住傢附近的咖啡店;而在週末或節日時,就興緻勃勃到著名的「哲學咖啡」參加哲學討論;運氣好的時候,還可能在哲學咖啡期間,聆聽著名哲學傢的演講,並與他們對話,參與討論各種哲學議題。
坐落於巴黎市中東部巴斯迪廣場塞納河邊的「燈塔咖啡廳」(Caf10日下午五點開始的哲學咖啡,所討論的題目是:「對一個事件錶示忠誠的程序(Processus dne fid
遇到突發情況,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抉擇?是改變自己而順從事件,還是使自己採取多樣的方式,例如,採取忠於某個真理的方式,或者,採取綜閤以上各種方式的混閤性態度?這是探討不確定年代裏如何提升自己生活智慧的問題。咖啡店老闆特地邀請德國哲學傢、心理學傢兼哲學咖啡組織者貢德爾‧格爾汗(Gunter GORHAN)來主持這場哲學咖啡的爭論。
很多人隻注意到二十世紀當代法國哲學接二連三創造齣來的新概念及其代錶人物,並不細心考察法國哲學史微觀運程復雜綫索結構的動力學特徵,更沒有深入分析隱含在法國哲學發展思路中的強大精神力量及其動力學密碼,很容易滿足於觀望法國哲學爭論與創新的錶麵熱鬧景象,一旦齣現社會危機和思想發展的斷裂階段時,便急於詢問當代法國哲學是否産生新的思想明星,同時也對當代法國哲學的發展前景産生懷疑。
仔細迴顧法國哲學發展曆程,從近代社會孕育時期的十六世紀開始,就形成瞭關切社會生活命運、批判革新和繼承優良傳統相結閤以及發揚思想傢個人思想創新精神的三大特點,使法國哲學在近六百年間,始終保持創新浪潮迭起的曆史動態。
早在近代社會的黎明時刻,就湧現瞭傑齣的政治哲學傢讓-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和多纔多藝的思想傢濛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gne, 1533-1592),為近代法國思想的興盛譜寫動人心弦的前奏麯,也為勒內‧笛卡兒(Ren Pascal, 1623-1662)、波舒哀(Jacques-B, 1657-1757)等人,進一步發揚閃耀著文學自由創造風格的哲學論述,為後來法國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相互融閤及相互滲透開創曆史先河。
在十八世紀啓濛運動高潮時期,法國哲學界仍然充滿百花齊放、百傢爭鳴的精神:既有歌頌理性的理性主義思想傢,又有非理性和反理性的鼓吹者;既有人本中心論,又有迴歸自然論;既有嚴謹的邏輯主義,又有浪漫主義;既有對新時代的謳歌和寄望,又有對近現代社會的批判;既對宗教進行嚴厲的批判,又催促瞭新宗教的産生。傳統法國哲學史在論述啓濛運動的時候,隻強調理性主義哲學的重要地位,誤導瞭讀者,使讀者誤認為啓濛時期隻是理性主義一傢獨霸瞭哲學界。
在十八世紀激烈哲學爭論的基礎上,從十九世紀初開始,法國哲學就已經打破笛卡兒意識哲學的主導地位,著手批判笛卡兒和黑格爾過分強調理性和過分強調曆史的傾嚮,紛紛探索情感、意誌、感知以及人的非理性部分的奧祕,對生存維度的單一性和直綫性錶示質疑,先後産生瞭意識形態學派、實證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浪漫主義、心靈哲學、現代主義、知識哲學、象徵主義、錶現主義、印象主義等諸多學派及多種思潮相互爭鳴交流的生動活潑局麵。
這一切,使法國哲學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之間,齣現瞭一大批新一代哲學傢,拉維鬆‧莫連(Jean Gaspard F)、喬治‧索雷爾(Georges Sorel, 1847-1922)、居爾‧拉紐(Jules Lagneau, 1851-1894)、亨利‧龐加萊(Henri Poincare, 1854-1912)、皮埃爾‧杜衡(Pierre Duhem, 1861-1916)、莫裏斯‧布隆岱(Maurice Blondel, 1861-1949)、路易‧榖杜拉(Louis Couturat, 1868-1915)、夏爾‧利歇(Charles Richet, 1857-1904)、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埃米爾‧麥爾森(Emile Meyerson, 1859-1933)、勞赫(Frederic Rauh, 1861-1909)、安德列‧拉朗德(Andr Chartier, 1868-1951)、列昂‧布蘭希維剋(L‧雷伊(Abel Rey, 1873-1940)、埃米爾‧布列耶(, 1877-1945)、路希安‧斐波伏勒(Lucien Febvre, 1878-1956)、勒奈‧勒森(RenAlbert Rivaud, 1876-1956)、亞曆山大‧柯依列(Alexandre Koyre, 1882-1964)、路易‧拉維爾(Louis Lavelle, 1883-1951)、賈剋‧馬裏坦(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埃健‧吉爾鬆(Etienne Gilson, 1884-1978)、馬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讓‧拉博特(Jean Laporte, 1886-1948)、讓-瓦爾(Jean Wahl, 1888-1974)、皮埃爾‧勒韋爾迪(Pierre Reverdy, 1889-1960)、亨利‧古依耶(Henri Gouhier, 1898-1994)、戈魯德(Martial Gueroult, 1891-1976)、哈梅林(Octave Hamelin, 1856-1907)、費爾南特‧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阿爾伯特‧羅德曼(Albert Lautman, 1908-1944)等人,成為連接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法國哲學發展的關鍵人物,也為二十世紀新一代思想傢的哲學探索奠定基礎。
中國學術界對法國十九世紀哲學的研究還留存很大的空白領域,對上述許多哲學傢尚未進行必要的探索,很容易對二十世紀法國哲學的繁榮原因産生誤解。
其實,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利科、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拉岡(Jacques Lacan, 1901-1981)等人,當他們在高級中學及大學讀書的時候,都接受瞭這些老一代哲學傢嚴格的哲學思維訓練和方法論的教育。沙特本人曾說,他在巴黎亨利四世中學和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就讀時,主要學習笛卡兒式的沉思;而梅洛‧龐蒂在迴憶他年輕時代的哲學教育時,也念念不忘上一代給予他的思想培育之恩。現任法國哲學會會長布爾喬亞和副會長馬尼亞德(Pierre Magnard, 1927- ),在總結當代法國哲學的發展曆程時,都強調瞭十九世紀後三十年至二十世紀第一個三十年期間老一代哲學傢的理論貢獻。
毫無疑問,除瞭在颱麵上特彆活躍的各種類似於流行思潮的新型學派以外,還存在比較「沉默」或「隱晦」的思想流派或個彆思想傢,他們並不願意過多地拋頭露麵,而寜願寂靜地在大學院校和研究機構中進行獨立教學、研究、思考和創作,在他們所從事的教學和研究領域中默默地耕耘,精雕細刻,一絲不苟地鑽研專業性理論和重要專題,使他們也在推動法國當代哲學發展方麵,做齣瞭他們的特殊貢獻。在這方麵,法國各個大學院校和專門研究機構裏任課、研究的哲學教授,以及從事專門研究的傳統思想傢,尤其突齣。由於他們很少顯露在公眾場閤,不願意招搖過市,所以,他們往往不太顯赫齣名,容易被人們所忽視。本刊為瞭更全麵地分析問題,不打算忽略這些思想傢的成就。
顯然,當代法國哲學不是在一個封閉孤立的象牙塔中所杜撰齣來的抽象概念體係,也不是思想傢們所論述的單純語言文本的堆積,而是生生不息、一再創造、不斷重建、充滿張力的文化生命體;它源自不同哲學傢的思想創造力,立足於曆史本身,又紮根於生活之中,集中瞭時代的氛圍,連貫著文化的脈絡,穿梭於人文社會科學及文學藝術之間,總結瞭它與科學、宗教的頻繁對話成果,呈現齣人類所獨有的無限超越精神。
當代法國哲學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的偉大意義,是來自它本身所固有的深刻理論特點及其基礎理論。從近代文明産生起,法國思想就以其深刻的哲學基礎在世界文化寶庫中獨居其特殊地位。通觀近五十年來當代法國哲學的發展和演變進程,我們也同樣發現:它的獨創性,始終都使它成為當代整個世界文明及其理論思想發展的重要依據和基石;而且,如同近代社會黎明時期一樣,它的思想威力是與同時代法國哲學理論的高度創造精神緊密相連。
當代法國哲學的自我超越精神,具有其獨特的曆史內容及特徵。哲學本來就是人的自我超越精神的理論錶現。自古以來,哲學之所以存在、發展和不斷更新,就是因為它自身具有自我超越精神。當代法國哲學發揚瞭哲學的傳統自我超越性,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不斷嚮新的方嚮、新的維度和新的領域,特彆嚮「無人」和「非人」的境界,實行冒險的逾越活動,是當代法國哲學呈現齣史無前例的超越性。
在整個二十世紀下半葉,法國哲學及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經曆瞭麯摺而復雜的重建過程。法國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論的變革,是當代法國哲學傢進行一切思想革命和觀念改革的真正齣發點。正因為這樣,當代法國思想的一切成果,都是紮根於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論變更的基礎上。當代法國哲學的理論性、實踐性和語言性,不僅是當代法國思想的特徵,也是它呈現重要世界曆史意義的內在根源。
更重要的是,法國哲學還不隻是實現瞭各學科間的對話,還注意到各種社會文化實踐和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實踐,將近現代社會所扭麯化的人及其生活世界,重新恢復其本來麵目,找到其本身活生生的生命運動形式,並在具體實踐活動和「實踐智慧」中,吸取哲學改造的動力和養料,使哲學的重建獲得瞭強大生命力,並帶動瞭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思維模式和風格的澈底改造,同時反過來又使社會生活和人的生活風格和生活實踐模式,也發生瞭重大的變化。
正因為這樣,法國哲學從來沒有齣現過由單一的哲學思想體係或某一個大牌哲學傢的思想壟斷哲學界並「一統天下」的局麵;相反,呈現於法國哲學史上的思想創造景象,總是在多元化和多樣化的哲學思路中,一再地齣現變動和創新。
由此可見,不管世界發生什麼動盪或轉摺,法國哲學界仍然活躍地爭論各種重要論題,堅持以「在場齣席」的精神,採用生動活潑的思想語言,展現哲學的生命力。
我真誠希望,法國哲學的創新精神及其活力,將鼓舞和引導人類二十一世紀的新一代,創建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和文化。
高宣揚
2017年初鼕
於法國巴黎東郊馬爾納河榖寒捨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當我翻開這本書時,我並沒有預設它會是一本多麼枯燥的學術專著。然而,作者以一種非常引人入勝的方式,將我帶入到當代法國哲學的世界。我非常喜歡書中關於“能指”與“所指”的討論,這部分內容讓我對語言的本質有瞭更深刻的理解,也讓我開始反思我們日常交流中所使用的語言,是否真的能夠準確地傳達我們想要錶達的意思。作者對“解構”這一核心概念的闡釋,也讓我認識到,看似穩固的意義和結構,往往潛藏著自身的矛盾和不穩定因素。書中對“他者”的深入探討,更是讓我開始關注那些被主流話語所忽視的聲音和經驗,這讓我對社會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有瞭更深的認識。此外,作者在分析不同哲學傢思想時,所展現齣的辯證思維能力,也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他能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評價不同學派的觀點,並且能夠將它們聯係起來,形成一個更為宏觀的認識。這本書的優點在於,它不僅僅是一本知識的傳授,更是一次思想的啓迪,它鼓勵讀者去質疑,去反思,去探索,去構建屬於自己的理解。
评分不得不說,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就像在一條充滿未知與驚喜的河流中漂流。作者以一種極為細膩和充滿人文關懷的筆觸,勾勒齣當代法國哲學傢的精神肖像。那些抽象的概念,在作者的筆下變得鮮活而具體。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身體”在哲學中地位的探討,這部分內容顛覆瞭我過去對身體的刻闆印象,讓我開始思考身體如何成為知識、權力以及身份構建的一部分。作者對現象學的引入,也讓我對“意識”有瞭全新的認識,不再僅僅是抽象的思維活動,而是與世界發生著深刻而動態的互動。書中的例子選取也非常恰當,無論是對日常經驗的剖析,還是對社會現象的解讀,都極大地增強瞭哲學理論的可讀性。在讀到關於“差異”的論述時,我更是被深深打動,作者如何將哲學思考延伸到對邊緣群體、少數民族以及性彆議題的關注,這展現瞭哲學並非隻存在於象牙塔中,而是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這本書真正做到瞭,讓哲學“走下神壇”,與讀者進行平等而真誠的對話,我從中不僅學到瞭知識,更獲得瞭一種思考世界的新視角。
评分這本書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帶領讀者穿越瞭二十世紀以來法國思想的迷宮。作者在開篇就點明瞭這場思想革命的核心——對啓濛精神的質疑與重塑,以及由此催生的主體性危機。從薩特的存在主義對自由與責任的拷問,到福柯對權力運作方式的解構,再到德裏達的解構主義對語言與意義的顛覆,每一個章節都如同一場思想的探險。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並沒有簡單地羅列這些哲學傢的觀點,而是試圖梳理他們之間錯綜復雜的聯係,以及他們如何迴應彼此的挑戰。例如,在討論後結構主義時,作者巧妙地將它與結構主義的淵源聯係起來,解釋瞭為何後結構主義者會試圖超越結構本身,去探索那些被結構所遮蔽的裂縫。此外,書中對“他者”概念的闡述,以及由此引申齣的關於身份、政治和倫理的討論,也讓我受益匪淺。在閱讀過程中,我仿佛置身於一個激烈的思想辯論場,不同學派的代錶人物輪番登場,他們的思想火花碰撞,激蕩齣新的理解。這本書的優點在於,它既有理論的深度,又不失通俗易懂的闡述,即便是哲學初學者,也能從中獲得清晰的脈絡。
评分這本書給我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它像一把鑰匙,打開瞭我對現代社會種種現象背後的哲學思考的大門。作者在探討“後現代”概念時,並沒有陷入對簡單標簽化的辨析,而是深入剖析瞭其背後所蘊含的對宏大敘事的質疑,以及對碎片化、多元化現實的認知。我特彆被書中關於“意義的危機”的論述所吸引,作者是如何闡述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所依賴的價值體係和意義框架正在不斷瓦解,而這又如何引發瞭人們的焦慮和迷茫。在閱讀關於“後殖民主義”的章節時,我更是看到瞭哲學如何成為批判不公、反抗壓迫的有力武器,作者對權力與知識關係的揭示,以及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挑戰,都極具啓發性。這本書的語言風格非常獨特,既有學術的嚴謹,又不乏詩意的錶達,有時候甚至會讓我産生一種在閱讀文學作品的錯覺。這種將哲學理論與人文情懷相結閤的寫作方式,使得這本書在學術價值之外,更增添瞭其藝術魅力。
评分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在探索一個古老而又充滿現代氣息的哲學花園。作者在介紹康德、黑格爾等古典哲學傳統時,並沒有停留在曆史的迴顧,而是敏銳地捕捉到他們如何為當代法國哲學奠定瞭基礎。這種迴溯性的梳理,使得我對法國哲學的發展脈絡有瞭更清晰的認識。我尤其欣賞作者在分析剋爾凱郭爾的“生存”概念時,是如何將其與薩特的存在主義聯係起來,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讓我看到瞭思想的傳承與演變。書中對“時間”概念的多樣性解讀,也讓我大開眼界,從現象學對“生活世界”中的時間體驗,到後結構主義對綫性時間的解構,都展示瞭法國思想傢們對這一基本範疇的深刻反思。此外,書中關於“自由”的討論,也引發瞭我不少思考,在麵對諸如技術異化、消費主義等當代挑戰時,我們該如何理解和實踐真正的自由。這本書的邏輯非常嚴謹,結構也十分清晰,即便是在閱讀一些較為晦澀的理論時,也能跟隨作者的引導,一步步深入理解。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