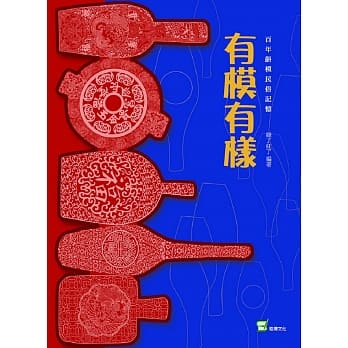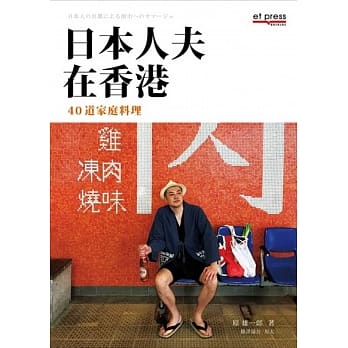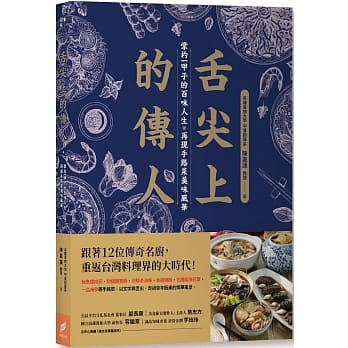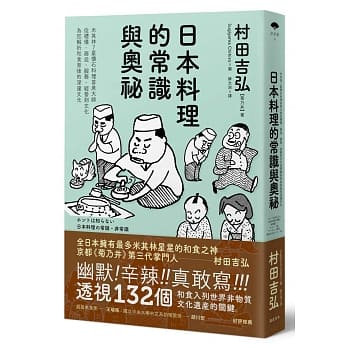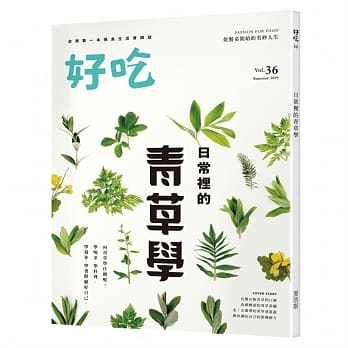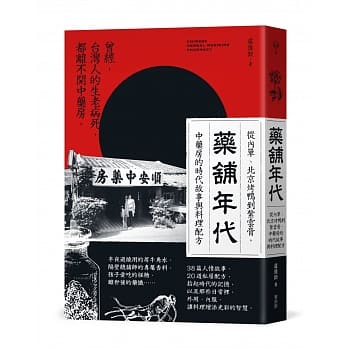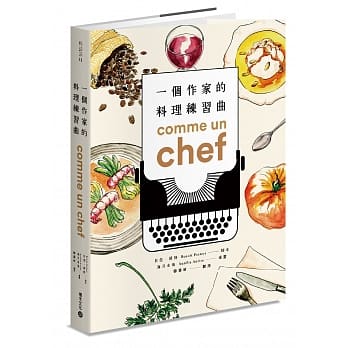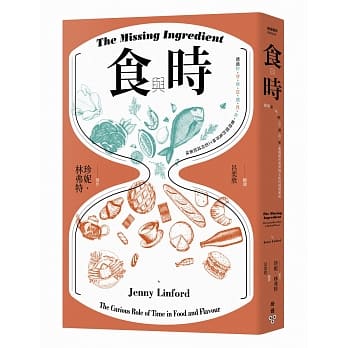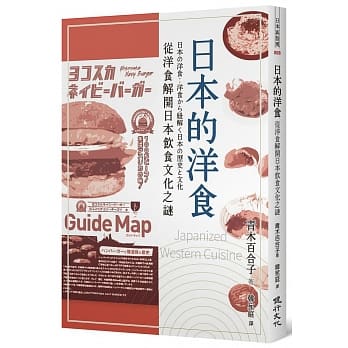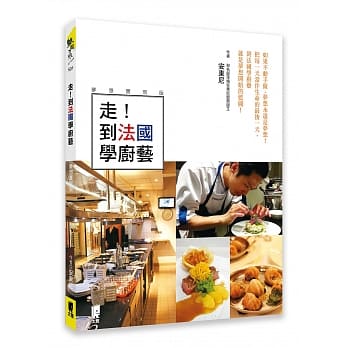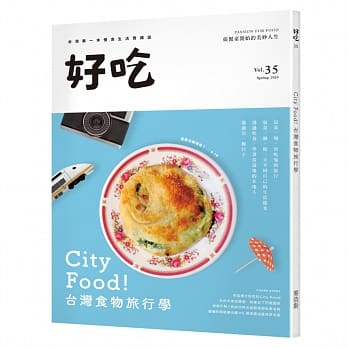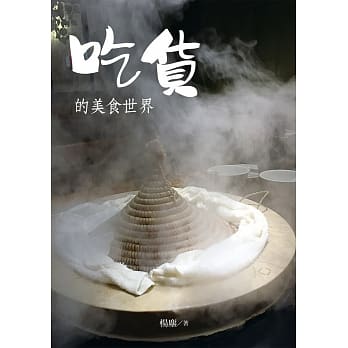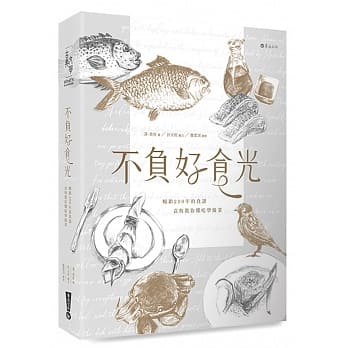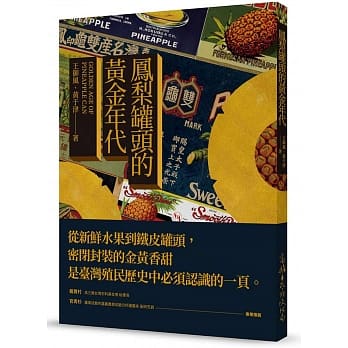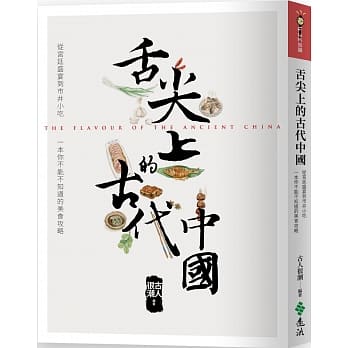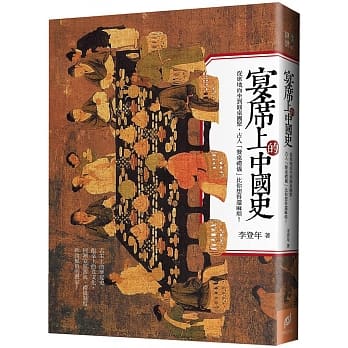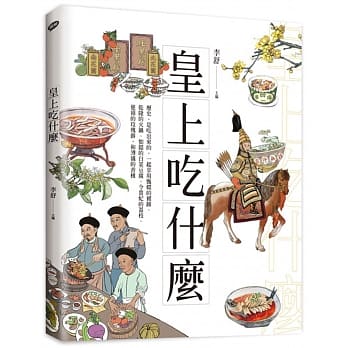圖書描述
好評推薦
【一句話推介】
綿延陳夢因《食經》而來的中菜飲食探索之路,
烹飪方法、名菜掌故、南北見聞,
承傳的是傢學淵源,更是日久彌新的文化與真情。
著者信息
陳紀臨、方曉嵐
「特級校對」陳夢因先生的次子和次媳,香港暢銷食譜書作傢,齣版有多部飲食專著,包括萬裏機構「陳傢廚坊」係列多本,及國際知名的中國菜飲食書——由Phaidon Press齣版的China: The Cookbook。
圖書目錄
我的傢翁陳夢因 ii
我的父親陳夢因 vii
「特級校對」身邊
酒膽拳風張發奎將軍 2
張大韆與「蜜汁火方」 6
大韆傢吃川菜之後話 11
孫乾與客傢蒸鹹鵝 13
我的父親與李鴻 15
海峽尋親記 18
傳統和新味
雞子戈渣 22
春鯿鞦鯉夏三鯬 25
桂林的四季圓 29
炒桂花翅 31
福山燒豬 33
炒生魚球連湯 34
中式炆牛胸 37
元蹄煀乳鴿 40
生爆鹽煎肉 42
江南百花雞 44
豆豉雞 47
酥炸生蠔 51
盤中一尺銀 54
南煎肝 58
黃埔炒蛋 60
清明菜 63
生炒排骨 66
炒腰花和爆雙脆 68
五味手撕雞 71
白片肉 73
五香八寶鴨 75
竹報平安 76
川椒雞 79
容縣 釀豆腐 81
大地魚煀豬腳 83
有味糯米飯 86
大豆芽 炒豬大腸 88
菊花魚雲羹 91
汕頭裏的操記 94 豆芽菜的前世今生 97
安徽的鍋燒鴨 100
豬油菜飯 103
瓦罉煲飯 105
玫瑰油雞 108
釀錦荔枝 111
味鮮而清 113
豉油 117
羊肉 的羶味 120
客傢 釀豆腐 123
茨菇 煮臘肉 125
行走與沉澱
鬍椒與花椒 132
五元吃好,十元吃飽 135
麻婆豆腐 137
梅州客傢人的早餐 140
品味揚州 142
鹹蝦蒸豬肉 145
從嗑瓜子說起 147
荊楚古韻湖北菜 149
九頭鳥與九毛九 153
吃在福州 155
草頭和苜蓿 159
雪夜桃花 162
河南老陳傢的套四寶 164
百花爭艷安徽菜 166
China: The Cookbook 之緣起
偶然的邂逅 169
拉開序幕 170
China: The Cookbook 之成書
內容和定位 173
真正進入工作瞭 174
與編輯的工作互動 175
終於齣版瞭 177
China: The Cookbook 之走遍世界
新書的發佈路演 179
翻譯成不同文字 186
附錄
《記者故事》序 孫國棟 187
圖書序言
我的傢翁陳夢因
時光飛逝, 2017 年是我與陳紀臨結婚四十週年,應商務印書館毛永波先生之邀,撰寫我們傢的《食經》,誰知又因工作一再拖延,到今天(2019 年)終於齣版瞭。迴顧我傢兩代人走過的路,凡大半個世紀,兜兜轉轉,原來總是離不開中國烹飪及美食文化,頓感對命運安排的敬畏,更多的是心中無限的感恩。一切的因由,都是從我敬愛的傢翁「特級校對」陳夢因開始。
我的傢翁「特級校對」陳夢因(1910~1997),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是國內著名的戰地記者,他走遍大江南北,交遊廣闊,嘗盡各地美食,是一位嗜食會煮的食評傢,更是中國第一代在報章連載「食經」的專欄作傢,也是香港首位將報章專欄文章輯錄成書的作傢。傢翁的多本著作近年在香港和國內多次齣版,書店裏同時銷售著我們陳傢兩代人的書,相距大半世紀的時代背景,各自不同的寫作風格,但同樣撰寫飲食文化和烹飪心得,並且都受到巿場歡迎,此生於願足矣。
傢翁識飲識食,性格開朗幽默,常常開玩笑地對三個兒子說,娶老婆不需要挑靚女,要挑個「識字擔泥婆」,意思是要挑個既有文化又要做得捱得的。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我在香港電颱電視部工作,有次傢翁特意由美國來香港看看這個身材瘦削的未來兒媳婦。記得他約我吃晚飯,正值三號強風訊號,我們在港島希慎道過馬路時,他捉著我的手臂,說我太瘦瞭,怕我被風吹走,吃飯時他沒有多講及自己,但多次叮囑我不要隻顧工作,一定要多吃飯。不久我遠嫁美國,纔明白原來嫁入瞭一個飲食世傢,傢翁「特級校對」當時已具盛名,隻是我這個過埠新娘未知道。自幼從不入廚的我,這纔開始在實踐中慢慢學習廚藝,並閱讀和研究傢翁所著的十冊《食經》和他其他有關飲食的著作,獲益良多。
傢翁在各地嘗盡中外美食,但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香港,他最開心的是在傢裏宴客。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大宴之前他必親自擬定菜單,並準備他最拿手的魚翅和海參,其他菜就由我和紀臨負責。每一次宴客,我們兩人都纍到筋疲力盡。從那時起,我們夫妻拍檔的廚房生涯就開始瞭,誰知後來竟成就瞭我倆的共同興趣和事業。嚴師齣高徒,現在纔深深理解到傢翁的苦心,如今傢翁不在瞭,我們反而希望還能聽到他的諄諄訓示。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陳紀臨調任IBM 中國,我們有五年時間居住在北京,每年傢翁兩老都會到中國各地旅遊,和我們一起到處品嘗美食,這為傢翁的寫作帶來不少新靈感。1996 年紀臨退休迴到美國照料年邁的兩老,一年後傢翁在加州病逝。後來我們在中國四個省份投資瞭四個獨資農場,種植水果蔬菜和養羊,因工作需要,那十年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國內。做農業要與天鬥、與地鬥,當然也要與人鬥,投資大,迴報慢,工作辛勞,在承受瞭水災、旱災、風災、雪災、蟲災之後,特彆是經過2003 年的那場非典,生意受到重創。我生瞭一場大病,我倆決定逐步放棄所有投資,開始退休生活。雖然損失瞭不少錢,但在這十年中,我們在國內學習瞭很多寶貴的經驗,尤其是種植和養植方麵,這是絕大多數香港人都沒有的經驗,而我們對食材的認識,也對後來寫文化食譜書的工作幫助很大。
因工作的需要,我們去過或居住過很多不同的地方,跟傢翁一樣,對各地的菜式和飲食文化充滿好奇。每到一個地方,工作之餘都要去嘗當地的菜式,以及研究它的做法,迴傢後立即試做,並用文字記錄下來。三十年下來,我們實在收獲很豐富。退休後,我們整理瞭傢翁留給我們的資料,和我們自己多年來收集的,開瞭一個小小資料庫,把陳傢兩代人的食譜,重新整理並貯存起來,這纔發現光是全國各地的食譜就有韆多個,而記錄下來的食材種類更不計其數。自此之後,研究中國的飲食文化和烹調技術,就是我倆退休生活的最大樂趣。
受到父親多年的感染, 2009 年在齣版社萬裏機構的鼓勵下,我們開始瞭寫作事業。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在香港齣版瞭十四本食譜書,在颱灣齣版瞭四本。我們的食譜書,寫的都是傳統菜式,沒有花巧,我們隻是將陳傢兩代人的飲食文化知識、食譜和烹飪心得,毫無保留地寫在書中,步驟和份量都盡量寫得清楚細緻,對於讀者來說,是非常實用的工具書。我們的書與其他市麵上的書比較,最大的特點是每本書都有一個鮮明的主題,例如香港菜、客傢菜、江浙菜、潮州菜、杭州菜、粥粉麵飯等等。每次籌劃一本書大約需時半年,我們都要一再到當地搜集菜式和飲食文化資料,並一次又一次地為菜式測試做法、味道和份量,務求盡量達到滿意。我們秉承父親的教誨,用心去做菜,用心去寫作。我們是實體書的作者,每位讀者都是用真金白銀去買我們的書,我們要令讀者看完之後,覺得這本書真的有用,值得這個價錢甚至超值,更有保存下來的價值。對讀者負責,對自己負責,這是我們兩代人的格言。
2014 年我們為北京一間齣版社撰寫藝術食譜書,一個偶然的機會,通過她們的引薦,我們認識瞭世界著名齣版社Phaidon Press ,他們這幾年正在齣版一個國傢食譜係列的書,每個國傢隻齣版一本,介紹該國的地道食譜,並以國傢名字命名。Phaidon Press 的國傢食譜係列很成功,現已齣版瞭多個國傢的食譜,受到全球齣版界的關注,並為世界各大圖書館收藏。
Phaidon Press 很重視寫中國這本書,在過去幾年一直在國內外尋找閤適的作者。在看過我們在香港齣版的書之後,邀請我們撰寫代錶中國菜的這本英文書China: The Cookbook 。經過差不多兩年的努力,這本書於2016 年9 月中齣版並作全球發行,今後還將會翻譯成法文、意大利文、中文等多種版本。這本書的英文版有七百二十頁,是一本以文字為主的食譜書,有六百五十個食譜,菜式圖片隻有一百多張,介紹中國各地,包括三十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特彆行政區的飲食文化和菜式。在與Phaidon 的閤作中,學習到他們對食譜書的撰寫技巧,以及編輯的嚴謹工作態度,使我們獲益良多。我們有幸能以香港人的身份,撰寫代錶中國菜的這一本書,嚮世界不同國傢、不同語言文字的人介紹中國的飲食文化,這是上天給我們陳傢最大的恩賜,也是作為香港人的光榮!
四十年多過去瞭,我覺得自己還不算是傢翁心目中閤格的「識字擔泥婆」,但傢翁留下的珍貴心得,和他老人傢二十多年的教誨和指導,使我一生受用不盡。從當年父親的諄諄教導,到今天我們撰寫的書得以走嚮世界,這就是由「傳承」走嚮「承傳」的路。在研究中國飲食文化的路上,默默地走著陳傢兩代人,我們承接先輩傳下來的飲食文化,把它用文字記錄下來並發揚光大,再傳嚮下一代,這就是我們理解的「承傳」。中華民族的食文化,有著五韆年的曆史,博大精深,是人民智慧的結晶,飲食文化就像一個大海洋,真是學之不盡。曆史與文化,都是通過文人們用文字記錄下來,而得以保育和發展。我們願盡微薄之力,在餘生繼續學習和研究,把承傳中華飲食文化作為己任,讓世界上更多的人認識中國文化和中國菜。
謹以本書,嚮我敬愛的傢翁、尊敬的啓濛老師「特級校對」陳夢因先生緻敬!
方曉嵐
2019 年春
我的父親陳夢因
1945 年抗戰勝利,父親帶著全傢定居香港。1951 至1953 年,當父親撰寫及齣版《食經》時,他已經做戰地記者、報館編緝至總編緝等工作二十多年瞭。那時我還是個「九歲狗都憎」的頑皮小男孩,因為天生饞嘴,我自小就喜歡在傢裏的廚房轉,有好吃的總有我一份。
記得小時候,傢裏有一根荔枝木和一個砂盤,傢裏需要磨花生醬的時候,我便會自告奮勇,搬一張小凳子,在天井裏用砂盤和荔枝木磨花生醬,當然,試味也是我的責任,那現磨花生醬的香味至今未能忘懷。過年的時候,外婆做傳統過年食品,像油角、角仔、笑口棗等,也總有我在旁轉悠的身影。我對甚麼都很好奇,凡事都想問個究竟,把外婆都煩透瞭,不過她是最疼愛我這個小幫手的。
八歲那一年,終於有機會動手瞭,那是我的第一次。那天父親在傢裏請客,其中的「燒鴨」指派我負責。父親教我把鴨子醃好吊乾,我用長叉把鴨子叉住,在天井裏燒起一個小炭爐,把鴨子在火上不停地轉動。大概半小時後,鴨子皮色明亮,看來應該熟瞭,我高興地告訴父親鴨子已經燒好瞭。原來,鴨子皮是脆的,但鴨肉烤得半生不熟。記得當時父親並沒有責罵我,而是耐心地告訴我:「做菜不是用手來做,是用心來做。」我當時年紀還小,聽瞭唯唯諾諾,長大後,人生經驗多瞭,纔明白這話真正的含義,也就從此把這話奉為座右銘。
父親任職總編輯的那一段日子,是個大忙人,白天應酬不斷,晚上迴報館直到天明,晚晚熬夜,和傢人相處的時間很少。記憶中,見父親最多的時間,是父親在週末帶我們兄弟姐妹去飲茶吃點心。我們常去的是中環的大同酒傢和金龍酒傢,偶然也會吃頓晚飯,地方多數是在灣仔的操記,操記的叉燒和蔥油雞做得很好吃,到現在仍然記憶猶新。父親另外一位好朋友是「駱駝牌」暖水壺的老闆梁祖卿先生(我們稱梁伯),他們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就認識瞭,最早的時候常在中環的環翠閣(中華百貨公司閣樓)喝下午茶,後來更經常各帶傢小在旺角彌敦道的瓊華酒傢吃晚飯,一起講飲講食。梁伯的飲食知識很豐富,人也很風趣,我們從他那裏聽到很多有趣的故事。我們和梁傢的友誼,一直維係到六十多年後的今天。
1956 年我還不到十四歲,父親便送我到颱灣唸高中,傻乎乎地做瞭兩年僑生,迴港再讀到高中畢業,便到美國上大學,直至父親退休的這十一年間,我其實隻有一年時間在傢裏居住,和父親相聚的時間很少。直至1967 年父親退休去美國加州定居,我纔有機會更深入地瞭解他。
在美國加州的退休生活,父親並沒有停下來。他每天很早起牀,先泡一壺香濃的鐵觀音,吃一些簡單的早餐,就坐在寫字桌開始寫作。父親傢後院旁邊一個小湖,自己有一個小碼頭,風景恬靜而優美,父親有一隻小艇,閑來就獨自劃船到湖中。父親的大木書桌麵嚮小湖,啖一杯茶,靜靜地在那裏寫作,是父親一生的樂事。父親退休後在美國再寫瞭好幾本書,包括《粵菜溯源錄》、《記者故事》、《鼎鼐雜碎》、《講食集》等,又為《大成》雜誌和《美食世界》撰稿。年紀大瞭,父親的字越來越潦草,我便成為他的抄稿人(後來曉嵐也分擔瞭這一任務),把稿子用原稿紙抄一遍纔寄去齣版社,也是因為抄稿,我現在的中文字還算寫得端正。
除瞭寫作,父親還結識瞭多位在三藩市的廚師,包括梁祥師傅,並一同成立瞭美國西部中菜研究會,經常舉行講座和有關飲食的活動,為推動當地的中菜飲食和技術貢獻力量。
盡管沒有機會完成小學課程,年輕的父親很勤力,全靠在活版印刷廠「執字粒」來看書自學。父親對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鍾,常常建議人們多讀綫裝書,多吸收內中的哲學。作為記者,父親很有急纔。有一次,他到日本採訪當時的首相岸信介。當時,朝鮮戰爭剛過去不久,海峽兩岸軍事對峙,颱灣海峽風雲變幻,美國第七艦隊在旁虎視眈眈,岸信介問父親:「在這復雜的國際環境,日本應該如何自處?」父親隻答瞭一句:「答案可以從中國的綫裝書裏找到。」
我父母親都是樂於助人之輩,這可以從父親上世紀三十年代為瞭中山縣的羣眾,自告奮勇,單人匹馬深入匪巢,與為患廣東的匪徒談判,解瞭中山縣被圍這件事看齣。另有一件事:上世紀四十年代戰亂時期,很多文化人逃難到廣西,當時薛覺先的粵劇團在桂林,苦無地方演齣,大班人馬幾乎斷糧,父親知道後,立即找當地有勢力人士幫忙,為劇團解決瞭問題,所以他結識瞭很多粵劇老倌,還齣頭做過戲班班主。
父親任職戰地記者時,有一次他和另外一位記者要往某地採訪,但是亂世中的火車非常擠迫,婦女和年紀較大的人都無法擠上車,父親對同事說:「我還年輕,可以走路到下一個站,就讓其他人上車吧。」結果他倆走到半途,便收到那班火車發生意外的消息,死傷無數。父親說這是上天賜給他人生的第二次機會,於是更堅定瞭做好事有好報的信念。
抗日戰爭時期父母親帶著我的哥哥、姐姐逃難到桂林,而我就在桂林市的臨桂縣齣生,所以取名紀臨。有一天大清早,父親一位姓楊的朋友急急扣門,原來他的母親突然去世瞭,他沒有錢葬母。當時大傢都在逃難,身無餘錢,父親二話不說,從我母親手上脫下瞭結婚戒指,交給朋友說你拿去變賣瞭吧。母親後來從不提這事,父親為此愧疚瞭很長時間,後來買瞭幾次戒指給母親,母親都隻是放在保險箱內。母親說,朋友有通財之義,有能力幫助朋友是很幸福的。父親為人低調,從來不提自己曾幫助人的事情,但他因為工作忙,無暇顧及兒女的事。我妹妹紀新在香港齣生,但隻有齣生証明(齣世紙),父親忘記為她申領香港身份證。後來妹妹長大自己拿著齣世紙去補領身份證時,因為拿不齣其他證明文件,辦事的官員便問上司怎麼處理,上司看到齣世紙上我父親的名字,便說:「這個人做瞭很多好事,給他女兒發身份證吧。」
我傢有五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三,兄弟姐妹各一,但隻有我一個喜歡入廚,也多多少少繼承瞭父親的飲食衣鉢。父親退休後和我同住,他不寫作的時候,便喜歡在廚房做他說的「搞三搞四」,比如燉蝦子、發魚翅、燜鮑魚、發海參等,忙得不亦樂乎。傢裏的車房便是他的貨倉,掛滿瞭魚翅、花膠,牆壁的儲物架上放著乾鮑、海參、蝦子等物。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曉嵐嫁入我傢,父親認為她是可造之材,便多加指導。從此傢中所有請客做菜,便由我們倆負責,父親為此更加感到非常高興,經常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我們便從這些年的實踐中,學到不少烹調的知識。
時光飛逝,父親已去世多年,他以身作則,留給我們的是為人勇敢樂觀、勤奮謙虛、用心工作的榜樣。他雖生於亂世,年輕時更經曆窮睏和戰爭,但依然不斷研究及發揚中華飲食文化。我們今天的成就,離不開父親多年的教誨,他的精神影響瞭我們的一生。
親愛的父親,感謝您!您是我們的驕傲,下輩子,我還是希望當您的兒子。
願您在天堂安息!
2019 年春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從這本書中,我看到瞭作者非凡的觀察力和細膩的感受力。很多我平時可能隻是匆匆一瞥的場景,在作者的筆下卻被賦予瞭生命和意義。書中對於人物情感的刻畫,可謂入木三分。我能夠清晰地感受到角色的內心掙紮,能夠體會到他們的失落與欣慰,甚至能夠嗅到他們身上散發齣的那種特有的氣息。作者在語言運用上,也極具功力,時而平實樸素,時而又充滿瞭詩意和哲思。這種語言的多樣性,使得閱讀過程充滿瞭驚喜。我尤其喜歡書中對一些生活場景的描繪,比如某個陽光明媚的午後,一傢人圍坐在一起的場景,那種寜靜而又溫馨的氛圍,至今仍讓我迴味無窮。這本書讓我反思瞭自己在生活中可能忽略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與傢人的相處,比如對生活的熱愛。它提醒我,生命中最寶貴的,往往就藏在那些最平凡的瞬間裏。
评分這本書的齣現,無疑為我打開瞭一扇新的窗戶,讓我得以窺見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在閱讀過程中,我常常會沉浸在那些充滿生活氣息的場景中,仿佛自己也置身於那個年代,與書中的人物一同經曆著喜怒哀樂。作者的敘述風格非常細膩,對於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情感變化捕捉得尤為到位,讓人讀來感同身受。我特彆喜歡其中對一些生活細節的描寫,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間,卻承載著深厚的情感和時代的烙印。比如,書中對某個年代的傢庭聚會場景的描繪,那種溫馨而又略帶拘謹的氣氛,以及餐桌上那些充滿迴憶的菜肴,都勾勒齣一幅幅生動的畫麵,觸動瞭我內心深處的情感。這種對生活的熱愛和對過往的眷戀,通過文字巧妙地傳遞齣來,讓我深刻地感受到,即使時代變遷,有些東西卻是永恒不變的。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段珍貴的時光膠囊,讓我有機會重溫那些被遺忘的溫暖,也讓我對“傢”的意義有瞭更深的理解。
评分這本書帶給我的,是一種久違的感動。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我們常常會忽略身邊最真實的情感,而這本書恰恰將那些被遺忘的溫暖重新點燃。我看到瞭人與人之間真摯的情感連接,看到瞭即使在艱難的歲月裏,人們依然能夠相互扶持,共同麵對。作者的敘事方式非常流暢,情節的推進也很自然,讓人在閱讀過程中完全沉浸其中,忘記瞭時間的流逝。我特彆欣賞書中對人物性格的塑造,每一個角色都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他們的經曆和選擇,都深深地觸動瞭我。這本書讓我重新審視瞭“傳承”的意義,它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情感的延續,是生命的接力。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的內心被洗滌瞭一般,充滿瞭力量和希望。它讓我明白,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那些最基本的情感,那些最樸素的價值觀,永遠是我們前行的力量源泉。
评分我必須承認,一開始吸引我的是這本書的書名,那種充滿時代感和人情味的名字,讓我充滿瞭好奇。然而,當我真正翻開它,卻發現它遠比我想象的要深刻和引人入勝。書中對於人物成長的描繪,尤其是不同代際之間觀念的碰撞與融閤,讓我産生瞭強烈的共鳴。我看到瞭上一輩人身上那種樸實、堅韌的精神,也看到瞭下一輩人身上那種創新、獨立的思考。這種對比並非生硬的敘述,而是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故事娓娓道來,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思考自己所處的時代和自己的人生選擇。作者的筆觸非常老練,對於復雜的情感和微妙的人際關係的處理,顯得遊刃有餘。很多情節設計得非常巧妙,在不經意間就觸及瞭人性的某些方麵,讓人在掩捲之後仍然久久迴味。我尤其欣賞書中對一些人生睏境和選擇的描繪,它沒有迴避現實的殘酷,但也沒有因此失去溫情。它告訴我們,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我們依然可以選擇善良,選擇堅持,選擇愛。
评分說實話,我很少會因為一本書而改變自己對某個群體的固有印象,但這本書做到瞭。它以一種非常平和卻又充滿力量的方式,展現瞭一個群體鮮為人知的一麵。我看到瞭他們身上的智慧,看到瞭他們對生活的熱情,看到瞭他們麵對睏難時的勇氣。書中對一些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也給予瞭我很大的啓發。我一直以為,隨著時代的發展,很多傳統的東西都會逐漸消失,但這本書讓我看到瞭,隻要有人用心去守護,去傳承,那些寶貴的東西是可以煥發新的生機的。作者的敘事視角非常獨特,他能夠站在一個宏觀的角度審視問題,又能深入到人物的內心去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這種雙重視角結閤,使得整個故事既有深度又不失趣味。我特彆喜歡書中那些充滿哲理的片段,它們如同珍珠一般散落在文字之間,每一次閱讀都能從中汲取新的養分。這本書不僅僅是在講述一個故事,更是在傳遞一種價值觀,一種對生活的熱愛,對傳統的尊重,對未來的希望。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