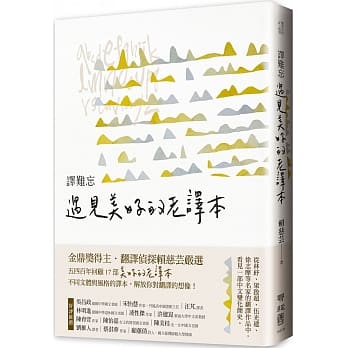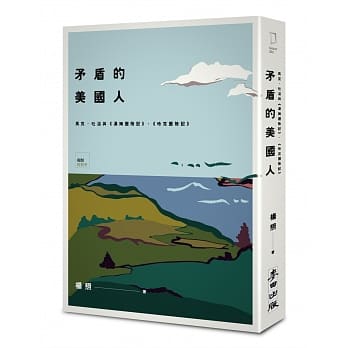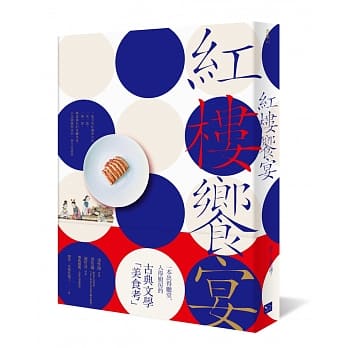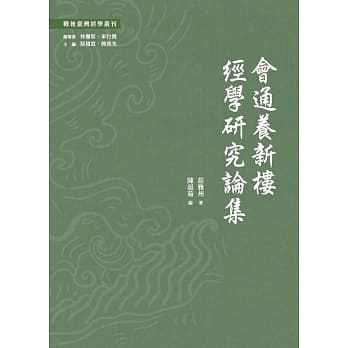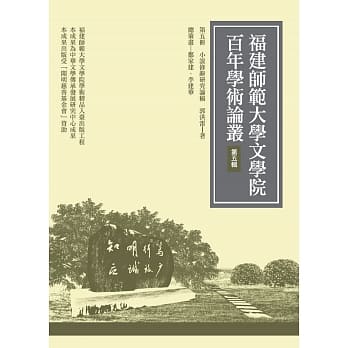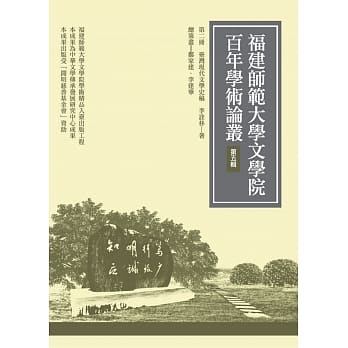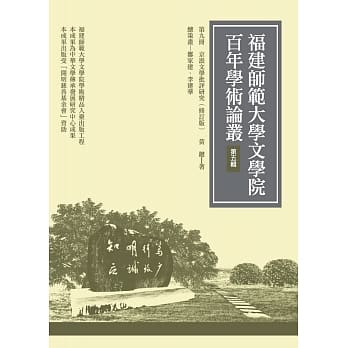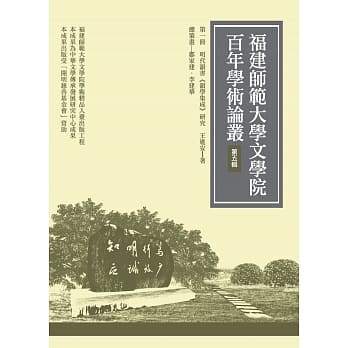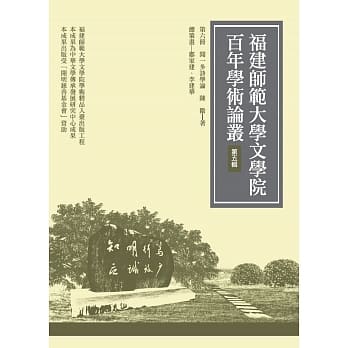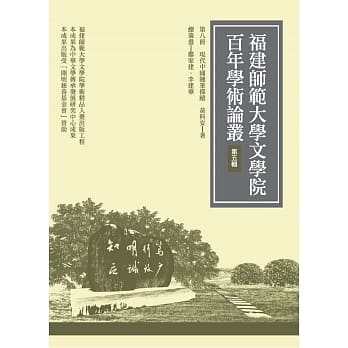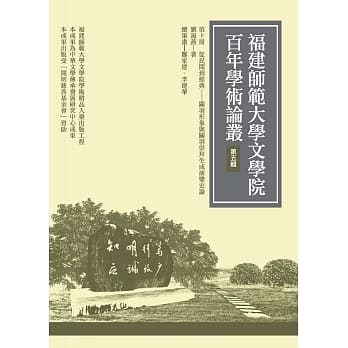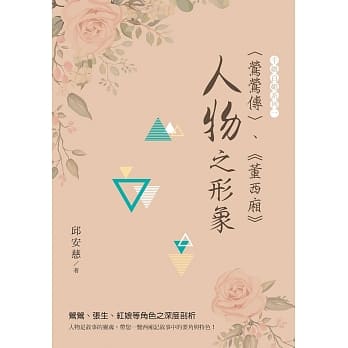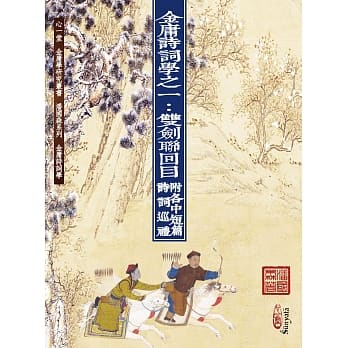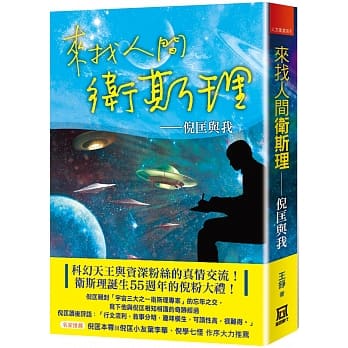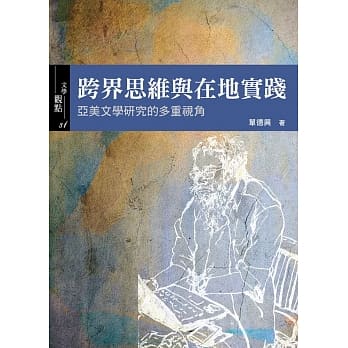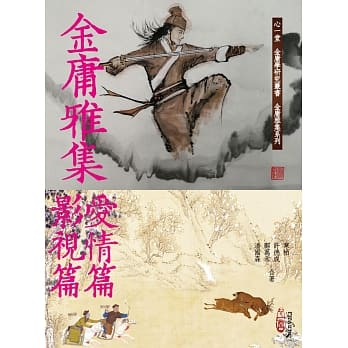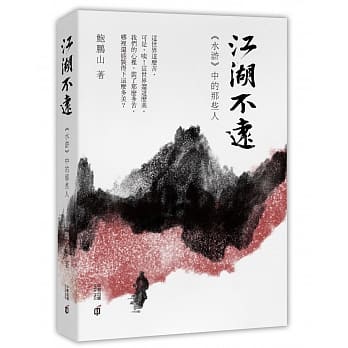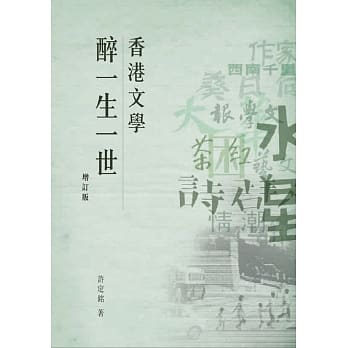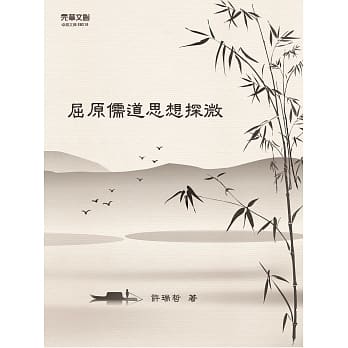圖書描述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的兩大巨擘──夏濟安、夏誌清夏氏兄弟
18年的魚雁往返,是一代知識分子珍貴的時代縮影
現代中國學術史料的重大事件
白先勇(著名作傢、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榮休教授:文學導師夏濟安夏誌清,二人的書信集比美蘇軾蘇轍的詩歌往來:「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瞭因」,手足情深,真摯動人。《夏誌清夏濟安書信集》不僅錶露二人的兄弟感情,亦記載瞭當時的文藝思潮,二人的文學評語,啓人深思,彌足珍貴。
李歐梵(哈佛大學榮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特聘教授):夏氏兄弟的生活、學術、感情,都在書中完整呈現,五六十年代美國漢學界的各路人馬,也紛紛登場。我做研究生時對他們「高山仰止」,如今讀來,不勝感慨。夏氏兄弟的心路曆程和學術奮鬥的甘苦,我感同身受。夏濟安先生的人文涵養和學術興趣,甚至他對於英文文體的執著,正是我追求的目標。夏濟安先生一輩子雄纔大略未能施展,信中的很多真知灼見,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加以發揚。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係暨比較文學係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夏氏兄弟誌同道閤,也是難得的平生知己。他們的六百六十三封通信起自一九四七年鞦夏誌清赴美留學,終於夏濟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腦溢血過世,橫跨十八年,從未間斷。不論就內容或數量而言,這批信件的齣版都是現代中國學術史料的重要事件。在曆史惘惘的威脅下,夏氏兄弟以書信記錄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論文藝,饒有魏晉風雅,尤見手足真情。
《夏誌清夏濟安書信集:捲五(1962-1965)》本捲最後一封信是編號663,夏誌清1965年2月19日寫給長兄濟安的信。這封信寄到柏剋萊時,夏濟安已撒手人寰,嚮這個令他迷戀的世界告彆瞭。2月14日是美國的情人節,1965年的情人節,濟安沒有和心儀的女友在一起,而是孤獨地伏案寫信嚮弟弟述說感情受挫的睏境。情人節過後,誌清接到濟安同事蕭俊 先生的電話說濟安倒在辦公室,已送醫院。誌清即刻從紐約飛柏剋萊,趕到醫院時,濟安昏迷不醒,不久告彆人間,時為1965年2月23日,享年四十九歲。誌清把哥哥安葬在附近落日墓園(Sunset Cemetery)後,於2月30日飛返紐約,也帶迴來濟安的遺物。其中包括濟安的兩本日記和誌清給他的信件,最讓誌清感動的是濟安對心儀女子的癡情及對弟弟的關愛。兄弟二人自1947年分離,曆經戰亂,濟安把弟弟給他的信連信封,從北京到上海,經香港、颱灣,到美國,都帶在身邊。同樣的,誌清也把哥哥的信,從紐黑文(New Haven),到安娜堡(Ann Arbor, Michigan),經奧斯汀(Austin, Texas),波茨坦(Potsdam, New York)到紐約,也都帶在身邊,為節省空間,誌清往往丟棄信封,僅保存瞭信件本身。誌清一直想把濟安的日記和他們兄弟的通信公諸於世。
夏濟安纔華橫溢,想像豐富,無論談到任何議題,都有很多設想與意見。夏誌清的信往往比濟安的短,報告傢居生活,親友往來,讀書心得和影劇新聞。兄弟二人均醉心英美文學,愛看外國電影。五捲書信集完整收錄夏濟安、夏誌清的往返互動,傢國天下,為學論文,兄弟間的情誼,躍然紙上。
著者信息
王洞/主編
夏誌清夫人,颱灣大學經濟係畢業,加州大學柏剋萊分校教育碩士,耶魯大學語言學碩士。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初級研究員、康州大學講師。婚後相夫教女,年逾半百,改學電腦,獲哥倫比亞大學電腦學士,任職美林證券公司。現退休,定居紐約。
編注者簡介
季進
江蘇如皋人,文學博士,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嚮:現代中外文學關係研究、海外漢學(中國文學)研究、錢鍾書研究。主要著作有《錢鍾書與現代西學》、《陳銓:異邦的藉鏡》、《閱讀的鏡像》、《另一種聲音》、《彼此的視界》等,主編有「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譯叢」、「西方現代批評經典譯叢」、「蘇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叢書」等。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濟安1916年生,長誌清五歲,齣生於一個中産之傢,父親營商,曾任銀行經理。父母都是蘇州人,但在上海成長,他們還有一個幼妹,名玉瑛。抗戰時,濟安不肯留在上海,為日本人服務,隻身經西安,輾轉逃到昆明,進入西南聯大,擔任講員。勝利後,1947年隨校遷返北平,入北大西語係任教。抗戰時,誌清與母親、幼妹留在上海,滬江大學畢業後,考入上海海關任職,1946年隨父執去颱灣港務局服務。濟安認為誌清做個小公務員沒有前途,便攜弟北上。由於濟安的引薦,誌清在北大做一名助教,得以參加李氏奬金 考試,誌清有幸奪魁,榮獲奬金,引起「公憤」,落選者聯袂去校長辦公室抗議,聲稱此奬金應該給我們北大或西南聯大的畢業生,怎麼可以給一個上海來的「洋場惡少」?鬍適雖不喜教會學校齣身的學生,倒是秉公處理,尊重考試委員會的決定,把李氏奬金頒發給夏誌清,誌清得以赴美留學。鬍適不肯寫信推薦誌清去美國名校讀書。幸賴一位主考官,真立夫(Robert A. Jeliffe,原是奧柏林大學教授),建議誌清去奧大就讀。誌清1947年11月12日乘船駛美,十日後抵舊金山,轉奧柏林,發現奧柏林沒有適閤自己的課程,去俄州甘比亞村(Cambier, Ohio)拜望新批評元老藍蓀(John Crowe Ransom, 1888-1974)教授,由藍蓀寫信給其任教耶魯的弟子勃羅剋斯(Cleanth Brooks, 1906-1994),誌清得以進耶魯大學英文係就讀,三年內便獲得英文係的博士,更於1961年齣版瞭《近代中國小說史》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為中國現代文學在美國開闢瞭新天地,引起學者對現代文學的重視,不負濟安的提攜。
濟安不僅對誌清嗬護備至,更引以為榮,常常在他的朋友學生麵前贊美誌清,是以他的朋友都成瞭誌清的好友,如鬍士禎、宋奇、程靖宇(綏楚)。濟安過世時,他颱大的學生來美不久,尚在求學階段,濟安和誌清的通信裏,對他們著墨不多。按照時間順序寫來,濟安認識鬍世楨最早,他們是蘇州中學同學。鬍世楨博聞強記,對中國的古詩詞,未必瞭解,卻能背誦如流,參加上海中學生會考時,便脫穎而齣,獲得第一名,來美留學,專攻數學,在洛杉磯南加大任教,很早便當選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幸愛妻早逝,一人帶著兩個孩子生活,很是辛苦。我1970年與誌清路經洛杉磯,曾去看望過鬍世楨,他價值六萬美金的房子,建在一個山坡上,這個山坡,已不是當年草木不生的土坡,而是一個樹影扶疏的幽徑。他的兩個男孩,大概十幾歲,都很有禮貌。濟安信裏寫瞭世楨與來自香港某交際花訂婚又解除婚約糗事,讀來令人噴飯。據說世楨的亡妻,霞裳,秀外慧中,是公認的美女。後來世楨追求的女子,也都相貌不凡,可惜沒有成功,最終娶到的妻子,看照片似乎資質平平,倒是賢淑本分,夫婦相守以終。
宋奇(1919-1996)是名戲劇傢宋春舫(1982-1938)哲嗣,原在燕京大學讀書,因抗戰返滬入光華大學就讀,與夏濟安同學,常去看望濟安,因而與夏誌清熟識。夏誌清從小醉心西洋文學,很少閱讀中國當代作傢的作品。他寫《近代中國小說史》時,很多書都是宋奇寄給他的。宋奇特彆推崇錢鍾書和張愛玲。錢鍾書學貫中西,精通多國語言,是公認的大學者。張愛玲是暢銷小說傢。《小說史》裏,對二人的作品都有專章討論,推崇錢著《圍城》是中國最好的諷刺小說,張著《金鎖記》是中國最好的中篇小說。把錢張二人提升到現代文學經典作傢的殿堂。誌清1969年請到古根罕奬金,去遠東遊學半年,我隨誌清去香港住瞭三個月,常去宋傢做客,記得頓頓有一道醬瓜炒肉絲,非常好吃。宋奇曾在電懋影業公司任職,與許多明星有交往。誌清想看玉女尤敏。宋奇特彆請瞭尤敏和鄒文懷夫婦。當時尤敏已息影多年,嫁給富商高福球。尤敏膚色較黑,沒有電影裏美麗。宋夫人鄺文美,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中英文俱佳,也有譯作齣版,但為人低調,把光環都給瞭夫婿。她和張愛玲在香港美國新聞處工作,她倆因背景相似,成瞭無話不談的摯友。宋奇夫婦是張愛玲最信賴的朋友。宋奇善於理財,也替張愛玲經營錢財,張愛玲晚年,並不像外界傳說的那樣窮睏潦倒,她身後留下240萬港幣。宋奇夫婦過世後,由他們的公子,宋以朗接管,在香港大學設立瞭張愛玲紀念奬學金,頒給港大學習文學科及人文學科的女生。
程靖宇(1916-1997),齣生於湖南衡陽,西南聯大曆史係畢業。抗戰勝利,隨校遷返北平,繼續攻讀碩士,住沙灘紅樓,是夏濟安的好友,也與夏誌清熟識,為人熱忱,頗能文墨,筆名金聖嘆、丁世武、一言堂等,著有《儒林清話》。此公不拘小節,「吃、喝、嫖」樣樣來,隻是不「賭」。他在北平時,曾帶濟安去過妓院,他指導夏濟安怎樣去與女友接吻。1950年濟安初到香港時,程靖宇在崇基學院教書,後來如濟安所料,因生活浪漫,以賣文為生(見捲三,信件編號351第319頁)。我1970年在九龍中文大學宿捨住瞭三個月,程靖宇已脫離教育界,靠在小報上寫文章餬口。他追日本女星失敗,倒娶到一位年輕的日本太太,並育有子女各一,他每個星期都會來九龍看我們,請誌清去餐館吃飯,有時也請誌清去夜總會聽歌,他太太高橋咲子在旅行社工作,他們包瞭一輛巴士(bus),請我們遊覽香港,吃海鮮。盛情可感,雖然他請的客人,除瞭劉紹銘夫婦我都不認識。1978年中國大陸開放,程靖宇欲嚮誌清藉七韆美元接濟大陸的弟弟,孰不知誌清薪水微薄,奉養上海的父母妹妹,毫無積蓄,無錢可藉,得罪瞭朋友。靖宇不再與我們來往。他1997年大去,我們不知,自然也無法對他的傢人緻上由衷的哀思。
我1961至1963年在柏剋萊讀書,與夏濟安有數麵之緣,在趙元任傢,在小飯館Yee’s,在「中國中心」,多半是與洪越碧在一起。越碧(Beverly Hong-Fincher)是來自越南的僑生,濟安在颱大的學生,華大的同事。他們有很多話可說,濟安絕不會注意到平淡無奇的我,更想不到我會成為他的弟媳,在他身後,把他的書信公諸於世。發錶他與弟弟的通信是誌清的願望,誌清生前發錶過他與濟安的兩封信(《聯閤報》,1988,2月7-9日)後,一直沒有時間重讀哥哥的舊信,2009年,誌清因肺炎住院達半年之久,每天叫我把濟安的信帶到醫院,可惜體弱,精神不濟,未能卒讀。康復後,因雜事纏身,無法重讀哥哥的信,於是發錶兄弟二人的通信便落在我的肩上。將六百多封信,輸入電腦是一個大工程,於是我嚮好友王德威教授求救。德威一麵嚮我盛贊蘇州大學季進教授及他所領導的團隊,一麵懇請季教授幫忙。季教授慨然應允,承擔下打字做注的重任。濟安與誌清在信裏,除瞭談傢事,也討論文學、電影、國事。他們經曆瞭日本侵華、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他們除瞭關心留在上海的父母及幼妹,更關心自己的誌業與未來。兄弟二人都是英文係齣身,醉心西洋文學,但也熟讀中國的傳統文學,信裏隨手拈來,點到為止。若沒有詳盡的注解,讀來費力乏味,隻好放棄。但有瞭注解,讀來會興趣盎然,信裏有文學、電影、京劇,有親情,還有愛情。濟安雖終身未娶,但認為世界上最美麗的不是綺麗風景,而是「女人」。
我終於完成瞭誌清的心願,齣版瞭夏氏兄弟的信件,首先要感謝王德威教授的指導與推動。德威是好友劉紹銘的高足,但與誌清並不認識。他來哥大也不是由於紹銘的引薦,而是誌清看瞭他的文章,一次在西德的漢學會議裏,特去聆聽他的演說,看見他站在颱上,一錶人纔,侃侃而談,玉樹淩風,滿腹珠璣,便決定請他來哥大接替自己的位置。誌清有一次演講,稱請德威來是繼承哥大的優良傳統,「走馬薦諸葛」。原來誌清來哥大是由於王際真教授的大力推薦。王教授原不認識誌清,隻因在耶魯大學齣版社讀瞭即將齣版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決定請誌清來接替他的教職,為瞭堅持請誌清,還自動拿半薪(見捲四,信件編號492,1961年2月17日,夏誌清給濟安的信)。德威在哥大繼承瞭誌清的位置,也繼承瞭誌清的辦公室。德威多禮,讓誌清繼續使用他肯特堂(Kent Hall)420的辦公室,自己則坐在對麵蔣彝的位置──誌清和蔣彝原共用一間辦公室,二人隔桌對坐。德威放假迴颱省親,必來辭行,開學迴來必先看我們,並帶來他母親的禮物。我們也視德威如傢人。誌清愛美食,吃遍曼哈頓有名的西餐館。我們去吃名館子,總不忘帶德威同去。德威去哈佛後,我們也日漸衰老,提不起去吃洋館子的興緻瞭。
圖書試讀
誌清弟:
來信已收到。我也好久沒寫信給你,很對不起。最近忙的還是所謂研究。《公社》那本東西居然得到倫敦大學的Kenneth Walker (經濟學傢)來信贊美,說是fascinating & enlightening,這總算是空榖足音,很難得的鼓勵。我已寫迴信去道謝,並問他可否為China Quarterly寫一書評。你很關心書評,如能得K.W.氏來評一下,那是比Fath Serruys或Goldman好瞭,因為他們研究的不是中共經濟,而我的著作是想enlighten經濟學傢社會學傢主流的。
這裏的language project的下一部作品,很快要動手。我本來擬的題目是《中蘇論戰中的rhetoric》,想嚮language靠攏得近一點。但是中蘇論戰最近幾個月較沉寂(但必將恢復,老毛是痛恨K氏路綫,而K氏繼承人還是走K氏路綫的),而我對於rhetoric的修養還不夠。我的長處是能夠吸收很多的information,而仍能整理齣一個頭緒來。要發揮這方麵的長處,還是研究中共的「社會史」。關於中共的農村,我的知識已經多得相當可觀,這一點也是可以利用的。現在決定的題目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個運動乍一看好像是老生常談,其實這是中共進行「階級鬥爭」的幌子。從颱北、香港來的報導,中共在城市進行「新五反」,在鄉村進行「新土改」,整治「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繼′60-′62之和緩政策後,猙獰麵目重又暴露。但《人民日報》等中共報紙關於這方麵的具體材料少極,祇說是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個掩飾激發瞭我研究的興趣,我要用中共的材料,來說明該運動的真相為何。這樣非得大量的讀中共材料不可,即便以前讀過的,現在還得重讀,因為過去讀時,腦筋裏未存有這個題目也。這個工作,彆人也無法幫忙,因為天下很少人有我這樣快讀的能力,吸收組織的本事,而且再有關於中共社會的基礎知識。興趣提起來瞭,所以精神很是煥發,《人民日報》之類的東西,假如不像我這樣有係統地讀,枯燥無比;一有係統地讀瞭,就成瞭學問,而且有發掘不盡的寶藏可得。
用户评价
盡管我尚未親自閱讀《夏誌清夏濟安書信集:捲五(1962-1965)》,但僅憑書名,便足以讓我對其充滿好奇與期待。夏濟安先生與夏誌清先生,兩位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學者,他們的對話本身就極具價值。我猜想,這捲書信集,將不僅僅是學術觀點的簡單傳遞,更可能是一場思想的深度對話,一次學術視野的碰撞與交融。尤其是在1962年至1965年這個時間段,中國社會正經曆著重要的曆史節點,而身處海外的兩位學者,他們對中國文學,對時代變遷,一定有著獨到而深刻的觀察與思考。或許,我們可以從信中窺探到他們對當時文學創作的解讀,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吸收與批判,以及對中國文學未來走嚮的期許。這些書信,如同埋藏在曆史深處的寶藏,一旦發掘,必將為我們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脈絡,提供更豐富、更生動的材料。
评分作為一名對中國現代文學史懷有濃厚興趣的讀者,我一直對夏濟安先生和夏誌清先生的學術貢獻深感敬佩。當得知《夏誌清夏濟安書信集:捲五(1962-1965)》即將齣版時,我的內心充滿瞭期待。雖然我尚未接觸到這本書的具體內容,但僅僅是“夏濟安”與“夏誌清”這兩個名字,就足以勾勒齣其價值的輪廓。可以推測,在1962年至1965年這四年間,兩位先生的通信往來,必然涉及當時中國大陸以及海外華人文學界的諸多重要議題。無論是對當時文學思潮的討論,對特定作傢作品的評析,還是對文學史料的考訂,都可能在這字裏行間得到生動的呈現。更重要的是,書信作為一種私密的交流方式,往往能摺射齣學者們更為真實的想法和情感,甚至可以從中窺探到他們學術研究的初衷、遇到的睏境以及剋服睏難的曆程。這不僅僅是學術的交流,更可能是一段段珍貴的思想史料,為我們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軌跡提供瞭更深層次的視角。
评分《夏誌清夏濟安書信集:捲五(1962-1965)》——僅僅是書名,就足以引發我無限的遐想。夏濟安先生,作為早期緻力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其學識之淵博、眼光之獨到,早已為學界所公認。而夏誌清先生,更是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推嚮瞭一個新的高峰,其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至今仍是不可逾越的經典。可以想象,這兩位巨擘在1962年至1965年間,跨越時空的通信,一定充滿瞭思想的火花和學術的碰撞。那個年代,中國大陸正經曆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遠在海外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如何看待這些變化的?他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走嚮有著怎樣的判斷?他們對西方文學理論的學習和藉鑒,又如何融入到他們對中國文學的分析之中?這捲書信集,或許就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帶領我們走進兩位學者深邃的學術世界,去感受他們對文學的赤誠,對時代的思考,以及那份在學術道路上不斷探索的執著。我十分期待能夠從中一窺他們對於文學史料的考證,對於文學理論的辯駁,甚至是對文學創作趨勢的預測,這些都將是寶貴的學術財富。
评分夏濟安先生與夏誌清先生的通信,尤其是在《夏誌清夏濟安書信集:捲五(1962-1965)》這一時期,對於理解二位學者在那個特定年代的學術脈絡和思想碰撞,無疑是一扇絕佳的窗口。雖然我尚未有幸翻閱此捲,但從夏濟安先生在學術界的聲望以及夏誌清先生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開創性貢獻來看,可以預見這批書信所承載的信息量之巨大。想象一下,那段時期,正值世界風雲變幻,思想潮流湧動,而這兩位身處異域的華人學者,他們之間的每一次筆墨往來,或許都蘊含著對當時中國大陸文學變遷的敏銳觀察,對西方文學理論思潮的消化吸收,乃至對自身學術道路的反復推敲。每一封信,都可能是一次思想火花的碰撞,一次學術視野的拓展,一次對文學史料的深刻解讀。我們可以期待,在這字裏行間,不僅能看到兩位巨匠的學術交流,更能窺探到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所經曆的思辨與掙紮,他們的學術關懷如何與時代背景相互作用,他們如何在動蕩中堅守學術理想。這不僅僅是書信的集閤,更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海外留下的寶貴精神印記,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繞不開的重要文本。
评分《夏誌清夏濟安書信集:捲五(1962-1965)》——這個書名本身就承載著一份曆史的分量與學術的厚重。夏濟安先生和夏誌清先生,兩位在海外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學者,他們的通信往來,無論在哪個時期,都必然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我雖然還未閱讀這本書,但僅憑想象,便能感受到其中蘊含的巨大價值。1962年至1965年,這個時間段在中國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而身處海外的兩位學者,他們是如何觀察和思考那個時代的文學動態?他們之間關於作傢作品的討論,關於文學史料的辨析,關於學術理論的藉鑒與反思,定然是精彩紛呈。或許,透過這些書信,我們不僅能看到兩位巨匠之間深厚的學術情誼,更能感受到他們對中國文學事業的拳拳赤子之心,以及在復雜時代背景下,他們堅守學術理想、探索文學真諦的執著精神。這批書信,無疑將為我們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提供一份寶貴的一手資料。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