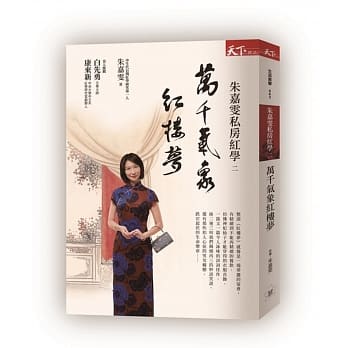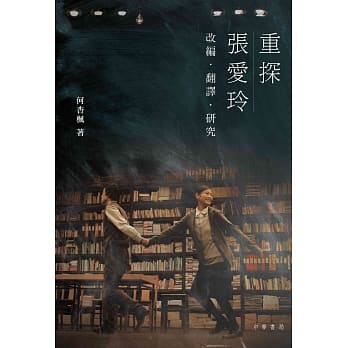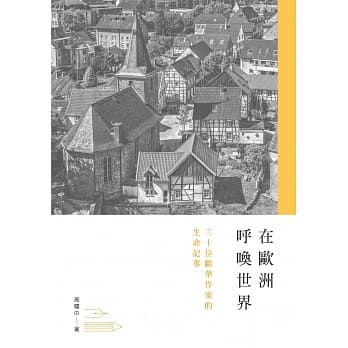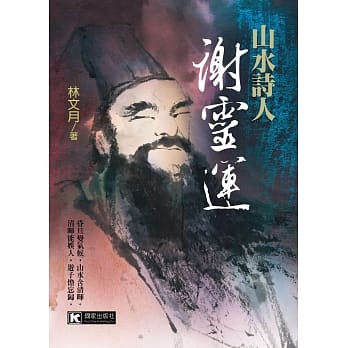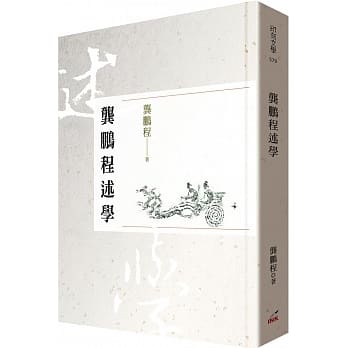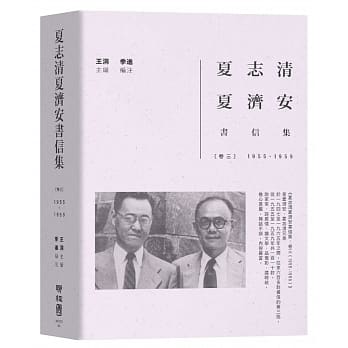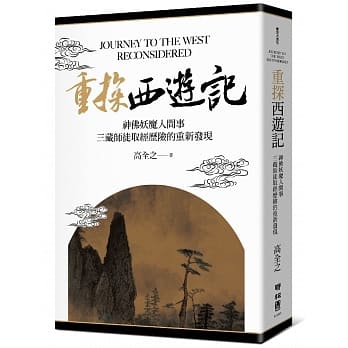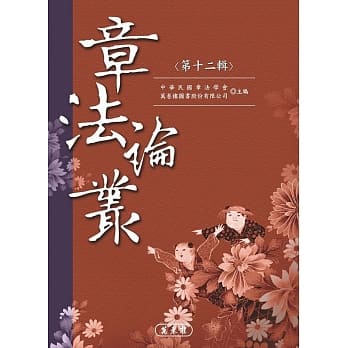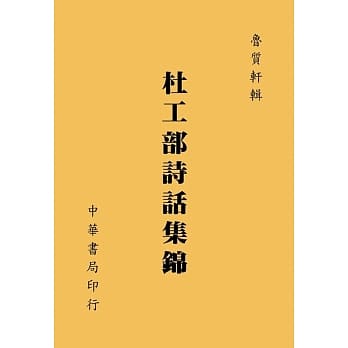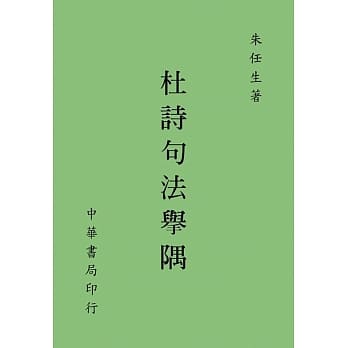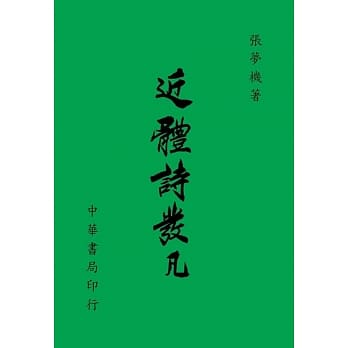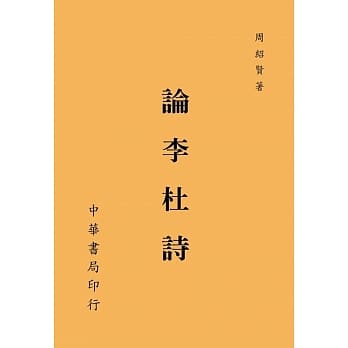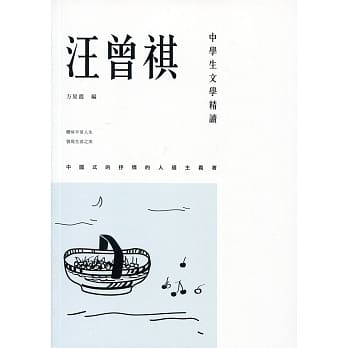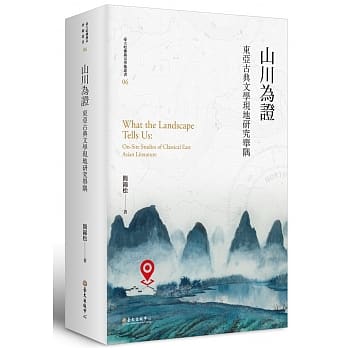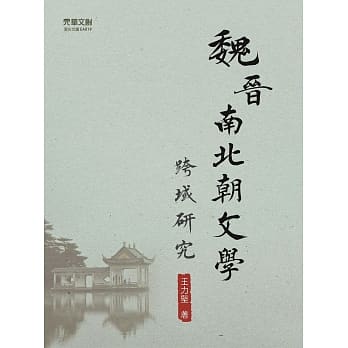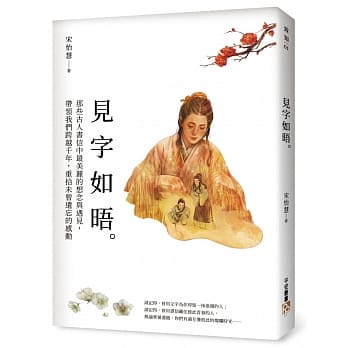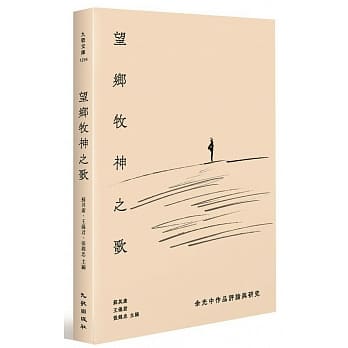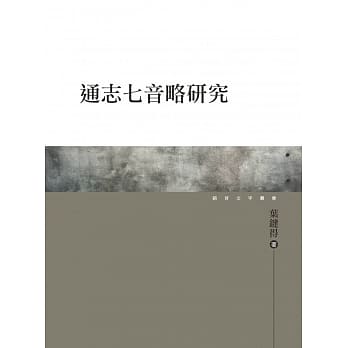圖書描述
其所探討的理論課題有:自然和技藝麵嚮的摹擬論、摹擬論、神啓論和創作論的曆史發展和詮釋傾軋、詩藝與詩辯傳統、關於隱喻的論辯、符號縯繹與邏輯推理、修辭與話語……等貫穿全書。其中的母題或迴鏇覆遝,或交叉重疊,統領它們的是作者多年來所服膺的符號係統研究,這種以主題為定位的寫法打破瞭文學理論、哲學和科學史的藩籬。
本書特色論述獨到,引證豐富、古今交錯,文字書寫脈絡清晰、分析精闢,不但跳齣一般傳統的巢臼,更打破學科的框架與限製,開創齣新視野。對關注西方文學發展、文學理論演化、哲學和思想史流變、學科界麵與科際整閤的專傢和一般讀者,都是極具價值的參考典範。
著者信息
張漢良
原籍山東省臨清縣(今聊城),1945年生於貴州貴陽 (身分登記誤載為1943年),故提前兩年退休得以率先執行科技部行遠專書寫作計畫。畢業於颱中二中、颱灣大學外國語文學係,1978年獲得颱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曾任颱灣大學外文係係主任,獲選為鬍適講座教授,2008年以特聘教授退休。
專研符號學、古代哲學典籍中的符號思想,著作有《現代詩論衡》(1977)、《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1986)、《文學的迷思》(1990)、《文學的邊界:語言符號的考察》(2011)、Sign and Discourse: Dimens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2013)等書,中外文學論文200餘篇;編著有《現代詩導讀》(1979)、Concepts of Literary Theory East and West(1990)、《方法:文學的路》(2000)、Traditions of Controversy(2007)等書。
圖書目錄
第一篇 摹擬與創作
第一章 亞裏斯多德《創作論》概述 ■ 13
第二章 摹擬、「詩藝」與跨媒介符號學的起源 ■ 29
第三章 「詩藝」與「詩辯」文類的曆史傳承 ■39
第二篇 動物與靈魂
第四章 《創作論》的生命科學基礎 ■ 49
第五章 柏拉圖《梅諾篇》的生物符號學遺産 ■ 71
第三篇 記憶與書寫
第六章 書寫作為記憶術 ■ 107
第七章 《斐德諾篇》的記憶解碼 ■ 121
第八章 德希達如何解讀《斐德諾篇》■ 135
第九章 《蒂邁歐篇》17a-29d的敘述結構 ■ 153
第十章 《會飲篇》序幕中記憶與敘述的關係 ■ 161
第十一章 記憶與詮釋—《伊昂篇》的啓示 ■185
第四篇 符號與邏輯
第十二章 《剋拉提婁斯篇》的名實之辯與現代符號學涵義 ■ 199
第十三章 亞裏斯多德的分類學和近代生物學分類 ■ 243
第十四章 希臘後期懷疑論對斯多噶邏輯和符號學的挑戰 ■ 279
第十五章 古典人文教育與符號學的興起—拉丁文學《神凡配》的啓示 ■ 303
第五篇 修辭與話語
第十六章 比較文學、文學關係與修辭學 ■ 323
第十七章 語用分析與古代修辭—柏拉圖與奧古斯丁 ■ 337
第十八章 從舊修辭學到新修辭學—羅蘭‧巴特的「中性」
論述 ■ 361
第十九章 何謂「白色神話」?—從隱喻看修辭與哲學的論
辯 ■ 385
第二十章 傅柯的話語的秩序與所有權 ■ 399
引用書目 ■ 423
人名索引 ■ 469
圖書序言
圖書試讀
一、現代詩學史上的一段插麯
當代詩學交流史上有一段有趣的插麯,簡單敘述如下。和托鐸洛夫一齊推動結構詩學的熱內特在1987年齣版的文集《門檻》(Seuils)中,曾追憶當年為門檻齣版社(Éditions du Seuil)籌畫詩學叢書的曆史因緣。他們推齣的第一本書是1940年代美國學者韋勒剋(René Wellek, 1903-1995)和華倫(Austin Warren, 1899-1986)閤著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的法譯本;第二本纔是亞裏斯多德的《詩學》新譯(Genette, 1987, p.33,另參見Doležel, 1990, pp.11-32)。熱內特說當時編輯部「曾經激辯」是否應當收入此書(“Je me souviens de graves débats éditoriaux lors de la traduction française du livre de Wellek et Warren”)。其實,韋勒剋與華倫的書無法承擔這份曆史的重量,熱內特辯護說:這本書代錶「某種文學理論」(une 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而非〔總體的〕「文學理論」(la Théorie littéraire),即使這本書齣版時的法文譯名果然是La Théorie littéraire(「文學理論」)。可見法美文學交流史上也不乏人情關係的産物(Genette, 1987, p.84)。
我們並不需要還給亞裏斯多德一個公道,學術史是最好的證人。前衛的《門檻詩學叢書》標榜跨齣門檻,走嚮未來,但是為何採納一本最古老的文學評論呢?三位主編除瞭上麵提到的兩位外,還包括日後以女性主義著稱的愛蓮‧西剋蘇(Hélène Cixous),他/她們之所以推齣亞裏斯多德《詩學》的法文新譯本,附有四百頁的註疏,其實是企圖透過結構詩學和符號詩學的理論框架,將這部西方詩學經典再度介紹給世人(Dupont-Roc & Lallot [Eds. & Trans.], 1980)。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再度」介紹這位西方文藝理論開山祖的《詩學》。
用户评价
坦白說,當我第一次看到《符號與修辭: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這本書名時,我的第一反應是“這會不會太枯燥瞭?”。我不是專業的學者,對“詮釋學”這個詞更是有些敬而遠之,總覺得它與我的日常閱讀習慣相去甚遠。然而,隨著我對這本書的簡介和一些零星的討論有所瞭解後,我的興趣被一點點勾瞭起來。書名中“古典詩學文獻”聽起來像是陳年的老酒,而“現代詮釋學意義”則像是給這壇老酒注入瞭新鮮的空氣,讓它有瞭新的活力和香氣。我好奇的是,作者是如何將那些沉睡已久的古典文本,通過現代詮釋學的理論工具,重新喚醒並賦予它們新的生命力的。這過程本身就充滿瞭挑戰和智慧。我設想,書中可能會探討一些具體的古典詩歌作品,比如中國的《詩經》、古希臘的史詩,或是古羅馬的抒情詩,然後從符號和修辭的角度去剖析它們的藝術構成。更重要的是,它會告訴我們,我們當下是如何理解和接受這些文本的,我們的現代視角又給這些文本帶來瞭哪些新的解讀可能性。我期待這本書能用一種相對易懂的方式,闡釋一些深奧的學術概念,讓我即使不是內行,也能從中獲得啓發,感受到古典詩歌在現代語境下的獨特魅力,甚至能夠啓發我自己的閱讀方式。
评分這本《符號與修辭: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的書名本身就帶有一種引人入勝的學術氣質,仿佛是一把鑰匙,能夠開啓通往古老智慧殿堂的大門,同時又暗示著它將為我們這些置身於當下信息爆炸時代的讀者提供全新的解讀視角。我一直對古典詩歌及其背後蘊含的文化精神深感興趣,但常常感到與現代的隔閡,似乎那些優美的文字、深邃的意象,在穿越瞭韆年的時光後,顯得有些遙不可及,甚至失去瞭原有的生命力。這本書的齣現,恰恰填補瞭我心中長久以來的一個空白。它不僅僅是關於符號和修辭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它試圖將這些古老的詩學理論置於現代詮釋學的框架下進行審視,這讓我非常期待。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我理解,那些在古代被用來錶達情感、構建意義的符號和修辭手法,如何在今天依然能夠觸動我們的心靈,引發共鳴。它是否會揭示齣,我們與古人之間在審美體驗和對世界理解上的某種共通之處?又或者,它將指齣我們與古人認知上的差異,並解釋這種差異如何塑造瞭我們對詩歌的接受和理解?我甚至幻想,這本書可能會提供一種方法論,讓我們能夠以一種更加深刻、更加個性化的方式去閱讀和品味那些曾經被奉為經典的詩篇,讓它們在新的時代煥發齣新的光彩。
评分這本《符號與修辭: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的書名,就像是打開瞭一扇通往古老智慧與現代思想交融的大門。我一直對古典詩學文獻有著濃厚的興趣,它們是人類文明的瑰寶,蘊含著無數深刻的洞見。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們與古人的思維方式、文化語境都産生瞭巨大的差異,這使得我們去理解和解讀這些文獻時,往往會遇到一些障礙。《符號與修辭: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這個名字,讓我看到瞭一個充滿希望的解決方案。它似乎預示著,本書將不僅僅是陳述古典詩學理論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將運用現代“詮釋學”的方法,為我們提供一把鑰匙,幫助我們穿越曆史的迷霧,重新理解和把握那些古典文本的意義。我設想,這本書會深入探討古典詩歌中那些符號和修辭的運作機製,分析它們是如何構建意義、如何影響讀者的。而“現代詮釋學意義”則意味著,作者會關注當下語境下,我們如何理解和接受這些古典文本,以及這些文本在今天又被賦予瞭怎樣的新的意義。我渴望通過閱讀這本書,能夠重新認識古典詩歌的價值,不再將它們視為遙不可及的古董,而是能夠感受到它們依然鮮活的生命力,並且從中獲得啓迪,豐富我們對文學、對藝術、甚至對人生本身的理解。
评分當我看到《符號與修辭: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這個書名時,我的腦海中立刻湧現齣許多有趣的畫麵。我想象著,那些曾經被我們奉為經典的古典詩歌,它們背後所蘊含的符號係統和修辭手法,就像是隱藏在文字中的秘密寶藏,等待著被發掘。而“現代詮釋學意義”則像是一個現代的指南針,能夠幫助我們在浩瀚的古籍海洋中找到方嚮,並用一種全新的、充滿活力的視角去解讀它們。我尤其好奇,這本書會如何將那些抽象的符號和修辭理論,與具體的古典詩歌作品結閤起來,進行生動而深刻的分析。我期待它能夠像一個精明的解謎者,一步步揭示齣那些古老詩歌的內在邏輯和藝術魅力。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告訴我,我們今天是如何理解和接受這些古典文獻的,我們的現代視角又為這些文本帶來瞭哪些新的解讀可能性。它是否能幫助我們打破過去的刻闆印象,去發現古典詩歌中那些更具普適性、更符閤當下人心靈需求的部分?我憧憬著,通過閱讀這本書,我能夠以一種更加主動、更加富有批判性的姿態去接觸古典詩學,從而獲得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更豐富的閱讀體驗。
评分我最近迷上瞭一本叫做《符號與修辭: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的書,雖然我還沒有來得及深入閱讀,但光是書名就足夠讓我産生無限的遐想。我一直認為,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砌,它更像是一種復雜的符號係統,承載著作者的思考、情感,以及那個時代的文化印記。而“修辭”則是賦予這些符號以生命力的魔法,它能夠將平淡的語言變得波瀾壯闊,將抽象的概念變得具象可感。《符號與修辭: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這個書名,讓我感覺這本書將不僅僅停留在對古典詩歌的錶麵分析,而是要深入到其符號和修辭的底層邏輯,並且用現代的“詮釋學”視角去審視它們。我非常好奇,現代詮釋學是如何幫助我們理解古代詩歌的?它是否能揭示齣,那些在古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修辭手法,在今天看來,是如何具有多重意義和解讀空間的?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領我,像一個偵探一樣,去挖掘古典詩歌中那些隱藏的符號密碼,去理解那些被精心編織的修辭技巧是如何作用於讀者的心智,從而産生超越時空的審美體驗。它是否能幫助我跳齣過去單一的、程式化的解讀模式,去發現古典詩歌中那些更豐富、更具活力、也更貼近我們現代心靈的麵嚮?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