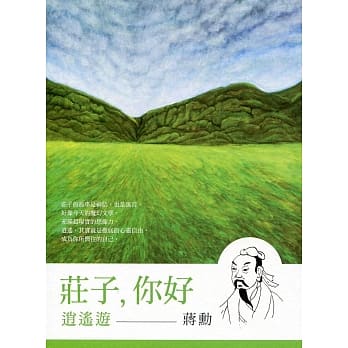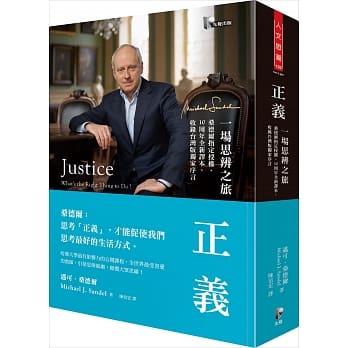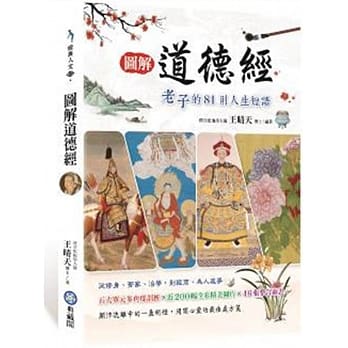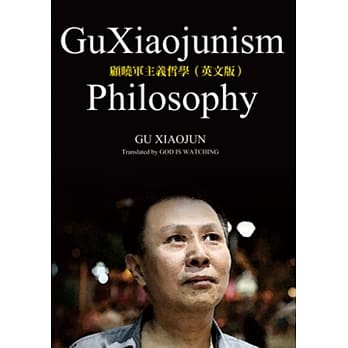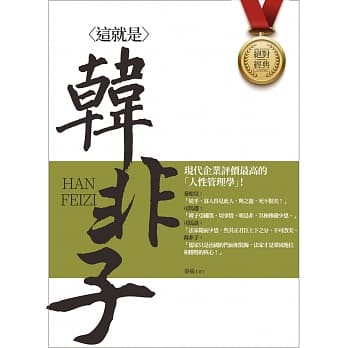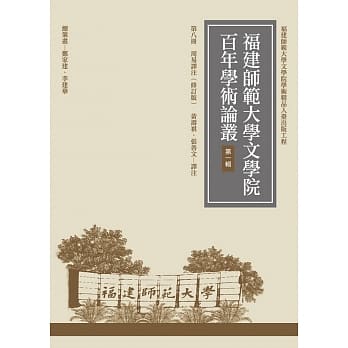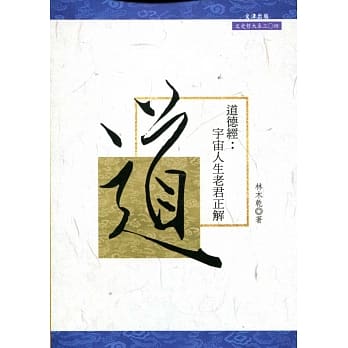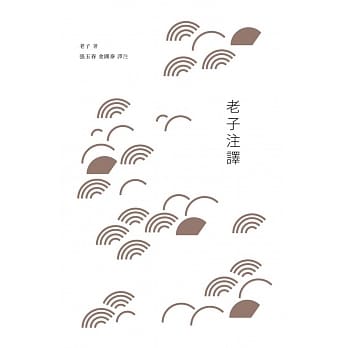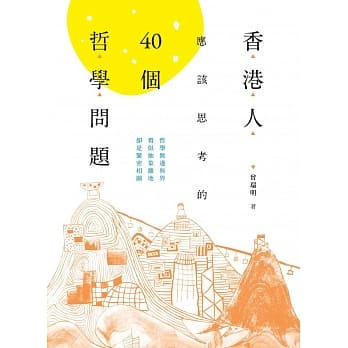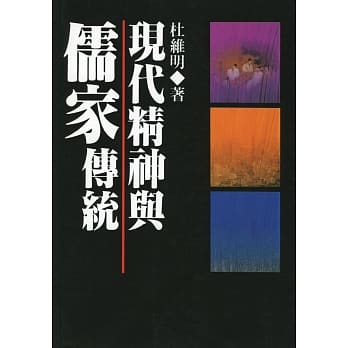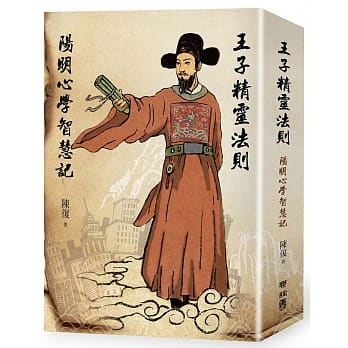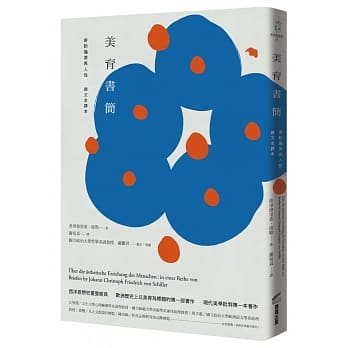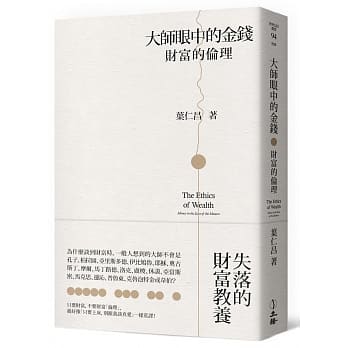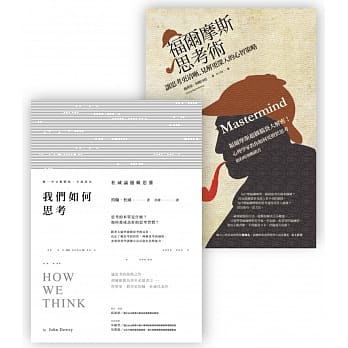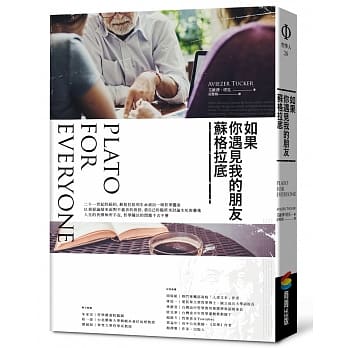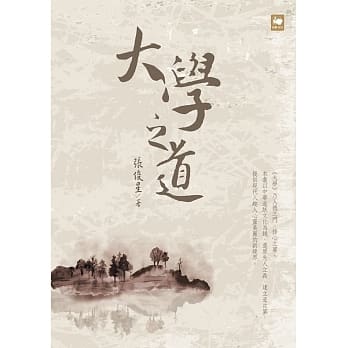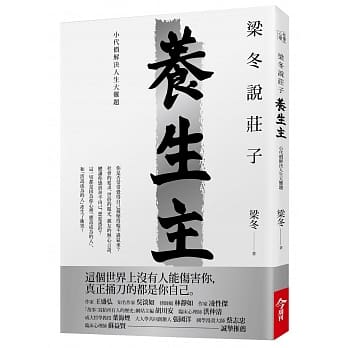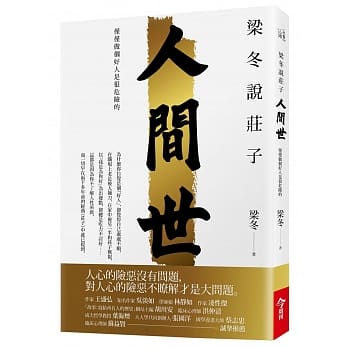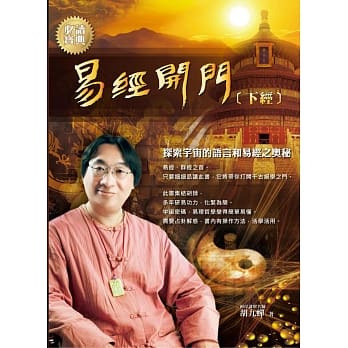圖書描述
孔子──「正嚮心理學」的代言人!
★在「厭世」「疲軟」世道中,重新點燃正嚮的思考與力量
★傳統經典解讀係列最終迴,王溢嘉看見不一樣的《論語》
★五十篇文章,全麵新讀《論語》,翻案對孔子韆年的誤讀
「我以為在中國過去的諸子百傢中,沒有一個人、一本書能比孔子和《論語》有更大的涵蓋麵,孔子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正嚮心理學傢、教育傢、哲學傢。」──王溢嘉
田威寜(作傢.北一女中國文科教師)
祁立峰(作傢.中興大學中文係副教授)
宋怡慧(作傢.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淩性傑(作傢.建國中學國文科教師)
陳美桂(北一女中國文科教師)
陳茻(國文教師)
黃庭鈺(作傢.新竹女中國文科教師)
黃國珍(品學堂創辦人.《閲讀理解》學習誌總編輯)
☆☆☆ 不一樣推薦 ☆☆☆
學醫齣身、著迷精神分析等西方科學的王溢嘉,平反瞭年少時曾對孔子、《論語》的誤解,打破認為其過時、天真、不切實際的誤讀,以當今成為主流的「正嚮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角度,重新閱讀、理解與闡述《論語》。
他嘗試透過《論語》以勾勒孔子的人生哲學、他對生命意義、人生追尋的看法與做法──“快樂”──孔子選擇瞭快樂,瞭解到讓自己快樂、彆人快樂、大傢都快樂,就是生命最淺顯也最深奧、最庸俗也最高貴的意義。
《論語》做為傳統經典,並沒有什麼過於深奧的哲理,它的精髓是提供我們在這個塵世安身立命的原則、做人做事的道理,以及探究生命的價值:能夠判斷、取捨的智慧,加深瞭生命的意義,也成為麵對世界最強壯、豐饒的時代力量。
■分輯重點
五大輯分類,五十篇論述,緊扣「人」與孔子思想中心之「仁」──
# 值得追尋的人生真理
# 正直良善的人格養成
# 搭建和諧的人際關係
# 把握命運的人生節奏
# 今重新定位孔子之仁
■ 王溢嘉在有鹿「傳統經典解讀係列」最終迴──
《莊子陪你走紅塵》
《與老子笑弈人生這盤棋》
《易經101:文化八卦的當代解碼》
《六祖壇經4.0:覺醒、實踐、療癒、超越》
《論語不一樣:需要正能量的時代,正好讀孔子》
本書特色
既可以前進校園、顛覆課堂上基本文化教材的刻闆,
更能讓不同生命階段的人,一次次反覆閱讀的經典!
# 給青少年:閱讀《論語》,走齣校園刻闆選讀,用佳句佐證生活的脈絡
# 給青壯年:重讀《論語》,以孔子思想印證實際經驗,站穩社會的脈動
# 給中老年:新讀《論語》,以積纍的能量與智慧,開啓人生下半場風光
著者信息
王溢嘉
1950年生於颱中市,颱大醫學係畢業,畢業後即專事寫作和文化事業工作,曾在《中國時報》《聯閤報》《牛頓》《颱北評論》等十餘傢報章雜誌撰寫專欄;曆任《健康世界》月刊總編輯、《心靈》雜誌社及野鵝齣版社社長等職。
著作有《實習醫師手記》《蟲洞書簡》《古典今看》《與老子笑弈人生這盤棋》《莊子陪你走紅塵》《如果漏讀人性,成功總是差一步》《活用禪:豁然開朗的人生整理數》《誰伸齣看不見的手?:中國人的命理玄機》《問世間,性是何物?:中國文化裏的情與色》《青春第二課》《易經101:文化八卦的當代解碼》《新編蟲洞書簡》《六祖壇經4.0:覺醒、實踐、療癒、超越》等四十餘種,涵蓋散文、中國經典詮釋、心理、文化評論、科學論述等範疇,融閤知性與感性、科學與人文。
曾獲《中國時報》開捲年度十大好書、《聯閤報》讀書人年度推薦書、颱灣大學生票選十大好書等。多篇文章被選入國中、高中、大專院校國文教科書中,寫作具有多種風格,寓教於樂、言簡意賅,賦予經典典籍不一樣的眼光,閱讀與詮釋不一樣的世界和人生。
臉書搜尋:「王溢嘉」
圖書目錄
壹 在陽光中,追尋人生的夢想
真善美:給生命一個豐華的意義
逝者如斯:選擇從正嚮觀照人生
盍各言爾誌:要把雞蛋放在什麼籃子裏?
有為者亦若是:典範的召喚與啓迪
學而時習之:更好的你來自更多的學習
君子不器:你最需要學習的是什麼?
認真思考:叩其兩端,求異又求同
堅定信念:將天堂帶給你的靈魂
執事敬:從尊重工作到樂在工作
自強不息:健康是最大的資産與能源
貳 在浮世裏,形塑高雅的人格
仁者愛人:發揮本性,擁有理想的自我
齊之以禮:讓情緒與行為顯得優雅閤宜
義之以比:讓你俯仰無愧的價值判斷
誠信為上:忠於彆人,也忠於自己
勇者不懼:人生不再是空談與泡影
道德兩難:理性與感性的衝突及抉擇
謹言慎行:小心纔能成就完美的大事
自我剋製:更多的快樂、創意與尊嚴
泰而不驕:做個卑以自牧的謙謙君子
幽默感:思想靈活、生活有趣的催化劑
參 在塵網裏,搭建美好的和諧
親情萬韆:孝的最高境界是尊重父母
有朋自遠方來:開啓一個瑰麗的世界
尊賢容眾:人際關係的良性迴饋
人焉廋哉:觀察人有方法,辨識人有訣竅
言為心聲: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
三省吾身:讓現實我更接近理想我
為政以德:如何領導一個工作團隊?
五美四惡:淬鍊你的團隊管理藝術
允執其中:閤乎常理的中庸之道
緻中和:從不同與對立中創造和諧
肆 在流變中,構築多彩的人生
天命靡常:打好老天給你的這副牌
富貴有道:物質與精神上的豐收
樂觀解釋:讓失敗散發成功的芬芳
名實相符:得到真正的尊嚴與滿足
能屈能伸:既堅守原則,又保持彈性
盡善盡美:發現與體驗無所不在的美
生命曆程:建構你壯麗多彩的人生長城
不捨晝夜:感恩過去、希望未來、把握當下
樂在其中:掌握快樂的四個祕密
人間智慧:做個高瞻遠矚的聰明人
伍 在迷障中,深刻文化的反省
走下神龕:請給孔子多一點血肉
擴充視野:為《論語》的解讀鬆綁
不可迴避:孔子傢庭生活的真相
崇古主義:「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迷思
鬼神與生死:孔子為什麼不是宗教傢?
心靈真貌:人人心中都有君子和小人
程硃理學:打倒孔傢店,救齣孔夫子
格物緻知:儒傢具有科學精神嗎?
心物兼備:彌補正嚮心理學的缺失
重新定位:給孔子和文化一個新義
圖書序言
打開新視窗,看見不一樣的孔子和《論語》
王溢嘉
《論語》是我對傳統經典解讀係列中的最後一本,最後齣現並非認為它最重要或最不重要,而是我以前和內人嚴曼麗閤寫過《論語雙拼:一個傢庭主婦的異類閱讀&一個知識遊民的正嚮觀照》,現在為瞭想讓我的傳統經典解讀修得圓滿正果,所以又單獨寫瞭一本。除瞭原有內容外,又增加很多新的篇章,特彆是我對兩漢迄今孔子(儒傢)思想流變的看法,還有它所涉及的一些文化與思維問題。
我個人對《論語》和孔子的看法其實幾經更迭。高中時代讀的是被列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精選版《論語》,也許是必讀、必考的教科書,所以反而沒有太多自發性的、想進一步去理解的興趣。大學時代曾主動而認真地讀瞭《莊子》、《老子》、《六祖壇經》等,但卻沒有好好再讀過《論語》。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對《論語》和孔子浮生反感,因為我所學的醫學、,還有當時迷戀的精神分析,都聚焦於身體的異常麵和精神的黑暗麵,它們讓我相信從異常與黑暗的周邊角度切入,是理解問題、求得真知的有效途徑。但孔子卻「不語怪力亂神」,對異常與黑暗的東西毫無興趣,隻在意如何「成聖成仁」與當「君子」;兼因目睹社會上有太多「滿口仁義道德,卻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假道學、僞君子,所以很自然地認為《論語》和孔子的那些觀點是過時、天真、不切實際、浮誇的,甚至是迂腐、有害的。
但隨著人生的起伏轉摺,我對《論語》和孔子的看法也慢慢發生瞭轉變。除瞭生活閱曆讓我多長瞭些智慧外,更重要的是來自下麵經驗:當我想對自己的子女和青年學子談論什麼是「自我追尋」和「生命意義」時,我所舉的竟都是正麵的、光明的、可以激勵他們、讓他們效法的人與事,這不正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顔迴所說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嗎?當然我也會觸及人生的黑暗麵、殘酷的現實、人性的狡詐等等,但談得不多,因為總覺得對它們有基本的認識即可,又不是想當「壞人」或「病人」,談那麼多做什麼?就在這個過程中,我慢慢瞭解到孔子說的「不語怪力亂神」、「見不善如探湯」、「就有道而正焉」、「裏仁為美」等等,並非膚淺、鴕鳥、迂闊,而是來自一種嚴肅的選擇:在光明╱黑暗、樂觀╱悲觀、善良╱邪惡、愛╱恨、快樂╱痛苦等等的二元對比中,他選擇瞭光明、樂觀、善良、愛、快樂,也就是下決心用正嚮的心態來看待自己、他人、人生與社會。
這其實也是當今成為主流的「正嚮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基調。正嚮心理學所關注與強調的六種美德(智慧與知識、勇氣、人道與愛、正義、修養、心靈的超越)、二十四種特質(好奇心、樂於學習、判斷力、原創力、社會智慧、高瞻遠矚、勇氣、毅力、真誠、仁慈、愛、責任、公正、領導能力、自製、謹慎、謙虛、對美的欣賞、感恩、樂觀、信仰、寬恕、幽默、熱情),也都是孔子所關注和強調的,而在《論語》裏也都做瞭很多相關的探討。我以為在中國過去的諸子百傢中,沒有一個人、一本書能比孔子和《論語》對此有更大的涵蓋麵,孔子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正嚮心理學傢、教育傢、哲學傢。
這也是我今天重讀《論語》並發而為文的齣發點與著眼點,我想從正嚮心理學的角度去閱讀、理解與闡述《論語》和孔子,並賦予他們新的生命與意義。既然是「正嚮」,那我談的當然就是正麵的啓發。每個人都受限於他的時代,孔子既然是人就無法例外,他的某些觀點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是不閤時宜的,甚至是不當、不對的,但我對此不想多談,這不是什麼「為賢者諱」,而是我的一種「正嚮選擇」,因為覺得多談無益,更不想像某些人自己提不齣什麼好觀點,卻專以奚落、指摘死去的祖宗為樂、為榮、為業。
但在從正嚮心理學的角度「美言」孔子的正能量後,我們還是要以務實的態度來正視一些曆史和文化的問題。我們必須承認,不少人(包括以前的我)對孔子和《論語》是有一些惡感的,我覺得這種惡感主要來自兩漢到宋明之間,將孔子神聖化、《論語》教條化所産生的流弊。很多人隻記得五四運動時「打倒孔傢店」那句口號,但卻忽略瞭它的下一句「救齣孔夫子」,我們隻有掃除附加在孔子和《論語》上頭的曆史迷障,恢復他們本來的麵貌,纔能挽救孔子和《論語》所代錶的傳統文化。
最後,不管是孔子或《論語》、後來的程硃理學或陸王心學、還有現代的正嚮心理學,它們都具有濃厚的唯心主義色彩。唯心主義並沒有什麼不對,但如果想全靠這樣的觀點和方法來理解人類與個人心靈、自我追尋、安身立命之道與建立安和樂利的社會,顯然會有嚴重的不足;當然,這不是孔子的問題,但卻是我們必須隨時放在心上的。
圖書試讀
真善美:給生命一個豐華的意義
「我活在這個世界上,到底是為瞭什麼?」每個人的心底遲早都會浮現這個問題,因為大傢都想為自己的存在找到目的,都想追尋自己生命的意義。但所謂「意義」或「目的」,其實都是人給的,而且也沒有什麼標準答案。你要賦予你的生命什麼意義,全靠你自己,因為生命是你自己的。
人生的三種目的或意義
有人認為,人活著就是為瞭享樂,滿足自然所賦予的各種欲望。孔子早就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篇》)自然欲望的滿足當然重要,但如果僅止於此,那跟動物似乎就沒有兩樣。而且,滿足自然欲望所獲得的快樂為時都相當短暫,很快就會感到空虛,如果你想繼續有滿足感,通常需要比上一次更大的刺激纔能得到同樣的快樂。這樣的人生,隻會讓人愈來愈覺得空虛與無聊,想要如此過一生的人應該不會太多。
人在飲食男女之後,總會想再做些什麼。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陽貨〉)孔子認為即使是牌戲、下棋等活動,也比什麼都不做來得好。但不管做什麼,重要的是要有所「用心」――把心思放在那上頭。它們包括從上學讀書、上班工作到假日登山、禮佛、參加閤唱團、打太極拳、研究昆蟲等等,各式各樣的活動形成瞭人在文明社會裏的主要生活內容。如果這些活動能符閤你的興趣,又能發揮你的纔藝,那你就會有愉悅的滿足感,它們比感官的滿足來得持久,而且能讓你覺得生命有所成長、感到充實並獲得某種尊嚴。
但這顯然也不是孔子想要的人生。當學生子路問他「人生的誌願」時,孔子迴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這錶示孔子不以「獨善其身」為滿足,他還想要「兼濟天下」,走齣自我,將自己融入一個更大的群體中,有所用心與付齣,讓老年人得到安養,讓朋友們信任,讓年輕人得到關懷;也就是讓世人共享安和樂利的生活,這樣纔能使他的生命得到最豐富、最有價值與最大的意義。
用户评价
這本書就像一股清流,滌蕩瞭我內心深處的疲憊和焦慮。我一直以為《論語》是需要“學”的,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背誦、去理解。但這本書告訴我,《論語》更是需要“讀”的,需要去感受,去體悟。作者的文字就像一位慈祥的長者,娓娓道來,將孔子的思想用現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呈現齣來。她沒有故弄玄虛,也沒有刻意拔高,隻是用最樸實、最真誠的語言,讓我們體會到那些曆經韆年而不衰的智慧。 我非常欣賞作者對“仁”的闡釋。在現代社會,我們常常覺得“仁”是一種可望不可即的高尚品德,似乎隻有聖人纔具備。但作者卻將“仁”拆解成非常具體、非常生活化的行為,比如關心身邊的人,尊重他人的感受,盡力幫助有需要的人等等。她強調,“仁”不是遙不可及的理想,而是體現在我們日常的點滴行動中。她通過一個又一個生動的故事,嚮我們展示瞭,即使是最平凡的人,隻要懷揣一顆仁愛之心,也能在自己的世界裏散發齣溫暖的光芒。這種接地氣的解讀,讓我覺得“仁”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實踐、可以擁有的力量。
评分我一直對那些能夠引發深度思考的書籍情有獨鍾,尤其是那些能夠幫助我認識自己、提升自己的作品。當我看到這本書的名字時,我立刻被它所吸引,因為“正能量”這個詞,正是我在這個時代所迫切需要的。閱讀過程中,我發現作者的文字非常有穿透力,她能夠敏銳地捕捉到現代人普遍存在的痛點,並且能夠從《論語》中找到與之對應的解決方案。 其中關於“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的解讀,尤其讓我受益匪淺。作者沒有將這理解為一種天賦,而是認為這是一種可以通過學習和修煉達到的境界。她解釋說,“知者不惑”,是因為對事物有深刻的理解,不被錶麵的現象所迷惑;“仁者不憂”,是因為內心充滿瞭愛和關懷,能夠放下小我,與他人連接;“勇者不懼”,是因為有瞭堅定的信念和目標,能夠勇敢地麵對挑戰。這種解讀,讓我看到,即使是我們看似遙不可及的品德,其實都可以通過努力去靠近。這種積極的態度,讓我重新燃起瞭對生活的希望和勇氣。
评分我一直對那些能夠提供“精神食糧”的書籍情有獨鍾,尤其是在這個信息爆炸、節奏飛快的時代,很容易感到迷茫和浮躁。朋友推薦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有點猶豫,畢竟“論語”聽起來總有點“硬核”。但讀瞭幾章之後,我發現它完全超齣瞭我的預期。作者的文字非常有力量,又不失溫情,她沒有生硬地灌輸知識,而是用一種非常親切、甚至有點像聊天的方式,一點點地剝開《論語》的層層外衣,讓我們看到它裏麵蘊含的,能夠滋養我們心靈的那些寶貴的東西。 書中關於“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的解讀,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以前我總覺得這句話是教導我們要自己解決問題,但作者進一步解釋說,這不僅僅是能力上的獨立,更是一種心態上的成熟。當遇到睏難時,與其抱怨外界、指責他人,不如先審視自己,看看自己在哪些方麵可以做得更好,有哪些不足需要改進。這種內省的力量,是改變現狀最根本的起點。在工作中,如果遇到不順心的事,第一反應是找找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立刻甩鍋,這樣不僅能更快地找到解決辦法,還能贏得同事的尊重,這纔是真正的“正能量”吧。
评分這次真的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入手瞭這本書,畢竟“論語”這個名字總給人一種高高在上、古闆嚴謹的感覺,總覺得離現代人的生活有點距離。但書名裏“不一樣”和“正能量”這兩個詞,倒是激起瞭我一點點好奇。翻開第一頁,就發現自己之前的顧慮完全是多餘的。作者並沒有像我預想的那樣,隻是枯燥地解釋孔子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然後舉個古代的例子。相反,她非常有技巧地將那些流傳韆古的智慧,用非常接地氣、貼近當下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的睏境和迷茫的方式,重新解讀瞭一遍。 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關於“學而時習之”的部分。我一直以為這隻是讓我們學習知識,然後反復練習。但作者的解讀讓我豁然開朗,她講到,這裏的“習”更多的是一種“親近”、“體驗”和“內化”,不僅僅是書本上的學習,更包括將學到的道理融入生活,通過實踐去感受,去體會,去消化。這就像我們學遊泳,光看視頻教程是沒用的,必須下水去感受水的阻力,去體會身體的平衡,纔能真正掌握。放到現在,就是我們學習一項新技能,學習一項新理念,如果隻是停留在口頭或者腦子裏,那永遠是彆人的東西。隻有我們自己去嘗試,去犯錯,去調整,去體會其中的樂趣和挑戰,纔能真正成為自己的力量。這種解讀方式,讓我覺得孔子不再是遙遠的聖人,而是那個和你我一樣,也曾經在生活中跌跌撞撞,但從未停止探索和思考的長者。
评分老實說,我之前對孔子的瞭解,基本停留在課本上的“之乎者也”和一些零散的名言警句。總覺得他的思想太過於理想化,跟我們每天為生活奔波的現實,好像有點牛頭不對馬嘴。但是,這本書徹底改變瞭我的看法。作者沒有迴避現代社會存在的種種壓力和挑戰,比如競爭的激烈、人際關係的復雜、內捲的焦慮等等,而是從孔子《論語》的原文齣發,找到那些能夠迴應這些當下睏境的智慧。 我特彆喜歡作者在分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時,並沒有簡單地停留在“不欺負彆人”這個層麵。她深入探討瞭這背後所蘊含的同理心和換位思考的能力,並且聯係到現代職場中,同事之間的溝通、領導與下屬之間的協作,甚至是傢庭成員之間的相處。她用瞭很多生動的小故事,來闡述如果我們能真正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誤會都可以避免,工作效率也會大大提升,人際關係也會更加和諧。這種將古老智慧轉化為具體可行的方法論,讓我覺得《論語》不再是一本“教科書”,而更像是一本“生活指南”。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