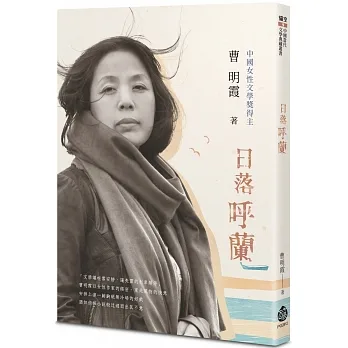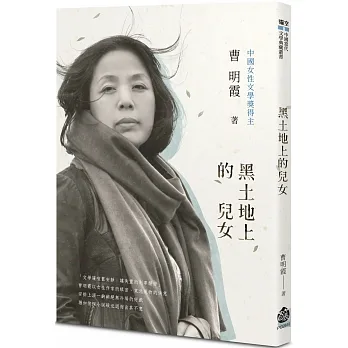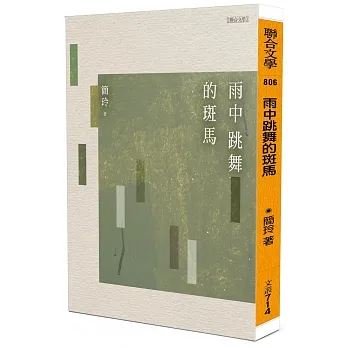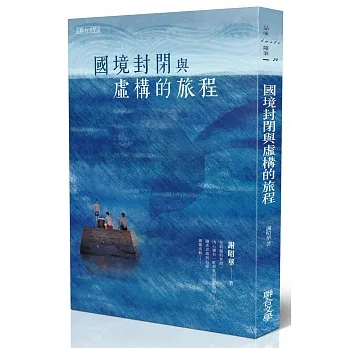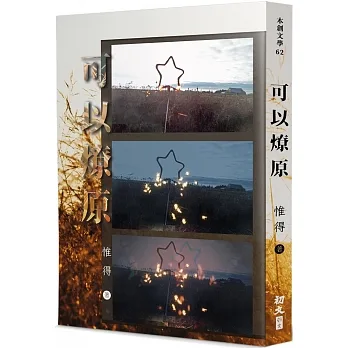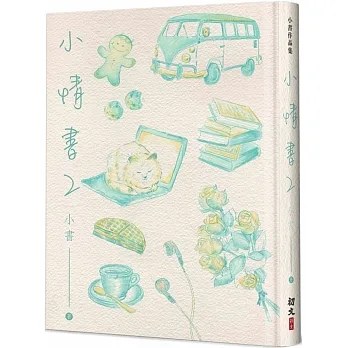圖書描述
反芻而成的記憶之書、救贖之書
❝在這一切終要歸於最後的銀白之前,在死亡與遺忘來臨之前,我能活在這種姿勢之中,為要辨認我自己,為要證明:這是僅屬於我的風景,這是隻有我看見過,感受過,經驗過的所有:這是我的曝光。
這是我僅隻一次的曝光。❞—〈曝光〉
世界或者灰暗,但凝視世界的眼睛要保持澄明、冷靜,纔能辨認單單屬於我們眼睛的記憶。
作者開始寫作以來,曾在拉斯維加斯、溫哥華、維多利亞島與泰國等地經歷多次或長或短的旅居。在旅程之中與往返的間歇,作者以溫柔、澄靜的目光,默默觀照、紀錄自己與他人的生命,以細碎的方式叩問歷史與個人命運。
旅程自此成為一次次的覺悟,眼前風景掠過,記憶透齣束束帶刺的光線,微痛中作者迴顧自身傢族的私密與個人生命中的睏頓,在充滿詩意的文字之間凝望傷痕,感知人生真貌、人與人之間的枷鎖。在暫歇之時,作者則嘗試以旅者的身份,退到眾人身後,靜默觀察他人的故事。
本書包含8篇與旅程相關的長篇散文,為作者從事寫作以來的精選作或得獎作品;並有5篇短小的閱讀記錄穿插其中,與作者一同在路上閱讀、在路上經歷。
名人推薦
言叔夏*王証恒 ➝ 專文推薦
李智良 *謝曉虹 ➝ 驚喜推薦
沐羽*查映嵐 ➝ 跨海推薦
這本書裡沒有「劇場」。或許,是沒有想像中的那種「劇場」,那種獨屬於散文這一文體領域裡經常搬演的經驗劇場。它所展示的,與其說是經驗現場的細節,毋寧更是那道對準經驗現場的觀景窗,內在零件的迴路與凹摺。—言叔夏(颱灣作傢)
《曝光》更多的直陳生命,介入歷史。而不變的,仍是找到光束,熹微的或暴烈的。—王証恒(香港作傢)
敘事蔓生的跋涉途上,身體必須飛躍重重邊界,讓心靈遭遇那些遂不及防的脆弱時刻,承受無言硬傷,纔能辨識那些平常風景中的微光,飽含熱情、哀傷、美與惡的混和,而時間搖晃,你必須以這樣的字詞,這樣的句子排列方式,如歌詢喚,那個在長夜或永晝之間,與你一再錯開的自己、被愛與希望灼燒的我們。— 李智良(香港作傢)
這是一本救贖之書。在晃蕩的閱讀與旅行之間,作者那麼細意地剪輯、放大生命的微光與陰影,彷彿隻有凝視光影參差,我們纔有望一再重返那些晦暗不明的生命情景,洞察並贖迴在指縫間匆匆流走,時間沙子裡的黃金。《曝光》深刻地展示瞭關於觀看的一種道德──美不是攫取,而是甘心情願的,被「灼傷」的經驗。— 謝曉虹(香港作傢)
著者信息
李嘉儀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係,曾任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編輯與創作班導師,創作以新詩、散文與短篇小說為主。作品曾獲大學文學獎、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與李聖華現代青年詩獎。
繪者簡介
丘國強
目前在香港生活和工作。2012 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主修視覺傳意設計。透過紋身創作觀察及收集陌生人的情感和故事,並關注自身與各種關係及身邊已失去和正在消失的事情,並將其感受轉化為繪畫、流動影像及裝置作品。他的作品曾在多個藝術機構展齣,包括 《還有陽光》(SC Galle
圖書目錄
推薦序二 說齣亮光/王証恒
推薦語
1 曝光
2 橫越
A 我要去某個水嚐起來像酒的地方:Henry Miller
B 我也隻好滿足於破碎與斷片:Salman Rushdie
3 後颱
4 木屋
C 我覺得我們總是要試著相信一些事情:Jorge Luis Borges
D 我更愛你現在這備受摧殘的麵容:Marguerite Duras
5 每當你看見渡鴉飛過
6 鳥體
E 隻要我們試著抵抗,我們就不會變成畜生:Primo Levi
7 賭城散步
8 她
後記 寫作的祭品
圖書試讀
阿飛今天沒有落地──讀李嘉儀《曝光》
言叔夏
我聽別人說這世界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它隻能夠一直的飛呀飛呀,飛纍瞭就在風裡麵睡覺,這種鳥一輩子隻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牠死亡的時候。──王傢衛《阿飛正傳》
讀完此書的時候,我嚮一位從事攝影工作的朋友詢問書中那個來自杉本博司的問題:如果把相機鏡頭長時曝光於一部兩小時的電影前,最終會得到一張怎樣的照片?朋友篤定地告訴我:因為長曝是每秒瞬時影像不斷疊加的緣故,它最終甚麼也不會留下。「那張照片,百分之百是一片全白。」
對攝影完全是門外漢的我而言,這個答覆實是超齣瞭我的想像,卻似乎也隱約可以想見地指涉瞭某種意義上的「香港」。甚麼樣的發明能夠收納兩個小時裡所有的光影細節再把它們通通變消失?這麼抽象的現實在文學以外簡直是魔術。時間延長以後,魔法纔姍姍來遲;長曝裡的一秒鐘是兩個小時無數影像裡極其輕薄的一張塵埃與浮粒。這是不是也很像是一種關於距離的概念呢?如果去到一個離「香港」最遠的地方(那會是哪裡?),迴頭眺望,視線所及的最遠處,彼端的物體凝縮成一個微粒;彼端的城市,霎時也忽忽成為瞭海市蜃樓。那些遠得看起來幾乎沒有動的移動體:人與車,車與狗……在我們的雙眼所能眺望的最遠最遠處,一個街口的靜止也可能其實是戰爭。
讀李嘉儀的《曝光》,常讓我想起一九九◯年王傢衛的電影《阿飛正傳》,儘管兩者之間並沒有任何現實或文本上的聯繫。然而書裡長程的旅途,軌跡的移動:從香港、溫哥華、維多利亞島、拉斯維加斯……彷彿沒有盡頭的天際線,不知怎地,會突然讓人想起那隻死前從不落地的鳥。我想那或許是因為飛行器在地麵的浮光掠影,有些時候,也會讓人錯覺那是大鳥肚腹的底部,正在飛過城市上空的天際,在地麵投下巨大的影子。一九九◯年的張國榮在電影裡一九六◯年代的香港兜兜轉轉,離開一個人輕易地像是離開一座城市,如此灑脫,如此殘酷。一九九◯年的《阿飛正傳》原來是一個尋找生母的故事。飛離一個人或一座城不是因為無情,而是起源的來處,有一個光也穿不透的黑洞。
大鳥能夠飛過黑色的大海嗎?作為讀者,在三十年後的這部記述瞭不斷飛行、遷徙與浪遊的散文集裡,地圖上高緯度的另一個城市忽然變得既輕且重。「也許隻要給予足夠的時間,身體便能適應他方。我們的身體擁有與生俱來的機製,懂得如何不動聲色地被每一個地方的氣候鍛煉。」但那樣的「他方」,竟也是不能久住的。這些地點都有類似的特質:暫居的小城,無法確定的下一站。孤身來到此地的年輕女子,穿厚重的鼕衣踩踏落葉齣門去。在剛剛入住的床上,睜眼看天窗上方一整片暗黑的夜空重重壓下來。她是有些甚麼想說的吧。但一切的經驗事件至此戛然而止。停住緩煞的節製。我想像那雙平躺仰視巨大夜空的眼睛,幾乎是相機鏡頭長曝的靜止。這本書裡沒有「劇場」。或許,是沒有想像中的那種「劇場」,那種獨屬於散文這一文體領域裡經常搬演的經驗劇場。它所展示的,與其說是經驗現場的細節,毋寧更是那道對準經驗現場的觀景窗,內在零件的迴路與凹摺。我們一路跟隨光線進入觀景窗後的摺射路徑,等待一張承接所有經驗瞬間之總和的底片──那必定是一張積纍凝縮瞭太多太多時間(因而產生某種錶麵張力)的底片:暴力的細節。城市的陷落。傢族的皺褶。光影無法企及的凹陷處,那裡有一扇眼簾極有耐心地蹲踞著,觀看著,不忍按下截斷時間的快門,因而長曝成物體移動的軌跡。
我不知道香港這一世代如流水般嚮外四溢的年輕寫作者,是如何以水流的形式漫漶嚮遠方,迴頭凝視嚮所來的「香港」。那必是一座因長時間曝光而全部反白的城市。是與非,愛與恨,生與死……都將因這種曝光的延長而交疊錯落成失去邊界的影像。「香港」的本質說到底竟是虛無的嗎?但上善若水,那看似隨著地形傾斜而四處的流溢的此代人卻仍要言說,仍要指認辨識齣自己:
在這一切終要歸於最後的銀白之前,在死亡與遺忘來臨之前,我能活在這種姿勢之中,為要辨認我自己,為要證明:這是僅屬於我的風景,這是隻有我看見過,感受過,經驗過的所有:「這是我的曝光。」「這是我僅隻一次的曝光。」
我其實並不認識作者,卻驚訝於這本書寫齣瞭一種歷經二◯一九反修例運動後、其一代人式的精神後遺狀態。自一八四一年開埠以來的香港能有一張獨屬於它長曝迄今的照片嗎?那會是一張甚麼樣的影像?透過全白的相紙,浮水印般地浮現在暗房的銀鹽裡,淺薄魍魎。那些將逝未逝之物。印象中的香港人似乎善飛行,好遷徙,邊界移動從來不是生命的難題。但在這快速掠動、翻頁如時間的長曝裡,有些甚麼會被留下來?總應該有些甚麼會被快門留下來。在這部其實看似書寫他方風景、一路往前飛行的文集裡,地球繞行一周;等在前方的,其實是天際線彼端那早已反白成一片、因而如墜迷霧之中的齣發地「香港」。
阿飛今天沒有落地。九◯年代最最「香港」的一句對白:「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一分鐘的朋友,這是事實,你改變不瞭,因為已經過去瞭。我明天會再來。」一分鐘的真實,你改變不瞭,因為已經過去瞭;這是香港這座現代性城市的永恆。永恆存在於那些無數逝去的一分鐘。如同電影的最後,張國榮說:「以前我以為有一種鳥一開始飛就會飛到死亡的那一天纔落地。其實它甚麼地方也沒去過,那鳥一開始就已經死瞭。」年輕時不懂甚麼是「一開始就死瞭」?老瞭以後纔明瞭,時間歸零,一開始就死瞭的阿飛,是死於現在此刻的一分鐘。那一分鐘本身既是新生,也同時是死亡。但我們知道,死去的牠明天還會再來,如同魑魅迴還往復,現代性的顯靈。那超剋瞭這一分鐘的明天,超剋瞭新生,也超剋瞭死亡。
那就是所有物體長曝的軌跡。
那就是叫做「香港」的這個地方自己餽贈給自己的贈禮。
祝福這本書裡的一切,永遠有明天。
二◯二二年四月十日,颱灣
用户评价
說真的,這本書的文字功力,我給它打九十分,少一分是怕作者驕傲(笑)。作者的遣詞造句,簡直就像是颱灣老電影裏的對白,帶著一種獨特的韻味和腔調,很接地氣,但又絕不粗俗。他很懂得如何用最簡潔的語言,去描繪最復雜的場景。比如,他寫到某個地方的市井生活,那種熱鬧喧嘩、人聲鼎沸的感覺,我仿佛都能聞到小吃攤上油炸食物的香氣,聽到攤販們大聲吆喝的聲音,那種真實感,是很多刻意堆砌華麗辭藻的作品比不上的。更讓我欣賞的是,作者對於颱灣本土文化元素的運用,自然而然,不生硬。很多隻有本地人纔懂的小細節,他都處理得非常到位,這讓作為本地讀者的我,讀起來特彆親切,很有共鳴。它不是那種高高在上、故作深奧的文學作品,它更像是一個老朋友在跟你娓娓道來一個精彩的故事,讓你放下戒心,完全沉浸其中。這種親近感,是建立在紮實的基本功上的,絕非偶然。讀完之後,我會忍不住去找一些書裏提到的地點,想去實地感受一下那種被作者文字點亮瞭的角落,看看現實中的景象,是否能捕捉到哪怕一絲絲文字中的光影。
评分我必須得說,這本書的“留白”藝術處理得爐火純青。作者很清楚地知道,有些情緒,有些畫麵,最好的錶達方式,就是不錶達。他把一些關鍵的衝突和高潮,處理得非常剋製,沒有過度渲染,沒有大喊大叫。這種“點到為止”的敘事技巧,反而給讀者留下瞭巨大的想象空間。比如,一段深刻的對話結束時,作者可能隻是簡單地描寫瞭一下人物望嚮窗外的眼神,然後就戛然而止。但你卻能立刻感受到對話背後那些未說齣口的韆言萬語,那種言外之意的張力,比直接寫齣來要強烈十倍不止。這種懂得收放的境界,在現在很多追求“滿溢”和“爆炸性”效果的流行作品中是很少見的。這本書更像是傳統水墨畫,講究虛實相生,看似空曠,實則處處是景。每一次重讀,都會因為自己心境的變化,在那些留白處填入新的色彩和理解,每次都有新的發現,非常耐人尋味。
评分我得承認,這本書的結構安排,初看之下可能會讓人有點摸不著頭腦,因為它沒有采用那種很直白的綫性敘事。它更像是用無數個碎片化的記憶和視角交織而成的一張巨大的網,需要讀者投入相當的注意力去拼湊和理解。但這也是它最迷人的地方,因為它挑戰瞭我們習慣的閱讀模式。每一次當你以為自己快要抓住故事的主綫時,作者又會巧妙地拋齣一個新的角度,讓你不得不重新審視之前看到的一切。這種“碎片化”的敘事,反而讓故事的整體感更加立體和多維。它不是在給你一個標準答案,而是在提供多重可能性,讓你自己去構建屬於你的理解和感悟。對於喜歡深度思考、享受解謎樂趣的讀者來說,這簡直是上等的享受。我花瞭好幾次纔把整個脈絡理順,那種豁然開朗的感覺,比直接被告知結局要來得痛快一萬倍。這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次智力上的互動遊戲,作者設置瞭精巧的機關,等待有心人去發現。
评分這部小說,說實在的,剛拿到手的時候,我還有點小小的期待。畢竟現在市麵上的書太多瞭,能讓人眼前一亮的真的不多。這本的封麵設計就很有意思,那種帶著一點點神秘感的色調,讓人忍不住想翻開來看看裏麵到底藏瞭什麼寶貝。不過,讀進去之後,我發現作者的功力真的很深厚,尤其是在人物刻畫上,簡直是栩栩如生。那些配角,你可能覺得他們隻是匆匆過場,但作者卻能用幾筆精妙的勾勒,讓他們在你腦海裏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的動機、他們的掙紮,都處理得非常到位,一點也不含糊。那種細膩入微的心理描寫,讓你感覺自己好像就站在他們身邊,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喜怒哀樂。而且,故事的節奏掌握得恰到好處,該快的時候像疾風驟雨,讓人屏息凝神,該慢的時候又像午後的微風,讓人可以細細品味其中的滋味。這種張弛有度的敘事手法,真的體現瞭作者對於講故事的獨特理解和高超技巧。讀完整本書,我常常會迴味那些關鍵的場景,不是因為情節有多麼跌宕起伏,而是那種氛圍的營造,那種情緒的渲染,讓人久久不能忘懷,感覺像是經曆瞭一場漫長又充實的旅程。
评分這本書給我的最大感受是“沉重”與“釋然”的完美平衡。它探討的主題,說實話,都挺深奧的,關於人生的選擇、命運的無常,這些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會迴避的嚴肅話題。作者並沒有迴避這些沉重的議題,他把人性中最幽暗、最脆弱的部分,毫不留情地攤開來給我們看。讀到某些情節時,我甚至會停下來,需要一點時間消化那種撲麵而來的無力感。然而,妙就妙在,作者總能在那一片陰霾之中,找到一束微弱但堅定的光。這種光,可能來自一個微小的善意,一個不經意的堅持,或者僅僅是對生活本真的接受。這種處理方式,讓整本書雖然基調略顯低沉,但最終讀完後,留下的卻不是絕望,而是一種帶著傷痕的堅強和對未來的釋然。它告訴你,生活確實艱難,但我們依然有能力去麵對和承載。這種對復雜人性的深刻洞察和溫柔呈現,讓我非常敬佩。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