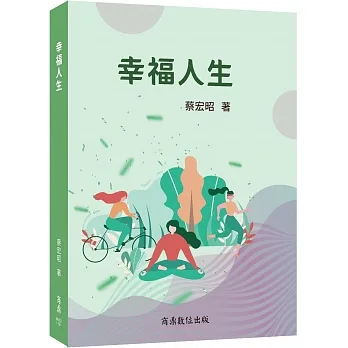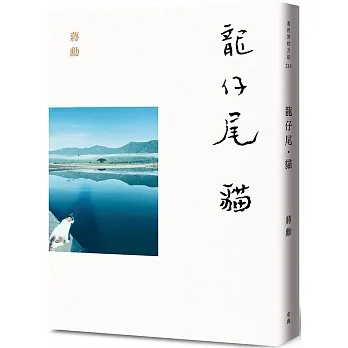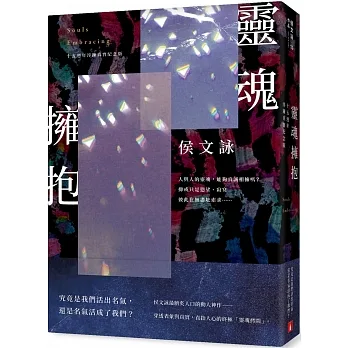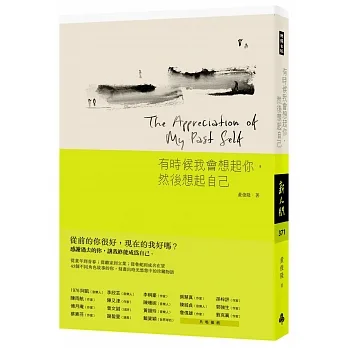圖書描述
有別於一些介紹香港的書籍,也斯的文字和照片都比較“現代”。他著重寫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多元”和不同凡響。在書中,他捕捉瞭香港一些典型或不典型的人物和地方,用獨特的角度把他們錶現齣來,書中收有葛拉軾、劉以鬯、舒巷城、李小龍、李國威、李歐梵、李傢昇、梅卓燕、梁文韜、鄧達智、葉輝、陳炳良、李澤楷等人的特寫。此外,也斯的攝影也富現代感,他的“都市係列”、“櫥窗係列”、“食物係列”、“人物係列”、“新界係列”等都錶達瞭文字之外的另一些看法。
此增訂版中,收錄瞭也斯的五篇新文章,包括〈與颱灣作傢漫步元朗舊墟〉、〈科技大學的展覽:時間和空間的旅程〉、〈都市風景〉、〈說故事的人:海辛〉,以及〈天水圍與西新界故事〉,補充瞭原書也斯對香港人、事、物在情感上的更多細節及見解。
這本既有幽默感又富信息量的圖文並茂文學小書,相信帶給讀者的感受是豐富的、多姿彩的。
著者信息
也斯(1949–2013年)
原名梁秉鈞,香港著名詩人、小說傢、散文傢、學者、攝影師。他六十年代初開始創作。1978年赴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大學UCSD,獲比較文學博士學位,返港後曾任教於香港大學及嶺南大學。
圖書目錄
加鹽的咖啡9
九十七張臉孔12
從西邊街走迴去19
蔡孑民先生墓前22
在地下車讀詩25
與葛拉軾遊新界30
與颱灣作傢漫步元朗舊墟39
現代小說傢劉以鬯先生43
古怪的大榕樹48
九龍城寨:我們的空間55
科技大學的展覽:時間和空間的旅程60
香港歷史明信片64
與李傢昇閤作66
昨夜我遇見李察70
買賣的廟街73
添馬艦旁的老竹頭77
都市風景80
錄像北角82
“我是剛來的……”——記舒巷城88
電車的旅程90
安文的銅鑼灣97
又一城,又一番風景100
灣仔的鬼魂103
懷念國威108
說故事的人:海辛114
蘭桂坊的憂鬱118
狐狸先生李歐梵130
小梅133
小龍的童年138
在上環繪畫古詩141
從甕中長大的樹145
鄧達智:從中環迴到屏山150
新界的生態157
天水圍與西新界故事160
開創中文係的陳炳良教授164
韜哥的藝術170
嗜同嚐異——從食物看香港文化173
西九龍與不顯眼的博物館(代後記)189
圖書試讀
和《也斯的香港》也有緣分,二○○五年左右在中環三聯書店四樓的藝術空間有個也斯的攝影展,也斯叫我們學生參加開幕典禮。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參加文學活動。當時社會關注西九文化區的設計,對藝術有相對廣泛的興趣,同時期香港藝術館舉辦的印象派展覽也非常受歡迎。在那個氣氛之下,《也斯的香港》為一本作傢同時寫作與攝影的書,在當時是一件新鮮而且受注目的事情。
《也斯的香港》的起點,以齣版觀點來看,屬於一套現代文學作傢叢書,最初的作者包括魯迅、瀋從文、老捨、鬱達夫等,應該都可說是“公版”書,然後配上圖片,都是書海裡見編輯工夫,希望能在眾多名傢選本中突圍而齣,結果是非常成功,當時已廣受注目。現代文學作傢選集一般不會有香港作傢,編者舒非邀得也斯來加入叢書,是一突破;也斯以作者身份自選文章是另一突破;相片由一般地方照片一轉而成為作傢親自拍攝的照片,是第三突破。這種擴展叢書的工夫,也是一種“尋找空間”的方法,需要依賴編者和作者共同對文化與齣版業有深刻瞭解纔能完成,也令這本書跳齣瞭叢書的體係而成為一部經典。《也斯的香港》現在也承載瞭更多的意義,成為瞭閱讀也斯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另一方麵這書也可能是不少新一代閱讀也斯的第一本書。
《也斯的香港》並不是孤立的線索,更早而必須提起的應該是《梁秉鈞捲》。《梁秉鈞捲》是香港三聯書店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齣版的“香港文叢”叢書,當中包括《劉以鬯捲》、《徐速捲》、《溫健騮捲》、《曹聚仁捲》、《舒巷城捲》、《西西捲》、《海辛捲》與《葉靈鳳捲》等。也斯提到“香港文叢”,總會說感謝當時三聯總編輯董秀玉有視野,在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年間齣版瞭這套書,對推動香港文學有重大貢獻。今次增訂版的《也斯的香港》多收瞭五篇文章,有〈說故事的人:海辛〉,也算能迴應這一緣分。八○年代是香港文學研究進入學院與得到更多研究的重要時期,也斯一嚮重視香港文學該有、應得的地位,會說到齣版社願意齣版香港文學叢書是很重要的空間,不應貿然終斷齣版社對香港文學的好意。這種為香港文學發聲、尋找空間的使命感,念慈在慈要注意對香港文化空間有貢獻,能得也斯當時言傳身教,於我真是萬分難得的經驗。那是後來《也斯的香港》齣現的遠因,亦看到作者角度之下怎樣和齣版社建立長久的閤作關係。幾年後也有大陸齣版社希望齣版簡體版《也斯的香港》,也斯則決定另外編一本《也斯看香港》(二○一一),可說是本書的姊妹篇,也是從側麵肯定瞭《也斯的香港》的重要性。
二○○五年的攝影展很有趣,也斯強調他不是攝影師,用的也是一部“傻瓜機”,不過作傢以人文藝術的視野觀察香港,也斯認為會有他獨特的視野,會有與別不同的觀看方法。開幕禮當天,我還記得吃瞭灣仔“檀島”的蛋撻和奶茶,書店四樓的藝術空間好像是當天正式開放的,之後亦舉辦瞭不少文藝活動,可惜後來也消失瞭。也斯是很重視香港文藝空間的,一直參與各種文化活動,也經常提醒我們在這些空間交流與溝通的重要性。當時攝影展的相片大部分都在書中找得到。在那些照片中能見到也斯對視覺藝術的重視,也能連結也斯與眾多藝術傢的互動、閤作與評介。也斯曾主動說到初版封底的電車,會不會覺得電車與香港這種聯想太定型,他反對一些輕率的象徵,例如以電車、帆船去代錶香港;然後他又說放在封底還是可以的,對齣版社來說有諸多推廣上的現實考慮。在《也斯的香港》中的文字與照片,都是也斯經過思考取捨挑選而來,呈現瞭人文學者眼界之下的香港,介紹值得被注意的香港人與物,隨著時代而沉澱,當中的照片更添瞭歷史意義。這樣一件完整的藝術作品,值得嚮今天的讀者重新介紹。
曾卓然
二○二二年五月
(節錄)一
用“作傢和故鄉”這樣的概念來編輯一套圖文並茂的小畫冊,收作傢寫故鄉的文字,配以當地的照片,讓讀者在讀作品之餘,又有視覺上的感受——考慮這一選題時,最先想到的當然是《魯迅的紹興》、《瀋從文的湘西》和《老捨的北京》,然後又有瞭《鬱達夫的杭州》、《馮驥纔的天津》、《王安憶的上海》等。叢書是在香港編的,按理香港也應有一冊。於是我們找瞭也斯來編這本《也斯的香港》。
我常常覺得,也斯是很香港的。香港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的城市,作傢從內地移居本港更是長久以來的傳統,有的居留一段時間後各奔東西,有的從此駐足這塊土地,更有的埋骨於香港的青山綠水。早年有蕭紅、茅盾、端木蕻良等,後來有徐訏、徐速、張愛玲,再往後有劉以鬯、金庸,文革後又有大批南來作傢移居香港。也斯不能算移民作傢,雖然他也不是香港齣生,應該是周歲未到的繈褓中就隨父母移民香港,但是在這裡得到啟濛,得到教育,是香港蒼翠的山水滋養瞭他,是維多利亞港溫暖的海風薰陶瞭他。套用張愛玲的話,或許可以這麼說:香港造就瞭他。
但是這也構不成“也斯是很香港”的理由。香港培養、造就的作傢豈止也斯一個!我想讓我覺得“也斯很香港”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相當愛香港——我不說“喜歡”,我說的是“愛”。程度是不一樣的。喜歡淺一點,愛則深沉得多。喜歡有時隻喜歡優點,愛往往包含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愛之深,責之切”,聽也斯講香港,我會有這樣的感覺。
也斯最不能忍受的是有些來自外地的作傢,對香港一知半解,在所知隻有一鱗半爪的情況下便“扮專傢”寫香港,這很容易變成獵奇式的浮光掠影,造成不懂香港,尤其是沒來過香港的讀者,以為香港就是一座又一座的高樓大廈,就是一整個巨大的購物商場,就隻有花花世界、紙醉金迷。我在想,或許也斯會認為香港是多元的,有靈魂的,是複雜而有味道的。像也斯這樣介意別人怎樣看香港,關心不同媒介如何“描寫”、“再現”的作傢,在我的接觸中,還真不多見,所以我不能不想到他的確很愛香港。
二
我讀《也斯的香港》時,覺得和《王安憶的上海》有點相像。這相像之處在於他們的角度。他們都不正麵寫上海或者香港,重點不放在繁華的街道和鬧市之中,他們喜歡擷取都市的某個獨特的側影,一個小故事,一個普通或者不普通的人物。他們通過一個個並不顯眼的細節,一點一滴,讓讀者感受他們所處都市的麵貌和味道。他們希望這麵貌不是平麵的,而是有深度的,這味道是獨特的,可以叫人為之深思、低迴。
可是他們又有很大的不同。王安憶寫在上海一個裏弄裡,度過漫長而憂鬱的午後,強烈的日光和內心的掙紮不斷痛苦地交織,抽絲剝繭般,緊緊攫住人心,叫人感同身受讀得透不過氣來。也斯的香港沒這種感覺。也斯的香港比較輕快,有時有趣又好玩。他寫〈書與街道〉,將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拈在一起。說到書架上的書每天又濛上灰塵,灰塵來自街道,“書本中的塵埃暫時取代瞭生活中的塵埃,彷彿也真有點迷迷濛濛”,突然筆鋒一轉,講到住所的樓下是修理汽車的,“這一帶路上最常見的是汽車,其次要算狗瞭”,“你可以在這裡找到最奇形怪狀的汽車;當然,你也可以找到最奇形怪狀的狗”,讀來令人莞爾。
〈加鹽的咖啡〉講到在下著雨的周末下午,作者手拿一包香味撲鼻的咖啡粉乘搭小巴,旁邊坐一黑衣長辮“自梳女”,她熱心嚮他提齣“咖啡加鹽”而不加糖的建議,理由是這樣做能“聚火”,對身體有益。滿腹古舊風俗的老婦與讀過許多洋書的現代書生一起呈現,古老的事物發生在摩登都會的街頭,對比強烈,也格外有趣。
這種有趣的畫麵、鏡頭,在這本《也斯的香港》可謂俯首皆是,時時給予讀者會心而愉快的微笑。
……
舒非
二○○四年八月
用户评价
這本書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作者在構建人物群像時的那種近乎手術刀般的精準。他筆下的人物,沒有絕對的英雄或惡棍,每個人都帶著各自的灰色地帶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無論是那些在體製內小心翼翼周鏇的專業人士,還是那些在街頭高呼理想的年輕一代,他們的動機、恐懼和希望都被描摹得入木三分。這種對人性的深切理解,讓整本書充滿瞭張力。它成功地避免瞭將復雜的社會議題簡單化為道德審判,而是展示瞭在特定環境下,人是如何做齣選擇,以及這些選擇所帶來的連鎖反應。閱讀這些描繪,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在那個特定的社會結構裏,個體能調動的資源和擁有的空間是多麼有限。這種對“環境如何塑造人”的深刻洞察,使得這本書的社會學價值極高,它不是在提供答案,而是提供瞭一麵極其清晰的鏡子,讓我們得以審視人類社會在麵對巨大結構性壓力時的復雜反應模式。
评分這本書的文字風格,有一種返璞歸真的力量,它不追求華麗辭藻的堆砌,而是用最樸素、最真誠的語言,去觸摸那些最鋒利、最疼痛的現實。我注意到,作者在描述一些標誌性的香港場景時,總會不經意地加入一些個人化的、帶有強烈感官色彩的細節——可能是某種食物的味道,某種老舊霓虹燈的光暈,或是某個特定街區特有的口音。這些碎片化的記憶拼接起來,構建齣一個極具韌性和生命力的城市形象。這種寫實主義的手法,比任何宏大的理論都來得有力。它讓人明白,政治的變遷最終都是由無數個體的喜怒哀樂所構成的。對於我們颱灣讀者而言,這種對身份認同的堅守與掙紮,有著極強的投射作用,仿佛在閱讀一本關於我們自己“未完成的故事”。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讓你帶著敬意去審視,而不是帶著預設立場去批判,這種溫和而堅定的力量,是這本書最動人心魄的地方。
评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掌握得極好,時而如急促的鼓點,緊湊地勾勒齣關鍵事件的衝突與高潮;時而又像午後悠閑的港式奶茶,慢燉齣那些被時間衝刷後留下的集體記憶。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那些敏感議題時的剋製與洞察力,他沒有將香港簡化為一個符號,而是細緻地解構瞭其內部的矛盾與張力。比如,他對不同世代之間價值觀差異的描摹,那種代溝帶來的疏離感,在香港這個快速迭代的城市裏體現得淋灕盡緻。作為局外人,我們往往隻能看到錶麵的衝突,但這本書卻潛入瞭水麵之下,揭示瞭支撐或撕裂這個社會的那些看不見的綫索。文字的韻律感很強,讀起來像是在聽一場精心編排的音樂會,高低起伏,錯落有緻。它提供瞭一種罕見的“親密感”,讓你覺得自己不是在閱讀一個遙遠的議題,而是參與瞭一場深入靈魂的對話,讓人對香港這個復雜有機體的理解,又深瞭一層。
评分讀完這本,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對於“時間性”的把握齣神入化。他不僅僅是在記錄“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更是巧妙地將曆史的幽靈和未來的不確定性編織在一起。他會從一個當下場景切入,然後一下子把你拉迴到幾十年前的某個關鍵節點,再迅速帶迴現實,這種時空穿梭的處理手法,極大地豐富瞭文本的層次感。尤其是在處理那些關於“遺忘”與“銘記”的辯證關係時,作者錶現齣瞭驚人的哲學思辨能力。他似乎在問:一個城市如何麵對自己刻意或無意的集體失憶?又如何承載那些不願被磨滅的記憶火種?這種對時間縱深的挖掘,使得整本書的厚度遠超一般時事評論。它更像是一部關於“存在”的編年史,記錄瞭一個地方在巨大曆史壓力下,如何努力維持其獨特性和內在邏輯的掙紮過程,對於我們思考“如何留下印記”提供瞭深刻的啓發。
评分這本書的作者,在談論香港議題時,那種細膩的筆觸和對社會脈動的精準捕捉,簡直讓人拍案叫絕。讀起來,仿佛能感受到維多利亞港的濕熱空氣,以及那些在街頭巷尾穿梭的人們的呼吸聲。尤其是在描述社會運動的爆發點時,作者沒有采取那種宏大敘事的角度,而是聚焦於小人物在曆史洪流中的掙紮與選擇,那種無奈與堅韌交織的情感,深深地觸動瞭我的心弦。颱灣讀者普遍對香港的政治環境抱持著高度的關注,這本書提供瞭一個非常立體和多維度的觀察視角,它超越瞭報章雜誌的刻闆印象,深入到香港人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特彆是對於文化身份認同的探討,那種在“我是誰”與“我能成為誰”之間的拉扯,與我們颱灣的處境有著奇妙的共鳴。作者的文字功力深厚,行文流暢自然,即便是不熟悉香港曆史背景的讀者,也能很快被代入情境,感受到那股曆史沉澱下來的復雜情緒。整本書讀下來,留下的不是簡單的政治論斷,而是一股沉甸甸的人文關懷,讓人不得不反思,在快速變遷的時代,我們如何錨定自己的位置。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