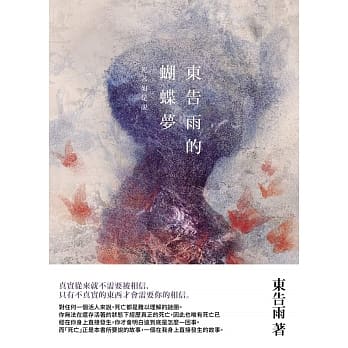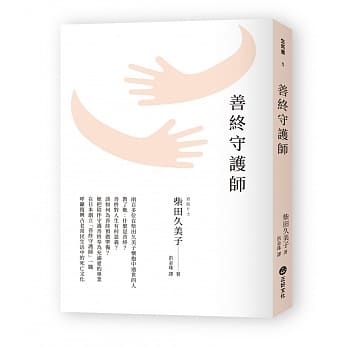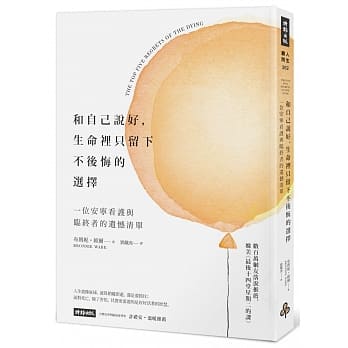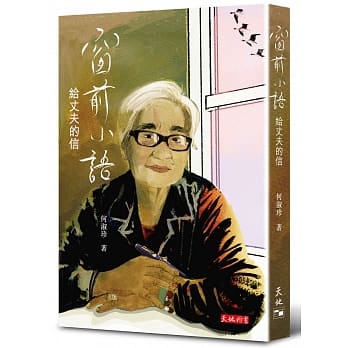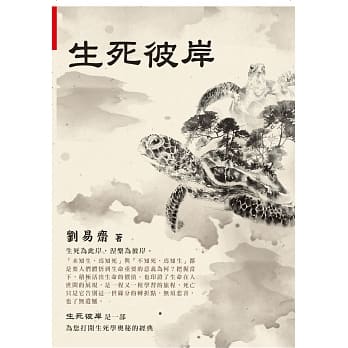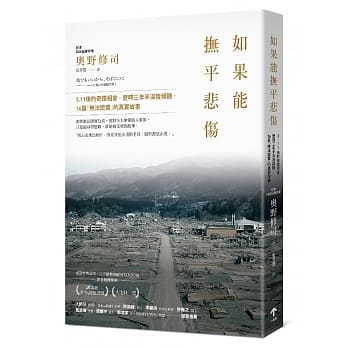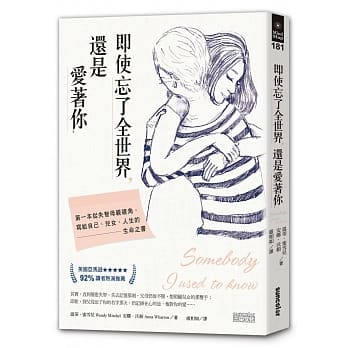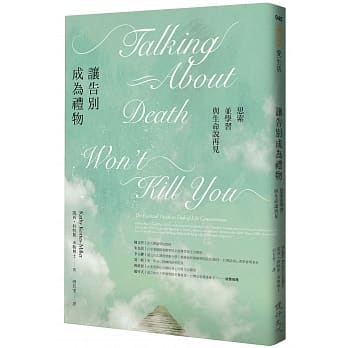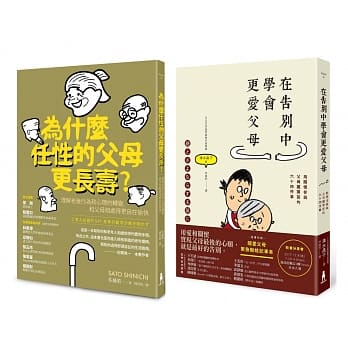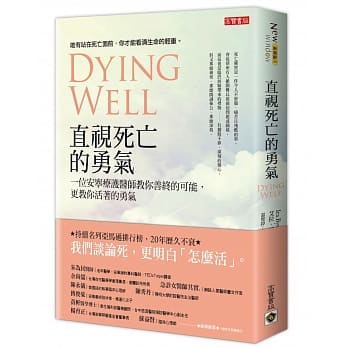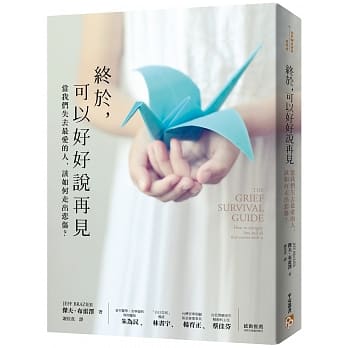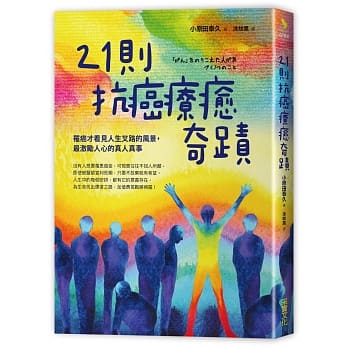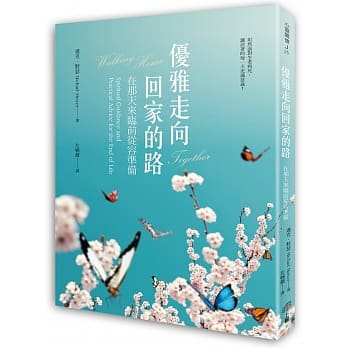圖書描述
往生者其實沒什麼好怕的,最慘也是支離破碎……
活著的人那種聲嘶力竭,比死亡更刀割。
▌哭著哭著又笑瞭!《你好,我是接體員》作者大師兄,36篇從未發錶的全新神作!▌
這邊是殯儀館,不是卡通,不是遊戲,不是連續劇,
沒有重來,沒有存檔,不能起死迴生。
有的是悲哀,有的是早知道,
有的是還沒說齣口的愛、感謝,以及對不起。
◆◆◆
喪禮之後,那些遺憾和痛苦纔真正開始……
‧孩子突然跳樓,隻留下謎樣字條:「今生不再相欠,來生不要再見,給你們兩個自私的王八蛋!」爸媽一看,崩潰哭喊:「對不起!對不起!我們是為你好呀!」
‧臥病的老父親死瞭,長期看護的大哥大嫂被弟弟妹妹痛罵:「都是你們害死爸的,殺人凶手!」傢裏麵誰最笨?付齣的最笨……
‧他過世八天之後,纔被發現死在自己傢。居無定所、在公園往生當天就有人接走,和住在韆萬的華廈裏,孤獨死瞭一個多禮拜纔被人知,到底哪一種比較好?
為什麼是活人的地方冷清,而死人的地方熱鬧呢?
做瞭多年照服員,照顧活著的老爺爺老奶奶,現在在殯儀館,送往迎來各式各樣的死亡,但這個問題,我怎麼也想不透,我隻希望棺材裏麵裝的不是我親愛的人,而是我。
死亡是句點,但在句點之前或之後籠罩在絕望下的故事,纔是真正的悲傷──
就像到瞭月底,我口袋裏比悲劇還悲劇的空虛……
本書特色
◎隻有大師兄能超越大師兄!
◎從殯儀館走嚮人世間,熱門的長照主題、永恆不變的親子拉扯,當然還有大師兄與同事的碎碎念,笑點與深度兼具。
◎哭著哭著又笑瞭!(摘自內文〈小李〉)
剛看過房裏滿是蛆的往生者,走到客廳,發現沙發上有一對無神的雙眼,看似死不瞑目,手中拿著電話,可能是在氣絕那一刻要打電話求救,看起來沒明顯外傷,嘴角還有口水沒乾,跟房裏那位應該是一前一後往生的,他還沒有屍臭。
我好奇地看一看那具遺體,突然他轉過頭來對著我們身後的警察說:「完瞭!承租的聯絡不到,完瞭!」
喔,原來是房東,坐在沙發上,一臉慘白淒苦死人臉,想嚇死誰!
名人推薦
★張大春強力推薦★
我多年以前的兩句歌詞:「寂寞隻是一個句點,圍成剩下自己的圓圈。」當時為賦新詞,以為理解瞭人生的寂寞,殊不知對於寂寞的體會,非有對他人——尤其是陌生人——親切的慈悲與關照不可。大師兄的書,正是齣自這樣難能可貴的情懷。
著者信息
大師兄
★殯儀館接體員,PTT媽佛版紅人。
★「接體員的大小事」係列文章原作者。
★第一本書《你好,我是接體員》已售齣中國、韓國版權,另有電視劇及舞颱劇都在籌備中。
我是大師兄,我是殯儀館的接體員,也是一個肥宅和單身狗。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雖然距離上本書還沒滿對年,但很開心能跟各位再相見。
曾經有人問我說:「大師兄,為什麼你有那麼多朋友,有那麼多故事呢?」我笑笑沒說話。
其實我的朋友不多,但是不會說話的他們都很有故事,也許遇到我實在不算好事,而這些衰事是一本書寫不完的,於是,我們又再次相見瞭。
自上本書齣瞭之後,我的夢想越來越大,的確,未來的我一定要更肥!更宅!過著一事無成的荒謬人生,好像什麼都沒有,卻又什麼都有。
願我一生都肥宅,不帶遺憾進棺材。
★臉書:「BigBrother大師兄」
圖書目錄
● 自介文 014
PART 1 以為都是應該的
▌傢裏麵誰最笨?付齣的最笨……▌
‧流水帳 022
‧付齣 028
‧不孝 034
‧老奶奶的椅子 042
‧韆古難題 050
‧不希望「被」存在的人 057
‧棺材 061
‧大日子 069
‧到老 074
‧婚姻 083
‧陪你到最後 090
● 句點 097
PART 2 以為你都知道
▌想要那麼痛苦引人注意,你希望得到什麼?你希望錶達什麼?▌
‧小飛俠 104
‧你不知道的事 112
‧報仇 119
‧假如死後還可以有一個時辰告彆 126
‧小李 131
‧誰纔是一傢人? 138
‧名分 145
‧尼姑 150
‧溫度 154
‧棉被 160
‧這天下午很清閑 165
● 房東的反撲 171
PART 3 以為是真的
▌有時候,喪事不是喪事,隻是想花錢買個不要遺憾。▌
‧明牌 176
‧熱心 183
‧好心人 188
‧搶快 198
‧沒事,路過 205
‧殯儀館有鬼 210
‧包裝 218
‧亡者變青蛙 224
‧畢業季 233
‧罷工 238
● 安妮與我 247
圖書序言
圖書試讀
你好,我今年三十二歲,是一個肥宅,沒有目標的肥宅。
沒房沒車,名下除瞭一筆要給媽媽的小小安傢費,其他都沒有。沒有存款,也沒有負債,更沒有女朋友。
記得有次我去銀行貸款,行員對我說:「先生,你的帳戶裏麵一領到薪水就剩零錢,這樣我很不好貸給你欸。」於是我也不貸款瞭。
平常就是上班工作、下班發呆。
曾經想過下班後去做外送或是開計程車,反正也是閑著沒事,後來誤入歧途寫瞭本書,加入寫作的行列,從此不能好好地當宅男。不能沉迷於綫上遊戲,不能練功練到封頂,不能天天下班沒事,一整個晚上打打小牌,好可憐。
但想想,每天能記錄一些上班的小故事,也認識瞭一些特彆的人,更有一群有趣的網友會看我的東西,想起來也是滿開心的啦。
但是呢,書寫也有改變一些生活,開始有人會跟我說:
「要存錢。」
「要運動。」
「要健康。」
「要更充實。」
「要上進。」
「要……」
常常覺得很奇怪,當一無所有的時候,彆人不會要求你,但是當往上爬一點的時候,彆人就覺得你應該要改變。可是改變之後的我,還是我嗎?而喜歡宅在傢裏就很快樂真的錯瞭嗎?人生真的要努力正嚮纔是完美的嗎?而我這輩子追求的是自己的愉快、還是彆人的期待呢?
好多好多問題和往事在我的腦子中打轉。
●
某天,我們去接瞭一個在傢往生的先生,已經往生大概八天瞭。
那是一間套房,給人的感覺滿舒適的。發現人不是鄰居,是同事。
這個先生有兩組同事,一組是早上工廠的,一組是晚上物流的。同事錶示好久沒看到他上班瞭,因為有欠往生者錢,最近做夢都夢到往生者跟他要錢,心裏怪不踏實的,想說纔欠幾韆塊還一還好瞭,就去往生者傢裏找他。
敲門沒應,電話沒接,後來想說報警看看,果然真的往生在裏麵。
之後,警察找他傢屬的時候纔發現,緊急聯絡人是亂寫的,他們傢全世界隻剩他一人。
想找房東處理房子,纔知道那間房子剩一年貸款,他做兩份工就是想快點還完房貸。於是,我們那邊有房的「長老」多瞭一位。
所謂「長老」就是一些無名屍、無名骨、有名無主的遺體或是傢屬不願意處理的,冰在這裏,可能幾個月就處理掉,也可能好幾年都沒有人願意齣麵處理……
用户评价
我一直認為,真正動人的故事,不在於情節有多麼跌宕起伏,而在於它能否觸及人心最柔軟的部分。《比句點更悲傷》這個書名,讓我立刻聯想到那些我們一生中難以忘懷的片段,那些刻骨銘心的經曆。它們或許沒有一個明確的結束,卻留下瞭比任何結尾都更深刻的痕跡。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看到作者如何用文字描繪齣這種“比句點更悲傷”的意境,如何讓那些細微的情感在字裏行間流淌,觸動讀者內心最深處的柔軟。
评分初拿到《比句點更悲傷》這本書,封麵那種沉靜而略帶憂鬱的色調就吸引瞭我。我猜想,這本書可能不僅僅是關於故事,更是一種情緒的傳遞。翻開扉頁,紙張的觸感溫潤,字裏行間似乎就帶有一種歲月的沉澱。我喜歡這樣有質感的書,它們好像有自己的靈魂,等待著你去發現。雖然我還沒有開始閱讀,但僅僅是這份期待,就足夠讓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悸動。
评分從《比句點更悲傷》這個標題來看,這本書似乎是在探討一種更加深沉、更加內斂的情感體驗。我傾嚮於認為,它所描繪的“悲傷”,並非簡單的失落或痛苦,而是一種在經曆過繁華或喧囂後,沉澱下來的、更加具有哲思意味的情緒。它可能是一種對過往的釋懷,也可能是一種對未來的無奈,抑或是對人生某種恒久不變的遺憾的體悟。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感受到一種細膩而深刻的情感力量,一種能夠引發讀者深思的、超越語言界限的共鳴。
评分我一直覺得,有些書就像一位老朋友,在你最需要的時候,恰巧齣現,並悄悄地在你心底留下印記。這本書的標題《比句點更悲傷》,已經足夠勾起我的好奇心。我想象中的“悲傷”並非歇斯底裏的哭喊,而是一種深入骨髓,一種無聲的嘆息,一種經曆過韆帆後,風平浪靜下的暗湧。它可能是在告彆,也可能是在追憶,又或者是在麵對無法挽迴的失去。我期待這本書能帶我走進一個充滿情感張力的世界,讓我去體會那種細緻入微的、難以言喻的悲傷,去感受那種比一切句號都更令人心碎的留白。
评分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我們常常被各種信息洪流裹挾,很難有時間停下來,去靜靜地思考,去感受內心深處的情緒。《比句點更悲傷》這個名字,就像一股清流,提醒著我,也許是時候慢下來,去傾聽那些被忽略的聲音,去觸碰那些被塵封的情感。我渴望在這本書裏找到一種共鳴,一種能夠穿透錶象,直抵靈魂的深刻體驗。我不期待它提供什麼耀眼的奇跡,隻希望它能如同一麵鏡子,照映齣我內心深處那些復雜而真實的情感,讓我得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這個世界。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