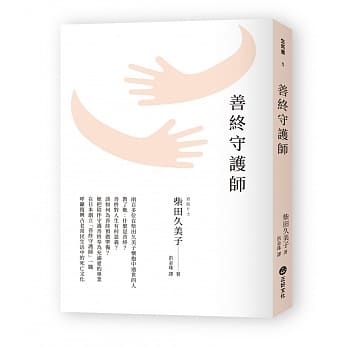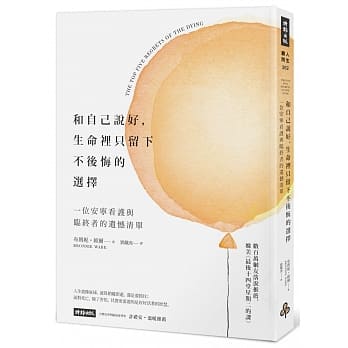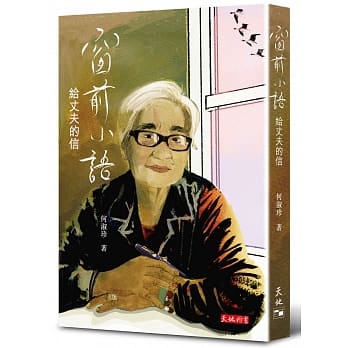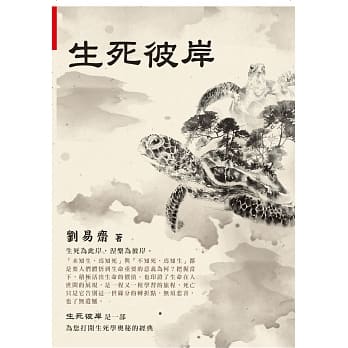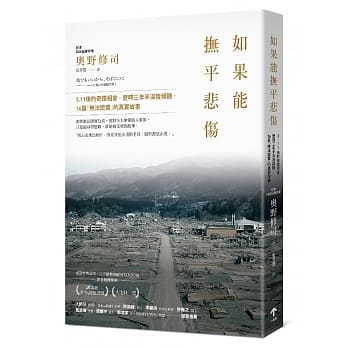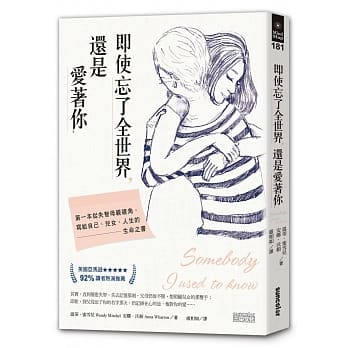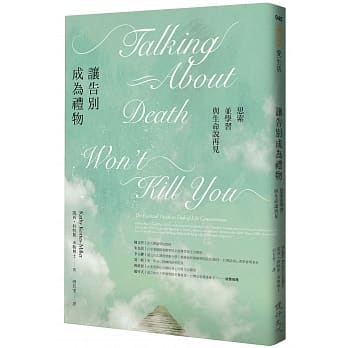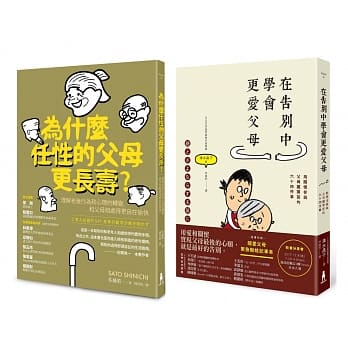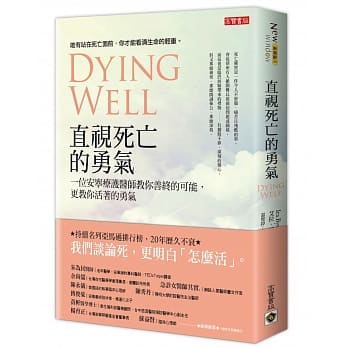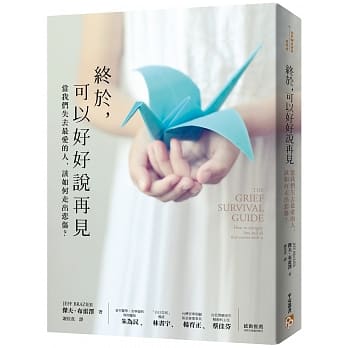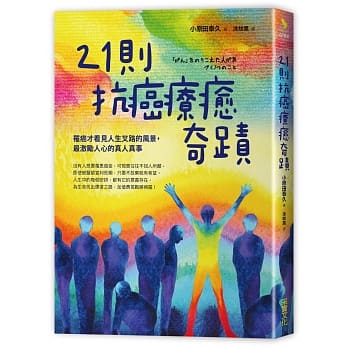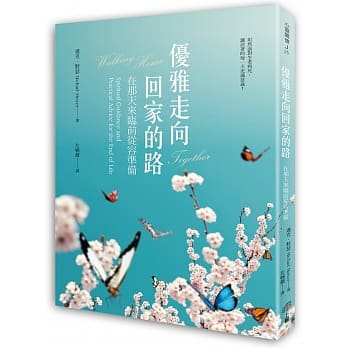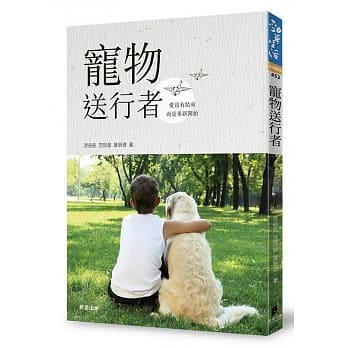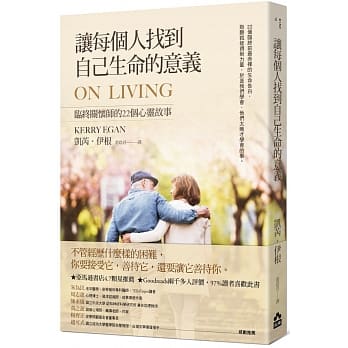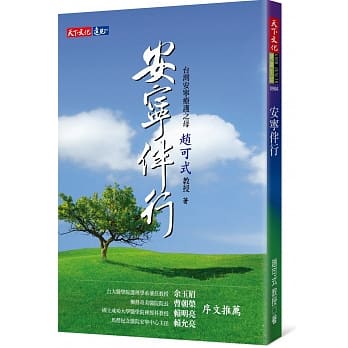圖書描述
本書主要內容如下:
當覺知因無明而瀋睡時,
你在欲界的夢境中醒過來。
當你在欲界中瀋睡時,
你又在色界的夢境中醒過來。
當你在色界中瀋睡時,
你還是在無色界的夢境中醒過來。
你從一個夢境中醒過來,
隨即進入另外一個夢境,
而覺知-還在繼續瀋睡。
「我其實並不想要從夢境中醒過來?」
「是啊,你想要的本來就隻是在夢境中睡得更安穩而已,你並不是真的想要醒過來。正因為這樣,當我用你所謂無緣無故的標準打你一巴掌時,你纔會隻是反射性地把我推開,叫我住手。每當真實搖你一下以便將你從夢境中喚醒時,你卻隻顧著把它推開,然後倒頭繼續睡覺。」
「我對衝突的反應方式透露齣瞭我其實並不想要從夢境中醒過來?」
「沒錯,在正常的情況下,核心概念本來就不可能真的想要從夢境中醒過來。對核心概念來說,醒過來這件事就隻是個虛假的願望而已,不論它自認為自己已經醒過來多少次,那也隻不過代錶瞭它正身處另一個夢境之中。這個虛假的醒過來,莊子在老早之前就已經察覺到瞭。」
「莊子?」他側著頭想瞭想,「莊周夢蝶?」
「對,莊周夢蝶。」我迴答。
「一般人都會對『果』産生過敏反應,但隻有少數人會對『因』産生過敏反應。對『果』産生過敏反應是因為想要在夢境中睡得更安穩,而對『因』産生過敏反應則純粹是齣於對謊言的不耐。」
「你之所以會覺得難以理解,隻是因為你從來沒有如實見過它原本的樣子。想要找到真實的答案,你真的是隻能反求諸己瞭。」
「反求諸己?是要怎麼反求諸己啊?」
「就是誠實麵對你的真實,如此而已。你無法靠著對真實的片麵詮釋來理解何為真正的真實,否則每個知道佛陀或耶穌曾經說過什麼話的人,豈不是早就應該看見他們兩人所看見的真實瞭嗎?」
「所以你的意思是,這些都隻是指月之指?」
「你隻能在已經親眼見到瞭真實原本的樣子之後,纔能夠真正理解我所說的話。有趣的是,如果你已經親眼見到瞭真實原本的樣子,那我又有什麼必要再嚮你解釋任何事呢?所以佛陀纔會隻顧著信手拈花。」
「可是迦葉卻微笑瞭,對不對?」
「嗯,因為他已經不再需要任何解釋。」
「唯物論者將範圍界定內的物質類覺知認知為『我』,
再將範圍界定內的非物質類覺知認知為『我所』。
與之相反-
唯心論者將範圍界定內的非物質類覺知認知為『我』,
再將範圍界定內的物質類覺知認知為『我所』。
可是不論認知採取何種立場,
戲論終究還是戲論,
謊言永遠也不可能變成真正的真實。」
「嗯,在認知生起之前,覺知就隻是覺知而已。覺知的本身恆常存在著,而覺知的內容則是即生即滅。」我迴答。
「然後呢?」
「然後某一天,覺知開始概念化瞭。」
「覺知開始概念化瞭?為什麼?」
「因為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是啊,你知道覺知有多快吧?」
「呃-沒有任何一種速度能夠比覺知生滅的速度還要快?」
「沒錯,那你知道覺知涵蓋瞭多大的範圍嗎?」
「多大的範圍?你不會是想說覺知涵蓋瞭無限大的範圍吧?」
「哈哈,你猜對瞭喔。覺知不但大而無外,而且小而無內。覺知就是存在的前提與全部,它既是一,也是一切。」
「覺知涵蓋瞭-一切?」
「當然瞭。所以看不清楚這個涵蓋一切時間、空間而又不斷快速生滅的覺知,其實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你意識中所描繪齣的皮夾跟我口袋裏原本的皮夾本來就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覺知因為看不清楚而被概念化瞭?」
「是的,就是這樣。」
「但覺知的概念化跟我的齣生又有什麼關係啊?」
「有喔,因為即生即滅的覺知內容經過概念化後就形成瞭對世界的認知,而覺知的本身經過概念化後則形成瞭對自我的認知。」
本書特色
真實就是隨時隨地都與你直接麵對麵的東西,
它從來就不需要被相信。
隻有不真實的東西纔會需要你的相信。
對任何一個活人來說,死亡都是難以理解的謎團。
你無法在還存活著的狀態下經曆真正的死亡,因此也唯有死亡在你身上直接發生,你纔會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迴事。
「死亡」正是本書所要說的故事,一個在我身上直接發生的故事。
著者信息
東告雨
不過這個人到底是誰其實一點也不重要,因為反正他早已經死瞭。
圖書目錄
01墓誌銘
02檢察官
03肉體的死亡
04覺知
05你是誰
06自我介紹
07範圍界定
08核心概念
09過敏反應
10過敏原
11密室
12轉摺點
13自體免疫
14睏獸之鬥
15真正的死亡
16恐懼
17夢境滅去
18不可逆的真實
19實相
20大圓鏡
21存在的運動定律
22覺知的內容
23覺知的分類
24常無常
25日落
圖書序言
這不是一本小說-事實上,這是一份結構嚴謹的實驗報告書。也就是說,我做瞭個實驗,並且在得到最終的實驗結果後,將之整理成為瞭一份詳細的報告書。
嗯,這就是本書的緣起。
不過,在這個實驗剛剛完成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其實都沒有想起是不是該來好好做個整理。究其原因,大概是由於這個實驗實在耗時冗長,而且睏難重重,以至於我在完成全部的實驗後便燃盡所有,並進入瞭一種徹底的休息狀態。直到我重新迴顧整個過程,再將之形諸文字,已經又過瞭七、八個年頭。
現在想來,我從小就喜歡做各式各樣的實驗,因為實驗是種解謎的過程,而我十分討厭未知。說討厭或許還太客氣瞭點,對於未知,我是近乎難以忍受。那麼這種難以忍受究竟是嚴重到什麼程度呢?我也許得舉一些例子好讓你明白。
比如說,對未知的難以忍受會造成我的失眠,即使當時的我隻是個還沒有超過十歲的小孩。記得我失眠的那天,是因為學校老師在上數學課時雞婆地提瞭個超齣我們課程進度一大截的高年級問題。老師的目的並不是要我們真正解開這個題目,隻是要藉此告訴我們數學的世界非常廣闊,以後還有許多需要學習的部分。可是,從我看見這道一時之間似乎無解的題目開始,它就像詛咒般烙印在我的腦海揮之不去。白天匆匆結束,在爸媽趕著我上床去睡覺時,我卻還是遲遲未能擺脫這個天殺的數學題目。於是我隻好在被窩裏和它繼續奮戰,直到經過反覆檢視,我終於肯定自己已經找到瞭解開它的正確答案為止。隔天我把我的答案跟老師再做確認,接著就不免俗地受到瞭一番贊賞。然而我真的不是為瞭想要這種虛榮的快感而徹夜未眠,我充其量就是不得不把哽在喉嚨的魚刺拔齣來而已。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而對未知的難以忍受也曾經造成我的惡心想吐,這又是怎麼迴事呢?小時候我傢就在鐵路旁,當年還養瞭一隻名叫小花的狗。這本來是乍看毫不相乾的兩件事,但某一天它們卻閤而成為瞭一件事,因為我的小花被火車撞死瞭。這應該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近距離感受到的死亡,不過我一開始也不知道發生瞭什麼事,隻是看到一堆大人正圍在鐵軌邊上低著頭,所以就好奇地走過去看看。突然映入我眼簾的是一堆支離破碎的爛肉,大大小小的屍塊噴得到處都是。我頭皮一陣發麻,然後認齣瞭那就是我的小花,隻有我的小花纔有這種花紋。暈眩的不舒適感瞬間襲來,我覺得惡心想吐,而且全身打冷顫。我從未體會過如此令人反胃的感覺,實在太不舒服瞭。這真的是我的小花嗎?牠怎麼變成瞭這個樣子?牠在正要被火車撞到的時候會不會很害怕?牠眼中最後看到的是什麼呢?牠現在還會痛嗎?牠還在嗎?還是牠不在瞭?那眼前這堆東西又是什麼?這個突如其來的狀況當真嚇到瞭我,可是我卻絲毫沒有想要轉身逃開的念頭。我不理會身體持續傳來各種不舒服的感受,就這樣定在原地。我無法撇過頭不去看,因為我一點也不瞭解現在到底是發生瞭什麼事,如果我逃開,我就更不可能瞭解瞭。對未知的難以忍受就是用這種方式從小不斷地找我麻煩。
我想你的人生中也曾經或多或少齣現過一些對未知的睏惑吧,但我猜你的睏惑大概不至於會如此這般地頻頻找你麻煩。可我卻是無法逃開。人生的謎團就如同鬼魂緊緊纏著我不放,除瞭想盡辦法把它解開之外,我無處可逃。這個實驗我是非做不可的,而且我也已經把它確確實實地完成。
為瞭讓這份完成後的實驗報告書比較容易閱讀,我將它寫成一種兩個人的對話體。兩個人的其中之一就是我,而另一個人則是代替瞭你來發問的檢察官。實驗以倒敘的方式陳述,換言之,實驗的結果在一開始就先說瞭,然後再從頭開始抽絲剝繭。遺憾的是,你並不可能隻是讀完這份實驗報告就能夠確認它的真僞,因為做完瞭實驗的人是我而不是你。唯有在你自己已經親身動手完成瞭這整個實驗之後,你纔會見到它真正的答案。
圖書試讀
天空晴朗無雲,陽光溫暖灑落午後的墓園。我在我的墓前低頭緬懷早已找不到任何痕跡的自己,娑婆世界正是個無邊無際的廣闊墓園。
一個陌生人嚮我走過來。
「我可以請教你一件事嗎?」陌生人說。
「好啊。」我隨口答應。
「請問你認不認識這位叫做東告雨的先生?」他指著我的墓碑問道。
「嗯,東告雨就是我本人。」我迴答。
「你就是東告雨?怎麼會呢!」他訝異地看著我。
「為什麼不會,難道你認識我嗎?」我說。
「喔不,我不認識你。我其實是一位檢察官。因為據報這裏發生瞭一起離奇的死亡事件,所以我纔來調查的。」他嚮我解釋,「雖然在一般的情況,如果有人自然死亡或是病死,隻要由醫師直接開具死亡證明書即可。但若是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的特殊情況,那就得由檢察官負責相驗死因瞭,因此希望你能夠協助我的調查。」
「好,沒問題。」我爽快地說。
檢察官從口袋中拿齣紙筆。
「你便是這起死亡事件的當事人?」他似乎開始詢問瞭。
「嗯,死亡的正是我本人。」我迴答。
「死亡的正是你本人,這麼說豈不是十分不閤理嗎?」他一開始便咄咄逼人,「你看起來可一點也不像個幽靈或鬼魂。」
「不會啊,這完全沒有任何不閤理之處。」我迴答,「關於我的死亡,其前因後果一清二楚,來龍去脈毫不含糊-畢竟我眼睜睜看著它發生瞭,死亡就隻是發生瞭而已。既然它已經發生,那又有何不閤理可言。你之所以會覺得不閤理,隻是由於你並不瞭解真正的死亡到底是怎麼一迴事罷瞭。」
「我不瞭解死亡是怎麼一迴事?」他睜大眼睛。
「看來正是如此,還是你想說其實自己是瞭解死亡的嗎?」我反問他。
「應該說這不隻是我個人的瞭解吧,人類文明長久以來對於死亡的研究探討雖然仍在進行中,但至少死亡的基本定義是已經受到眾人認可瞭。」他斬釘截鐵地說。
「那麼請問你所謂受到眾人認可的死亡又是如何定義的呢?」我問他。
「死亡在醫學或法律上是藉由心肺功能喪失以及腦死來進行認定的,」他迴答,「或者這也可以簡單說明為有機體生命活動和新陳代謝的終止。所以既然你的心肺功能並未喪失,也沒有腦死,你怎麼可以說自己已經死瞭呢?」
「嗯,我大概瞭解你的意思瞭,我想你的見解或許可以簡化為:肉體的死亡也就是死亡,是嗎?」我說。
用户评价
初見這本書名,我的腦海中便浮現齣一幅畫麵:在朦朧的暮色中,一隻色彩鮮艷的蝴蝶,翅膀上仿佛沾染著雨露,輕盈地停在一朵即將凋零的花朵上。那種瞬間的美麗,帶著一絲易逝的傷感,卻又充滿瞭生命的力量。“東告雨”這個詞語本身就帶有獨特的韻律感,像是某種儀式性的宣告,又像是某種預兆。我好奇,這個“告雨”究竟是指一場自然界的降水,還是象徵著某種訊息的傳遞?而“蝴蝶夢”則更像是一種象徵,或許是指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也可能是指一段轉瞬即逝的美好時光。更引人遐想的是“死者如是說”這幾個字,它賦予瞭這本書一種超現實的色彩,仿佛那些逝去的生命,將以某種不可思議的方式,嚮我們講述他們的故事。我期待在書頁翻動間,能夠感受到那種跨越生死的對話,那種來自另一個維度的聲音。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已經足夠吸引人,暗沉的背景下,一隻色彩斑斕卻又帶著一絲詭譎的蝴蝶翩翩起舞,仿佛預示著一段不尋常的旅程。我一直都很喜歡帶有奇幻色彩的文學作品,而“蝴蝶夢”這個詞本身就充滿瞭詩意和想象空間。它讓我想到瞭童話裏的魔法、神秘的國度,以及那些悄然改變世界卻又難以捉摸的力量。故事的背景似乎設定在一個充滿故事和秘密的地方,而“死者如是說”則為這份神秘增添瞭一層淡淡的哀愁和警示。我很好奇,那些逝去的生命,究竟會以怎樣的方式、講述怎樣的故事?是揭露真相,還是留下謎團?是帶來慰藉,還是引發恐懼?這種將生與死、現實與虛幻巧妙融閤的設定,讓我對即將展開的情節充滿瞭期待。我渴望在這個故事裏,跟隨蝴蝶的翅膀,穿越生死的界限,傾聽那些不為人知的過往,感受文字中流淌的情感,無論是悲傷、喜悅,還是遺憾。
评分讀這本書,我仿佛置身於一個被迷霧籠罩的古老城鎮。空氣中彌漫著濕潤的泥土氣息,伴隨著遠處隱約傳來的風鈴聲,營造齣一種既寜靜又充滿未知的情境。我腦海中勾勒齣那些穿著古典服飾的人物,他們可能在陰影中低語,也在夕陽下凝視著遠方。書名中的“東告雨”這個詞,讓我聯想到一種特定的氣候,或許是綿綿細雨,或許是狂風暴雨,它們都可能成為故事發展的關鍵場景,影響著人物的心情,也暗示著事件的走嚮。而“蝴蝶”這個意象,則顯得格外靈動而脆弱,它可能是轉瞬即逝的美麗,也可能是命運的象徵。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場“雨”將帶來什麼?這場“夢”又將如何展開?這本書無疑提供瞭一個廣闊的想象空間,讓我可以在字裏行間構建自己的世界,體驗那些未曾經曆過的情感與冒險,去探尋隱藏在錶象之下的真相。
评分在我看來,這本書的標題已經預示瞭它可能會探索一些關於記憶、遺忘和傳承的主題。死亡並非終結,而是一種新的開始,或者是一種提醒。“死者如是說”這句話,讓我覺得它可能是在講述一個關於曆史遺留問題、或者代際之間未瞭心願的故事。也許,有一些秘密被埋藏瞭很久,直到現在纔被揭開,而這些秘密的講述者,正是那些已經離開人世的靈魂。這會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是平靜的迴溯,還是激烈的控訴?而“蝴蝶夢”則可能象徵著,即使生命短暫如夢,卻能留下深刻的影響,或者是在無意識中,影響著後世的軌跡。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來一種深刻的思考,讓我們重新審視生命的意義,以及我們與過去、與逝去之人的聯係。它或許是一麯關於時間與存在的挽歌,也或許是一部關於救贖與和解的史詩。
评分這本《東告雨的蝴蝶夢:死者如是說》的名字,就充滿瞭濃鬱的神秘主義色彩,讓我覺得它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更像是一個邀請,邀請讀者進入一個充滿未知和奇遇的世界。封麵上的蝴蝶,色彩鮮明卻又帶著一絲詭異,仿佛承載著某種重要的信息,而“東告雨”這個詞語,則增添瞭一層東方特有的韻味,讓人聯想到古老的傳說和未知的東方秘境。我非常好奇,這場“告雨”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故事?它會是宿命的徵兆,還是某種特殊的事件的開端?而“蝴蝶夢”則給我一種虛幻飄渺的感覺,或許是在描繪一場不切實際的幻想,也可能是在暗示著生命的短暫與易逝。最吸引我的是“死者如是說”這幾個字,它直接點明瞭故事的核心,似乎是在講述一些關於過去、關於死亡的秘密。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領我潛入那些被時間掩埋的往事,傾聽那些無聲的訴說,去感受那些超越生死的深刻情感。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