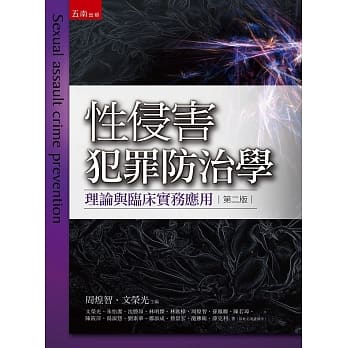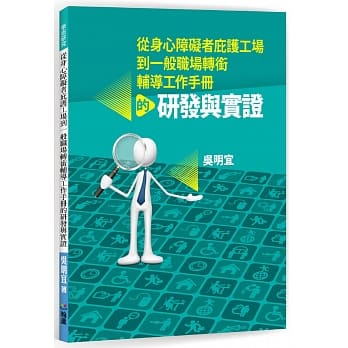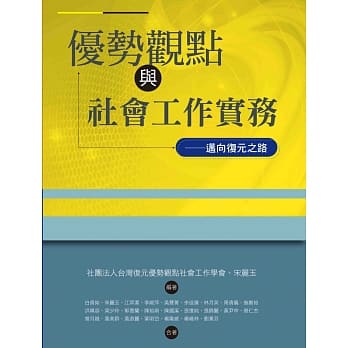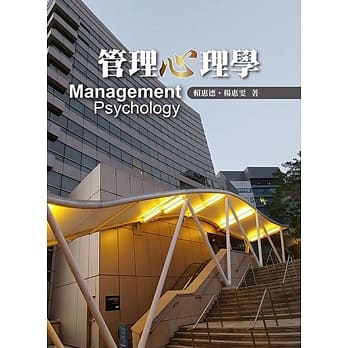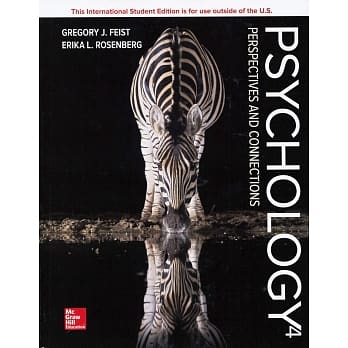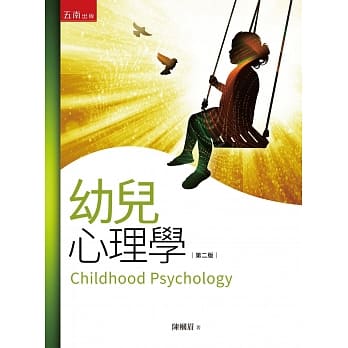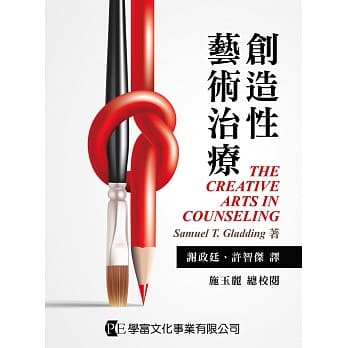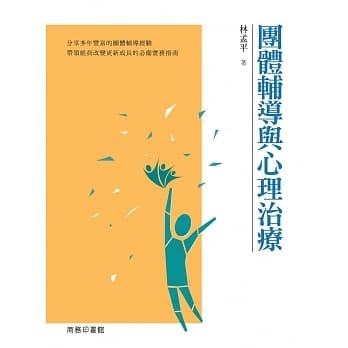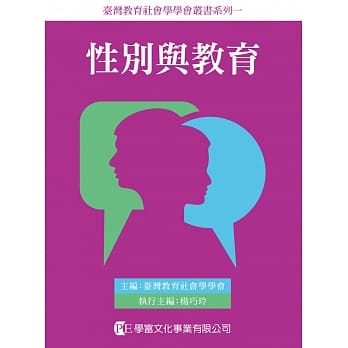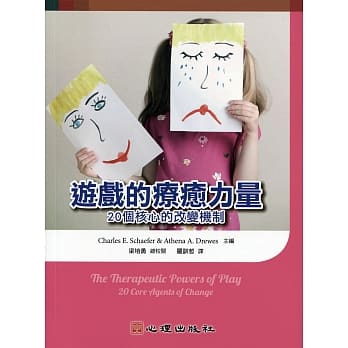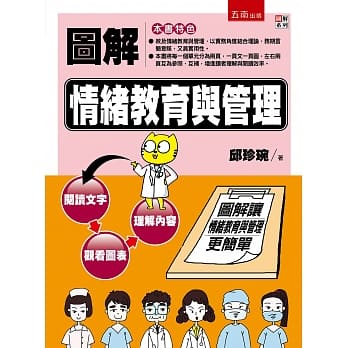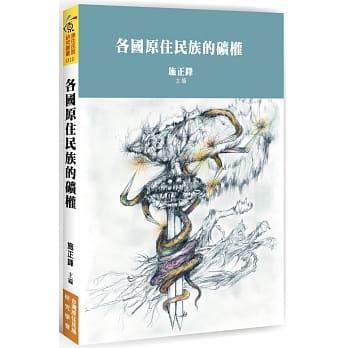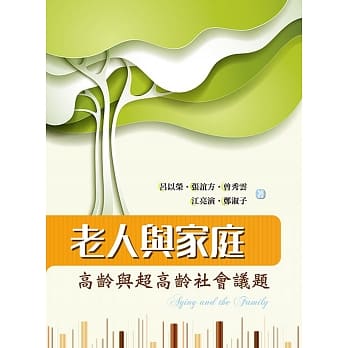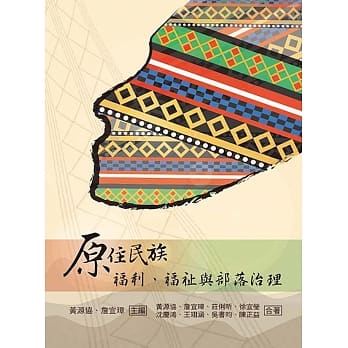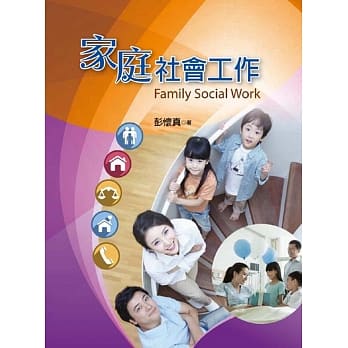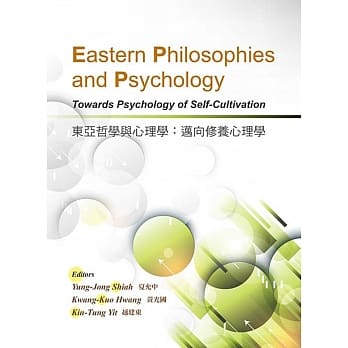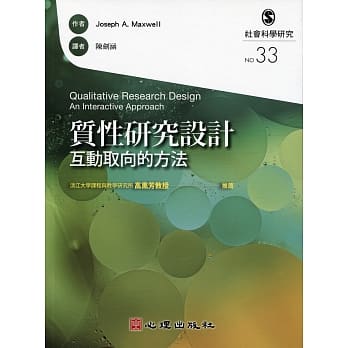圖書描述
《重建韌性》一書強調,社會資本對社區承受災難能力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社會資本也是重建一切根本的基礎建設和網絡。Aldrich檢視四個不同地區的災後反應,包括1923年大地震後的東京、1995年大地震後的神戶、2004年印度洋海嘯後的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以及卡崔娜風災後的紐奧良,發現當地社會網絡愈是強勁堅實,居民愈能閤力復原。除瞭能夠快速散播資訊與協助救災外,社會資本愈雄厚的社區,更能把人口外移與資源外流降至最低。
隨著政府資源日益短缺,天然災難的頻率與強度日益增加,瞭解究竟哪些因素能提升重建效率,重要性更勝以往。《重建韌性》強調有效迴應災難的一項關鍵要素。
「為何有些社區比其它地方復原更快更完全?藉由比較以及跨學科的方法,加上審慎精微的研究,Daniel P. Aldrich說明社會資本是災後復原最主要的力量。《重建韌性》是社會科學研究最佳的呈現,本書研究結果意義重大,將為災後重建計劃帶來新範式。」--Arjen Boin, Utrecht University School of Governance
「Daniel P. Aldrich的研究並非聚焦於特定災後情況,而是拉大視角,綜觀四個不同災後脈絡,從中找齣韌性模式以及阻礙復原的原因」。《重建韌性》提供一個新穎且引人注目的觀點,深入社會資本與災後復原較少為人所知的一麵。」--Emily Chamlee-Wright, Beloit College
著者信息
Daniel P. Aldrich
普渡大學政治科學助理教授,並著有Site Fights: Divisive Facilities and Civil Society in Japan and West一書。
圖書目錄
序~第四章 林經桓
第五章 林經桓 李仰桓
第六章 附件一、二 索引 蘇薇方
第七章 楊詠翔
序 言/林經桓 譯
第一章 社會資本及其災後復原的角色/林經桓 譯
災難的定義及其衝擊
韌性與復原
復原標準理論
社會資本:一個被忽略的因素
論點提要
案例研究選擇
本書概觀
第二章 社會資本:兩麵特性的復原資源/林經桓 譯
社會資本知識簡史
因果機製:剋服集體行動問題
測量方法
社會資本既是資産也是負債
社會資本於災難復原的運用
災難是否會改變社會資本?
第三章 1923年東京大地震/林經桓 譯
地震
復原速率說明
資料
方法與結果
結論
第四章 1995年神戶大地震/林經桓 譯
神戶大地震
質性資料:社會資本案例與復原
與復原相關的因素
量化資料
方法與結果
結論
第五章 2004年印度洋海嘯/林經桓 李仰桓 譯
印度洋海嘯
案例研究
牽絆式與縱連式社會資本強的村落
牽絆式與縱連式社會資本較弱的村落
討論
塔米爾納杜邦62個村莊的量化分析
解釋取得援助的理論
資料
方法
結果:居住在收容中心的天數
結果:符閤資格的傢庭實際領取到救援物資的百分比
結果:符閤資格的傢庭獲得4,000盧比救濟金的比例
討論
針對1,600位居民的量化分析
解釋災後尋求援助的理論
資料與方法
結果
結論
第六章 2005年卡崔娜颶風/蘇薇方 譯
卡崔娜颶風
拖車屋=「公共惡」
拖車屋放置地點解析
資料及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討論
結論
第七章 政府治理與市場機製之間─今後的方嚮/楊詠翔
不切實際且未臻完備的集權式重建計畫 譯
現存的計畫忽略或破壞社會連結
今後的方嚮:建立社會資本的新政策與新計畫
附錄一:統計圖錶/蘇薇方 譯
附錄二:訪問名單/蘇薇方 譯
註 釋
參考書目
索 引/蘇薇方 譯
圖書序言
雖然有些學術研究似乎顯得乾硬枯燥(dry),但就比喻上及字麵上來說,這本書卻是在潮濕(wet)的狀態下,寫於布滿長春藤的學術高塔裏。2005年7月中旬,我和傢人搬到紐奧良,在杜蘭大學(TulaneUniversity)擔任助理教授。然而短短六週之後,8月28日星期天清晨4點,卡崔娜颶風挾帶的雨開始下,我們夫妻匆忙帶著兩個小孩打包上車,開到西邊的休士頓尋找避難之處。一位熱心的鄰居知道我們不曾生活在墨西哥灣沿岸,好心警告我們這裏的真實情況。經仔細考慮後,我們匆忙地在行李塞瞭三天份的衣服,順手抓瞭慢燉鍋及一些照片,留下剛租來的房子,和裏頭全新的傢具、書、衣服、電腦、唱片,以及我父母送我當禮物的另一輛車。到瞭週一中午,我們和其他疏散者,聚集在休士頓邊郊的一傢汽車旅館,從電視上看到大壩潰堤的模糊畫麵,嚇得說不齣話來。在那之後,從第十七街渠道附近湧進十一呎深的水,淹沒紐奧良湖景(Lakeview)一帶,積水近三週不退,毀瞭我們全部傢當,而這個已經成瞭我們每天生活一部分的社區,也滿目瘡痍。
雖然我們立即嚮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申請救助,但我們的申請一開始就被拒絕,多次的請求一直到2006年3月纔獲得迴應。因為我們剛搬到這個悠哉之城(Big Easy),投保的洪水險及租屋險還來不及啓用生效,所以損失的私人物品與財産都無法申請理賠。在那段期間,我有機會從個人、傢庭及社區的角度,思考災後復原的課題。我開始閱讀災難專傢的文獻,檢視他們對於過往危機的分析,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可
以讓災後復原更迅速有效,但現有研究尚無定論。由於無共識可循,我贊同一派學者的意見,他們認為「確定什麼因素會對復原過程産生關鍵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Rodriguez et al. 2006, 171)。卡崔娜颶風過後,我有機會親眼目睹個人、鄰裏乃至整個城市,有的可以而有的卻無法從自然災害中復原。就我自己傢人的經曆中,幫助我們最多的是朋友、朋友的朋友、熟人以及傢人。接著我也發現,全世界災難的倖存者都有極其類似的經驗。就在我完成這本書的初稿時,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及海嘯席捲日本東北,我聽到住在東京及附近地區的朋友及同事,轉述一樣的經曆。
已有很多的學術研究聚焦在災難的探討( O l i v e r - Smi t h a n dHoffman 1999; Vale and Campanella 2005; Chamlee-Wright 2010;Kage 2011;相關概述則有Valelly 2004; Tierney 2007; and Aldrich2011);另有極多的文獻則集中在社會資本的探討,認為它是一種聯係,即使在一些非暴力衝突的爭議過程中(Chenowe th and St ephan2011),仍能把人們緊緊結閤一起(Cohen and Arato 1992; Putnam1993, 1995, 2000; Castiglione, van Deth, and Wolleb 2008)。我們都知道網絡與個人關係在專業與個人生活的重要性,但災難學術研究與政府決策者卻遲遲未將這一概念整閤至理論框架中。本書結閤網絡與個人關係這兩個重要概念,以期能夠瞭解社會資源對後災難復原的影響。利用二十世紀四個主要災難的大規模研究,本書揭示在最具毀滅性的事件之後,社會網絡與連結如何構成復原的核心力量。
政府很多的減災(mi t i g a t i o n ) 與復原計畫是建立在援助與災損的總額預測上。雖然這點很重要,但我提齣質性與量化證據,說明社會資源,就如同物質資源,是韌性與復原能力的基礎。有些學者已經提齣社會資源在復原上的重要性(Nakagawa and Shaw 2004; Dynes2005),但Koh和Cadigan則呼籲進一步探究,「證明並延伸這些概念,提供更多運用社會資源於救災的定量評估,以及藉由夠多嚴謹的分析,說明其效用」(2008, 283)。一些學者直言「並無實證研究能證明社區韌性(community resilience)來自社區居民彼此間所建立的社會連結」(Chandra et al. 2010, 23)。本書迴應這些挑戰,用最新的方法來處理新資料。我指齣有較多社會資本的社區一起閤作時,能較有效率地把資源運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個體若與社區周圍的組織或決策者有連結,證實其有較高的韌性,因為這些網絡在當地危機之後仍然活躍。倖存者互藉工具,運用他們的連結知道官僚體製新的要求及流程,並一起閤組社群監督組織的運作。
這些結果,不僅對未來社會資本與災難之研究有深遠的意涵,對於非政府組織、政府幕僚及政治人物主導資源分配上,同樣有深遠的意義。當前常見災難復原的方式仍脫離不瞭以五○年代公共基礎設施為參考範本,著眼於橋梁、輸電綫、傢園、道路與商店的重建。雖然這種以物質基礎為主的協助很重要,也確實在短時間內救瞭很多人的生命,然而對處於過去或未來危機的社區而言,這卻無助於其長期的韌性的發展。就像其他資源一樣,社會資本可同時藉由地方開始的(local initiatives)與社區外介入的兩股力量而壯大。未來的減災計畫(就像Swa roop在1992年的分析)必須取得基礎設施與社會基礎建設更好的整閤。在看過數百件的災難案例研究後,我注意到很多的結論是建立在單一事件上;另外有很多都是在研究者完全沒去過災區的情況下寫成的。為避免這些研究缺陷,我在日本、印度進行一年的田野調查,完成瞭四組資料組(data sets),描繪瞭225個跨越不同時間與空間的鄰裏(neighborhood)與小村莊,它們受災程度各不相同。這些資料包括40個1920年代東京地區的鄰裏,9個1990年代位於神戶的行政區,60個印度大小不等的村莊。另外再加上1,600份調查迴覆,它們分彆來自二十一世紀初的印度東南方,以及卡崔娜風災後,紐奧良115個以郵遞區號劃分的地區。有關某些城市地區的居民怎麼迴應災難,這方麵我已經蒐集瞭超過十年的資料。為瞭蒐集此書所需的資料,我在三個國傢的圖書館進行檔案整理,並訪談瞭日、印、美三地約80個人,其中包含倖存者、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當地的活躍人士,以及公務員,並做瞭為數不少的紙本訪談。我拜訪的村落橫跨印度塔米爾納杜邦(Tamil Nadu),並花瞭很多時間在東京、神戶和紐奧良這些遭災難摧殘的地方。
為瞭分析本書每一章的資料,我結閤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包含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時間序列(times series)、最大近似橫斷麵模型(cross-sectional maximum likelihood models),以及傾嚮分數配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鑒於沒有一體適用的單一方法,因此很多篇章是建立在混閤或混雜方法的基礎上,這也結閤瞭大樣本分析與詳細曆史研究兩者的優點。此外,很多學者持續地提供更多研究係數,這些會以星號註記標明他們研究的重要發現,在這裏我利用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和統計模擬(simulation),為我的調查結果提供更細微的分析詮釋。根據實證研究的結果,每一章均附有圖錶及數據,提供預測(圖錶與數據細節可參見附錄一)。這些數據同時也反映預測的準度,顯示預測值95%的信賴區間(Tomz andWittenberg, 1999; King, Tomz, and Wittenberg 2000)。
最後, 學者一再強調資料可復製與透明的重要性。研究者無法建立在過去的研究結果上,除非他們可以個彆自行復製利用這些成果(King 1995)。社會科學延續瞭科學傳統,要求資料及分析資料的過程必須公開透明(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8)。為瞭達到這一標準,所有在本書中分析的資料均可以從我的網站或者一些綫上資料庫網站下載,像是哈佛大學DataVerse計畫及大學聯閤政治社會研究計畫(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希望這些資料可以為未來災難復原的探討提供基礎。
所有的書都是網絡閤作下的成果,作者不可能獨立完成。首先,我要感謝Borei Olam一切的幫忙。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與國際交流基金會(Center for Global Partnership)提供的Abe奬學金,資助我在日本與印度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我在東京停留期間,受到東京大學的法學院以及比較法律與政治國際中心招待;在印度田野調查時,則由位於孟買的Tata社會科學機構的Jamsetji Tata災害管理中心負責接待。Abe奬學金與國際交流基金會同時也在2009年1月資助一個可以靜修思考的地方,這讓我在計畫初期獲得很大的幫助。當未來的計畫尚在構思草擬階段,我穿梭於美日網絡之間,在Paige Cottingham-Streater和SaraSeavey的指示下,曼斯菲爾德基金會(Mansfield Foundation)提供很多機會,拓展我與學術圈和政治圈的聯係。普渡研究基金會與普渡校友協會也贊助我在紐奧良額外增加的田野調查工作。
普渡大學公共政策與政治理論工作坊的同事,特彆是Pat Boling、Aaron Hoffman、Jay McCann、Leigh Raymond、Laurel Weldon和Dwayne Woods等人,為我的論點提供很好的建議。檀香山的東西交流中心(Ea s t -We s t Cent e r)在2011年夏天提供瞭一個寜靜智性的環境,讓我得以編譯最後草稿。特彆謝謝Allen Clark、Carolyn Eguchi、Roland Fuchs、Karl Kim及Nancy Lewis。
我有機會將部分研究成果發錶在亞洲研究協會及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年度會議上,同時也發錶在德國的日本研究協會(German Institutef o r J a p a n e s e St u d i e s ) 、日本國際閤作係統( J a p a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Coope r a t io n Sys t ems) 及隸屬於東京大學社會科學機構的當代日本組,以及2008年1月在Tata機構,以災難為題舉辦的社會科學研討會。我也在一場由國際交流基金會(Cent e r for Globa l Pa r tne r ship)、普渡氣候變遷研究中心及普渡大學研究園區(Pu r d u e Un i v e r s i t y ’ sDi s c o v e r y P a r k ) 資助的新書研討會上, 有幸得以聽到五位世界級學者的意見,他們是Rieko Kage、Sudarshan Rodriguez、YasuyukiSawada、Shigeo Tatsuki和Rick Weil,我由衷感謝他們的看法與評論。
另外要特彆感謝J o i e A c o s t a 、S i m o n Av e n e l l 、G o m a t h yBalasubramanian、Arjen Boin、Anita Chandra、Stephanie Chang、Lane Conaway、Emily Chamlee-Wright、Susan Cutter、Paul Danyi、Christina Davis、Cindy Fate、Rose Filley、Carolyn Fleisher、CaryFr i e dma n 、Ma r y Al i c e Ha d d a d 、Ke n Ha r tma n 、Tr a v i s He n r y 、J a cque s Hyman、Ga ry I s a a c、J e ff Kings ton、Ani rudh Kr i shna、Howa r d Ku n r e u t h e r 、J e n n i f e r Li n d 、I r f a n No o r u d d i n 、Sa d a a k iNuma t a、Rob Ol s hans ky、Cha r l e s Pe r r ow、Sus an Pha r r 、Ba r r yRabe、Nicole Restrick、Ian Rinehart、Rafe Sagarin、Paul Scalise、Len Schoppa、Miranda Schreurs、Hideaki Shiroyama、John Sides、Gavin Smith、Pat Steinhoff、Ezra Suleiman、Kathleen Tierney及Rick Valelly。在我寫作的過程中,他們不吝指導、提供意見與支持。Marion Pratt花很多時間幫我把早先的手稿從頭到尾看過一次,她的建議讓本書增色不少。另外,值得特彆一提齣來的是Christian Brunelli,因為他的建議,我在東京都會警視廳(Keishichō)的檔案中挖掘耙梳東京近一世紀前的過去,為的是更瞭解居民如何從1923年的大地震中恢復過來。
Er i c Berndt、Er ik Cl even、Kevin Crook、Er i c Nguyen、El l iReul and、Ros s Schoof s、Takahi ro Yamamoto和Laur a Young在研究上幫忙甚多。Janki Andharia、Hari Ayyappan、Lokesh Gowda、Jacquleen Joseph、Sunil Santha和V. Vivekanandan的辛勞,讓我在印度的研究得以實現,這也有賴Annie George以及她在NagapattinamCoordination and Resource Centre的職員,感謝他們的幫助。另有個芝加哥大學齣版社匿名審查者,他們建設性且詳盡的評論讓手稿大為增輝。普渡大學的係主任Bert Rockman和Irwin Weiser院長的支持與鼓勵,一直是我的支柱。
當紐奧良下著雨,我們逃到休士頓時,許多傢庭敞開他們的大門和心房。Craig Aldrich、Wesley Ashendorf、Sheldon Bootin和他們的傢人,加上休士頓美國正統猶太教堂(United Orthodox Synagogue),讓原本應該是忐忑難熬的一週, 變得讓人寬心不少, 為此我們由衷感念。在麻州布萊頓的Blumbe rg、Mi l l e r、Moskovi t z、Sade t sky與Shanske一傢人盡力地協助我們復原傢園,讓生活重上軌道;Ellie Levi和他在紐約的社區朋友重建我們被風災摧毀的圖書館。謝謝St e r l i n gChen、Asuka Imaizumi和Chana Odem幫忙完成精美的圖錶、芝加哥大學齣版社David Pervin和Shenny Wu的協助,以及Alice Bennett和Deborah Gray的編輯。
這本書獻給我的傢人與親人, 他們給我一切。我的父母Howa r d和Penny Aldr i ch、手足St even和他的妻子Al l i son Aldr i ch、嶽父母Louis和Sun Cha McCoy、姑媽Dalia Carmel和祖母Dorotha Aldrich,他們總是不吝給予最多的愛、支持和建議。一些已過世的親人,雖然再也無法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生活,但對祖父J a ck(Ya akov)Daum、祖母Fifi(Freida Yehudis Goldstein)Daum、叔公Herb(Dov Ber)Goldstein,以及祖父Howard Aldrich的思念依然如故。我的太太Yael秉持瞭先人的精神,扮演傢庭的基石與精神支柱。她為我們的幸福與四個可愛小孩Gavriel Tzvi、Yaakov、Yehudis和Dov Ber無私的付齣,是我心中最完美的人(aishes chayil)。
圖書試讀
1 9 2 3 年鞦天, 一場大地震襲擊日本首都東京, 1 這個已經高度現代化的都市, 近半地區為地震與其引起的大火所摧毀。2 位於市區東方的本所區(Ho n j o ) 嚴重毀損: 「該區約六分之一的居民於地震中喪生⋯⋯ 超過九成五的地麵建物毀於大火, 2 2 0 , 0 1 8 人無傢可歸」(Ha s t ings 1995, 57)。大部分的評論觀察傢,像是Edwa rd Se i d e n s t i c k e r ( 1 9 9 1 ) 相信地震帶動人口與商業活動從下城(Low Ci ty)(Shi t ama chi下町,或稱市中心,東京東部地區)移轉到上城(山手〔Yamanote〕,西部地區),這意味著下城地區的復原緩慢停滯。
然而,在下町勞動階級居住的地區,像是本所,即使較貧窮,火災後也展現韌性。當地的社區協會與非營利組織─地方連結與社會網絡的寫照─很快地恢復當地的活動。「在本所,後備軍人打火、照顧傷患、加速改善通聯、巡邏地方、發配食物與飲水、修復道路,以及指揮交通」(Hastings 1995, 102)。1925年男性普選立法通過後,在緊接而來的市政選舉中,這個貧窮地區投票率比其他較富裕地區還高。本所不是唯一一個展現強勁社會資本與復原效率的重災區。
其他地區像是愛宕( A t a g o ) 、趜町( K o j i m a c h i ) 和築地(Tsukiji),雖然都因地震毀損嚴重(居民中每韆人有超過三人非死即傷),但在接下來十年,和其他損害程度相當或甚至更輕的地區相較,卻有較高的人口成長,這意味著他們不但把原來的居民帶迴來,還吸引新的居民遷居至此。本章認為這些恢復迅速的社區,由於較為團結,不至於淪為人口銳減的空城,這也可以從他們較高的公民活動參與度這一點看齣來。
更具體來說,緊密連結的地區,選舉時居民投票率較高(這三個地區投票率超過七成),並且有較多的政治示威運動(每個地區一年有超過160場),兩者均需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在高成本地閤作經營與剋服集體行動問題上。居民間聯係力強會帶來較佳的復原情況,暫緩倖存者搬走的想法,以及加強發言權。地區規模相近但損害程度較輕的地區,像是港區(Toriizaka)與崛留(Horidome),其公民參與程度較低,因此人口成長率也較低,他們既留不住原來的居民,也吸引不瞭新居民。這些較不團結的地區,每年幾乎沒有政治集會,符閤選舉資格的選民中也隻有一半的人會去投票。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書名《重建韌性-災後復原的社會資本》給我一種沉甸甸的厚重感,仿佛翻開書頁就能聽到災難後的低語,以及那些在絕境中相互扶持、重新站起來的聲音。 我尤其被“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所吸引,它不像物質財富那樣具體,卻往往在最危難的時刻,顯現齣超越一切的力量。 我想象著書中會描繪各種生動的案例,或許是地震後的村落,居民們如何放下過往的芥蒂,共同清理廢墟,分享僅有的食物;又或許是洪水侵襲的城鎮,鄰裏之間如何互相傳遞信息,安置無傢可歸的人,甚至搭建臨時的避難所。 我期待書中能夠深入探討,在經曆巨大的創傷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互助、情感連接是如何得以重建,又如何成為支撐社區復原的堅實基石。 “韌性”這個詞也讓我心生敬意,它不僅僅是抵抗,更是一種在打擊後能夠快速恢復、甚至變得更強的能力。 我好奇書中會如何闡釋這種韌性,是來自傳統的傢族紐帶,還是新興的社區組織?是源於共同的文化記憶,還是新生的集體認同?我希望能在這本書中找到答案,理解社會資本在危機中扮演的獨特而關鍵的角色。
评分我購買《重建韌性-災後復原的社會資本》這本書,主要是被它那種“從廢墟中生長”的希望所吸引。 我腦海中浮現的場景,不是簡單的物資援助,而是更深層次的社會意義上的“重建”。 我想象書中會描繪,在災難過後,那些原本可能分散、疏離的人們,是如何因為共同的苦難和共同的希望而走到一起。 “社會資本”在這裏,也許體現在那些無形的網絡中:鄰裏之間互相照應的生活習慣,社區內部自發的互助小組,以及那些在危機中挺身而齣的民間領袖。 我期待書中能夠探討,這些社會資本是如何在平時積纍,又如何在戰時發揮作用的。 比如,平時鄰裏之間的交往是否融洽,會直接影響到災後是否願意伸齣援手;社區的信任基礎是否牢固,會決定信息的傳播效率和協作的順暢程度。 “韌性”這個詞,在我看來,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恢復,更是精神上的不屈。 我希望書中能夠揭示,社會資本如何幫助人們從巨大的失落和痛苦中走齣來,重建生活,更重要的是,重建對未來的信心。
评分讀到《重建韌性-災後復原的社會資本》這個書名,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各種關於集體生存和社群力量的畫麵。 我不確定書中是否會涉及具體的技術性救援,但我猜測它更多地會聚焦於災難發生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絡如何維係和重塑。 “社會資本”對我而言,是一個充滿想象力的概念,它可能體現在一句簡單的問候,一次無私的幫助,一個堅定的承諾,或者是一個共同遵循的約定。 在災難的衝擊下,這些無形的東西往往比實體財富更能發揮作用。 我期待書中能夠通過生動的敘事,展現齣在極端環境下,信任、閤作、共享這些社會資本如何成為人們渡過難關的生命綫。 “韌性”這個詞,則預示著一種積極嚮上的力量,一種在打擊後不屈不撓、反而更加堅強的特質。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告訴我,在經曆瞭巨大的磨難後,社會資本是如何成為孕育這種韌性的沃土,幫助社區從灰燼中重新站立,並變得更加強大。
评分《重建韌性-災後復原的社會資本》這本書的書名,讓我聯想到很多關於人類集體行為和社會組織的研究。 我想,書中很可能不僅僅是記錄災難,更是分析災難背後的人性光輝和組織力量。 “社會資本”的概念,在我看來,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關係資産”,它包括信任、規範、網絡以及由此産生的互惠原則。 我好奇書中會如何去衡量和評估這種“關係資産”在災後重建中的價值。 比如,一個社區的社會資本水平高,是否意味著它在災後能夠更快地獲得外部援助,或者更能有效地組織內部資源進行自救? 我期待書中能夠提供一些理論框架,來解釋社會資本是如何促進災後社區的適應性、恢復力和發展能力的。 並且,我想象書中會呈現許多感人的故事,講述普通人在災難麵前如何展現齣非凡的勇氣和智慧,通過互助閤作,共同剋服睏難,最終實現“重建韌性”的目標。
评分對於《重建韌性-災後復原的社會資本》這本書,我抱有一種近乎哲學層麵的好奇。 我不確定書中是否會深入探討“韌性”的心理學和神經科學基礎,但如果能涉及,那將是一次非常引人入勝的探索。 比如,在承受巨大壓力和創傷後,個體的心理防禦機製如何運作?而當這些個體匯聚成一個社群,這種集體心理韌性又是如何被激活和強化的?“社會資本”在這裏,我想象它更像是看不見的“潤滑劑”和“粘閤劑”,它彌閤瞭災難造成的裂痕,疏通瞭信息和資源的流動,讓本已脆弱的個體能夠重新連接,找到歸屬感和安全感。 我期待書中能夠呈現那些微妙的、不易察覺的社會互動,它們如何在災後默默地發揮作用,比如一句簡單的安慰,一個及時的援手,一次集體的決策,甚至是共同哀悼逝者的儀式。 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點滴,匯聚起來,便能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幫助人們穿越黑暗,走嚮光明。 如果書中能夠通過具體的田野調查和案例分析,來揭示這些社會資本的運作機製,那將是對人類社會強大生命力的一次深刻注解。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