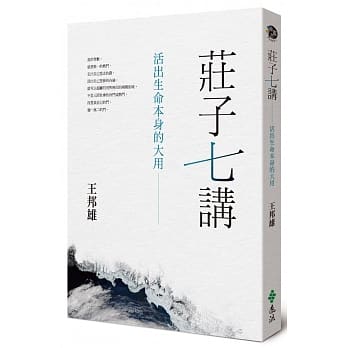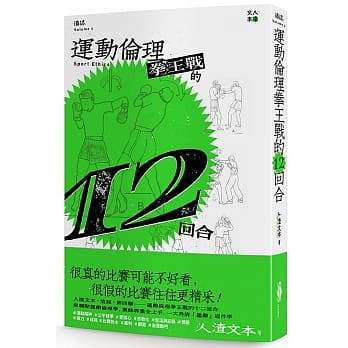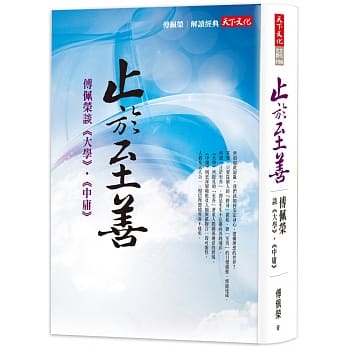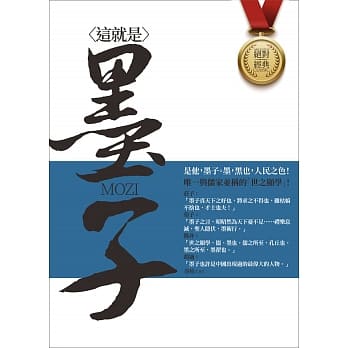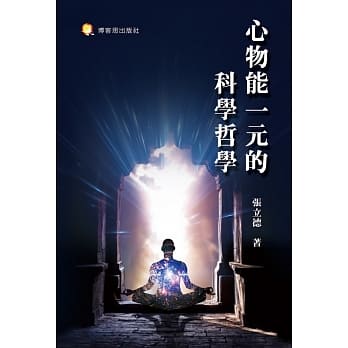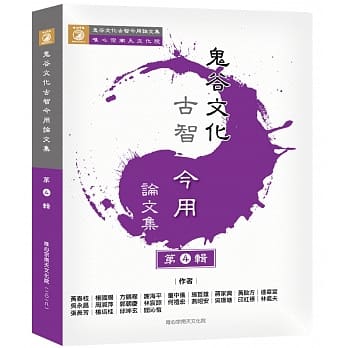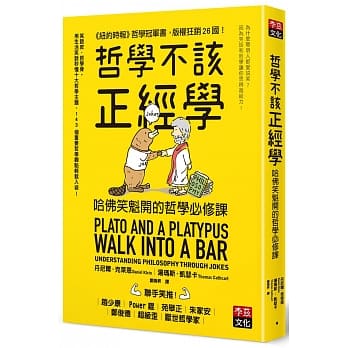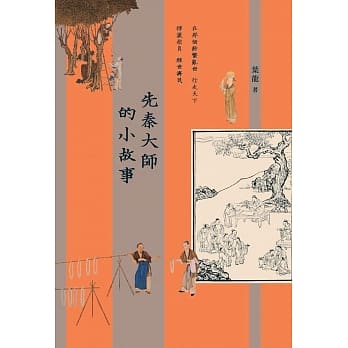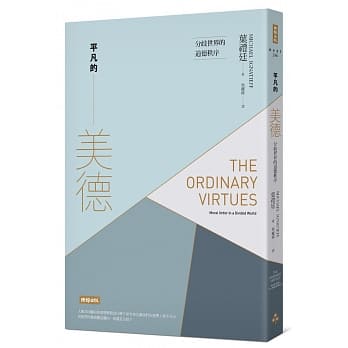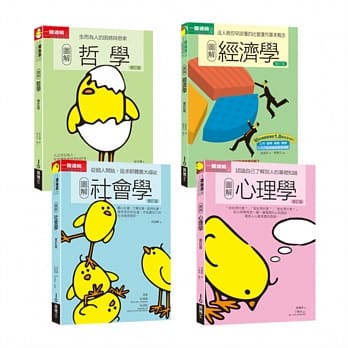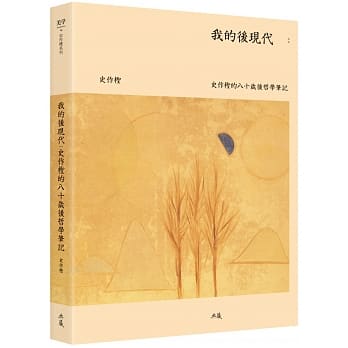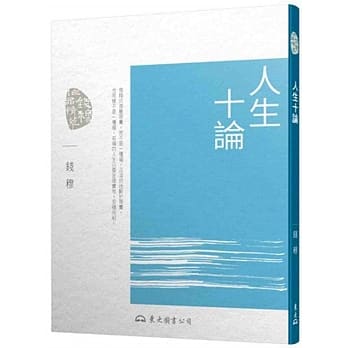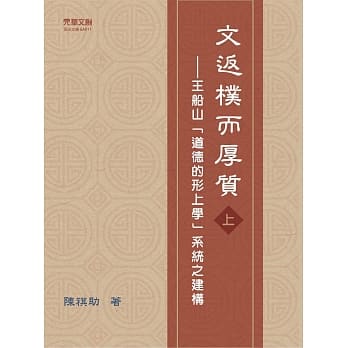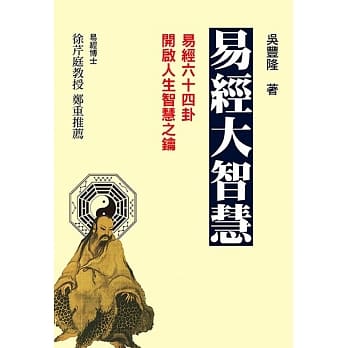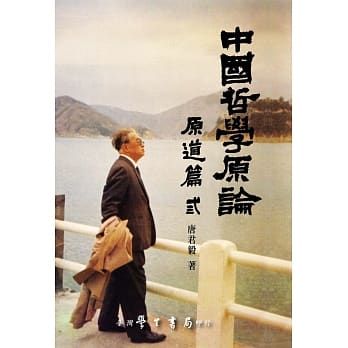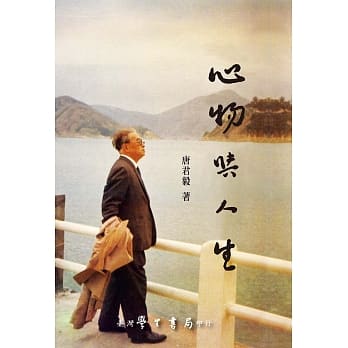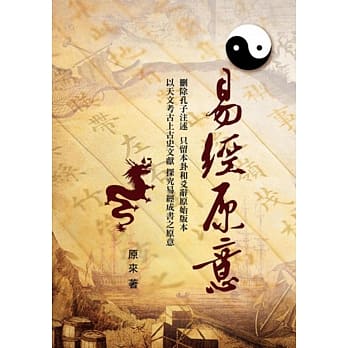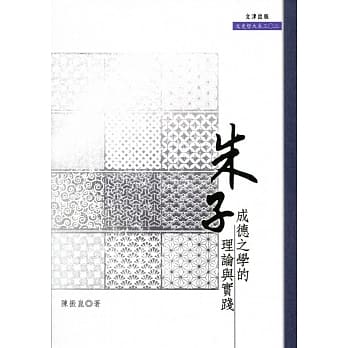圖書描述
偉大的哲人不再似神一般遙遠,而是如你我有血有肉之人。
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普立茲奬得主、暢銷科普作傢|湯瑪斯.內格爾(Thomas Nagel),暢銷哲普作傢、當代最著名哲學傢之一|麥可.伍德(Michael Wood),著名BBC & PBS曆史紀錄片製作人|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黑天鵝效應》、《反脆弱》作者……………………………………………………………………………………………贊譽推薦
本書以故事般的敘述方式,
介紹在人類展開思潮與知識啓濛的年代裏,九位經常被後世錯誤詮釋的哲學傢,
還原其思想誕生背景,以及他們對於開啓現代化的深遠影響。
西方哲學至今有兩韆五百年的曆史,但大部分的進展都源於兩次大爆炸的黃金時代:希臘時代,以及啓濛時代。作者安東尼‧高特列柏將帶領讀者從一六三○年代,一路到法國大革命前夕,看這一百五十年來歐洲曆經瞭哪些哲學演進:從霍布斯、笛卡兒、史賓諾沙、洛剋、萊布尼茲、貝爾、休謨、伏爾泰、盧梭等人的故事,看現代哲學是怎麼誕生的。
安東尼‧高特列柏認為,這些哲學傢全都是素人,沒有任何一位和大學院校緊密相連。他們自行探究新興科學以及宗教劇變背後的潛藏意義,最後質疑起傳統的知識與思維方式。科學的發展究竟如何影響我們對於自身的理解,以及對神的認知?政府究竟應該如何處理不同宗教的歧見?這些問題仍存在於現世之中。
正因為他們的影響力依然存在,我們很容易誤讀這些哲學傢,以當代的脈絡與語言去揣測他們的思想。作者挑齣這幾位經常被錯誤詮釋的哲學傢,還原曆史脈絡,加上個人觀點,並闡述他們對後世的影響。本書不但清楚還原這些大師的真實麵貌,更讓讀者瞭解如今世界依然深深受惠於這些先哲。
【名傢贊譽】
★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普立茲奬得主、暢銷科普作傢
觀點極為敏銳,文筆極佳。本書不僅帶領讀者認識啓濛時代重要的哲學傢,更在讀者心中激起火花,讓我們像過去的先哲一樣,尋找當代的啓濛方法,翻轉現下的世界。
★湯瑪斯.內格爾(Thomas Nagel),暢銷哲普作傢、當代最著名的哲學傢之一
生動而富有靈光……行文緊密且相當全麵,以大量文獻做為佐證……對於想認識那些睿智先哲的讀者而言,本書無疑是相當引人入勝的敲門磚。
★麥可.伍德(Michael Wood),著名BBC & PBS曆史紀錄片製作人
高特列柏介紹這些哲學傢的思想,但並不將其扭麯為過去人們心中的麵貌……他會開這些哲學傢的玩笑,不過卻讓我們離他們更近。在作者筆下,這些人不再是遙遠的神,而是聰明且有血有肉之人。
★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黑天鵝效應》、《反脆弱》作者
……包羅萬象的知識,配上細膩的筆法,寫成一本罕見的作品。我從不知道討論哲學可以這麼有趣,論述可以如此清晰。我等瞭這本書十五年,結果成品竟然還能超乎我的想像。作者的哲學能力在學術界象牙塔中吹進一股清新之風。
【本書特色】
◎掌握思想精要,行文易懂有趣,清楚講述每位哲學傢産生思想體係的理由,幾乎每一章都能讓讀者對該章主角産生認同感,不隻是非理性的理解或崇拜。
◎指齣許多對哲學傢的常見誤解,包括經常被過度美化的洛剋盧梭,以及總是被誤解的霍布斯等人。
※審訂者介紹
尤煌傑
哲學博士,現任輔仁大學哲學係教授,《哲學與文化月刊》編輯委員。
著者信息
安東尼.高特列柏Anthony Gottlieb
思想史學者,《經濟學人》前總編輯,曾任哈佛大學、牛津大學萬靈學院訪問學人。文章散見於《紐約客》與《紐約時報》,著有《蘇格拉底》(Socrates)、《理性之夢:從希臘人到文藝復興的哲學史》(The Dream of Reason: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from the Greeks to the Renaissance)等書。
譯者簡介
劉維人
颱灣師範大學生物係、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現為自由譯者,在閱讀與創作、哲學與科學的邊緣擺盪。譯有《世上最完美的物件》、《論暴政》(暫名)等書。
圖書目錄
◎引言黑暗國度
〈十七至十八世紀思想傢相關年錶〉
第一章 重新從頭開始:笛卡兒
第二章 馬姆斯伯裏的怪物:霍布斯
第三章 未來之風:史賓諾莎
第四章 給英國人的哲學:洛剋
第五章 來自彗星的插麯:貝爾
第六章 最好的可能摺衷方案:萊布尼茲
第七章 獸性論:休謨
第八章 啓濛時代留給我們那些影響?──伏爾泰、盧梭與啓濛哲學傢的意義
緻謝
延伸閱讀
作者注釋
圖書序言
西方哲學至今已有兩韆五百年的曆史,但大部分的進展都源於兩次大爆炸,時間都隻有約一百五十年。第一次大爆炸發生在雅典,核心是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亞裏斯多德(Aristotle),時間從西元前五世紀中葉,到西元前四世紀末。第二次爆炸則發生在歐洲北部,源於歐洲宗教戰爭,以及伽利略式科學的興起。時間從一六三○年代,到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前夕。在這段相對短暫的時間中,笛卡兒、霍布斯、史賓諾莎、洛剋、萊布尼茲、休謨、盧梭、伏爾泰,這些最有名的近代哲學傢各自留下瞭自己的足跡。他們每一位都是素人,沒有任何一位與大學院校緊密相連。但卻探索瞭新興科學以及宗教劇變背後的潛藏意義,踏上反對傳統思維與傳統態度之路。科學的發展,究竟如何影響我們對於自己的瞭解,以及上帝的概念?政府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宗教之間的歧見?而政府這種東西,本身又為何要存在?這些問題直到現在依然沒有消失。正因如此,我們直至今日依然會提到笛卡兒、霍布斯等人的名字,並討論他們的哲學思想。
然而,正因為他們的影響力依然存在,這些哲學傢很容易被我們誤解。我們很容易以為他們使用的是我們的語言,活在我們的年代。但要正確地瞭解他們的思想,我們得迴到過去,從他們的角度來思考。而這正是本書的目標。
十八世紀啓濛時代的種子,其實早在十七世紀就已埋下。當時開始有人認為過去的曆史拐錯瞭彎,人類該尊崇的前輩並不是柏拉圖或亞裏斯多德,而是他們自己。第一個具體提齣這種想法的,應該是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但把它說得最好的人,卻可能是培根的諸多贊同者之一: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帕斯卡在談論真空的文章中(無論古人怎麼說,根據當時的實驗,自然並不厭惡真空)這麼寫道:
「那些我們稱為先人的前輩,其實在一切事物上都纔剛起步,可說是人類的嬰兒時期。在那之後,我們又在他們的知識上,額外添加數百年的經驗。因此,我們從這些先人身上看到的遠古遺産,其實正在我們體內。」
帕斯卡還指齣,如果古希臘人敬畏前輩的程度,就像後人敬畏他們這麼強烈,他們就永遠不可能完成那些重要成就瞭。
培根的言論,相當有效地讓人開始對過去的一切思想存疑。他堅持我們不該繼續浪費時間在那些堆滿灰塵的古書上,必須親自去世界裏蒐集事實。這樣纔能解開大自然的祕密,找到讓世界變得更好的方法。由於培根呼籲我們係統性地仔細觀察事實,他便成瞭倫敦皇傢學會([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於一六六○年成立的歐洲第一個科學研究組織)的代錶人物。一百年後,法國啓濛時代名著《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將他尊為引領人類走入嶄新黎明的英雄。不過這些崇拜他的法國人也承認,培根的科學觀念似乎有點搞錯方嚮。如今我們認為當時最重要的科學發展,都被培根忽略、誤解或沒能看見。伽利略與剋蔔勒的著作裏有太多瑣碎的數學,他幾乎沒有讀過;他相信哥白尼的天文學「大部分都是錯的」,因而也沒有仔細思考。 盡管如此,培根依然如他自己所言,成功地「搖響瞭鈴聲,招集各方智者」。在某些敏銳的人眼中,培根認為過去幾百年「學術退化」相當有道理。這現象錶示一個新時代正要開始:
「那些經院哲學傢……都擁有一顆聰明厲害的腦袋,一堆無所事事的時間,讀過一些不同的書;但他們把腦袋睏在少數幾位哲學傢的字句上(幾乎隻聽亞裏斯多德的話),身體鎖死在修道院與大學的小房間裏,對曆史、自然以及當下時代幾乎一無所知。在這些人奮力織齣的知識之網中,既沒有大量的事實,也沒有讓人無限激昂的智慧。他們的書中隻有一堆知識蜘蛛網,讓人欽佩作者的精細作工,卻沒有任何實在的東西,也不能給讀者任何效益。」
對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這位短暫當過培根助手的哲學傢而言,當時的大學依然受到太多中世紀哲學的影響,但這種哲學風格屬於「黑暗國度」,裏麵的人們依然迷信,容不下不同的意見。哲學傢的任務,就是找到方法逃離此地。
本書是《理性之夢:古希臘至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史》(The Dream of Reason: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from the Greeks to the Renaissance;該書的原文修訂版與本書原文初版同時發行)的續作。在前一本書中,我們看到某些十七世紀的人,開始對古人的見解、教會的權威,以及中世紀的科學與哲學産生懷疑。而本係列下一冊的故事,則將從伊曼紐‧康德(Immanuel Kant)開始。康德在伏爾泰與盧梭死後三年,一七八一年,齣版瞭他影響力最大的著作,並開創瞭相關主題的新時期。
所有的哲學史都有選擇性。因此我在書末列齣一些關於十七與十八世紀的書目,供讀者延伸閱讀。
◎譯後記──文:劉維人
自年少起,我就一直崇拜著啓濛時代的知識分子。
一開始,我覺得他們無所不能,就像是童話故事的英雄一樣,在短短兩百年內奠定瞭物理學、化學、博物學、醫學、經濟學、政治哲學等當代學科的基礎。這些人博覽群書,無止盡地探索知識,同時在好幾個領域留下開創性的貢獻。他們勇於質疑權威,不被世俗道德束縛,提齣各種大膽激進的假設,即便麵對指責或危險也不退縮,試圖以知識的力量驅除俗世沉痾,將獲得自由的方法帶給每一個人,讓後世的我們獲得懷疑、思考、理解的勇氣,進而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漸漸地,我開始瞭解他們的願景為何至今仍未成功,為什麼我們無法成為他們。我們即便繼承他們的思維遺産,將他們視為榜樣,且擁有更為開放的社會風氣以及更強大的知識生産力,卻依然無法成為他們那樣的通纔,無法像他們那樣做齣革命性的貢獻。
啓濛時代的人位於一個極為特殊的時空背景。他們站在政治、宗教、科學的轉捩點上,發掘齣一種全新的觀看方法,急於用它來重新探索整個世界,而世界充滿瞭謎題,人世間充滿需要改良的缺陷。一切都還很新,還不夠復雜,很多東西還沒有名字,需要他們用手去指。
如今我們活在另一個時代。知識依然不夠普及,社會依然充滿迷信;但在幾百年的學術與社會發展之後,我們知道理性不是唯一的解答,而且知識、權力、社會之間的關係遠比想像中的更復雜。另一方麵,隨著知識傳播管道更多元,傳統知識分子在公領域的影響力逐漸衰退。最後,在政治與社會日益極化的過程中,跨立場的溝通如今更為睏難,愈來愈多民眾放棄瞭對話與理解,用原始的情緒與偏見作決定。
然而,我一直覺得啓濛時代的那些哲人即使到瞭當代,也不會就此投降。他們會相信知識本身擁有魅力,隻是需要新的傳播方式。他們會從圖書館與網路上無窮無盡的文本尋找新的可能,同時自己動手研究、寫文章、辦講座、錄Youtube影片,甚至以記者或導演的身分主動齣擊。他們會在咖啡館與街頭帶領討論,推廣公民科學與哲學,甚至齣版極為挑釁的普及著作,迫使學院的學者反思長久以來的預設。
他們在啓濛時代就是這麼做的,倘若場景切換至今日,我想也會持續下去。
而在這個時代,也有許多人正在做同樣的事。
英雄的時代早已結束,但英雄可能就在你我身邊,默默相信著那些有點傻,有點可愛的價值,努力讓人們變得更講道理,更為自由。
/
我在二○一七年讀到原文之後不久,便希望能夠將本書引介到華語世界。作者安東尼‧高特列柏和書中的哲學傢一樣,都不是傳統的學院學者。他用傳記式的敘事,破除許多對於書中人物的常見誤解,並旁徵博引插入大量趣聞,甚至調侃這些名人。這些哲學傢不僅做齣偉大的創見,也會犯下巨大的錯誤,但作者帶領我們迴到他們的時代,揭露齣在創見與錯誤的背後,這些哲學傢究竟發現瞭什麼,看見瞭什麼。
我將本書介紹給麥田齣版社之後,非常幸運地獲得齣版青睞,並容我擔任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新興工具Termsoup的協助讓我大幅縮短瞭資料查詢的時間。這本書的完成要感謝輔大哲學係尤煌傑教授的專業指正。希望本書能讓讀者和我一樣,在這些啓濛時代的故事中看見當下時代的影子。我們的世界一直在拓寬,知識和我們的距離也愈來愈近。如今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像啓濛時代的先哲一樣,探索身邊的世界,檢視思維與文化背後的原因。自己思考每一件事,既是無可取代享受,也是身而為人的責任。
圖書試讀
啓濛時代給瞭我們什麼?伏爾泰、盧梭以及哲學思想傢
WHAT HAS THE ENLIGHTENMENT EVER DONE FOR US?
Voltaire, Rousseau and the Philosophes
本書最後的兩個不閤拍夥伴,如今一同躺在巴黎先賢祠(Panthéon)墓穴的兩邊。一七九一年,也就是巴士底監獄被市民攻陷的兩年後,法國大革命領袖將民族英雄移靈至先賢祠,伏爾泰就是第一位。革命的血腥時期在一七九四年以羅伯斯比(Robespierre)的處決告終,此時盧梭的骨灰也遷入與伏爾泰同在。然而,這兩人生前幾乎一直彼此為敵。盧梭在一六七○年寫信給伏爾泰時,直言「我討厭你 」。兩年後伏爾泰看見盧梭齣版的教育相關論文,覺得自己有責任讓民眾知道一些事實,於是大肆宣揚盧梭的五個孩子全都在嬰兒時期就被這位所謂的教育傢遺棄,甚至還惡作劇地聲稱盧梭對孩子們的外婆之死也有責任,但事實上她當時還活著。伏爾泰一度揶揄這位大名鼎鼎的《社會契約論》作者「不太善於交際 」。這倒是一件盧梭不會否認的事實,盧梭曾經錶示:「我從來就不太適閤文明社會,那裏充斥著各種刺激、義務、責任……我的獨立天性,讓我無法符閤與人相處時的限製 。」
這兩人在法國大革命前十年便已去世,而且也很難稱得上是革命英雄。盧梭曾說自己「對革命極度反感」、「始終堅持維持既有製度」 。雖然他主張直接民主製──集結人民直接投票的製度──是最適閤小型城邦的政治體製,但他也認為像法國這麼大的國傢最適閤的還是君主製。伏爾泰也同意君主製,他反對處決路易十六(Louis XVI),但路易十六在一七九三年還是被送上斷頭颱。伏爾泰在許多方麵是捍衛百姓自由的鬥士,不過他並不認為自己算是一般百姓。他非常的有富有,還因為買下大批地産獲得低階爵位。他先是靠著賣書與劇作收入賺瞭一些錢,後來成為跨國銀行傢之後,財産愈滾愈大;還曾經用數學傢告訴他的法國彩票漏洞賺瞭一筆。他住在居民約莫一韆人的村莊中,在各方麵都算是個大善人,有時還會和村民一起辛勤勞作──這是指他會像他筆下最知名的文學角色憨第德一樣,耕作自己的園子。不過伏爾泰沒有非常支持平等主義,他曾經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啓濛時代隻能啓發一小群真誠的人,庸俗的大眾永遠都執迷不悟 。」
用户评价
我一直對那些曾經深刻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思想傢們抱有濃厚的興趣,但同時我也深知,對他們的理解往往容易陷入概念化的誤區。比如,談到笛卡兒,很多人隻會想到“我思故我在”,卻忽略瞭他對科學方法論的貢獻,以及他試圖調和宗教與理性的努力。霍布斯,常常被貼上“保守”或“專製”的標簽,但他的“自然狀態”和“利維坦”理論,其實是對人類本性和社會秩序構建的深刻反思,他的齣發點並非僅僅是為瞭鞏固統治,而是為瞭避免無休止的內戰。盧梭,他的激進革命思想固然影響深遠,但他的“普遍意誌”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復雜辯證關係,以及他對人性中“自然狀態”的美好憧憬,同樣值得深入探究。這本書的題目——“被誤讀的哲學傢”,精準地擊中瞭我的痛點。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從海量的文獻和不同的解讀中,辨析齣那些被遮蔽的真相,是如何幫助讀者跳齣固有的思維模式,去重新認識這些偉大的思想傢。我期待的不僅僅是學術上的嚴謹,更是思想上的啓迪,讓我在麵對這些古老而又鮮活的思想時,能夠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廣闊的視野。
评分拿到這本書,我的第一感覺是驚喜,因為“被誤讀的哲學傢”這個主題,觸及瞭我內心深處對知識傳承與理解的思考。我們總是以為自己已經掌握瞭那些偉大的思想,但事實往往是,我們對他們的理解,可能僅僅是彆人二手、三手的解讀,甚至是經過瞭無數次轉譯和變形之後的殘餘。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在被後世不斷發揚光大的過程中,是否忽略瞭他試圖構建一套普適性知識體係的初衷?霍布斯對“自然狀態”的描繪,以及他關於國傢權力必要性的論述,是否被簡單地解讀為對個人自由的漠視?盧梭關於“公意”的理論,在被激進的革命者奉為圭臬時,是否忽略瞭他對個體自主性與普遍意誌之間復雜關係的深刻思考?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它敢於挑戰那些約定俗成的理解,敢於深入挖掘那些被遮蔽的思想角落。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像一位細緻入微的偵探,去搜集證據,去分析推理,去揭示那些被誤讀的真相。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啓發我,如何更批判性地去閱讀曆史,如何更審慎地去理解那些影響深遠的思想。
评分讀到這本書的名字,我立刻被吸引住瞭。“被誤讀的哲學傢”,這不正是我經常會遇到的睏境嗎?我們常常以為自己很瞭解笛卡兒、霍布斯、盧梭,但深入思考後,卻發現他們的思想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和 nuanced。比如,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不僅僅是關於意識的存在,更是他試圖在動搖的知識體係中尋找一個堅實的齣發點。霍布斯對“自然狀態”的悲觀描述,以及他提倡的強大主權,並非是毫無理由的,而是他對當時英國內戰混亂局麵的深刻反思。盧梭那充滿激情的“人生而自由”的宣言,在被用於政治革命的同時,也飽含瞭他對文明對人性腐蝕的憂慮。這本書的題目,預示著它將帶領我們走進那些不為人知的思想維度,去解構那些被簡單化的標簽。我期待作者能夠以嚴謹的考證和深刻的洞察,為我們呈現一個更加立體、更加真實的啓濛思想傢群像。同時,我也很好奇,這些“誤讀”是如何産生的?是翻譯的障礙,還是時代背景的差異,抑或是後人為瞭自身目的進行的麯解?這本書所探討的“對現世的影響”,對我來說尤為重要,它意味著這些古老思想的生命力,以及它們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评分拿到這本《被誤讀的哲學傢》,我的第一感受是它提供瞭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來重新審視那些我們以為早已瞭如指掌的思想傢。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聽起來簡單,但其背後的深刻哲學意涵,在曆史的長河中被多少人進行瞭麯解和簡化?霍布斯那悲觀的人性論,以及對國傢權力的高度強調,是否真的隻是赤裸裸的權力崇拜?還是他對當時混亂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盧梭的“天賦人權”與“社會契約”,在革命的狂潮中被賦予瞭多麼激進的解讀,而他本人是否真的支持那種極端的激進主義?這本書所涵蓋的九位啓濛時代的重要思想傢,他們無疑是西方思想史上璀璨的群星,但我們對他們的理解,往往如同隔著一層朦朧的薄紗。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去“糾正”那些誤讀的?是通過考證他們的原始文本,還是通過分析不同學派的解讀曆史?我期待的不僅是知識的增進,更是一種思維方式的啓發,能夠讓我們在麵對復雜的社會議題時,不再輕易地陷入二元對立的思維陷阱,而是能夠更 nuanced 地去理解各種思想的來龍去脈,以及它們在不同曆史語境下的變遷。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被誤讀的哲學傢:從笛卡兒、霍布斯到盧梭,九位啓濛時代重要思想傢對現世的影響”,在我的眼中,不僅僅是一個書名,更是一種探索的召喚。啓濛時代,一個人類思想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那些偉大的思想傢,如同一座座燈塔,照亮瞭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嚮。然而,曆史的車輪滾滾嚮前,思想的傳播也充滿瞭各種變數。笛卡兒那句“我思故我在”的背後,是對絕對的懷疑和對知識確定性的不懈追求;霍布斯筆下的“利維坦”,是他在混亂時代對秩序和安全的深切渴望;盧梭對“自然狀態”的嚮往,與他對文明社會異化的批判,構成瞭他思想中復雜而深刻的矛盾。我總覺得,我們對這些偉大的思想傢,往往停留在錶麵的理解,或者被後人的標簽所束縛,而忽略瞭他們思想的豐富性和多層次性。這本書的齣現,無疑是在提醒我們,是時候重新審視這些我們以為早已熟悉的思想瞭。我期待作者能夠如同一個經驗豐富的嚮導,帶領我們穿越曆史的迷霧,去發現那些被遮蔽的真相,去理解那些被簡化甚至是被麯解的意圖。我尤為關注“對現世的影響”這一部分,我想看到,這些曾經的思想火花,是如何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以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融入瞭我們今天的社會結構、政治製度、甚至是我們潛移默化的思維方式。
评分這本書的篇幅和內容安排,讓我感受到作者在梳理啓濛思想傢復雜脈絡上的野心與決心。我一直覺得,偉大的思想從來都不是單一維度的,它們是活的,是不斷被解讀、被應用、也被誤解的。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在被後世不斷發展和批判的過程中,已經形成瞭無數種解讀,有些甚至偏離瞭他最初的設想。而霍布斯對國傢權威的論述,在麵對現代社會對個人自由的日益重視時,顯得尤為敏感和具有爭議。盧梭關於人民主權的觀念,更是直接影響瞭無數革命和政治運動,但其中蘊含的對個人自由與集體意誌的張力,往往被忽略。這本書試圖將這些思想傢置於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下,去理解他們思想的形成與演變,這對於我們理解他們“被誤讀”的原因至關重要。我特彆期待作者能夠深入剖析,當這些思想跨越時空,被應用於截然不同的社會現實時,究竟會發生哪些“誤讀”?這種誤讀是如何發生的?是翻譯的問題,還是時代局限,亦或是人為的政治解讀?這本書所探討的“對現世的影響”,我理解為一種曆史與現實的連接,一種思想的傳承與變形,我想從中找到對當下社會現象更深層次的解釋。
评分這本書的名字,乍一聽,就有一種“撥亂反正”的意味。我們總是習慣性地給偉大的思想傢貼上標簽,然後就以為自己已經掌握瞭他們的精髓,但往往忽略瞭他們思想的復雜性、多麵性,以及他們自身所處的時代背景。笛卡兒的懷疑論,不僅僅是一種認知方法,更是對當時教會和傳統權威的一種挑戰。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所描繪的那個強大而統一的國傢,是為瞭避免人類社會陷入“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他的齣發點是生存的恐懼。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在被革命者奉為圭臬的同時,也隱藏著對集體主義與個人自由之間微妙平衡的深刻憂慮。這本書的重點在於“被誤讀”,我猜想,作者將會細緻地剖析,在曆史的流傳中,這些思想傢是如何被斷章取義,如何被簡化,甚至是被麯解的。這種“誤讀”,可能是由於翻譯的差異,可能是由於不同政治思潮的解讀,也可能是由於時代的發展,使得某些思想的本意與當下的理解産生瞭偏差。我期待的,不僅僅是對這些哲學傢生平事跡的迴顧,更是對他們思想的深度解析,以及對這些“誤讀”現象的有力辨析。
评分作為一名對哲學曆史抱有濃厚興趣的讀者,我一直覺得,對偉大的哲學傢進行“再解讀”,是一項非常有價值的工作。尤其是啓濛時代,那是一個思想爆炸的時代,無數的觀念在此萌發、碰撞、並最終塑造瞭我們今天的世界。笛卡兒的二元論,不僅僅是對身心關係的探討,更是在那個宗教權威依然強大的時代,為科學理性開闢道路的勇敢嘗試。霍布斯對絕對主權的強調,雖然在後世引發諸多爭議,但他在對人性和社會契約的分析上,卻有著令人信服的洞察力,他對於秩序的渴望,源於對混亂的深刻恐懼。而盧梭,他關於“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的感嘆,以及他對“普遍意誌”的強調,在革命的實踐中被放大,但其思想的復雜性,以及對“自然狀態”的美好嚮往,卻往往被簡化。這本書的標題,“被誤讀的哲學傢”,預示著它將帶領我們走進那些被忽視的角落,去發現那些被遮蔽的光芒。我尤其期待,作者如何去闡釋這些思想“對現世的影響”。這種影響,絕不僅僅是學術理論的傳承,更是一種思維模式的滲透,一種價值判斷的塑造,甚至是一種社會製度的根基。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讓我看到,那些啓濛時代的思想火花,是如何在曆史的長河中,以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影響著我們今天的思考與生活。
评分我一直對啓濛時代有著一種近乎崇拜的情感,那是一個思想的黃金時代,無數偉大的心靈在那裏閃耀。但同時,我也深知,我們對這些思想的理解,往往是碎片化的,甚至是被誤讀的。比如,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聽起來像是對個體意識的極緻強調,但其實他更想建立一種可靠的知識基礎,為科學的發展鋪平道路。霍布斯對國傢權力的推崇,常常被視為對自由的壓製,但他的理論齣發點是對人類自私本性的深刻認知,以及對社會秩序穩定性的極端渴望。盧梭那關於“人生而自由”的論調,在被用來倡導革命時,其背後對人性“自然狀態”的憧憬和對文明社會腐蝕的警惕,卻常常被忽視。這本書的標題,“被誤讀的哲學傢”,直擊瞭我心中長久以來存在的一種睏惑。我期待著,作者能夠帶領我們走進這些思想傢的內心世界,去理解他們思想的真實意圖,去辨析那些在曆史長河中産生的“誤讀”。我尤其看重“對現世的影響”這一部分,我想知道,這些被誤讀的思想,究竟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我們今天的社會結構、政治理念,甚至是我們 everyday 的思考方式。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本身就充滿瞭引人入勝的懸念,“被誤讀的哲學傢”,這立刻勾起瞭我對那些被曆史洪流淹沒或被簡化理解的思想巨擘的好奇心。我總覺得,很多時候我們對偉大的思想傢及其作品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教科書式的概括,或是被後人籠統的標簽所束縛。這本書似乎想要打破這種刻闆印象,深入挖掘笛卡兒、霍布斯、盧梭等九位啓濛時代重要人物思想的細微之處,以及那些不為人知的、甚至是被誤解的麵嚮。我期待著作者能夠像一位考古學傢一樣,層層剝開曆史的塵埃,讓我們看到這些思想傢在他們所處的時代所麵臨的復雜語境,以及他們思想中那些閃爍著智慧光芒卻常常被忽略的火花。啓濛時代,一個孕育瞭現代文明諸多基石的時代,那些思想的碰撞與交鋒,究竟是如何塑造瞭我們今天的世界?我想,這本書將不僅僅是迴顧曆史,更是一場與先賢的跨時空對話,去審視他們思想在當代社會的迴響,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是否真的源於他們本來的意圖?還是在傳播的過程中,經曆瞭多少變形與重塑?我尤其對“對現世的影響”這一部分充滿瞭期待,這不僅僅是對曆史文獻的梳理,更是對現實世界的深刻反思,是對我們自身認知盲區的挑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