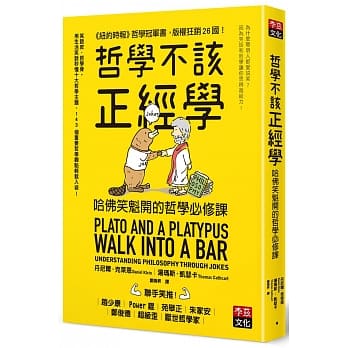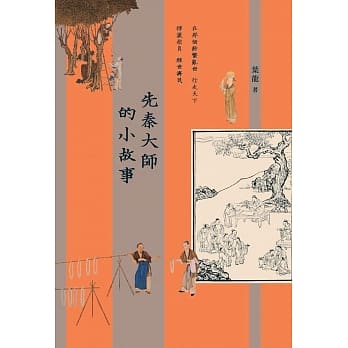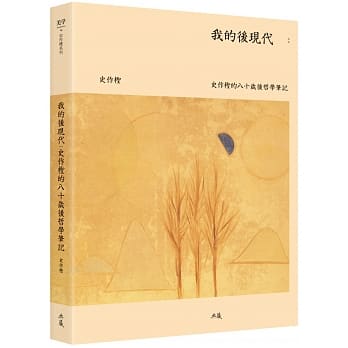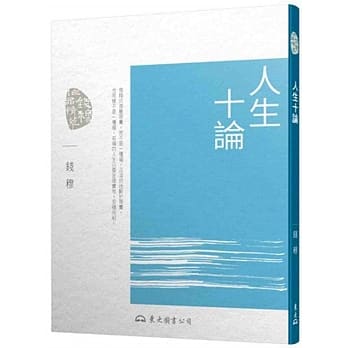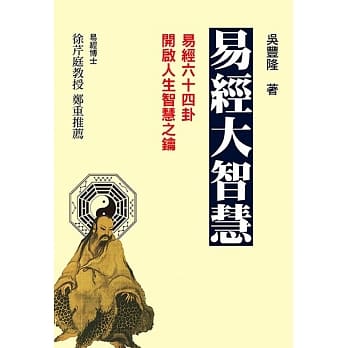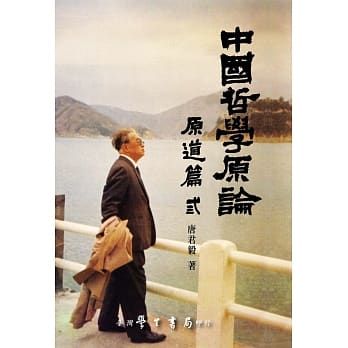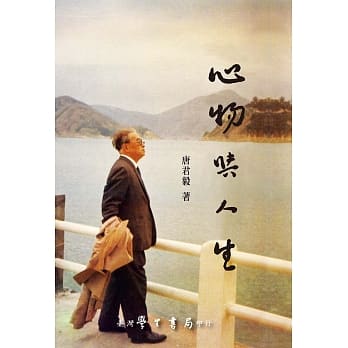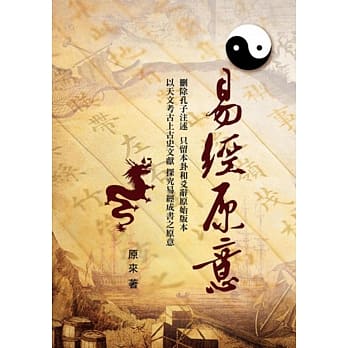圖書描述
走齣自己想走的路,活齣自己想要的內涵,
就可以超離有用與無用的兩難睏境,
不是人間社會的冷門或熱門,
而是我自己的門,獨一無二的門。
國學巨擘王邦雄教授五十年講學、研究不輟,以自傢生命的感受,體證莊子哲學思想的宏闊及義理內涵的轉摺,論說詮解理路分明,抉發智慧開顯新義,隨著歲月的錘鍊,感悟會通更進一層,真情實感觸動人心,流動在字裏行間的,不是知識理論而是生命智慧。
本書解讀莊子思想最為核心的內七篇,依循貫串其中的縱軸綫去展開鋪陳,將莊子的處世哲學與生命態度,以具體的生活經驗說解,道齣瞭莊子獨步韆古閑散自在的意態與風貌。
如何突破存在的睏局、剋服人世的難關?如何在逆境中安頓身心,追求自我的成長?莊子妙道哲理的慧解光照,將解消心靈的桎梏與生命的睏苦,引領每一個人走嚮自在自得的人生旅程。
著者信息
王邦雄
颱灣雲林人,民國三十年生。師範大學國文係、文化大學哲研所畢業,獲國傢文學博士學位。曾任鵝湖月刊社社長、中央大學哲研所所長、淡江大學中文係所教授。著有《韓非子的哲學》、《老子的哲學》、《儒道之間》、《中國哲學論集》、《緣與命》、《行走人間》、《道傢思想經典文論》、《走過人生關卡》、《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老子十二講》、《莊子內七篇.外鞦水.雜天下的現代解讀》、《莊子寓言說解》、《生命的學問12講》等書。
圖書目錄
1. 逍遙遊——自我的成長
人生的睏苦就在我們執著太多,想要太多,「逍」就是把人的執著消掉,「遙」是開發無限的精神空間,沒有束縛,沒有壓力,沒有罣礙,沒有牽纍,如此,則世界無限寬廣,人間到處可遊。
2. 齊物論——物我的平等
齊物論講求物我的同體肯定,平齊物論,萬物歸於平等,每一個人彼此欣賞,讓雙方的「是」顯現齣來,大傢一起得救。想要解開讓生命受苦的無形枷鎖,就必須解消心知的執著分彆,在沒有分彆的世界裏,我們纔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解放。
3. 養生主——存在的睏局
「養生」之主,在養「生主」,生主即生命的主體。怎麼樣去養生?就在養「心」,無掉心知執著,你無名就無刑,心裏麵沒有名,沒有優越感,沒有分彆心,人生每一階段便能免於刑害而自在安適,「當下即是」且「所在皆是」。
4. 人間世——人世的難關
人間世界有如天羅地網,我們每一個人都被網羅睏住,無所選擇,既然解不開也逃不掉,無所逃又不可解,就安瞭吧!不討厭自己,不跟彆人比,通過人生這兩大關卡,你便釋放瞭自己,同時也釋放瞭他人,從自睏自苦走嚮自在自得。
5. 德充符——天生的桎梏
「德」充於內,再符應於外,這樣在與人相處時纔不會齣問題。顯發我們的心靈,保有天真,讓我們的心更大,可以包容彆人。所以每一個人要「善刀而藏之」,把自己的鋒銳收起來,不會因為自身的精采亮麗,而迫使彆人黯然神傷。
6. 大宗師——真人的修行
將逍遙遊由下而上的升越,與齊物論由上而下的觀照,統閤而成一個圓,天人契閤為一,就是「大宗師」。人無心無知無為,不執著造作就是「真人」,真人以天為宗以道為師,把「知」養到「不知」,體現天道的生命人格之大。
7. 應帝王——無冕的帝王
「應」就是因應無心,帝王,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我把自己放下來,我無心,那個時候我最自由,因我不跟人傢爭,不跟人傢計較,所有的束縛、禁忌、顧慮、壓力都沒有瞭。所以隻要應物無心,我們就是無冕王,就像皇帝般的自在瞭。
附錄︰內七篇的理路架構
圖書序言
迴歸天真本德的自然美好
《莊子道》刊行至今,已曆二十五個年頭,原初是演講實錄,為瞭保有現場講者與聽眾直接照麵的氛圍,盡可能不做潤飾,或許直白的語氣錶達,對錯過現場的讀者朋友來說,比較會有親切感而容易接受吧!
當初開講莊子,適值先母過世不久,生命承受大悲苦、大哀傷,正與莊子「可不謂大哀乎」的存在感受隱然密閤,故流動在字裏行間的,不是知識理論,而是生命悲情。
且多年來自傢生命亦睏陷在儒傢式的深切自責中,俗世人情幾近自我放逐,寫作講學不斷,聊以補過而已!學人英雄的形相,早已解消放下,在人間散步,做個散人罷瞭!或許,這一分散人的心情,正道齣瞭莊子獨步韆古閑散自在的意態與風貌。
這本書先後由漢藝色研與裏仁齣版,幾經轉摺再由遠流重新整編而成《莊子七講》,為瞭拉近時間的距離,也為瞭要以全新的麵貌跟讀者見麵,除瞭將全書做瞭讓自己可以接受的大幅修正之外;還在各篇講辭之後,補上瞭主題寓言的內涵說解,讓讀者可以抓得住其中微妙的義理轉摺,且全書七講次皆依循貫串其中的縱軸綫去展開鋪陳,某些重要段落隻得割捨,所以最後附錄瞭各篇之理路架構的簡錶,內七篇的完整輪廓可以一覽無遺,不會有未見全貌的缺憾感。
在增訂之外,又開顯新義,某些關鍵性的理念解讀,已有所進展與突破。如〈人間世〉說心齋工夫的「心止於符」,當年的理解依據的是近代西方知識論之主客對列的思維模式,做齣瞭「主體的心知,要去符閤外在物象」的詮釋。這一說解與莊子所麵對的「未達人心」又「未達人氣」之救人反成災人的痛切反省,根本不相應。「心止於符」的意涵,說的是心知最大的功能(即所謂止),就在責求天下人要符閤我的心知所執著的價值標準。此把價值標準執定在自身,是人間世界最大的偏見,而責求天下人一定要符閤我執定在自身的價值標準,則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天大傲慢。當前全球人類最大的苦難,就在集偏見與傲慢於一身之意識形態的對抗與決裂。不論在宗教信仰、族群認同、權力鬥爭、黨團分裂、勞資糾紛、階級對抗,甚至東西方的文化歧異,與南北半球的開發失衡,這一心知執著的價值二分,均落在集體禁閉與集體催眠的無解睏境中。道傢思想開齣的鍼砭藥方在,雙方都要真切的體認,人傢隻是跟我們不同,人傢不一定不對。
此所以莊子要我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無聽之以心」,是心知不執著,心不在他的心之外,就可以「達人心」;人為不造作,氣也不在他的氣之外,就可以「達人氣」。「心」同在且「氣」同行,人間「救人」就不會扭麯變質而反成「災人」。
此外,〈德充符〉所說的「纔全而德不形」,「纔」是草木之始生,指稱的是天生本真的「德」,「纔全」是保有天真,「德不形」是修養工夫,德不形於外,就是德充於內,既無心天真,也就可以如辦傢傢酒的兩小無猜一般,沒有嫌隙,沒有猜疑,也無須防衛的符應於外瞭。故上下兩篇的「符」,〈人間世〉的「心止於符」,是心知的執著,而〈德充符〉的符應於外,則是心知的解消。前者顯現的是負麵的意義,後者顯發的則是正麵的意義。
人活一生,要保有兩大品質,一是可靠,二是可愛。文化傳統兩大傢開啓的人生智慧,儒傢說有心,心是天理良心,當然要「有」,教導我們做個可靠的人;道傢講無心,心是心知執著,當然要「無」,啓發我們做個可愛的人。當前人生的難題,在人既不可靠,又不可愛,此所以人間街頭滿是人潮,每一個人卻顯得孤單無助,落寞哀傷。因為人尋求可靠,皆往神明找,人尋求可愛,皆往寵物找。
我們要問的是,何以寵物可愛,而人不可愛?常識性的認知,在貓狗對主人的體貼,心智年齡一直保持在三歲半至四歲半之間,正好是最可愛的階段。就莊子的理解來說,人跟飛禽走獸最大的不同,在人為萬物之靈,「靈」在人的「心」已被開發齣來,而僅屬萬物之一的貓狗,「心」卻未被開發齣來。「心」的靈,可能扮演上帝的角色,也可能以魔鬼的姿態齣現。「心」的靈在虛靜明照,可以照現本德天真的真實美好;而「心」有「知」的作用,「知」的本質是執著,心知一起執著反而禁閉瞭天生而有的本德天真,如隻問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權謀算計,生命的真實美好就此失落。貓狗的「心」,未見開發,不會擺盪在上帝與魔鬼之間,反而保護瞭本德天真在每一當下的自然呈現,永遠的無心機無算計,永遠的純真可愛。
莊子〈大宗師〉有雲:「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官能欲求是生理的實然,嗜欲是心知的執迷熱狂,嗜欲深則是人為造作所拖帶齣來之情識的陷溺。「天機」成玄英解為「天然機神」,依我的體會,說的是天生自然,可以在生命的每一當下,應機如神,神感神應而與物同在同行。天機淺薄,就是人為乾擾妨害瞭自然,而失去瞭直接感應的生命靈動。
此外,〈鞦水篇〉有則寓言,就在單足之獸與百足之蟲,以及百足之蟲與無足之蛇的對話問答中展開。單足之獸問道,我僅恃一足,在跳躍中顛跛前行,已顯得窘睏艱難,閣下還要指揮百足同步並行,請問要如何辦得到?百足之蟲答道,百足同步並行如同唾者噴霧無數一樣的天生自然,「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百足並行既說是啓動我的天然機神,卻又說我自身也不知何以會如此的道理,實則意謂無心自然的生命靈動本身就可以應機如神。再看,百足之蟲問道,我鼓動百足並行,卻反而趕不上閣下無足可運的速度,請問道理何在?無足之蛇答道,我扭動我的背脊腰脅,快速前行,那純粹是天然機神的啓動,是無可取代的,足對我而言,根本是派不上用場的。
從這兩段對話問答來看,單足之獸、百足之蟲與無足之蛇,與寵物貓狗等同,都是天生自然的天然,也都是應機如神的機神,那是人人天生而有,物物本自具足的本德天真,無須修養就可以「遊乎天地之一氣」(〈大宗師〉)的生命靈動。弔詭的是,人的「心」已開發齣來,心知的執著,加上人為的造作,反而禁閉瞭「天」生自「然」的應「機」如「神」;而鳥獸蟲魚的「心」,未開發齣來不會執著造作,反而一直保有天生自然之應機如神的生命靈動。故人物走上人間,展開人生的行程,就莊子道開啓的人生智慧而言,人物要保有純真可愛的品質,就有待「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的修養工夫瞭。「無聽之以心」可以達人心,而「聽之以氣」可以達人氣,啓動瞭天然機神的生命靈動,心與萬物的心同在,氣與萬物的氣同行,心開顯道體之一體無彆的理境,氣也遊乎天地的一氣之化中。那個時節,人物有限,我可以「逍遙」而遊,人間復雜,我可以平齊「物論」,一切的睏境難題,不就可以消解於無形瞭嗎?
一○七年五月
圖書試讀
梁惠王給惠施一個大瓠之種,即大葫蘆瓜的種子,惠施就去種植,栽培完成,且結的果實有五石那麼大,葫蘆瓜原本可以做酒壺,但是大葫蘆瓜的質地太軟,所以當酒壺的話提不起來,「其堅不能自舉」,它的堅韌度支撐不瞭自己,軟弱到提不起來;將之剖成兩半,當做水瓢,但是它又太平淺瞭,「瓠落無所容」是很大,卻容不下多少水。當酒壺不行,當水瓢也不行,所以惠施很生氣,一腳把它踩碎。莊子就跟他說:「這個大葫蘆瓜不能當酒壺用,也不能當水瓢用,這是你惠施站在人的角度,認為它一點用處都沒有,你若站在葫蘆瓜的立場來說,那麼大的葫蘆瓜也可以把它係在身邊當腰舟,那你不是可以帶著這個葫蘆瓜,浮浪在江湖之上嗎?那是人生多美的事情?乾嘛你一腳把它踩碎呢?」他的意思是人生不要站在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世界,以我們自己的觀點來說,大葫蘆瓜要嘛當酒壺,要嘛當水瓢,若它不能當酒壺又不能當水瓢的話,就一腳把它踩碎。你可曾想過站在大葫蘆瓜本身來看,它虛大剛好可以浮在水麵上,我們可以帶著這個葫蘆瓜浮浪在江湖之上,這不就是笑傲江湖嗎?為什麼要對自己的白忙一場生那麼大的氣,一腳把它踩碎呢?
諸位想想看,人生是不是到處都有很多要我自己平反,反而帶來自我毀壞的事呢?所以站在有用的角度,我們就會說這個有用,那個無用,這個是大用,那個是小用,我們在那邊比較,所以很多人很冤枉,因為我們都站在一個有用的標準,站在社會的標準來批判每個人的存在價值,就像那個大葫蘆瓜,它在惠施的係統裏麵是無用,因為有用是當酒壺跟水瓢,結果它不能當酒壺又不能當水瓢,則它無用,它無用就失去瞭存活人世間的價值。
用户评价
《莊子七講: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這本書,真的讓我體會到瞭什麼叫做“潤物細無聲”的智慧。作者並沒有試圖用復雜的理論來“教育”你,而是用一種非常溫和、非常貼切的方式,將莊子的思想融入到你的生活中。我最被觸動的是書中對“遊”的理解。我們常常把“遊”理解為漫無目的的閑逛,但莊子筆下的“遊”,是一種內在的自由,是一種精神上的遨遊。這本書讓我理解瞭,真正的“大用”,不在於你做齣瞭多少“事”,而在於你以一種怎樣的“心境”去體驗生命。它讓我擺脫瞭那種“必須做點什麼”的焦慮,而是能夠更安然地享受當下的每一個時刻。我通過這本書,學會瞭“放下”——放下對過去的迴憶,放下對未來的擔憂,放下對他人的評判。當我們能夠真正做到放下,你會發現,內心的空間會變得無比廣闊。這本書並沒有給我提供一個現成的答案,而是引導我去思考,去探索,去發現屬於自己的答案。它讓我感覺到,我不再是一個被動接受信息的人,而是一個主動參與生命探索的旅者。這本書,是我近期最滿意的一次閱讀體驗,它帶給我的,遠不止是知識,更是一種生命狀態的提升。
评分讀完《莊子七講: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我最大的感受是,原來智慧可以如此溫柔而有力。作者在解讀莊子的時候,並沒有試圖將他“現代化”到失去原有的韻味,而是保留瞭莊子思想最核心的部分,並通過淺顯易懂的方式呈現齣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關於“心齋”的章節。我們常常被各種外界的信息所乾擾,思緒萬韆,難以平靜。而“心齋”,在我看來,就是一種讓心靈迴歸寜靜、純粹的狀態。作者用瞭很多貼切的比喻,讓我能深刻地理解,當我們真正做到“心齋”,便能清晰地看到事物的本質,不再被虛妄的錶象所迷惑。這本書並沒有給我灌輸任何具體的“人生指導”,它更像是一個引領者,帶我走進一個充滿智慧的花園,讓我自己去采摘屬於我的那朵花。我尤其喜歡書中對“道”的理解,它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貫穿於萬事萬物之中的一種自然規律。當我們能夠理解並順應這種規律,我們便能更好地“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我發現,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感到痛苦和睏頓,是因為我們逆著“道”而行,試圖用自己的力量去強行改變一些本該自然發生的事情。這本書讓我學會瞭“無用之用”,明白很多看似“無用”的東西,往往蘊含著最深刻的價值。它讓我不再追求那些錶麵的、功利的“用”,而是去發掘生命最本真的、最自在的“用”。這是一種非常深刻的轉變,讓我感覺自己的心靈得到瞭極大的解放。
评分《莊子七講: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這本書,我拿到手的時候,就被它的名字吸引住瞭。莊子,這個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古老而深邃的智慧,而“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更是點齣瞭這本書的核心——不是教你如何“做”什麼,而是如何“是”什麼,如何在天地萬物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並發揮齣最本質的價值。拿到書後,我迫不及待地翻開。我一直覺得,在現代社會這個快節奏、高壓力的環境下,我們常常迷失在各種外在的評價和目標裏,忘瞭生命最根本的需求是什麼。這本書仿佛一股清流,讓我停下腳步,重新審視自己。我尤其喜歡書中對於“逍遙遊”的解讀,不再是簡單的放浪形骸,而是看到一種內在的自由,一種不受外物拘束的心境。作者的講解,沒有那種居高臨下的說教,而是像一個老友,娓娓道來,將莊子那些看似玄奧的哲學,化解成生動鮮活的道理。我經常會在閱讀過程中,停下來,看著窗外的雲捲雲舒,感受風的吹拂,仿佛莊子筆下的那個北冥巨鯤,在廣闊的天地間遨遊,那種感覺,是無比放鬆和自在的。這本書不僅僅是閱讀,更是一種體驗,一種對生命本質的迴歸。我發現,很多時候,我們所謂的“煩惱”,其實源於我們對事物看得太重,對自我看得太大。莊子提倡的“無為”,在我看來,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一種順應自然,不強求,不執著的狀態。當你不再糾結於得失,不再被他人的眼光所束縛,你會發現,生活本身就充滿瞭無限的可能。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它能喚醒我們內心深處沉睡的智慧,讓我們重新認識生命,並找到屬於自己的“大用”。我強烈推薦給所有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壓力大,或者隻是想獲得一種心靈平靜的人。
评分這是一本讓我感到“醍醐灌頂”的書,雖然它講的都是非常古老的哲學,但卻對現代人的生活有著極其深刻的啓示。《莊子七講: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這本書的名字本身就蘊含著一種強大的吸引力。作者的講解,我真的要好好誇贊一下,他沒有使用任何生僻的術語,也沒有故作高深,而是用一種非常親切、非常樸實的語言,將莊子那深邃的智慧,一一展現在我們麵前。我最喜歡的部分是關於“逍遙”的闡釋。我們常常把逍遙理解為一種逃避,一種不負責任。但莊子告訴我們,真正的逍遙,是一種超越,是一種自在,是一種在不被外物所束縛的狀態下,活齣生命的本真。這本書讓我開始審視自己那些不必要的“追求”。我們總是被外界的評判標準所左右,不斷地追逐名利,追逐認可,卻忽略瞭內心最根本的需求。莊子提醒我們,生命的“大用”,不在於你擁有多少,而在於你如何“是”自己。它讓我學會瞭“接受”,接受自己的局限,接受生活的不確定,接受萬物的無常。這本書,就像是一劑心靈的良藥,讓我能夠卸下許多不必要的包袱,以一種更輕盈、更自由的狀態去麵對生活。我真的覺得,這本書能夠幫助很多人找迴內心的寜靜和力量。
评分讀完《莊子七講: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原來真正的智慧,是如此的樸實無華,卻又蘊含著無窮的力量。作者的敘述,沒有絲毫的矯揉造作,完全是以一種非常純粹的方式,去解讀莊子。我尤其喜歡書中關於“順其自然”的論述。在現代社會,我們總是被“掌控”、“規劃”、“改變”這些詞匯所包圍,仿佛一切都應該按照我們的意願發展。但莊子提醒我們,很多時候,強行改變隻會帶來更多的痛苦。接受事物的本來麵貌,順應自然的規律,反而能獲得真正的自由。這本書讓我開始審視自己那些不必要的“抗爭”。我們總是與各種事物抗爭,與他人抗爭,甚至與自己的內心抗爭。但當我們學會放下那些執念,學會“無爭”,你會發現,生活會變得異常平靜。我通過這本書,理解瞭“生命本身的大用”並不在於外在的成就,而在於內在的覺醒。它不是要你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而是要你迴歸到你本來就是的那個“生命”。它讓我學會瞭“欣賞”,欣賞落葉的飄零,欣賞風的無形,欣賞生命中的一切不完美。這本書為我打開瞭一扇新的窗戶,讓我看到瞭一個更廣闊、更自由的世界。
评分坦白說,剛開始拿到《莊子七講: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這本書,我有點忐忑。莊子,在我印象中,是個難以企及的智者,他的思想深奧難懂,總感覺距離我的日常生活很遙遠。然而,這本書徹底顛覆瞭我的認知。作者的講解方式極其巧妙,他沒有生硬地羅列晦澀的理論,而是用一種非常生活化、非常貼近人心的語言,將莊子的智慧娓娓道來。我尤其驚嘆於書中對“安時處順”的闡釋。在現代社會,我們總是被“追求”、“目標”、“成功”這些字眼裹挾著,仿佛停滯不前就是一種失敗。但莊子提醒我們,生命本身有其自然的節奏,順應這個節奏,反而能獲得更大的自在。這本書讓我開始審視自己那些不必要的焦慮和掙紮。我常常會因為一些小事而耿耿於懷,因為達不到彆人的期望而感到沮喪。但讀瞭這本書,我纔明白,很多時候,我們是把自己活成瞭“工具”,而不是“生命”。“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對我來說,不再是宏大的概念,而是迴歸到最根本的層麵——如何在這個世界上,以最真實、最自在的方式存在。我發現,當我不再糾結於“應該”做什麼,而是去感受“想要”做什麼,去關注自己內心的聲音時,生活反而變得更加充實和有意義。這本書讓我學會瞭“不爭”,不是消極避世,而是懂得在恰當的時候放手,懂得尊重事物的自然發展。它幫助我卸下許多不必要的包袱,讓我能夠更輕鬆、更從容地麵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
评分《莊子七講: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這本書,我真的非常喜歡。它不像很多暢銷書那樣,提供一些所謂的“成功秘訣”或者“快速緻富的方法”,而是引導你去探索更深層次的生命智慧。作者的講解方式,我個人覺得非常棒,他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學者,而是像一個同行者,帶著你一起去領悟莊子的思想。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齊物論”的部分。我們總是習慣於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一切,區分“是”與“非”,“好”與“壞”。但莊子告訴我們,很多事情並沒有絕對的對錯,隻是看你站在哪個角度。這本書讓我學會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們常常因為外物的得失而影響自己的情緒,因為彆人的評價而否定自己。但莊子提醒我們,這些都是外在的,真正的價值在於我們內在的生命本身。我通過這本書,開始理解“大用”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做齣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是能夠順應自然,發揮自己最本質的潛能。它讓我擺脫瞭那種“非要證明自己”的衝動,而是能夠更安然地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並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力量。這本書對我來說,就像是一次心靈的“洗禮”,讓我能夠卸下許多不必要的負擔,以更輕盈、更自由的狀態去生活。我真的覺得,這本書能夠幫助很多人找迴內心的平靜和方嚮。
评分這是一本讓我深刻反思自己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嚮的書。當我拿起《莊子七講: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時,我就被書名所吸引,它觸及瞭我內心深處對生命意義的追問。作者並沒有用艱澀的語言來解釋莊子的哲學,而是用一種非常接地氣的方式,將莊子思想中的精華提取齣來,並與我們當下的生活聯係起來。我最喜歡的部分是關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闡釋。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我們常常感到孤立無援,與自然、與他人之間仿佛隔著一道無形的牆。莊子卻告訴我們,我們本身就是這個宏大宇宙的一部分,萬物皆是你的兄弟姐妹。這種“一體感”,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溫暖和力量。這本書讓我開始審視自己那些不必要的執念和欲望。我們常常被社會的評價體係所裹挾,不斷地追求物質的滿足和外在的認可,卻忽略瞭內心最真實的需要。莊子提醒我們,生命的“大用”不在於擁有多少,而在於如何“是”自己。它讓我學會瞭“知足”,不是得過且過,而是懂得感恩當下,珍視生命本身的價值。我發現,當我對生活中的一切不再那麼“較真”,而是以一種更輕鬆、更豁達的態度去麵對時,生活反而變得更加有趣和豐富。這本書為我提供瞭一種全新的視角,讓我能夠跳齣固有的思維模式,去發現生命中那些被我們忽略的美好和可能性。
评分這是一本讓我腦海中那些模糊的關於“智慧”的概念,瞬間變得清晰起來的書。莊子,我之前對他的印象,停留在一些零散的典故和成語裏,總覺得他的思想離現代生活太遠,太過飄渺。但這本書,通過“七講”的結構,非常有條理地把我帶入瞭莊子的世界。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它不是一本枯燥的哲學說教,而是真正地引導你去“理解”莊子,去“感受”莊子。作者在闡釋“齊物論”的時候,真的讓我眼前一亮。我們總是習慣於將世界分為“你”和“我”,“好”與“壞”,“對”與“錯”,然後在這些對立中掙紮。但莊子告訴我們,這些都是相對的,是視角的問題。當你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你所見的“真相”也會不同。這本書讓我開始反思,我是否過分執著於自己的觀點,是否在不知不覺中製造瞭許多不必要的衝突?作者用瞭很多生動的例子,把莊子那些哲學思辨,化解成瞭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場景。比如,在談論“德”的時候,我突然明白,真正的“德”,不是刻意去做什麼,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流露,是一種生命的本真狀態。我不再覺得“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是一個多麼遙不可及的目標,而是變成瞭一種可以去實踐的、一種生活態度。它讓我意識到,我們每個人內在都蘊藏著巨大的能量,隻是常常被我們自己的觀念和執念所束縛。這本書就像一個鑰匙,打開瞭我內心的一扇門,讓我看到瞭更廣闊的風景。閱讀這本書,讓我感覺像是在進行一次深刻的自我對話,每一次翻頁,都是對自我的一次重新認識和整閤。
评分《莊子七講: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這本書,絕對是我近期閱讀中,最讓我“耳目一新”的一本。我一直對中國古典哲學很感興趣,但莊子,對我來說,始終是那個最難懂的“一座山”。然而,作者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讓我翻越瞭這座山,並看到瞭山上絕美的風景。書中的“七講”結構,就像是為我量身定做的登山路綫,每一講都引導我走嚮更深層、更開闊的視野。我最被觸動的是,作者在解讀“莊子”的“無為”時,並沒有將其描繪成一種消極的避世態度,而是將其升華為一種積極的順應自然、不妄為的智慧。這讓我擺脫瞭之前對“無為”的誤解,理解瞭它是一種更高級的“有為”。在現代社會,我們被教導要“努力”、“奮鬥”、“拼搏”,仿佛不這樣做就是落後。但莊子提醒我們,有時候,“不爭”纔是真正的智慧,順應大勢,反而能事半功倍。我通過這本書,重新認識瞭“我”這個概念。我們常常過於執著於“自我”,固守自己的想法和立場,從而與他人産生隔閡,與世界産生衝突。莊子倡導的“物化”,讓我看到瞭超越個體局限的可能性,讓我明白,當放下“我執”,你纔能真正地融入萬物,體驗到“活齣生命本身的大用”的那種廣闊與自由。這本書真的像一盞明燈,照亮瞭我內心深處的一些盲區,讓我看到瞭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