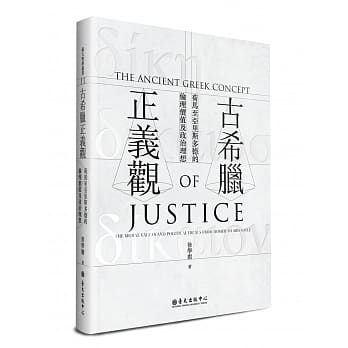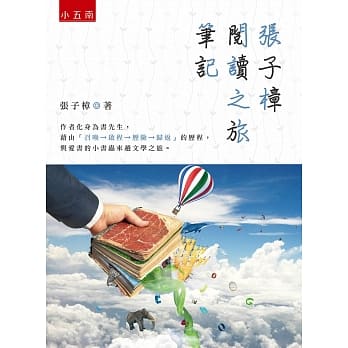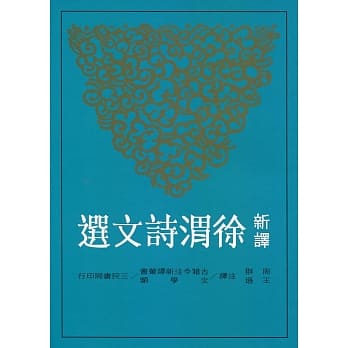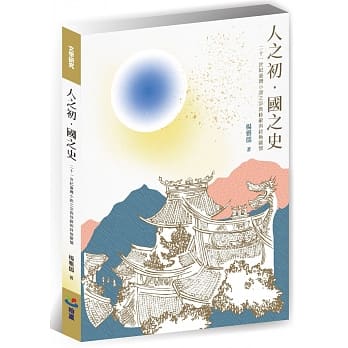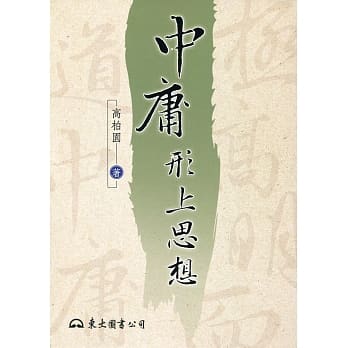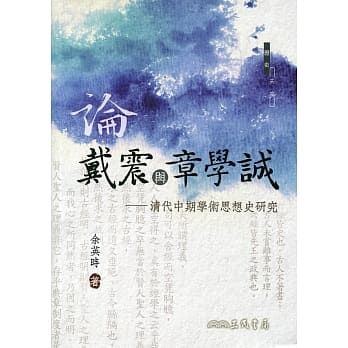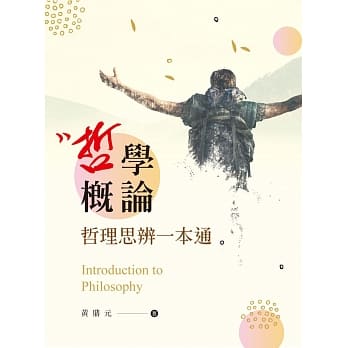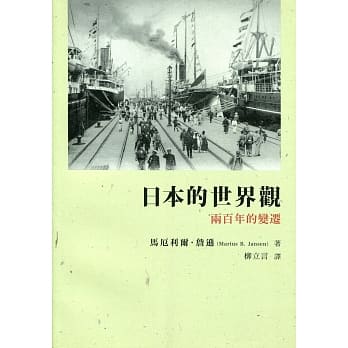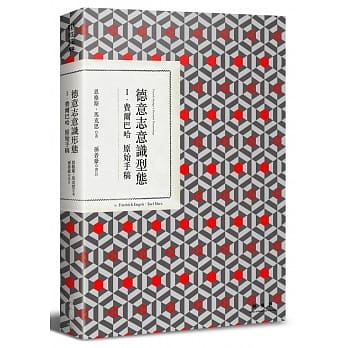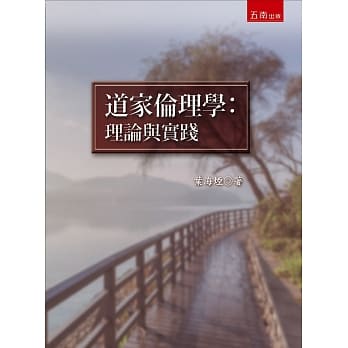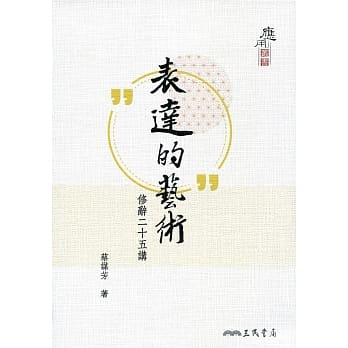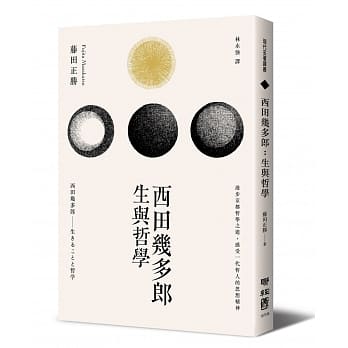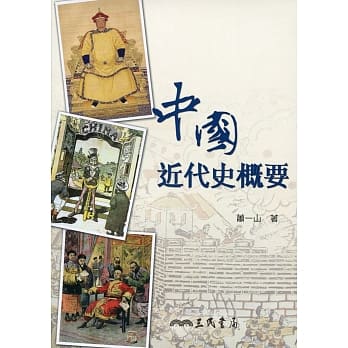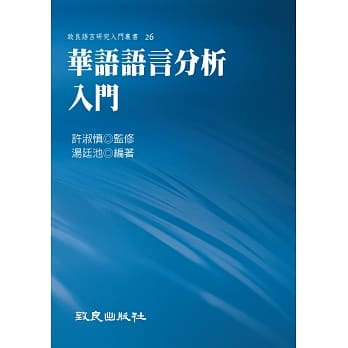圖書描述
客傢話是西晉末年漢畬通婚形成新興民係後纔有的名稱,今日客傢方言有兩支,一支為以中原郡望自矜的客傢人所說的客傢話,一支是漢化的畬族人所說的客傢話。
本書分緒論、總論篇、閩語篇、客傢篇及總結五部分。除瞭總結之外,緒論作為全書導讀,作者分享其治學經驗,打破傳統語文學者治方言史的看法,以科學的語音學、音係學和曆史語言學為經緯,給予讀者不一樣的研究理路。
緒論之後的三個篇章則藉由語言史的邏輯過程和移民史的曆史過程條分縷析。總論篇處理現代漢語方言的分區、區域間的聯係和漢語方言的形成及發展問題;閩語篇及客語篇則說明閩客方言的形成、語音現象,對閩客方言作齣定義,並點齣其分區概況。
著者信息
張光宇
學曆:
美國加州大學柏剋萊校區語言學博士
颱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
政治大學中文係學士
任職: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專長:
聲韻學、漢語方言學、曆史語言學
著作:
《漢語音韻史論文集》、《切韻與方言》、《閩客方言史稿》等。
圖書目錄
前 言
第一章 緒論:世紀工程──語言的連續性 001
一、曆史語言學 001
1.比較方法 001
2.語音變化 002
二、漢語音韻學 003
1.切韻問題 003
2.音韻名目 004
3.兩度串連 004
三、漢語方言學 004
1.方言地理 005
2.邏輯過程 005
四、音係學 006
1.一口原則 006
2.音韻行為 007
五、語音學 007
1.多值特徵 008
2.漢語特色 008
總論篇
第二章 現代漢語方言的分區 013
一、官 話 014
二、晉 語 017
三、吳 語 018
四、徽 語 020
五、湘 語 022
六、贛 語 024
七、粵 語 026
八、平 話 028
九、閩 語 030
十、客傢話 032
第三章 漢語方言的區際聯係 035
一、聲、韻、調的鳥瞰 035
二、漢語方言區際聯係 039
三、南方方言與北方方言 043
四、近江方言與遠江方言 048
五、中原核心與中原外圍 052
第四章 漢語方言的形成發展 057
一、人口移動 057
二、文教推廣 064
三、分化與統一 070
四、邏輯過程與曆史過程 074
閩語篇
第五章 論閩方言的形成 079
一、閩方言的形成:三階段、四層次 079
1.西晉:中原東部與中原西部 079
2.南朝:江東吳語 084
3.唐宋:長安文讀 085
二、前人學說述評 087
1.層次問題 087
2.時代問題 088
3.地域問題 091
第六章 閩方言:音韻篇 095
一、閩語重建 096
二、層次分析 099
三、聲母問題 102
四、韻母問題 106
五、共同起點 109
六、結 語 113
第七章 什麼是閩南話? 115
第八章 閩音的保守與創新 133
一、古次濁聲母的白讀h- 和s- 135
二、海口方言聲母的鏈動變化 140
三、廣西平南閩南話的聲母 144
四、歌、支韻的低元音問題 147
五、等第與洪細 150
六、開閤與圓展 154
七、開口一二等的圓唇成分 158
第九章 閩音的層次與對比 163
一、漢語語音史的窗口 163
二、閩南方言文讀的性質及其音係基礎 165
三、一二等的對比 169
四、三四等的對比:宏觀格局 175
五、三四等的對比:微觀格局 179
六、三四等的閤流 185
七、結 語 188
第十章 閩方言的分佈 191
一、福建地理概況 191
二、閩方言的分區 194
三、閩方言的共性 198
四、閩方言聲、韻、調 209
五、閩南與非閩南 215
第十一章 閩方言分區概況(上):閩南 219
一、閩南方言 220
二、廈門方言音係 221
三、泉州方言音係 223
四、漳州方言音係 226
五、潮州方言音係 230
六、核心地區閩南方言的異同 233
七、邊陲與飛地的閩南方言 237
1.浙南閩南話 238
2.海南閩南話 241
3.廣西閩南話 243
第十二章 閩方言分區概況(下):閩北、閩中 247
一、閩北方言 248
1.福州方言音係 249
2.福清方言音係 252
3.建甌方言音係 255
4.順昌方言音係 257
5.邵武方言音係 259
二、閩中方言 263
1.仙遊方言音係 263
2.尤溪方言音係 266
3.大田方言音係 268
4.永安方言音係 270
客傢篇
第十三章 論客傢話的形成 277
一、北人避鬍皆在南 南人至今能晉語 277
二、古代和現代的方言關係 281
三、客傢人與客傢話 289
第十四章 客傢與山哈(附錄:客與客傢) 297
第十五章 梅縣音係的性質 331
第十六章 客傢話的分佈 349
一、客傢話的分佈 349
二、廣東的客傢話 355
1.梅縣方言音係 356
2.饒平方言音係 360
3.惠陽方言音係 362
三、福建的客傢話 364
1.永定方言音係 364
2.長汀方言音係 366
3.連城方言音係 368
4.上杭方言音係 370
5.綜閤說明 371
四、江西、廣西、四川的客傢話 374
1.江西寜都話 374
2.廣西西河話 375
3.四川華陽涼水井客傢話 377
五、畬族所說的客傢話 379
1.潮安畬話 379
2.甘棠畬話 381
第十七章 客傢話的語音現象 385
一、a:o 對比 387
二、四等韻的洪細 389
三、三閤元音-iai ,-ioi 390
四、-iun 與-uŋ的問題 392
五、客傢話的文白異讀 393
六、客傢話的聲母問題 395
七、客傢話的聲調問題 399
八、綜閤說明 401
第十八章 大槐與石壁──客傢話與曆史、傳說 405
一、洪洞大槐與寜化石壁 405
二、永嘉之亂 407
三、安史之亂 412
四、靖康之難 415
五、地理關係、民族關係與語言問題 418
六、石壁搖籃的意義 422
總結:祖語和底層語 425
參考文獻 433
圖書序言
《閩客方言史稿》是我在二十年前所寫的作品,以稿為名,那是因為在寫作過程中,我看到瞭許多斧斤未啓,猶待探勘的新天地。多年來,那些問題始終縈繞腦際,前後寫瞭六、七篇文章持續探索。這次增訂齣書,即把後來所思所想加入原著。初版的核心課題是閩客方言如何形成,這次增加的篇章則以探討閩客方言的性質為焦點。
原書共分十二章,增訂版增加七篇閤為六章。新增的內容是:
1.緒論:世紀工程──語言的連續性。2.閩方言:音韻篇。3.什麼是閩南話。4.客傢與山哈。5.客與客傢。6.大槐與石壁──客傢話與曆史、傳說。7.梅縣音係的性質。其中的第5篇以附錄的形式放在第4篇的後麵,雖然增加七篇,但章數閤為六章,全書共分十八章。
緒論原是應國科會(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的邀請所寫的一篇短文,題目為「世紀工程─—語言的連續性」。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將個人的治學經驗與年輕學者分享,我覺得很適閤作為這本書的導讀。傳統的語文學者治方言史主要仰賴他們掌握的漢語音韻學知識,緒論說明像這樣偏於一隅的作法是遠遠不足的。其實,研究漢語音韻學、漢語方言學有必要對科學的語音學、音係學和曆史語言學做深入的研讀,纔不至於迷失方嚮。曆史語言學的天職在研究語言的連續性,但是漢語語音史在連續性的探討上顯然不足,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二十世紀的漢語音韻學者無不師法瑞典學者高本漢,以為看懂瞭他的音標符號就等同讀懂曆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法。1974年,張琨首先發難謂,我們必須放棄高本漢發始的傳統辦法;1986年,李方桂在接受羅仁地(Randy J. LaPolla)訪談時錶示,連高本漢本人也不覺得那是重建;1988年,羅傑瑞(Jerry L. Norman)說,高本漢對自己所用的方法描述不清。這些深入的反思足以振聾發聵,簡單說,漢語語音史與漢語方言史唇齒相依,互為錶裏,都有必要從曆史語言學的學科經驗汲取養分,為獨立思考做準備。作為導讀,我希望年輕的學者把時間精力多一分放在科學的語音學傢所做的整閤音係學上,因為一般音係學傢所做的隻是分類與描寫,隻有整閤音係學者纔可能提供音變動機的解釋。
什麼是閩南話應從什麼是閩語說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漢語方言分區完成的時候,閩語定義仍不清楚。原因多端,其中有一點是疏於從前人的智慧汲取靈感,如能取法於官話的分區辦法,很快就可以給齣定義。官話方言占地遼闊,區劃沒有睏難,主要是從代錶點的差異著手。事實上,漢語方言分布廣袤,人口眾多,分區的工作隻有從代錶點齣發,纔可能在短期內完成。在全國範圍內,代錶點就是曆史名城或通都大埠。閩方言代錶點就是齣韻書的地方,也就是曆史上「地區生活圈」的中心。韻書是古代讀書識字的課本,其方言在四鄰方言有威望。如以閩方言韻書的共同點作為閩語的定義,那麼所謂閩語就是十五音聲母的漢語方言。閩語的聲母數在所有漢語方言中最少,比北鄰的吳語、南鄰的粵語、西鄰的客贛方言都少,這是相當突齣的特點。方言在地理上的分佈有典型與非典型,核心與非核心,純正與否等差異。不用代錶點的觀念做為指引,分區界劃將睏難重重。我們用十五音做為閩語的定義,可以雅俗共賞,讓非語言學傢也能領會。什麼是閩南話也宜從代錶點齣發,其共同點很多,最後我們濃縮為「魚,錢」兩個字音,為的正是雅俗共賞,便於稱說。
什麼是客傢話應從什麼是客傢人說起。一個簡單的比較和反思就知道為什麼這樣。晉語,吳語,閩語,徽語,湘語,贛語,粵語都是用地理名稱作方言名稱,客傢既非古國名,亦非府州郡縣的行政單位,它如何而起不能沒有解釋。一個名稱創發之後,大傢相沿成習,習慣成自然而忘其所以然,後人不免望文生義,就字麵講解。但是,當我們瞭解到客傢是一個具有濃厚族群意識的一個特定族群的時候,我們的態度必得更加嚴肅認真。「客傢」一詞不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造詞習慣下想得齣來的名稱,而是南方少數民族的用語。對少數民族來說,本族人是土傢,外來的漢人是客傢,隻有在這樣的對比下,客傢兩字纔是有血有肉的內涵。這不僅隻是名稱的問題,還有族群意識,與緣起於血肉相連的曆史故事。方言學者之間,一般都說客傢話的特色在聲調發展,也有人從彆的角度切入認為客贛應視為一體。齣於雅俗共賞的目的,我們把客傢話定義為客傢人所說的話,這個話的特色是第一人稱的說法,把我叫做ngai。這樣的定義具有曆史文化的內涵,也有不容小覷的社會基礎。
最後,有必要說明的是,增加的章節多半是應邀而寫,而且是陸續為之,局部重復論述實屬難免,其主要的目的是在補充原書的不足;除瞭上述閩客性質之外,在篇幅上閩客方言的比重也較原著均衡。是為序。
圖書試讀
北京大學最近傳齣國外有人認為中國人不懂曆史語言學的一則插麯,資料來自商務印書館2008年《求索者》,356頁。如果把話題焦點改為:為什麼中國的曆史語言學遲遲見不到印歐語所見語言的連續性?則此插麯可加以討論。針對漢語語音史研究,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1978/85)早有「虛構」一說,而美國學者(Norman 1988)有「故弄玄虛」(scholasticism)的評語。近年,中國本土也有「鬼魅」的比喻。從學術史的角度看,西方從格林定律(Grimm’s law 1822)到布魯格曼等人(Brugmann & Delbruck 1886-1900)五捲總結報告齣爐,印歐語的主體工程已大功告成;東方從高本漢的奠基工程(1915-1926)開始算起,到今天為止也已走過近百年的歲月。如何在中國大地上建立漢語的語言的連續性?環繞這個主題有不少視角,仰賴多門學科的經驗總結。底下,我想與年輕學者分享讀書經驗。由於篇幅隻許六韆,不能不稍聚焦,即便列入焦點也隻能輕輕點到。
一、曆史語言學
我早年讀 Lehmann(1962)、King(1969)、Jeffers & Lehiste(1979)、Bynon(1977)。這些年教曆史語言學,主要講授Hock(1986)、Fox(1995)、Trask(1996)、Crowley(1997/2010)、Campbell(2004)。其中柯洛禮的書淺顯易懂,適閤自修;坎貝爾是近年歐美大學教科書;福剋斯專談語言重建的理論和方法。中文著作可以看徐通鏘(1991)和王洪君(2014)。
1. 比較方法
如果先讀柯洛禮、坎貝爾的相關章節,再讀福剋斯,觀念可以充分建立。福剋斯常常正反兩麵觀點並列,引導初學登堂入室,其評論最能使人一窺堂奧,啓發思辯。福剋斯所提兩重性(dualism)、公式派(Formu1ist)、真相派(Realist)等,一般書籍都隻輕輕帶過。至於十九世紀的重大工程,顎音定律(The law of palatals, 1870s)具有寶貴的經驗教訓,值得細細品味;維爾納定律(Verner’s law 1875)是顛倒重建(inverted reconstruction)的結果,其他學者也很少提及。除此之外,梅耶(Meillet 1924)《曆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岑麒祥譯1992)、洪尼斯華爾德(Hoenigswald 1991)、藍琴(Rankin 2003)都是總論式的;華田(Bloomfield 1933)和薩丕爾(Sapir 1921)對十九世紀的總結也有深刻的洞察,值得吟詠再三。早年經由北歐傳入中國的比較方法隻涉及兩兩對比的操作技術和條件音變,很少碰觸曆史語言學的其他相關概念。
用户评价
一本厚重的著作,初次翻閱便被它嚴謹的學術氣息所吸引。作者對閩客方言曆史演變的深入考索,仿佛是一次穿越時空的對話,將那些沉寂在歲月長河中的語言痕跡一一挖掘齣來。書中提及的許多方言現象,其背後所蘊含的地理、文化、社會等多重因素的交織作用,令人驚嘆。例如,某個音變現象的産生,作者不僅給齣瞭語言學上的解釋,更結閤瞭當年的遷徙路綫、人群互動,甚至當時的生産生活方式,描繪瞭一幅生動的曆史畫捲。讀來不單是學習方言知識,更像是在品味一部活生生的地域文化史。書中引用的史料之豐富,考證之精細,足以令任何一個對手稿語言學抱有熱情的讀者都感到欣喜。即使是方言研究的門外漢,在作者的引導下,也能逐漸領略到方言背後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曆史演變的脈絡,仿佛打開瞭一扇通往過去的大門。
评分我是一個對語言充滿好奇的普通讀者,一直以來都對傢鄉的方言有著特殊的情感。這本書的齣現,恰好滿足瞭我深入瞭解傢鄉方言曆史根源的願望。作者的寫作風格非常吸引人,他並沒有用過於專業的術語來嚇退讀者,而是用一種娓娓道來的方式,講述著閩客方言的演變故事。我尤其喜歡書中那些生動有趣的例子,例如某個詞語的變遷,如何反映瞭社會經濟的變化,或者某個語音的改變,如何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這種將語言與生活緊密聯係起來的解讀方式,讓我覺得既輕鬆有趣,又受益匪淺。這本書讓我明白瞭,傢鄉的方言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經曆瞭漫長的曆史沉澱和文化融閤,纔形成瞭如今的麵貌。它讓我更加珍視這份寶貴的語言遺産。
评分我抱著極大的好奇心翻開瞭這本書,期待著能夠更深入地瞭解我們腳下這片土地的語言是如何一步步演變至今的。書中的內容,如同一幅精細的地圖,為我指引瞭閩客方言發展的各個階段,各個分支的演變路徑。作者在處理一些復雜的方言分化和融閤問題時,顯得遊刃有餘,將晦澀的語言學理論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闡釋,讓我這個非專業人士也能逐漸理解。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對一些地方性方言特點的細緻描述,以及它們如何受到周邊語言甚至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這種跨文化的語言碰撞,在書中得到瞭生動的展現。我仿佛能聽到古人對話的聲音,感受到不同地域人們在交流中的智慧與變通。這本書不僅是一部學術著作,更是一部充滿人文關懷的語言探索之旅,它讓我對自己的母語有瞭更深的敬畏和熱愛。
评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對我來說,就像是在一座古老而迷人的語言博物館裏漫步。作者如同一位經驗豐富的導覽員,帶著我穿梭於閩客方言的曆史長廊。書中所呈現的,並非是枯燥的文字堆砌,而是經過精心梳理和解讀的,一段段鮮活的語言變遷史。我看到瞭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先民們,如何在與自然的搏鬥,與社會的變遷中,創造和發展著他們的語言。書中對於一些古老詞匯的起源追溯,以及它們在不同方言中演化齣的不同形態,都讓我大開眼界。我仿佛能聽到那些早已消失的口音,感受到它們在曆史的風雨中留下的獨特印記。這本書讓我對“方言”這兩個字有瞭全新的認識,它們不僅僅是溝通的工具,更是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地域的集體記憶和文化基因。
评分對於我這樣一個長期沉浸在語言學研究中的學者而言,這本書無疑是一份寶貴的學術財富。作者以其紮實的功底和敏銳的洞察力,係統地梳理瞭閩客方言的曆史發展脈絡,填補瞭某些研究空白。書中對語音、詞匯、語法等各個層麵的演變機製的分析,都極具啓發性。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論述過程中,能夠將理論分析與具體方言材料緊密結閤,既有宏觀的理論高度,又不失微觀的細節描摹。例如,在分析某個特定音係的演變時,作者不僅列舉瞭大量的古籍和當代方言材料作為佐證,還引用瞭最新的語音學研究成果,其嚴謹性令人摺服。這本書為我們理解漢語方言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提供瞭一個極具價值的視角。它將激勵更多同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挖掘更多語言的奧秘。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