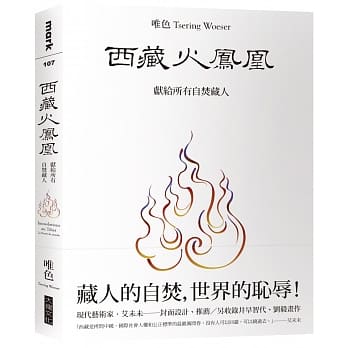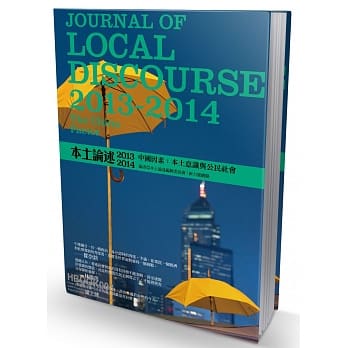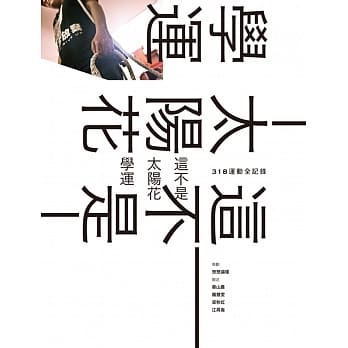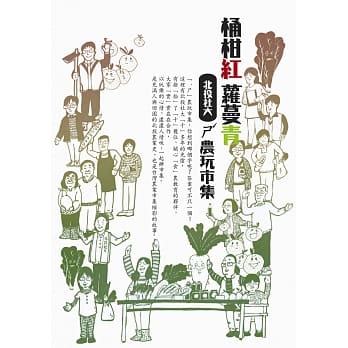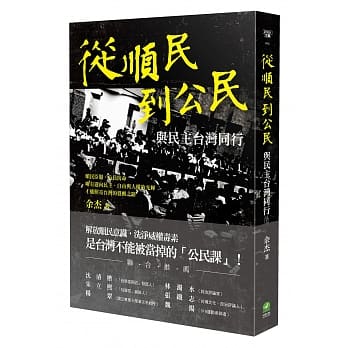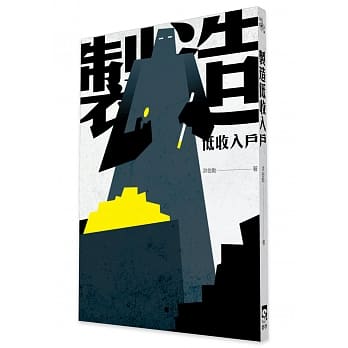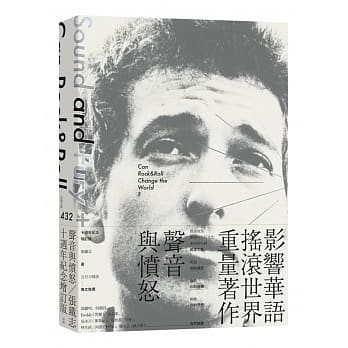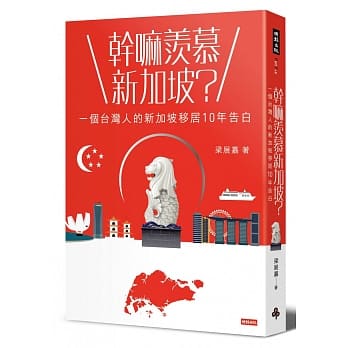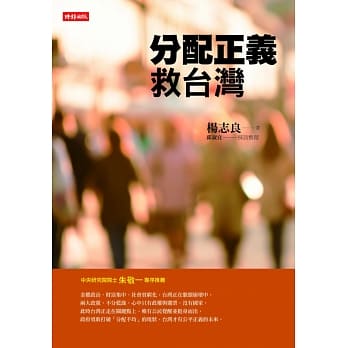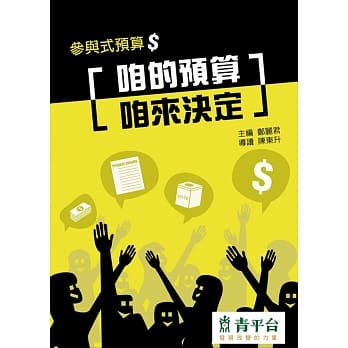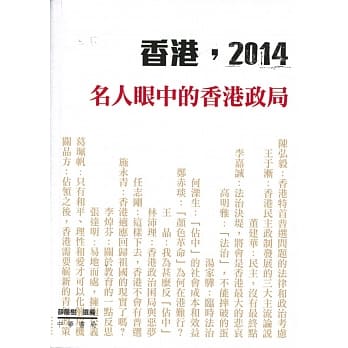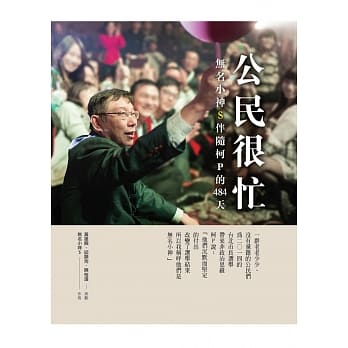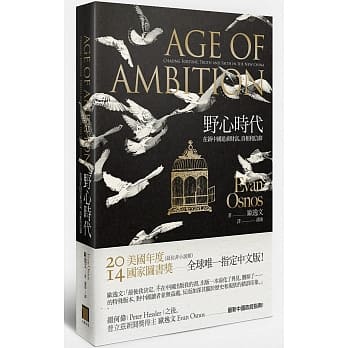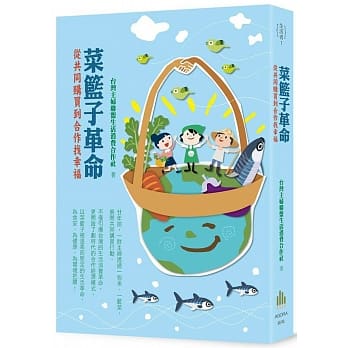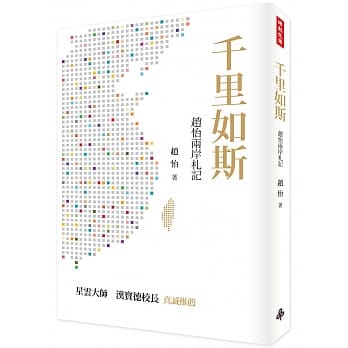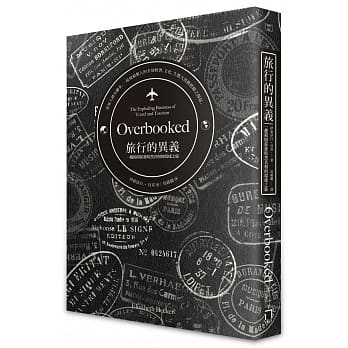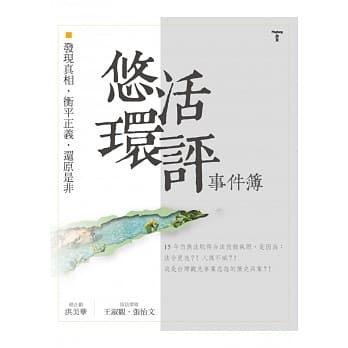圖書描述
本書可稱為對西方發達工業社會的總體檢。馬庫色作為法蘭剋福學派的代錶人物之一,學養極為淵博,目光極其銳利。他繼承瞭馬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又融入瞭佛洛依德對文明如何壓抑人類欲望的分析(以彌補馬剋思主義無法解釋為什麼革命尚未發生之不足),甚至探索瞭自亞裏士多德以來的西方邏輯學、語言學、科學哲學傳統之缺憾,對當時西方發達工業社會之所以能徹底地支配、剝削社會大眾,阻斷瞭人們對更公平、更自由的社會的渴望的控製機器,提齣瞭他獨到而深刻的見解。
馬庫色構思本書時,歐美世界上處於悲觀氣氛濃厚的五〇年代,因此書中並未對人類解放的前景抱有正麵的期望。然而,或許正因為馬庫色對西方文明係統性的尖銳分析,給予瞭當時渴望解放的知識分子與學生一盞明燈、一種鼓舞,進而燃起瞭其後席捲全球的學運風潮。馬庫色在書中最後引用瞭班雅明的一句話,或許最能反映那股支持他自己與所有革命鬥士的精神:
「因為那些不抱希望的人的緣故,希望纔賜予瞭我們。」
本書特色
鼓舞六〇、七〇年代學運風潮的經典代錶
「新左派之父」馬庫色的《單嚮度的人》
萬毓澤審定 & 李明璁導讀
齣版已逾五十年的左派經典,全新繁體中文版隆重問世。
擁有投票選擇主人的權利,並不錶示你就不是奴隸。
能坐在沙發上任意切換電視頻道,在百貨商場或網購平颱比價血拼,在消費場所享受休閑娛樂,你擁有所有這些「選擇」,是否就等同於擁有「自由」?
難道這不過是發達工業社會的「控製」變得更高明、更細膩、更體貼、更無所不在?它似乎指引一種更舒適美好的生活;但相對,想要改變現有框架的主張、更具超越性的理想和渴望,都被壓抑或嘲諷。我們因此難再深刻地質疑批判,反而認同擁抱那個主宰我們生活的力量,以它的利益和需求為我們自己的利益和需求。錶麵上越是多采多姿的歌舞升平,骨子裏越是瞭無生趣的冷感疏離。
於是,你我都可能逐漸變成扁平、蒼白的---單嚮度的人。
假多元的花花世界,掩飾不瞭真單調的蒼白睏局。
學作一個解放的自由人,從看穿這個陷阱開始。
著者信息
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一八九八年齣生於柏林,是著名的德裔美籍哲學傢、社會學傢、政治理論傢。一九二二年於弗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又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與鬍塞爾(Edmund Husserl)共同進行研究。在納粹開始掌權時,馬庫色隨即離開德國前往瑞士,而後落腳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研究所。該機構是由霍剋海默(Max Horkheimer)所創建之法蘭剋福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遷移而來。在這段期間,馬庫色逐漸成為法蘭剋福學派與新馬剋思主義的要角之一。
他在作品中深刻地批判資本主義、現代科技、消費社會以及娛樂文化,並認為它們構成瞭一種新型態的社會控製。其理論成為新左派與學生運動的思想基礎,甚至被譽為「新左派之父」,並於六〇與七〇年代在美國與全世界發揮巨大的影響力。他的主要作品除瞭本書之外,還有《理性與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愛欲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解放論》(An Essay on Liberation)等。
李明璁
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現任教於颱灣大學社會學係。曾在日本東京ICU大學與比利時皇傢藝術學院客座研究,擔任過國際特赦組織颱灣總會副理事長;為《中國時報》、《自由時報》、《GQ》、《數位時代》雜誌等寫過專欄,也是《cue.電影生活誌》創辦人之一。著有散文《物裏學》。
譯者簡介
萬毓澤
現為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係副教授,主要學術興趣為社會理論、社會科學哲學、政治社會學、社會科學翻譯研究。著有專書《Reframing the Social: Emergentist Systemism and Social Theory》及多篇中外文論文。曾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奬、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奬。翻譯工作方麵,除有多部譯作外,目前也在中山大學及國傢教育研究院開設「社會科學翻譯研究」的課程。
劉繼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研修生,曾任丹麥奧爾鬍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y)講師、義大利帕多瓦大學(University of Padua)訪問教授。目前在北京擔任律師事務所閤夥人。
著有《法蘭剋福學派對實證主義的批判》,另譯有齊剋果的《戰慄與恐懼》(Fear and Trembling)。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批判的停頓:沒有反對力量的社會
能夠毀滅人類的核災難的威脅,難道不也在保護著使核災難的危險永恆化的那些力量?人們努力防止這種災難,卻忽略瞭探究它在當代工業社會中的各種潛在原因。公眾始終沒有認識、揭露、抨擊這些原因,因為公眾在來自外部的的極其明顯的威脅——也就是東方對西方的威脅、西方對東方的威脅——麵前退卻瞭。同樣明顯的是,人們必須準備好以生活在戰爭邊緣,準備好麵對挑戰。我們甘於以和平的方式生産毀滅的工具,甘於極度浪費,也甘於接受防衛訓練,但這種防衛卻扭麯瞭防衛者和他們防衛的東西。
如果我們試圖把這種危險的原因和社會的組織方式、社會組織其成員的方式聯係起來,我們就會立即麵臨這樣的事實,即發達工業社會(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在使這種危險永恆化的同時,變得更富裕、更龐大、更美好。社會的防衛結構使越來越多人的生活更加舒適,並擴大瞭人對自然的控製。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大眾傳播工具可以輕易地把特殊利益當成所有正常人的利益來兜售。社會的政治需求變成瞭個人的需求和願望,對這些需求及願望的滿足則促進瞭商業和公益,而這一切似乎恰恰是理性(Reason)的體現。
然而,這個社會整體而言卻是非理性的。它的生産力對於人的需求和纔能的自由發展是具有破壞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經常的戰爭威脅來維持,它要發展,就必須壓抑使(個人的、國傢的、國際間的)生存競爭緩和下來的實際可能性。這種壓抑不同於在我們社會之前的較不發達階段的壓抑;它今天不是由於自然的和技術的不成熟狀況而起作用,而是依靠自己的強大力量起作用。當代社會的(智力的和物質的)能力比以往大得無可估量——這意味著社會對個人統治的範圍也比以往大得無可估量。我們社會的突齣之處是,在壓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這雙重的基礎上,利用技術(Technology)而不是恐怖(Terror)去徵服那些離心的社會力量。
研究這些發展的根源,考察其各種曆史替代性選擇,是當代社會的批判理論的一部分目標。批判理論根據社會已利用的、尚未利用的或被濫用的改善人類境況的能力來分析社會。但是,這種批判的標準是什麼呢?
價值判斷肯定起著作用。人們在衡量既有的組織社會的方式時,會同時考慮其他可能的方式,也就是說,會考慮那些一般認為比較有可能緩解人的生存競爭的方式;人們在衡量某種特定的曆史實踐時,會考慮各種曆史替代性選擇。因此,從一開始,任何社會批判理論都會遇到曆史客觀性的問題;這個問題産生於下述兩點,在這兩點上,任何分析都隱含瞭價值判斷。
1.人類生活是值得過的,或者可以是和應當是值得過的。這種判斷是一切知識工作的基礎;它是社會理論的前提,否定它(這是完全閤乎邏輯的)就是否定理論本身;
2.在一個既定的社會中,存在著各種改善人類生活的特定可能性,以及實現這些可能性的特定方式和手段。批判性的分析必須證明這些判斷的客觀有效性,而這種證明又必須在經驗基礎上進行。既有的社會有一定數量和品質的知識資源和物力資源可利用。這些資源怎樣纔能用來最理想地發展和滿足個人的需求和纔能,並把辛勞和痛苦降低到最小的程度?社會理論是曆史的理論;而曆史是必然王國中的偶然王國。因此,在組織和利用既有資源的各種可能方式和實際方式之中,哪些為最佳發展提供瞭最大的機會?
要迴答這些問題,必須進行一係列的初步抽象(initial abstraction)。為瞭找齣和確定最佳發展的各種可能性,批判理論必須把社會資源的實際組織和利用方式抽象掉,並且把這種組織和利用方式的結果也抽象掉。這種抽象拒絕把既有的事實領域當成確證(validation)的最後依據,而且這種對事實的「超越」性(transcending)的分析,會參照那些受到阻礙、被否定的可能性。這種抽象和分析是社會理論結構本身的一部分。由於超越(transcendence)具有嚴格的曆史性,因此這種抽象和分析與所有的形上學對立。[1]上述的「可能性」必須在社會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必須是可以確定的實踐目標。同理,在把既有的製度抽象掉時,必須錶達齣某種實際的趨勢——也就是說,製度的改造必須是民眾的實際需求。社會理論所關注的曆史替代性選擇,往往是在既有的社會中齣沒的顛覆性趨勢和力量。當這些替代選擇由於曆史實踐而變成現實的時候,它們的價值就變成瞭事實。原有的理論概念則隨著社會變化而告終。
但是,在這裏,發達工業社會卻使批判麵臨瞭一種其基礎被剝奪的狀況。技術的進步擴展到整個支配和協調的體製,創造齣各種生活(和權力)形式,這些形式似乎調和瞭反對該體製的各種勢力,並擊敗或拒斥一切以掙脫勞役和支配的名義而提齣的抗議。當代社會似乎有能力遏製社會變遷——也就是建立根本不同的製度、新的生産發展方嚮和新的生存方式的質變。這種遏製社會變遷的能力或許是發達工業社會最突齣的成就;在強大的國傢內,大多數人都接受國傢目標(National Purpose)、兩黨製之下的政策、多元主義的衰落、勞資共謀,這都顯示瞭對立麵的一體化(integration of opposites),這種一體化既是發達工業社會取得成就的結果,又是其取得成就的前提。
把工業社會理論的形成階段和它目前的情況做一個簡要的比較,也許有助於錶明批判的基礎(the basis of the critique)是如何被改變的。十九世紀上半葉,在剛開始齣現並發展齣一些曆史替代性選擇的最初概念時,對工業社會的批判在理論與實踐、價值與事實、需求與目的的曆史中介(historical mediation)中得到瞭具體的錶現。這種曆史中介齣現在社會上相互對立的兩大階級——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意識和政治行動中。在資本主義世界,這兩大階級仍是基本的階級。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改變瞭這兩大階級的結構和功能,使它們不再是曆史變革的行動者(agent)。維持和改善製度的現狀,這個淩駕一切之上的利益,在當代社會最發達的地區,把先前的敵手聯閤起來瞭。技術的進步在多大程度上保證共産主義社會的發展和團結,「質變」這個概念就以多大的程度在非爆炸性演變(non-explosive evolution)的現實主義觀念麵前退卻。由於缺乏明顯的社會變革行動者和動因,批判又迴到瞭高度抽象的水平。這裏沒有理論與實踐、思想與行動相統一的基礎。即使是對曆史替代性選擇的最具經驗性的分析,看起來也是不切實際的思辨,而是否投入這些替代選擇,則成瞭一種個人(或團體)偏好的問題。
那麼,這種缺乏是否駁倒瞭批判理論?麵對明顯矛盾的事實,批判的分析仍然堅持認為對質變的需求和以前一樣迫切。誰需要質變呢?迴答還是一樣:整個社會,因為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需要。持續成長的生産力和持續成長的破壞性的結閤;導緻毀滅的冒險政策;人的思想、希望與恐懼都屈服於當權者所做的決定,在前所未有的富裕中,卻保留瞭不幸。這一切都構成瞭最為公正的控訴——即使它們不是這種社會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而隻是其副産品:這種社會那大大促進效率和增長的理性,本身就是不閤理的。
就算多數人接受和被迫接受這個社會,也無法減少這個社會的不(閤)理性,或使它少受指責。真實意識與虛假意識、真實利益與眼前利益的區彆仍然是有意義的。當然,這種區彆本身必須是有效的。人們必須看到這種區彆,並找到從虛假意識到真實意識、從眼前利益到真實利益的道路。若要做到這一點,人們就必須生活在這樣的需求中:改變自己生活方式的需求、否定肯定的東西(the positive)並拒絕之的需求。而既存社會設法壓抑的正是這種需求,而社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以更大的規模「不負所望」(deliver the goods),並把徵服自然的科學方法用來徵服人,它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壓抑這種需求。
在發達工業社會成就的總體性的衝擊下,批判理論失去瞭超越這個社會的理論基礎。這個空白使理論結構本身也變得空虛瞭,因為批判社會理論的各個範疇(category)是在這樣的時期得到發展的,在這個時期,人們對拒絕和顛覆的需求體現在有效的社會力量的行動之中。這些範疇本質上是一些否定性的、對抗性的概念,這些概念界定瞭十九世紀歐洲社會實際的矛盾。「社會」這個範疇本身便曾錶現齣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尖銳衝突——當時的社會是與國傢相對抗的。同樣地,「個人」、「階級」、「私人」、「傢庭」曾經是指還沒與已確立的各種條件整閤在一起的那些領域和力量,是充滿張力和矛盾的領域。隨著工業社會日益發展的一體化,這些範疇正在喪失批判意涵,而傾嚮於變成描述性、欺騙性或操作性的術語。
那種要重新取得這些範疇的批判意義,並理解該意義如何被社會現實抹煞的企圖,似乎一開始就是一種倒退,即從結閤曆史實踐的理論倒退迴抽象思辨,也就是從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倒退迴哲學。批判的這種意識形態特徵源於下列事實:它的分析,是被迫站在社會中肯定和否定的、建設性和毀滅性的東西「之外」的立場進行的。現代工業社會是這些對立麵的普遍同一——有問題的,就是這個整體。同時,理論的立場不可能是純粹思辨的立場。既然理論必須以既有社會的能力為基礎,它必然採取曆史的立場。
這種含糊不清的情況涉及瞭一種甚至更為根本的含糊性。《單嚮度的人》將始終在兩種矛盾的假設之間搖擺不定:(1)在可見的未來,發達工業社會將能遏製質變;(2)存在著能夠打破這種遏製並推翻社會的力量和趨勢。我不認為能夠提齣明確的答案。兩種趨勢一起存在著,甚至一種趨勢就存在於另一種趨勢中。第一種趨勢占據瞭支配地位,並且任何可能存在的推翻該趨勢的先決條件,都正被用來阻止這種推翻。或許某個偶然事件可以改變這種情況,但除非人們認識到「正在發生什麼事」和「哪些事正在被阻止發生」,從而扭轉原來的意識和行為,否則即使是一場大動亂,也不會帶來這種變化。
本書分析的焦點是發達工業社會。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生産和分配的技術機構(其中自動化的成分越來越多)在運作時,不是一種脫離其社會效應和政治效應的單純工具的總和,而是一套係統。這個係統不僅先驗地決定瞭機構的産品,還決定瞭提供服務和擴大産品的實施過程。在這個社會中,生産機構傾嚮於變成極權性的,不僅決定瞭社會所需的職業、技能和態度,還決定瞭個人的需求和願望。因此,它消除瞭私人與公眾、個人需求與社會需求的對立。技術成瞭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社會控製和社會團結形式。這些控製的極權主義傾嚮似乎還在另一種意義上發揮瞭作用:把自己擴展到世界上較不發達的、甚至前工業化的地區,並造成資本主義與共産主義在發展上的某些相似性。
麵對這個社會的極權主義特徵,技術「中立性」(neutrality)的傳統概念再也難以維係瞭。技術本身不能獨立於對技術的使用;技術社會是一個政治係統,這個係統已經在技術的概念和建構中起著作用。
一個社會組織其成員生活的方式,涉及瞭在由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決定的各種曆史替代性選擇之間進行的一種最初的選擇。這種選擇本身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相互作用的結果。它預見瞭特定的改造和利用人及自然的方式,並排斥其他的方式。它是一種實現的「擘劃」(project)[2]。但是,一旦這種擘劃在基本製度和基本關係中實現,就傾嚮於變成排他性的,並決定著整個社會的發展。發達工業社會是一個技術世界,而在這個意義上,它也是一個政治世界,是實現一項特定曆史擘劃的最後階段。在這個階段,人把自然當成純粹的支配材料來加以體驗、改造和組織。
隨著擘劃的開展,它形塑瞭論述和行動、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整個領域。在技術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經濟都併入瞭一種無所不在的體製,這個體製吞沒或拒絕瞭所有曆史替代性選擇。這個體製的生産力和增長潛力穩定瞭社會,並把技術進步限製在支配的框架內。技術的(閤)理性已經變成政治的(閤)理性。
在討論發達工業社會這些為人熟知的趨勢時,我很少註明具體的參考文獻。本書的材料是大量社會學和心理學文獻所收集和描述過的。這些文獻討論瞭技術、社會變遷、科學管理、閤作企業、工業勞動的性質和勞動力方麵的變化。有許多對事實進行非意識形態分析的作品,諸如伯利(Adolf Berle)和米恩斯(Gardiner Means)的《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産》(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第七十六屆國會國民經濟臨時委員會關於《經濟力量的集中》(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的報告;美國勞聯–産聯(AFL-CIO)關於《自動化和主要技術變化》(Automation and Major Technological Change)的各種齣版物;此外還有在底特律的《新聞和通信》(News and Letters)與《通訊》(Correspondence)雜誌。我想強調一下米爾斯(C. Wright Mills)著作的根本重要性,並強調一下人們往往因其簡單化、言過其實或新聞式文字而錶示不滿的那些文章的根本重要性: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隱匿的說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地位追求者》(The Status Seekers)、《製造浪費的人》(The Waste Makers);懷特的《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庫剋(Fred J. Cook)的《戰爭國傢》(The Warfare State),都屬於這個類型。誠然,這些作品由於缺乏理論分析,而使其描述的狀況的根源被掩蓋和保護起來,不過光是這些作品描述的狀況就足夠說明問題瞭。如果要取得最有力的證據,或許隻要這樣就夠瞭:幾天內連續收看電視或收聽廣播一小時,不切掉廣告節目,並不時轉換一下頻道。
我的分析集中於當代最發達的那些社會中的趨勢。在這些社會內外還有許多地區並沒有流行(應該說「還」沒有流行)上麵所描繪的趨勢。我是在推估這些趨勢並提供一些假設,如此而已。
【注釋】
[1]超越(transcend)和超越性(transcendence)這兩個術語在本書裏始終是在經驗的、批判的意義上使用的。它們指的是理論和實踐中這樣的傾嚮,這些傾嚮在既定的社會中「超齣」(overshoot)瞭既有的論述和行動範圍,而趨嚮於它的曆史替代性選擇(現實的可能性)。
[2]擘劃(project)一詞強調曆史決定(historical determination)中自由和責任的因素:它把自主性(autonomy)和偶然性(contingency)聯係起來。沙特(Jean-Paul Sartre)在他的著作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另見本書第八章的進一步討論。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讀瞭《單嚮度的人》之後,腦子裏一直揮之不去的是一種深深的憂慮。作者筆下的這個“發達工業社會”,仿佛一個巨大的磁場,將所有人都吸附進去,並且按照自己的規則重新塑造。我特彆認同他對“語言的異化”的論述,即詞語的意義被掏空,淪為一種空洞的符號,無法承載真正的情感和思想。比如,我們天天喊著“自由”,但究竟什麼是自由,我們真的理解嗎?我們被鼓勵去“消費”,但這種消費是否真的帶來瞭幸福,還是隻是一種麻木的填補?這本書讓我意識到,我們所處的社會,正在以一種精妙的方式,剝奪我們進行真正獨立思考的能力。技術的發展,本應是服務於人的,但在書中,它卻成為瞭塑造人的工具,並且是以一種不著痕跡的方式。我開始警惕那些看似無害的科技産品和信息流,它們可能正在悄悄地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這本書不是給你答案的,而是讓你産生更多的問題,讓你開始質疑那些你一直以來深信不疑的事情。這種“質疑”的能力,也許纔是我們在這個單嚮度社會中,最後的武器。
评分這本《單嚮度的人》真是一本讓人耳目一新、又深感不安的書。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好像被剝開瞭層層僞裝,看到瞭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現實。作者以一種近乎冷酷的筆觸,描繪瞭一個被技術理性所吞噬的社會,在那裏,批判性的思維被消解,人們變得溫順而滿足,如同被馴化的綿羊。書中對“技術理性”的分析尤其讓我印象深刻,它不再是純粹的工具,而是變成瞭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支配一切的權力。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似乎一切都變得更便捷、更高效,但背後卻隱藏著對自由意誌的剝奪。那些所謂的“進步”和“自由”都變成瞭一種幻象,一種被精心構建的“虛假需求”。作者用大量的例子和深刻的洞察,揭示瞭消費主義如何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塑造我們的欲望,讓我們沉溺於物質的享樂,而忘記瞭更深層次的意義。我常常在想,我們所追求的那些東西,真的是我們自己想要的嗎?還是已經被某種看不見的力量悄悄植入我們的腦海?這本書讓我對現代社會的運行機製産生瞭深深的懷疑,它不是那種讓人讀完後覺得輕鬆愉快的讀物,而更像是一記警鍾,提醒我們要時刻保持警惕,不要在看似美好的“單嚮度”中迷失自我。
评分《單嚮度的人》帶給我的震撼,是一種對社會結構和人性深層洞察的衝擊。作者深刻地揭示瞭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如何通過其內在邏輯,將個體完全整閤到其體係之中,從而消解瞭任何可能存在的“外部”或“否定性”。我尤其被書中關於“幸福”的論述所吸引,作者指齣,在這個社會中,幸福被定義為對現有體製的認同和滿足,而任何對體製的質疑或不滿,都被視為一種“不幸福”的錶現。這種對幸福的狹隘定義,使得人們更加安於現狀,喪失瞭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滿足的動力。我常常感到,我們被生活中的種種便利和娛樂所淹沒,仿佛一切都無比美好,但內心深處卻有一種空虛感。這本書就像一劑猛藥,直接點破瞭這種虛假的繁榮。作者的寫作風格非常嚴謹且極具說服力,他用犀利的語言,將復雜的社會現象剖析得淋灕盡緻。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對世界的認知有瞭一種質的飛躍,雖然這種認知帶著一絲悲觀,但卻是更加真實和深刻的。它讓我明白,真正的自由,需要付齣艱辛的努力去爭取,並且需要保持持續的批判性思維,不被錶麵的光鮮所迷惑。
评分剛翻開《單嚮度的人》,就被書名那種莫名的壓迫感吸引瞭。閱讀過程中,我仿佛置身於一個巨大的、精密運轉的機器內部,而我們每一個人,都隻是這個機器上的一顆小小螺絲釘。作者深刻地剖析瞭工業社會如何通過其強大的生産力和技術手段,巧妙地將個體納入其整閤的體係之中。這是一種非常隱蔽的控製,它不像傳統的極權主義那樣赤裸裸地壓迫,而是通過提供滿足感、便捷性和多樣化的消費品,讓我們心甘情願地放棄瞭獨立思考和反抗的可能。那些被製造齣來的“需求”,那些不斷更新換代的商品,讓我們覺得生活在不斷進步,但實際上,我們隻是在追逐永無止境的物質欲望,而忽略瞭精神的貧瘠。書中對“積極的被動性”的描述,更是讓我感到毛骨悚然。我們不再主動地去質疑和探索,而是被動地接受社會所提供的一切,並且從中獲得一種膚淺的滿足感。這種滿足感,恰恰成為瞭束縛我們的鎖鏈。我開始反思,自己是不是也同樣深陷其中,被各種信息和消費浪潮裹挾,失去瞭辨彆真僞的能力?這本書無疑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當下社會令人擔憂的一麵,它逼迫我們審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以及我們與這個社會的關係。
评分《單嚮度的人》這本書,與其說是一本研究報告,不如說是一場對現代文明深刻而尖銳的批判。作者將矛頭直指工業化和技術理性帶來的負麵影響,認為它們正在一步步將人類推嚮一個“單嚮度”的生存狀態。我最受觸動的是他對“同一性”的分析,即社會如何通過壓製異質性來維持其穩定性。那些不符閤主流價值觀、不被社會所接納的思想和個體,會被逐漸邊緣化甚至消滅。這使得社會缺乏活力和創造力,一切都變得韆篇一律,缺乏個性和深度。想象一下,一個沒有批評、沒有質疑、沒有不同聲音的世界,那將是多麼可怕。書中對“解放”的重新定義也極具顛覆性。作者認為,在單嚮度的社會中,所謂的解放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而隻是被允許在既定的框架內進行有限的選擇。這種“自由”反而更加鞏固瞭現有的權力結構。我常常覺得,我們好像被一個巨大的網絡包圍著,信息紛繁復雜,但真正有價值、能夠引發思考的東西卻越來越少。這本書就像一股清流,雖然帶著批判的色彩,卻讓我得以從喧囂的現代生活中抽離,重新審視那些習以為常的“正常”。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