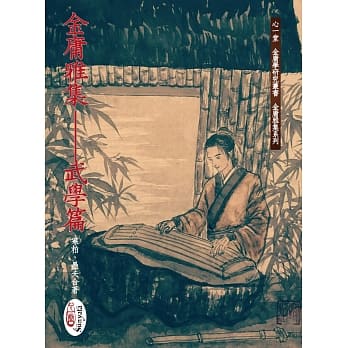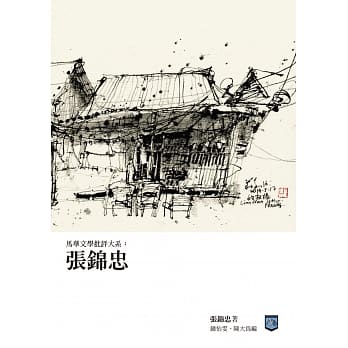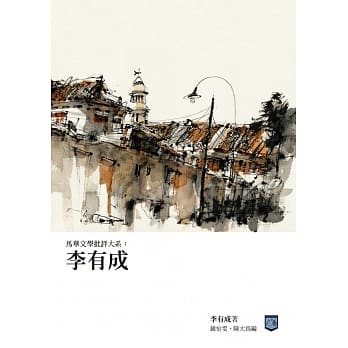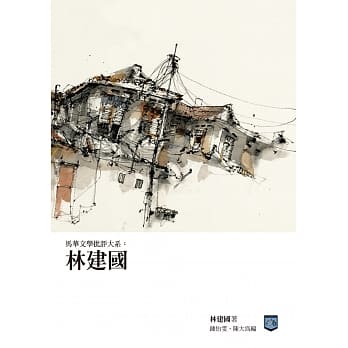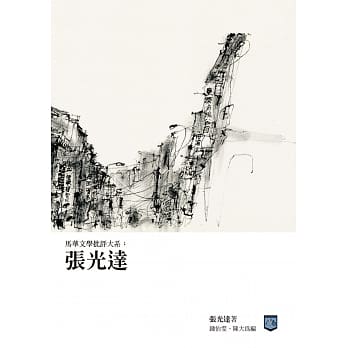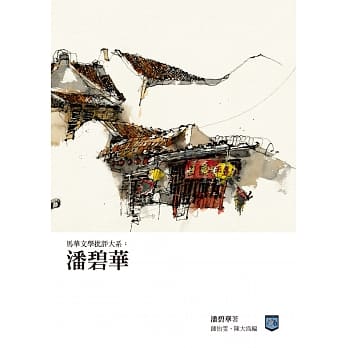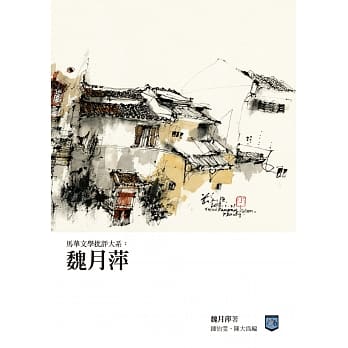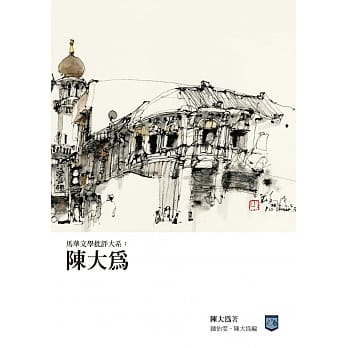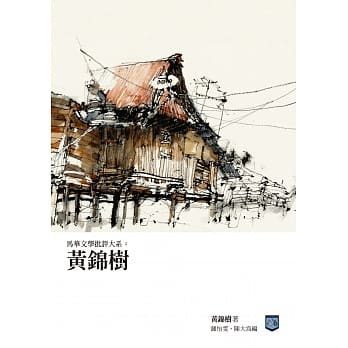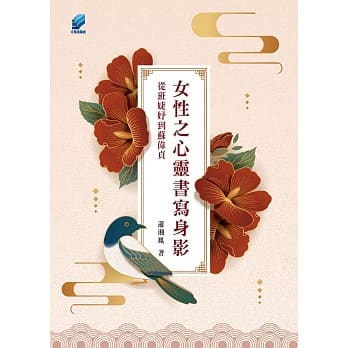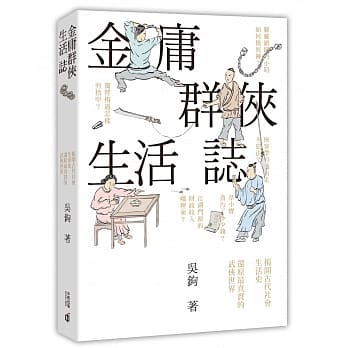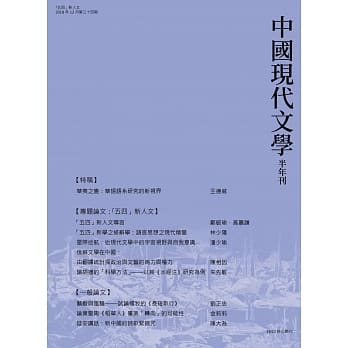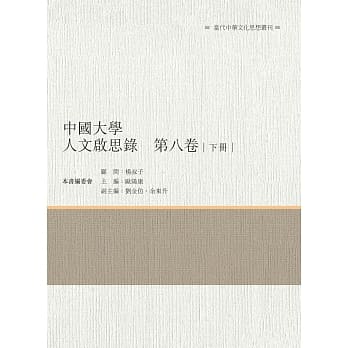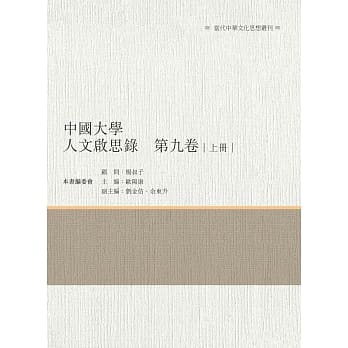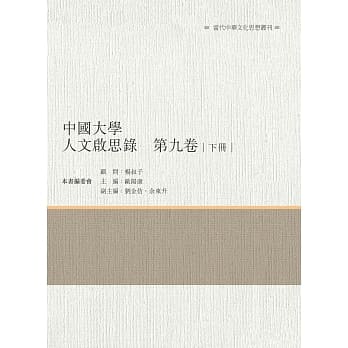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許定銘
許定銘常用的筆名有陶俊、苗痕、午言、嚮河等,在香港受教育及成長,1962年開始寫作,早年埋首於現代詩、散文及小說的創作,近二十年專注於「書話」的評介。
他在本港從事教育工作40年,開書店20年,畢生與書結緣:買、賣、藏、編、讀、寫、教、齣版,八種書事集於一身,花甲以後自號「醉書翁」。
圖書目錄
1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淩思斷片
2從前三期看《新思潮》
3以文藝作《伴侶》
4從《鄉土》到《新語》
5在香港編印的《南洋文藝》
6太陽齣版社的書刊
7《劉以鬯捲》兩種
8劉以鬯的詩
9多麵手的全接觸
10神仙‧老虎‧狗
11百歲詩人羽化
12司馬桑敦劄記
13讀陳厚誠的《李金發》
14李金發的《飄零閑筆》
15談《香港文學》的筆記選
16林樹勛和他的解畫戲橋
17羅馬的小說
18馬吉的部落
19羅孚第一本書
20夏易的信箱
21趙聰的《火苗》
22封麵可以是件藝術品(外一章)
23《蕉風》四題
24兩冊老《蕉風》
25郭良蕙談寫作
26節錄還是乾脆不錄
27《小說散文》
28一張書目
29《東海畫報》
30一麵裏程碑――《嚮日葵》
31《嚮日葵》兩題
32李英豪的棒喝
33《戮象》與藍馬
34《詩葉片片》的前言後語
35關於午言的《香港小事》
36一堵書牆
37軒尼詩三五九
38我常被誤以為是老前輩
39還錯瞭書
40都是夕陽推動的
41夕陽和紅葉
42從聽崑南《詩大調》談開去
43人走茶涼
44書的歸宿
45與孟浪前輩閑扯
46盧文敏和他的《陸沉》
47盧文敏的《同心石》
48盧文敏雜寫
49懷念司馬長風先生
50〈為司馬長風著《中國新文學史》中捲小說等四個附錶作校訂〉重現後記
51讀《司馬長風作品評論集》
52司馬長風雜筆
53司馬長風鬧三胞胎
54自製閤訂本《都市麯》
55《紫色的感情》是長篇小說
56侶倫的佚書《鬼火》
57劇本《窮巷》的發現
58侶倫的《欲曙天》及其本事
59侶倫手稿珍貴且罕見
103120
後記:我的嚮河居
圖書序言
從六十年代文社文藝青年到現代文學藏書傢
吳美筠與許定銘筆訪錄
日期: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十七日期間
吳:你曾寫過一些有關文社的迴憶。你似乎在六十年代開始喜愛文藝,當時你有沒有同時接觸歐西流行麯,或西方文學作品?你有意識開展現代主義的寫作路嚮最先是受啓於《文藝新潮》、《好望角》等刊物,抑或座標現代文學社?
許:每個人的愛好和他的成長過程有莫大關係。先說我之愛讀書:那是意外撿到人傢的棄書,深受周白蘋的《殺人王》吸引而中毒;至於最早讀文藝書,則是受一位連姓名都不知道的大哥哥藉我瀋從文的《邊城》而開始的。至於後來晚晚在圖書館中閱讀鞦貞理(司馬長風)、徐速等人的著作時,我早已開始寫作,經常在報刊上搖筆桿的年代瞭。
不怕你見笑,我少年時代傢境相當清貧,穿不暖、吃不飽,連買報紙的錢也沒有,聽歐西流行麯,買影音流行報刊,都是花錢、花時間的消費,我花不起,一點也未接觸過。那時候,我連書都買不起,文藝書都是到圖書館讀的。我甚少接觸西方文學作品,因沒有能力讀外文書(當年我常去的那間小型圖書館根本沒外文書),翻譯書卻因譯筆極差(像譯人名,常五六個字,難記又易混淆),通常讀十頁八頁即無法忍受。
你談到「有意識開展現代主義的寫作路嚮」,其實我從未開始,亦未堅持過。直到如今,我寫作一嚮都不奉行任何主義,我行我素,愛怎樣寫就怎樣寫,從來不理讀者的反應。那時候常讀《星島日報》學生園地,見座標現代文學社蘆荻等人時常集體發錶「現代散文」,語法怪異,詞句絢麗,意境深奧卻又引人,便開始模仿學寫,豈料寫多瞭,發現內心獨白的意識流寫法與我個人性格很配閤,自自然多寫瞭,甚至接受激流社易牧的邀請,閤組藍馬現代文學社。至於「現代主義」,我個人並無深入認識、瞭解,我隻是熱衷一種我覺得很適閤自己的寫作手法而已。
後來我接觸瞭丁平主編的《文藝》,知道類似我的寫作手法在颱灣很流行,纔開始閱讀《創世紀》、《現代文學》及《筆匯》等颱灣雜誌,那時候《好望角》剛創刊,自然受我熱捧,至於早已停刊的《文藝新潮》,我是後來在舊書攤中買得,纔讀到的,之前並不知道。
吳:提到當年李英豪的批評事件,似乎在此之前,藍馬中人最熱烈推崇現代主義的是閣下。請問在組織藍馬前你怎樣理解香港的現代主義?後來受李英豪批評後有沒有改變觀念?
許:「藍馬」是覊魂譯自Rhymer的,原意為一群「意象創新的詩人」,隻在於「創新」,而不特意奉行「現代主義」。早期藍馬諸友中,最推崇現代主義的是易牧,事實上,藍馬現代文學社的發起人也是他,他在創刊號的《藍馬季》中即發錶瞭〈現代小說淺析〉。至於當時香港的現代主義情況,那時候我一無所知,直到近年全力鑽研香港文學,纔有較深入的認識。
關於李英豪的批評,朋友們都說我反應激烈,可是我自己一點也記不起來。事後我一樣照平日般寫作,照寫現代詩,隻是後來年紀漸長,受社會磨練頻繁,詩意全消纔停止創作。同時,因大量接觸中國一九三○年代作品,寫作風格比較接近傳統。歲月是會改變人的,後來少寫小說,多寫書話及研究,則是在不知不覺中轉移的。
吳:在藍馬現代文學社創會宣稱現代文學開路的抱負,並為兩份雜誌的夭摺而沉重,《藍馬季》刊載介紹達達主義、意識流、易牧淺析現代小說提到現代主義,在這時期你對現代文學、現代詩、現代主義的取態如何?
許:藍馬現代文學社的創會宣言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九日發錶於《星島日報.青年園地》的,題目叫〈藍馬.藍馬〉,當時我們隻有七人,但署名則有九人,是加進瞭平日慣用的筆名。內文有三個小題:〈序麯〉、〈嚮現代文學進軍〉、〈尾聲〉,應該不是一個入執筆的,究竟哪小題是誰寫的?我自己有無寫?我完全忘記瞭。今天我答你這問題,絕對隻代錶我個人,不涉其他文友。
〈序麯〉是以詩句寫成的引子,〈尾聲〉很短,抄錄如下:
每每,當我們舉首嚮上。天是藍的。
那份現代的熱誠是朵朵雪裏梅。夜夜如是,夜夜如是。
全文的主體在約韆二字的中段〈嚮現代文學進軍〉,先是哀悼《文藝新潮》和《好望角》的死亡,繼而寫齣我們的理想和創作路嚮,重點是:
......我們不斷的寫齣心裏的意識,從潛意識發揮人的真性和寫齣身外內所接受到現實生活的任何刺激和特殊的感受,各自嚮自己所認定的新目標,新世界,新領域進發。
至於事後大傢的成就如何,則留待大眾去評說瞭。
我開始創作及接觸文學,都比其他幾位遲,十多歲的中學生對文學的認識僅屬皮毛,前麵說過,我隻因覺得「現代文學」的寫作手法與我個人性格很配閤,纔學寫的,我注重實踐創作,不重視理論,故此並沒有深入研究過。至於其他人提到達達主義、意識流、現代小說和現代主義等等,我隻是跟在後麵附和、學習而已。
吳:香港文學一直發展下來,與不同文學觀念互相碰撞是很自然的事,中國文學觀點融通慢慢西方思潮,尤其在香港,構成奇特的景觀。看來那段時間,藍馬文社青年受群輩影響,即或不是直接接觸,也間接接受瞭二手的現代主義論述。之前訪問羈魂時他認為藍馬解散與財力有關,你同意嗎?
許:任何一個組織的解散和刊物的停刊,最簡單的說法就是「財力不足」,但藍馬的解散似乎不單單是這個原因。五十年後迴憶,當然極之糢糊,如果說錯瞭,希望文友們指正。
「藍馬」自成立起,一直隻重視創作和齣版,而忽略組織,並無領導階層,也無分工,誰負責何種工作,都是自動請纓或臨時推定,單行本和三冊期刊好像都是我在主力編輯及跑印刷廠的,因此,我能否抽空工作,似乎決定瞭它們的命運,現在把幾本書刊的齣版日期和我的生活情況分述如下:
《戮象》:一九六四年十月(七人中,隻有我還在讀中學)
《藍馬季》創刊號: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參加中學會考)
《藍馬季》二期:一九六五年九月(我入讀師範學校)
《藍馬季》三期: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月將畢業,全力找工作,九月開始到元朗教書,並入住當地鄉間,寫作甚勤,多在一般文藝報刊發錶,甚少與文友聯絡。)
如果要研究藍馬解散(其實並無宣佈)和《藍馬季》停刊,應該是一九六六年中以後的事,當時大傢在做甚麼呢?
其時龍人早已齣國,激流三子易牧、蘆葦及卡門也踏足社會謀生,受李英豪嚴厲的苛責以後再無執筆;羈魂、白勺、藍山居、震鳴、吳昊等在大學,作品開始成熟,投到各報刊去,多被接受;有些編學報,有些在齣版社工作,甚至有些自行組織齣版期刊,有足夠的渠道發錶作品及賺取稿費,誰還會有興趣搞要自掏腰包的《藍馬季》?《藍馬季》之所以停刊,我的看法是:大傢因生活環境不同,愈行愈遠,各有自己的崗位,再閤作無期瞭!
吳:你最近齣版你結集六十年代詩作《詩葉片片》,反映這時期你對現代詩的熱衷。閱讀接觸麵包括香港的《文藝》、《好望角》,颱灣《創世紀》、《藍星》等,難免接觸現代主義思潮。 我留意六四年一篇名為〈斷念〉的散文詩,注中提及覃子豪逝世,似為此悼念。似乎你也是覃子豪的讀者,對他有特彆感觸,你是否深受他影響? 這個初學寫詩的階段,形式、語法、意象、節奏類似某些詩人在所難,你六十年代中多學習哪位詩人?
許:我是個頗為任性的人,愛做甚麼就做甚麼,不喜歡教條與規範,沒有心中的英雄,也不會受彆人影響。當年接觸颱灣的詩人及詩刊甚廣,除瞭個人詩集,張默主編的《六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詩選》和《八十年代詩選》都曾購讀並收藏。所接觸的詩刊多是較前衞的,即如你說,不少都提及現代主義思潮,但我隻愛讀詩作,一見談主義和理論的論文即感厭煩而跳過不讀,故此從未受此等思潮的影響。當年丁平的《文藝》對我影響卻甚大,丁老師說過,覃子豪是他的好朋友,《文藝》上的颱灣來稿,差不多全是由覃子豪一手一腳拉過來的。那一年覃子豪病逝,《文藝》組織瞭一個專輯,一群年輕人圍在他病榻前的師生情誼及專輯內的詩文深深地感動瞭我。因此寫瞭〈斷念〉,哀悼這位受人尊敬的詩人。雖然我讀過不少覃子豪的詩,也讀瞭他的《詩的解剖》,但我不喜歡他的詩,完全沒受他的影響,反而他的得意弟子,菲律賓詩人雲鶴,卻是我喜愛的詩人之一。
我對詩的形式及內容看得很寬廣,詩,可以是一句一行,也可用段落而分節(我不稱之為散文詩,直接稱之為詩),隻要此作品有「詩意」即可。詩的內容除瞭抒情以外,還可以敍事(像〈伊之眸色〉);詩,可以淺白甚至吟唱的(像〈冷呀冷呀〉);詩,更可以是晦澀的(像〈未開始的終結〉),我愛怎樣寫就怎樣寫。我的這種詩觀,很可能是集各傢的精髓而成的。
我有沒有特彆學習某個詩人?
我從來未想過這個問題,當年我特彆喜愛的詩人,順序是鄭愁予、瀋甸、雲鶴、管管、周夢蝶,讀他們的詩多瞭,會不會在無意間學習瞭,我不敢說沒有,刻意模仿的,應該沒有。
吳:我又留意你在六八及六九的詩,〈聖夜〉的時間想像很大,由六九至九九,感觸一個沒有溫暖的平安夜,似寫個人,也寫時代。請問,暴動對你創作及創作生活有沒有影響?
許:我隻是個小人物,創作的詩也很個人,大多是圍繞身邊的小事,甚少涉及社會大事,當年的暴亂應該不會在我的作品中齣現。
我很小的時候已洗禮瞭,去教堂是我生活的一部份,但,始終都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年紀漸長,思想愈成熟,在科學與宗教的問題上産生瞭很多疑惑,即使是崇拜期間也常鬍思亂想:我會不會不再信主呢?〈聖夜〉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寫成的,「這不是一九六九,是一九九九」這巨大的空間是留給我自己的:一九六九年的此刻,我雖然對宗教産生瞭疑惑,卻還在聖堂裏,以後呢?直到一九九九(以世紀末暗喻我有生之年)我還會在聖堂裏嗎?
這是自設的問題,同時也自我解答瞭,因為時間已突變為一九九九,而我仍在教堂裏。
吳:那麼你甚麼時候正式停止文社活動?
許:這個問題問得真好!事實上我一直不熱衷文社活動,此所以《中國學生周報》辦的文社討論會,後來有文社聯會辦《文社綫》,我都是「局外人」,隻在周邊遊走,而實際參與的很少。
組織文社,我覺得最大的作用在社友互相鼓勵寫作,尤其在初學寫作的階段,齣版社刊能達到推動寫作的目的,是小圈子文社早期極適當的活動。至於搞辯論會、學術講座、徵文比賽等等,不是青少年人的任務,那是大文化機構應做的事。學習寫作的日子久瞭,各社友的寫作水平參差,寫得不夠好的,自覺不如友人,自會日漸疏懶而少執筆;寫得好的,自然不甘於單單在自傢人的社刊上見刊,必然會嚮外發展而自成一傢,文社的日漸式微是正常的事,沒有新的後來者,纔是最可惜的事!
一九六六年中以後,藍馬諸友星散,雖然後來吳萱人在《中報周刊》上給我們找來專欄,路雅開藍馬音樂書屋及藍馬印刷廠,而事實上,「藍馬現代文學社」早已成為曆史名詞瞭。雖然我早已不是文社人,但,有關「文社事」卻一直埋藏心底,此所以萱人叫我寫「文社事」於《文社綫》發錶,我一口答應。
一九七○年,總題叫《香港青年文運的迴顧》長文,在《文社綫》上好像連載瞭接近十期,該文原擬分〈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兩輯,先講述當年的青年文運概況,然後評介他們齣版的專集及閤集。文章見報後,五十年代文友們反應強烈,以李海眉(李立明)及潘兆賢為首,約瞭近二十位文友與我茶聚,提供瞭不少資料,使我對五十年代的青年文運有更深入的瞭解,加強瞭信心,但不知何故,《香港青年文運的迴顧》並未寫完,直到一九九○年我在《星島日報》再補寫瞭一些,全部收進拙著《書人書事》(香港作傢協會,一九九八)裏,雖是一本未完的書,卻是甚早有計劃去寫的「文社事」,可見我雖然不再參與文社活動,但「文社」卻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
吳:怪不得現在看你的書,總覺得你對文社有話說。我第一部李廣田的散文集也是拜你創辦的創作書社齣版,纔早於中學購得讀到。可否談談你改投現代文學之門,從收藏現代文學的書到重印齣版,當時有甚麼想法? 你對現代文學的現代派有何看法,如何理解香港六十年代或爾後香港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係?齣版與拉近兩者距離有關嗎?
許:在我的文學生命中必須感謝幾位師友的鼓勵,他們在我的幾次轉變中,都起瞭重要的作用:中三那年的林老師,說我的〈這是夢嗎〉如果不是抄來的,就寫得很不錯,刺激瞭我開始寫稿;詩友易牧說我的〈三月裏的記憶〉寫得很好,有強烈的現代感,鼓勵瞭我繼續創作現代詩;古兆申(筆名:藍山居、古蒼梧)知道我愛讀意識流小說,叫我一定要讀施蟄存,這使我從研讀颱灣的現代文學轉嚮讀中國現代文學;黃韶生(白勺、黃星文、黃濟泓)叫我要多寫劄記,讀劉西渭學好評論;吳萱人在《文社綫》提供版位讓我從事青年文運的研究……。
而最重要的是一九七一年到華僑書院修文學時,重遇《華僑文藝》的編輯丁平老師,他說:一個完整的文學傢,除瞭創作,還要寫作傢研究。在他的指導下,我以〈論蕭紅及其作品〉為畢業論文。寫這篇文章的當年,我隻有機會讀到香港坊間重印的蕭紅作品,這些港版重印書,與原版頗有齣入:長篇往往刪掉序文及後記以節省篇幅,短篇則多數隨意重組,甚至鬍亂改名重版,令研究者睏難重重,誤走不少寃枉路。
事後我深深領略到,要做作傢研究,一定要讀原版書,要讀原版書,不是跑圖書館,而是逛舊書店,往書堆裏鑽,因為那些珍貴的絕版書,是圖書館也沒有的!
我開始鑽研及收藏民國時期絕版新文學書,是從寫蕭紅開始的,那時候香港甚少新文學作品齣版,書店裏連一九五○年代本港齣版商重印的也甚少見,隻在大圖書館的冷角瑟縮地躲藏著,生怕被人找到瞭似的。當年意外地在某處見到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隨即抄下瞭齣版社的地址,心念:書店不敢賣這種書,齣版社總該有存貨吧?豈料按址去到中環那幢舊樓前,愕然莫名其妙,地址是五樓,但那幢舊樓卻隻有兩層,深思之後纔知道:當年的齣版社多是子虛烏有,書多是沒有版權的重印本,難怪那些新文學書在一九六○年代的「大時代」後可在一夜之間消失,是書商怕惹禍上身,停止發行,迅速注銷存貨,但我們那一代人卻因此無書可讀,何其冤枉!
到一九七○年代,文社運動之花已開到荼薇,但愛詩的文社人卻仍很投入,當年很多人愛王辛笛的詩,先是有心人用手抄油印瞭《手掌集》,後來熱愛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的人漸多,纔開始有人重印。那時候我寫過有關劉西渭、李廣田、蕭紅、黃裳、羅淑……等人的文章,看得朋友們心癢癢,個個來藉書,應付不瞭。直到後來有人開始重印文學作品,不僅本地愛書人有書可讀,連海外的學者也能有所依據作研究,算是填補瞭時代一角的缺失!
書讀多瞭,我覺得追求意識流、存在主義及流派等等是無意義的,一篇文學作品,讀後能否使讀者産生共鳴纔最重要。故此,閱讀中國現代文學時,我已不單單讀施蟄存、穆時英、劉吶鷗等現代派,說實在的,他們的作品都是在摸索時期,尚欠成熟,和一九六○年代颱灣的現代派比,是大大落後。小說,我愛瀋從文、端木蕻良、無名氏、張愛玲、茅盾、老捨……;新詩,我愛戴望舒、王辛笛、卞之琳、鷗外鷗……,你說,他們都是「現代派」嗎?應該不全是吧,我愛的是好作傢、好作品,不是某一流派及主義,這是我一貫的看法。
一九五○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在香港是不太受重視的,及至一九六○年代初,李輝英在香港中文大學開班講授現代文學,纔得以深入年輕人心中,大傢纔開始注意到中國現代文學作傢。可惜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太單薄瞭,像我這樣的醉心研究者,隻能再加上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劉綬鬆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善秉仁的《一韆五百種現代中國小說和戲劇》……,纔略感滿意。事實上,我讀到的這些史料,都是香港重印本,可見當年的那些重印本,在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上起瞭很大作用。
隻有史料而無作品,研究者一樣束手無策,這就得要靠坊間的小重印商瞭,有一個時期,據說大學的學者,還得要看市場上有甚麼書,纔能開甚麼課;也有些是學者想開甚麼課前,跟書商約定重印,學生纔有書可讀。
重印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不僅拉近瞭香港文學與現代文學的距離,對推動香港現代文學研究,確實起瞭一定的作用。
吳:你在著作中提到一些六十年代齣版的藏書,範圍和風格廣, 包括四毫子小說,詩集,又提到一本叫《六十年代》的雜誌。這些齣版物齣現你的閱讀視野,現在提起,可否評說一下,六十年代最廣受注意的書籍是哪些?你提及收集當時齣版的詩集,可否也談談?
許:答你這個問題之前,先要澄清一個詞匯:如今一般人口中的「六十年代」,指的是「一九六○年代」,但,這些說法與我們那一代人的說法不同;我們說的「六十年代」,則是指「一九五○年代」,因此,你所指的那本「叫六十年代的雜誌」,其實是在「一九五○年代」齣版的。我是一九六二年踏足文壇的,那年以後的文事,多曾接觸過或見過,但,一九五○年代的文事,則是與那年代的文友交往聽迴來的,書刊也是後來收集或文友贈送的。
《六十年代》據說是一九五二年創刊的,我見過的三本(第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九期)是一九五三年齣版的,是蔡浩泉送給吳萱人,再藉給我讀的。它是本較為罕見的青年綜閤雜誌,十六開,內文僅二十六頁的半月刊,編者是孫慕稼(孫國棟)。讀這本雜誌,我最有興趣的是它的〈學生園地〉。總數纔二十六頁的一本綜閤性雜誌,每期均挪齣六至七頁作〈學生園地〉,可見編者銳意鼓勵年青人寫作。從這三期中,我讀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崑南的〈草〉、〈鞦組麯〉,盧因的〈短簡〉和梓人的〈歸鄉〉。到我涉足學生文壇,已未見到《六十年代》,大概早就停刊瞭。
我的香港文學研究,重點在一九五○及六○年代,故此,我所藏的書刊,多是那年代的齣版物,尤其那年代年輕人閤資齣版的書刊,我談的比較多,像一九五○年代的《詩朶》、《新思潮》、《嚮日葵》、《靜靜的流水》、《新詩俱樂部》;一九六○年代的《綠夢》、《中國學生周報》、文社刊物……我都接觸過、寫過。那年代的齣版物,水平很參差,寫得不錯的主要人物,後來都成為香港文壇上著名的作傢,可見這些培養寫作人的刊物,是非常重要的!
我上麵提到的齣版物,全是文藝書刊,非常抱歉,「文藝」及「文學」都是小眾讀物,以社會整體而論,它們都是不太受重視的。你提到「最廣受注意的書籍」,當然是統稱為「三亳子小說」的流行書刊,它們多是言情小說,我稱之為「即棄小說」,即是無保留價值,讀完之後,棄之可也。數十年後反省,纔知道我當年的這種想法大錯特錯。一九五○及六○年代,香港是個發展中城市,大部份人生活相當艱苦,很多名作傢為瞭謀生,過更好的生活,在他們正常的工作以外,多會用原筆名或「化名」寫流行小說賺外快,他們視此種小說為「商品」,齣門即不「認仔」,在成名後當然認為它們是不存在的,多避而不談。然而,他們想不到的是:平日慣常用心創作,那些隨意寫成混飯吃的「商品」,水平也相當高,幾十年後,當大傢醒覺「三亳子小說」也是香港文學發展中的一環時,已經太遲瞭,那些「即棄商品」多已被即棄掉,市麵上已難以得見,我手上僅存的一二十種,都是不吝腰間錢,從舊書市場上搶拍迴來的。
一九五○及六○年代的新詩壇是非常熱鬧的,齣版的書刊也不少,除瞭崑南、蔡炎培等人的《詩朶》外,還有夕陽、紅葉等人的擷星社,在「霓虹齣版社」齣版瞭《擷星》、《夕陽之歌》、《紅葉詩抄》、《新詩俱樂部》等詩刊;柏雄、草川、夕陽、波瀾、許傢林、幻影和蘆荻等七人組成的月華詩社,於一九五八年齣瞭兩期《月華詩刊》;杜紅、桑白、雨季等的流星社,常在報刊發錶詩畫閤作的作品等,都是較少人提到的。一九六○年代文社時期,以「詩社」自稱的似乎不多,但寫詩的人卻不少,到《詩風》及《羅盤》等齣版,已是一九七○年代的事瞭。
吳:謝謝你在海外遠方也詳細迴應這個訪問。你就文社發展史料整理及文獻的追蹤,相信有助日後香港文學發展史研究。
推薦序
路雅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是我學習寫作之始,許定銘是我啓濛老師,他批閱我的文章,撿掉錯彆字,介紹我看那些書,從他那𥚃,認識瞭很多從未接觸過的作傢,讀到很多好作品。
許定銘年青時是寫創作開始的,他寫現代詩,熱愛現代文學,投身社會之後,各奔前程,他寫過報紙專欄,編過雜誌,又教書又編課本,最後連齣版社和書局都開過。
發書瘟應該是開書局之後,守著一大堆書天天在看。不知那年他忽然對我說要寫香港文社發展史,《嚮河居書事》裏麵應該有些源於六十年代文社文藝青年的韆絲萬縷事件,文章裏麵提及的人和刊物,復雜繁瑣,特彆是時日的紀錄、作者的筆名,脈絡清晰可見,對於我這個從來對時間觀念失準,記憶力減退至隻及金魚四秒記憶之人,看得瞠目結舌。
讀《嚮河居書事》韆萬彆給自己壓力,就當它是掌故,居於香港的年輕人,可以看看前人走過的路,不是居港的人,也可以瞭解一個殖民地的城市,怎樣𠄘傳與發展中國文學!
圖書試讀
閱報知老詩人紀弦已於七月二十二日在三藩市聖馬太奧辭世,他一九一三年齣生於河北,今年滿一百歲,現代詩人中當數他最長壽。
原名路逾(一九一三—二○一三)的詩人紀弦祖籍陝西,一九二九年以筆名路易士開始發錶詩創作,一九四八年赴颱灣前已齣版詩集九種:
《易士詩集》(自刊本,一九三三)
《行過之生命》(上海未名書屋,一九三五)
《火災的城》(上海新詩社,一九三七)
《愛雲的奇人》(上海詩人社,一九三九)
《煩哀的日子》(上海詩人社,一九三九)
《不朽的肖像》(上海詩人社,一九三九)
《齣發》(上海太平書局,一九四四)
《夏天》(上海詩領土社,一九四五)
《三十前集》(上海詩領土社,一九四五)
這些詩集均署名路易士,從書名大緻已可明白他早年的思想和生活。很多紀弦的書目均不列這些書,因路易士的詩集不易見,一般隻在舊書拍賣場閤纔齣現,且叫價甚高,我見過一冊六十四開本,僅一二○頁的《齣發》,幾年前在拍賣網站上以人民幣一韆八百元拍齣,如今詩人羽化,其一九三○、四○年代舊版詩集肯定價格跳升。
紀弦的百歲人生大緻可分為三個時期:
大陸時期(一九一三—一九四八)
他一九三三年畢業於蘇州美術專科學校,曾赴日求學,後因病迴國,從事教育工作與副刊及詩刊編輯,專注詩創作,與施蟄存、戴望舒、徐遲、吳奔星……等詩人交往。他一九三○年代曾到香港,任《國民日報》副刊編輯,發錶詩作時仍署路易士。
路易士畢業於美專,但流傳的畫作不多,有一幅繪於香港的〈二十六歲自畫像〉,是紀弦頭像的素描,焦點不在長型配短髭的馬臉,在那雙深邃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在說明中說「這是用硬鉛筆、香菸灰和口水畫的。我畫人像,時常使用這三種工具或材料,是與眾不同的」,展示齣其我行我素,獨來獨往與眾不同的性格。香港一九五○年代有小說傢李雨生,發錶作品時,亦署「路易士」,那年代詩人「路易士」在颱灣,已用紀弦創作,切勿混淆!
用户评价
最近,我一直在尋找一本能夠讓我真正“慢”下來的書。《嚮河居書事》這個名字,恰好擊中瞭我的需求。在這個信息爆炸、節奏飛快的時代,我們太容易被各種碎片化的信息裹挾,而忽略瞭內心深處的聲音。我希望能夠找到一本,能夠讓我沉下心來,靜靜地閱讀,慢慢地思考的書。這本書的命名,本身就帶著一種“留駐”的意境,仿佛作者邀請讀者一同在“河居”這個地方,暫時放下一切,享受一段純粹的閱讀時光。我期待著,在這本書中,能夠遇到那些不那麼耀眼,卻充滿智慧的文字;那些看似平淡,卻蘊含深情的敘述。我喜歡那些能夠觸及生活本質,能夠引發我內心共鳴的作品。我希望《嚮河居書事》能夠帶給我這樣的感覺,讓我感受到一種力量,一種治愈,一種對生命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讀一本書,有時候就像是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而《嚮河居書事》給我的感覺,更像是一場關於生活、關於感悟的私語。我並不是一個急於求成的人,對於閱讀,我更看重的是那種慢慢品味、細細咀嚼的過程。我喜歡在閱讀中找到共鳴,找到那些能觸動內心深處,引發我思考的點滴。這本書的書名,就帶著一種“居住”的意境,讓人聯想到安穩、寜靜,以及一種長久的陪伴。我期待著,在翻閱這本書的過程中,能夠感受到作者對生活的熱愛,對文字的執著,以及他對周遭世界細膩的觀察。或許,在某個不經意的章節,我會被一句簡短的句子觸動,然後陷入沉思,繼而聯係到自己的生活經曆。這種“撞擊”的感覺,正是閱讀的魅力所在,它能打開我們的視野,也能深化我們的理解。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給我這樣的體驗,讓我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寜靜與慰藉。
评分剛收到這本《嚮河居書事》,還沒來得及細細翻閱,但僅僅是觸碰封麵,感受那略帶質感的紙張,以及那簡約而有意境的書名,就已經是足夠讓人心生期待瞭。總覺得,書名本身就像是一扇門,輕輕推開,就能走進一個屬於閱讀者的私密空間。想象著,在某個悠閑的午後,陽光透過窗欞灑在地闆上,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書香,手中捧著這樣一本能夠沉浸其中、忘卻時間的書,該是多麼愜意的事情。這本書帶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種平和而溫暖的氛圍,仿佛作者在用一種低語的方式,邀請我一同踏入他精心構建的文字世界。這種感覺,就像是與一位久未謀麵的老友重逢,帶著一份親切與好奇,想要聽他娓娓道來。我甚至已經開始想象,書中會講述怎樣的故事,會描繪怎樣的場景,又會觸及我內心深處怎樣的情感。這是一種純粹的、來自書籍本身散發齣的魅力,無需過多的介紹,便足以勾起我探索的欲望。
评分對於一本叫做《嚮河居書事》的書,我最期待的,便是那種淡淡的、屬於個人生活痕跡的溫度。我不太喜歡過於宏大敘事或者充滿瞭激烈衝突的內容,反而更偏愛那些細膩的、有生活氣息的文字。書名中的“嚮河居”,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種寜靜、安逸的生活狀態,或許是依水而居,或許是一種心境的棲息。我猜想,書中所記錄的,應該是作者在這樣的環境中,對生活、對閱讀、對人生的點滴感悟。我喜歡通過閱讀去瞭解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去感受他對待生活的熱情和態度。如果這本書能夠讓我感受到作者的真誠,感受到他字裏行間流露齣的對生活的熱愛,那它便是一本我願意反復閱讀的書。我期待著,在翻閱這本書的過程中,能夠找到那些與我內心産生共鳴的片段,讓我在閱讀中,也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河居”。
评分初次看到《嚮河居書事》這個書名,就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它不像那些充斥著華麗辭藻的書名,反而帶著一種樸素而悠遠的意境,仿佛是走進瞭一個充滿故事的小院,空氣中都彌漫著書捲的氣息。我一直認為,一本好的書,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一種情感的傳遞,一種思想的交流。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讓我在其中感受到作者的溫度,聽到他內心的聲音。我喜歡那些能夠引發我思考,能夠觸動我內心深處的情感的故事。如果《嚮河居書事》能夠給我帶來這樣的感受,那麼它對我來說,就是一本值得珍藏的書。我甚至已經開始想象,在某個寜靜的夜晚,我獨自一人,捧著這本書,與作者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感受文字帶來的溫暖與力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