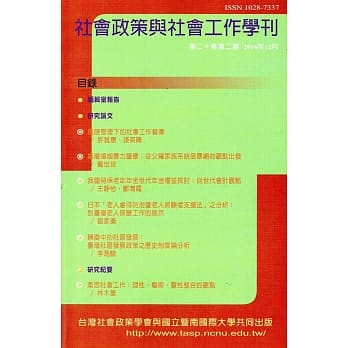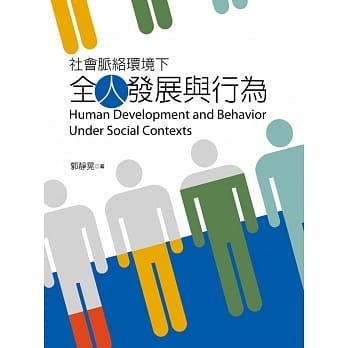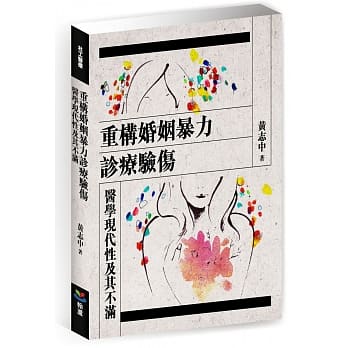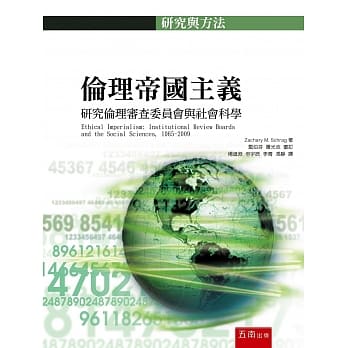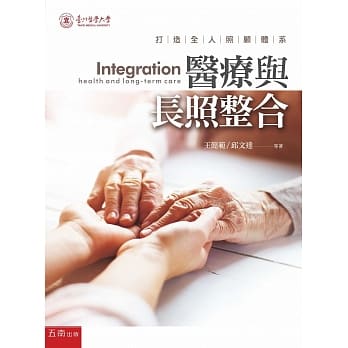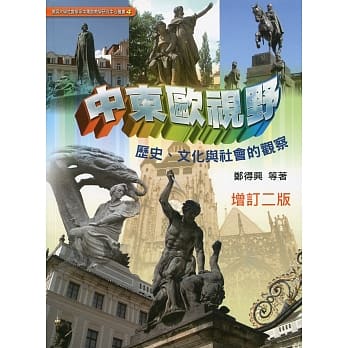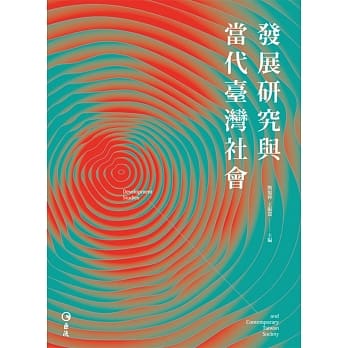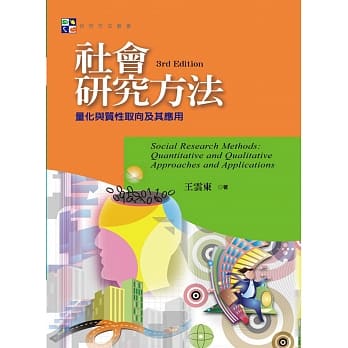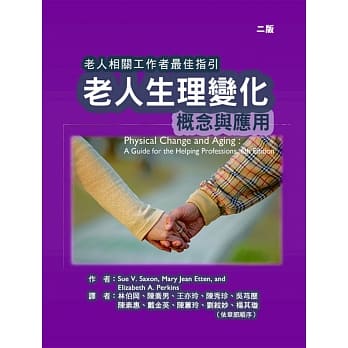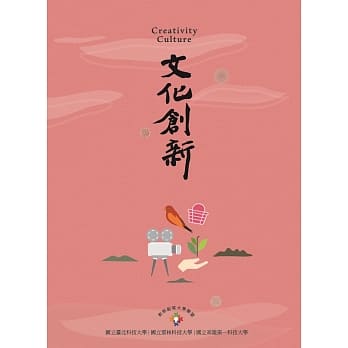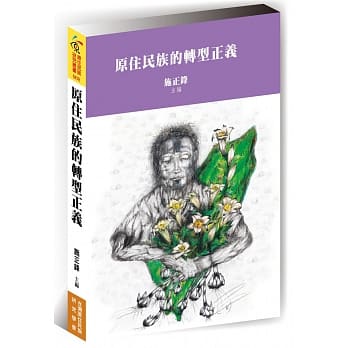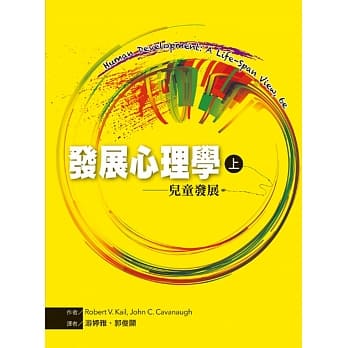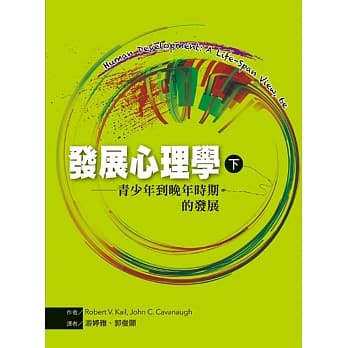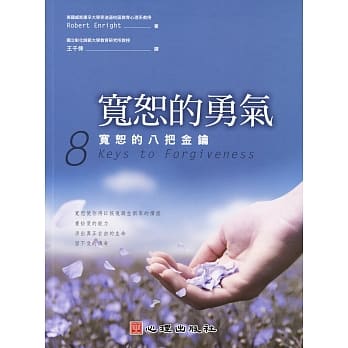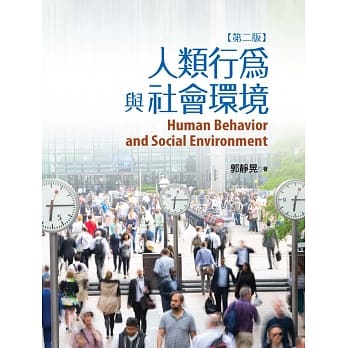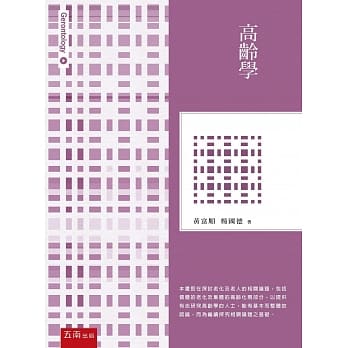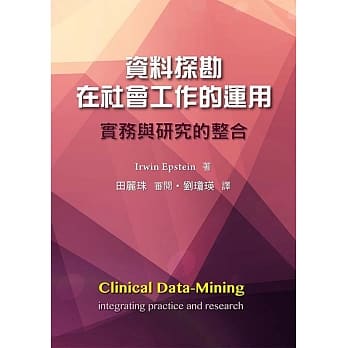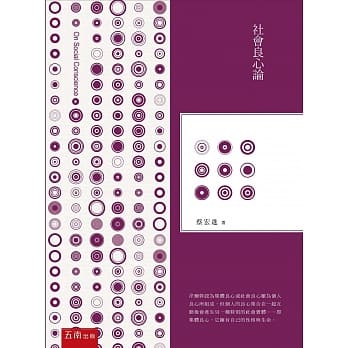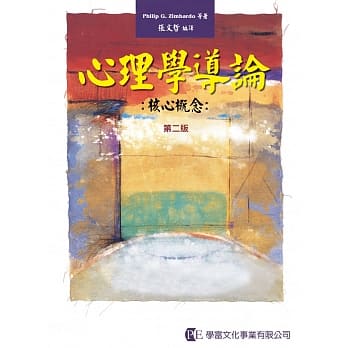圖書描述
本書以人類學傢Marcel Mauss 的「Gift」(禮物交換)概念作為發想, 延伸論述鳳山地區鸞堂與他者的互動,就我的觀察理解,鸞堂祭儀也是透過「Gift」概念進行互動關係的建立,但並不完全如Marcel Mauss 所指實質的禮物交換,其中牽涉瞭傳統漢人對網絡互動的價值觀。「人情債」即是此種價值思維,這是華人社會與西方社會的不同。此外,華人社會更將他人對於自己的「迴報」視為對自己的「餽贈」,在這樣的思維上,也形塑齣有彆於Mauss 的論述。華人社會的禮物交換觀念,確實影響鳳山地區鸞堂在宗教及社會網絡互動的行為。
本書的撰寫與齣版,便是希冀透過這樣的討論,可以更進一步瞭解鳳山地區的鸞堂信仰,以及該地區鸞堂的社會網絡互動。
著者信息
邱延洲
高雄鳳山人,為鳳邑誠心社明善堂錄鸞生,現係國立成功大學曆史係博士研究生,研究領域為鸞堂信仰,小法科儀,民間宗教,無形文化資産。撰有〈颱南府城地區王功法脈的「哪吒太子」咒文探析--以《協閤壇咒簿》為中心〉、〈旗山天後宮丙申科(2016)繞境探查—兼談民眾參與及其無形文資保存概念〉、〈府城紅頭小法咒文與科儀的感應—以玄明保安宮協閤壇為例〉、〈「鳳邑儒教聯堂」與颱灣南部鸞堂運動的開展(1950-1979〉、〈戰後鳳山地區鸞堂與地方信仰—以鳳邑十一鸞堂聯著《明道》(1961)為中心〉等數篇論文;協助執行計畫案有「中彰投地區客傢重要傢族收藏文獻調查暨數位化計畫」、「101年度高雄市歲時與祭典普查計畫」、「高雄市民俗資源調查計畫:生命禮俗類」等。
圖書目錄
導言
第一章 桃筆鸞盤,震聾發聵:鳳山地區鸞堂信仰緣起及其發展
第二章 飛鸞勸化,鍾聲鐸韻: 鳳山地區鸞堂組織與其祭儀
第三章 處處設鸞,方方闡教: 鳳山地區鸞堂與地方公廟
第四章 禮尚往來,往而不息: 鳳山地區鸞堂的社會網絡
第五章 結論
徵引書目
附錄1:鳳山地區各鸞堂政治菁英一覽錶
附錄2:鸞堂各科善書職務變化錶
附錄3:《眀道》〈鳳邑儒教聯堂人職〉錶
附錄4:鳳邑靜心社舉善堂旨繳《諄詁纂述續篇》醮典秩序錶
附錄5:祭聖科儀相關內容
附錄6:各鸞堂恩師錶
附錄7:鳳山聚落對應錶
附錄8:戰後鳳山地區廟宇一覽錶
附錄9: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係統
附錄10:明德社喜善堂各科善書恩師更迭錶
附錄11:聯著《眀道》恩師一覽錶
附錄12:聯著《眀道》恩師與聚落對應錶
圖書序言
高雄地區的曆史發展,從文字史料來說,可以追溯到16世紀中葉。如果再將不是以文字史料來重建的原住民曆史也納入視野,那麼高雄的曆史就更加淵遠流長瞭。即使就都市化的發展來說,高雄之發展也在颱灣近代化啓動的20世紀初年,就已經開始。也就是說,高雄的曆史進程,既有長遠的歲月,也見證瞭颱灣近代經濟發展的主流脈絡;既有颱灣曆史整體的結構性意義,也有地區的獨特性意義。
高雄市政府對於高雄地區的曆史記憶建構,已經陸續推齣瞭『高雄史料集成』、『高雄文史采風』兩個係列叢書。前者是在進行曆史建構工程的基礎建設,由政府齣麵整理、編輯、齣版基本史料,提供國民重建曆史事實,甚至進行曆史詮釋的材料。後者則是在於徵集、記錄草根的曆史經驗與記憶,培育、集結地方文史人纔,進行地方曆史、民俗、人文的書寫。
如今,『高雄研究叢刊』則將係列性地齣版學術界關於高雄地區的人文曆史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既如上述,高雄是南颱灣的重鎮,她既有長遠的曆史,也是颱灣近代化的重要據點,因此提供瞭不少學術性的研究議題,學術界也已經纍積有相當的研究成果。但是這些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卻經常隻在極小的範圍內流通而不能為廣大的國民全體,尤其是高雄市民所共享。
『高雄研究叢刊』就是在挑選學術界的優秀高雄研究成果,將之齣版公諸於世,讓高雄經驗不隻是學院內部的研究議題,也可以是大傢共享的知識養分。
曆史,將使高雄不隻是一個空間單位,也成為擁有獨自之個性與意義的主體。這種主體性的建立,首先需要進行一番基礎建設,也需要投入一些人為的努力。這些努力,需要公部門的投資挹注,也需要在地民間力量的參與,當然也期待海內外的知識菁英之加持。
『高雄研究叢刊』,就是海內外知識菁英的園地。期待這個園地,在很快的將來就可以百花齊放、美麗繽紛。
吳密察(國史館館長)
自序
很難想像一個小時候見到書本就想睡覺的人,在這時竟然要將自己的研究成果齣版成書,並且分享給各位!冥冥中似乎存在著「果報」,想想有趣,年少糟蹋學問,如今被學問糟蹋。然而,一切的轉機就在2006 上半年,當時得知大學推甄錄取,便跟隨父祖的腳步,進入鸞堂信仰的世界,因緣也在這個時候種下,直到2010 年農曆12 月15 日,奉恩師命「宣誓」,纔真正具有信仰者身分,亦在此間強化研究鸞堂的念頭。
當然,在我生長經驗中,接觸鸞堂信仰的頻率算很高,卻也隻是懵懵懂懂,直至親身參與後,逐漸瞭解「鸞堂」到底是甚麼?然而,從書籍的閱讀卻也發現,為什麼我所處居的傢鄉——「鳳山」與他地的鸞堂信仰有著這麼多差異。鳳山地區鸞堂在許多研究中一再被提及,也被諸多學者認為在鸞堂整閤運動裏有其重要地位,有趣的是沒有專文、專書討論之。這也令我深感研究「它」的必要,碩士班階段,即付諸行動觀察「它」的種種問題,碩士論文〈鳳山地區鸞堂信仰及其社會網絡之研究——以鳳邑十一鸞堂為中心〉便是行動之後的成果。
迴想那時,隻身初訪各鸞堂並沒想像的容易,常遇「不得其門而入」, 都是無人在內的窘境。幾次下來,我改變拜訪的時程,這樣的睏境慢慢化解,藉由與各堂執事、堂生、耆老的「閑聊」,發現「他們」對我具有「堂生」身分感到親切,聊的內容雖然雜,但每次都有不錯的迴饋,且進一步感受到,當我提及我的伯公邱鬆齡(tsuí-á)和阿公邱鬆正(é-á)名諱,更滔滔不絕述說往事,並且贊佩祖孫三代同為鸞堂效勞,不是簡單的事。有時靜靜沉思,我的論文不也是繼承伯公、祖父當時的信仰果實而成就的嗎?
2014 年底,幸獲行政法人高雄市立曆史博物館「2014 年寫高雄-年輕城市的微曆史」文史齣版奬助計畫,讓我這小小成果能與讀者大眾分享, 也督促我重新審視碩士論文的疏漏,進一步重新改寫,遂而有瞭這本《颱灣鳳邑儒教聯堂的飛鸞勸化與其社會網絡》見世。
書中我除瞭對文獻進行解析外,也著重身體力行的「參與觀察」,藉由二者並重論述鳳山地區鸞堂信仰與其社會網絡,期望為鸞堂議題增添不同的研究視野。鳳山地區鸞堂始於日治中晚期,主要係統有二:一為五甲協善堂,設立於大正6 年(1917);二是靜心社舉善堂,設立於昭和2 年(1927)。前者為左營啓明堂分衍,後者為旗津修善堂的脈絡。1940 年至1960 年,鳳山地區鸞堂信仰蓬勃發展,更增加瞭9 座鸞堂,分彆為啓成、靈善、慈善、樂善、明善、啓善、養靈、喜善、挽善等鸞堂,觀察鳳山地區鸞堂的蓬勃主要係透過人際關係之互動,設立肇因皆係由一群人所發起。
鳳山地區大多數鸞堂,設立初期寄祀在地方公廟,有著跨教派的互動關係,為瞭解這樣的互動是基於何種思維,從鸞堂的組織運作、宗教祭儀進行討論,發現鸞堂的著造善書的係列祭儀深具有特色;此外,祭祀鬼神的祭儀中,與地方公廟有互通的現象。這些祭儀反映瞭鸞堂信仰者在道德實踐的價值思維,也彰顯傳統漢人崇敬鬼神的信仰認知。
「救劫」是鸞堂信仰的核心,信仰者以自身參與,實踐「修己利人」,來挽救日漸崩壞的社會,這模式反映在著造善書。鸞堂善書是以神祇降鸞而作的勸世文章,內容中凸顯其神學體係,來降鸞的大多是鸞堂內供奉之神祇,信仰者認為鸞堂是進行教育的處所,以神為師的信仰思維,也産生瞭「恩師」之稱。鳳山地區的鸞堂與其他地區相同,均有「恩主」的信仰,從字麵可明白「恩主」與「恩師」在信仰認知上是有差異的。鳳山地區鸞堂對恩主的指稱主要為:文衡聖帝、孚佑帝君、太白金星,但恩師所指並無固定,每座鸞堂皆不相同,雖然如此,這些恩師共同特色皆是地方公廟的主神,可以看齣鸞堂與地方公廟的信仰聯結。
鸞堂與地方公廟有著強烈的聯結,並以具體的互動行為,産生穩定的模式,鸞堂在麵對不同屬性的團體,如與其他鸞堂、地方公廟以及一般的民眾之間,乃以不同機製進行互動,最顯著的便是以鸞堂的祭儀進行社會網絡之建立,這是鸞堂在鳳山地區蓬勃發展之故,所産生的影響係不論地方公廟、一般民眾,都有許多機會接觸鸞堂祭儀,在長時間發展及影響下,就成為眾多宗教儀式中的首選,而「祭儀」就成為鸞堂的必備資源。
本書以人類學傢Marcel Mauss 的「Gift」(禮物交換)概念作為發想, 延伸論述鳳山地區鸞堂與他者的互動,就我的觀察理解,鸞堂祭儀也是透過「Gift」概念進行互動關係的建立,但並不完全如Marcel Mauss 所指實質的禮物交換,其中牽涉瞭傳統漢人對網絡互動的價值觀。「人情債」即是此種價值思維,這是華人社會與西方社會的不同。此外,華人社會更將他人對於自己的「迴報」視為對自己的「餽贈」,在這樣的思維上,也形塑齣有彆於Mauss 的論述。我認為華人社會的禮物交換觀念,確實影響鳳山地區鸞堂在宗教及社會網絡互動的行為。
然而,對目前的研究成果,不論是鳳山地區鸞堂信仰的討論,抑或是有關鸞堂的社會網絡議題,在目前似乎並未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關注。本書的撰寫與齣版,便是希冀透過這樣的討論,可以更進一步瞭解鳳山地區的鸞堂信仰,以及該地區鸞堂的社會網絡互動。
這本書的完成,首先感謝逢甲大學曆史與文物研究所王誌宇教授、高雄師範大學颱灣曆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劉正元教授,以及颱中教育大學颱灣語文學係林茂賢教授三位師長的教導。王師與劉師係我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研究路途受到二師的提攜與照顧,王師齣身曆史學門,劉師則是人類學門,透過如此的學習,讓本書增添許多不同的觀點,在二師的鼓勵下,纔得以有今日之作;我在民俗領域的奠基,更要感謝林師,初入大學殿堂學習,即被林師的教學風格所吸引,學習曆程上,更受林師「牽教」, 促使我迴歸在地研究,感謝三位師長的知遇之恩。此外,更要嚮齣版計畫的匿名審查委員,有瞭委員建議,也讓這本專書更為臻備。
在田野及參與觀察的過程中受到各位鸞堂前輩先進幫助,於此緻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感謝誠心社明善堂主王國柱先生、副堂主林義雄先生、司經柯鳳明先生細心的指導,感謝舉善堂、協善堂、靈善堂、慈善堂、樂善堂、啓善堂、養靈堂、喜善堂等堂主、執事前輩,豐富瞭本書田野資料的厚實,其中啓善堂主黃海含先生、養靈堂主王文鴻先生、喜善堂主鄭客仁先生不厭其煩接受我的叨擾,由衷緻謝。
也感謝我的傢人,因為你們的容忍與體諒,我纔能堅持在研究的路途上。最後,特彆要嚮諸位聖真感謝與緻意,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曾麵臨多次的瓶頸,每當萌生退意之時,隻要心中靜禱求助恩主及諸位恩師,問題、瓶頸總是迎刃而解,或許這樣的說法過於玄異,更或許因為筆者身為鸞堂信仰者,如此信仰之心,得濛諸真眷顧,纔得成就本書。故而,將撰寫本書過程無法解釋的情況,歸結於受到恩主及諸位恩師的幫助,就讓我用這本《颱灣鳳邑儒教聯堂的飛鸞勸化與社會網絡》聊錶寸心吧!
2016 年12 月1 日書於成功大學曆史係館
圖書試讀
參與寺廟活動大概是多數颱灣人共同的生活經驗與記憶,其中以神明誕辰,也就是俗稱的「神明生」最多,從俗諺「三月痟媽祖」,即可反映此種現象,顯現颱灣民眾對寺廟活動的參與程度,然而在颱灣不僅僅隻有農曆三月的「媽祖生」,每個月也都有各種神祇誕辰,可見寺廟活動的影響力是不容小覷。
與多數颱灣民眾相同,「看熱鬧(kuànn láu liat)」係從小養成的經驗和興趣,迴憶幼時,因住傢緊鄰寺廟,接觸宗教活動可謂頻繁,當時也與外界認為神秘之宗教儀式「扶鸞」有微妙的邂逅,小時候並不知這是多特殊的信仰儀式,如此的邂逅確實也影響筆者至今。其實接觸扶鸞並非偶然或者意外,祖父與父親皆是正鸞生,算是一種傢族信仰,隻是當時不知悉而已,這種兒時的經驗,也在成年之後化為實際的信仰行為,高三那年開始「行堂(kiânn tng)」,大學四年級(2010)奉恩師之命正式宣誓入堂。
基於這樣的生活經驗,又加上所學與民俗文化、民間信仰相關甚深,遂而提筆撰文,藉由大學以降的課程修習,啓發瞭對民間信仰與鸞堂議題的求知慾,閱讀相關的研究與書籍,深刻發覺書中呈現與筆者生長地「鳳山」的鸞堂信仰有甚多差異之處,這是本書得以成形的始端。經由大量的閱讀及田野觀察發現,許多研究者為避免探討主題失焦,都會免除討論周邊問題,鸞堂研究亦然,如王見川兩篇著作〈西來庵事件與道教、鸞堂之關係——兼論其周邊問題〉、〈略論陳中和傢族的信仰與勸善活動〉提供對鸞堂研究之反思。
王見川兩篇文章,前者討論西來庵與鸞堂的關係,除全颱白龍庵開基五大傢將團外,西來庵亦有五團的傢將,其堂號以「吉」字為頭,是全颱灣「吉」字頭傢將團之源,在整個傢將信仰與文化的發展過程極為重要, 但王氏並未談及西來庵傢將與鸞堂間的互動,令他人無法得知西來庵的信仰全貌及西來庵事件中,傢將團是否參與或是扮演角色為何?後者亦是聚焦於陳中和及其傢族在鸞堂的勸善事業,對陳中和傢族是否為單純的鸞堂信仰者也未有討論。傳統上,地方神廟是公眾的議事場域,仕紳掌握瞭寺廟,亦是掌握瞭分配利益的權力,在此文中,隻見身為仕紳階層的陳中和奔走於鸞堂的勸善活動,卻未見投身更廣泛之民間信仰相關事務,這顯然與一般大眾對大多數仕紳的地方參與情況印象有所不同。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書名《颱灣鳳邑儒教聯堂的飛鸞勸化與其社會網絡》讓我立刻聯想到的是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的融閤。我對“飛鸞”這個儀式一直感到非常著迷,它代錶瞭一種直接與神明溝通、獲取指導的獨特途徑,而“勸化”更是點齣瞭這種行為背後深刻的社會功能——它不僅僅是為瞭個人修行,更是為瞭引導整個社區嚮善。儒教聯堂的存在,則錶明瞭傳統儒傢思想在颱灣民間社會中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如何與充滿神秘色彩的飛鸞儀式相結閤,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這本身就極具研究價值。我期待書中能詳細闡述,在鳳邑這個地方,儒傢所倡導的道德規範,如仁、義、禮、智、信,是如何通過飛鸞的方式被具體實踐和傳遞的。是藉助神諭的指引,還是通過信徒的感召?而“社會網絡”的引入,則為我的閱讀增添瞭更廣闊的想象空間。我好奇書中會如何描繪齣,以儒教聯堂為中心,所形成的龐大而復雜的社會關係網。這個網絡是如何運作的?它包括哪些群體?信徒之間是如何相互支持的?這種網絡結構又如何影響著飛鸞勸化的效果和範圍?這本書承諾為我揭示一個充滿活力、根植於傳統卻又不斷適應時代的颱灣社會麵貌,讓我能夠從一個更宏觀、更深入的角度去理解民間信仰與社會結構之間的緊密聯係。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颱灣鳳邑儒教聯堂的飛鸞勸化與其社會網絡》本身就勾起瞭我的極大興趣。一直以來,我對颱灣民間宗教的復雜性和它如何與社會結構深度交織在一起有著濃厚的探究欲望。尤其是“飛鸞”這一獨特的儀式,聽起來就充滿神秘感,似乎是連接人神、引導世俗的關鍵媒介。而“儒教聯堂”的齣現,則讓我對傳統儒傢思想在現代颱灣社會中的傳承和變形有瞭新的想象。書中探討的“勸化”作用,是否意味著在社會變遷的浪潮中,儒傢思想依然扮演著一種道德規範和精神指引的角色?更讓我好奇的是,這種勸化是如何通過飛鸞儀式的具體實踐來實現的?是藉助神靈的啓示,還是通過群體性的參與和互動?而“社會網絡”的引入,則進一步拓展瞭我的視野。我期待書中能夠清晰地梳理齣,以鳳邑儒教聯堂為核心,其周圍圍繞著怎樣的社群關係?這些社群在飛鸞勸化過程中扮演瞭怎樣的角色?是參與者、傳播者、還是受益者?它們之間又形成瞭怎樣的互動模式?我相信,這本書一定能為我揭示一個充滿活力的、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不斷對話的颱灣社會圖景,讓我對颱灣的文化肌理有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颱灣鳳邑儒教聯堂的飛鸞勸化與其社會網絡》如同一個精巧的鑰匙,打開瞭我對一個鮮為人知的文化現象的好奇之門。我對“飛鸞”這個概念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文學作品中關於神鬼溝通的描繪,而這本書則將其置於具體的曆史和地域背景下——颱灣的鳳邑,以及儒教聯堂這樣一個組織。這立刻引發瞭我對文化在地化和宗教變遷的思考。儒傢思想作為中華文明的基石,在颱灣民間宗教中以何種形式得以延續和發展,並且與“飛鸞”這樣的薩滿式儀式相結閤,這本身就是一個引人入勝的研究課題。我特彆期待書中能夠深入剖析“勸化”的具體內容和方式。它是否是一種溫和的說教,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還是帶有一定的強製性?它針對的是哪些社會問題,又試圖解決哪些人生睏惑?而“社會網絡”這個詞,則讓我看到瞭本書超越單純的宗教研究,觸及社會學領域的潛力。我設想書中會描繪齣一個龐大而精細的網絡,將信徒、傢庭、宗族、甚至地方政治和社會力量都聯係在一起。這個網絡是如何支撐飛鸞活動的運行,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當地社區的日常生活和價值觀?我渴望瞭解,在這種儀式和網絡交織的動力下,鳳邑當地的社會是如何運作的,以及人們是如何在其中找到歸屬感和意義的。
评分讀到《颱灣鳳邑儒教聯堂的飛鸞勸化與其社會網絡》這個書名,我首先聯想到的是那些流傳在我們生活中的、充滿瞭智慧與教誨的民間故事。飛鸞,這個詞本身就帶有一種古老而神秘的韻味,仿佛是溝通天地、傳遞神諭的獨特方式。我一直對這種“降筆”的儀式感到好奇,它究竟是如何發生的?那些被認為是神明附體的乩童,又是如何解讀和傳播神諭的?而“勸化”二字,則直接點明瞭飛鸞的核心功能——引導人們嚮善,淨化心靈。在當今社會,物質至上、價值多元的洪流中,這種具有精神導嚮性的勸化,顯得尤為珍貴。我尤其關心的是,在颱灣的鳳邑地區,儒教聯堂是如何將儒傢的倫理道德融入到飛鸞勸化之中?是強調孝道、仁義,還是宣揚忠誠、信義?這些古老的價值,又如何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以適應現代人的生活和觀念?而“社會網絡”的視角,則讓我預見書中對集體行為和人際互動的大量論述。一個聯堂的建立和運作,必然牽扯到眾多信徒、道士、以及地方社區的成員。他們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又在怎樣的社會結構中,共同參與和維係著飛鸞的活動?這本書似乎提供瞭一個絕佳的窗口,讓我得以窺探隱藏在宗教儀式背後的,復雜而精密的社會運作機製。
评分《颱灣鳳邑儒教聯堂的飛鸞勸化與其社會網絡》——僅僅是這個書名,就足以讓我産生一種抽絲剝繭的探索欲。在我看來,“飛鸞”是一種充滿儀式感和神秘感的溝通方式,它不僅僅是宗教的錶達,更可能是一種社會記憶和集體情感的載體。而“勸化”二字,則暗示著這種溝通背後有著明確的目的性,是希望通過某種方式來引導、修正甚至淨化人心。我很好奇,在颱灣鳳邑這個特定的地理和文化語境下,儒教聯堂是如何將儒傢思想的精髓,例如“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理念,通過飛鸞這一載體加以轉化和傳播的。這種轉化是否會涉及對傳統儒傢思想的創新性解讀,以使其更符閤現代社會的價值觀?而“社會網絡”的視角,更是讓我看到瞭本書的廣度和深度。我設想,本書會對以聯堂為中心,嚮外輻射的各種社會關係進行細緻的描繪。這其中可能包括信徒之間的互助,與地方仕紳的聯係,甚至與其他宗教團體或民間組織的互動。我特彆想知道,這些網絡是如何促進飛鸞活動的有效運作,同時又如何反過來影響著網絡的鞏固和擴張?這本書無疑為我提供瞭一個理解颱灣社會文化復雜性的絕佳平颱,讓我得以一窺隱藏在儀式和信仰之下的,真實而鮮活的人群圖景。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