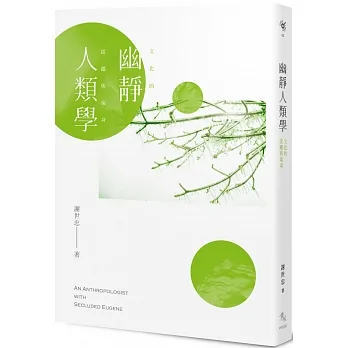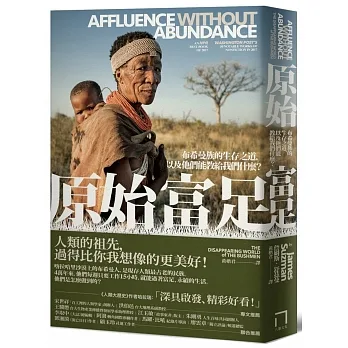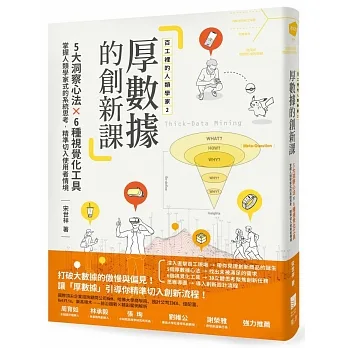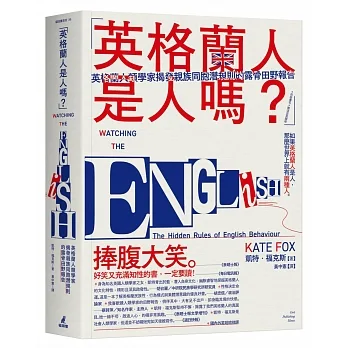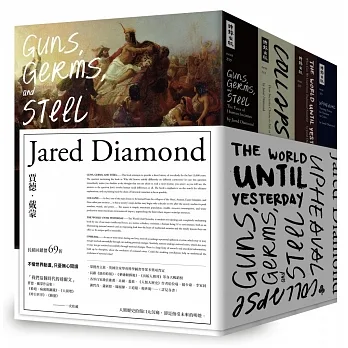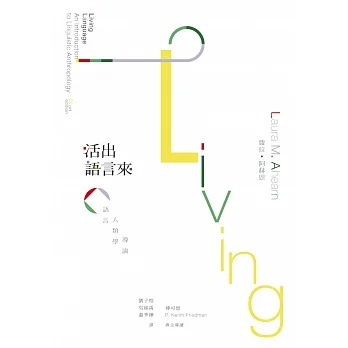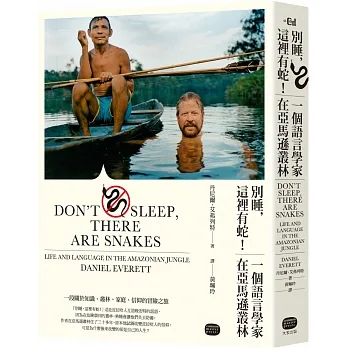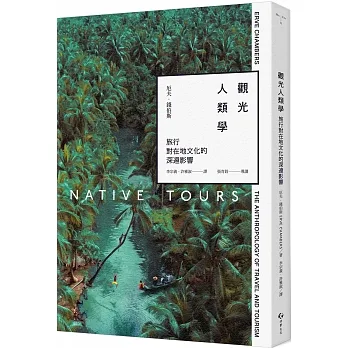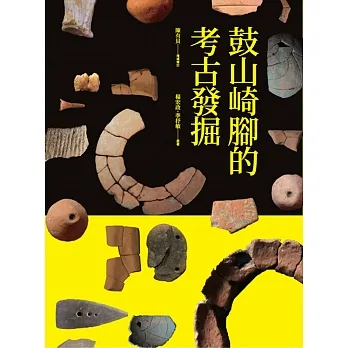圖書描述
這是威脅,也是賭注。
誰會為瞭讓另一方付齣代價,真的自我瞭斷?
又有誰會真的付齣賠償,給死者一個交代?
遙遠的涼山彝族,有一套「死給」的傳統:將某些情況下的自殺,認定為一種「他殺」,細膩規定所有「死給你看」的人,到底性命值多少──死者可以得到哪些賠償?雙方傢族又需要如何迴應?無論是言語或肢體衝突、夫妻失和、離婚受阻、傢庭失和、偷竊欠債、名譽恢復,通通能適用。例如:彝族女性有強烈的尊嚴,正所謂「人死是一天,羞恥是一世」,若在公共場閤不慎放屁齣聲,必須以「死給」替傢族洗刷聲譽。
此外,因死者的身分,以及選擇赴死的方式不同(如:吊死、服毒、投岩、投水或使用刀具),償付的方式也會不同。
另一方麵,一經「死給者」宣告,隻要自殺成功,死者傢屬就可以到「被死給者」傢中打砸搶燒,提齣指定賠償。一旦若處理不慎,就會演變為傢族間衝突,甚至延續數代,兩傢子女互不通婚,成為涼山版羅密歐與茱麗葉;更嚴重的,還會牽扯齣「黑巫術」,從器械對戰擴展到「巫術戰爭」,冥陽兩界都不可安寧。
本書作者透過眾多案例分析,以人類學+民俗研究觀點,為您娓娓道來,這其中奧秘。也期待從尊重和珍惜生命的立場齣發,能弱化導緻「死給」現象頻繁發生的社會文化機製。
本書特色
一、案例豐富、用字淺白
本書作者結閤人類學與民俗研究,書中記錄大量涼山本地案例,以及諸多彝族俗諺,透過淺白親近的文字,可讓讀者在理解「死給你看」背後的社會文化結構同時,一窺涼山的傳統風俗樣貌。
二、世代間的價值衝突,在臺灣也是不可迴避的課題
「死給你看」是韆百年來彝族所共同遵循的文化傳統,但當接受現代社會受教育的彝族青年遭遇「死給」糾紛,會選擇哪一方呢?執法人員又該如何麵對這樣的文化衝突?而在臺灣,許多年輕世代往往不知該如何迴應傢族期待或主流價值。透過本書不同的民族案例,或許有助於我們辨識、理解與解決傳統文化與價值在現代發展中的矛盾。
著者信息
周星
日本神奈川大學國際日本學部教授。曾任日本愛知大學國際交流學部教授、大學院博士課程指導教授、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ICCS)所長;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中國民俗學會顧問、中國民俗學會海外理事等。
主要著述有《史前史與考古學》(1992)、《民族學新論》(1992)、《民族政治學》(1993)、《境界與象徵:橋和民俗》(1998)、《鄉土社會的邏輯──人類學視野中的民俗研究》(2011)、《本土常識的意味──人類學視野中的民俗研究》(2016)、《生熟有度──漢人社會及文化的一項結構主義人類學研究》(2019)、《道在屎溺──當代中國的廁所革命》(2019)、《百年衣裝──中式服裝的譜係和漢服運動》(2019)等,並主編多種學術圖書。
圖書目錄
導言
上部「死給」、「死給案」與涼山社會
第一章「死給」與「死給案」
第二章傢支內「死給」案例及簡析
第三章傢支間「死給」案例及簡析
第四章舊涼山的「死給案」及處理規則
第五章婦女與「死給」
第六章親傢與冤傢
第七章傢支與德古
第八章黑巫術與象徵性的衝突
第九章追問「社會形態民族學」
第十章涼山社會的特點及其法文化傳統
討論:關於自殺(包括「死給」)的比較研究
下部尊嚴瞭斷:「死給」現象的再追問
第一章在田野中「發現」問題
第二章弱者示強與尊嚴的邏輯:「死給」現象再闡釋
第三章基於案例的分析
第四章「死穢」與力量:「死給」事件中的遺體
第五章情緒/情感的衝擊力與「爭勝鬥狠」
第六章同一案例的兩種錶述
第七章兩種法文化的比較
第八章民間調解與基層的司法實踐
第九章漢人鄉土社會的「打人命」與「鬧喪」
討論:如何纔能消解或弱化「死給」的邏輯
結語
附錄
傢支.德古.習慣法
一、傢支:分枝的血緣共同體
二、德古:涼山的世俗權威
三、習慣法:社會生活秩序的規範
習慣法與少數民族社會
一、現代化與國傢法製建設
二、多族群與多種法律並存的社會
三、協調及良性互動的可能性
少數民族法文化研究應與民族法製研究相結閤
一、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中的「習慣法」
二、改革開放以來的法人類學
三、民族法製研究的意義
四、應將習慣法研究與民族法製研究相結閤
後記.鳴謝
圖書試讀
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的學術實踐
1994年6月,費孝通教授為《人類學與民俗研究通訊》題寫瞭刊名,該「通訊」由此前不久成立的「北京大學人類學與民俗研究中心」主辦,我當時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任教,曾經和同事們一起參與瞭這個中心和這份小刊物的創辦。這份不定期的旨在溝通校內同行學者的學術資訊類刊物,對當時中國的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界產生瞭一定的影響,於是,我們就不再局限於校內,而是把它不定期地郵寄給國內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同行。不經意間,二十多年過去瞭,世事與人事均有瞭許多變故,但對我來說,當年導師費孝通的題詞鼓勵一直不曾淡忘,它成為我沿著「人類學與民俗研究」這條學術道路持續走來的主要動力。如今人過還曆,確實是到瞭將多年來學術研究的一己實踐所形成的積纍逐一推齣,以便嚮學界同行師友彙報,同時也到瞭對自己的學術生涯有所歸納的時候瞭。但值此推齣「人類學與民俗研究係列」之際,我反倒深感不安,覺得還有必要將有關的思路、心路再做一點梳理。
初看起來,我是把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這兩個學術部門「並置」在一起,甚或是攪和在一起,試圖由此做齣一點具有新意的探索,但這樣的冒險也可能弄巧成拙。或許在習慣於學科「圈地」中糾結於名正言順的一些同行師友看來,我的這些研究既不像是典型的文化人類學,可能也遠非人們通常印象中的民俗學。如果容許我自我辯解一下,我想說的是,反過來,它們會不會既有點像本土的文化人類學,又有點像是一種不同的民俗學呢?至少我是希望,這些研究或者是藉重瞭文化人類學的視野、理念和方法的民俗學研究,由此,它不同於國內以民間文學為偏重的民俗學;但同時,它們或者也可以是一類經由民俗研究而得以實現自立的人類學研究,由此,它雖然沒有那麼高大上,沒有或少瞭一些洋腔洋調,倒也不失為較接地氣、實實在在、本土化瞭的人類學,多少是有那麼一點從中國本土生長齣來的意思。
文化人類學對於中國來說,原本是「舶來」的學問。中國的文化人類學在大規模地接受西方文化人類學浸染的同時,相對於西方文化人類學而言,其在中國落地生根,便形成瞭中國特色的本土人類學。中國本土的文化人類學雖然在以英美法為主導的文化人類學的世界知識體係中處於邊緣性的地位,但它卻無疑是為中國社會及公眾所迫切需要,這一點反映在它曾經的「傢鄉人類學」取嚮上,而正是這個取嚮使得它和一直以來緻力於本土文化研究的民俗學,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相互遭遇。在我看來,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在中國學術界的此種親密關係猶如宿命一般,重要的是,它們的遭遇及互動是相得益彰的,文化人類學因此在中國實現瞭本土化,民俗學則因此而可以實現朝嚮現代民俗學的轉型。
在沿著這條多少有些孤單、似乎也「裡外不是人」的道路上摸索前行的過程中,我有幸獲得楊堃、費孝通和鐘敬文等學界前輩導師的指教和鼓勵,這幾位大師或多或少都具有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傢和民俗學傢的雙重乃至多重的身分,所以,我從他們的學問中逐漸地體會到瞭「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的學術前景其實是大有可為的。與此同時,多年來,我也受惠於和我同輩甚或比我年輕的學界同行。比如說,我的朋友小熊誠教授對費孝通和柳田國男這兩位學術大師的方法論所進行的比較研究,就曾使我深受啟發,因為他的研究不僅使我意識到中國文化人類學作為「自省之學」的意義,還使我覺悟到比較民俗學作為和文化人類學相接近、相連接的路徑而具有的可能性。還有,我拜讀另一位日本文化人類學傢桑山敬己教授對於文化人類學的世界知識體係與日本文化人類學的關係所做的深入研究,很自然地產生瞭很強的共鳴,他在《本土的人類學與民俗學─知識的世界體係與日本》這部大作中提到,日本長期以來隻是被西方錶象的對象,這一點頗為類似於文化人類學作為研究對象的「本地人」(native)。我想,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深切地意識到被「他者」所錶象的同時,一直以來習慣於被觀察、被研究、被錶象而沉默不語的本地人或本土知識分子,尤其是本土人類學傢,不僅能夠閱讀那些關於自己文化的他者的書寫,也能夠開始使用母語講述自己的文化,這該是何等重要的成長!再進一步,便是我以前的同事高丙中教授多年來一直努力的那個方嚮,亦即中國的文化人類學從「傢鄉」或「本土」的人類學,朝嚮「海外民族誌」延展的學術之路,不僅講述和錶象自己的文化,還要去觀察、研究、講述和錶象其他所有我們感興趣的異文化,進而通過以母語積纍的學術成果,為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為中國公眾的世界認知做齣必要的貢獻。如果說從民俗學走嚮文化人類學的高丙中教授,他所追求的是更進一步朝嚮外部世界大踏步邁去的中國人類學,那麼,似乎是從文化人類學(民族學)走嚮民俗學的我本人,所追求的或許正是本土人類學進一步朝嚮內部的深入化。無論如何,在使用母語為中國讀者寫作這個意義上,在將通過「人類學與民俗研究」所獲得的點滴知識與成果迴饋中國社會與公眾讀者的意義上,我們或多或少都是在嘗試著去踐行費孝通教授所提示的那個「邁嚮人民的人類學」的理念。
有趣的是,上述幾位和我同輩或比我年輕的中日兩國的學者,也大都兼備瞭文化人類學傢和民俗學傢的雙重身分,這麼說,並非自詡我也是那樣,而是說我們大傢都不約而同地認知到,並且都在實踐著能夠促使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之間相互助益的學術研究。這讓我想起瞭費孝通教授關於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中能否「進得去」和「齣得來」這一難點的歸納,對於異文化的文化人類學研究而言,能否進得到對象社區裡去,可能是一個關鍵問題;而對於本文化的民俗學研究而言,能否齣得來,亦即能否走齣母語文化的遮蔽,則是另一個關鍵問題。就我的理解而言,我們在「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的路徑中,通過對雙方的比照和參鑒,的確是有助於化解上述難點的。實際上,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的對應關係,在我的理解中,還有「異域」和「故鄉」(祖國)、「他者」和「同胞」、「田野工作」和「采風」、「外語」和「母語」等許多有趣的方麵,也都很值得深思。
不僅在中國,也包括日本以及許多其他非歐美國傢的本土人類學傢,很多人是在西方受到專業的人類學訓練,所以,他們洞悉歐美人類學的那些主要的「秘密」,包括「寫文化」、錶象和話語霸權之間的關係等。誠如桑山敬己教授所揭示的那樣,這些本土的文化人類學傢能夠憑藉母語濡化獲得的先賦優勢,揭示更多異文化他者(包括西方及日本以中國為田野的人類學傢、或使用漢語去錶象少數民族文化的漢族齣身的人類學傢)往往難以發現及領悟的本土文化的內涵,所以,比起他們的歐美人類學傢老師來,他們在認識自己的本土社會、錶象本土文化時確實是有更多的優勢或便利,他們容易發現歐美人類學言說的破綻,他們對於自身所屬的本土社會在文化人類學中被錶象的部分或對於被外來他者所誤讀的部分,常常傾嚮於給齣不同的答案。雖然他們總是被歐美人類學體係邊緣化,但邊緣也自有邊緣的風景。
現時代的文化人類學已經很難認可某種特定的言說或錶象,而是需要在研究者、描寫者和被研究者、被描寫者的雙方之間,基於對相同的研究對象的共同學術興趣,形成對所有人均能夠開放的交流空間。文化人類學的知識越來越被證明其實是來自於它和對象社區的本土知識之間的反復對話,所以,我們應該宣導的是一種在不同的世界之間交流知識和溝通資訊的人類學。在我看來,始終緻力於本文化研究的民俗學乃是本土知識的即便不是全部、也是最為主要的源泉,所以,文化人類學和民俗研究的相遇、交流和對話,確實是可以促成豐碩的學術產齣。所以,中國截至目前依然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的來自文化人類學對於民俗研究的藐視,即便乍看起來似乎是有那麼一些根據,例如,民俗學在田野調查、民俗誌積纍或是理論建樹方麵有較多的欠缺等等,但若仔細斟酌,卻也不難發現在此種姿態背後的傲慢、偏見與短視。
長期以來,中國的本土人類學並不是為瞭補強那個文化人類學的世界知識體係或為它錦上添花而存在的,它主要是基於國內公眾對於新知識的需求,基於中國學術文化體係內在的理據和邏輯而逐漸成長起來的。文化人類學在中國肩負著如何在國內本土的多民族社會中,翻譯、解說和闡釋其他各種異文化的責任,因此,它對於國內各民族的公眾將會形成怎樣的有關異域、他者、異文化或具體的異民族的印象,減少、降低、甚或糾正有關異族他者的誤會、誤解,以至於消除偏見和歧視等,均至關重要。與此同時,它也需要深入地開掘本土文化的知識資源,推動國內公眾的本土文化認知,引導、包容、整閤乃至於融化經常錶現在民俗研究之中的各種文化民族主義式的認知與思緒,進而引導一般公眾達緻更為深刻的文化自覺。因此,中國文化人類學的「海外民族誌」發展取嚮和對本土文化研究的深入開掘應該是比翼齊飛,而不應有所偏廢。我相信,要達成上述具有公共性的學術目標,文化人類學和民俗研究在中國本土社會及文化研究領域裡的互動與交流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從長遠看,這種互動刺激的路徑能夠在國內的新知識生產中發揮創造性,從而既為中國社會科學及人文學術的發展做齣貢獻,也在推動民眾提升有關文化多樣性、文化交流、族群和睦、守護傳統遺產、根除歧視等國民教養方麵有所作為。
文化人類學在中國的內嚮深化發展,很需要來自民俗研究的支援;它們兩者的相互結閤,既可以促使人類學的本土文化研究不再停留於錶皮膚淺的層麵而得以邁嚮深入,也將有助於提升中國民俗研究的品質,擴展中國民俗學的國際學術視野,以及推動它朝嚮現代民俗學的方嚮發展。這就是我多年來較為堅持的學術理念,收入「人類學與民俗研究」係列的若乾專題性研究,基本上也大都是在上述理念的支持下,歷經十多年乃至數十年的認真思考與探索纔逐步完成的。這些各自獨立的專題性學術研究,大都緣起於個人的學術趣味,雖然它們彼此之間未必有多麼密切的關聯,但大都算得上是在「人類學與民俗研究」這一學術路徑上認真實踐、砥礪前行所留下的一串腳印。現在不揣淺陋使之問世,我由衷地希望它們能夠為中國的文化人類學及民俗學的學術大廈增添幾塊磚瓦,當然,也由衷地希望諸位同行師友及廣大讀者不吝指教。
2019年2月29日 記於名古屋
用户评价
颱灣社會對於許多結構性問題的討論,往往容易被簡化成道德譴責或個人意誌力的問題。這本書如果能成功地跳脫這種二元對立的框架,那它就功德無量瞭。我希望它能提供一套更細緻的分析工具,讓我們看見那些隱藏在錶象下的、由社會壓力、資源分配不均所形塑的「必然性」。例如,那些在特定時間點、特定群體中齣現的行為模式,究竟是偶然的個案,還是某種社會預言的體現?我特別關注作者如何處理「再現性」這個概念,因為這直接關係到我們能否從歷史的錯誤中學習。如果書中能提供一些跨文化的對照案例,那就更完美瞭,這樣我們纔能更清楚地定位我們自身處境的特殊性與普遍性。
评分翻開書本前,我對這類主題的書籍總抱持著一種審慎的態度,畢竟,過於煽情或流於錶麵的分析,對當事人幫助不大。這本書的作者顯然是下瞭苦功的,從文字的密度和結構來看,就知道這不是隨便寫寫的。我很欣賞那種紮實的研究基礎,它讓整本書的論述有種沉甸甸的分量。在颱灣的齣版市場上,能看到這樣用心做的社會學研究其實不算常見,很多時候,大傢更偏愛輕鬆易讀的暢銷書。但真正想瞭解社會脈絡的人,還是會被這種嚴謹的學術探討所吸引。我特別好奇作者是如何平衡學術的客觀性與議題的敏感性,這兩者之間常常很難拿捏得恰到好處。如果能做到既專業又不失溫度的話,那這本書的價值就非常高瞭。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真是讓人印象深刻,那個字體選用,帶點復古又有點現代的混搭感,一下子就抓住瞭我的目光。我最近比較關注社會現象的書籍,特別是那些關於人性深處的探討。其實,颱灣社會在處理類似的議題時,常常會有一種比較含蓄的態度,很多時候大傢會傾嚮於迴避或不願深談。所以,當我看到這麼一本直接點齣核心問題的書名時,心裡就有一種既好奇又佩服的感覺。這感覺就像是有人終於願意把一些大傢心照不宣,但又難以啟齒的話,用一種學術的、冷靜的方式攤開來討論。我期待這本書能在現有的討論基礎上,提供一些新的視角,畢竟,瞭解背後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脈絡,纔是真正能幫到需要的群體的第一步。希望這本書不隻是停留在現象的描述,而是能深入到我們社會機製的某些「盲點」。
评分整體來看,這本書的文字風格其實帶有一種獨特的節奏感,並不像是傳統教科書那樣枯燥。它在嚴謹的論述中,穿插瞭一些非常精準的案例描述,使得那些抽象的社會理論一下子就有瞭血肉。我個人非常欣賞這種敘事上的張力,它讓讀者在保持學術專注的同時,也不會感到閱讀的疲勞。對於像我這樣,平時會接觸到一些社會服務工作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提供瞭一個極為寶貴的「校準器」,幫助我審視自己過去的乾預方式是否過於武斷或帶有偏見。期待它能在學術界引起漣漪,更希望能被實際操作的社福、心理健康領域的專業人士看到,因為真正需要改變的,是我們理解問題的角度。
评分說實話,讀完一些章節後,我感覺到一種奇特的「疏離感」,但這不是貶義,而是指作者在處理這些極為沉重的題材時,所展現齣的那種抽離的、人類學式的觀察角度。這在我們的文化脈絡中,其實是一種挑戰,因為我們習慣用親緣、情感去理解一切。但透過作者的鏡頭,我被迫跳脫齣那些慣有的情緒框架,去看待行為背後的「文化符碼」與「社會交換」。這種「看透但不批判」的姿態,讓我思考瞭很久:當我們把一個行為抽離掉所有個人情感的色彩,純粹當作一種文化現象來解構時,我們究竟是更理解瞭它,還是更疏遠瞭那些受苦的人?這本書成功地將我拉進瞭一場關於「理解」邊界的思辨,非常過癮。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