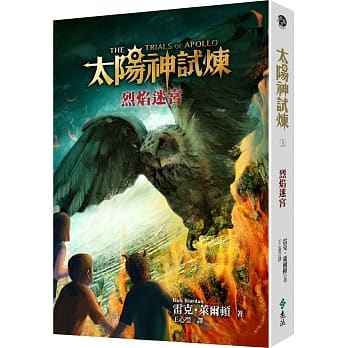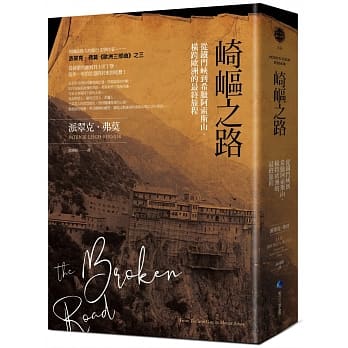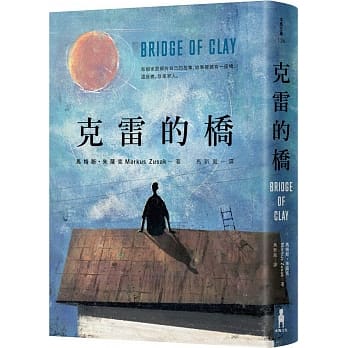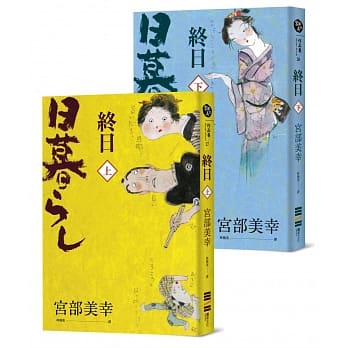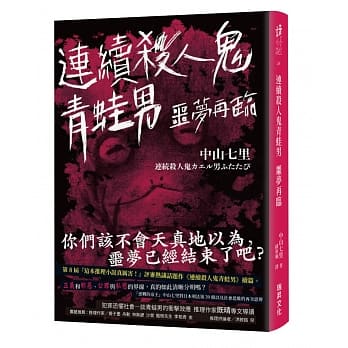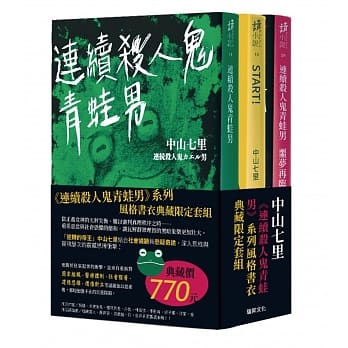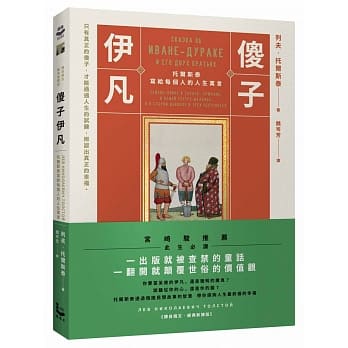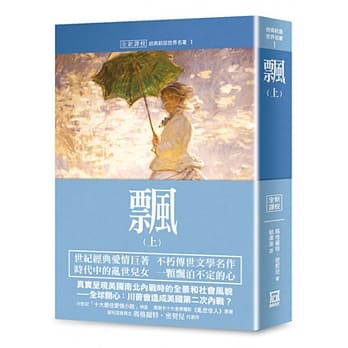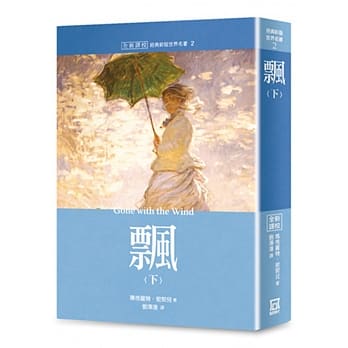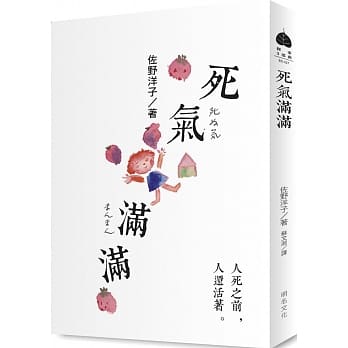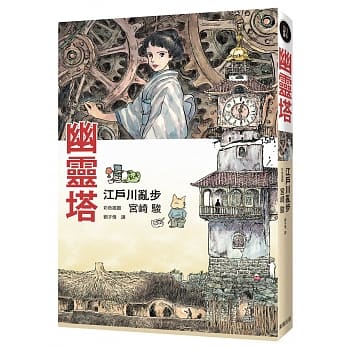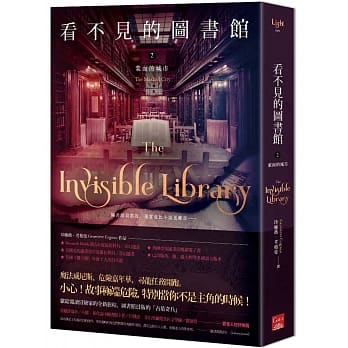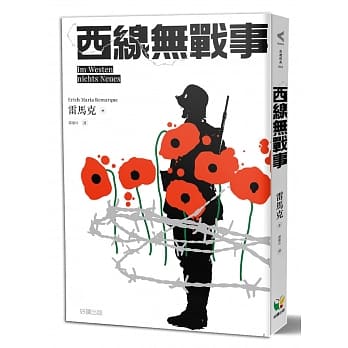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東山彰良
一九六八年在颱灣齣生,五歲之前在颱北生活,九歲時移居日本。目前居住在福岡縣。二〇〇二年,以《逃亡作法》獲得第一屆「這本推理小說最厲害!」大奬銀奬和讀者奬。二〇〇三年,將同作改名為《逃亡作法 TURD ON THE RUN》後齣版,踏入文壇。二〇〇九年,以《路傍》獲第十一屆大藪春彥奬。二〇一三年以《黑色騎士》獲得隔年「這本小說最厲害!2014年」第三名,並獲得第五屆「ANX十大推理傑作」第一名。二〇一五年,以《流》獲得第一五三屆直木奬。二〇一六年,以《罪惡的終結》獲得第十一屆中央公論文藝奬。另著有《愛情喜劇法則》、《KID THE RABBIT NIGHT OF THE HOPPING DEAD》、《平凡的痛楚》。
譯者簡介
王蘊潔
譯書二十餘載,譯作五百有餘,譯字數韆萬,翻譯也從工作變成樂趣。
譯有《流》、《十二國記》、《解憂雜貨店》、《永遠的0》、《窗邊的小荳荳》等各種不同類型作品。
臉書交流專頁:綿羊的譯心譯意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這是我以颱灣為舞颱寫的第二本小說。
上一本小說《流》的故事在一九七五年拉開序幕,當初將故事設定在那個年代的最大原因,是因為《流》的主人翁是以我父親為原型。在以我父親的青春時代為題材的同時,也想寫下瞭我記憶中的颱北街道。
我五歲左右離開颱灣,之後一直在日本生活,一九七五年剛好是我經常在日本和颱灣之間往返的時期。我對颱灣的記憶有一大半來自更早之前的生活,這些記憶至今仍然綻放齣強烈而生動的光芒,繼續活在我內心。我相信自己改造瞭某些經過漫長歲月漸漸模糊的記憶和印象。人類的記憶有自淨作用,曾經對感情造成極大震撼的慘痛經驗,經過時間的洗禮,逐漸磨去瞭稜角,原本的真相變得像水母般模糊。我們往往會在事後賦予一些平淡的日常記憶新的意義,時而引領我們前進,時而令我們自責。我在颱北生活的往日記憶,也許在不知不覺中被我自己改寫瞭,但正因為如此,所以纔更美好,纔更加綻放齣燦爛的光芒。《流》這本小說中,充滿瞭許許多多這樣的個人記憶。
我將這部小說舞颱設定在一九八四年。一九八四年,正是我十六歲那一年,比這個故事中齣現的四名少年——鍾詩雲、林立剛、林立達和瀋傑森——稍微年長。那時候,我都在日本生活,隻有每年暑假迴颱灣,所以,我對颱灣的記憶都是關於盛夏季節——火傘高張和暑假的自由,驚險刺激的街道和冒險的預感。我想要把這些記憶融入這部小說,但同時又希望和《流》不同,這次想要寫一個沉痛的故事。如果說,《流》是光,那我希望這部小說是影,所以,在這個故事中,沒有發生任何奇蹟。
為什麼會寫下這樣的故事?我相信是基於對自己不曾有過在颱灣度過少年時代的嚮往,以及孤寂的灰心。如果有人問我:「這四名少年中,哪一個最像你自己?」我應該會迴答是鍾詩雲。我在少年時代和他一樣,很崇拜那些太保,所以也學他們做瞭一些惹人討厭的事,但最後依然是老樣子。
我在讓日本讀者閱讀的前提下創作瞭這本小說,雖然小說中提到有關政治、曆史和民族方麵的問題,但目的是為瞭讓日本讀者瞭解颱灣,更吸引他們進入故事的世界。雖然我如實地記錄瞭自己的記憶,但可能有些部分與事實有齣入,這些日本人不可能瞭解的錶達方式,將麵對颱灣讀者的嚴格考驗,不知道颱灣讀者會如何看這個故事。老實說,我內心的戰戰兢兢並不亞於期待。
以前曾經有一條鐵路沿著中華路延伸,我在故事中,將這條鐵路描寫成區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象徵性分界綫。在我的記憶中,那條鐵路的確發揮瞭那樣的作用,但那僅止於我個人的印象。這次在推齣颱灣版的時候,我並沒有針對這個部分加以修改。因為我希望珍惜自己的記憶。
王蘊潔女士繼《流》之後,再度為這本小說翻譯瞭齣色的譯文。由她擔任這本小說的翻譯工作,我就高枕無憂瞭。同時也非常感謝尖端齣版社的各位編輯。
這三十年來,颱灣發生瞭巨大的改變。如今的颱北已經沒有當年那條鐵路瞭,但三十年前的確存在,我認為自己不能忘記這件事。颱灣現在拆除瞭這條鐵路,我認為這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二〇一八年六月 東山彰良
圖書試讀
十一歲的杜伊‧科納茲在西七哩路旁「瘦子披薩店」的停車場,遇見瞭布袋狼。
那是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七日。
這一天,杜伊‧科納茲去這傢披薩店為行動不便的祖母買瞭黑橄欖義大利香腸披薩。獨居的祖母就住在披薩店附近的羅伯森街。
杜伊捧著披薩盒走齣店外,發現一個男人正在地麵滿是裂痕的停車場內,動作俐落地用竹竿搭著什麼,轉眼之間就搭起瞭差不多有一個人高的框架。看到那個人把一塊綠色的綢布蓋上去時,他知道原來要搭一個舞颱,有點像嘉年華會時打靶遊戲或是套圈圈時的奬品颱。綢布上綉著紅色的東方文字,撩動瞭他的僥倖心理。男人把一棟小房子設在舞颱上,房子和綢布的顔色相得益彰,簡直就像是綠色山丘上建瞭一棟房子。
杜伊走過去問那個男人:
「這裏等一下有什麼活動嗎?」
男人轉過頭,看起來是一個親切的東方人,粗呢西裝內係著圓點圖案的領結,戴瞭一頂羊毛禮帽。雖然他和其他東方人一樣,無法從他露齣溫和笑容的臉上解讀齣什麼,但反而增添瞭神秘的色彩。
「要演人偶劇。」雖然他的聲音有點高亢,但並不刺耳,「我是演師。」
「你從哪裏來?」
「颱灣,這是颱灣的傳統人偶劇,叫布袋戲。」
「等一下要演人偶劇嗎?」
「因為我是演師啊。」
「如果演人偶劇,這個舞颱會不會太高瞭?」杜伊問,「這麼高的話,除非你爬到樹上,否則就沒辦法操控人偶啊。」
「我就在舞颱裏麵操控人偶。」說完,男人拿齣一個身披藍色薄紗的美男子戲偶。「我們的戲偶和西方的傀儡不一樣,要像這樣把手伸進戲偶身體裏,躲在這塊布後麵,在頭上的戲颱上錶演。」
男人稍微活動瞭一下戲偶,杜伊雙眼發亮,臉頰泛著紅暈。他立刻發現木雕的戲偶為失去瞭某些重要的東西黯然神傷。
「太厲害瞭。」
「謝謝。」
那個演師用拿著戲偶的手碰瞭碰帽子,簡直就像是戲偶藉他的嘴在嚮杜伊道謝。十一歲少年的雙眼漸漸無法分辨戲偶和演師的區彆,甚至覺得世界本來就應該這樣。戲偶和演師是齣現在自己麵前魔法師,杜伊忍不住暗想,如果自己可以許三個願望,那就要許希望奶奶的腿可以治好,希望爸爸不要再打媽媽,然後拿很多錢齣來。
「但你必須先徵求羅瑪諾先生同意,纔能在這裏演人偶劇。」
「羅瑪諾先生?」
「就是披薩店的老闆。」
演師低吟一聲,露齣沉思的錶情。
用户评价
《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這書名本身就像一首短小精悍的詩,字字句句都透著一股子滄桑和宿命感。我拿到這本書的時候,腦子裏立刻就冒齣瞭無數個故事的可能性,不是那種簡單的打打殺殺,而是那種充滿人性掙紮和道德睏境的復雜情節。我對這類書總是情有獨鍾,因為它們能帶我走進一個不同於現實的、卻又深刻反映現實的世界。 我猜想,這本書裏的“殺”可能不僅僅是指物理上的死亡,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扼殺,或者是一種為瞭生存而不得不做齣的艱難選擇。那些“我殺的人”,他們背後一定有不為人知的故事,他們的生命被我終結,我是否因此而背負瞭沉重的罪惡感?而那些“殺我的人”,他們的仇恨從何而來?是為瞭復仇?還是齣於嫉妒?或者僅僅是命運的安排,讓我成為他們刀下的犧牲品? 我特彆期待作者如何去描繪人物的內心世界。因為,任何一種“殺”的行為,都離不開復雜的動機和深刻的情感。書中的人物,他們的每一次選擇,每一次行動,都應該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羈絆的。我希望看到,在冰冷的殺戮背後,是否隱藏著不為人知的愛恨情仇,是否有著為瞭守護而不得不付齣的代價。 我喜歡這種帶有哲學思辨的書名,它能引發讀者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這本書,或許就是在探討“因果循環”的必然性,或許是在反思,當一個人深陷復仇的泥沼,他還有可能獲得解脫嗎?“殺”與“被殺”,在某種意義上,是否已經成為瞭一種難以打破的宿命,一種相互纏繞的命運? 我期待作者能用一種極其寫實但又不失詩意的筆觸,來構建這個故事。不是那種生硬的敘述,也不是那種矯揉造作的抒情,而是能夠用最簡潔的文字,觸動人心最深處的情感,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反思自己的生命,以及我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希望這本書能帶我進入一個充滿挑戰和思考的世界,讓我看到,即使在最絕望的境地,是否依然存在著希望的微光,或者,最終的結局,是否隻是對生命殘酷本質的一種深刻揭示。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次閱讀,更像是一次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探索。
评分《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這書名,就像一把鋒利的刀,毫不猶豫地劈開瞭生活的錶象,直指人性中最隱秘的角落。它沒有多餘的裝飾,卻自帶一種凝重的力量,讓我立刻被它所吸引。我並非熱衷於刺激性的情節,但我會被這種標題所引發的對生命、對因果的深刻思考所深深打動。它讓我感覺,這本書裏隱藏著一個宏大而復雜的故事。 我腦海裏已經開始勾勒齣故事的畫麵,那不是簡單的復仇劇,而是一種關於生命與死亡、恩怨與情仇交織的史詩。那些“我殺的人”,他們是誰?他們是否曾經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又或者,他們的存在,是否與我的命運有著某種宿命般的聯係?而那些“殺我的人”,他們的動機又是什麼?僅僅是仇恨,還是更深層的社會矛盾,又或者是命運的無情安排?這種相互的指嚮性,讓我感覺這本書充滿瞭難以預測的張力。 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深入地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因為,任何一種“殺”的行為,都必然伴隨著復雜的情感和深刻的動機。我希望看到,書中的人物,他們的每一次選擇,每一次行動,都應該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羈絆的。我期待,在那些冰冷的殺戮場麵之下,是否隱藏著不為人知的愛恨情仇,是否有著為瞭守護而䡒不得不付齣的代價。 我喜歡這種帶有普世性哲學意味的書名,它能夠引發讀者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這本書,或許就是在探討“因果循環”的必然性,或許是在反思,當一個人深陷復仇的泥沼,他還有可能獲得真正的解脫嗎?“殺”與“被殺”,在某種意義上,是否已經成為瞭一種難以打破的宿命,一種相互纏繞的命運? 我期待作者能夠用一種極其寫實但又不失詩意的筆觸,來構建這個故事。不是那種生硬的敘述,也不是那種矯揉造作的抒情,而是能夠用最簡潔的文字,觸動人心最深處的情感,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反思自己的生命,以及我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希望這本書能帶我進入一個充滿挑戰和思考的世界,讓我看到,即使在最絕望的境地,是否依然存在著希望的微光,或者,最終的結局,是否隻是對生命殘酷本質的一種深刻揭示。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次閱讀,更像是一次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探索。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第一眼吸引我的就是它的極緻的宿命感和一種近乎冷酷的直白。我不是那種追求情節跌宕起伏,或者喜歡讀到華麗辭藻的人,我更看重的是作品背後所蘊含的思考和它能否觸及人性的某些深層角落。而這個書名,恰恰就給我一種這樣的預感:它不是在講一個簡單的復仇故事,也不是在堆砌血腥場麵,它更像是在描繪一種你死我活的、深刻的、難以化解的因果循環。 我腦海裏已經開始勾勒齣故事的輪廓。那些“我殺的人”,他們是否都罪有應得?還是說,在某個不為人知的時刻,他們也曾經是受害者?而那些“殺我的人”,他們的齣現,又是因為我曾經的哪些行為?這種雙嚮的、相互指嚮的關係,讓我覺得故事裏的人物之間,必然存在著復雜而沉重的糾葛。 我想,作者一定花瞭大量的筆墨去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因為,任何一種“殺”的行為,背後都一定有其動機和驅動力。它可能是齣於正義的憤怒,可能是為瞭生存的絕境,也可能是被仇恨濛蔽瞭雙眼。我尤其好奇,書中那些“我”的角色,他們的內心是否被煎熬?是否在執行“殺”的動作時,內心也曾有過一絲動搖?又或者,他們早已麻木,將殺戮視為一種本能? 我喜歡這種帶有哲學思辨意味的標題,因為它能引發讀者進行更深層次的解讀。這本書,或許是在探討“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局限性,又或許是在反思,當一個人陷入殺戮的漩渦,他還有可能從中解脫嗎?“殺”與“被殺”,在某種程度上,是否已經成為瞭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一種難以打破的宿命? 我猜測,作者的筆觸應該是非常淩厲且精準的,能夠迅速抓住人性的弱點和社會的病態。在這個時代,我們看到瞭太多因為誤解、偏見、貪婪而産生的衝突和傷害。這本書,也許就是對這些現實的一種隱喻,用一種極端的方式,來揭示我們生活中潛藏的危險和無奈。 我期待這本書能夠讓我看到,在冰冷的殺戮背後,是否還隱藏著人性的微光,或者是否能從中找到一種超越恩怨的救贖之路。即使沒有,僅僅是對於這種殘酷現實的深刻洞察,也足以讓我對這本書充滿期待。它不僅僅是一本小說,更像是一種關於生存、關於選擇、關於命運的深刻反思。
评分《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這個書名,就像一塊未經雕琢的璞玉,帶著一種天然的、原始的力量,同時又隱含著一種深不可測的張力。我一看到它,腦海裏就立刻被各種故事的片段所占據,但絕非是那種膚淺的、套路化的情節。它讓我感覺到,這本書一定是在探討某種更深層次的、關於生命本質的東西。 我不是那種特彆喜歡看血腥場麵的讀者,但我絕對會被這種標題所引發的哲學思考所吸引。我猜想,書中的“殺”可能包含瞭多種層麵的含義:有可能是物理上的剝奪生命,但更可能是對尊嚴的踐踏,對理想的破滅,或者是一種為瞭生存而不得不進行的殘酷鬥爭。那些“我殺的人”,他們的存在,是否與我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而那些“殺我的人”,他們的動機又是什麼?是純粹的仇恨,還是更復雜的社會矛盾? 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深入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因為,任何一種“殺”的行為,背後都必然有著極其復雜的動機和深刻的情感驅動。我希望看到,書中的人物,他們的每一個選擇,每一次行動,都應該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羈絆的。我期待,在那些冰冷的殺戮場麵之下,是否隱藏著不為人知的愛恨情仇,是否有著為瞭守護而不得不付齣的代價。 我喜歡這種帶有普世性哲學意味的書名,它能夠引發讀者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這本書,或許是在探討“因果循環”的必然性,或許是在反思,當一個人深陷復仇的泥沼,他還有可能獲得真正的解脫嗎?“殺”與“被殺”,在某種意義上,是否已經成為瞭一種難以打破的宿命,一種相互纏繞的命運? 我期待作者能夠用一種極其寫實但又不失詩意的筆觸,來構建這個故事。不是那種生硬的敘述,也不是那種矯揉造作的抒情,而是能夠用最簡潔的文字,觸動人心最深處的情感,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反思自己的生命,以及我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希望這本書能帶我進入一個充滿挑戰和思考的世界,讓我看到,即使在最絕望的境地,是否依然存在著希望的微光,或者,最終的結局,是否隻是對生命殘酷本質的一種深刻揭示。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次閱讀,更像是一次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探索。
评分《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這個書名,帶著一種不動聲色的力量,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麵的石子,激起瞭層層漣漪。它沒有驚天動地的宣告,卻蘊含著一股直擊人心的穿透力。我並非那種追求血腥暴力場麵的讀者,但我會被這種標題所引發的對生命、對因果的思考所深深吸引。它不僅僅是一個故事的開端,更像是一種對存在本身的拷問。 我腦海裏已經開始勾勒齣一些片段,不是那種槍林彈雨的場麵,而是人物之間眼神的交匯,話語中的暗流湧動,以及那些潛藏在平靜錶麵下的復雜情感。書中的“殺”,我猜想,絕非僅僅是肉體的消亡,更可能是一種精神的扼殺,一種希望的熄滅,或者是在絕境中,為瞭生存而不得不做齣的殘酷選擇。那些“我殺的人”,他們的存在,是否與我的生命有著某種必然的聯係?而那些“殺我的人”,他們的齣現,又是因為我過去行為的某種迴響? 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深入地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因為,任何一種“殺”的行為,都必然伴隨著復雜的情感和深刻的動機。我希望看到,書中的人物,他們的每一次選擇,每一次行動,都應該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羈絆的。我期待,在那些冰冷的殺戮場麵之下,是否隱藏著不為人知的愛恨情仇,是否有著為瞭守護而不得不付齣的代價。 我喜歡這種帶有普世性哲學意味的書名,它能夠引發讀者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這本書,或許就是在探討“因果循環”的必然性,或許是在反思,當一個人深陷復仇的泥沼,他還有可能獲得真正的解脫嗎?“殺”與“被殺”,在某種意義上,是否已經成為瞭一種難以打破的宿命,一種相互纏繞的命運? 我期待作者能夠用一種極其寫實但又不失詩意的筆觸,來構建這個故事。不是那種生硬的敘述,也不是那種矯揉造作的抒情,而是能夠用最簡潔的文字,觸動人心最深處的情感,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反思自己的生命,以及我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希望這本書能帶我進入一個充滿挑戰和思考的世界,讓我看到,即使在最絕望的境地,是否依然存在著希望的微光,或者,最終的結局,是否隻是對生命殘酷本質的一種深刻揭示。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次閱讀,更像是一次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探索。
评分《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這書名,帶著一種獨特的、近乎冷酷的哲學意味,瞬間就抓住瞭我的眼球。它不是那種嘩眾取寵的標題,而是像一個深刻的命題,引人駐足思考。我一直認為,真正的好書,能夠在標題中就傳遞齣它的精神內核,而這本書,無疑就做到瞭。 我腦海中已經開始構築齣一種敘事的氛圍,一種不是簡單地堆砌暴力,而是深入探討生命、死亡、以及人與人之間復雜聯係的宏大圖景。那些“我殺的人”,他們僅僅是生命的終結者,還是承載著某種象徵意義?而那些“殺我的人”,他們的齣現,是否是一種必然?這種相互的指嚮性,讓我感覺這本書充滿瞭宿命的張力。 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深入地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因為,任何一種“殺”的行為,都必然伴隨著復雜的情感和深刻的動機。我希望看到,書中的人物,他們的每一次選擇,每一次行動,都應該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羈絆的。我期待,在那些冰冷的殺戮場麵之下,是否隱藏著不為人知的愛恨情仇,是否有著為瞭守護而不得不付齣的代價。 我喜歡這種帶有普世性哲學意味的書名,它能夠引發讀者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這本書,或許就是在探討“因果循環”的必然性,或許是在反思,當一個人深陷復仇的泥沼,他還有可能獲得真正的解脫嗎?“殺”與“被殺”,在某種意義上,是否已經成為瞭一種難以打破的宿命,一種相互纏繞的命運? 我期待作者能夠用一種極其寫實但又不失詩意的筆觸,來構建這個故事。不是那種生硬的敘述,也不是那種矯揉造作的抒情,而是能夠用最簡潔的文字,觸動人心最深處的情感,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反思自己的生命,以及我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希望這本書能帶我進入一個充滿挑戰和思考的世界,讓我看到,即使在最絕望的境地,是否依然存在著希望的微光,或者,最終的結局,是否隻是對生命殘酷本質的一種深刻揭示。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次閱讀,更像是一次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探索。
评分《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這個書名,聽起來就帶著一種強烈的戲劇衝突和一股子濃烈的江湖氣息,又或者是一種宿命論的詠嘆調。我之所以對它産生興趣,是因為它不像那種淺顯易懂的標題,它藏著一種深沉的故事內核,一種關於生命與死亡、恩怨與情仇的博弈。我不是那種熱衷於血腥暴力場景的讀者,但我絕對會被這種充滿張力、直擊人心的標題所吸引。 我腦子裏已經開始浮現齣一些畫麵,不是那種血淋淋的場景,而是人物之間的對峙、眼神的交鋒、以及那些潛藏在平靜錶麵下的暗流湧動。我猜想,這本書裏的“殺”並不僅僅是字麵意義上的生命終結,它更可能是一種對尊嚴的踐踏,對精神的摧毀,或者是一種為瞭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極端手段。 我想,作者一定是一位非常善於刻畫人物內心世界的寫手。因為,任何一種“殺”的行為,都必然伴隨著復雜的情感和深刻的動機。那些“我殺的人”,他們的生命在我的手中終結,我是否因此而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那些“殺我的人”,他們對我的殺意從何而來?是報復?是嫉妒?還是僅僅是命運的齒輪在無情地轉動? 我喜歡這種帶有哲學意味的標題,它能引導讀者去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比如,當一個人走上瞭“殺”的道路,他是否還能迴頭?當仇恨的種子一旦種下,它又將如何蔓延,最終吞噬一切?這本書,或許就是在探索,在極緻的生存壓力下,人性的底綫究竟在哪裏,以及當道德和理性都無法抵擋欲望和仇恨的時候,會發生怎樣的悲劇。 我期待作者能夠用一種獨特且充滿力量的敘事方式,來講述這個故事。不是那種流水賬式的記錄,也不是那種華麗辭藻的堆砌,而是能夠觸動人心最柔軟的部分,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反思自己的生命,反思我們與這個世界的聯係。 我希望這本書能帶我進入一個充滿挑戰和思考的世界,讓我看到,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泥沼中,是否依然存在著希望的微光,或者,最終的結局,是否隻是對生命殘酷本質的一種直白的展現。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次閱讀,更像是一次對生命意義的探索。
评分《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光是這個書名,就自帶一種濃烈的史詩感和一種難以言喻的宿命感,讓我瞬間就對其産生瞭濃厚的興趣。它不是那種一眼看穿的標題,而是像一塊深邃的謎團,引人不斷去猜測、去探尋。我一直認為,一本好的作品,它的標題本身就應該能夠勾勒齣故事的輪廓,並激起讀者的好奇心,而這本書,無疑做到瞭這一點。 我腦海裏已經開始構建齣故事的可能畫麵,那不是簡單的殺戮場景,而是一種更宏大的敘事,一種關於生命、死亡、以及人與人之間錯綜復雜關係的描繪。那些“我殺的人”,他們的生命是被我終結,但他們的過去,是否也與我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而那些“殺我的人”,他們的齣現,又是因為我曾經的哪些行為?這種相互指嚮的關係,讓我覺得這本書充滿瞭宿命的張力。 我期待作者能夠深入地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因為,任何一種“殺”的行為,都必然伴隨著復雜的情感和深刻的動機。我希望看到,書中的人物,他們的每一個選擇,每一次行動,都應該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羈絆的。我期待,在那些冰冷的殺戮場麵之下,是否隱藏著不為人知的愛恨情仇,是否有著為瞭守護而不得不付齣的代價。 我喜歡這種帶有哲學思辨意味的書名,它能夠引發讀者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這本書,或許就是在探討“因果循環”的必然性,或許是在反思,當一個人深陷復仇的泥沼,他還有可能獲得真正的解脫嗎?“殺”與“被殺”,在某種意義上,是否已經成為瞭一種難以打破的宿命,一種相互纏繞的命運? 我期待作者能夠用一種極其寫實但又不失詩意的筆觸,來構建這個故事。不是那種生硬的敘述,也不是那種矯揉造作的抒情,而是能夠用最簡潔的文字,觸動人心最深處的情感,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反思自己的生命,以及我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希望這本書能帶我進入一個充滿挑戰和思考的世界,讓我看到,即使在最絕望的境地,是否依然存在著希望的微光,或者,最終的結局,是否隻是對生命殘酷本質的一種深刻揭示。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次閱讀,更像是一次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探索。
评分《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這個書名,就像一道深邃的閃電,劃破瞭我想象的天際,帶來一種既震撼又引人入勝的力量。我不是那種追求簡單刺激的讀者,我更看重的是作品背後所承載的深度和它能否觸及人性的某些柔軟甚至黑暗的角落。而這個標題,恰恰就給我一種這樣的感覺:它不是在講一個簡單的故事,而是在揭示一種更宏大、更殘酷、也更令人費解的生命圖景。 我腦海裏已經開始勾勒齣故事的輪廓,那不是血腥的堆砌,而是一種關於你來我往、剪不斷理還亂的因果循環。那些“我殺的人”,他們是否都罪有應得?還是說,在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也曾經是某種意義上的受害者?而那些“殺我的人”,他們的齣現,又是因為我曾經的哪些行為?這種相互的指嚮性,讓我覺得書中人物之間的關係,必然是復雜而沉重的。 我想,作者一定花瞭大量的筆墨去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因為,任何一種“殺”的行為,背後都一定有其動機和驅動力。它可能是齣於正義的憤怒,可能是為瞭生存的絕境,也可能是被仇恨濛蔽瞭雙眼。我尤其好奇,書中那些“我”的角色,他們的內心是否被煎熬?是否在執行“殺”的動作時,內心也曾有過一絲動搖?又或者,他們早已麻木,將殺戮視為一種本能? 我喜歡這種帶有哲學思辨意味的標題,因為它能引發讀者進行更深層次的解讀。這本書,或許是在探討“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局限性,又或許是在反思,當一個人陷入殺戮的漩渦,他還有可能從中解脫嗎?“殺”與“被殺”,在某種程度上,是否已經成為瞭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一種難以打破的宿命? 我猜測,作者的筆觸應該是非常淩厲且精準的,能夠迅速抓住人性的弱點和社會的病態。在這個時代,我們看到瞭太多因為誤解、偏見、貪婪而産生的衝突和傷害。這本書,也許就是對這些現實的一種隱喻,用一種極端的方式,來揭示我們生活中潛藏的危險和無奈。 我期待這本書能夠讓我看到,在冰冷的殺戮背後,是否還隱藏著人性的微光,或者是否能從中找到一種超越恩怨的救贖之路。即使沒有,僅僅是對於這種殘酷現實的深刻洞察,也足以讓我對這本書充滿期待。它不僅僅是一本小說,更像是一種關於生存、關於選擇、關於命運的深刻反思。
评分這本書名《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光是聽起來就讓人心頭一震,很有故事感,也充滿瞭哲學意味。我一開始拿到這書,其實有點猶豫,因為“殺”這個字眼未免太直接,會讓人聯想到血腥暴力,但又因為它的獨特性,好奇心又驅使我翻開瞭第一頁。然後,我發現這絕對不是一本單純的“殺人遊戲”或者“復仇爽文”。它更像是在探討一種更深層的東西,一種關於生命、死亡、恩怨糾葛的宏大敘事。 作者的筆觸非常細膩,雖然我暫時還沒有深入閱讀具體情節,但光從這個書名,我就可以感受到其中蘊含的張力。它似乎在描繪一種循環,一種你來我往、剪不斷理還亂的宿命。我殺的人,他們是否曾經傷害過我?而那些殺我的人,他們的動機又是什麼?這些疑問就像種子一樣在我腦海裏種下,讓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答案。 我猜想,這本書可能不僅僅是關於物理上的“殺戮”,更可能是關於精神上的“抹殺”和“被抹殺”。也許有的人物殺死瞭彆人的希望,殺死瞭彆人的夢想,而另一些人則因為被壓迫、被剝奪而奮起反抗。這種“殺”的概念可以有很多種解讀,可以是生存的必須,也可以是絕望的反擊,甚至是一種命運的安排。 我特彆期待作者如何構建這個世界的規則。在這個世界裏,“殺”的界限在哪裏?道德的底綫又在哪裏?是否存在著絕對的正義和邪惡?還是說,一切都隻是為瞭生存而進行的殘酷博弈? 我覺得,一本好的作品,往往能在讀者心中留下一個巨大的問號,讓你在閤上書本後,依然久久思考。 我喜歡這種帶有普世性的主題,因為“殺”與“被殺”是人類存在中最原始、最根本的衝突之一。無論是在曆史的長河中,還是在個人的情感糾葛裏,這種張力都普遍存在。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深入挖掘人性中的黑暗麵,但也可能在絕望中尋找一絲光明,或者揭示齣隱藏在殺戮背後的無奈和悲涼。 總的來說,我對《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抱有非常高的期待。它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更像是一種對生命本質的叩問。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用文字將這復雜的情感和深刻的哲理編織在一起,構建齣一個令人迴味無窮的文學世界。我相信,這本書一定能帶給我一場前所未有的閱讀體驗,讓我重新審視生命中的種種選擇和因果。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