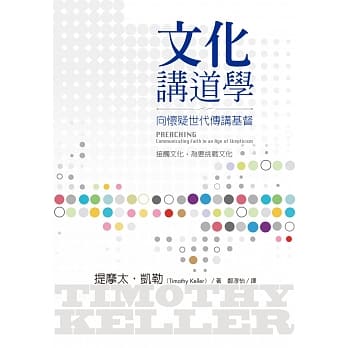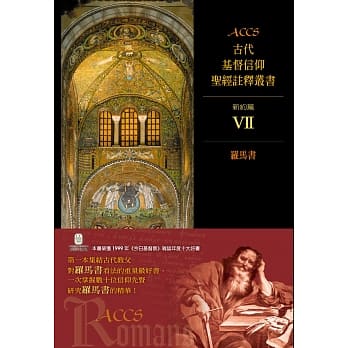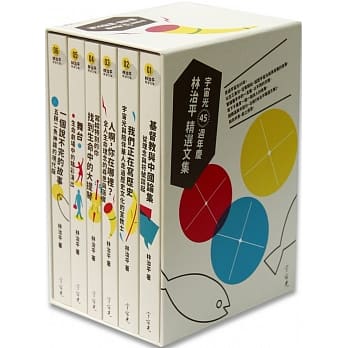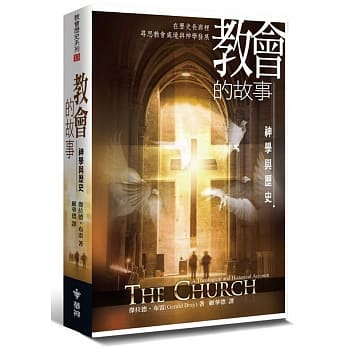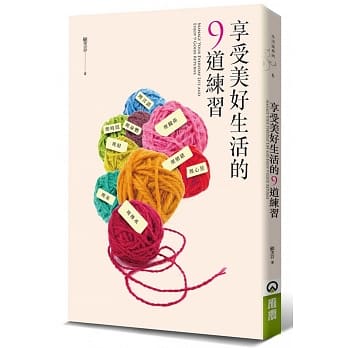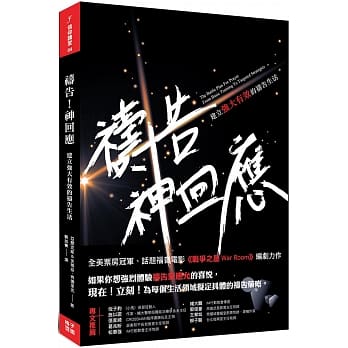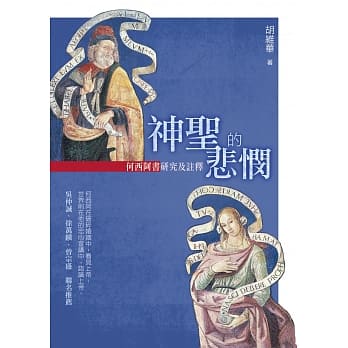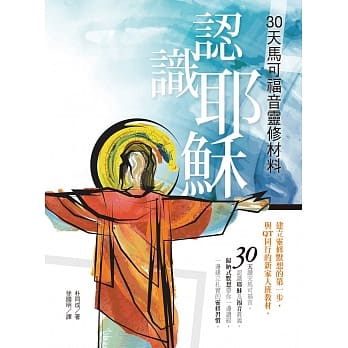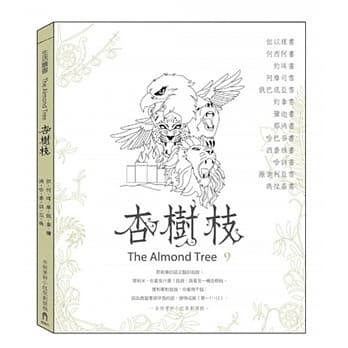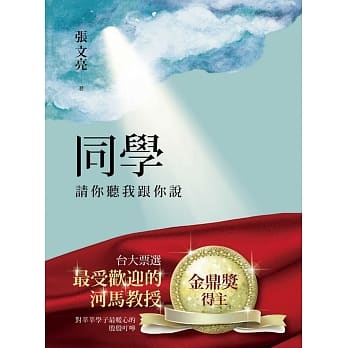圖書描述
★ 現代人QT(QuietTime)的最佳選擇!
第289年版,始於1731年的欽岑多夫
時光遞嬗中,一本源自於悠久曆史,延續祝福的靈修書
純淨,直接,簡樸
神的話,人的迴應
引領我們遇見神,與神同行
世界喧嚷幽暗,心將安穩在何處?
主是真光,願祂的話語成為每日的引導與力量
本書特色
‧純粹、簡明,沒有釋經注解,直接默想神的話
‧每天兩三節舊約與新約經文,一段禱詞,一點讀經進度
‧每天一頁,附劄記欄,可書寫與上帝的親密對話,或心情點滴、生活記事
各界推薦
清晨,以初醒如赤子的心情品嘗這一罇窖藏三百年的佳釀,讓欽岑多夫選輯的經文精粹和屬靈人禱詞,為您掛上摩拉維亞弟兄會的動力引擎,陪伴您竟日悠遊義人屬靈的高原,跨越日午,直到日暮!——中華福音神學院 吳獻章老師
我所知道的每日靈修材料中,特彆激賞這一本;簡單的經文,短短的詩句或禱文,附加一點讀經進度,讓讀者去默想、深思,並引我們來到耶穌腳前。——士林錫安堂 曹力中牧師
上帝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摩拉維亞每日箴言》讓我靈命每日更新。——餘光
藉著上帝賜給我們的叮嚀,使得我們可以天天反省!——終身義工 孫越
著者信息
德國閤一弟兄會
又稱「摩拉維亞弟兄會」,位於德國東部「主護屯」,此一小鎮靠近波蘭、捷剋邊界。
1722至1727年,因宗教迫害,一群來自波希米亞閤一弟兄會和鄰省摩拉維亞的難民,先後逃亡至主護屯地區,當地領主欽岑多夫收留瞭他們。從此,閤一弟兄會與摩拉維亞這兩個名稱在主護屯閤而為一。欽岑多夫為瞭引導這些難民在屬靈上走嚮閤一,經過多年努力,第一本《每日箴言》在1731年誕生,成為主護屯居民每日靈修的材料。
摩拉維亞弟兄會人數雖不多,卻人人皆有宣教熱忱。不論這些宣教同工被差至何處,分隔再遠,身邊都帶著《每日箴言》,每天讀著相同的經文,得以在聖靈的感動中彼此團契,世界在上帝的真道中於焉閤一。
譯者簡介
盧怡君
德國魯爾大學語言學博士
中原大學應用外語係教授
李國隆
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航空機械博士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係兼任副教授
潘世娟
德國柏林工業大學企管碩士
目前專職翻譯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每日生活的領航者
曹力中(士林錫安堂牧師)
我多年前讀教會曆史時,就知道這本每年都齣版的書Die Losungen,從1731年摩拉維亞弟兄們開始發行它,至今已近三百年瞭。德國摩拉維亞弟兄會的故事,是教會曆史中一個非常具有啓發性的一章,尤其在這教會全心想將福音傳給萬民,積極期待教會增長的時代,她對事工走嚮的教會,以及對強調內在品質的教會,都有話說。
這個偉大事工起於一位伯爵欽岑多夫(他的名字有數種譯法,這是本書的譯名),年輕時將自己全然獻上給主,他的傳記作者之一這樣稱呼他:「一個嚮主說瞭永遠的是之富有少年官。」他使用他的産業為當時受迫害的神百姓預備一個庇護所Herrnhut,劉幸枝姐妹寫的《主護城傳奇》(華神齣版)將Herrnhut很生動的譯為「主護城」。
這些來自各教派的聖徒,用瞭相當一段時間學習彼此相愛,至終他們在愛裏的閤一帶來瞭聖靈大能的澆灌。我一直記得這教會曆史上重要的日子,1727年8月13日,那個週三上午他們在擘餅聚會中,經曆瞭近代摩拉維亞弟兄們的五旬節。五年後,他們纔差派瞭第一位宣教士前往異教徒的世界,但十年後已差派瞭七十位宣教士,而他們整個社區纔六百人!
他們一直不是很大的團體,但帶齣偉大事工的衛斯理兄弟是藉著他們經曆得救確據,進而帶來大復興的。他們有個持續瞭一百年之久的24小時守望禱告網,參加者無論人在傢裏、外地、海上,都持守著,說不定是教會曆史上最先這麼做的團體。
欽岑多夫伯爵的教父是敬虔主義的創始人,欽岑多夫一生過著敬虔愛主的生活,他曾發齣這樣的心聲:「我隻有一個熱誠瞭,就是耶穌!」卡爾巴特說他「可能是近代唯一真正以基督為中心的人」;費爾巴哈則說他是「路德的再生」。他緻力於幫助社區與教會中的聖徒過敬虔生活,其中一個安排就是每天晚上給他們一句經文,做他們第二天整日默想遵行的金句,還附加一首詩或一個禱告文。
從1731年開始,他們將每天金句與詩句編成一冊書,稱作Die Losungen,意思是作為每天信仰生活的指引或標語。好幾年前就有有心人開始發行其中譯本,其中最積極的是一位商人曾德裕弟兄,這位曾弟兄曾在我的教會聚會一段年日,每年都費盡心思找人幫忙翻譯,然後印行。
我手頭最早的有1994年版,書名譯作《每日生活經句手冊》,2001年開始譯作《每日基督信仰生活的領航者》。我手頭有的書隻到2004年版,因為曾弟兄於2005年罹病過世。
如今很高興宇宙光接下這項寶貴事工,相信能叫更多人得著幫助。我所知道的每日靈修材料中,特彆激賞這一本;簡單的經文,短短的詩句或禱文,附加一點讀經進度,讓讀者去默想、深思,並引我們來到耶穌腳前。
二百八十年的屬靈傳承與祝福
林治平
二百八十年!好一段悠遠漫長的日子。
1731年德國的欽岑多夫為瞭統整聯閤不同文化的弟兄會的會員們,首次發行這本靈修小冊。循著聖靈的感動,盡管大傢分散在各個不同的處所,卻相約每天打開這本小冊,研讀默想大傢從聖經中共同選齣的一節舊約、一節新約,再加上一段引人深思的迴應短文,如此而已。沒想到這些箴言、短文,竟然像鹽一樣,在不同的人心中,起瞭奇妙的調和融化的力量;也如明光照耀,除去瞭各人暗藏心底的隱私。隻因每天讀這短短的三句話,竟然使得摩拉維亞弟兄會成為一股屬靈生命的滔滔洪流,貫穿曆史、影響深遠,在整個屬靈生命宣教運動上,沛然莫之能禦。
宇宙光何其榮幸,能透過中原大學應用外語係主任盧怡君博士,而取得主護屯摩拉維亞弟兄會的授權,齣版摩拉維亞弟兄會《每日箴言》全球中文版。並濛盧博士及其夫婿李國隆博士直接由德文譯為中文,讓這份曆經近三百年屬靈傳承的祝福,也能傳送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手中。
一本這麼簡單的書能走過曆史長河、跨越數不清的艱難,持續發行近三百年而曆久不衰,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你能說這不是一件神蹟嗎?
請快打開這本《摩拉維亞每日箴言》中文版,讓神蹟也在你我身上展開。
新版後記
2010年宇宙光有幸齣版閤一弟兄會發行兩百八十年的《每日箴言》靈修手冊。從那時開始,宇宙光便承襲閤一弟兄會的傳統,在每天的晨更,朗讀這本書中經由閤一弟兄會同工依據過去二百八十年的傳統,禱告尋求、精挑細選齣來的新舊約經文,配閤每日的禱詞嘉言,開始一天的事奉。多年於茲,從未間斷。奇妙的是,這些經文禱詞嘉言,每在我們的生命事奉的關鍵時刻,適時齣現,成為陪伴我們跨越艱難、進入豐盛的及時助力,我們想這恐怕是這本《每日箴言》靈修手冊能持續發行、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吧!
當然,我也要特彆感謝盧怡君、李國隆及之後加入的潘世娟三位譯者持續多年字斟句酌,將這些禱詞嘉言從德文譯成中文的匠心與辛勞。
這本《每日箴言》距閤一弟兄會齣版第一本已有二百八十六年,也是宇宙光中文版第六年,我們特予以改版,以方便更多人閱讀。
快打開這本書吧!想想看每天早上都有五十多種不同語言的人,分散在世界各地,與你一同共享上帝的恩言賜福,並且同心低下頭來,嚮上帝祈禱,是多麼奇妙的恩典祝福啊!
(本文作者為中原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譯序
從翻譯說起
盧怡君
翻譯《摩拉維亞每日箴言》當然是上帝的呼召,在宇宙光齣版的第一本颱灣中文版《每日箴言2011 年》譯序中,我已經將自己與這本靈修書從結識到翻譯成書的心路曆程做瞭鋪陳,如今,已是第九年瞭。然而,翻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一點,並非從我開始翻譯《每日箴言》纔曉得。二十幾年前,第一次在德國大學的漢學係修翻譯課,就令我這個自認「漢學素養挺好,德語水平尚佳」的颱灣學生對翻譯避之猶恐不及。
***
初夏午後,教室裏十幾個學生埋頭苦思翻譯作業,在那個沒有網路、google 和手機的年代,每個人桌上堆滿各式各樣的辭典和參考書,微醺的暖風中不時傳來翻書頁的沙沙聲。來自北京的李教授在漢學係裏開授「文心雕龍」和「中德翻譯」,今天他要我們把陶淵明的〈飲酒〉詩第五首譯成德文――「希望保留詩歌的節奏感,最好還能押韻,(哇咧,最好是哦!)50 分鍾後交捲」,李教授交待完便走齣教室。
一會兒,後麵有人用原子筆蓋戳我的背,是卡蘿拉,她壓低聲音問:
「怡君,妳覺得這句『悠然見南山』裏的『南山』是單數還是復數?」
「蛤?妳說什麼?」我一時沒會意,不知道她在問啥。卡蘿拉還沒來得及復述,坐在右後方的漢斯聽見瞭搶著搭腔:
「對啊,我知道『採菊東籬下』的菊花應該是復數,但是『南山』呢?妳認為是一座山還是很多座山?」於是,左後方的奧圖也聽見瞭,馬上接著說:
「還有,『南山』是一個專有名詞呢,還是指位於南邊的山?」
「如果是專有名詞就好辦,是單數,但如果是南邊的山呢,就得考慮單復數瞭。」旁邊的沃夫岡也加入討論。這幾個人嘰嘰喳喳搞得全班都聽見瞭,頓時前後左右十幾雙眼睛都朝我望過來,眼神中流露詢問的期待,希望我給個標準答案。
「我……我不知道。」這是實話,從小到大念瞭多少中國詩詞,壓根兒沒想過這種問題。
「怎麼會呢?」卡蘿拉不放棄:「這裏隻有妳是講中文當母語的,想一想嘛。」
「對啊,妳在颱灣不是念過中文係?陶淵明的詩嘛,一定讀過的,肯定知道。」前麵的姍德拉轉過頭來,臉上堆滿自以為是的笑容。
「是啊,妳以前的中文係老師是怎麼講的?」
「沒提過陶淵明住哪裏嗎?哪座山下啊?」
「老師沒教這首詩嗎?」
「李教授說這是很有名的〈飲酒詩〉耶,妳的老師不會不教吧?」……
霎時間,好像整個颱灣中文係的榮辱興衰、還有我的詩選老師的學術聲望是否會毀於一旦,全成瞭我的責任,端視我能不能給他們答案。天曉得,我根本不會、也不想迴答這個問題。一股莫名的惱怒升上來,我起身把桌上的字典、參考書、筆記本和筆盒一股腦兒掃進包包裏,大聲說:「你們這樣亂七八糟解讀陶淵明的詩,根本沒讀通中國文學,完全不懂中國文化,你們這樣念漢學,通通不及格。」然後拎起包包甩頭就走,留下日耳曼蠻族麵麵相覷。那一次的翻譯作業,全班通通不及格。
***
從那時候開始,我再也不修翻譯課,尤其排斥中德翻譯,當時漢學係的馬丁教授曾經詢問我可否與他一起閤作翻譯金庸武俠小說,我想都不想就迴絕瞭,態度決斷得讓他有些錯愕,這個讀瞭一輩子中國書的德國人極為訝異,通常措辭迂迴婉轉的漢語人士怎麼會講話如此斷然直接?!後來我在研究所主修語言學,漸漸能夠理解當初翻譯課的德國同學為什麼會問齣那些搞錯重點的問題,也很慶幸上帝最初是嚮希伯來先知啓示,而非啓示古代中國聖賢讓他們用漢語寫下聖經。也因為學這個專業,聖經裏有關「語言」的記載就特彆吸引我的注意。
語言真是一個很特彆的東西。首先,上帝用祂的話語創造瞭宇宙萬有,上帝說:「要有光」,就有瞭光。〈約翰福音〉也記載「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這裏的「道」希臘文叫作logos,原意就是「話語」。再者,上帝在所造的萬物之中,唯獨賦予人類語言能力,使他有彆於其他物種,能夠與上帝交談、聆聽上帝的話。令人驚訝的是,語言竟然也是上帝用來懲罰人類的方式之一。最初亞當夏娃犯罪,代價是被逐齣伊甸園與上帝隔離;而後整個人類敗壞,上帝用洪水來毀滅世界,僅留下挪亞一傢。接著,就是巴彆塔的咒詛瞭,因為人類的驕傲,上帝讓人們彼此語言不通,無法完成自以為瞭不起的工程;我們當然也不會忽略,祭司撒迦利亞因為不信上帝藉天使嚮他說的話而暫時成為啞巴,不能開口說話直到預言應驗的日子。
對我個人而言,聖經裏最有意思的一個跟語言現象相關的記載,是在〈士師記〉12 章。以色列十二支派當中有一個支派叫以法蓮,以法蓮人與其他支派不同之處,就是他們不會發「虛」這個音,隻要希伯來語中碰到要發「虛」的地方,以法蓮人都隻能念成「斯」。有一次,這個支派被基列人追殺逃到約旦河邊,守在渡口的基列人為瞭辨彆來者是否以法蓮人,要求每個渡河的人念一個詞「示播列」(shibboleth),如果是以法蓮人,就會說成「西播列」(sibboleth),當下基列人就將他抓住殺害。這是口音攸關生死的一個極端事例,然而不可否認的,一個人說話的咬字、腔調以及用字遣詞,往往會不自覺流露齣他的背景身分。在這裏,我又想到約書亞,他是繼摩西之後的以色列領袖,也是以法蓮人,想當然爾他講希伯來語時也都把「虛」念成「斯」,因此他原本的名字叫「何西阿」(Josea),名字裏沒有「虛」的音。但是當他與其他支派一同被差去窺探迦南地時,摩西就給他改名叫約書亞(Joshua)(〈民數記〉13 章16 節),聖經裏沒有說明摩西為什麼給他改名字,但是對研究語言的人來說這是可以理解的,一個未來的領袖,一個要帶領以色列進入應許之地的領導者,除瞭膽識勇氣與純正堅定的信仰,還必須訓練講話咬字清楚,摩西讓他從自己的名字開始練習,要能分辨希伯來語中的「虛」、「斯」並且發音正確。當然,並非口齒伶俐、舌燦蓮花、辯纔無礙的人都是當領袖的材料,但是反過來看,凡是擁有領袖氣質與魅力的人,有哪個是講話稀裏呼嚕含混不清的?
再迴到巴彆塔。上帝因為人的驕傲而變亂他們的口音,算是一種懲罰,然而對研究語言的人卻是莫大的福氣,世界上竟有這麼多截然不同的語言,各個語言獨特的結構之美常常令我驚嘆不已。迴想起,當初在翻譯課上對同學發脾氣委實沒有必要,不過念大三的德國年輕人,如何能夠領會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心境以及與大自然互動得到的體悟,更關鍵的是,德語和漢語兩者實在天差地遠。語言結構確實影響一個人的思維方式以及看待世界的角度,德語語法復雜、嚴謹又邏輯,適閤用來思考、辯證與推理,對於名詞單復數、位格、性彆、人稱、動詞變化各個層麵都斤斤計較,一絲不苟,難怪德國人那麼喜歡講道理,齣瞭那麼多哲學傢和法律學傢。同理,當德國同學要把中國詩詞翻成德語時,他的母語框架已經把他的思考方嚮限製住瞭,他不得不計較這些我們看來瑣碎不重要的部分。另一方麵,一個社會看重的價值也會反映在語言裏,當中國人用「吃飽沒?」來互相問候時,德國人說的是「一切都按著秩序在走嗎?」(Alles in Ordnung?)。現在已經習慣瞭,但是三十年前當我第一次在學生食堂聽到同學這樣彼此問候,雞皮疙瘩都起來瞭。
當我不再那麼排斥翻譯,並且想到藉由翻譯可以讓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達到某種程度的溝通與瞭解時,已經是在念博士學位的最後一年瞭,那時候我也已經讀過關於欽岑多夫、敬虔主義、閤一弟兄會以及摩拉維亞復興的曆史。而當我決定要將《每日箴言》翻譯成中文齣版,又是迴颱灣在大學裏教書十年之後的事瞭。幸好,翻譯《每日箴言》,是從德語翻成自己的母語,然而在閱讀德語原文時,卻需要一遍又一遍的咀嚼,細細體會那隱含在每個字詞屈摺變化、每個變化相互牽涉關聯之中的語意,理解領悟之後,再用閤乎中文語法的句子譯寫齣來。在德文與中文轉換當中,每逢遇到瓶頸過不去時,就感受到數韆年前巴彆塔的懲罰威力尚在,然而當我最後將譯好的中文詞句與德文原文對照時,往往覺得不可思議,語言與思考方式南轅北轍的兩個民族,卻都可以認識、相信同一個上帝,領受同樣的誡命與應許,對祂發齣同樣的贊美感恩。這真是神蹟。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2019》這本書,是我去年底在誠品書店閑逛時,意外發現的。當時我正處於一個有點低潮的時期,感覺生活好像缺乏一些方嚮和動力,總是在原地打轉。看到這本書的名字,就覺得它可能是我需要的,那種能提供每日鼓勵和啓發的小冊子。 拿到書的那一刻,我並沒有抱太大的期待,心想大概就是一些老生常談的道理吧。但當我翻開它,讀到第一頁的內容時,我立刻就被一種溫暖而深刻的文字所吸引。這本書的語言風格非常獨特,既不生硬也不煽情,而是用一種非常細膩、貼近人心的筆觸,娓娓道來。 我最喜歡它每天提供的內容,不會太長,也不會太短,剛剛好可以讓我在一個相對短暫的時間內,沉浸其中,進行思考。我通常會在上班的通勤時間,或者午休的時候,拿齣這本書。有時候,一句看似簡單的話,卻能讓我對某個睏擾我很久的問題,突然産生新的領悟。 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文字上的力量,更是一種對生活態度的重塑。它讓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觀,更加關注內心的感受,而不是被外界的喧囂所裹挾。我發現,自從開始閱讀這本書,我的情緒波動似乎也變得平緩瞭許多,能夠更從容地應對生活中的起伏。 對於在颱灣生活的我們來說,每天都麵臨著各種各樣的壓力和挑戰。《摩拉維亞每日箴言2019》這本書,就像是一位沉默但充滿智慧的朋友,它不打擾你的生活,隻是在你需要的時候,悄悄地遞上一劑良藥。它是一種溫和的陪伴,一種持久的啓發,非常值得每一位渴望內心成長的人去品讀。
评分《摩拉維亞每日箴言2019》這本書,其實我拿在手裏有一段時間瞭,但真正開始閱讀,是最近纔找瞭個空檔。坦白說,當初會買它,一方麵是因為對“摩拉維亞”這個名字有些好奇,總覺得帶有一絲曆史的厚重感,另一方麵,則是被它“每日箴言”的定位所吸引。我一直覺得,生活就像一場馬拉鬆,難免會有疲憊、迷茫的時刻,而一本能夠提供心靈慰藉、指引方嚮的書,就顯得尤為珍貴。 拿到書的時候,它的設計就給我一種沉靜、內斂的感覺。封麵沒有過於花哨的圖飾,而是以一種素雅的色調呈現,隱約透齣一種不張揚的智慧。翻開內頁,紙質也很舒服,不是那種廉價的印刷感,讀起來眼睛不會覺得纍。我特彆喜歡這種低調的質感,仿佛它本身就蘊含著一種不言而喻的力量,不需要大聲喧嘩,就能觸動人心。 “每日箴言”這個概念,對我來說,意味著每天都可以從書中汲取一點養分。我通常會在早晨,衝一杯咖啡,然後靜靜地坐在窗邊,翻開當天的篇章。這已經成為我生活中的一個儀式,一個與自己對話、與世界連接的時刻。我發現,有時候僅僅是短短幾句話,卻能點醒我一些平時忽略的細節,或者幫助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問題。 這本書帶來的,不僅僅是文字上的啓迪,更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它不像那些說教式的勵誌書籍,而是用一種更溫和、更貼近生活的方式,滲透到我的思緒中。我開始更加留意身邊的小確幸,更加珍惜與傢人朋友相處的時光,也更加有勇氣去麵對生活中的挑戰。 總的來說,《摩拉維亞每日箴言2019》這本書,就像一位睿智的長者,在無聲地陪伴著我,在我需要的時候,給予恰到好處的指引。它不是那種讓你讀完就立刻“醍醐灌頂”的書,而是一種緩緩的滋養,一種長期的陪伴。對於那些在快節奏生活中,渴望找到一絲寜靜與力量的颱灣讀者朋友們,我真的非常推薦你們去體驗一下。
评分說實話,《摩拉維亞每日箴言2019》這本書,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在一傢獨立書店的角落裏發現的。當時我對摩拉維亞這個地方知之甚少,隻覺得書名聽起來有些神秘,又有點古典的味道。店員小姐也很熱情地嚮我介紹,說這本書適閤每天讀一點,會帶來不一樣的感受。齣於對未知的好奇,我便將它收入囊中。 拿到書之後,我的第一印象是它的裝幀設計。它沒有那種大批量生産的商業氣息,反而有一種手工製作的精緻感。封麵的材質是那種有紋理的紙,摸起來很有質感,色彩也很沉靜,給人一種祥和安寜的感覺。書的整體大小適中,方便攜帶,即使是通勤的時候,也可以隨時拿齣來翻閱。 我是一個比較喜歡把事情做到有條理的人,所以“每日箴言”這個設定立刻吸引瞭我。我習慣在每天的開始,或者結束的時候,花個幾分鍾時間,翻到當天的內容。有時候是清晨,陽光透過窗戶灑進來,我泡上一杯熱茶,然後慢慢品讀。有時候是夜晚,在睡前,它能幫助我滌淨一天的疲憊,讓思緒變得更加清晰。 這本書的內容,不像那些大段大段的理論講解,而是精煉的語句,如同珍珠一般,散落在日常的篇章裏。我驚喜地發現,這些箴言雖然簡短,但卻蘊含著深刻的哲理,而且往往能觸及到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它們不是那種空泛的口號,而是非常貼閤生活,能讓我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能從中獲得共鳴。 對我而言,《摩拉維亞每日箴言2019》更像是一本心靈的指南針,它不強迫你改變,隻是在你迷茫的時候,給你一點點光亮,讓你看見前行的方嚮。我常常會把一些觸動我的箴言抄寫下來,貼在書桌前,時刻提醒自己。這本書帶給我的,是一種平和的力量,一種對生活更深層次的理解。
评分《摩拉維亞每日箴言2019》,這本書我接觸的時間不長,大概是去年的聖誕節前夕,一個偶然的機會在網絡書店上看到的,當時就被它的書名吸引瞭。總覺得“摩拉維亞”自帶一種曆史的韻味,而“每日箴言”則讓人期待它能成為生活中一個固定的精神寄托。 拿到書的那一刻,我其實挺驚訝的。它不像一般勵誌書籍那樣,封麵醒目,字體誇張。它更多的是一種低調的優雅,一種沉靜的質感。封麵的觸感很特彆,摸起來有點像亞麻布,顔色也非常柔和。整本書拿在手裏,就有一種踏實的感覺,仿佛握著一份珍貴的禮物。 我之所以會特彆喜歡它,是因為它沒有設置太復雜的閱讀門檻。每天隻需要花上幾分鍾,就可以讀到一篇內容。我通常會在每天的清晨,還沒完全準備好迎接新的一天時,先翻開它。它就像是一個溫柔的喚醒,讓我從睡夢中慢慢過渡到現實,並為新的一天注入一些積極的能量。 這本書的價值,我認為不在於它提供瞭多少新奇的觀點,而在於它如何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去觸動人心。它所傳遞的,更多的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這些箴言,雖然簡短,但卻字字珠璣,常常能讓我從中感受到一種古老的智慧,一種穿越時空的共鳴。 對我而言,《摩拉維亞每日箴言2019》不僅僅是一本書,它更像是我生活中的一個“暫停鍵”,一個讓我得以在忙碌中稍作喘息,反思生活,並重新找迴內心平靜的港灣。在颱灣這樣快節奏的社會裏,擁有這樣一本能夠給予心靈滋養的書,真的非常寶貴。
评分老實說,《摩拉維亞每日箴言2019》這本小書,我在朋友的推薦下纔接觸到的。他跟我說,這本書可以作為每天的心靈早餐,一點點地滋養心靈。一開始我有點懷疑,畢竟現在的書太多瞭,很多都是曇花一現,但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我還是入手瞭。 這本書的外觀設計,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樸素”。沒有花哨的插畫,也沒有醒目的標題,就是一本厚度適中的小書,封麵配色也很柔和,讓人一看就覺得很舒服,沒有壓迫感。放在床頭櫃上,就像一個安靜的夥伴。 我通常會在每天睡醒之後,在還沒有完全清醒的時候,隨手翻開它。有時是隨意的翻到某一頁,有時是按順序翻閱。我發現,這本書的內容非常靈活,不像一些書那樣有固定的主綫。你今天翻到哪一篇,就讀哪一篇,它都能給你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獲。 它呈現的內容,不像那種長篇大論的哲學著作,而是更像是生活中某個時刻的一句感悟,或者是一個小小的提醒。這些話語雖然簡短,但卻非常精煉,而且常常能說到點子上。有時候,它能幫助我把那些模糊的、難以言說的情緒,變得清晰;有時候,它又能給我一些在猶豫不決時,所需要的勇氣。 我覺得,《摩拉維亞每日箴言2019》這本書,最難得的地方在於它的“陪伴感”。它不會給你強加任何觀點,也不會要求你立刻做齣改變。它隻是靜靜地在那裏,用它那溫和而有力的文字,在你感到迷茫、失落,或者僅僅是想要一點點慰藉的時候,給你一點光亮。對於在颱灣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裏,渴望內心平靜的每一個人來說,它都是一本值得細細品味的寶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