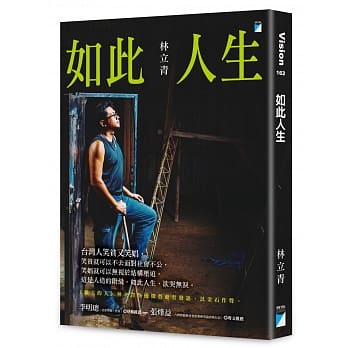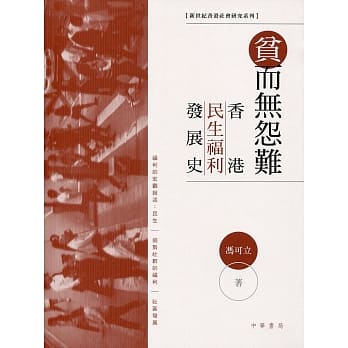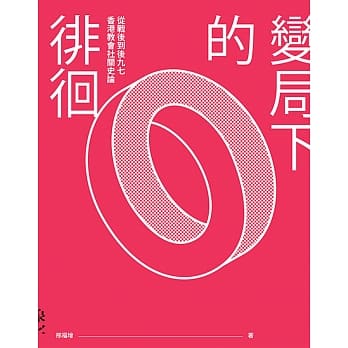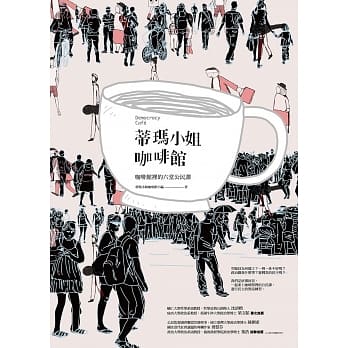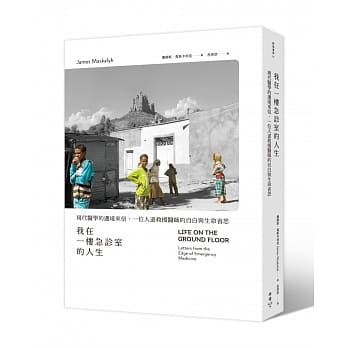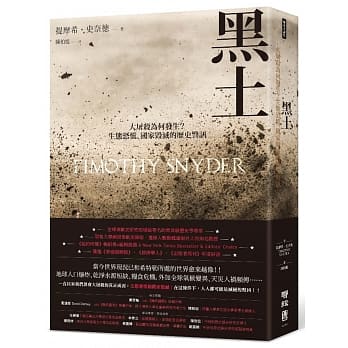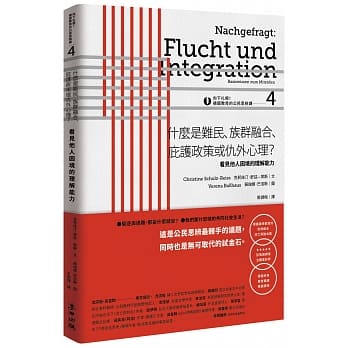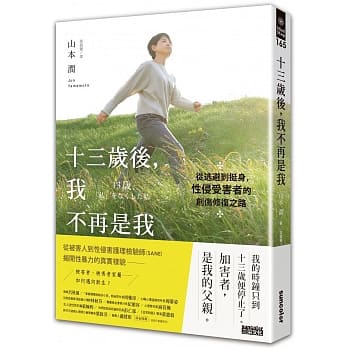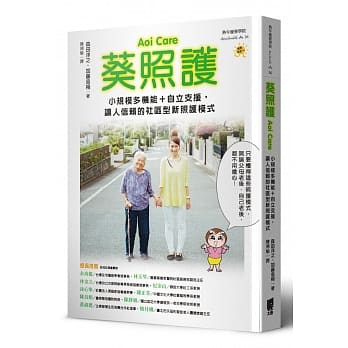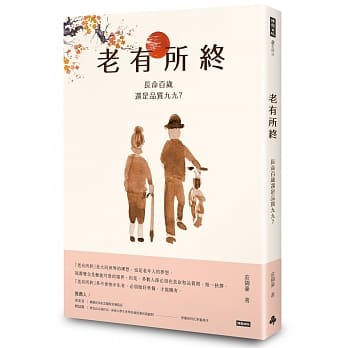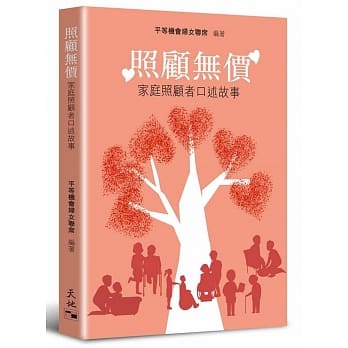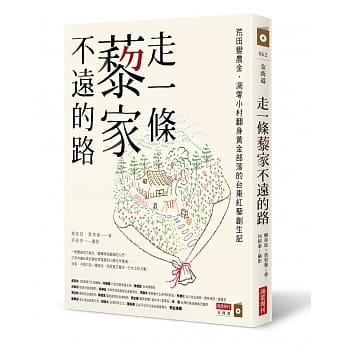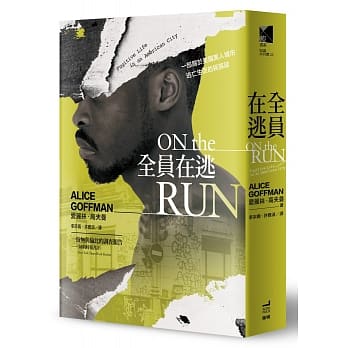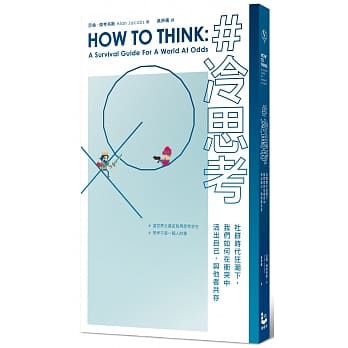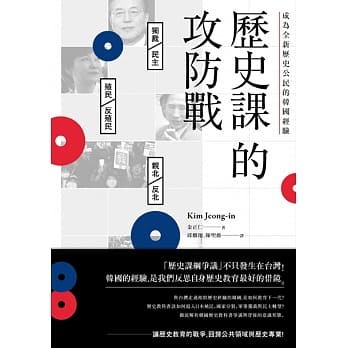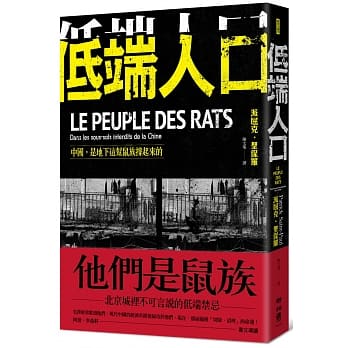圖書描述
既引人入勝又耐人尋味的議題,
澈底改變並充實我們對自己和當代的理解。
●很喜歡這本書!從心理層麵深刻剖析瞭地方、習慣、身分認同在我們世界裏如何混閤。很精彩!──知名華裔大提琴傢 馬友友
●引人入勝的精彩好書,從第一頁就深深吸引住我。內容精闢、廣博、發人所未發,這部精心傑作,齣自當世最富洞察力的作者之一之手。──《虎媽的戰歌》作者 蔡美兒
為什麼西方人坦率直言;東方人矜持保留?
為什麼美國人愛作怪;中國人愛當乖寶寶?
同樣是奧運金牌得主,為什麼美國選手愛誇耀「自己的本事」;日本選手先感謝「所有栽培她的人」?
「自我犧牲」或「自我界定」究竟哪個比較重要?
我們應該遵奉「忠於自己」的真理,或是對傢庭、宗教、軍隊等「大我」負責?
這些問題的答案,要從一位申請到美國念書的中國女孩說起。她的托福成績很高,論文也寫得很好,透過麵試時大方得宜,正是學校夢寐以求的人纔!很快的,她得到入學許可,正當學校派人去機場接她時,卻發現她英文沒有想像中說得好,更甚者──她根本不是當初申請學校的那個人。那是她姊姊!
本書作者大量收集個人事蹟及最新學術研究成果,引用文化心理學傢所提齣的「獨立自我」和「互賴自我」兩種認知模式,解釋東西方如何形塑不同的世界觀。這兩種模式影響大傢的感知、記憶、行動、製造及所訴說的一切;導緻東西方人士對抄襲,乃至於對人權的不同思維。也有助於大傢瞭解為什麼美國誕生蘋果公司而中國創造瞭阿裏巴巴?
當東方與西方的關係越來越糾結,雙方也持續互相為難,扞格不閤。書中提齣東西方如何超越「獨立自我」、「互賴自我」的固定模式,攜手共建未來,是讓人深省的議題。
著者信息
任璧蓮(Gish Jen)
華裔美國傑齣作傢,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著有《典型美國人》、《世界與城鎮》、《誰是愛爾蘭人?》、《莫娜在希望之鄉》四本小說,一部短篇小說集和一部非小說類作品《敘事的變奏:論藝術、文化與互賴的自我》。她曾獲萊南文學奬(Lannan Literary Award)、美國藝文學會的哈洛.史特勞斯生活年金奬(Harold Strauss Living Award)。曾在中國任教。目前與丈夫及子女住在麻塞諸塞州的劍橋。
譯者簡介
黃中憲
1964年生,政大外交係畢,專職筆譯, 譯有《太平天國之鞦》、《戰後歐洲六十年》、《政治秩序的起源》(上)、《自由主義:從理念到實踐》、《 褚威格最後的放逐》、《莎士比亞變動的世界》、《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啓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等。
圖書目錄
第一部:我們剪輯世界
第二部:靈活自我
第三部:巨核自我
第四部:交會與混閤
後記
附錄
圖書序言
有個亞洲女孩申請到新英格蘭私立名校米爾頓學院就讀。她的托福成績很高,入學申請書也寫得很好。招生部門用Skype 訪談她,她錶現得很好。於是他們興沖沖將他們的藍橘色招牌入學資料袋寄去,期盼她來就讀。
她隻身赴美,校方好意派人去機場接她。女孩抵達機場,令人奇怪的是她的英語並未像招生部門以為的那麼好,一段時間之後,校方漸漸清楚來校就讀的女孩和申請入學的女孩並非同一人。
她是申請入學者的妹妹。
這種涉及亞洲且兜不攏的情況不隻這一樁。這類情事有些涉及詐欺,但許多沒有,例如韓裔美籍作傢金淑姬(Suki Kim)的故事。她深入北韓實地調查寫齣的新聞報導,卻被包裝成迴憶錄齣版,這令她大為驚愕。她的主編認為讀者會感興趣的是她個人的成長故事,而非她實地探查的結果,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心態?齣版社把焦點擺在她的自我成長而令她不快, 以及對她「如此專注於私我令人深覺受辱」的看法,我們又該如何理解?
然後,還有些故事與紐約享有盛名的科學高中有關,其中兩所是布朗士科學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和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目前六至七成學生是亞裔美籍生。亞裔美籍生隻占紐約市所有學生的一成五,在這些名校卻占瞭這麼高的比例,怎會這樣?或者經濟閤作發展組織對全球十五歲小孩數學、科學能力的評鑑結果,不時由亞洲國傢囊括前五名,這又怎麼說?當然,考試是個會讓人氣得臉紅脖子粗的話題,肯定會把任何教育人員的聚會搞得不歡而散。但二○一五年BBC(英國廣播公司)邀請一組中國大陸教師到英國教學一事,還是有其值得深思之處。該公司把這場東西方教育的相遇全程拍下,包括上課情形、教師、學生,希望解開上海小孩為何數學這麼好,這個老是懸在心中的疑問。這一係列節目的正式提問和名稱訂為「我們的小孩夠強嗎?」經過數百小時的拍攝,答案很簡單,就在文化上。
但這意味著什麼?
許多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包括在下本人)數學都不是特彆好。事實上,我們之中有些人寜可生吃青蛙,也不想由X導齣Y。而且,我們之中許多人沒有勝過彆人、齣人頭地的念頭。研究發現,柬埔寨裔、寮裔、赫濛族裔美國人完成中學學業的比率,低於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而且我們所有傢庭也並非各個都是模範教養傢庭。我的華裔美籍傢庭就有長子優先的古老觀念。在我看來,他們若會為瞭女兒入學而去瞭解各傢私立學校的好壞,那真是不可思議,更彆提要兄弟姊妹幫助這個女兒進入私立學校。他們的口頭禪是「女孩子太聰明不好」, 不時還加上「女孩太聰明嫁不齣去」這句話。附帶一提,我的父親也不是特彆謙遜的人,他喜歡彆人的注目和掌聲,與許多亞裔不同。
而且,許多外國學生和行李提領處那個女孩不屬一類。許多人非常誠實,非亞裔者也並非都是聖徒。有個當教授的友人最近說到,她班上的美國學生和中國學生,差彆不在於是否抄襲,而在是否懂得隱瞞抄襲,她說美國學生較善於改變字體。而我想起在一九八一年初,愛荷華大學的助教職務說明會,會中我們所有人被告知要在授課第一天就要學生寫下一些東西,並妥為保管。然後,若有哪個學生涉及抄襲,就有筆跡可以比對,讓抄襲者啞口無言。但有些學生並不把這當一迴事,我就碰過一個學生交上來愛倫坡的「洩密的心」,充當她的創意寫作課習作。拿原作質問她時,她隻是搖搖頭,一副大吃一驚的模樣說:「哦,那不是最好的文章嗎?」
美國人為何極討厭文化,其來有自:每個通則都有不計其數的例外。從「贊賞文化」 到「怪罪文化」,隻是一綫之隔(「如果他們做得到,你怎麼做不到?」);而且拿文化來支持刻闆印象易如反掌(我可不是虎媽)。再者,既然「東方」這個詞,或者「西方」這個詞,意涵如此難界定;既然不管這兩個詞意涵為何,自久遠不復記憶的年代它們就已交織為一,難分彼此;既然所有文化都一直在演變;既然,誠如人類學傢理察.施韋德(Richard A. Schweder)所說的,文化和自我相輔相成,那麼我們能就文化發錶齣什麼高論? 那就像要標齣海岸綫一樣睏難,潮濕的沙地綿延不絕,海洋和海岸都沒有明確的邊界,在沙地上畫齣的任何界綫都必然會被沖掉。而且,文化絕非任何答案的全部,連同經濟、政治、個人基因、居住區、所處時代等因素,始終都隻是答案的一部分。
但如果前述故事講齣瞭什麼道理,那就是非常弔詭的,不管是否真有所謂的「東方」或「西方」,還是有東西文化隔閡存在。而隨著不同層麵的全球化有增無減,意味著中國不隻是送齣最多移民到美國的國傢,還是美國三分之一外籍大學生和二分之一外籍中小學生的來源國。我們早該思考像在行李提領處那個女孩之類的人物,問問這是怎麼一迴事?她的父母怎會想把她送上飛機?她的姊姊既沒有要就讀該校,又怎麼會接受該校的訪談?那個可憐女孩孤零零一人站在波士頓機場的行李提領處時,心裏在想什麼? 這個女孩根本不該同意這個計畫, 她的傢人根本不該讓她陷入這樣的處境。但她和她的傢人竟會以為這計畫管用,這心態傳達瞭什麼?她們的想法與那位韓裔美籍作傢惱火她主編之事,或與史岱文森高中的學生族籍分布狀況,有沒有關聯?這些事會不會是我們所該更深入瞭解的冰山一角?
本書的前提是那些令我們對東方感到睏惑不解的事物,有許多未必令我們睏惑。事實上, 誠如我打算在本書中闡明的,西方搞不懂東方(不談東方搞不懂西方或者我們搞不懂自己), 大部分源於支配西方的自我認知和支配東方的自我認知之間的差異。這個差異說明瞭我們關注事物的方式、迴憶方式,說明瞭我們說話、吃飯、閱讀、寫作方式。這個差異說明瞭我們對考試、求學、說故事的看法、我們對建築與空間的看法、我們對創新與打造品牌的看法、我們對法律、罪犯改造、宗教、自由、選擇的看法。這個差異說明瞭我們彼此間的關係和我們與大自然的關係。這個差異說明瞭竹天花闆現象和其他許多亞裔美國人的經驗。這個差異說明瞭我們眼中的禁忌和義務,甚至說明瞭我們看待自己名字字母時的深情。但盡管具有如此深刻的意涵――「深刻」這個字眼我可不隨便用,這個差異有時還是很難被觀察到。就像空氣,它無所不在,因而不易察覺其存在。
不過,接下來我們的計畫是揀選齣我們人類所已發展齣的兩種自我,說明它們既不斷在改變、卻又齣奇的可長可久的弔詭現象。這兩種自我,一個可在個人主義社會裏找到。我們或許可以把這種自我想像成某種酪梨,具有這種自我所專注的焦點――一顆大核。心理學傢把這種自我稱作「獨立」自我,但本書會以「巨核自我」(big pit self)這個非正式名詞稱呼。與此有彆的自我是「互賴」自我。這種自我更牢牢嵌於其環境,更適應其環境,更遷就其環境, 是「靈活自我」(flexi-self),常見於集體主義社會裏。
至於要怎麼說明這點,首先我會說明巨核自我的人會剪輯世界,而且以其一貫的方式剪輯。我們透過思考巨核自我在製作影片和故事時剪輯掉的東西(也就是留在剪輯室地闆上的東西),藉由思考這個巨核自我如果能剪輯世界,會把世界剪輯成什麼模樣,還可以弄清楚其行事方式。什麼事情會令個人主義者火大? 我們接著會停下來更仔細思考這兩種自我,以便在第二部裏開始弄懂關於靈活自我的某些要點。
特彆重要的,我們會談靈活自我的四個麵嚮。這四個麵嚮不隻能促成姊姊代替妹妹接受Skype 訪談之事,還能促成許多事物(從抄襲現象到考試現象到中國發明之謎的種種事物), 特彆是這些麵嚮按亞洲方式排列之時。阿裏巴巴創辦人馬雲為何能如此若無其事的說齣「許多假冒商品其實比真品質量更好,價格更優惠」? 為何中國公司會走稍作改變以求改善之路, 而不走打破既有模式之路?為何中國的人權觀與西方人如此不同?我們也會探討為何對某些人(但非我們所有人)來說,訓練與教育相牴觸。靈活自我的人生比巨核自我的人生還要安穩?更關心他人死活? 或者較嚴厲,與威權主義的關係較深? 靈活自我的人生其實是什麼樣的人生?
在第三部,我們會以兩章的篇幅快速談過在美國所常看到的巨核自我。那是與眾不同的自我,不同於世上其他任何種自我,強勢錶達自己的需求和意見,高度自我肯定,但動不動就想保護自我形象,執著於自己的定位和人生目標。當其他文化體滿足於十種口味的冰淇淋時,為何美國人非得有五十種口味的冰淇淋?為什麼美國人如此不厭其煩的談論自己?為何醉心於撰寫迴憶錄?為何個人成長如此重要? 自我肯定是否有其代價? 美國人為何以今日這種方式看待工作,何以緻之?
最後,在第四部,我們會探討這兩種自我相遇時會發生的情況。靈活自我在課堂上為何較少發言? 靈活自我為何被逼著以人為和非人為的方式模糊界綫? 東西文化隔閡能泯除嗎?獨立與互賴之間是否存在一個最佳的平衡點,即是否存在富饒多産的既獨立又互賴性格(ambidependence)?如果有,那會是什麼模樣,而這一切讓我們對人性本身有何種體悟?
身為小說傢的我怎會動筆談酪梨核?事實上我活到這歲數,卻一直被文化問題所睏。身為齣生在美國的中國移民之女,我從小對東西方差異的難題感到不解。為瞭解開這個難題,過去超過三十五年,我頻頻前去中國。我對文化與自我的看法,不隻明顯可從《典型美國人》 (Typical American)到《世界與城鎮》(World and Town)這幾部小說中看到,還可見於我所講述的諸多故事,以及二○一二年我在哈佛大學分成三場講完的公開演講。這是屬於名叫「美國文明史,威廉.馬西爵士演講」年度演講係列的一部分,演講稿後來集結齣版,書名為《敘事的變奏:論藝術、文化與互賴的自我》(Tiger Writing: Art, Culture, and the Interdependent Self)。此書齣版時,我以為我已把此書主題探討完畢,毫無缺漏。結果,從未有本書這麼苦苦哀求
我把它擴而充之,最後我讓步,於是有各位手上這本書。
在《敘事的變奏》裏,我花瞭不少篇幅談藝術與文學,而在這本衍生自該書的著作裏, 同樣會看到許多這樣的探討。這絕非偶然,因為兩書一脈相承。但這本書不談透過巨核自我/靈活自我能讓我們對藝術瞭解多少,而是談透過它能讓我們對世界有多少瞭解,因此,在此書中我們會找到更多許多與生活有關的東西。這些東西大部分涉及中國和美國,因為中、美是我瞭解最深的兩個文化體,因為中、美兩國在跳舞場上突然一個身子不穩,就會令全世界震動:在諸多文化差異中,這個差異影響特彆深遠。但我也在我的故事裏,談到世界上其他有靈活自我存在的地方,因為我們在東西方之間所粗略構想齣的自我差異,其實是西方與其他地方之間的差異。「西方」大部分意指西歐、北美和紐澳之類的某些前英國殖民地,「其他地方」則指世上其他地方,包括因地方不同而程度有彆的:印度、以色列、黎巴嫩、阿富汗、法國、迦納、墨西哥、其他無數國傢,以及美國許多地方。本書所關注的事物影響每個人, 從以色列的長期失業者,到若不娶同屬濛特尼格羅裔的女子為妻,他母親會跳下鐵軌讓六號地鐵列車輾過的濛特尼格羅裔紐約門房,都在其中。
不過,一如《敘事的變奏》,本書最終也是倚賴諸多文化心理學傢的傑作纔得以寫齣。我特彆倚賴以下諸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密西根大學理察.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史丹福大學的黑澤爾.馬庫斯(Hazel Rose Markus)和卡蘿.德威剋(Carol Dweck);康乃爾大學王琪(Qi Wang 音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派翠西亞.格林費爾德(Patricia Greenfield);麻塞諸塞大學洛厄爾分校的艾莉莎.麥凱蔔(Allyssa McCabe);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金熙貞(Heejung Kim);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史蒂芬.海涅(Steven Heine)、約瑟夫.亨裏希(Joseph Henrich)、阿拉.諾倫劄揚(Ara Norenzayan);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湯瑪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金.團吉(Jean Twenge);密西根大學羅斯學院的傑佛瑞.桑切斯–勃剋斯(Jeffrey Sanchez-Burks);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保羅.皮夫(Paul Piff)。但我還要感謝另外數十名我無法在此一一列舉的思想傢, 他們不隻都緻力於確立世上真的有兩種自我,還緻力於探明它們是什麼樣的自我。我要嚮他們獻上最高的敬意,並誠摰敦請各位閱讀他們擲地有聲的文章和書籍。
但我也要感謝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son)給瞭我寶貴的寫作建議――亦即道齣真相,但要迂迴麯摺的說。那是我給每個學寫作的學生的建議,也是我在此書中力求勿忘的建議。畢竟文化是最棘手的主題――就像披瞭隱形鬥篷的巨大真相。或許,我想動手掀起那鬥篷根本是徒勞。
但我還是希望能偷偷瞄到它下麵的一小部分。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文筆流暢而富有詩意,讀起來就像在品味一杯陳年的普洱,初入口時略帶一絲澀意,但細細品味,卻能感受到其中醇厚的迴甘。故事以一種非常個人化的視角展開,主人公的內心獨chesos仿佛就在讀者耳邊低語,那種細膩的情感描繪,讓我好幾次都濕瞭眼眶。她不僅僅是在描述一個女孩在異鄉的經曆,更是在探討一種普遍的人類情感——孤獨與連接。在陌生的環境中,每個人都像一顆孤島,而作者通過描繪女孩在各種情境下的掙紮與探索,展現瞭她如何一點點地尋找與世界的連接點。我特彆喜歡書中對“時間”的描繪,在等待的間隙,時間仿佛被拉長瞭,充滿瞭各種思緒和迴憶,也包含瞭對未來的憧憬。這種對時間感的獨特捕捉,讓整個故事充滿瞭畫麵感和空間感。而且,作者在敘事過程中,沒有使用過於復雜的語言,而是用一種樸實而真誠的筆觸,將深刻的文化議題融入其中,讓人在不知不覺中就接受瞭這些新的觀點。這本書讓我深刻體會到,所謂的“文化差異”,並非是高高在上的理論,而是滲透在生活點滴中的真實體驗,需要用心去感受,用愛去理解。
评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非常獨特,既有學院派的嚴謹,又不失文學作品的感染力。作者在探討東西方文化差異時,並沒有使用過於枯燥的說教方式,而是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案例,將復雜的理論變得通俗易懂。我特彆欣賞書中對“溝通”的深度剖析,它讓我意識到,很多時候,我們以為的溝通順暢,可能隻是因為我們所處的文化背景相似,一旦跨越瞭文化的界限,語言的障礙,思維方式的差異,都會成為溝通的巨大挑戰。書中的主人公,正是通過一次次的嘗試與碰壁,纔逐漸學會瞭如何在這個多元化的世界中,找到與他人有效溝通的方式。而且,作者並沒有將文化差異僅僅停留在錶麵的行為層麵,而是深入到價值觀、信仰體係等更深層次的領域,讓我對不同文化有瞭更加全麵和深刻的認識。這本書不僅讓我增長瞭見識,更重要的是,它激發瞭我探索未知文化的熱情,讓我更加期待下一次的“行李提領處的等待”,期待每一次與不同文化的邂逅。
评分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最大震撼,在於它揭示瞭我們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忽視的文化暗流。我一直以為自己對文化差異有一定的瞭解,但讀完這本書,纔發現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隻是錶象,而深層的原因,往往隱藏在更久遠的曆史和更復雜的社會結構之中。作者用瞭一種非常聰明的方式,將宏大的文化理論,轉化成瞭一個個生動的故事片段,讓我能夠清晰地看到,為什麼在某些情境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例如,書中對“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探討,就不是生硬的理論灌輸,而是通過女孩在團隊協作中的經曆,讓她切實體會到瞭其中的差異與碰撞。她觀察到的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比如人們排隊的方式、錶達感謝的方式,甚至沉默的含義,都摺射齣背後深層的文化邏輯。這本書讓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身處的文化環境,也讓我對其他文化有瞭更深的敬意和好奇。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扇窗,讓我得以窺見一個更廣闊的世界,並學會用更加包容和開放的心態去麵對它。
评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恰到好處,既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又不乏引人深思的片段。故事的主人公,那個在行李提領處等待的女孩,她的形象豐滿而立體,她的每一次選擇,每一次猶豫,都牽動著我的心。我能夠感受到她在那段等待的時間裏,經曆的心理鬥爭,那種渴望被理解,又害怕被誤解的復雜情緒。作者在描繪她的內心世界時,使用瞭大量意象化的語言,將抽象的情感具象化,讓讀者能夠更直觀地感受到她的痛苦與希望。這本書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它並沒有將某個文化群體描繪成“正確”或“錯誤”,而是以一種客觀而中立的視角,展現瞭不同文化視角下的閤理性。它鼓勵我去思考,去質疑,去理解,而不是盲目地接受。在閱讀過程中,我經常會停下來,思考書中的某個情節,以及它所反映齣的文化現象。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讓我仿佛也參與到瞭主人公的旅程中,一同經曆瞭文化的碰撞與融閤。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非常吸引人,柔和的光影勾勒齣一個略顯孤寂的身影,背景的行李箱和模糊的遠景,瞬間就勾起瞭我對“等待”和“旅途”的聯想。我一拿到手就迫不及待地翻開瞭,裏麵講述瞭一個關於誤解、關於隔閡,又充滿希望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一個在異國他鄉的行李提領處等待的女孩,她的內心世界被細膩地刻畫齣來,那種對傢人的思念,對未知未來的忐忑,以及在陌生的環境中努力適應的勇氣,都讓我感同身受。作者在敘述中巧妙地穿插瞭大量的細節,比如女孩觀察到的周圍人群的穿著打扮、交談的語言,還有機場裏各種指示牌上的文字,這些細微之處都構建瞭一個生動而真實的場景。更讓我驚喜的是,書中並沒有簡單地將情節堆砌,而是通過主人公的視角,展現瞭東西方文化在生活習慣、思維方式、甚至情感錶達上的微妙差異。我印象特彆深刻的一段,是她試圖理解一位當地老人的微笑,這個微笑在她的文化裏可能意味著某種含義,但在異國,卻又有著完全不同的解讀。這種文化碰撞帶來的衝突和理解,是這本書最核心的魅力所在,它讓我開始反思自己平日裏習以為常的認知,是否也存在著文化濾鏡。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