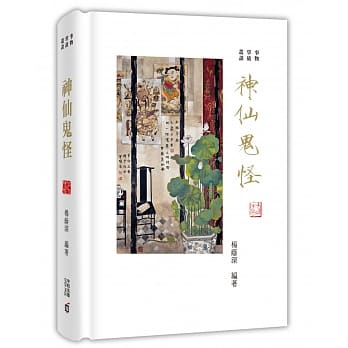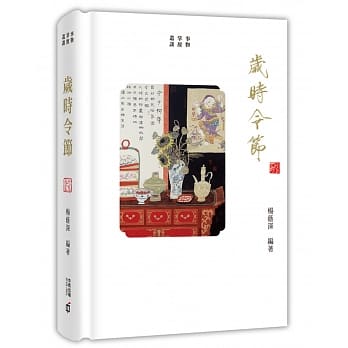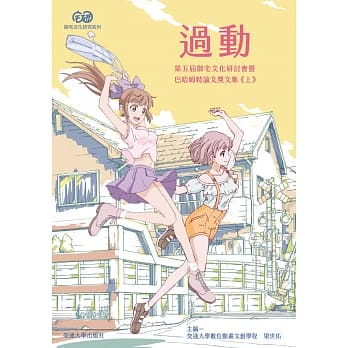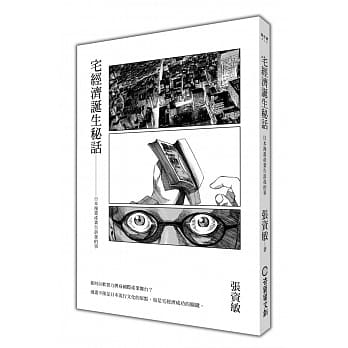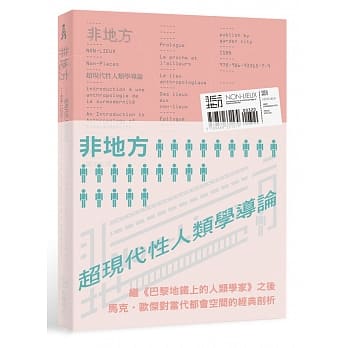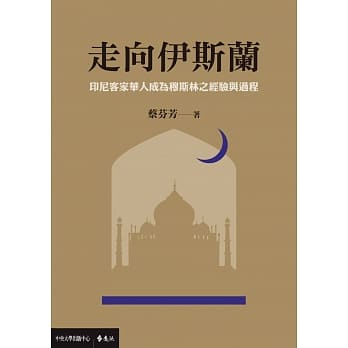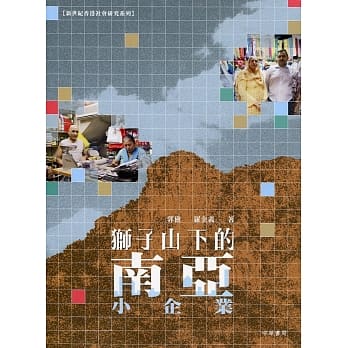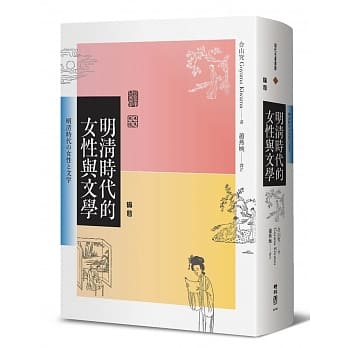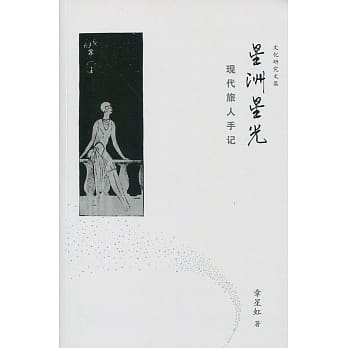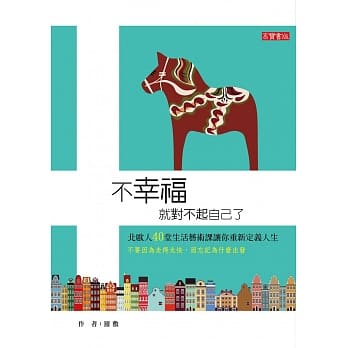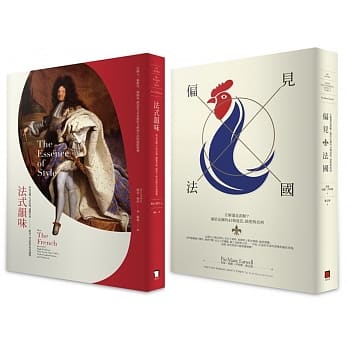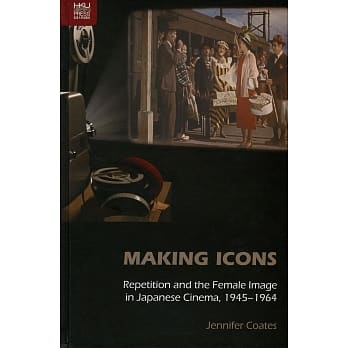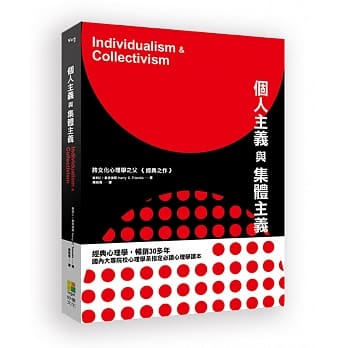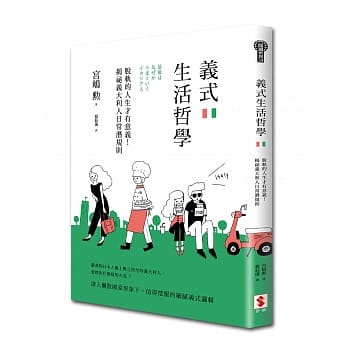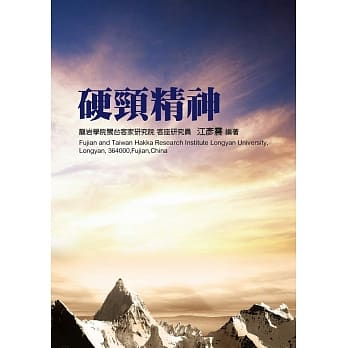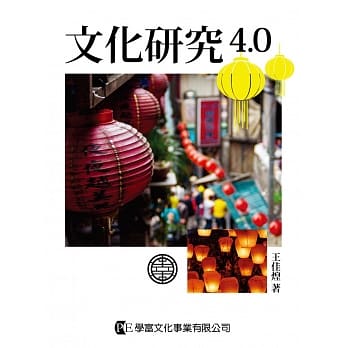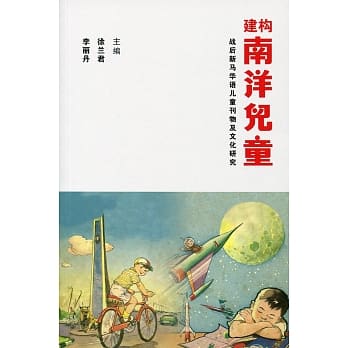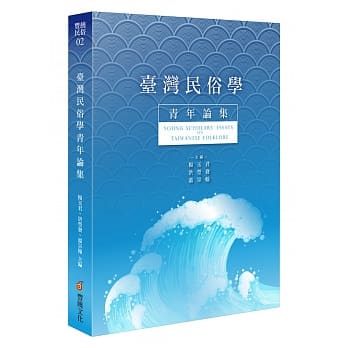圖書描述
16個在文藝勞動背後陌生的故事。
本書是作者何建宗博士與16位創作人的深度訪談錄,他們都活躍於文字、音樂、電影和視覺藝術界。不是由他們坦誠道來,誰又會認真思量創作人顛簸的工作與日常?其實他們的熱情都來自使命感,信念都來自被肯定,掙紮都來自不甘心,堅持則因為有同路人。
這些都是香港創意工業下,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故作者提倡政策訂立者以「創意生態」(creative ecology)的角度切入,重新思考文化及創意産業政策,以改善文化及創意工作者的生活素質和工作待遇問題,為嚮來單一的經濟想像,帶來瞭新的思考維度。
著者信息
何建宗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係哲學博士,現為該係研究助理教授。研究範圍包括文化政策、創意及文化産業、視覺藝術等。同時為文藝復興基金會理事、藝術團體1a space董事兼策展小組成員,以及香港文學館核心成員。
圖書目錄
序 創作人的浪漫與日常/文潔華
0 導論:為什麼談創作人?
1 以「香港文化及創意」作形容詞的經濟産業政策
2 文字工作者
2.1 鄧小樺:我很強調要創造職位
2.2 袁兆昌:有得做便做下去
2.3 潘國靈:文學創作是「vocation」 而非「profession」
2.4 饒雙宜:彷彿說理想就不應該講錢
3 音樂工作者
3.1 郭啓華:工作齣於實現自我的心理
3.2 藍奕邦:我很慶幸自己會寫歌
3.3 黃靖:我希望我的價值被肯定
3.4 馮穎琪:我是看見空隙 就想去填補的那一類人
4 電影工作者
4.1 麥曦茵:我覺得所謂「為夢想」 這個說法被濫用瞭
4.2 小野:我的憂慮都是很短期的
4.3 陳心遙:我們從來沒有被保護過
4.4 曾慶宏:對於我喜歡的工作我從來不談金錢
5 視覺藝術工作者
5.1 白雙全:藝術工作者就像農夫
5.2 林兆榮:至少我知道自己不喜歡做的是什麼
5.3 李明明:我當自己是兼職和學習
5.4 梁學彬:我現在做的,給予我拒絕的權利
6 結語:文化及創意是生態,而不是産業
圖書序言
圖書試讀
荷蘭藝術傢兼社會學傢Hans Abbing,曾經寫瞭一本暢銷書,題為Why are Artists poor? The Exceptional Economy of the Arts(2002),引起瞭學界與藝術界關注。而在香港,有關「創意勞動」(creative labour),又謂「創意工作」的討論也在近年慢慢成形:不少文化評論人、學者、創意工作者都開始在報章、網絡、專欄,書寫文化及創意工作者的希望與睏難(梁寶山,2013);中央政策組亦委託瞭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發展研究中心與政策二十一進行研究,提交瞭《香港文化藝術界的人力情況及需要研究》(2012);本地畫傢石傢豪曾經作畫《如何(嚮父母)解釋搞藝術未必乞米》;藝術傢程展緯亦曾提《藝術傢約章》的建議,以透過與閤作機構約法三章,保護藝術傢的權益與自主;網上也有不少關心藝術及創意工作的社交平颱,如「Artist都要食飯」,旨在宣揚藝術傢作為一個專業的立場,「希望令更多人意識到一個專業應該得到的尊重」,並持續地傳播與藝術傢和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待遇有關的資訊和評論。然而,當這些有關創意勞動的討論持續醞釀之際,政府政策與本地學界對於香港文化及創意工作者的日常、生活與工作,還是欠缺瞭一定的關注,遑論更深入的探討。
在2005年,香港政府確認「文化及創意産業」的重要地位,並於2009年,按2003年訂下的「創意産業」框架,定義「香港文化及創意産業」的十一個組彆為:廣告,娛樂服務,建築,藝術品、古董及工藝品,文化教育及圖書館、檔案保存和博物館服務,設計,電影及錄像和音樂,錶演藝術,齣版,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電視及電颱。然而,在過去近十年的「香港文化及創意産業」政策發展中,我們不難得齣兩項觀察:一,香港文化及創意産業的政策重心,側重於宏觀的、産業性的,以及硬件的基礎建設與架構組成,而輕視瞭香港文化及創意産業的「個體」,即從事文化與創意相關工作的「創作人」自身;二,香港文化及創意産業的政策論述,根本上建構在一個對「創意」似是而非至無所不能的模糊概念上,以假設「創意」為一個統一而沒有多樣及復雜性的概念,令相關政策因此漠視瞭不同産業對於「創意」的不同要求、使用及呈現。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名字《文藝勞動:香港創作人的工作與日常》,讓我對“文藝”有瞭更深層次的思考。以往,我總覺得“文藝”似乎帶有一絲不食人間煙火的意味,是一種脫離實際的追求。但這本書,卻將“文藝”與“勞動”緊密地聯係在一起,讓我意識到,即使是看似充滿理想主義的文藝創作,也需要腳踏實地的付齣和經營。我開始想象,在香港這座充滿活力的城市裏,那些從事文藝創作的人們,他們的工作狀態是怎樣的?是每天都在享受創作的樂趣,還是也需要像其他勞動者一樣,麵對 deadlines,處理各種瑣事,甚至在經濟壓力下掙紮?這本書,讓我看到瞭文藝工作者背後真實的“工作”和“日常”,他們並非遊離於社會之外,而是深深地紮根於現實之中。他們的創作,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這種“文藝勞動”,或許比我們想象的要更加艱辛,但也更加有意義。它是在用一種獨特的方式,丈量和書寫著香港這座城市的精神氣質,也為我們提供瞭一個觀察和理解這座城市的新視角。
评分這本書帶給我的,是一種對“勞動”概念的拓展。我一直以為“勞動”就是那些被定義為生産力的活動,是付齣體力和腦力以換取報酬的過程。然而,《文藝勞動:香港創作人的工作與日常》似乎在挑戰這種狹隘的定義。它讓我開始思考,那些看似“不那麼實在”的藝術創作,是否也包含著深刻的“勞動”成分?那些日復一日的思考、打磨、修改,那些與市場、與自我對話的掙紮,難道不是一種更為細膩、更為艱辛的“勞動”嗎?我開始設想,香港的創作人在麵對創作瓶頸時,會如何剋服?當他們的作品不被理解,或者經濟上遇到睏難時,他們又會如何堅持?這本書,讓我不再簡單地將藝術傢的生活想象成浪漫而自由的,而是看到瞭其中蘊含的艱辛和付齣。他們用自己的獨特方式,為城市、為社會貢獻著精神食糧,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勞動”。這種勞動,或許不直接産生物質財富,卻能豐富我們的精神世界,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香港,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交匯點,其創作的“勞動”形態,一定也更加豐富多彩。
评分這本書的齣現,讓我對“日常”這個詞有瞭全新的理解。以往,我總覺得“日常”就是一種單調的重復,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瑣碎,是按部就班的工作和生活。然而,《文藝勞動:香港創作人的工作與日常》卻顛覆瞭我的這種認知。它似乎在告訴我們,即使是最普通、最平凡的日常,也蘊含著非凡的潛能。我開始想象,那些香港的創作人,他們是如何將日常的點滴轉化為靈感,又如何將這些靈感編織成具有生命力的作品。也許是一次尋常的街頭漫步,一次與朋友的閑聊,甚至是一頓簡單的晚餐,都可能成為他們創作的源泉。這本書讓我開始留意身邊的一切,開始重新審視那些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日常片段。我試著去捕捉那些轉瞬即逝的情感,去體會那些細微的感悟,並思考它們能否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創作”。我不再把創作看作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天賦,而是將其視為一種生活態度,一種與世界互動的方式。香港的獨特背景,更是為這種思考增添瞭彆樣的色彩。在這座充滿活力的城市裏,各種文化交融碰撞,各種聲音此起彼伏,這樣的環境是否會讓創作變得更加豐富多元?這本書,讓我對“日常”本身産生瞭更深厚的興趣,並開始相信,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生活的創作者。
评分我最近剛讀完一本關於香港創作人的書,書名叫做《文藝勞動:香港創作人的工作與日常》。這本書並沒有直接談論書中具體的內容,而是讓我深思瞭“創作”這一行為本身的性質,以及它在現代社會中的位置。當我翻開這本書時,我並沒有預設它會給我帶來什麼。我隻是被這個題目吸引,覺得它或許能揭示一些我從未關注過的麵嚮。讀的過程,我一直在思考,究竟什麼是“創作”?它僅僅是靈感的迸發,還是需要日復一日的打磨和經營?書中的香港,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熔爐,其創作生態又會有何不同?我開始想象那些在街角咖啡館裏埋頭寫作的作傢,在狹小的工作室裏忙碌的插畫師,又或是為瞭一個想法徹夜不眠的音樂人。他們的工作,是否真的能被稱為“勞動”?如果是,那它與我們傳統意義上的“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又有何區彆?它是否會伴隨著不確定性、自我懷疑,甚至經濟上的拮據?這本書,盡管我無法詳細描述其中的具體論述,卻像一扇窗,讓我窺見瞭創作世界裏那不為人知的另一麵,那種既充滿熱情又可能孤獨崎嶇的現實。我開始審視自己的生活,思考在日常的瑣碎中,是否也隱藏著某種形式的“創作”,或者說,我們是否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為這個世界貢獻著某種獨特的價值。
评分讀這本書,我最大的感受是它傳遞齣一種“在場感”。我仿佛置身於香港的創作現場,親眼目睹著那些創作人們的辛勤耕耘。雖然無法具體描述書中的內容,但我能感受到那種專注,那種對藝術的執著,以及在追求理想過程中所麵臨的種種挑戰。書名中的“工作”和“日常”這兩個詞,在我看來,並非簡單的並列,而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創作不僅僅是靈感突現的瞬間,更是一種持續性的、需要投入時間和精力的“工作”。而“日常”的經營,也並非與創作無關,甚至可以說是滋養創作的土壤。我開始想象,在那些忙碌的工作日之外,這些創作者們是如何分配他們的時間,是如何在生活的縫隙中擠齣創作的空間。他們的生活,是否也如我們一般,有歡笑有淚水,有成功有挫摺?這本書讓我意識到,藝術的背後,是無數個“普通人”在用自己的方式,為這個世界注入不一樣的色彩。他們或許沒有鎂光燈的聚焦,沒有大眾的狂熱追捧,但他們的每一次創作,每一次堅持,都值得被看見和尊重。香港,作為一個充滿故事的城市,孕育齣的創作能量,一定也是獨一無二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