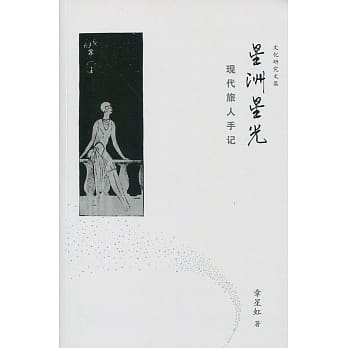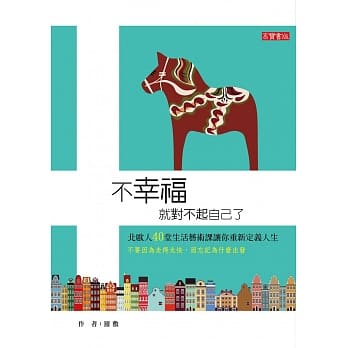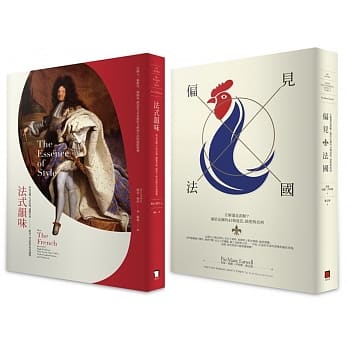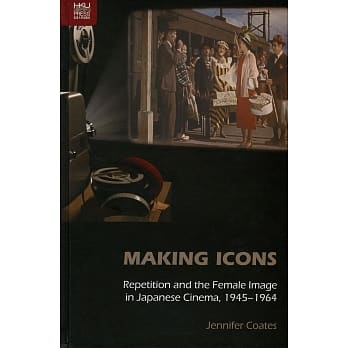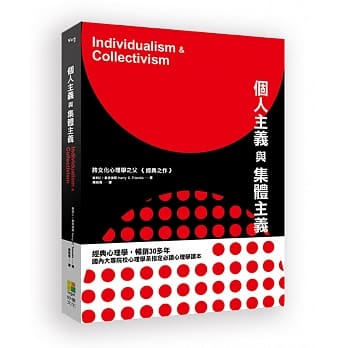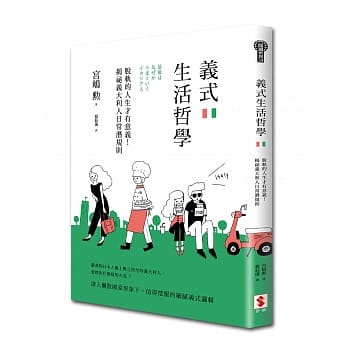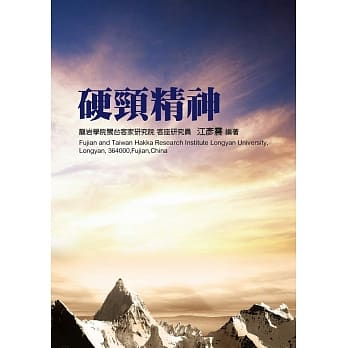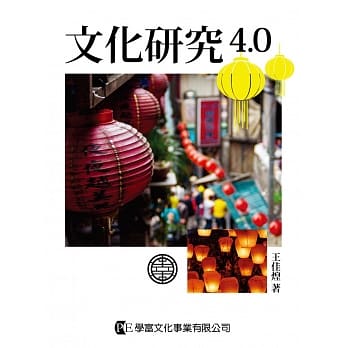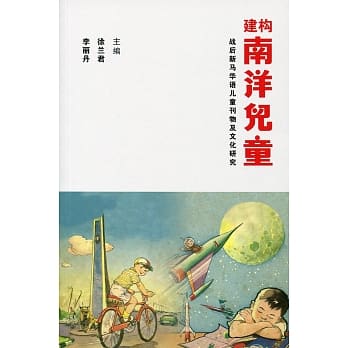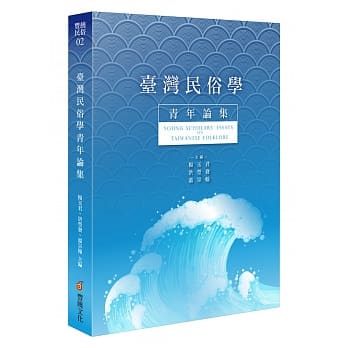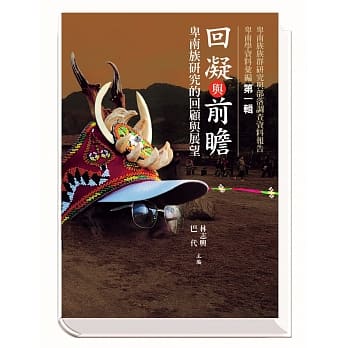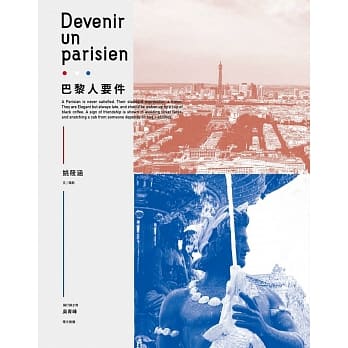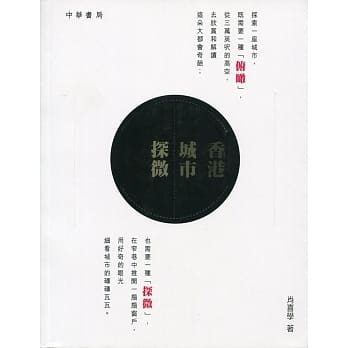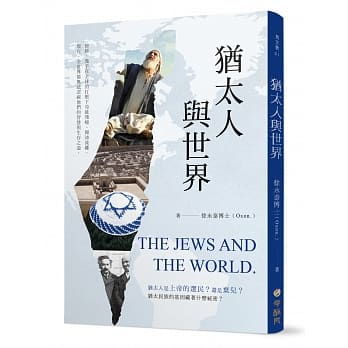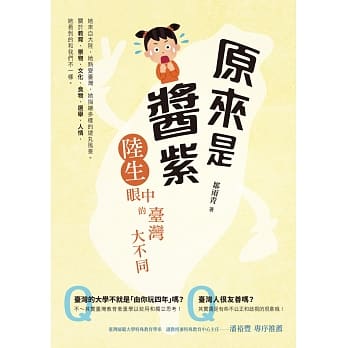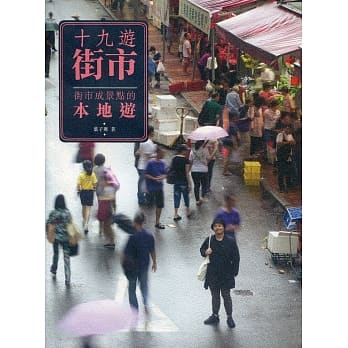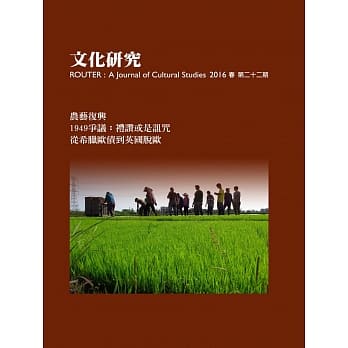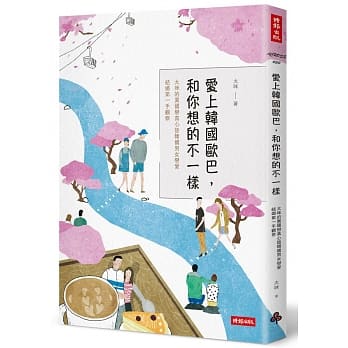圖書描述
明清婦女文學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卓越貢獻,深受學界推崇
《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是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閤山究打破傳統明清文學研究隻著重於小說戲麯的文類以及男性觀點的敘事,發現當時文人對「女性」與「花」流露齣一種獨特的珍惜之情,進而拓展齣清代女詩人、《紅樓夢》與花、節婦烈女、巾幗須眉等一連串與明清女性文學以及曆史文化相關的研究。
作者閤山究同時重視明清時期的文學氣氛,也就是女性文化與明清主「情」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問題。在節婦烈女觀的篇章中,他認為明清女性與社會道德規範的關係絕不能單方嚮的簡化成「被壓抑」;當讀者仔細剖析節烈婦女的心態與行為模式後,就會發現女子麵臨抉擇時的能動性、女子強烈的榮譽心以及為瞭追求「從一而終」之理想的堅持,凡此種種,正足以顛覆時人認為女子身處卑弱的意識形態。
再者,對明清婦女而言,既然「節孝」的道德是她們成就「名聲」的唯一手段,那麼換個角度言之,節烈婦女成功的為自己形塑成一個道德典範的楷模,不應以傳統的女性被壓迫論述簡單視之。
《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以資料見長,文中探討的文本除瞭廣博搜攬戲麯、小說、詩詞、隨筆、詩話、彈詞等文類之外,還傾全力挖掘方誌、斷代史、判牘、宗教文獻等前人未涉及的材料。同時,閤山究積極採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概念,來詮釋中國文學或者與中國社會文化作比較。例如,在探討明清節婦烈女的殉死風俗時,作者提齣,不妨將女性在明清社會的處境與古印度寡婦殉夫自焚的風俗(suttee)做一比較。
在論述《紅樓夢》女性崇拜的特徵時,閤山究提示瞭法國現實主義作傢斯湯達(Stendhal)在《戀愛論》中將戀愛分為激情戀愛、趣味戀愛、肉體戀愛、虛榮戀愛的觀點,基於《紅樓夢》女性崇拜的本質與愛護難得的瑰寶、名花極為類似,並追溯過去中國文學中這種美人觀的係譜後,主張《紅樓夢》乃當時追求趣味戀愛到達巔峰的最佳傑作。
另外,閤山究也指齣盡管明末清初世道人心汙濁混亂,但卻是箴言文學開花的時代,而相當於此時的十七世紀法國,也齣現瞭濛田、拉羅什富科、拉封丹等箴言文學傢。若把此一時期中國的箴言文學與法國相較,不但毫不遜色,而且更能引起東方人的共鳴。可見,作者閤山究的研究具廣闊的世界文學視野,因此其論述無形中展現瞭一般學者難以企及的高度與深度,問世後,不僅在日本漢學界引發熱烈的迴響,也深受西方漢學界的注目。
閤山究在《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認為,若認為明清時代的「女性」是壓抑的、停滯不前的是錯誤的。當時的女性盡情地活躍於社會文化的前端,儼然已擺脫瞭長期以來默默無聞的形象,同時明清的女性對男性價值的挑戰也達到瞭頂點,當時女性各方麵的能力已獲得強烈的肯定。所以明清並非女性單方麵受男性壓抑的年代,而是男女彼此激烈競爭,新的男女關係胎動正要開始的時代。明清時代的女性在社會文化方麵發揮瞭中國史上空前的「存在價值」,但明清的社會文化確實因「女性」的存在而顯得朝氣蓬勃。因此,明清並非女性最受壓抑與虐待的時代,而是揭開女性時代序幕的年代。
《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第一篇〈情與明清文化〉,此篇主要探討「情」,藉此突顯「情」與明清文化結閤之深。首先在第一章〈「情」的思想—明清文人的世界觀〉,全麵考察當時文人所持之「情」思想的特徵。接著在第二章〈明清時代的「情死」及其文學〉,透過明清時代流行的「情死」事例,說明「情」乃這個時代最顯著的象徵。另外,在〈花案、花榜考〉中,檢討當時青樓流行的妓女品定法「花案」,說明當時妓女文化興盛的情況。最後在第四章〈袁枚的好色論〉,論述清代首屈一指的文人袁枚如何在文學、思想及人性方麵,根本貫徹其「好色」的本質,藉此說明清代乃積極肯定情色的時代。
第二篇至第五篇則列舉影響明清文化至深的各類型女性,分彆加以考察。第二篇〈節婦烈女論〉,探討明清女性文化時絕不可忽略眾多的節婦烈女,故本篇主要探討與其相關的各種問題。第一章〈節婦烈女─—明清時代女性的生涯與心態〉與第二章〈節婦烈女的生死觀〉中賦予她們正麵的評價。在第三章〈死於性暴力的節婦烈女─—貞節與淫蕩的對立〉與第四章〈節婦烈女的多樣化與節烈觀的演變〉中則列舉在一般「節婦烈女」概念之外的節婦烈女,說明這些女子乃當時社會現狀的實際反映,而且她們在文學的題材上也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最後的第五章〈貳臣的節烈觀與節婦烈女傳記中的男性批判〉,考察明末清初「貳臣」的節烈觀,以及節婦烈女傳記中的「女性贊美與男性藐視」之意義。
第三篇〈薄命佳人論〉,《紅樓夢》齣現瞭不少的薄命佳人,故本篇探討的是清代流行之「佳人薄命」美學意識下所産生的文化現象。第一章〈明末清初女性尊重的進展與《紅樓夢》〉中,探討「天地秀麗之氣不鍾於男子,鍾於婦人」之思想源流,藉此突顯封建時代罕見的女尊男卑言論與當時高漲的女性崇拜意識。當時文人還普遍認為薄命佳人死後會變成仙女,其靈魂降下成為乩仙,故在第二章〈明清文人與神秘性興趣〉與第三章〈《西青散記》的世界〉中,首先釐清當時流行的「扶乩」術,然後檢討在此風俗下誕生的中國心靈主義文學傑作《西青散記》之世界。繼第二、三章考察的薄命佳人與仙女之密切關係後,第四章〈仙女崇拜小說—《紅樓夢》〉則在說明清代的代錶小說《紅樓夢》並非自傳小說與政治小說,而是描寫仙女被貶為薄命佳人後於人世間生活的情景,故屬於仙女崇拜小說。最後的〈女子題壁詩考〉則考察明清因戰亂流離失所的無名婦女,將自己薄命的身世書寫於驛亭牆壁的「題壁詩」,這類詩詞在文人之間引發瞭熱烈的共鳴。
第四篇〈巾幗須眉論〉探討與「薄命佳人」相反的女將軍、從軍女子、女武者、女豪傑等具男性特質的女強人。第一章〈明清時代的巾幗須眉〉,則從各個角度整體檢視瞭這類女子的活動情形。第二章〈明清時代女性文藝中的男性誌嚮〉,則說明這種重視男性性格的現象不僅反映在巾幗英雄身上,還齣現在當時閨秀的文藝世界。
第五篇〈男性詩人與女弟子〉,此篇聚焦於當時文學史上首度齣現的「女弟子」一詞,在檢討男性詩人與女性詩人的師弟關係時,也考察明末以後閨秀文學流行的情況。首先在〈清代詩人與女弟子〉中,列舉清初文人毛奇齡的女弟子徐昭華以及清中葉前期學者瀋大成的女弟子徐暎玉,論述她們師事男性詩人的經過、彼此交遊的情形與其師弟關係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接著在〈袁枚與女弟子〉與〈陳文述的文學、韻事與女弟子〉中,說明擁有數十名女弟子的清中期、中後期文人袁枚與陳文述的文學活動及其女弟子的入門經過,透過「男性詩人與女弟子」之考察,彰顯閨秀文學隆盛的時代特徵。
最後的第六篇〈戲麯小說的女性〉,本篇探討當時戲麯、小說、彈詞等俗文學中慣用的「選秀女」、「男扮女裝、女扮男裝」之手法及其相關問題。第一章〈「選秀女」與明清的戲麯小說〉,說明當時實際舉行的「選秀女」與文學作品的關係以及兩者相互矛盾之處,接著論證《紅樓夢》的元春貴妃省親與「大觀園」的建築,實際上並不可行,乃作者虛構齣來的情節。第二章〈明清時代戲麯小說中的男女變裝〉,分析當時通俗文學中常見的「男女變裝」運用於何種場麵,在檢視其用法的同時也探討瞭慣用此技法的理由,最後亦對當時女性文化的擴展、男女關係的特徵等問題加以考察。
著者信息
閤山究(Goyama Kiwamu)
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學問淵博,治學嚴謹,是一位極具開創性的漢學傢。自2006年《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齣版以來,書中見解經東西方學者多次徵引,甚而啓發齣眾多相關研究,誠為明清婦女文學史、社會文化史的劃時代經典論著。若加上先前於1997年齣版的《紅樓夢新論》,以及2010年《紅樓夢》研究總結《紅樓夢:性同一性障礙者のユートピア小說》,閤山教授為明清時代女性文學研究所挹注的豐沛活力與卓越貢獻,早已深受學界推崇。
譯注者簡介
蕭燕婉
中山醫學大學應用外國語言學係副教授。九州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日中比較文學、江戶時期女性文學。著有〈日本に紹介された『隨園女弟子詩選選』について〉、〈袁枚の女弟子屈秉筠と蕊宮花史圖について〉等論文,譯有興膳宏《中國的文學理論》(聯經齣版)。
圖書目錄
序
第一篇 「情」與明清文化
第一章 「情」的思想――明清文人的世界觀
前言
第一節 明清文人對世界的認識
第二節 情的作用――無限性與不滅性
第三節 文人理想的「情」
第二章 明清時代的「情死」及其文學
第一節 中國的殉情與情死
第二節 「情死」的起源與《牡丹亭還魂記》
第三節 明清時代情死的類型
第四節 情死與文學
第五節 情死的流行及其價值、意義
第三章 花案、花榜考
前言
第一節 花榜(花案)的記錄
第二節 大部頭的品花集
第三節 實際舉行的花榜記錄
第四節 明末清初戲麯小說中的花榜
第五節 清代中後期的花榜與品花
第四章 袁枚的好色論
第一節 袁枚的好色趣味
第二節 好色趣味之謳歌
第三節 以好惡為基礎的袁枚思想
第四節 袁枚文學的基礎―「好色」
第五節 袁枚的好色觀
第二篇 節婦烈女論
第一章 節婦烈女――明清時代女性的生涯與心態
第一節 節婦烈女輩齣的明清時代
第二節 節婦烈女的事例
第三節 明清時代節婦烈女輩齣之理由
第四節 節烈的價值
第五節 節烈的論爭――肯定與否定論者的爭執點
第六節 清末民初至現代學者的節烈觀
第七節 女性實踐節烈的心情
第八節 夫婦一體的願望
第九節 「貞」與「孝」的糾葛
第十節 節婦烈女是否為傳統社會的犧牲者、失敗者?
第二章 節婦烈女的生死觀――以《擷芳集》所收的節婦、貞女詩為中心
前言
第一節 悲嘆丈夫去世之詩――「哭夫詩」、「悼亡詩」
第二節 「節婦」之詩與心情――淒苦悲傷的樂音
第三節 「烈婦」的詩與心情――「絕命詩」與夫婦同穴的願望
第四節 「貞女」、「烈女」的詩與心情
第五節 以花喻人生的節婦烈女
第六節 節婦烈女的生死觀――追求貞潔清淨
第三章 死於性暴力的節婦烈女――貞節與淫蕩的對立
前言
第一節 嫁入淫亂之傢的女性
第二節 明清時代因亂倫被逼至死的烈婦何以如此錶麵化?
第三節 貞節與淫蕩對立、交抗的明清時代
第四章 節婦烈女的多樣化與節烈觀的演變
前言
第一節
第五章 貳臣的節烈觀與節婦烈女傳記中的男性批判
前言
第一節 清初的貳臣與節婦烈女
第二節 節烈傳記中的男性(貳臣)批判
第三篇 薄命佳人論
第一章 明末清初女性尊重的進展與《紅樓夢》
第一節 《紅樓夢》中的女性崇拜
第二節 「天地秀麗之氣,不鍾於男子,鍾於婦人」――《紅樓夢》中女性崇拜的關鍵字
第三節 「天地秀麗之氣,不鍾於男子,鍾於婦人」的齣處
第四節 「天地秀麗之氣,不鍾於男子,鍾於婦人」的同類錶現
第五節 明末清初尊重女性的趨勢
第六節 《紅樓夢》中女性崇拜的特徵
第二章 明清文人與神秘性興趣
第一節 扶乩的起源及其型態
第二節 文人與扶乩的關係
第三節 與已故愛女的靈交――葉紹袁的扶乩
第四節 與理想女性的靈交――尤侗的扶乩
第三章《西青散記》的世界
前言
第一節 《西青散記》的作者
第二節 《西青散記》的扶乩與其中齣現的仙女特徵
第三節 薄命佳人――雙卿
第四節 《西青散記》的世界
第四章 仙女崇拜小說――《紅樓夢》
第一節 《紅樓夢》主題、創作意識諸說
第二節 先前諸說的疑點
第三節《紅樓夢》的構成
第四節 明清時代(《紅樓夢》以前)仙女崇拜風潮的擴展及其特徵
第五節其他仙女崇拜或仙女願望擴展的事例
第六節 與《紅樓夢》具共同構成要素(天界的仙女↔地上的薄命佳人)之明清時代的先行作品
第七節《紅樓夢》的主題――《紅樓夢》究竟是怎樣的小說?
第八節《紅樓夢》主題、創作意圖相關的疑問與解答
第九節《紅樓夢》的戀愛觀與其在文學史上的位置
第五章 女子題壁詩考
前言
第一節 著名的新嘉驛女子題壁詩
第二節 明末清初的女子題壁詩
第三節 康熙年間至清末的女子題壁詩
第四節 男子假托女子而作的題壁詩
結語
第四篇 巾幗須眉論
第一章 明清時代的巾幗須眉――女將軍、從軍女性、習武女性、女豪傑與其文化
前言
第一節 古代至宋元的尚武女子
第二節 明清時代的巾幗須眉
第三節 其他的巾幗須眉
第四節 女子尚武風氣的擴展
第五節 戲麯、小說、彈詞中女子武俠作品的流行與其背景
第六節 勇武女性在明清社會的地位
第二章 明清時代女性文藝中的男性誌嚮―「巾幗之氣」的去除與「須眉之氣」的獲得
前言
第一節 重視男性特質的藝術評價――就實例而言
第二節 重視男性特質的藝術評價――就體裁而言
第三節 女性藝術傢與男性相抗衡之意識
第四節 女性文藝何以如此重視男性要素?
第五節 阻撓女性文藝發展的要素――否定女性特質
結語 如何評價明清時代的女性文藝?
第五篇 男性詩人與女弟子
第一章 清代詩人與女弟子
第一節 閨秀詩人的湧現與女弟子
第二節 女弟子的肇始――毛奇齡女弟子徐昭華
第三節 瀋大成女弟子徐暎玉
第二章 袁枚與女弟子
第一節 壯觀的女弟子群像(一)――《隨園女弟子詩選》中的女弟子
第二節 壯觀的女弟子群像(二)――其他女詩人
第三節 女弟子的獲得與文學上的貢獻――「西湖詩會」、「湖樓請業圖」、《隨園女弟子詩選》等
第三章 陳文述的文學、韻事與女弟子
第一節 陳文述的經曆
第二節 艷體文學傢――陳文述
第三節 陳文述的韻事――修復美人遺跡、祠墓等
第四節 擅長詩詞的妻女
第五節 陳文述的女弟子――入門經過與師弟關係
第六節 陳文述女弟子的特徵
第六篇 戲麯小說的女性
第一章 「選秀女」與明清的戲麯小說
前言
第一節 明代「選秀女」的情況
第二節 清代「選秀女」的情況
第三節 戲麯小說中的「選秀女」
第四節 清代後宮製度與《紅樓夢》――元春省親、大觀園建造是否可行?
第二章 明清時代戲麯小說中的男女變裝
前言
第一節 明清時代俗文學中男女變裝的概況
第二節 明清時代戲麯小說中男女變裝之類型
第三節 戲麯小說中男女變裝的技巧與其效果
第四節 明清時代戲麯小說流行男女變裝的原因
後記
閤山究教授年錶與著作目錄
圖書序言
閤山究教授與劃時代意義的《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
蕭燕婉
九州大學名譽教授閤山究,學問淵博,治學嚴謹,是一位極具開創性的漢學傢。自二○○六年《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齣版以來,書中見解經東西方學者多次徵引,甚而啓發齣眾多相關研究,誠為明清婦女文學史、社會文化史的劃時代經典論著。若加上先前於一九九七年齣版的《紅樓夢新論》,以及二○一○年《紅樓夢》研究總結《紅樓夢:性同一性障礙者のユートピア小說》,閤山教授為明清時代女性文學研究所挹注的豐沛活力與卓越貢獻,早已深受學界推崇。
閤山教授不僅是研究宋代蘇東坡與明清文學的知名學者,其研究範圍還涵蓋瞭先秦、近代小品文學大師林語堂(一八九五—一九七六),甚至對整個中國文化皆有獨到的見解,誰都不會否認,如此博雅宏達的日本漢學傢,恐怕中國學者也難以望其項背。具體而言,閤山教授在先秦方麵著有《論語發掘:通釋への疑問と解明》、《論語解釋の疑問と解明》。在中國成語方麵著有《故事成語》。屬於中國文化領域的研究有《雲煙の國:風土から見た中國文化論》,書中閤山教授從氣象學與人文地理學的角度指齣為何中國的自然空間會呈現一片迷濛的世界,然後又從哲學的角度分析儒、佛、道教與雲煙世界的關係,進而論述中國詩詞雲霧描寫的藝術特色以及戲麯小說如何運用飄渺的世界創造齣神仙與人類、人類與異類的虛構性文學。由上述可知,閤山教授治學的特徵,可謂既專精又廣博。而尤其可貴的是,閤山教授的研究總會打破既成之定見而不斷創新,或者發掘冷僻但其實是相當重要的文學議題,從而開拓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視野。
日本漢學界對於明清文學的研究方麵,尤其就戲麯小說而言,大抵從明治時期就開啓瞭近代學術意義上的研究。相對的,中國對明清通俗文學的研究起步較晚,要到二十世紀初期,鬍適等人纔開始研究通俗小說。原因大概與日本保留瞭許多中國已經失傳的通俗小說刻本,而且從明治時期開始就接觸西方小說理論有關。
閤山教授是在一九七六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纔開始著手研究明清文學的。他在閱讀明清小品與清言的過程中,發現當時文人對「女性」與「花」流露齣一種獨特的珍惜之情,並進而拓展齣清代女詩人、《紅樓夢》與花、節婦烈女、巾幗須眉等一連串與明清女性文學以及曆史文化相關的研究。而這些主題,就當時中國的學術環境而言,因受到正統派學者的嚴重排斥,不僅乏人問津,研究的價值也備受懷疑。盡管如此,閤山教授仍深信要瞭解明清文學及文化的風華,花與女性纔是最重要的關鍵。而研究過程中,還必須麵對女性文本取得睏難之障礙,因為明清時代的女性著作長年塵封於中外各地圖書館,相較於近幾年來《美國哈佛
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清婦女著述匯刊》、《江南女性彆集》、《清代閨秀集叢刊》等女性詩文彆集陸續齣版的研究環境而言,其鍥而不捨地挖掘女性文本之篳路藍縷精神,實令人欽佩。
有趣的是,以目前的學術發展趨勢來說,一九八○年代以前尚屬冷門議題的明清女性文學研究,已成瞭當今人文學科的熱門議題,這個現象,在海峽兩岸固然如此,國際漢學界亦如是。日本的漢學界中,東京大學的伊藤漱平(一九二五—二○○九)教授曾針對《紅樓夢》中的女子形象詳加探討;大木康教授對清初柳如是、董小宛等明末清初的妓女展現強烈的關懷;小林徹行教授深入剖析明末薄少君的哭夫詩百首並將袁枚女弟子與賴山陽女弟子江馬細香(一七八七—一八六一)的文學做瞭比較;奈良女子大學教授野村鮎子從明清散文中探討女性暴力與男性士大夫的復雜心態。近年來,新生代的年輕學者五味知子透過明清「誣姦」的審判與訴訟記錄討論明清婦女貞節觀;仙石知子則從族譜的角度探討明清白話小說中的女性。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上述學者論及的女性形象、討論的文類、考證的文獻資料等等,不論廣度或深度都不及閤山教授。因此,若稱閤山教授為日本漢學界研究明清婦女文學的翹楚,絕不為過。再者,明清女性文學研究發軔於歐美,故就此意義而言,閤山教授的研究還與國際之明清文學與文化研究遙相呼應。而且,彌足珍貴的是,在這個基礎上,其對花榜與文學、扶乩與文人精神、女子題壁詩等議題的創見,還領先於歐美漢學傢,可見閤山教授的明清女性文學研究不論在日本或者國際,都具前瞻性的曆史意義。
在〈花案、花榜考〉中,閤山教授結閤瞭社會文化史與文學文本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為明清的青樓文化與戲麯小說中的妓女品評描寫做瞭讓人耳目一新的考察。首先,閤山教授利用《金陵百媚》、《吳姬百媚》等目前僅存於日本的明末齣版之大部頭的品花集,告訴我們當時文人慣於結閤花與人來評價美女,以及從這些品花集的陸續編纂中,說明明末鑑賞女性的情色風氣是如何的興盛。接著他分析瞭《占花魁》、《秦樓月》、《慎鸞交》、《續金瓶梅》、《女開科傳》等明末清初的戲麯小說,發現作品中雖然反映齣某種程度的實際花案風俗,但也交織瞭不少虛構的成分。此篇論文還指齣,曹雪芹之所以在《紅樓夢》中設置「警幻情榜」,或許與當時流行的品花風俗(花榜)有關。
此外,閤山教授還以民俗學、宗教學的角度考察瞭明清文人與扶乩的關係。這項研究的具體成果首先錶現在〈明清文人與神秘性興趣〉。此篇論文主要對曆來學界尚未釐清的扶乩起源、扶乩的特殊儀式做瞭詳細的考證,接著以豐富的資料呈現明清江南文人異常沉迷扶鸞請仙的風俗以及絡繹齣版的乩仙文學,最後藉由葉紹袁與早逝的愛女葉小鸞、尤侗與瑤宮花史靈交的兩個個例,說明明清文人的精神世界與當時社會思潮及文學的關係。在瞭解明清文人與扶乩之密切關係後,閤山教授繼續在〈《西青散記》的世界〉中,考察瞭《西青散記》薄命佳人賀雙卿的形象與仙女的相似處,並對史震林、趙闇叔等邊緣文人憐憫薄命佳人的心理做瞭細膩的解讀。綜閤這二章,閤山教授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將文學與民俗宗教交相為用,進行層次分明的推衍,其主要目的在為《紅樓夢》乃仙女崇拜小說的推論,預作精心的鋪陳,因為在史震林的世界裏有著根深蒂固的仙凡一體之世界觀、女性觀,而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呈現齣薄命佳人與仙女相互對應的構思。總之,隱藏在兩人背後的文人集體心靈問題是解讀明清文學中不容忽視的關鍵。同時,〈明清文人與神秘性興趣〉一文的學術貢獻不僅在作為解讀《紅樓夢》本質的樞紐而已,也因為此文首度在中國思想文化史與文學史的脈絡下論述晚明文人的宗教修養,至今凡論及明清文學與宗教的論文,幾乎都會提及此篇現行研究。
綜觀《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一書的學術研究特徵,首先可知,此書以資料見長,論文中探討的文本除瞭廣博搜攬戲麯、小說、詩詞、隨筆、詩話、彈詞等文類之外,還傾全力挖掘方誌、斷代史、判牘、宗教文獻等前人未涉及的材料,因此,將此書置之日本漢學界明清文學研究的脈絡中,不難發現,閤山教授研究所突顯的特殊意義並不在文獻版本的考證與田野調查,而是以堅實的文獻基礎,對文本重新進行精讀與詮釋,然後從詩文中抽絲剝繭般追尋作者的生命意義與思想投射,帶齣具規律性的結論,而且無論在資料、選題,還是研究角度上,處處閃爍嶄新的突破,故本書所代錶的不僅是實證性的專門著作,更是日本明清女性文學研究的裏程碑。
其次,閤山教授非常嫻熟過去的研究成果,每篇論文之前幾乎都會迴顧日本學界的研究趨嚮,然後用新的角度來探討舊問題,故多有新解,例如,在節婦烈女論與《紅樓夢》的相關考證中,這種研究傾嚮尤其明顯。另外,值得矚目是,閤山教授研究的重要意義還在於積極採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概念,來詮釋中國文學或者與中國社會文化作比較。例如,在探討明清節婦烈女的殉死風俗時,閤山教授提齣,不妨將女性在明清社__會的處境與古印度寡婦殉夫自焚的風俗(suttee)做一比較。在論述《紅樓夢》女性崇拜的特徵時,閤山教授提示瞭法國現實主義作傢司湯達(Stendhal,一七八三—一八四二)在《戀愛論》中將戀愛分為激情戀愛、趣味戀愛、肉體戀愛、虛榮戀愛的觀點,基於《紅樓夢》女性崇拜的本質與愛護難得的瑰寶、名花極為類似,並追溯過去中國文學中這種美人觀的係譜後,主張《紅樓夢》乃當時追求趣味戀愛到達巔峰的最佳傑作。而這種結閤西方文學思想與中國古典文學的論述方式其實早在一九七七年齣版的張潮《幽夢影》譯注與解說中便齣現瞭端倪。閤山教授指齣盡管明末清初世道人心汙濁混亂,但卻是箴言文學開花的時代,而相當於此時的十七世紀法國,也齣現瞭濛田(一五三三—一五九二)、拉羅什福科(一六三三—一六八○)、拉封丹(一六二一—一六九五)等箴言文學傢。若把此一時期中國的箴言文學與法國相較,不但毫不遜色,而且更能引起東方人的共鳴。可見,閤山教授的研究具廣闊的世界文學視野,也因為如此,其論述無形中展現瞭一般學者難以企及的高度與深度。
總之,在本書中,閤山教授恰如其分的將眾多的研究材料帶入分析框架,藉由貼近明清女性真正的人生與時代的研究方式,引領讀者重新認識明清時代的女性如何與文藝交織齣復雜的樂章。加上其研究方法緊緊扣住錶層文化現象的解構與深層曆史的挖掘,讓讀者深入認識各個文類中女性穩定不變的原型與變相,同時也揭示瞭明清社會文化結構的復雜與多樣,成功的顛覆瞭傳統中國女性乃受害者的形象。以下繼續針對本書處理的重要問題範疇,做簡要的說明。
序(節錄)
就中國史大緻的時代區分來說,唐宋年間發生瞭巨大的社會變化,此後宋、元、明、清這一韆多年來,主導政治與文化的乃齣身中小地主階級的知識份子(士大夫)。而後半部長達五、六百年的明清士大夫社會,由於商人與市民的抬頭以及明末開始因商業、手工業發達,導緻資本主義萌芽,故與宋元相較之下,社會經濟産生瞭極大的轉變。然除此之外,宋元與明清主導政治、文化的依舊是士大夫階層,並無太大的差異。不過,雖然同屬士大夫社會,宋元與明清在文化、藝術、思想等文化層麵上的氣氛,卻有相當大的不同。
其中最大的差異就是宋元重視「理」,屬於主知主義;明清時代,尤其是明代後期,開始變成重視「情」的主情主義文化。宋代以後至元、明中期,「理」的文化較「情」佔優勢;然而自明末開始、清代、乃至中華民國則是「情」的文化比「理」更佔優勢。
明代中期的江南蘇州,已經有徵兆顯現「理」的時代即將轉換成「情」的時代,不過,情的文化真正澎湃興起是在明末,也就是十六世紀中期左右。在此之前,以硃子學等儒學思想為中心的理知主義、道德主義,維持瞭一段很長的時間,然而到瞭明代後期,因為政治腐敗,嚴格的政治、道德約束開始鬆動,當情性一解放,抨擊先前社會以硃子學思維為主的浪潮前僕後繼,於是「情」的文化急速興起,最後終於變成瞭以「情」為優勢的時代。不過,情的錶現方式,因時期的不同,多少有些變化,清初仍帶著明末奔放不羈的情性解放之風,略顯放縱;到瞭清代中期,由於王朝政治與道德上的限製,情逐漸的變得內斂,並且從唯美的情轉換成唯心的情。然而,有清一代並非完全籠罩在「情」的文化之下,「理學」、「考證學」等「理」的文化依然存在,但就整體而言,清代的時代思潮是「情」優於「理」,而且,這個現象一直持續到中華民國。
如上所述,十六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中期,「情」的文化較「理」的文化佔優勢,這段期間長達瞭約四百年。若有人問起以「情」為基礎的明清文化最關心的文學對象為何,筆者一定毫不猶豫的迴答:「女性」。雖然當時許多人對「花」傾注瞭無比的熱情,但歸根究柢,這乃是在關心「女性」的基礎上衍生齣來的現象,因此,「女性」可謂構成明清時代「情」文化的中心。故要理解此一時期「情」的文化,是不可能將「女性」排除在外的。
截至明代後期為止,女性在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存在一直是被忽略的。或者更直接的說,明代中期以前,女性根本是被置之於中國社會文化體製之外的。即使有女性登上曆史的正麵舞颱,那也是極少數的例外,絕大部分的女性,都將其身影隱藏在舞颱背麵。然而,明末以後,女性彷彿突然自舞颱背麵傾巢而齣,成群的齣現在社會文化的前麵,開始強烈的強調其存在。
例如,明清時代齣現瞭幾萬名貞節慘烈的「節婦烈女」。也有幾韆名縱橫詩壇、留下著作的「閨秀詩人」。更有眾多在曆史上留下鮮明足跡的女將軍、從軍女子、女武者、女豪傑等「巾幗英雄」。另外,還有無數纔貌兼備的「薄命佳人」讓這個時代染上哀艷的色彩。而且,明清時代的妓女文化盛極一時,不少名妓與著名文人對等的談戀愛,她們獲得「纔子佳人」的美名,並受時人的稱羨。有遵循女訓書教誨的「賢妻良母」;相反的,也有如「淫詞小說」描寫的放縱情慾的淫蕩女子。上述各種類型的女性群體,大舉登上明清社會文化的正麵舞颱,貫徹其生活型態。以前並非沒有這樣的女性,隻是明清時代與其他時代相較之下,不管質與量,都呈現顯著的差異,可謂劃時代的現象。
毋庸置疑,齣現上述各種類型的女性會給當時的社會文化帶來影響,並促進新變化的産生。例如,明清齣現瞭強烈的欲突破原本封閉、固定的男女關係之現象。在社會地位與身分方麵,雖然不至於顛覆男性優位的封建體製,但在個人方麵,已經縮短瞭曆來男女的差距,男尊女卑的意識變得薄弱,逐漸釀成瞭男女平等的氣氛。尤其在品格與氣概方麵,女性更是優於男性。此外,很多女性在學問、文學甚至武藝等肉體上的能力,皆淩駕於男子之上。女性的存在,在各個方麵越來越重要,於是引發瞭顛覆傳統男尊女卑觀念的地殼變動。隨著女性能力評價的上升,男性的評價相對的下降,世上不爭氣的男子變得醒目,以至於男子的重要越來越薄弱。因此,當我們考察明清的男女關係時,必須特彆注意從明末至有清一代綿延不絕的男性藐視與女性贊美之評論。
明末以後,女性地位之變化並非單靠女性自身的力量而緻。當時男性所發揮的力量亦不容忽視。由於男性文人最重視的文學創作對象是「女性」,他們對女性寄予憐憫、贊賞、崇拜之情,從旁協助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並善意的支援女性能力的擴展。換言之,明清時代的女性得以在社會文化中抬頭,乃女性自身能力與男性背後助力這兩股力量相互交乘的結果。本書基於以上觀點,擷取明清時代社會文化中關於「女性」的各種現象,從各個角度深入考察以「女性」為基礎的明清時代之文化與文學,並將其實際型態、重要因素、特色、意義等作整體的研究。各章的詳細內容有待讀者詳閱每篇論文,在此僅簡單的說明各篇的概要與研究動機。
圖書試讀
筆者認為曆來各種說法中最具學問基礎的,就是把《紅樓夢》當成自傳小說、現實主義小說所進行的研究。亦即主張《紅樓夢》的主題與創作意圖為作者的體驗及反映當時政治社會現實的研究。站在此立場的學者,詳細調查瞭作者曹雪芹及其祖先的事蹟與當時的政治社會狀況,同時,亦不容否認,上述這些問題與《紅樓夢》有何連結之研究,進展地極為快速。尤其是主張自傳派的學者,如鬍適、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研究業績,實屬壯觀。不過,現今不論這種研究如何進展、或者學者們如何努力尋找《紅樓夢》中所影射之人,不僅無法迴答上麵列舉的問題,也難以掌握《紅樓夢》的本質。因為《紅樓夢》的本質更近於虛構小說,所以不能以上述方法去研究它。以至於自傳派的研究越深,事實與作品的矛盾也越深,而當現實與虛構的距離拉大後,彷彿走入迷宮,愈加不知如何是好。我們應該趕快擺脫自傳派的研究方法,重新摸索新的道路。
究竟該如走齣自傳派研究的迷途?首先,必須摒除小說就是以作者為主體來創作的現代小說觀以及小說是根據事實來創作的中國傳統觀念,另外,也不可以一開始就認定《紅樓夢》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總之,我們必須排除先入為主的觀念,重新審視《紅樓夢》作品的世界,並如實的接受清代中期作者的思考模式與創作小說的方法。在這個前提下,首先我們要注意的是《紅樓夢》是在某鞏固的架構下構築齣來的小說。眾所周知,其主要架構如下:
用户评价
《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這個名字,讓我立刻聯想到那些在曆史的長河中,或明或暗閃耀的女性智慧之光。我非常好奇,在明清這樣一個禮教森嚴、男權至上的時代,女性是如何在文學創作的領域中尋找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我期望書中能夠展現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生活背景的女性,她們的文學創作與她們的生存狀態之間有怎樣的聯係?比如,閨閣中的纔女,她們的詩詞是否充滿瞭細膩的情感和對生活的觀察?而一些齣身相對普通的女性,她們的作品又會有怎樣的特點?我特彆希望書中能提供一些具體的史料和文本分析,來佐證作者的觀點,而不是空泛的論述。例如,我很好奇,當時女性文學作品的讀者群體是怎樣的?她們的作品是否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還是更多地被女性群體所欣賞?書中是否會涉及到一些女性與男性文人之間的交流,這種交流對她們的文學創作又産生瞭怎樣的影響?我想從這本書中,看到一個更加立體、更加鮮活的明清女性文學圖景。
评分光是看到《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這個書名,我的思緒就立刻飄嚮瞭那些纔華橫溢卻又被曆史長河掩蓋的女性。我尤其想知道,在明清這個時期,文學創作對於女性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是一種錶達內心世界的齣口,一種對現實社會抗爭的方式,還是一種僅僅為瞭滿足傢族或社交需求的點綴?書中是否會深入剖析女性文學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藝術價值,而不僅僅是羅列作品和作者?我希望作者能夠提供一些具體的個案分析,例如,某位女性作傢是如何在保守的社會環境中,堅持自己的創作風格,或者是如何通過作品來反思和批判當時的社會現象。我也會關注書中對女性文學作品的接受度和傳播機製的探討,比如,在那個時代,女性的作品是否能得到男性的認可?她們的作品是通過怎樣的渠道被讀者接觸到的?有沒有一些女性的作品,因為某些原因而受到壓製或者被遺忘?我想從這本書中獲得更深入的理解,不僅僅是知道有哪些女性作傢,更重要的是理解她們在曆史長河中留下的獨特印記。
评分這本書的名字讓我立刻想到瞭那些纔華橫溢卻又被時代束縛的女性文人,腦海中浮現齣李清照、管道升、薛濤等人的身影,她們如何在男權社會中尋覓創作的自由,又如何將內心的情感與對世界的觀察融入字裏行間?我特彆好奇書中是否會深入探討明清時期女性文學創作的獨特之處,比如在詩詞、小說、戲麯等不同體裁中,女性的聲音是如何被錶達和被接受的。我也會關注作者如何勾勒齣當時女性的日常生活,她們是否能接觸到教育,她們的社交圈子是怎樣的,這些細節是否又反過來影響瞭她們的文學創作。例如,很多女性的詩詞似乎都流露齣一種細膩的情感和對自然的感悟,這與她們相對封閉的生活環境是否有關聯?又或者,一些女性作傢是否會通過筆下的虛構人物來寄托自己的理想和不滿?我希望這本書能提供豐富的史料和細緻的分析,讓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女性的內心世界,理解她們的文學成就不僅僅是纔情的展現,更是她們在特定曆史文化背景下,努力生存和錶達自我的重要方式。
评分我一直對中國古代女性的地位和她們在社會文化中的角色抱有濃厚的興趣,這本書的標題《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恰好觸及瞭這一點。我特彆期待書中能夠展現明清時期女性在文學領域,無論是作為創作者還是作為接受者,所扮演的多樣化角色。我好奇的是,當時社會的哪些因素促進或阻礙瞭女性文學的發展?比如,傢庭教育、婚姻狀況、社會階層等,這些都會不會在書中得到深入的探討?我很想知道,是否有那麼一些女性,她們的文學作品能夠挑戰當時的社會規範,或者至少為後世女性樹立瞭某種榜樣。書中會不會列舉一些具體的女性作傢及其代錶作品,並對她們的創作風格、題材內容進行詳細的解讀?例如,我聽說過一些關於女性小說傢的故事,她們的作品中經常齣現對女性命運的關注和對社會不公的隱喻,我想知道這些是否在明清時期尤為突齣。此外,我也想瞭解,明清時期男性作傢筆下的女性形象,與女性作傢筆下的女性形象,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又反映瞭怎樣的時代特徵和性彆觀念?
评分這本書的名字《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引起瞭我極大的好奇心,特彆是“文學”這個詞,讓我聯想到無數的筆墨丹青,以及隱藏在文字背後的女性身影。我非常希望書中能呈現一些我並不熟悉的女性作傢,她們可能不像李清照那樣名垂韆古,但同樣擁有動人的纔情和獨特的視角。我期待作者能挖掘齣那些被埋沒的文學瑰寶,並為我們講述她們的生平故事和創作經曆。我想知道,在那個男尊女卑的時代,女性是如何獲得創作的資源和機會的?她們的靈感來源是什麼?她們的寫作內容又受到哪些方麵的限製?書中是否會探討一些女性作品的傳播方式?例如,她們的作品是通過傢族內部流傳,還是能夠得到更廣泛的齣版和閱讀?我特彆關注書中是否會涉及女性的文學社群或雅集,女性之間是否能夠相互鼓勵、交流心得,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學生態。如果能有一些關於女性文學作品的解讀,分析其藝術特色和思想內涵,那就更好瞭,這樣我纔能真正理解她們的價值。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