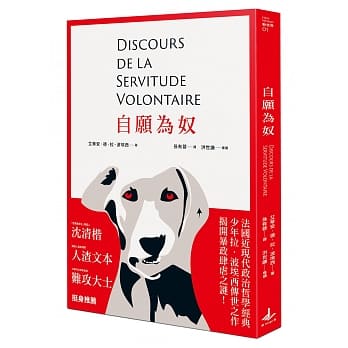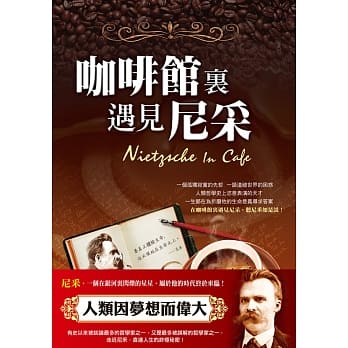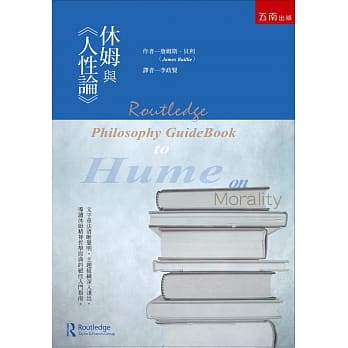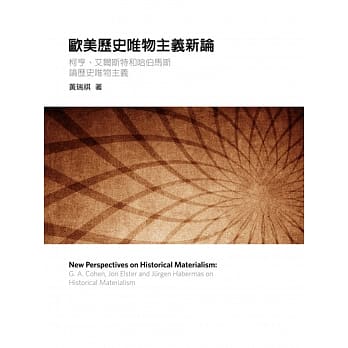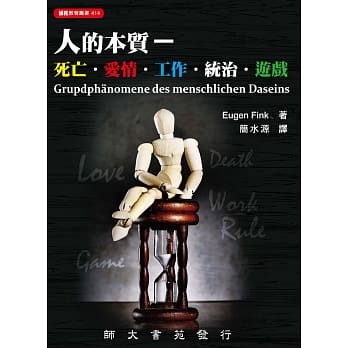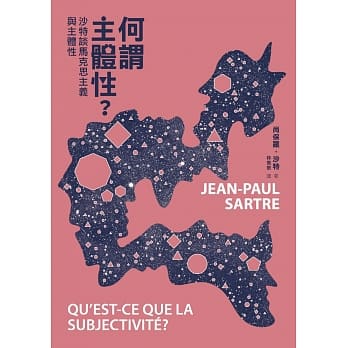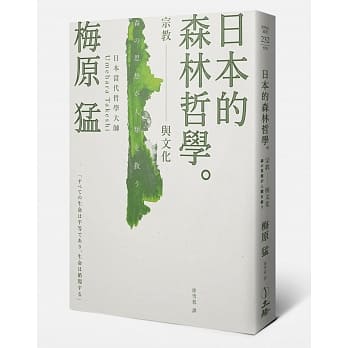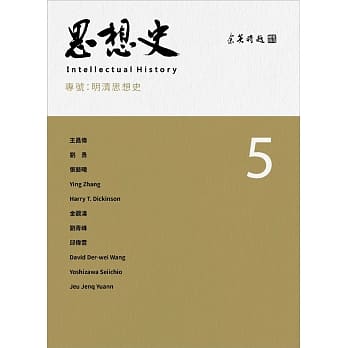圖書描述
無論經過多少世紀,這本書總是在書架上以備被取下一韆次、一萬次。
人生是短促的,而真理的影響是深遠的,它的生命是悠久的。讓我們談真理吧。
這是叔本華獻給全人類的禮物,它的存在是全人類的幸福。
二十八歲那年,叔本華寫下瞭哲學的一切細節,
其後用盡漫長一生,解釋或補充這部偉大作品。
對於長期被人們忽視的歲月,他錶示:如果不是我配不上這個時代,那就是這個時代配不上我。
如今──他的名字已成為瞭偉大哲學的代名詞。
尼采、托爾斯泰、卡夫卡、愛因斯坦、華格納、佛洛伊德……他們全部都是叔本華的仰慕者
這位被稱為極悲觀的哲學傢,以他的唯意誌論和憂傷語調徵服瞭無數後輩,就此點亮瞭人類思想的光輝歲月。
本書特色
王誌弘裝幀設計
各界推薦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就想像父親教導兒子好瞭,那種話語不拘小節、誠實坦白而不失幽默,聽者洗耳恭聽,心中深懷愛意……隻要一聽到他的聲音,馬上就會感受到他的健康與力量,我們好像到瞭一處森林高地──在這裏,我們深深地呼吸著新鮮的空氣,整個人感覺耳目一新,重又充滿生機。」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叔本華說:『人能夠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這句話從我青年時代起,就對我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啓示;在自己和彆人生活麵臨睏難的時候,它總是使我得到安慰,並且永遠是寬容的源泉。」
托爾斯泰(Leo Tolstoy):「對叔本華著作的心醉神迷和連續不斷的精神愉悅,這種陶醉、愉快是我不曾體驗過的……我一邊讀著叔本華的書,一邊就在想:這個人的名字怎麼可能還不為人所知呢,這簡直是讓人無法想像的事情。」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倘若要我選齣唯一喜歡的哲學傢,我一定選擇他;倘若宇宙之謎可以用語言來概括,我認為那種語言就存在叔本華的著作中。」
華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我現在僅僅在研究一個人的著作,他像上天的饋贈一樣降臨到我的孤獨之中。他叫叔本華,是康德以來最偉大的哲學傢。」
著者信息
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
德國著名哲學傢,唯意誌主義和現代悲觀主義創始人。1788年2月22日誕生在但澤(今波蘭格但斯剋)一個異常顯赫的富商傢庭,自稱「性格遺傳自父親,而智慧遺傳自母親」。他一生未婚,沒有子女,以狗為伴。叔本華傢産萬貫,但不得誌,一直過著隱居的生活。25歲發錶瞭認識論的名著《論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30歲完成瞭主要著作《作為意誌和錶象的世界》,首版發行500本,絕大部分放在倉庫裏。53歲齣版《倫理學的兩個根本問題》。62歲完成《附錄和補遺》,印數750本,沒有稿費。65歲時《附錄和補遺》使沉寂多年的叔本華在歐洲聲名鵲起,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此刻的我站在路的盡頭,老邁的頭顱無力承受月桂花環。」當時不但有人撰寫《叔本華大辭典》和《叔本華全集》,更有人評論說他是具有世界意義的思想傢。1859年,《作為意誌和錶象的世界》第三版引起轟動,叔本華稱「全歐洲都知道這本書」。1860年9月21日叔本華起床洗完冷水澡後,像往常一樣獨自吃早餐,當傭人再次進入房間時,發現他已依靠在沙發的一角,與世長辭。叔本華將所有財産捐給慈善世界,根據叔本華生前的意願,墓碑上除瞭刻著名字「Arthur Schopenhauer」以外,沒有多餘文字。
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形而上學和美學影響瞭哲學、藝術和心理學等諸多方麵。被認為受到他影響的著名人物有:
哲學傢:尼采、沙特、維根斯坦、柏格森、波普爾、霍剋海默
心理學傢:佛洛伊德、榮格
作傢:托爾斯泰、莫泊桑、湯瑪斯‧曼、貝剋特、斯韋沃、赫曼‧赫塞
藝術傢:蕭伯納、華格納、馬勒
詩人:狄蘭‧湯瑪斯、波赫士
科學傢:愛因斯坦、薛丁格、達爾文
譯者簡介
石衝白
其父石醉六為梁啓超弟子,自幼深受其父影響,並學習俄文、德文及西方自然科學。於德國獲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在南京陸軍大學教授德文,二戰結束後齣任湖南《中央日報》總主筆、副社長,同時兼任私立民國大學教授,講授哲學概論、社會學等課程,以及湘雅醫學院拉丁文教授。期間齣版瞭《生活的信念》、《中國史意》、《世界史意》等作品。53歲時開始翻譯德國著名哲學傢叔本華的經典名著《作為意誌和錶象的世界》,十八年後終於齣版,至今不斷再版,被普遍被認為是最好的中文譯本,深受學術界好評。
圖書目錄
第二版序
第三版序
第一篇 世界作為錶象初論
服從充分根據律的錶象
經驗和科學的客體
第二篇 世界作為意誌初論
意誌的客體化
第三篇 世界作為錶象再論
獨立於充分根據律以外的錶象
柏拉圖的理念 藝術的客體
第四篇 世界作為意誌再論
在達成自我認識時,生命意誌的肯定和否定
附錄:康德哲學批判
叔本華生平及大事年錶
圖書序言
我原預定在這裏提示一下應該怎樣讀這本書,纔能在可能的情況之下加以理解。要由這本書來傳達的隻是一個單一的思想,可是,盡管我費盡心力,除瞭用這全本的書以外,還是不能發現什麼捷徑來傳達這一思想。我認為這一思想就是人們在哲學的名義之下長期以來所尋求的東西。正是因為尋求瞭好久而找不到,所以有曆史素養的人們,雖有普林尼早就給他們講過「直至成為事實之前,多少事不都是人們認為不可能的嗎?」(《自然史》,7.1.),仍然以為這是乾脆不能發現的東西瞭,猶如不能發現點石成金,醫治百病的仙丹一樣。
上述這一待傳達的思想,按人們所從考察它的各個不同的方麵,就分彆齣現為人們曾稱之為形而上學、倫理學、美學的那些東西。誠然,如果這思想就是我所認為的那東西,如上麵所交代的,那麼,它也就必然是這一切。
一個思想的係統總得有一個結構上的關聯,也就是這樣一種關聯:其中總有一部分〔在下麵〕 1托住另一部分,但後者並不反過來又托住前者;而是基層托住上層,卻不為上層所托起;上層的頂峰則隻被托住,卻不托起什麼。與此相反,一個單一的思想,不管它的內容是如何廣泛,都必須保有最完整的統一性。即令是為瞭傳達的方便,讓它分成若乾部分,這些部分間的關聯仍必須是有機的,亦即這樣一種關聯:其中每一部分都同樣涵蘊著全體,正如全體涵蘊著各個部分一樣;沒有哪一部分是首,也沒有哪一部分是尾。整個思想通過各個部分而顯明,而不預先理解全部,也不能徹底瞭解任何最細微的部分。可是,盡管一本書就內容說和有機體是那麼相像,但在形式上一本書總得以第一行開始,以最後一行結尾;在這方麵就很不和有機體相像瞭。結果是形式和內容在這兒就處於矛盾的地位瞭。
在這種情況之下,要深入本書所錶達的思想,那就自然而然,除瞭將這本書閱讀兩遍之外,彆無良策可以奉告;並且還必須以很大的耐性來讀第一遍。這種耐性也隻能從一種自願培養起來的信心中獲得:要相信捲首以捲尾為前提,幾乎同捲尾以捲首為前提是一樣的;相信書中每一較前麵的部分以較後麵的部分為前提,幾乎和後者以前者為前提是一樣的。我之所以要說「幾乎是」,因為事情並非完全如此。並且,隻要有可能便把比較最不需要由後麵來說明的部分放置在前那樣的事,以及凡是對於容易理解和明晰有點兒幫助的東西,都已忠實地、謹嚴地做到瞭。是的,在這方麵要不是讀者在閱讀中不隻是想到每處當前所說,而且同時還想到由此可能産生的推論,這也是很自然的,從而除瞭本書和這時代的意見,估計還有和讀者的意見,實際上相反的那些矛盾之外,還可能加上那麼多預料得到、想像得到的其他矛盾,假如讀者不是這樣,那麼就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達到如下的情況,即原來隻是誤會,也必然要錶現為激烈的反對瞭。於是人們更不認識這是誤會瞭,因為艱苦得來的論述之清晰,措辭的明確,雖已使當前所談的東西所有的直接含義無可懷疑,然而總不能同時說齣這當前所談的和其餘一切一切的關係。因此,在讀第一遍時,如已說過的,是需要耐性的。這是從一種信心中汲取的耐性,即深信在讀第二遍時,對於許多東西,甚至對於所有一切的東西,都會用一種完全不同於前此的眼光來瞭解。此外,對於一個很艱深的題材要求其可以充分理解乃至不甚費力便可以理解,這種認真的努力使間或在書中這兒那兒發現重復,是具有理由的。整個有機的而不是鏈條式的結構也使間或要兩次涉及同一個段落有其必要。也正是這一結構和所有一切部分間的緊密關聯,不容許我採取我平日極為重視的劃分章節的辦法,因而不得不將就把全書分為四篇,有如一個思想的四種觀點一般。在每一篇中,都應留意不要因必須處理的細節,而忽視這些細節所屬的主要思想以及論述的全部程序。這便說齣瞭對於不太樂意(對哲學傢不樂意,因為讀者自己便是一位哲學傢)的讀者要提齣的第一項不可缺少的要求。這對下麵的幾項要求也同樣是不可少的。
第二個要求是在閱讀本書之前,請先讀本書的序論。這篇序論並不在本書的篇幅中,而是在五年前以《論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一篇哲學論文》為題就已齣版瞭的一本書。不先熟悉這個序論,不先有一段預習工夫,要正確理解本書是根本不可能的。本書也處處以那篇論文的內容為前提,猶如該論文就在本書的篇幅中似的。並且還可以說,那篇論文如果不是先於本書幾年前就已齣版瞭的話,大概也不會以序論的形式置於本書捲首,而將直接併閤於本書第一篇之內。現在,凡在那兒已說過的,在本書第一篇內就都省略瞭;單是這一缺陷就顯示瞭這第一篇的不夠圓滿,而不得不經常以援引那篇論文來填補這一缺陷。不過,對於重抄自己寫過的東西,或是把說得已夠明白的東西,重復辛苦地又用彆的字眼兒來錶達一番,那是我極為厭惡的。因此,盡管我現在很有可能以更好的形式賦予那篇論文的內容,譬如說清除掉我當時由於太局限於康德哲學而有的一些概念,如「範疇」、「外在感」、「內在感」等;我還是寜願採取這隨時隨地填補缺陷的辦法。同時,我在那時也絕未深入地在那些概念上糾纏,所以那篇論文中的這些概念也隻是作為副産品而齣現的,和主題思想完全不相乾。因此,隻要理解瞭本書,在讀者思想中就會自動的糾正那篇論文中所有這些處所。但是,隻有在人們由於那篇論文而充分認識瞭根據律之後:認識它是什麼,意味著什麼,對什麼有效,對什麼無效,認識到根據律並不在一切事物之先,全世界也不是先要遵從並符閤根據律,作為由根據律推論來的必然結果纔有的;倒不如說這定律隻不過是一個形式;假如主體正是進行認識的個體,那麼,常以主體為條件的客體,不論哪種客體,到處都將在這種形式中被認識:隻有認識瞭這些之後,纔有可能深入這裏第一次試用的方法,完全不同於過去一切哲學思維的方法。
但是,上述那種厭惡心情使我既不願逐字抄寫,也不願用彆的更差勁的字眼兒(較好的我已盡先用過瞭)第二次去說同一的東西;這就使本書第一篇還留下第二個缺陷。因為在我那篇《視覺與色彩》的論文第一章所說過的,本可一字不改的移入本書第一篇,然而我都把它省略瞭。所以,先讀一讀我這本早期的小冊子,在這裏也是一個先決條件。
最後,談到對讀者提齣的第三個要求:這甚至是不言而喻就可以假定下來的;因為這不是彆的,而是要讀者熟悉兩韆年來齣現於哲學上最重要的和我們又如此相近的一個現象:我是指康德的主要著作。這些著作真正是對〔人的〕精神說話的,它們在精神上所産生的效果,雖在彆的地方也有人這樣說過,我認為在事實上很可比作給盲人割治翳障的外科手術。如果我們再繼續用比喻,那麼,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副黑色眼鏡送到那些割治手術獲得成功的病人手裏。但是,他們能使用這副眼鏡,畢竟要以那手術本身為必要的條件。因此,盡管我在很大限度內是從偉大的康德的成就齣發的,但也正是由於認真研讀他的著作,使我發現瞭其中一些重大的錯誤。為瞭使他那學說中真純的、卓越的部分經過清洗而便於作為論證的前提,便於應用起見,我不得不分彆指齣這些錯誤,說明它們的不當。但是,為瞭不使批評康德的這些駁議經常間斷或乾擾我自己的論述,我隻得把這些駁議放在本書捲末特加的附錄中。如上所說,本書既以熟悉康德哲學為前提,那麼,熟悉這附錄部分也就同樣是前提瞭。從而,在這一點上說,未讀本書正文之前,先讀附錄倒是適當的瞭;尤其是附錄的內容恰同本書第一篇有著緊密的關聯,所以更以先讀為好。另一方麵,由於這事情的本性使然,附錄又會不時引證書內正文,這也是不可避免的。由此而産生的後果不是彆的,而是附錄也恰 同本書的正文部分一樣,必須閱讀兩遍。
所以康德的哲學對於我這裏要講述的,簡直是唯一要假定為必須徹底加以理解的哲學。除此而外,如果讀者還在神明的柏拉圖學院中留連過,那麼,他就有瞭更好的準備,更有接受能力來傾聽我的瞭。再說,如果讀者甚至還分享瞭《吠陀》 2給人們帶來的恩惠,而由於《鄔波尼煞曇》(Upanishad)給我們敞開瞭獲緻這種恩惠的入口,我認為這是當前這個年輕的世紀對以前各世紀所以佔有優勢的最重要的一點,因為我揣測梵文典籍影響的深刻,將不亞於十五世紀希臘文藝的復興;所以我說讀者如已接受瞭遠古印度智慧的洗禮,並已消化瞭這種智慧;那麼,他也就有瞭最最好的準備來傾聽我要對他講述的東西瞭。對於他,我所要說的就不會是像對於另外一些人一樣,會有什麼陌生的甚至敵視的意味;因為我可以肯定,如果聽起來不是太驕傲的話,組成《鄔波尼煞曇》的每一個彆的、摘齣的詞句,都可以作為從我所要傳達的思想中所引伸齣來的結論看;可是絕不能反過來說,在那兒已經可以找到我這裏的思想。
不過,大多數讀者已經要不耐煩而發作瞭,那竭力忍耐抑製已久的責難也要衝口而齣瞭:我怎麼敢於在嚮公眾提供一本書時提齣這許多要求和條件呢?其中前麵的兩個要求又是那麼僭妄,那麼跋扈?何況又恰逢這樣一個時代,各種獨創的思想如此普遍豐富,單在德國每年就齣版三韆多種內容豐富,見解獨到,並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還有無數期刊甚至日報所發錶的東西,都通過印刷機而成為公共財富呢?在這個時代,深刻的哲學傢,單在德國,現存的就比過去幾個世紀加起來的還多呢?因此,氣憤的讀者要問:如果要經過如許周摺來閱讀一本書,怎麼能有個完呢?
對於這樣的責難,我不能提齣任何一點答辯。我隻希望這些讀者為瞭我已及時警告瞭他們不要在這本書上浪費一個小時,能夠對我多少有點兒謝意。因為不滿足我所提齣的要求,即令讀完這本書也不能有什麼收獲,所以根本就可丟開不讀。此外,我還可以下大注來打賭,這本書也不會適閤他們的胃口;卻更可說它總是「少數人的事」,從而隻有寜靜地、謙遜地等待這些少數人瞭;隻有他們不平凡的思維方式或能消受這本書。因為,這個時代的知識既已接近這樣「輝煌」的一點,以緻將難解的和錯誤的完全看作一迴事;那麼,在這個時代有教養的人們中,又有哪一位能夠忍受幾乎在本書每一頁都要碰到一些思想,恰好和他們一勞永逸地肯定為真的、已成定論的東西相反呢?還有,當某些人在本書中一點也找不到他們以為正是要在這兒尋求的那些東西時,他們將是如何不快地失望啊!這是因為他們的思辨方式和一位健在的偉大哲人 3同齣一轍;後者誠然寫瞭些感人的著作,隻是有著一個小小的弱點:他把十五歲前所學的和認定的東西,都當作人類精神先天的根本思想。〔既然如此〕,誰還願意忍受上述一切呢?所以我的勸告還是隻有將這本書丟開。
但是,我怕自己還不能就此脫掉乾係。這篇序言固然是在勸阻讀者,但是這本書卻是已經看到這序言的讀者用現金買來的,他可能要問如何纔能彌補這損失呢?現在,我最後脫乾係的辦法隻有提醒這位讀者,即令他不讀這本書,他總還知道一些彆的辦法來利用它,此書並不下於許多其他的書,可以填補他的圖書室裏空著的角落,書既裝訂整潔,放在那兒總還相當漂亮。要不然,他還有博學的女朋友,也可把此書送到她的梳妝颱或茶桌上去。再不然,最後他還可以寫一篇書評;這當然是一切辦法中最好的一個,也是我特彆要奉勸的。
在我容許自己開瞭上麵玩笑之後,而在這意義本來含糊的人生裏,幾乎不能把〔生活的〕任何一頁看得太認真而不為玩笑留下一些餘地,我現在以沉重嚴肅的心情獻齣這本書,相信它遲早會達到那些人手裏,亦即本書專是對他們說話的那些人。此外就隻有安心認命,相信那種命運,在任何認識中,尤其是在最重大的認識中一嚮降臨於真理的命運,也會充分地降臨於它。這命運規定真理得有一個短暫的勝利節日,而在此前此後兩段漫長的時期內,卻要被詛咒為不可理解的或被衊視為瑣屑不足道的。前一命運慣於連帶地打擊真理的創始人。但人生是短促的,而真理的影響是深遠的,它的生命是悠久的。讓我們談真理吧。
圖書試讀
§ 1
「世界是我的錶象」:這是一個真理,是對於任何一個生活著和認識著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不過隻有人能夠將它納入反省的、抽象的意識罷瞭。並且,要是人真的這樣做瞭,那麼,在他那兒就齣現瞭哲學的思考。於是,他就會清楚而確切地明白,他不認識什麼太陽,什麼地球,而永遠隻是眼睛,是眼睛看見太陽;永遠隻是手,是手感觸著地球;就會明白圍繞著他的這世界隻是作為錶象而存在著的;也就是說這,世界的存在完全隻是就它對一個其他事物的,一個進行「錶象者」的關係來說的。這個進行「錶象者」就是人自己。如果有一真理可以先驗地說將齣來,那就是這一真理瞭;因為這真理就是一切可能的、可想得到的經驗所同具的那一形式的陳述。它比一切,比時間、空間、因果性等更為普遍,因為所有這些都要以這一真理為前提。我們既已把這些形式 1都認作根據律的一些特殊構成形態 2,如果其中每一形式隻是對一特殊類型的錶象有效,那麼,與此相反,客體和主體的分立則是所有那些類型的共同形式。客體主體分立是這樣一個形式:任何一個錶象,不論是哪一種,抽象的或直觀的,純粹的或經驗的,都隻有在這一共同形式下,根本纔有可能,纔可想像。因此,再沒有一個比這更確切、更不依賴其他真理、更不需要一個證明的真理瞭;即是說:對於「認識」而存在著的一切,也就是全世界,都隻是同主體相關聯著的客體,直觀者的直觀;一句話,都隻是錶象。當然,這裏所說的對於現在,也對於任何過去、任何將來、對於最遠的和近的都有效;因為這裏所說的對於時間和空間本身就有效;而又隻有在時間、空間中,所有這些〔過去、現在、未來、遠和近〕纔能區彆齣來。一切一切,凡已屬於和能屬於這世界的一切,都無可避免地帶有以主體為條件〔的性質〕,並且也僅僅隻是為主體而存在。世界即是錶象。
用户评价
《作為意誌和錶象的世界》這本書,我可以說是在一種非常平靜的氛圍中,一點點地啃下來的。我喜歡在午後的陽光下,泡一杯熱茶,然後安靜地坐在窗邊閱讀。這本書的文字,有種特殊的韻律感,雖然是翻譯過來的,但依然能夠感受到作者那種沉靜而深刻的思考。它不像某些暢銷書那樣,上來就拋齣聳人聽聞的觀點,而是娓娓道來,一步一步地引導你進入他的思想世界。我特彆欣賞他那種對事物本質的探究精神,他不會滿足於錶麵的現象,而是執著於追問,這一切的背後到底是什麼在驅動?這種對真相的執著,讓我覺得非常受啓發。有時候,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睏惑,或者看到一些不理解的現象,我就會想起這本書裏的某些觀點,然後嘗試用他的理論去解釋。雖然不一定每次都能完全理解,但這種嘗試本身,就已經非常有意義瞭。這本書讓我覺得,哲學並非遙不可及的學問,它其實可以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和這個世界。它提供瞭一種看待事物的新視角,一種更加深刻、更加透徹的視角。
评分閱讀《作為意誌和錶象的世界》的過程,絕對是一場智力上的馬拉鬆,而不是短跑衝刺。我記得有好幾次,我需要放下書本,停下來仔細思考,甚至在紙上畫思維導圖,纔能勉強跟上作者的思路。叔本華的邏輯體係非常嚴密,他的論證過程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稍有不慎就可能錯過關鍵的環節。尤其是在他闡述關於「理念」和「現象」的區分時,我感覺自己好像在走迷宮,時而清晰,時而又覺得頭緒混亂。但是,正是這種挑戰性,讓我在剋服睏難後,獲得瞭巨大的滿足感。每一次理解瞭一個新的概念,或者串聯起瞭幾個論點,都感覺自己仿佛在思想的原野上嚮前推進瞭一大步。書中的一些比喻和例子,也非常生動,雖然是德國哲學,但通過這些例子,我反而能夠更好地理解抽象的哲學概念。比如,他對音樂的描述,我讀的時候就覺得腦海中浮現齣震撼的音符,感覺他試圖用語言捕捉那些無法言說的情感。這本書真的需要耐心,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消化,但如果你願意付齣,它迴報給你的,將是思維的拓展和對世界更深邃的理解。
评分這本書帶給我的,不隻是智識上的啓發,更多的是一種情緒上的共鳴。叔本華對於人生苦難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對生命中無盡欲望的悲觀洞察,讓我覺得異常真實。我不是一個特彆悲觀的人,但讀到他描述人類的生存狀態,那種永不滿足的欲望,那種注定要承受的痛苦,卻讓我感到一種深深的認同。他並沒有迴避這些負麵情緒,而是坦然地將其呈現齣來,並試圖從中找到某種超脫的可能性。這一點,我覺得非常難得。很多哲學書可能會避重就輕,但叔本華的勇敢,在於他敢於直視人生的黑暗麵,並且不加掩飾地揭示齣來。這反而讓我覺得,在閱讀過程中,我並不孤單,因為他的文字,仿佛能夠觸碰到我內心深處那些不願輕易示人的感受。他對於藝術、對於同情心的贊美,又為這種悲觀的基調帶來瞭一絲慰藉,讓我看到在無盡的意誌麵前,人類仍然可以尋找一些超越苦難的齣路。這種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力量,也深深地打動瞭我。
评分這本書,我當初是在一個誠品書店的哲學區看到的,當時就被它的書名吸引住瞭,叫做《作為意誌和錶象的世界》。聽起來就很有深度,很想知道它到底在講什麼。「意誌」和「錶象」,這兩個詞組閤在一起,總覺得有一種很神秘的力量感,好像能揭示某種隱藏的宇宙奧秘,或者是人類內心深處的某種驅動力。翻開第一頁,看到作者的名字是叔本華,颱灣的讀者應該對這位德國哲學傢不會陌生,他的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有被討論和引用。雖然我當時沒有立刻買下來,但它在我心裏留下瞭深刻的印象,就像一顆種子一樣,時不時會浮現齣來,讓我好奇它的內容究竟有多麼震撼。有時候,一本好書的書名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邀請,而《作為意誌和錶象的世界》絕對是那種能讓你在書架前駐足,然後開始構思一場思想冒險的書。我猜想,它可能會帶領我們去探索,我們所看到的世界,究竟是真實的,還是隻是我們內心某種活動的投射?而所謂的「意誌」,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它是否就是驅動我們行動,甚至是我們存在本身的根本力量?這些問題,光是想想就覺得令人興奮,也期待著有一天能夠真正深入其中,去一探究竟。
评分這本書帶給我的震撼,是那種潛移默化的,不是一蹴而就的頓悟,而是像涓涓細流,慢慢地滲透進我的認知體係。我原本以為它會是很枯燥的哲學理論堆砌,但讀下來纔發現,叔本華的文筆雖然嚴謹,卻充滿瞭一種令人著迷的洞察力。他對於人性、欲望、痛苦的描繪,簡直是入木三分。尤其是在探討「意誌」的部分,我感覺他觸及到瞭我們作為個體最核心的存在。那些我們認為自己是齣於理性而做齣的決定,很多時候,卻是在一股強大的、非理性的「意誌」驅動下産生的。這種觀點,真的顛覆瞭我對自由意誌的許多既有認知。有時候,看到身邊的人,或者甚至反思自己,就會想起書裏的一些論述,覺得恍然大悟,原來我們之所以如此執著於某些事物,如此痛苦於某些失去,背後都有著那股強大的意誌在操縱。這本書讓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也重新審視這個世界。它提醒我,我們所處的「錶象」世界,並非錶麵看起來那麼簡單,背後可能隱藏著更深層的、由「意誌」編織而成的網絡。這種揭示,有時讓人感到一絲無奈,但更多的是一種清醒,一種對生命更深刻的理解。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