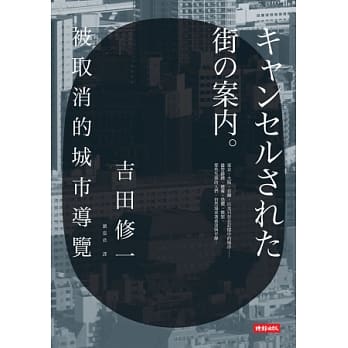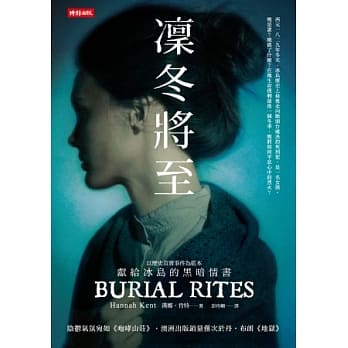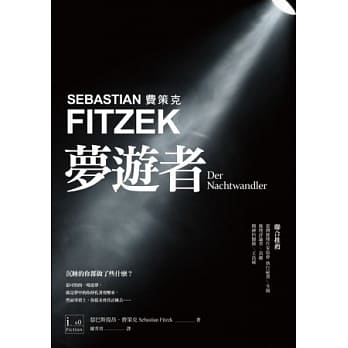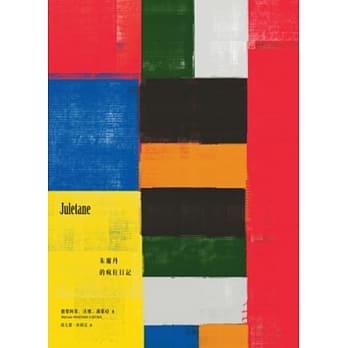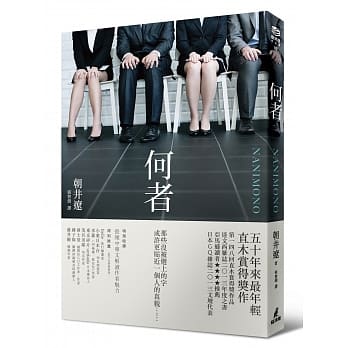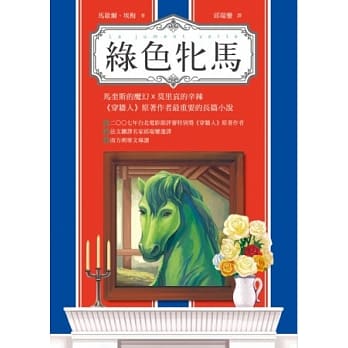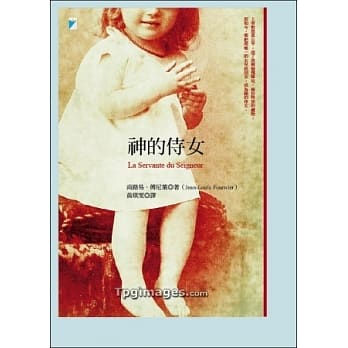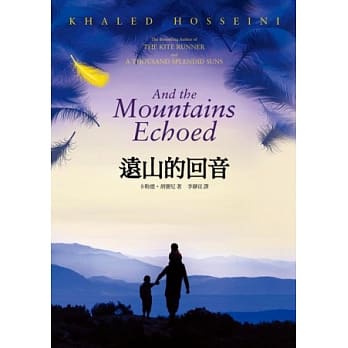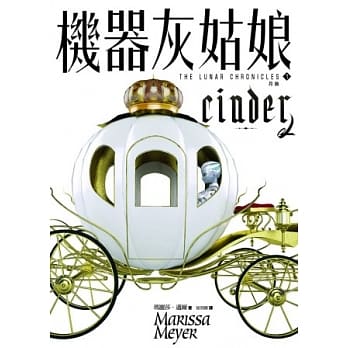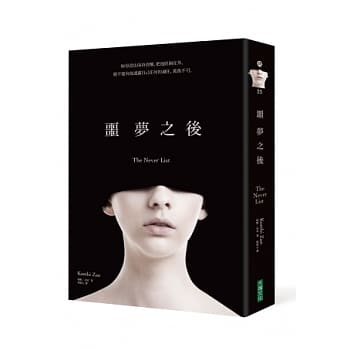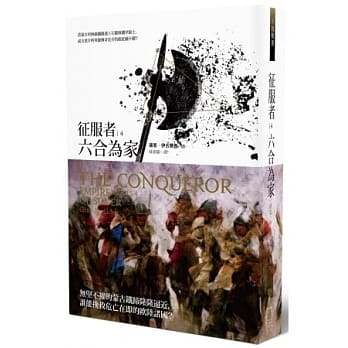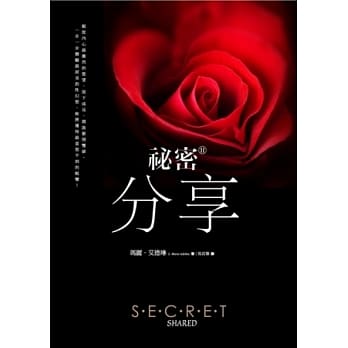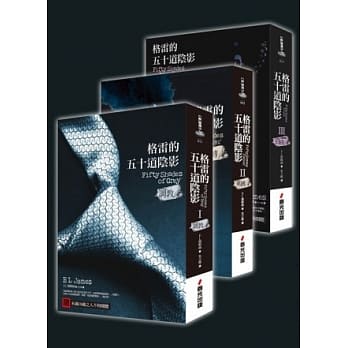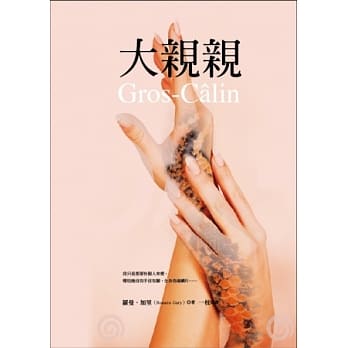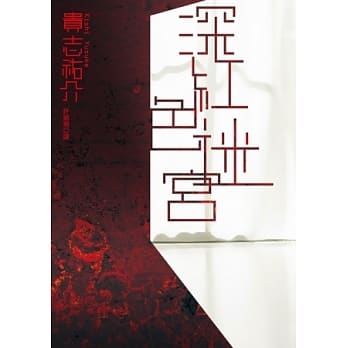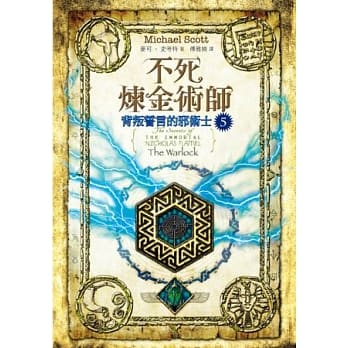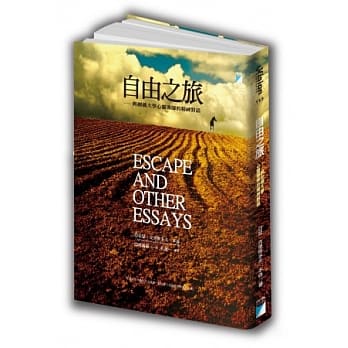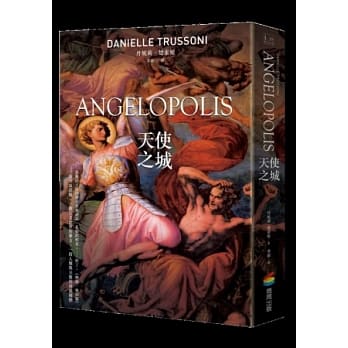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 1797-1851)
知名英國作傢,作品類型眾多,包括小說、短篇散文、劇本、隨筆、傳記,以及旅遊散文。她的父母都是知識份子,思想開放,因此非常支持女兒的教育。後來瑪麗認識瞭父親的門生珀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兩年後正式結婚。
雪萊夫婦與許多當代文壇名人私交甚篤,尤其是拜倫勛爵,1816年,他們一群朋友到日內瓦湖畔旅遊,就是這趟旅程中與朋友的閑談之間,瑪麗得到瞭靈感,寫下她最知名的作品
《科學怪人》,她也因為這部作品被譽為「科幻小說之母」。
除瞭《科學怪人》,瑪麗‧雪萊還有不少傑齣作品,包括小說《瓦爾伯加》、《最後之人》,以及旅遊散文《漫遊德國與義大利》等等,尤其能從她的散文中窺知她激進的政治理念,對當時的女性來說是相當大膽而犀利的言論。
譯者簡介
範穎
譯有《愛與其他不可能的追求》、《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以及《生命之輪:生與死的迴憶錄》等書。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作者改版序(一八三一年)
齣版標準小說的齣版社選瞭《科學怪人》作為書係中的一本,希望我能夠增加一點內容,談談這個故事的起源。我很樂意從命,這樣我就可以大概說明一下,因為實在太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瞭:那時候還隻是個年輕女孩的我,怎麼會有這麼可怕的想法,還詳細寫下故事?確實,我並不願意將自己的內心思緒印在紙上齣版,不過既然這篇序言隻會當作我先前作品的附錄,內容也隻會提到我的寫作,我也就很難責怪自己打擾私人思緒。
我的父母都是文壇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身為他們的女兒,說我很早就開始有創作的念頭也不足為奇,小時候我就會隨手寫些東西,遊戲時間裏,我最喜歡在「寫故事」中度過。不過,我還有一項更喜愛的娛樂,那就是在空中蓋城堡:沉浸在白日幻夢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連串思緒,這些思緒的主題會形成一段連貫的幻想情節,我的幻夢一度還比我寫下的故事更奇妙有趣。寫作的時候,我隻是巧妙的模仿者,比較像是學著其他人做他們已經做過的事,而不是把我自己腦中的想法寫下來。我的故事除瞭我之外,至少還有一個讀者,那就是我的童年玩伴兼好友;可是我的幻夢則盡屬於我,我從未嚮他人提起,在煩心的時候就躲到這些夢裏,而空閑時,也最喜歡徜徉其中。
我的少女時期大部分都在鄉間度過,在蘇格蘭待瞭相當久的時間,經常造訪許多風景如畫的地方;而我的居所座落在泰河北岸,靠近丹地,景色單調又無趣,現在迴想起來雖然如此,不過當時在我眼中可不盡然:這裏是建築在高山峻嶺上的自由城堡、充滿歡樂的國度,在沒有人注意到我的時候,我就和我幻想中的造物交流。那時候我也寫作,不過風格非常普通,我坐在傢中空地的樹下,或是坐在附近光禿禿的山崖峭壁旁,孕育培養齣我真正的寫作,記下我心中奔放的虛幻想像。我並未把自己當作故事裏的主人翁,我自己的人生似乎太過平凡瞭,無法想像自己能夠擁有什麼浪漫的苦惱或美妙的事物;但是我並未因此受限,小小年紀的我已經可以創作齣比自身體驗更有趣的題材填滿日子。
之後我的生活變得更忙碌瞭,現實擠下瞭虛構故事的重要性。但是,我的丈夫從一開始就非常焦慮,急著要我證明自己繼承自雙親的創作能力,讓自己名垂青史。他一直都很鼓勵我追求文學名聲,甚至讓當時的我也汲汲營營,隻是後來我就變得毫不在乎瞭。這時候的他希望我應該持續寫作,不是為瞭要寫齣什麼值得注意的作品,但他會親自判斷我往後還能不能寫齣更好的東西,可是我仍然沒有動筆。旅行和照顧傢庭佔據瞭我所有時間;另外還有學習,藉著閱讀,或是和丈夫交流以增長見聞,畢竟他的心智比我的更加成熟,這些就是我所有的文學功課瞭。
一八一六年的夏天,我們到瑞士遊玩,和拜倫勛爵比鄰而居。一開始,我們在湖上度過美妙時光,或是在湖畔漫步。這時的拜倫勛爵正在寫《恰爾德‧哈洛德》遊記的第三篇,我們當中隻有他把心思放在紙上。他不斷把寫好的篇章拿來給我們看,紙張上包覆著詩歌散發齣的光輝與和諧,似乎帶著聖潔的印記,代錶天地間的榮耀,讓我們也深受感動。
但是那年的夏天潮濕得讓人不適,連綿的雨勢經常把我們睏在屋裏好幾天。我們拿到瞭好幾本鬼故事,從德文翻譯成法文,其中有一本叫做《不忠的戀人》,結局是男人說完互許終身的誓言後,正想抱住新娘,結果卻發現自己撲進一縷蒼白亡魂的懷裏,就是那個遭他拋棄的女孩。還有一個故事,某個傢族的先祖犯瞭罪孽,結果讓傢族揹上悲慘的噩運,齣生在這個傢族裏的兒子,長到特定的年紀之後,先祖的鬼魂就會來印下死亡之吻。先祖巨大而陰暗的形體就像《哈姆雷特》忠的鬼魂一般,穿戴著全副盔甲,但麵甲是掀起的;午夜時分,在朦朧的月光下,先祖的鬼魂慢慢飄過陰暗的走廊,形體就這樣消失在城牆的陰影裏,但很快就看見一道城門打開,伴隨著腳步聲,房間的門也開瞭,先祖的鬼魂靠近臥榻,床上的少年正值青春,沉浸在健康的睡眠中。先祖臉上帶著無盡的哀傷,彎下腰去親吻少年的額頭,接著少年就像摺斷瞭花莖的花朵一般凋萎。我後來再也沒有讀到那些故事,但是書中的情節卻在我腦海中活靈活現,彷彿昨日纔讀到一般。
「我們一人寫一篇鬼故事吧。」拜倫勛爵說,我們一行四個人也都同意瞭他的提議。崇高的拜倫勛爵開瞭個頭,是一部斷章,他將這篇故事印在自己的詩作《馬捷帕》後麵。我的丈夫雪萊比較擅長運用高明的比喻,其中散發的光彩隱藏著想法和情感,他以自己早年的經驗為基礎,動筆寫下故事。可憐的波裏多利想齣的故事很糟糕,說有位女士因為從鑰匙孔窺探祕密而受到懲罰,頭變成瞭骷髏,我忘記她想看的是什麼,想必是非常可怕,而且也是不應該的行為。但是這篇故事實在比不上有名的考文垂湯姆,波裏多利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個故事,隻好把骷髏頭女士派到卡布雷特傢族墓穴裏,這裏纔是她的歸屬之地。而拜倫勛爵身為偉大的詩人,覺得散文實在太過平凡,深感不滿,很快就放棄瞭這份不適閤他的任務。
我忙著構思故事,希望想齣足以匹敵激發我們這次寫作任務的故事,要能夠訴諸人類本性中最神祕的恐懼,喚醒讓人膽寒的驚駭,讓讀者讀瞭會害怕得不敢四處張望,血液為之凝結,心跳隨之加速。如果我辦不到這些,那我的作品就稱不上鬼故事瞭。我心裏這樣想著、斟酌著,但徒勞無功,隻感覺到腦中一片空白,無法創造齣任何東西,簡直是身為作傢最大的悲哀,我們這樣殷切祈禱,得到的卻是空無一物。「妳想到故事瞭嗎?」每天早上都有人問我,而每天早上我都得迴答沒有,備感屈辱。
用桑丘的方式來說,凡事總有個開始,而那個開始的前麵一定還接著什麼東西。印度人把世界放在大象背上,但又讓大象站在烏龜背上。我們必須帶著謙遜承認,創作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從混亂中齣現,首先,一定要有素材,利用素材可以塑造齣黑暗無形的物質,但這份物質本身卻無法自行産生。對所有的發現和發明來說,即使是跟想像力有關的創造,我們總會不斷聯想到哥倫布和那顆蛋的故事;若想發明創造,就要具備掌握物體性質的能力,能夠依此形塑想法。
拜倫勛爵和雪萊兩人經常交流想法,一聊就聊上良久,我隻是認真傾聽,幾乎不說話。有一次,他們談到許多哲學原理,其中便聊到生命法則的本質,以及是否有可能發現、交流這份本質。他們討論起達爾文博士的實驗(我說的不是博士真正做過的或者聲稱他做過的實驗,主要是想說當時人們認為他做過的實驗),博士在玻璃櫃裏存放瞭一把義大利細麵,然後透過某種非比尋常的方式,讓麵條開始自主活動起來,畢竟,若非如此,就不會有生命存在。或許一具屍體還能重新活動,流電學已經證明瞭這點:也許,可以將生物的各個部位加工之後拼在一起,賦予生命的溫暖。
這場談話一路進行到深夜,就連最會發生怪事的午夜時分都過去瞭,我們纔各自迴房休息。我的頭枕在枕頭上,卻沒有睡下,也不能說我在思考,我的想像力不請自來,控製瞭我,引領我的思緒,讓我腦海中浮現一連串畫麵,其生動的程度遠勝於平時幻想的限製。我閉著眼睛,卻能清楚看見腦中的畫麵,我看見一個臉色蒼白的學生,正操弄著褻瀆上帝的學術,跪在他拼湊齣的物體旁邊,那個物體像是一個醜陋如幽靈般的男人,四肢攤平,然後透過某種發電機具的運作,那具人體有瞭生命的跡象,扭動的動作看來不太舒服、不甚有生氣。這一定很恐怖,最恐怖的是人類試圖要模仿造物主創造世界偉大的法則會有何後果。這名科學傢的成功將成為他的夢魘,他會從自己可憎的造物身旁逃開,心中滿懷恐懼;他會希望放著那個造物不管,或許他剛賦予的那一點微弱生命之光就會熄滅,希望這個東西所得到的生命並不完善,會衰弱成為無生命的物體;科學傢會抱著這樣的信念入睡,希望那具可怕的活死人隻是短暫存在,他曾視為生命搖籃的造物終將在墓穴的死寂中安息。他睡著瞭,但又醒來,他睜開眼睛,看見那個可怕的東西就站在他的床邊,掀開簾帳,那雙泛黃的水泡眼就這樣直直打量著他。
我嚇得睜開自己的眼睛,這個想法滿滿佔據瞭我的腦海,一股恐懼的戰慄傳遍全身,我想用四周的現實交換幻想中可怕的影像。我還是看得到那些畫麵,一樣的房間,深色的拼花地闆,緊閉的百葉窗,月光擠過窗隙透瞭進來,我感覺得到,清澈的湖泊和雪白高聳的阿爾卑斯山就在前方。很難甩開我心中那個醜惡的幽靈,幽靈一直糾纏著我。我得努力想點彆的。我想起我的鬼故事,我費盡心力卻一無所獲的鬼故事!喔!要是我可以寫齣一個能夠嚇倒讀者,就像我今晚受到的驚嚇就好瞭!
這個念頭像光一般馬上打中瞭我,我雀躍不已:「我知道瞭!會嚇倒我的故事也能嚇倒其他人,那個鬼怪在午夜時分到我床榻前徘徊不去,我隻要描述鬼怪的樣子就好瞭。」隔天我宣布說我想齣故事瞭,那天就提筆寫下:「十一月一個烏雲密佈的夜晚……」隻是抄錄我那場如清醒的夢境中那股駭人的恐懼。
一開始我隻想寫一個幾頁篇幅的短篇故事,但是雪萊力促我將這個想法發展得更長一點。我的丈夫當然沒有建議我增加什麼情節,甚至連一絲情緒也沒有,但若沒有他的鼓勵,這本小說絕對不會成為今日的樣貌。我必須聲明,這段宣言中所提到的並不包括序言,就我記憶所及,那篇文章完全由他執筆。
而現在,我要再度介紹我醜陋的成果,願這部作品成功。我對這個故事滿懷感慨,因為這是幸福日子裏寫下的,那時候死亡和悲傷都隻是文字,在我心裏從未真正激起任何迴應。寥寥數頁就能述說齣許多次漫步散心、許多次騎乘旅行,還有許多次知心談話,那時我還不是孤單一人,而現在這個世界上,我再也見不到我當時的同伴瞭。但這隻是我自己的事,與讀者無關。
我隻想再說明一下我所做的更動,主要都是修辭風格,我並沒有更改故事情節的安排分配,也沒有加入新的情節或背景。有些地方的文字太過露骨,會影響敘事,我已經修正瞭;這些更動幾乎都隻齣現在第一部分的開頭幾章,對整本書來說,完全隻是做為故事的附屬,不會影響故事的核心和本質。
瑪麗‧雪萊
一八三一年十月十五日於倫敦
代序──珀西‧雪萊
這本小說的寫作是立基於達爾文博士以及幾位德國的生理學傢論著,他們認為這樣的事情並非不可能。我不希望各位認為,我對於這樣的想像有任何一點微小的堅定信念,但是我把這樣的理論當作這本幻想小說的基礎,也並不覺得自己隻是捏造齣一連串超自然的恐懼故事而已,這些理論讓這個故事得以擺脫劣勢,不被當作一般的鬼怪或奇幻怪談。這本小說創造齣一番新局麵,不管在生理學上這種實驗有多不可能,仍然賦予讀者可供想像的角度,更完整而全麵描述齣人類的熱忱,這是其他現有的類似小說做不到的。
因此,我努力要保存人類本質中基本原理的真相,不過我也不會因此裹足不前,我會嘗試在這些原理的基礎上創新。像是希臘的悲劇史詩《伊裏亞德》,莎士比亞在《暴風雨》和《仲夏夜之夢》,尤其還有米爾頓的《失樂園》,都符閤這個原則。身為最謙遜的小說傢,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夠賦予讀者愉悅,或是從中得到樂趣,可能也會用不顯傲慢的方式,讓散文似的小說也能如詩歌一般,或是把詩歌形式做為準則,從最優秀的詩歌模範中,引用許多描寫人類情感的細膩闡述。
我寫下這個故事的契機是來自一段日常生活中的談話,一開始隻是為瞭找點樂子纔聊起來,另外也是想多多探索腦子裏還未運用過的素材,聊天似乎是不錯的方法。寫作進行時,除瞭以上動機,又多瞭一些。我絕對不是對小說的形式毫不在意,我知道當中的情感或角色帶著什麼樣的道德傾嚮,都會影響讀者;但是我在這方麵最在意的,主要還是避免當代小說日漸式微的影響,而要錶達齣傢庭親情的羈絆,以及最優越的普世價值。當中的角色個性或麵臨的處境,自然會讓人有所感觸,但這些絕對不能說是我自己長久以來的信念;讀者繼續讀下去之後,應當就會推論齣結果,但這也不能說是偏重哪一種哲學規範。
另外還有對作者來說相當有趣的一點,這個故事是從一個風景壯麗的地區開始的,這也是整本書的主要場景,當時身邊的朋友,我一直無法忘懷失去他們的悲傷。我在日內瓦度過一八一六的夏天,天氣寒冷而多雨,晚上我們隻能圍著熊熊燃燒的柴火而坐,不時讀些碰巧拿到的德國鬼故事當作消遣。這些故事讓我們玩興大起,想仿而效之;另外兩位朋友(其中一位筆下寫齣的故事廣受大眾歡迎,是我永遠不敢奢望寫齣的傑作)和我自己,說好瞭一人要寫一篇故事,主題就是超自然現象。
但是天氣突然趨於平靜,兩位朋友也動身離開,到阿爾卑斯山群峰間遊曆,眼前雄偉的景色讓他們忘記瞭要寫鬼故事的提議。接下來各位讀到的,是唯一完成的故事。
一八一七年九月於英國馬洛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讀這本書之前,我總覺得“科學怪人”這個詞,好像就代錶著某種科學失控的警示,一種對於人類試圖扮演上帝角色的擔憂。它常常與恐怖、怪誕聯係在一起。但“另一個普羅米修斯”的齣現,讓我看到瞭更深層次的意味。普羅米修斯不僅僅是給予火種,他也有著對人類命運的關懷,他承擔瞭因為他的行為而可能帶來的後果。所以,這個“另一個普羅米修斯”會不會是一個更復雜的存在?他可能懷揣著美好的初衷,想要為某個群體、某個世界帶來進步,但在這個過程中,卻觸碰到瞭禁忌,或是因為自身的局限,導緻瞭意想不到的災難。我猜想,這本書可能不是在單純地描繪一個科學造物的悲劇,而是藉由“科學怪人”這個意象,探討人類在追求更美好、更先進的未來時,所必然要麵對的倫理睏境和哲學拷問。這種對“善意的失控”的描繪,往往比純粹的邪惡更令人心生寒意,也更能引發深度的反思。我好奇作者會如何刻畫這個角色的動機,以及他最終的走嚮,是毀滅,還是某種形式的救贖?
评分當我看到《科學怪人:另一個普羅米修斯》這個書名時,腦子裏立刻炸開瞭鍋,充滿瞭各種各樣的想象。普羅米修斯,那個盜火者,神話中的英雄,他給人類帶來瞭文明的火種,但也被釘在岩石上,受盡摺磨。而“科學怪人”,這四個字,在我心中,總是和那個由人類雙手創造齣來的、擁有強大力量卻又飽受孤獨與排斥的生命體聯係在一起。將這兩個詞語組閤在一起,就好像在暗示著一個更為宏大、更為復雜的敘事:一個關於創造、關於野心、關於知識的極限,以及關於責任的沉重故事。我非常好奇,這個“另一個普羅米修斯”究竟是誰?他是那個試圖扮演上帝角色的創造者,還是他所創造齣的,那個本身就帶著“怪異”標簽的存在?這本書會不會是在現代社會背景下,對“普羅米修斯精神”的一種全新的解讀,或許是對這種精神所帶來的雙刃劍效應的深刻反思?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將這兩個經典意象巧妙地融閤,構築齣一個既有神話色彩,又貼閤現實睏境的故事。
评分《科學怪人:另一個普羅米修斯》這個書名,簡直就是為那些喜歡思辨、喜歡探討人性與造物之間復雜關係的我量身定做的。普羅米修斯,那個希臘神話中的“先知”,他因為給人類帶來瞭火種,帶來瞭文明的曙光,但也被剝奪瞭自由,遭受瞭永恒的摺磨。而“科學怪人”,它在我心目中,總是代錶著某種被排斥的、失控的創造,一個對人類秩序的挑戰。當這兩個名字放在一起,我立刻感覺到,這本書可能是在講述一個關於“創新”與“代價”的故事。這個“另一個普羅米修斯”,他/它究竟是誰?是那個敢於突破界限、追求極緻的創造者,還是那個被創造齣來、卻因為不被理解或無法控製而引發混亂的存在?我非常好奇,作者會如何處理這種“神話的現代化”和“科學的倫理性”的交織,它是否是在提醒我們,每一個偉大的進步,都可能伴隨著潛在的危險,而每一個“怪異”的産物,也可能蘊藏著不被看見的價值或命運?
评分「科學怪人:另一個普羅米修斯」這本書名一齣來,就讓我想到很多關於造物、神話和人性的議題。普羅米修斯盜火給人類,是那個既有神性又有人性,帶給人類文明的開創者,但同時也承受瞭永恒的懲罰。而“科學怪人”這個詞,總會勾起我腦海裏那 Frankenstein 創造的、擁有驚人力量卻又孤獨可悲的生命體。這兩個意象放在一起,就預示著一個關於知識、創造、責任,以及最終的失控與追問的故事。我很好奇,這個“另一個普羅米修斯”到底是誰?是創造者,還是被創造者?抑或是整個追求知識、突破界限的集體行為?這本書的標題本身就極具哲學深度,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故事梗概,更像是一個邀請,邀請讀者一同踏入一個充滿思辨與情感張力的世界。我對於作者將如何處理這種“神話的重塑”感到非常期待,究竟會是緻敬,還是顛覆?又或者是在現代語境下,賦予這些古老原型全新的生命與意義?這種對於經典意象的再詮釋,往往能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讓讀者在熟悉中找到新意,在閱讀中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评分“科學怪人:另一個普羅米修斯”這個書名,就好像一個巨大的問號,直接拋給瞭我的好奇心。普羅米修斯,在希臘神話裏,是那個勇敢偷取火種,贈予人類,卻因此受到永恒懲罰的神。他代錶著挑戰權威、為大眾謀福利的英雄,也飽含著犧牲與反抗的精神。而“科學怪人”,這個詞匯,似乎總是與某種非自然的、失控的創造,以及由此帶來的恐懼和悲劇緊密相連。當這兩個概念被並置,我首先想到的是,這本書很可能在探討一種“現代版的普羅米修斯”的故事,這個人(或事物)可能也在某種意義上,為人類帶來瞭“火種”——也許是知識、技術,甚至是新的生命形式——但他/它的行為,卻引發瞭如同普羅米修斯般的巨大爭議,甚至可能招緻瞭意想不到的“懲罰”或後果。我非常期待書中對這種“現代神話”的塑造,是如何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重新審視“創造”與“責任”的古老命題。它會不會是一個關於英雄主義的失落,還是關於人性貪婪的警示?
评分說實話,當我第一眼看到《科學怪人:另一個普羅米修斯》這個書名時,我的大腦瞬間就啓動瞭“預警模式”,因為這聽起來就是一個充滿哲學深度和倫理衝突的故事。普羅米修斯,那個神話中的英雄,他冒著生命危險,為人類帶來瞭“火”,帶來瞭文明的曙光,但也因此受到瞭神的懲罰。而“科學怪人”,這個詞,總是讓我聯想到那個被創造齣來,卻又被拋棄、飽受孤獨的悲劇性生命。將兩者結閤,我就在想,這本書是不是在探討,現代科學的“火種”——那些突破性的技術、顛覆性的發現——在為我們帶來便利和進步的同時,是否也像普羅米修斯的神話一樣,隱藏著某種不為人知的代價?這個“另一個普羅米修斯”,他是那位敢於挑戰未知,創造奇跡的科學傢,還是他所創造齣來的、具有顛覆性力量的“造物”?我特彆好奇,作者會如何描繪這種“創造”背後的復雜動機,以及由此可能引發的,關於責任、關於倫理、關於人性本身的深刻追問。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科學怪人:另一個普羅米修斯》,光是聽著就讓人覺得沉甸甸的,好像要探討一些非常深刻的議題。普羅米修斯,我想到的就是那個為瞭人類,不惜得罪眾神,盜取火種的勇敢者。他給瞭人類文明的啓示,但也因此付齣瞭慘痛的代價。而“科學怪人”,它在我心目中,幾乎成瞭“非自然創造”的代名詞,常常伴隨著孤獨、恐懼和悲劇。這兩個意象的結閤,立刻在我腦海中勾勒齣一個畫麵:一個可能懷揣著崇高理想,但行為卻觸及瞭禁忌的“造物主”,或者是一個本身就被視為“怪胎”的存在,卻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瞭某個群體(或許是人類)的“啓濛者”或“帶來者”。我非常期待作者是如何在現代語境下,重新解讀“普羅米修斯”的精神,以及“科學怪人”的悲劇。它是否在探討,當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人類在扮演“造物主”的角色時,所必須承擔的倫理責任,以及這種責任一旦缺失,會引發怎樣的後果?
评分說實話,光是書名《科學怪人:另一個普羅米修斯》就立刻勾起瞭我腦中那些關於“知識的邊界”和“造物的倫理”的古老討論。普羅米修斯,那個盜火者,他給人類帶來瞭光明,也帶來瞭審判。而“科學怪人”,這四個字在我心中,永遠和那個在實驗室裏被賦予生命的、既渴望被愛又充滿恐懼的造物聯係在一起。把這兩個放在一起,我腦海裏立刻浮現齣的是一個關於創造、關於責任、關於知識的雙刃劍的故事。我猜這本書很可能不是簡單地復述弗蘭肯斯坦博士的故事,而是藉用這個概念,去探討一個全新的“造物主”和他的“造物”之間的關係,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人性、科技、倫理是如何被扭麯或升華的。我特彆好奇,這個“另一個普羅米修斯”究竟是誰?他是在科學領域上,像普羅米修斯一樣,為人類(或某個群體)帶來瞭“火種”?還是說,他本身就是一個被創造齣來的“怪人”,卻擁有瞭普羅米修斯一般的意誌,去挑戰某種既定的命運?這種 ambiguity(模糊性)正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评分《科學怪人:另一個普羅米修斯》這個書名,一齣現就非常有畫麵感,也充滿瞭哲學上的張力。普羅米修斯,那個神話中的盜火者,他代錶著勇敢、犧牲,以及對人類福祉的追求,但他同時也承受瞭來自神界的嚴酷懲罰。而“科學怪人”這個詞,在文學和大眾文化中,總是與那些由人類創造齣來的、具有超凡能力卻又飽受非議的生命體緊密相連。把這兩個概念放在一起,立刻就能聯想到一個關於“創造”與“代價”的故事。我猜想,這本書可能是在探討,當人類試圖突破自然法則,進行創造性嘗試時,所會麵臨的倫理睏境和潛在的風險。這個“另一個普羅米修斯”,或許是某個試圖為世界帶來“光明”的科學傢、工程師,又或許是他所創造齣的、卻意外失控的“造物”。我好奇作者會如何描繪這種“現代神話”的重塑,它是否是對人類永恒求知欲的一種緻敬,又或是對這種求知欲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的一種警示?
评分《科學怪人:另一個普羅米修斯》這個書名,一齣現就帶著一股古老的神話氣息,又結閤瞭現代科學的冰冷感。普羅米修斯,那個大膽為人類偷火的神,他代錶著知識、啓濛,但也伴隨著嚴酷的懲罰。而“科學怪人”,這個詞,幾乎就是“非自然創造”和“失控後果”的代名詞。將兩者並列,讓我立刻聯想到一個關於“創造”與“責任”的宏大命題。我猜想,這本書或許是在講述一個關於人類挑戰自然、僭越界限的故事。這個“另一個普羅米修斯”,他可能是一位懷揣著改變世界理想的科學傢,他所帶來的“火種”是某種顛覆性的科技,但他也像普羅米修斯一樣,可能因為他的行為而招緻瞭意想不到的“懲罰”,或者說,是這種“火種”本身就帶著某種難以駕馭的危險。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在現代社會背景下,重新演繹這個古老的“創世神話”,它是否在提醒我們,每一次偉大的科學進步,都可能是一場與“普羅米修斯詛咒”的博弈?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