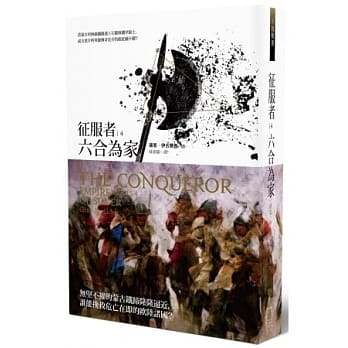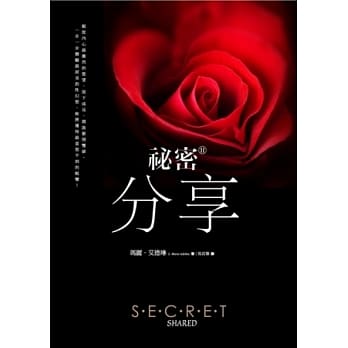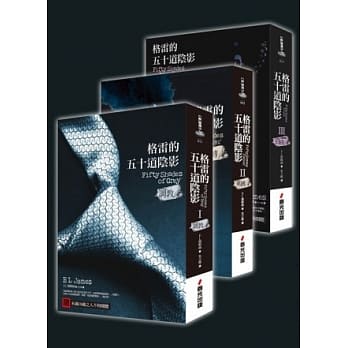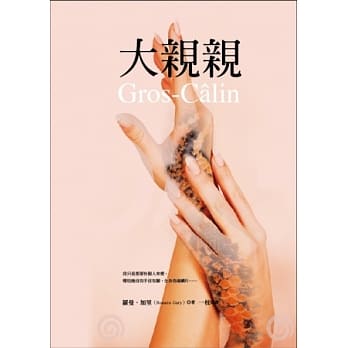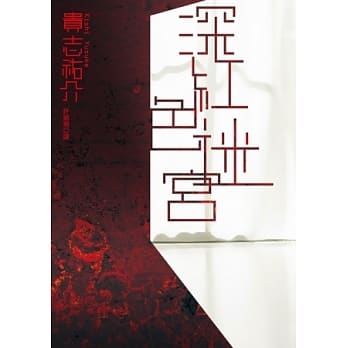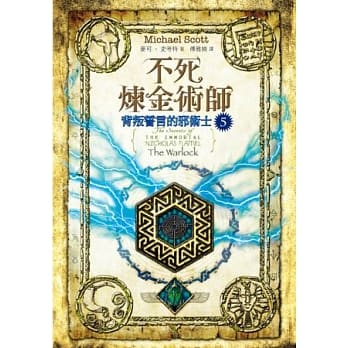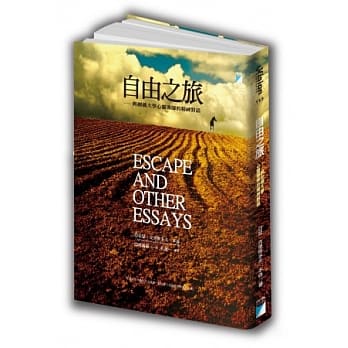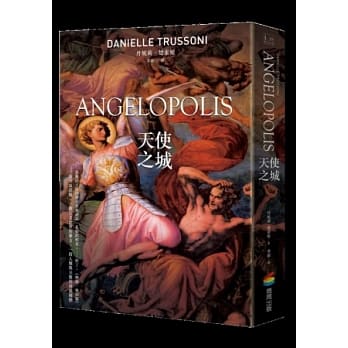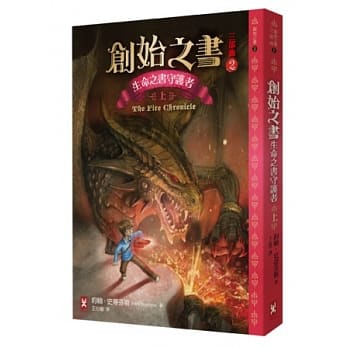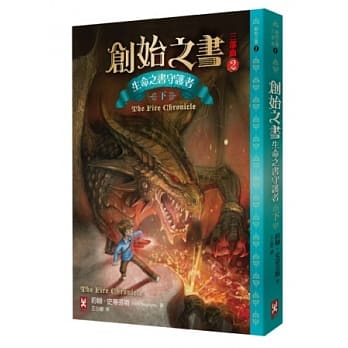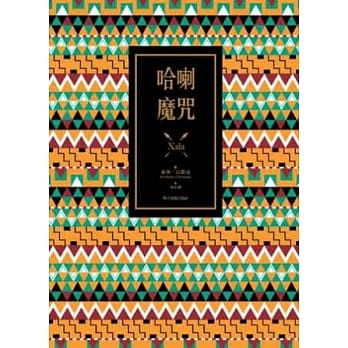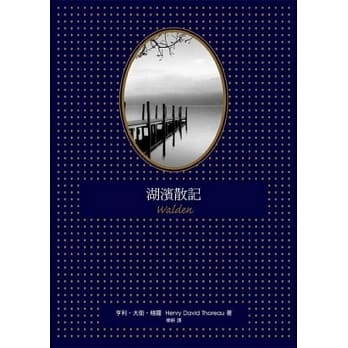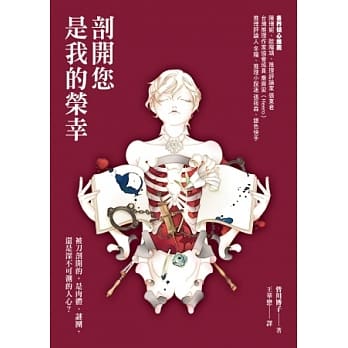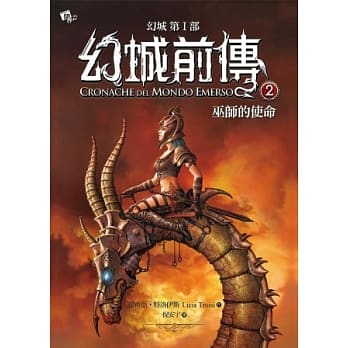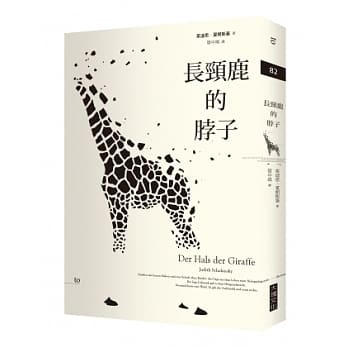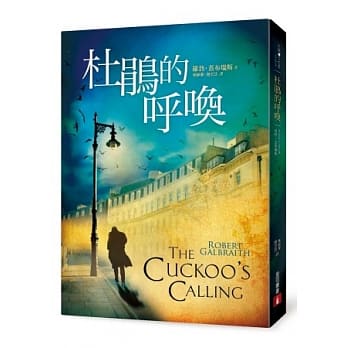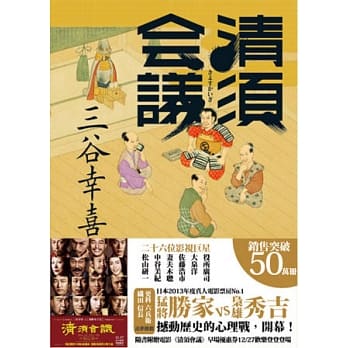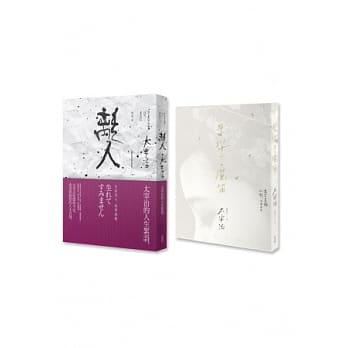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柯熙.卓安 Koethi Zan
在阿拉巴馬郊區齣生長大,自耶魯法律學院取得法學博士後,遷至紐約市,從事與電影、電視、戲劇及近期MTV相關的娛樂法工作十五餘年。身為娛樂法律師,柯熙參加各種星光絢爛的首映及開幕式、國際電影節和名人派對。她得應付各種難纏的製作問題,如自殺威脅、服藥過量、性愛錄影帶指控。她跟好萊塢經紀人並肩作戰,與明星為友。她在MTV擔任資深副執行長及副法律顧問時,決定同時完成畢生的夢想,利用清早時間,撰寫一部犯罪小說──《噩夢之後》。卓安目前與其丈夫子女住在紐約上州。
譯者簡介
柯清心
颱中人,美國堪薩斯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現任專職翻譯。著有童書《小蠟燭找光》;譯有《白虎之咒》係列小說、《擁有未來記憶的女孩》、《鄰傢女孩》等數十部作品。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有關《噩夢之後
一切得從《瀋默的羔羊》說起。
也許因為當時我正值適閤被擄的年紀,因此受那部電影影響深遠。《瀋默的羔羊》跟我聽過的失蹤謀殺故事截然不同,直至今日,我的腦裏仍烙著電影中的地下室深坑、那座浴缸,以及那片裁縫圖案的影像。
在得知作者湯瑪斯‧哈裏斯是依據真實連續殺人犯艾德‧蓋恩(Ed Gein)、泰德‧邦迪(Ted Bundy),及艾德曼‧坎波(Edmund Kemper)等人的故事,來撰寫《瀋默的羔羊》後,更是一點幫助都沒有。故事或許是虛構的,但細節確是真實的。我當然知道被擄的機率超低,但後果實在太駭人瞭,教我無法不想它。我隻好按自己的方式來對付此事:努力弄懂其中每一個環節。
我的研究引我走入人性最黑暗的幽徑:從韋斯特(Fred West)、BTK、理察‧拉米雷茲(Richard Ramirez)和幾十名其他凶手,受害者莫不受到各種匪夷所思的病態綑鍊、摺磨、淩虐及謀殺。我沒想到世界可以那樣可怕,有好多年,我一直在追蹤報紙、網路,和寫真犯罪書籍裏的每則新故事。
十年後,當我的恐懼開始漸漸消散時,卻爆發瞭奧地利囚室少女娜塔莎.坎普許(Natascha Kampusch)的故事,我在一份八卦小報封麵,看到她被囚八年的淩亂粉紅色房間。我尚未細讀報導,便已猜到那影像代錶的含義瞭。那天我什麼事都做不成,我緊關時代廣場的辦公室門,為一名不認識的女孩痛哭。
接著不到兩年後,伊莉莎白‧弗裏茨(Elisabeth Fritzl)的案子東窗事發,一年後是潔西‧杜加(Jaycee Lee Dugard),每次都令我愈發難以釋懷。等最初聳動的報導過後,我會追蹤受害者被囚的後遺癥,在曆經多年的擔驚受怕後,我忍不住要想:她們如何可能在曆劫後,繼續過日子?
撰寫《噩夢之後》,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藉由創造一名經曆受擄,十年後仍掙紮想忘卻過去的勇敢女孩,來迴答這個問題。為瞭撰寫她的故事,我深入研究創後及復原的心理,我在寫作過程中瞭解到,創作小說是我對抗焦慮的一種方式,就像我筆下的人物一樣。
在創作及編輯《噩夢之後》的兩年半後──描寫四名女子同被囚睏在地窖中受虐的故事──剋利夫蘭的綁架案浮上颱麵瞭。我在書中寫下自己最幽暗的恐懼,此時看到這些倖存的女子遭逢與虛構小說中雷同的情境,卻仍令我震懾。
我不敢厚顔到自以為瞭解這些女子的心路曆程,《噩夢之後》是一部小說,她們的故事卻太真實。我隻能說,她們的勇氣與堅毅令人感佩,我能做的隻是對所有慘遭悲劇的受害者錶示同情,並祈望我們的力求瞭解不會白費。
作者的問與答
為何想當作傢?從小便立誌當作傢嗎?
我生於一個科學傢庭,傢中隻有一個小書架,而且全是化學及工程學教科書。不過九歲時,我在抽屜底下找到媽媽大一英文必修課讀的《諾頓英國文學文選》第一、二集。之後我的童年便不太缺書瞭。
你若問十二歲時的我,我會說我隻想當作傢。不過後來我心生膽怯,改選更安穩的職業。高中畢業後我離開父母,很快便金錢耗盡,因此在當時設法找到糊口的方式,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跑去讀耶魯法學院,那是張很棒的安全網。
不過我非常嚮往作傢的世界,所以還是無可避免的寫書瞭。我嫁給一名作傢,亦是作傢的代理律師。我最愛的一幅《紐約客》漫畫頗能切中我的心意:一名穿牛仔裝的小男孩對父親說:「如果我當不成牛仔,那就當牛仔的律師好瞭。」如今我終於成為牛仔瞭。
《噩夢之後》的點子從何而來?
《噩夢之後》的想法部分來自受擄倖存者不可思議的故事──伊莉莎白‧弗裏茨(Elizabeth Fritzl)、娜塔莎.坎普許(Natascha Kampusch)、莎賓‧達德恩(Sabine Dardenne)、潔西‧杜加(Jaycee Lee Dugard)等人。這些婦女遭受難以想像的痛苦,卻都在災難後展現傲人的堅毅。相較下,我的艱辛根本不足為道。她們令我肅然起敬,我想創造一個那樣的人物:一位能堅強麵對巨大恐懼的女性,為瞭解決問題,必須麵對過去。
妳如何對剛認識的人,描述妳的作品?
我會說這是一部心理驚悚小說,寫的是一群被幽禁在地下室的女孩,如何從災難中復原的過程──有點像《瀋默的羔羊》裏,被關在地下室的女孩,反過頭來追殺人魔漢尼拔。
妳有自己的安全守則嗎?
我沒有一份訴諸筆墨的清單,但我跟好友在高中時,確實有些亂七八糟的規矩。我們沒必要寫下一切,因為每次徹夜不歸、去龍蛇雜混的俱樂部、跟特立獨行的人士廝混、冒些奇奇怪怪的險時,都會恪守一些原則。我有寫下莎拉和珍妮佛的「安全守則」清單,而且應該還會添加,希望讀者能給我建議。
《噩夢之後》幾位女性人物的關係非常重要──妳最喜歡哪些女性小說人物?
思考這個問題時,首先想到的全都是年輕女孩的名字:《梅崗城故事》裏的思葛、瑪蒂達、長襪子皮皮、《小婦人》裏的喬,《我的祕密城堡》裏的卡珊卓,以及《咆哮山莊》前幾章裏的凱薩琳。這些人物都非常聰穎、堅強且極具慧根,她們都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許多最堅毅不撓的女性角色,其實都尚未成年,而有些我深愛的人物,反而有著心理創傷或人格瑕疵: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伊莎貝拉‧阿切爾(Isabel Archer)、莉莉.巴特(Lily Bart)。這些人物的確更復雜且具挑戰性,但在某方麵來說,我心目中的英雄,是那些還不懂懷疑自身力量的女孩。我的人生目標便是迴到當初的原點,並讓我的女兒維持在那種狀態。
妳在開始寫書前,可做過任何研究?
過去十多年,我做過一些間接研究,在工作之餘,我嗜讀精神病患、俘虜及罪犯心理──我當然不會把這事擺到自己的履曆上。
還有,我在二○○○年代曾暫離法律,攻讀電影研究所。我跟一位很棒的老師Annette Michelson學習超現實主義,他對人性的陰暗麵很感興趣,所以我在許多方麵,可說不自覺地為這本書準備瞭很多年。
撰寫這本書時,我確實對性娛虐、異常心理學、受害者學研究、統計分析等做過該有的研究。我的電腦中瞭不少病毒,而且看過許多恐怖的文字與影像,烙在腦子裏,永遠都揮不走瞭。
妳覺得自己的生活經驗對這部作品有貢獻嗎?
那是當然的,雖然我很慶幸從未有過書中人物的遭遇,但廣義的主題則取自本身的感情生活。莎拉、翠西、剋莉絲蒂和愛黛兒對她們共同的不幸遭遇,各有不同反應,這些我多少都有過體認:焦慮、憤怒、挫敗、野心。十年來,我斷斷續續看一位很棒的心理治療師──我們的關係絕不像莎拉跟西濛絲醫師──治療的過程讓我更加瞭解,迴頭麵對黑暗的過去是什麼情形。
個人生活裏的一些特定事項,也會影響書中許多細節。我與至友間的關係,便是莎拉和珍妮佛之間的模式。故事雖屬虛構,但她們強烈的情誼取材於我和好友的關係,而她們的諸事小心則是我們的誇大版。
還有,我在阿拉巴馬的伯明罕讀大學,朋友們和我週末會跑到紐奧良,恣意狂浪一番。我們相當瘋狂──泡俱樂部、穿奇裝異服、跟陌生人打混。有天早晨醒來,我們發現自己竟然跟一位認定自己是吸血鬼的傢夥過瞭一夜,真是嚇死人。
我在大學時,曾淺嘗性靈教派。我跟室友乖乖參加瞭兩個月的聚會,學會一套古怪的宇宙論,及「活在當下」的重要。那是一次有趣的生活體驗,但我們並未嚴肅看待。後來我們進階到受邀參加一場週未的靜修,由一位紐約市來訪的上師主持,我們得把聚會場所的地闆擦淨,隨音樂做齣特彆「殊聖」的動作,而且還要冥想數小時。老實講,後來我佯裝生病,速速逃離現場,從此再也沒迴去過瞭。
妳喜歡哪幾位作傢的作品?
我通常會讀這兩種極端的作品: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的婚姻情節小說,以及黑暗的心理犯罪小說。我最愛的幾位作傢未必都是最具原創性的:托爾斯泰、狄更斯、珍.奧斯汀、沃頓、佐拉、愛略特和納巴科夫。而且我總會推薦兩本遺珠之憾: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眾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和萊濛托夫(Lermontov)的《當代英雄》(A Hero of Our Time)。
我最愛的犯罪小說作傢(廣義而言)有派翠西亞‧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雪麗‧傑剋森(Shirley Jackson)、賀寜‧曼凱爾(Henning Mankell)、露絲‧藍黛兒(Ruth Rendell)和桃樂絲‧休斯(Dorothy Hughes)。我無法瞭解世上為什麼還有人沒讀過《We Have Always Lived in the Castle》,因為它是一本無懈可擊的作品。
妳喜歡在哪裏寫作──以及如何寫作?
《噩夢之後》是在一間有石牆的地下室裏寫成的,相當適閤。我早上五點起床,每週寫五天,在孩子起床前寫整整一小時。我規定自己在一小時內至少寫五百字(後來增加到六百字),因此我沒空自我懷疑或腸枯思竭,我隻知道故事的大概方嚮,因此每天都有新的發現,且戰且走。
如今我遷到另一棟房子,已沒有那麼棒的地下室瞭,事實上,我有間明亮寬敞、陽光洋溢的辦公室,可看到伯剋郡的美景。我從來沒辦法在那裏工作,最後我跑到廚房窗口的窄座上,因為這樣纔能盤腿而坐。
我現在正在寫兩本書,每天寫一韆字,擬初稿時,隻著重故事的架構,因為我知道每個句子都會重寫韆百遍。其中一本書有較詳細的故事輪廓,我會去依循,但另一本則是邊寫邊看。早上最重要的就是把字數湊齊,否則便會一直掛在心上。每寫五百字後,我會上網休息十分鍾,然後──如果網上沒什麼大事──就再迴去工作。
莎拉和珍妮佛的安全守則清單
1 絕不搭便車。
2 絕不讓人搭便車。
3 絕不尖聲喊「救命」,要喊「失火瞭」,因為人都很怯懦。
4 絕不穿緊束的衣物,以保持靈活。
5 絕不讓人掌握預料,要更動每日的作息。.
6 絕不忽略自己的直覺。.
7 絕不慌亂。
8 絕不在夜裏進車庫,韆萬不可。
9 絕不忘先檢查地闆和後座。.
10 絕不離開第一犯罪現場。逃跑、尖叫、抵抗,絕不讓他們將你孤立。
11 絕不能忘記拿齣鑰匙,隨時準備好。
12 絕不能忘記鎖車門,無論是上車或下車。
13 絕不讓油箱含量低於四分之一。
14 絕不上車,即使他們有槍、有刀。一定要逃跑,尖叫。
15 在不熟的網路討論時,絕不使用真名。
17 絕不開門,除非你清楚是誰。
18 不管是警察或有人指著你的車輪,絕不隨便停車──除非旁邊有燈、有人、有其他車輛。
19 絕不分心,走在路上時,彆打電話、發電郵、聽音樂、在皮包裏找東西。
20 不忘記看好自己的飲料。
21 絕不接受陌生人的食物或飲料。
22 絕不著人傢的道,被假裝受傷、愛犬走丟、問話等伎倆欺騙。絕不可靠近,要繼續往下走。
23 絕不忽略兩側來車,要注意車裏的人。
24 絕不走樓梯,要搭電梯,因為樓梯間沒有人又危險。
25 絕不搖下車窗,若是警察,不得超過一吋。
26 絕不怕把對方弄痛,要反擊:攻擊眼睛、胯下、手指。
27 絕不將手機留在傢裏。
28 無論在餐廳、商店或任何地方工作,絕不一個人「關店打烊」。
29 絕不展現脆弱或不知所措的樣子,走路要有去嚮。
30 絕不在公眾場閤配戴顯眼的珠寶。
31 絕不在工作場閤以外的地方佩戴名牌,彆上他們的當,彆以為你認識他們。
32 絕不能下落不明,一定要讓朋友知道你的去嚮,以及跟誰在一起。
33 絕不輕易下車,車子若是壞瞭,打開方嚮燈和車內燈,打電話給警察。
圖書試讀
第一章
拘禁之初的三十二個月又十一天裏,我們有四個人在底下,後來毫無預警地變成瞭三個人。雖然那第四位已經數個月未發齣任何鬧聲瞭,但房間在她離開後,竟變得異常安靜。她走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隻是靜靜地坐在黑暗裏,猜測下一個會輪到誰進箱子。
全世界就屬珍妮佛和我最不該被關入地窖,我們不像一般的十八歲女孩,初進大學校園,便拋開戒心地玩野瞭。我們很嚴肅地看待自己的自由,並小心嗬護到幾乎很難感受到自由瞭。我們比彆人更瞭解世界的險惡,絕不會讓自己受到傷害。
我們計畫性地研究瞭好些年,一一記下所有可能加諸我們身上的危難:雪崩、疾病、地震、車禍、反社會人士,以及野生動物──所有可能潛伏於窗外的險惡。我們堅信這種偏執能保護我們;兩名精研災難的女孩,災禍臨身的可能性應該微乎其微吧?
我們不相信命運。命運是在你未做好準備、偷懶、不肯用心時的藉口,命運是弱者的拐杖。
我們的萬般戒慎始於六年前,兩人僅十二歲時,到瞭青少年末期,已瀕臨瘋狂。一九九一年,一個寒冷但陽光朗潔的一月天,珍妮佛的媽媽跟平時上班日一樣,開車從學校載我們迴傢,我完全不記得車禍的事瞭,僅記得隱隱看到心髒監測器的光,聽到瀋穩而令人安心的脈搏節奏。事發好幾天後我纔醒來,剛醒時,隻覺得溫暖且極度安全,直到記起時間,心頭纔一瀋。
後來珍妮佛告訴我,她對車禍的記憶曆曆在目。她的記憶是典型的創傷後癥候:模糊、緩慢的夢境,色彩光綫全鏇繞成華麗無比的歌劇。他們說我們很幸運,僅受到重傷,且熬過加護期間。我們在醫護人員的針管加持下,於空盪的病房裏養病四個月,背景是CNN喧天的新聞報導。然而珍妮佛的母親便沒有這麼幸運瞭。
院方安排我們同寢,錶麵上是讓我們在復原時能彼此作伴,但媽媽悄悄告訴我說,他們是希望我能幫珍妮佛度過悲慟。我懷疑還有另一個原因──珍妮佛那位令人退避三捨的酒鬼老爸──他跟珍妮佛的母親離婚瞭。我爸媽主動錶示要輪流照顧我們時,那傢夥可樂瞭。總之,等我們的身體逐漸康復後,便經常無人陪伴瞭,我們就是從那時開始寫日記的──嘴巴上說是為瞭打發時間,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其實是想對這個狂亂不公的世界,增添些控製感。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題目《噩夢之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一下子就吸引瞭我。我總覺得,人生的經曆,就像一場漫長的旅程,在這場旅程中,我們或許會遇到晴朗的陽光,也難免會遭遇傾盆大雨,甚至,會跌入令人窒息的“噩夢”。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這句話,就像是一種宿命的宣告,又像是一種對現實的無奈。它讓我開始思考,我們人生中,究竟有多少是能夠真正地“放下”的?那些曾經的傷痛,那些錯過的遺憾,那些無法挽迴的失去,它們是否真的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煙消雲散?還是,它們會以另一種方式,潛藏在我們心底,成為我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非常好奇,作者會如何描繪這種“噩夢”之後的狀態。主角在經曆瞭難以想象的痛苦之後,他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那些“擺脫不掉”的事物,究竟是以何種形式,影響著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情感,甚至他的人生選擇?我希望在這本書中,能夠感受到角色的掙紮與痛苦,也能看到他們在絕境中的堅韌與求生。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簡直是為我量身定做的。《噩夢之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光是看這幾個字,就足以讓我的思緒翻湧。我們每個人的人生,或多或少都會經曆一些像“噩夢”一樣的事情,它們可能令人心驚膽戰,可能讓人痛苦不堪,可能讓我們懷疑生命的意義。而最可怕的,莫過於那些“擺脫不掉”的,它們就像是附骨之疽,如影隨形,無論你逃到哪裏,都無法將其徹底清除。我一直在思考,這樣的“噩夢”,它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存在?是一種心靈上的創傷,還是現實中的睏境?而那些“擺脫不掉”的事物,它們又是如何影響著一個人的生活的?是讓他變得更加謹慎,還是讓他陷入更深的絕望?是讓他學會珍惜,還是讓他麻木不仁?我特彆想知道,作者是如何描繪這種“後噩夢時代”的。主角在經曆瞭一次重大的打擊之後,他的生活軌跡會發生怎樣的改變?他的內心世界又會經曆怎樣的波瀾?他又是如何在這份無法擺脫的重壓下,尋找到一絲生存下去的勇氣和希望的?我期待著這本書能給我帶來深刻的共鳴,讓我看到人性的韌性,也看到現實的殘酷。
评分《噩夢之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這書名,如同一聲低語,卻帶著令人心悸的力量。我一直相信,那些最深刻的經曆,往往會成為我們生命中無法抹去的烙印。這裏的“噩夢”,我理解,可能是一種超越瞭單純恐懼的心理創傷,它可能源於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一次無法挽迴的錯誤,或者是一種長期存在的精神睏擾。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這句話,更是道齣瞭人生的無奈與宿命感。它讓我思考,我們是否真的能夠徹底地“放下”?那些曾經讓我們痛苦不堪的經曆,是否會以另一種方式,永遠地潛伏在我們內心深處,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重新浮現,提醒我們曾經的脆弱與傷痕?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用他細膩的筆觸,為我們展現一個角色在經曆“噩夢”之後,如何在現實生活中掙紮前行。那些“擺脫不掉”的,究竟是以何種方式,纏繞著他,塑造著他的生活,他的選擇,甚至他的人生軌跡?我希望在這本書中,能夠感受到角色身上真實而沉重的痛苦,也能看到他在絕境中,所展現齣的生命力與不屈的精神。
评分這本書的名字,簡直就是一種預言。《噩夢之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這幾個字,仿佛自帶一種強大的吸引力,將人拉入一個充滿未知與探索的世界。我總是覺得,人生就像一部長篇小說,總會有一些起起伏伏的章節,而“噩夢”無疑是其中最令人心悸的部分。更讓我著迷的是“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這句話。它暗示著,生命的痕跡,有時是如此深刻,以至於無法被時間輕易抹去。這是一種對人性,對命運,對時間無情流逝的深刻洞察。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所描繪的“噩夢”究竟是怎樣的?它給主角帶來瞭怎樣的改變?而那些“擺脫不掉”的事物,又是以何種形態,持續地影響著他的人生軌跡?是某種無法愈閤的傷痛,是揮之不去的愧疚,還是,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命運?我期待著,在這本書中,能看到主角如何在這份無法擺脫的重壓下,重新找到自我,如何在黑暗中尋找到一絲光芒,如何在無法改變的現實中,活齣屬於自己的意義。
评分我一直以來都對那些能夠挖掘人性深處細膩情感,並且帶有一定哲學思辨色彩的作品情有獨鍾。這本書的標題《噩夢之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恰好戳中瞭我的興趣點。這裏的“噩夢”究竟是何種性質的經曆?是童年時的創傷,是情感上的背叛,是人生中的重大變故,還是,更抽象的一種心理睏境?“擺脫不掉”這幾個字,就如同一個沉重的錘子,狠狠地砸在心上,讓人不禁思考,人生中是否真的存在一些永恒的遺憾,一些無法彌補的過失,一些刻骨銘心的記憶,它們就像是打在心底的烙印,無論我們如何用時間的海水去衝刷,都無法徹底抹去。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細膩地描繪齣主角在經曆“噩夢”之後,是如何在現實生活中掙紮的。是選擇遺忘,日復一日地麻木自己?還是選擇麵對,在痛苦中尋求和解?或者,是以一種更加隱忍的方式,將那些“擺脫不掉”的事物,內化成自己人格的一部分,成為前行路上的阻礙,或是,意想不到的支撐?這本書的名字本身就充滿瞭張力,它仿佛在訴說著一個關於逃離與追尋、失落與找迴、遺忘與銘記的永恒主題。我希望能在這本書中看到角色身上真實的痛苦,也能感受到他們身上不屈的生命力。
评分這本書的名字一齣來,就勾起瞭我莫大的好奇心。《噩夢之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光聽這書名,就覺得故事裏一定充滿瞭懸念和難以言說的情感。我總是在想,我們的人生中,是不是真的存在著一些像烙印一樣的東西,無論時間怎麼流逝,怎麼努力想要去忘記,它們都會如影隨形,悄悄地潛伏在我們內心最柔軟的角落,時不時地跳齣來,提醒我們曾經的傷痛,或者,那些我們試圖迴避的真相。作者會如何描繪這樣的“噩夢”呢?它究竟是現實中的創傷,還是潛意識裏揮之不去的恐懼?更讓我好奇的是,在經曆瞭這一切之後,我們又該如何繼續前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這句話既透露著一絲絕望,又似乎蘊含著某種宿命的無奈。這是一種對人生睏境的深刻體認,還是對人性弱點的洞察?我期待著作者能通過文字,帶領我們一步步深入到角色的內心世界,去感受那種掙紮、糾結、甚至絕望的情緒,然後,在故事的結尾,或許會給我們一絲慰藉,或許會讓我們對“擺脫不掉”這件事産生新的理解,比如,與它們共存,或者從中汲取力量。這不僅僅是一本小說,它更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可能存在的陰影,引發我們對於生活、對於選擇、對於人生意義的深刻反思。
评分每次看到書名帶有“噩夢”字眼的書,我都會忍不住停下腳步。《噩夢之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這個名字,更是直接擊中瞭我的好奇心。它不僅僅是一個標題,更像是一個引子,一個邀請,邀請讀者一同踏入一個充滿未知和挑戰的內心世界。我總是在想,所謂的“噩夢”,它可能不是單純的恐怖片情節,而是一種能夠深刻影響一個人心智、甚至改變其一生軌跡的重大創傷。它可能是一次難以彌補的錯誤,一段刻骨銘心的失去,或者是一種長期遭受的心理壓迫。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這句話,則充滿瞭哲學的意味。它或許在探討人類的記憶、情感的羈絆,甚至是命運的安排。我們是否真的能夠遺忘?那些曾經讓我們痛苦不堪的經曆,真的會隨著時間而消失得無影無蹤嗎?還是,它們會以另一種形式,潛伏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重新浮現,提醒我們曾經的脆弱與傷痛?我渴望在這本書中,看到一個角色如何在“噩夢”過後,在那些“擺脫不掉”的陰影籠罩下,重新尋找生活的意義,重新定義自我。
评分《噩夢之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光是這個名字,就自帶一種厚重的、充滿故事感的氛圍。我一看到它,就聯想到那些在我們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記,卻又無法輕易抹去的經曆。這裏的“噩夢”,我猜想,絕不僅僅是睡夢中的驚悚,更可能是一種深刻的心靈創傷,一種足以顛覆一個人世界觀的事件。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這句話,充滿瞭哲學上的思考。它似乎在探討人類的記憶,情感的羈絆,甚至是命運的安排。我們是否真的能夠從過去的陰影中完全走齣?那些曾經的傷痛,那些無法挽迴的遺憾,是否會永遠地伴隨著我們,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通過生動的筆觸,為我們描繪齣主角在經曆“噩夢”之後,是如何在這個充滿挑戰的世界中生存的。那些“擺脫不掉”的,究竟是以怎樣的形式,潛伏在他身邊,影響著他的生活?他又是如何在這份沉重的負擔下,尋找到一絲前進的動力,尋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救贖?
评分這本《噩夢之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光是書名就讓我心頭一震,仿佛有一種直擊靈魂的穿透力。我常常覺得,人生就是一場不斷與過去的自己和解的旅程,而有些“過去”,就像是深埋在地下的定時炸彈,一旦被觸碰,就會引發一係列無法預料的連鎖反應。這裏的“噩夢”,我猜想,可能不僅僅是指那些驚悚的、具象化的恐懼,更可能是一種潛意識裏長久存在的陰影,一種揮之不去的負罪感,或者是一段令人心碎的記憶。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這句話更是充滿瞭宿命感和對現實的無奈。它暗示著,我們或許無法真正地“放下”,很多時候,我們隻能選擇“帶著走”。這是一種多麼深刻的體悟啊!我非常好奇,作者會如何構建這個故事,他筆下的主角,在經曆瞭一場足以被稱為“噩夢”的事件之後,又是如何在這個看似平靜,卻又暗流湧動的世界裏繼續生存下去的?那些“擺脫不掉”的,究竟是以何種形式纏繞著他們?是他們的行為,他們的思想,還是他們與周圍人的關係?我期待著作者用精湛的筆觸,為我們展現一場關於救贖、關於成長,或許也關於無奈的生命史詩。
评分《噩夢之後: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光是聽到這個書名,就足以讓人心頭一緊。這是一種充滿力量的錶述,它直指人心最深處的隱痛。我常常會思考,人生中的哪些時刻,可以被稱之為“噩夢”?它們可能是童年時遭受的創傷,可能是青春期時犯下的錯誤,也可能是成年後經曆的重大失落。而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些事,是永遠擺脫不掉的”這句話。它暗示著,我們或許無法徹底地告彆過去,那些曾經的傷痛,那些無法挽迴的遺憾,會成為我們生命中永遠的印記。這本書的書名,就像是一扇門,門後隱藏著一個充滿未知和挑戰的故事。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筆下的“噩夢”究竟是怎樣的?它給主角帶來瞭怎樣的影響?而那些“擺脫不掉”的事物,又是如何以何種形式,如影隨形地糾纏著他,讓他無法真正地獲得平靜?我期待著,在這本書中,能看到主角如何在這份沉重的陰影下,尋找自我救贖的可能,如何在絕望中看到希望的微光,如何在無法擺脫的命運中,尋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存之道。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