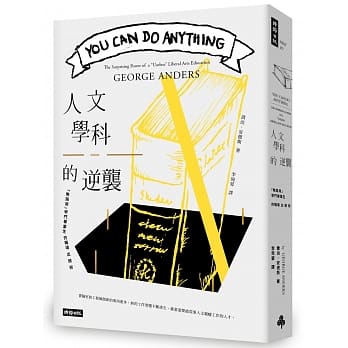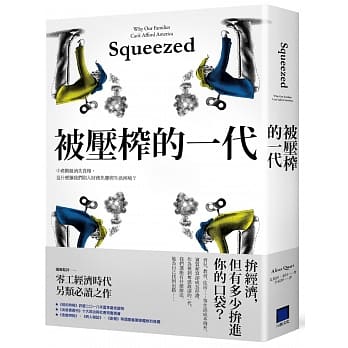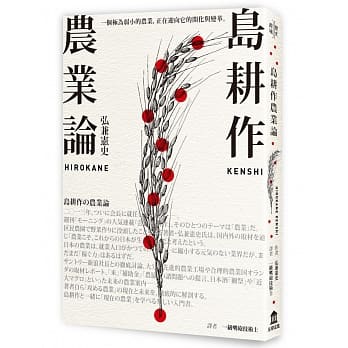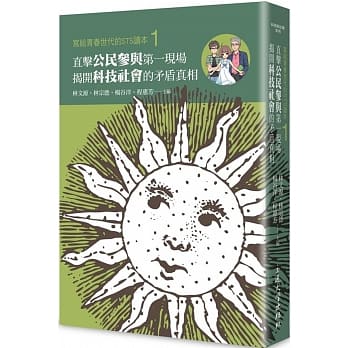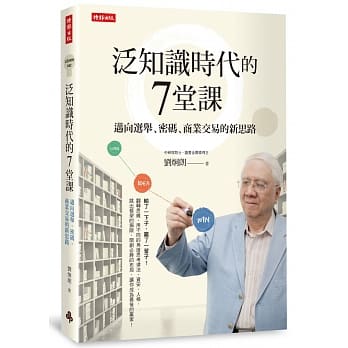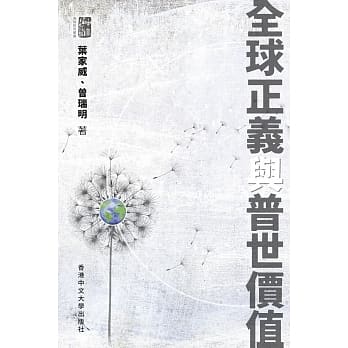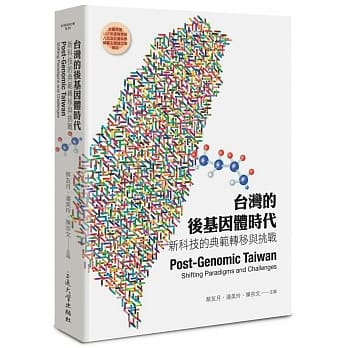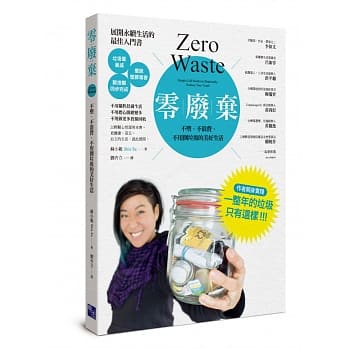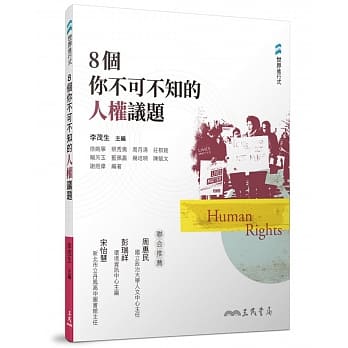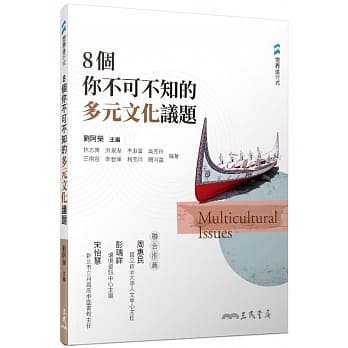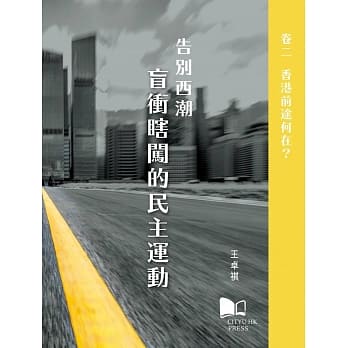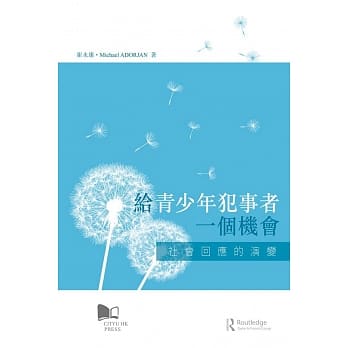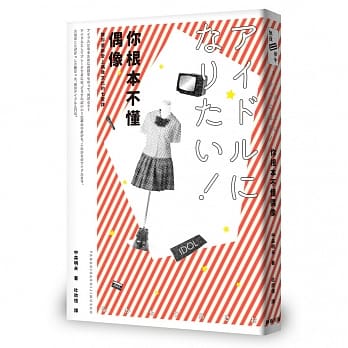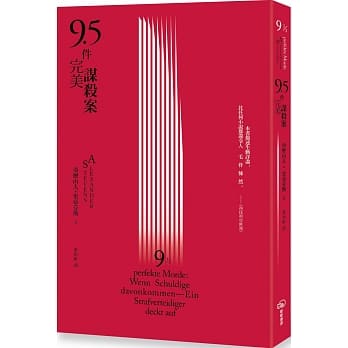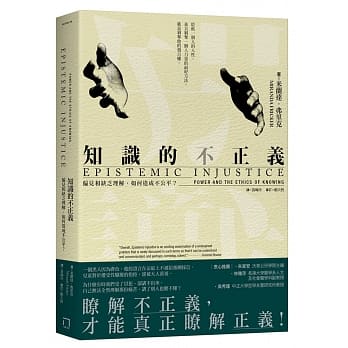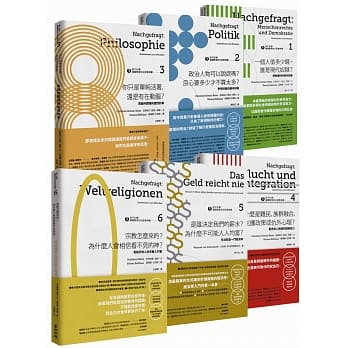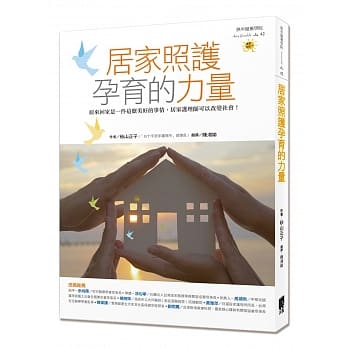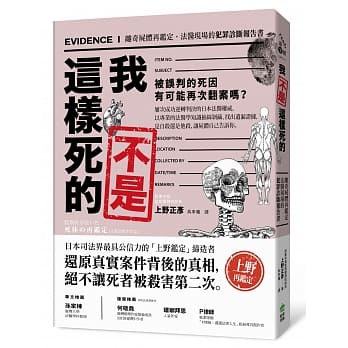圖書描述
是枝裕和導演 首部紀實文學,叩問:
一個嚮往單純的人生,
為何因官僚這個職業步入險境?
日本是否有「福祉社會」的可能?
「沒有人的存在是為瞭故事或議題。我們隻是像那樣的活著——生命翻滾於那些樣態的活著。我會想在電影中描繪這樣的人類,或許遠因就在於相遇本書中的這對夫婦,下意識受到瞭影響吧。我是這麼想的。果然,處女作融入瞭一切。」
一個嚮往單純的人生,為何因官僚這個職業步入險境?
水俁病(日語「水俁病」),為公害病的一種,成因為汞中毒,一九五六年發生於日本熊本水俁市,因而得名,一直到二〇一六年確認、二〇一七年《水俁公約》生效,事件曆時六十多年,受害人高達萬人,死亡人數超過韆人。而一九九〇年已耗時數年的受害訴訟,企業與民間的對峙期間,負責居間調解的官方環境廳調整局局長山內豐德,忽然自殺身亡。
一九九一年二十八歲的導演是枝裕和,因執導「但是⋯⋯割捨福祉的時代」紀錄片,過程中,被山內豐德這個人物深深吸引,於是為追溯山內的生平,閱讀瞭他留下的大量信件、詩、隨筆和論文等,更重要的是採訪瞭山內夫人等許多相關人士,拚構山內五十三年的人間軌跡,寫下是枝第一本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本的Nonfiction。雖然是水俁病背景,但是跳脫瞭紀實報導的框架,更多是無比惋惜一位愛好文藝的菁英如何在官僚這個職業上,沒能跳脫自身的美學、誠實,和誠實造成的衝突,以至於自我毀滅。而這同時,他也在叩問日本當真有「福祉社會」存在的可能?
「隨著年齡增長,人們也在心中失去瞭『但是』這個詞。於是,人們將這個詞變成瞭『盡管……』這般藉口,不斷活下去。或許山內無法原諒這一點。」是枝裕和如是說。
著者信息
是枝裕和
電影導演、製片人。一九六二年生於東京。一九八七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院文藝學科後,進入TVMAN UNION,主要負責執導紀錄片節目。一九九五年以首度執導作品《幻之光》,於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榮獲Golden Osella奬。二〇〇四年《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使得演員柳樂優彌以史上最年輕身分,於坎城影展榮獲最佳男演員奬。其他執導作品如《下一站,天國!》(一九九八)、《花之武者》(二〇〇六)、《橫山傢之味》(二〇〇八)、《空氣人形》(二〇〇九)、《奇蹟》(二〇一一)等。二〇一二年,首度負責連續劇《Going My Home》(關西電視颱、富士電視颱)的編劇、導演。二〇一三年由福山雅治主演之《我的意外爸爸》榮獲第六十六屆坎城影展評審團奬。二〇一八年《小偷傢族》獲第七十一屆坎城影展金棕櫚奬。
譯者簡介
郭子菱
東吳大學日文係畢業,京都同誌社大學交換生。現為自由譯者兼插畫傢,錶達齣文字與圖像的意境,即是對工作的堅持。譯有《江戶那些事:穿越三百年老東京,原來幕府將軍和庶民百姓是這樣過日子的》、《動物醫生的熱血日記》、《職場問題地圖》等作品。
圖書目錄
序章 遺書
第一章 記憶
第二章 救濟
第三章 電話
第四章 背影
第五章 代價
第六章 誤算
第七章 餐桌
第八章 不在
第九章 迴傢
第十章 結論
第十一章 忘卻
終章 重逢
後記(單行本)
山內豐德年錶
後記(文庫版)
圖書序言
常聽人說,無論電影或小說,處女作都融入瞭該作者的一切。假使這個論點成立的話,那對我而言,處女作顯然就不該是電影,而是這本《雲沒有迴答》。
這本紀實報導,是以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二日富士電視颱深夜播放的NONFIX《但是⋯⋯在捨棄福祉的時代》紀錄片為基礎,幾經取材寫成的作品。
第一次自己企劃、導演,將取材編纂成六十分鍾長的節目,過程經曆瞭許多睏難。最主要的,是我從未有過採訪這類「社會議題」的經驗,大學時也沒學過記者的專業訓練,純粹一介新手製作人,當時恐怕也完全不瞭解何謂取材吧。
這次重新迴顧二十多年前寫的文章,讓我憶起瞭某些事。當時,我針對本書的主角,名為山內豐德的菁英官僚自殺一案,想要採訪水俁病訴訟狀況,因而前往環境廳(當時)的廣報課,將載明採訪宗旨的企劃書交給對方。對應的窗口負責人意外的親切。不料,幾天後我緻電確認結果時,對方的態度卻有瞭極大的轉變。
「我們拒絕採訪。」
他直截瞭當地說。為什麼呢?我反問,對方如下迴應。
「你不是電視颱的人對吧?我們沒有義務接受像你這種承包商的採訪。」
說完,他就掛掉電話。之後電視颱的工作人員也打電話來,叮囑我:「製作公司的人要是擅作主張,我們會很睏擾。」
透過話筒,我充分感受到環境廳官員所謂「承包商」意涵的侮衊,如今迴想起來,甚至湧起一股怒火攻心的激憤,然而當時的我,卻持著完全不同的情緒,放下話筒。
「是啊……我不是記者。」
假使我並非因為能力,而是因為立場和所屬團體不同,一開始就被為國民「知的權利」而採訪的記者所隸屬的媒體排除在外,到頭來,我又能憑藉什麼,將攝影機對著採訪對象,遞齣麥剋風呢?懷抱著這種如同青春期煩惱般,對自身存在意義的自問自答,我繼續進行取材。多麼可悲的齣航。然而,意外的,問題的答案竟然就在取材的對象身上。
既然取材的山內豐德已經不在人世,再怎麼說都應該採訪他的太太。當然,我把攝影機和麥剋風遞給她,並不是為瞭讓對方說齣失去丈夫的悲傷。而是希望能藉著夫人最貼近他的視角,闡述山內對福祉政策的投入及挫摺。
我造訪瞭山內夫人位於町田的自宅,在被領往玄關旁的榻榻米房間裏,含糊不清、毫無自信地說明瞭採訪宗旨。
(看來就算被拒絕也無可奈何吧……)
還記得話說到一半,我就已經陷入這種半放棄的悲慘狀態。但盡管如此,夫人說齣來的話,卻與我想像的截然不同。
「對我來說,丈夫的死完全是私人的事,不過從他的立場來看,他的死也有著公共意義吧。這麼一想,我也認為由我來闡述丈夫對福祉的態度,會是丈夫所期望的。」
她把視綫一直落在自己手上,卻意誌堅定地接受瞭我的採訪。那就是一切的開端。
當時她口中的「公共」一詞,給予瞭我取材的憑藉,即便過瞭二十多年,我依然持續思考著有關電視颱外包製作節目一事,而那次採訪成瞭為它找齣意義的契機和緣起。
人類既然無法獨自生存,那麼,人生中就有一部分會不斷處在「公共」領域,公開個體的存在。「傳播」這種方式或「採訪」的行為,說穿瞭就是為瞭促成個體在公共領域和時間裏與他人相遇、時而衝突、進而成長的存在。
在此,我們沒有必要用「權利」和「義務」等某些帶有痛苦、一廂情願的詞匯。單就「廣播」來說,不僅相關工作的製作者、傳播者與演齣者,還有贊助者藉由齣資,觀眾藉由觀賞,促使這個與他人相遇的「公共圈」成熟發展,包容多元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都是在實踐參與社會的行為。至於這些是否為本意就暫且不談瞭,就結果而言,毋庸置疑,廣受歡迎。
二十八歲的我,當然不是因為考量到這些纔製播節目。然而心裏確實有某種意識在其中。無論節目,還是後來重新取材並齣版的這本紀實報導,我都想盡可能的意識到所謂的「社會性」,避免以聳動的方式來處理菁英官僚自殺一事。
話雖如此,我還是要說,現今與山內自殺的五十三歲僅僅一步之遙的我,重新審閱這本著作,驚訝地發現,書中描寫得最鮮明的部分,並非因「公共」而展開的福祉話題,而是有關夫妻相處模式這類完全屬於私領域的內容。這對夫妻如何相遇、相攜、苦惱、彆離,透過放映後重新取材,我纔知道當時目睹的,是一位被遺留下來的妻子正在進行的療傷過程(grief work)。藉由她的語言重現夫婦倆的身影,恐怕就是過程的一環。這纔是本書的核心吧(我幾乎可以斷言,本書不是我寫的。我隻是傾聽她的心內話,並動筆寫下來而已。這無關謙虛,而是事實)。就紀實報導如何評斷這意外的事態?或許各方見解分歧,但無論如何,該部分的描寫,無疑是讓這本著作脫離社會紀實框架的原因。
我不喜歡用議題或訊息這類詞匯來闡述或是被闡述作品。會被這類詞匯歸納的作品,鐵定是因為處理人的部分太弱瞭。我一嚮邊拍電影邊思考。「沒有人的存在是為瞭故事或議題。我們隻是像那樣的活著——生命翻滾於那些樣態的活著。我會想在電影中描繪這樣的人類,或許遠因就在於相遇本書中的這對夫婦,下意識受到瞭影響吧。我是這麼想的。果然,處女作融入瞭一切。」
這本《雲沒有迴答》是我的處女作,一九九二年時書名為《但是⋯⋯某福祉高級官僚 死亡的軌跡》,到二〇〇一年改以《官僚為何選擇絕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齣版。
這是我二十幾歲時寫的紀實報導,二十二年後三度齣版,對作者來說,實在是少有的幸褔。
在此,我想對給予我機會的編輯堀香織小姐,以及決定齣版的PHP研究所根本騎兄先生緻上謝意。非常感謝。期望在他們的熱情幫助下,能夠讓這部作品被更多讀者看見。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電影導演 是枝裕和
圖書試讀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四日上午九點。
山內知子在東京町田的傢中,接到一通電話。
是丈夫打來的。
「我接下來會失蹤。會是無法說明地點的行蹤不明……
除此之外,我沒辦法阻止北川長官前往水俁。
目前並非適閤前往水俁的狀況啊。
或許新聞會引起騷動,不過不需要擔心。
隻是,我想我會辭去公務員的工作……」
丈夫有氣無力說完後,便掛斷電話。
知子聽不懂這番話的含義,因而相當混亂。並非前往水俁的狀況,是指丈夫的身體狀況不好嗎?還是各種狀況都不好?光憑這通電話實在難以判斷。
九月二十八日,東京地方裁判所針對水俁病訴訟嚮國傢提齣瞭和解勸告,丈夫比起之前更形忙碌瞭。
他是個在傢隻字不提工作的人,不過,知子還是感受得到他在就任環境廳企劃調整局長的七月之後,工作量就增加瞭。
據說他大都超過淩晨十二點纔迴傢,迴傢後也會到二樓的房間,埋頭閱讀資料、做報紙剪報等,持續工作到半夜兩、三點。
隔天早上,知子上瞭二樓,經常發現丈夫就穿一件襯衫和袍子趴睡著。知子非常擔心不吃飯、工作有如著魔似的丈夫身體,都會事先準備維他命等營養劑,放在桌子上。
著手處理水俁病問題的這兩個月,他連星期天早上也會接到電話,按照指示前往工作,沒得休息。
九月下旬,知子得瞭感冒,咳嗽個不停,嚮來說話不會刻薄的丈夫竟罕見地對她說:「希望妳彆把感冒傳染給我。現在我可不能感冒。」S
備受寵愛的小狗五郎最黏丈夫瞭。一到晚上,牠會鑽到棉被裏,丈夫無論多疲纍也不會生氣,就讓五郎待在裏麵。知子擔心丈夫是否可以熟睡,也擔心自己的感冒傳染給對方會很不好意思,為此便將一直鋪在一樓房間裏的兩人被褥抽齣丈夫的,拿到二樓去。知子後來感到非常後悔。
到瞭十一月,丈夫益發憔悴,迴到傢後也毫不放鬆,漸漸變得神經質。
每天隻睡三、四個小時的日子持續瞭好幾個月,知子很擔心再這樣下去身體會弄壞,加上通勤往返還需要花上三個多小時,她便對丈夫說:
「如果把通勤時間拿來睡眠,身體比較能夠休息,那就不必擔心傢裏的事瞭,假使工作太晚,就住旅館吧。」
之後,工作時間晚瞭,丈夫就會住在旅館。不過,隻要當天是這樣的狀況,他一定會打電話報備「今天要住外麵」。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書名就足夠引人遐思,"雲沒有迴答:高級官僚的生與死"。光是這個名字,就勾勒齣一種深沉而宏大的敘事空間,讓人忍不住去想象其中蘊含的故事。我一直對那些在體製內經曆復雜變遷的人物故事很感興趣,因為他們的命運往往牽扯著無數的時代洪流和社會變遷。想象一下,在一個龐大而精密運轉的官僚體係中,一個身居高位的人物,他的每一個決定,每一次升遷,每一次沉浮,都可能像投入平靜湖麵的一顆石子,激起層層漣漪,影響著無數人的生活,甚至是國傢的走嚮。而“雲沒有迴答”,這四個字又帶著一絲神秘和哲學意味,仿佛暗示著某種命運的不可捉摸,或者是一種超越個人意誌的巨大力量在起作用。是自然規律?是曆史的必然?還是某種冥冥之中的安排?這種留白,反而讓故事的空間更加廣闊,讓讀者得以填補想象的空白,去揣測其中的深層含義。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描繪這位高級官僚的“生”與“死”的?是寫他如何憑藉智慧和手腕步步高升,贏得權力和地位?還是描繪他如何在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中,從雲端跌落,經曆人生的至暗時刻?“死”又僅僅是指肉體的終結,還是包括瞭權力的剝奪,名譽的掃地,甚至是精神的瓦解?這些都是我非常期待在書中找到答案的。
评分這本書的吸引力在於它所構建的那個龐大而壓抑的官僚體係,以及在這個體係中,一個高級官僚所經曆的起起伏伏。作者對於權力運作的描寫,是這本書的一大亮點。他並沒有簡單地將官僚描繪成冷酷無情的機器,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內心,去揭示他們在體製內的掙紮、妥協與堅持。那些看似微小的權謀,那些不動聲色的較量,都被作者描繪得淋灕盡緻。我能感受到那種身處高位的壓力,以及為瞭維持地位所要付齣的代價。而“生與死”的命題,在書中也得到瞭多層次的解讀。不僅僅是肉體的生與死,更是權力的生與死,名譽的生與死,甚至是精神的生與死。作者在處理這些宏大主題時,展現齣瞭極高的藝術技巧。他用一種近乎白描的手法,卻勾勒齣瞭一個龐大的世界,以及在這個世界中,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這本書讓我對官僚體係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也讓我開始思考,在看似堅固的體製背後,隱藏著怎樣的個人故事,怎樣的復雜人性。
评分讀完之後,我腦海裏縈繞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復雜情緒。這本書不僅僅是在講述一個人的故事,更像是在解剖一個時代的側影。作者的筆觸非常細膩,將宏觀的政治格局與微觀的人物內心世界巧妙地融閤在一起。我仿佛能看到那個時代特有的氣息,那些在會議室裏激蕩的言論,那些在深夜燈光下斟酌的公文,還有那些隱藏在笑容背後的算計與無奈。書中的人物,尤其是那位高級官僚,他的形象並非臉譜化,而是充滿瞭人性的矛盾和掙紮。他有他的雄心壯誌,也有他的脆弱和恐懼;他可能曾為瞭理想而奮鬥,也可能在現實的泥沼中迷失自我。這種立體的人物塑造,使得故事更具感染力,讓我能夠感同身受,去理解他所麵臨的睏境,去揣測他內心的掙紮。我尤其喜歡作者對於細節的刻畫,那些看似不經意的描寫,往往能勾勒齣人物的性格,或者暗示著某種潛在的衝突。比如,一次不經意的眼神交流,一個遲疑的停頓,或者是一句語焉不詳的迴答,都可能成為解讀人物內心世界的重要綫索。這讓我讀起來仿佛置身其中,成為一個旁觀者,靜靜地觀察著曆史的車輪滾滾嚮前,以及在這場洪流中,一個個鮮活生命的起起伏伏。
评分總的來說,這本書給我留下瞭非常深刻的印象。它不僅僅是一部關於官僚的書,更是一部關於人性、關於時代、關於命運的深刻反思。作者的文字功底非常深厚,語言簡潔有力,卻又飽含深意。在閱讀過程中,我多次被作者的洞察力所摺服,他能夠如此精準地捕捉到人物內心最深處的想法,以及時代變遷中最微妙的痕跡。這本書讓我有機會去審視那些在曆史長河中看似宏大卻又被模糊化的個體命運,去思考在巨大的時代洪流中,個人的選擇和掙紮究竟有多少意義。我從書中看到瞭權力的復雜性,看到瞭人性的多麵性,也看到瞭命運的無常。每一次翻開書頁,都像是在進行一場與曆史對話,與人性對話。那些發生在高級官僚身上的故事,雖然背景和時代可能與我有所不同,但其中所映射齣的關於權力、欲望、良知、妥協的探討,卻是跨越時空,具有普遍意義的。這種閱讀帶來的思考,遠比單純的故事吸引力更加持久。
评分這本書的結構安排得十分巧妙,讓人讀起來既有連貫性,又不失驚喜。作者似乎並不急於拋齣所有答案,而是層層遞進,引導讀者一點點地深入到故事的核心。在閱讀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常常會陷入思考,去反芻作者所呈現的每一個片段,去推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有時候,我會為主人公的某個選擇感到惋惜,有時候,又會為他的某種堅持感到敬佩。這種閱讀體驗,與其說是被動地接收信息,不如說是一種主動的探索和發現。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敘事節奏上的把控,有緊張的衝突,也有舒緩的沉思,恰到好處地吊足瞭讀者的胃口。而且,書中對政治運作的描寫,雖然深刻,卻並沒有顯得枯燥乏味,反而充滿瞭戲劇性。那些權力博弈中的微妙之處,那些復雜的人際關係,都被描繪得栩栩如生,仿佛能夠聽到那些隱秘的對話,感受到那些無聲的較量。“雲沒有迴答”這個意象,在書中也得到瞭很好的延展,它不僅僅是一個標題,更像是一種貫穿始終的哲學命題,在不同的情境下,以不同的方式被解讀和呈現。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