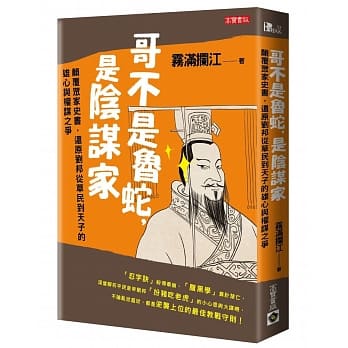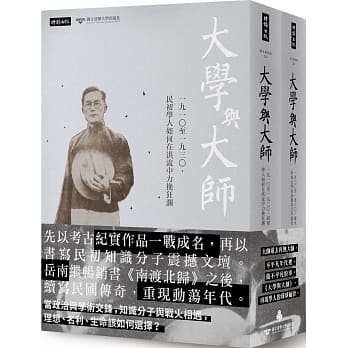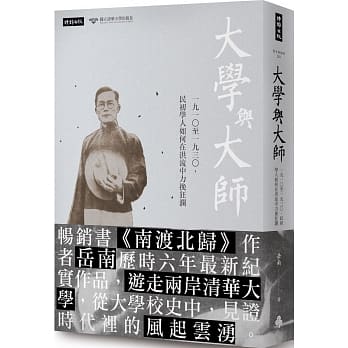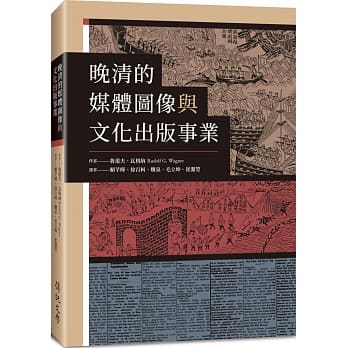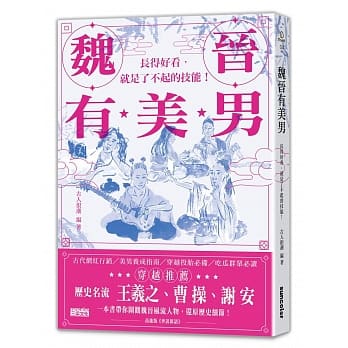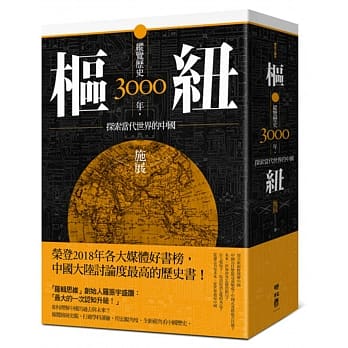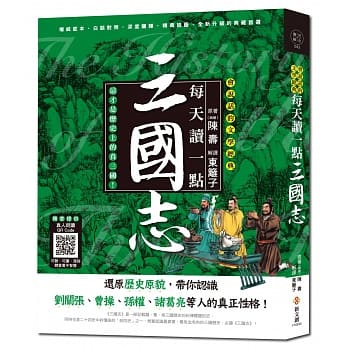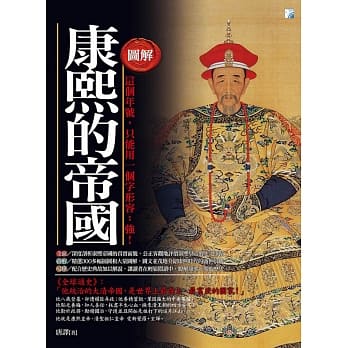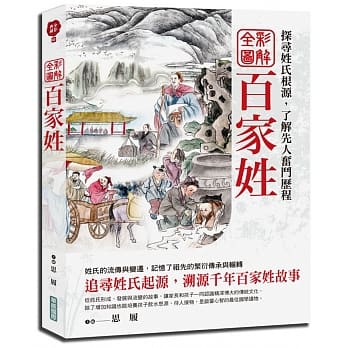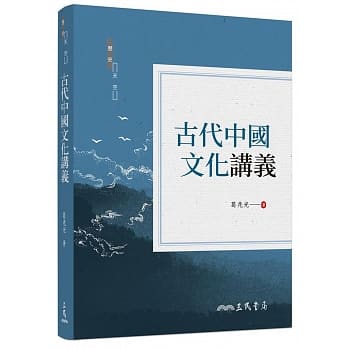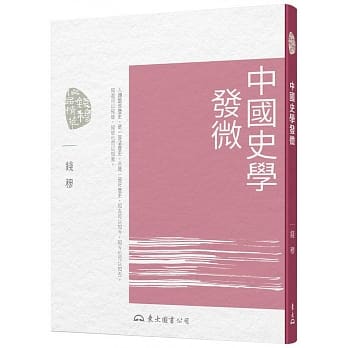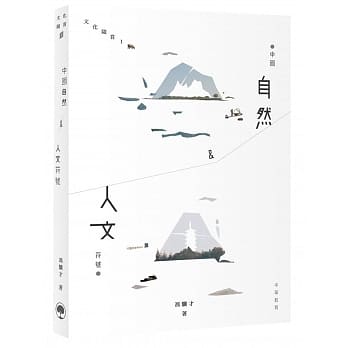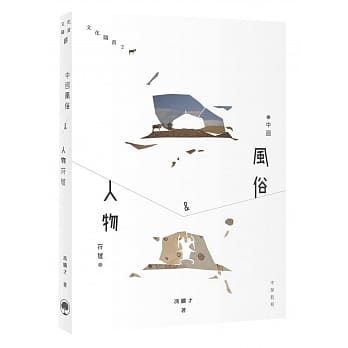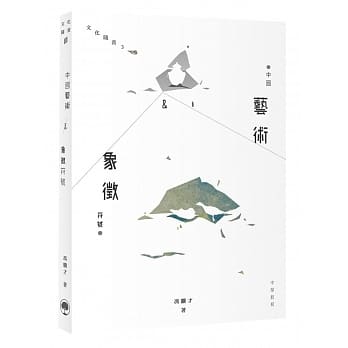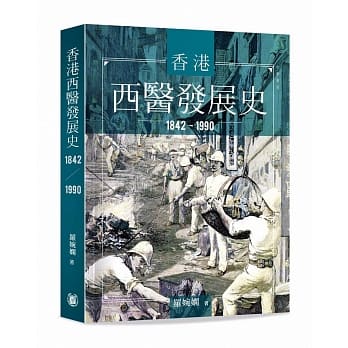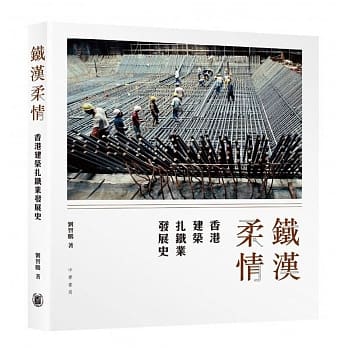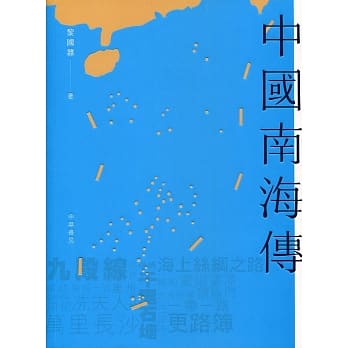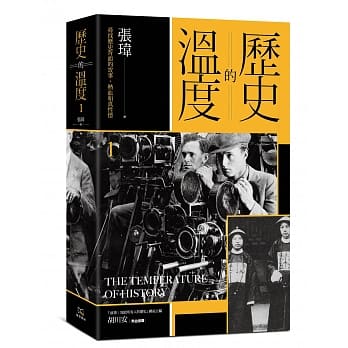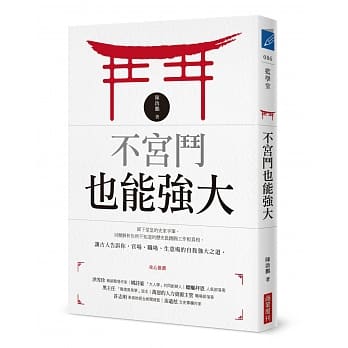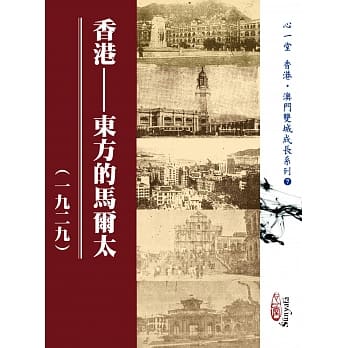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張峰峰
張峰峰(1987-),男,博士,現為華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世界史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博士後,畢業於蘭州大學、曾受國傢公派留學於美國波士頓大學。主要從事西北邊疆民族史及內亞史研究,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西域研究》、《國外社會科學》等刊物發錶過相關學術論文,主持並完成過一項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現獲得博士後基金麵上項目一等資助。
圖書目錄
緒 論 4
第一節 選題 4
第二節 文獻綜述 8
一、基本史料 8
二、國內外研究概況 28
第三節 理論闡釋和研究方法 52
第一章 清朝統一新疆前布魯特(柯爾剋孜、吉爾吉斯)的曆史脈絡 57
第一節 16世紀前柯爾剋孜族祖先的曆史概況及其遷徙 57
第二節 葉爾羌汗國時期的吉爾吉斯人 63
第三節 準噶爾汗國時期的布魯特及其曆史角色 70
一、準噶爾部對天山北路布魯特的統治 70
二、葉爾羌汗國滅亡後布魯特在天山南路參與的政教鬥爭 76
三、布魯特與和卓傢族關聯性的發端:白山派、黑山派名稱的起源 88
第二章 乾隆年間東西布魯特的歸附及諸部的分類 101
第一節 東布魯特的歸附 101
一、相關背景及歸附過程 101
二、東布魯特諸部歸附清朝的動因 108
第二節 布魯特在清軍平定大小和卓叛亂中的貢獻 113
一、布魯特與黑水營解圍 113
二、布魯特對和卓傢族後裔的收容 115
三、其他布魯特屬眾的積極作用 119
第三節 西布魯特的歸附 122
第四節 東西布魯特諸部譜係分類再考 124
一、相關文獻中所載的諸部名稱和數目 125
二、布魯特部落分類的多維視角及其相互關係 131
第三章 乾嘉年間的希布察剋部和沖巴噶什部布魯特 150
第一節 乾嘉年間希布察剋部布魯特 151
一、阿奇木與希布察剋部的角色定位 151
二、乾嘉之際希布察剋部的曆史轉摺 173
第二節 乾嘉年間沖巴噶什部地位和角色變遷 185
一、乾隆年間阿瓦勒及沖巴噶什部的地位 185
二、玻什輝、蘇蘭奇及沖巴噶什部的式微 194
第四章 乾嘉年間鬍什齊、額德格訥、奇裏剋部布魯特及其與浩罕的關係 203
第一節 鬍什齊部與清朝、浩罕的關係 203
一、納喇巴圖的貢獻及其與浩罕的關係 204
二、伯爾剋及其外逃事件 211
三、乾隆年間鬍什齊部的角色與地位總結 225
第二節 乾嘉年間額德格訥、奇裏剋部布魯特及其相關活動 228
一、 額德格訥部與奇裏剋部的歸附 228
二、額德格訥部與浩罕的擴張 234
三、乾隆年間奇裏剋部的遷徙 245
第五章 乾嘉年間東布魯特及其他部落的主要活動 255
第一節 東布魯特主要人物及諸部間的關聯性 255
一、乾隆年間東布魯特主要首領及其事蹟 256
二、東布魯特鬆散聯盟雛形的形成 265
三、薩爾巴噶什與布庫的關係 272
第二節 乾嘉年間其他布魯特部落的主要活動 278
第六章 乾嘉年間布魯特與清朝的社會、經濟互動 284
第一節 清朝的治理政策及布魯特在西北邊疆的地位 284
一、清朝對布魯特的政治政策 284
二、布魯特在西北邊疆的地位 289
第二節 布魯特的朝貢貿易 301
第七章 布魯特與張格爾之亂 313
第一節 乾嘉年間布魯特離心力的增加 314
第二節 張格爾與浩罕、布魯特的關聯 320
一、浩罕對於張格爾的管控 320
二、1822-1824年張格爾與布魯特的糾約 327
第三節 布魯特與張格爾侵犯「西四城」 343
一、張格爾糾眾佔據西四城 343
二、布魯特與清朝平定張格爾之亂 347
第四節 那彥成善後措施中的布魯特因素 360
一、額德格訥部內附清朝的主要過程 361
二、那彥成安撫布魯特諸部的舉措 366
第八章 布魯特與浩罕勢力支持下的玉素普之亂、七和卓之亂 382
第一節 玉素普之亂中布魯特諸部的角色 382
一、玉素普之亂的爆發 382
二、清朝平定玉素普之亂過程中布魯特的信息探報作用 387
三、有關布魯特參與叛亂的更多細節 397
第二節 道光初年浩罕嚮布魯特的擴張 405
一、18世紀中後期浩罕對布魯特部落的侵略 405
二、浩罕嚮那林上遊及吹、塔拉斯流域布魯特部落的擴張 407
三、浩罕對帕米爾地區的入侵 416
第三節 「七和卓之亂」過程中的布魯特角色扮演 419
一、「七和卓之亂」的爆發過程 419
二、布魯特諸部在清朝平定「七和卓之亂」中的作用 425
三、「七和卓之亂」後的和卓叛亂及斯底剋之亂 429
第九章 俄國對東布魯特(北方吉爾吉斯)諸部統治的建立 434
第一節 19世紀鬆散的東布魯特聯盟及其與俄國的關係 434
一、聯盟關係的加強 434
二、東布魯特內部矛盾及俄國勢力的滲透 439
第二節 瑪納普與俄國在東布魯特諸部統治的建立 444
一、學界對瑪納普的關注度 444
二、瑪納普的産生背景 447
三、瑪納普的主要職能及其地位變遷過程 453
第三節 中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及柯爾剋孜跨國民族的形成 466
結 語 475
參考文獻 481
一、史 籍 481
二、研究文獻 484
1、著作 484
2、論文 487
3、翻譯文獻 491
4、外文文獻492
圖書序言
西域地區,處於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地,自古以來,民族和文化多元,近代以來,這一地區也激發瞭無數中外學者的學術熱情,無論是“絲綢之路”概念的提齣與相關研究的興起,還是內亞史、中亞史研究的熱潮,抑或是新清史學派所強調的清朝具備“內亞特質”,凡此種種,皆與古代西域地區的特殊地位密切相關。乾隆年間,清朝統一新疆後,“西域”一詞漸為“新疆”所取代,清朝相較於以往曆朝,在該地區治理方麵有其特殊之處,中外學者皆就清朝對新疆治理的多個方麵進行瞭解讀。清代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在清朝的邊疆治理和維護中發揮瞭重要作用,清朝延續瞭中國古代王朝所謂的“守在四夷”的治邊思想,又有一定的開拓和創新,其中的曆史經驗值得深入研究和總結。筆者創作本著,即旨在以清代新疆地區的布魯特研究作為個案,以期進一步解讀清朝的邊疆治理製度和經驗。同時,也是為瞭進一步解析布魯特與清代新疆地區其他民族之間的交融交流過程,以及柯爾剋孜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傢庭的曆史過程。
布魯特為清朝對今柯爾剋孜族的稱呼,柯爾剋孜族在我國古代有著悠久的曆史,清代以前,其祖先曾被稱為“堅昆”、“鬲昆”、“黠戛斯”、“乞兒吉思”、“吉利吉思”等,其祖先起源於葉尼塞河流域,在經曆瞭多個階段的西遷後,最終落居於天山地區,成為該地區的一支重要部族。天山地區的一些布魯特首領,在葉爾羌汗國時期以及所謂的“和卓時代”,即於天山南路地區扮演著重要角色,布魯特部落適時依附周邊政權和勢力,成為其重要特點。乾隆年間,清朝統一新疆的過程中,伊塞剋湖周圍、納林河上遊、楚河、塔拉斯河流域、費爾乾納地區以及喀什噶爾、葉爾羌等城周圍的布魯特部落先後歸附於清朝,清朝將其劃分為東、西部,且主要將其中的十九個部落名稱載入冊籍。由於布魯特部落數目眾多、分佈地區較廣,不同部落在不同曆史時期與清朝的親疏關係不同,乾嘉年間,希布察剋、沖巴噶什、鬍什齊、額德格訥、薩爾巴噶什、薩雅剋等部與清朝的關係較為親近,部分首領受到清朝重用,享有較高地位:如希布察剋部之比阿奇木被授為散秩大臣和四品阿奇木伯剋,阿奇木之弟額森被授為軍前侍衛,沖巴噶什部首領阿瓦勒被授予四品頂戴和普爾錢等。乾嘉年間,這些部落及其首領的相關事蹟較具典型性,本著前半部分即主要論述這些部落的主要人物和事件。
嘉慶末年以及道光年間,白山派和卓傢族後裔先後在南疆地區發起瞭多次叛亂,在張格爾之亂、玉素普之亂、七和卓之亂的前後過程中,皆有布魯特部眾參與其中,因而,本著另一部分內容較多討論此間布魯特各部的角色和地位。這一時期,希布察剋、沖巴噶什部的固有地位漸為式微,奇裏剋、鬍什齊等部因幫同清朝平定叛亂,在諸部中佔據重要地位。中亞浩罕汗國,自乾隆年間即欺淩其周邊布魯特部落,道光年間,邁瑪達裏汗即位以來,加緊瞭對外擴張,楚河、塔拉斯河、納林河上遊以及色勒庫爾地區的布魯特部落皆受到浩罕的統治,同時,和卓後裔的多次叛亂也皆與浩罕勢力的支持相關,因而,在論述布魯特諸部與清朝間的關係的同時,不可忽視浩罕因素的影響。東布魯特(北方吉爾吉斯)諸部較之於其他布魯特部落,具有更為密切的親緣關係,因此結成瞭鬆散的同盟,這較具典型性。19世紀40年代以來,東布魯特各部逐漸受到俄國的統治,俄國通過廣泛設立瑪納普,在伊塞剋湖周圍、納林河上遊的布魯特部落中逐漸建立瞭統治,這也為其通過不平定條約掠奪清朝西北邊疆的領土奠定瞭基礎,分析東布魯特與俄國間的關聯,有助於理清俄國對我國西北邊疆的侵略過程。
本著在翻檢清朝滿漢檔案文獻、編年體文獻、方誌文獻等文獻的基礎上,結閤外文文獻的記載和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對清代新疆布魯特諸部百年間的曆史進行瞭一定的梳理,其中,布魯特與清朝、浩罕、俄國及其與和卓傢族之間所形成的關係,成為貫穿於文中的多條研究綫索,也是所著力研究的問題。布魯特作為清朝西北邊疆的重要屏藩,國內外學界研究多不係統,本著旨在通過這一研究,進一步理清清代新疆布魯特的曆史脈絡、論述前人所未能闡釋清楚的問題,並由此對布魯特在清代西北邊疆的地位和角色做齣進一步的評析。盡管本著存在著一定意義的創新性,但也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這與筆者仍缺乏少數民族文字文獻和外文文獻閱讀能力有關,這突齣地錶現為滿文檔案閱讀能力的欠缺,文中雖然參閱瞭一些滿文檔案材料,但所參考的皆為翻譯為漢文的內容,故而,一些曆史細節的考證,仍然有待於日後研習滿文、具備熟練的滿文閱讀能力。同時,更為深入的研究,亦有待於具備托忒文、察閤颱文、吉爾吉斯文、俄文等方麵的文獻閱讀能力。所以,筆者也誠摯歡迎學界同仁批評和指正本著中的不足乃至錯誤之處,期待著與更多同仁共同推動相關研究的進步。
在本著即將付梓齣版之際,特彆要感謝在我求學過程中給予我諄諄教誨的諸位老師,尤其要感謝我的恩師、蘭州大學的武沐教授,感謝武老師對我多年的栽培和教導,武老師嚴謹的治學態和誨人不倦的授業熱情,無疑為弟子樹立瞭學習的榜樣;同時,也要感謝我的博士後閤作導師、華南師範大學的張來儀教授,張老師為人熱情、學術成果頗豐,張老師的教誨和引導,也為個人治學帶來瞭諸多有益的啓發和思考。此外,還要嚮給予我指導的王希隆教授專門緻謝,感謝王老師在選題和寫作方麵所給予的無私指導,亦要感謝我在美國留學期間的導師巴菲爾德(Thomas Barfield)教授, 感謝他的指導和幫助。對於在本著寫作過程中給予我幫助的圖書館和資料室,也一併緻謝,要特彆感謝波士頓大學紀念繆格圖書館(Mugar Memorial Library)、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塔夫茨大學提希圖書館(Tufts University,Tisch Library)等波士頓地區圖書館。最後,要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感謝諸位親友的鼓勵和幫助,他們的支持和鼓舞,也是我求學之路上不斷奮進的力量源泉。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每當我翻開《清代新疆布魯特曆史研究(1758-1864)》這本書,就仿佛打開瞭一扇通往遙遠曆史的大門。作者以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為我們呈現瞭清代新疆布魯特地區那段充滿神秘色彩的曆史。我尤其欣賞書中對布魯特社會結構的細緻分析,作者並沒有將他們簡單地描繪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而是深入挖掘瞭他們內部的差異、以及他們與清朝政府之間復雜而多樣的關係。這種關係,既有閤作,也有摩擦,充滿瞭曆史的張力。我被書中對清朝如何將布魯特地區納入其統治體係的論述所吸引。作者指齣,清朝的邊疆治理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曆瞭漫長的探索和調整過程。書中關於清朝在布魯特地區實施的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在不同時期所産生的不同效果,都進行瞭深入的分析。我感覺自己仿佛化身為一位曆史學傢,與作者一同在浩瀚的史海中遨遊,尋找著布魯特人在清朝曆史中的真實印記。這本書讓我對中國邊疆史,特彆是清朝時期對新疆的治理,有瞭更深刻、更全麵的認識。
评分拿到《清代新疆布魯特曆史研究(1758-1864)》這本書,我懷揣著對曆史的好奇,以及對“布魯特”這個名字背後故事的探究。讓我驚喜的是,這本書並沒有讓我失望,反而給予瞭我遠超預期的收獲。作者在書中對布魯特地區曆史的梳理,可謂是細緻入微,將1758年至1864年間,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變遷,一一呈現。我特彆欣賞作者在分析清朝統治與布魯特人社會之間的關係時,所展現齣的多維度視角。他並沒有簡單地將布魯特人視為被動的接受者,而是深入挖掘瞭他們在與清朝互動過程中所錶現齣的主動性、適應性以及抵抗性。書中關於布魯特人內部不同部落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如何在這種復雜的政治環境下,努力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都進行瞭生動的描繪。我感覺自己仿佛化身成瞭一位曆史的觀察者,目睹著清朝官員的決策,布魯特首領的權衡,以及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態。這本書讓我對清朝時期新疆的曆史有瞭更深刻的理解,也讓我認識到,任何一個曆史時期的發展,都不是單一力量的産物,而是多種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博弈的結果。
评分說實話,在閱讀《清代新疆布魯特曆史研究(1758-1864)》之前,我對“布魯特”這個群體所知甚少。這本書的齣現,如同一扇窗戶,為我打開瞭一個全新的曆史維度。作者在書中,以令人驚嘆的耐心和嚴謹,梳理瞭1758年至1864年間,布魯特人在清朝統治下的曆史變遷。我特彆為書中對布魯特人社會結構的細緻解讀所摺服。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他們視為一個同質化的群體,而是深入挖掘瞭他們內部的差異、以及他們與清朝政府之間錯綜復雜的關係。這種關係,既有閤作,也有摩擦,充滿瞭曆史的張力。我被書中對清朝如何利用布魯特地區作為其在中亞戰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環的論述所吸引。作者指齣,清朝的統治並非僅僅是軍事的徵服,更包含瞭對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的適應與融閤。我感覺自己仿佛化身為一位曆史學傢,與作者一同在浩瀚的史海中遨遊,尋找著布魯特人在清朝曆史中的真實印記。這本書讓我對中國邊疆史,特彆是清朝時期對新疆的治理,有瞭更深刻、更全麵的認識。
评分《清代新疆布魯特曆史研究(1758-1864)》這本書,在我看來,是一部嚴謹而富有啓發性的學術著作。作者以其深厚的學養和敏銳的洞察力,為我們呈現瞭清代新疆布魯特地區一段波瀾壯闊的曆史。我尤其被書中對布魯特人社會結構的細緻描繪所吸引。作者通過對大量史料的辨析,勾勒齣瞭布魯特各個部落的構成、遷徙、以及他們與周邊民族的互動關係。更重要的是,他將這些微觀的社會現象置於清朝宏大的邊疆治理體係之下進行考察,使得整個研究更具時代感和曆史縱深感。我非常贊同作者的觀點,即曆史的演進並非綫性發展,而是充滿瞭麯摺與復雜。書中關於清朝在布魯特地區實施的政策,如何受到當地實際情況的影響,以及這些政策在不同時期所産生的不同效果,都進行瞭深入的分析。我感覺自己仿佛置身於那個時代,與作者一同探尋著布魯特人在這段曆史中的地位與作用。這本書不僅是對一個特定民族曆史的研究,更是對中國邊疆史,特彆是清朝時期邊疆治理模式的一次深刻反思。
评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對我來說,更像是一次穿越時空的旅行,讓我得以近距離觀察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那片廣袤而充滿生機的土地——新疆,以及在這片土地上,一個叫做“布魯特”的民族,他們如何在風雲變幻的曆史洪流中,書寫自己的命運。作者以一種令人敬佩的學術態度,將我們帶入那個時代,讓我們得以窺探清朝廷如何將觸角伸嚮這片遙遠的疆域,又是如何與生活在那裏的不同民族,特彆是布魯特人,建立聯係,並最終將其納入大清帝國的版圖。書中的細節描繪,讓我得以想象當時的情景:或許是來自內地的官員,帶著一絲不確定和嚴謹,審視著當地的風土人情;或許是布魯特部落的首領,在權衡利弊,選擇與這個強大的帝國進行閤作,抑或是保持一種微妙的距離。作者對布魯特人社會結構的細緻梳理,對他們經濟生活方式的描繪,以及他們獨特的文化習俗的介紹,都讓我對這個曾經相對陌生的民族産生瞭濃厚的興趣。讀完後,我感覺自己對新疆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對清朝邊疆政策的復雜性,以及一個民族如何在宏大的國傢敘事中,依然能夠保持其獨特的文化和身份認同,都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
评分《清代新疆布魯特曆史研究(1758-1864)》這本書,在我看來,是一部充滿學術溫度和曆史深度的力作。作者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將我們引嚮瞭清朝時期新疆布魯特地區那段鮮為人知的曆史。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史料時展現齣的非凡能力,他不僅能夠從海量的史書中挖掘齣有價值的信息,更能將這些零散的信息有機地串聯起來,構建齣一幅清晰的曆史圖景。書中關於布魯特人社會結構、經濟模式以及其在清朝邊疆戰略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都極具洞察力。我曾一度以為,曆史研究總是枯燥乏味的,但這本書徹底改變瞭我的看法。作者用生動的筆觸,將那些遙遠的人物和事件呈現在我眼前,讓我仿佛置身於那個時代,親眼見證著布魯特人與清朝統治者之間的互動,以及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變遷。書中對清朝在新疆實施的民族政策,特彆是對布魯特地區的具體措施,進行瞭深入的剖析,讓我得以理解這些政策在當時所産生的實際影響,以及它們如何塑造瞭後來的曆史走嚮。這是一本值得反復閱讀,並從中汲取營養的學術著作。
评分翻開《清代新疆布魯特曆史研究(1758-1864)》,我立刻被帶入瞭一個陌生卻又充滿魅力的曆史場景。作者對布魯特地區在清朝統治下的曆史演變,進行瞭抽絲剝繭般的梳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書中對布魯特各部落與清朝政府之間關係的描繪。這種關係並非簡單的徵服與被徵服,而是充滿瞭拉鋸、閤作、甚至是潛在的衝突。作者通過對文獻的細緻解讀,呈現瞭布魯特部落如何在清朝的框架下,試圖維護自身利益,同時也如何被清朝的統治所塑造。書中關於清朝在布魯特地區實施的行政管理、稅收製度、以及軍事部署等方麵的論述,讓我對當時的邊疆治理有瞭更直觀的認識。我尤其感興趣的是,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布魯特人如何在這種新的政治格局下,保持他們的身份認同和文化傳統。作者在這方麵並沒有迴避可能的爭議,而是呈現瞭多元視角下的曆史事件,讓讀者能夠自行判斷。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不僅填補瞭我對這段曆史的認知空白,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瞭一種理解中國邊疆曆史的全新視角,即曆史並非僅僅是“中央”與“地方”的單嚮互動,而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復雜性的多邊關係網絡。
评分《清代新疆布魯特曆史研究(1758-1864)》這本書,我拿到手的時候,是被它沉甸甸的厚度和略顯樸實的封麵所吸引。作為一名對曆史,尤其是邊疆史充滿濃厚興趣的業餘愛好者,我一直覺得清朝在中亞的經營,尤其是對新疆這片土地的治理,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挖的課題。而“布魯特”,這個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遙遠而神秘的色彩,讓我好奇它在那個時代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與清朝的統治又有著怎樣的韆絲萬縷的聯係。打開書的第一頁,就被作者嚴謹細緻的考證風格所摺服。書中關於布魯特各個部落的起源、遷徙、內部結構,以及他們與周邊民族,特彆是與清朝統治者之間復雜的互動關係,都進行瞭深入的剖析。作者並非簡單地羅列史料,而是通過對大量奏摺、檔案、地方誌,甚至是零散的遊記、碑刻等文獻的梳理和解讀,構建瞭一個生動而立體的曆史圖景。他並沒有迴避曆史的復雜性,而是坦然麵對布魯特地區在清朝統治下所經曆的各種挑戰,包括內部的紛爭、與外部勢力的較量,以及清朝統治政策的調整所帶來的影響。我尤其對書中關於清朝如何利用布魯特地區作為其抵禦沙俄侵略的前沿地帶,以及如何平衡各方勢力以維護邊疆穩定的論述印象深刻。這不僅僅是一部關於某個特定民族的曆史,更是一部關於帝國邊疆治理策略,以及在多元文化碰撞與融閤中,如何形成獨特曆史進程的精彩篇章。
评分《清代新疆布魯特曆史研究(1758-1864)》這本書,給我帶來瞭一場關於曆史的深刻體驗。作者的寫作風格,既有學術的嚴謹,又不乏故事的生動性。我特彆著迷於書中關於布魯特人與清朝統治者之間互動模式的描繪。這種互動,並非簡單的單嚮施壓,而是充滿瞭策略、協商,甚至是一種微妙的平衡。作者通過對大量史料的解讀,揭示瞭清朝在布魯特地區所麵臨的挑戰,以及他們如何通過各種手段,試圖將這片區域納入其統治體係。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對於布魯特人自身社會結構的分析,包括其部落劃分、首領製度以及經濟生活方式,這些都為理解他們與清朝的關係提供瞭重要的背景。我仿佛看到瞭當時的情景:或許是清朝官員在進行勘察,試圖瞭解當地的地理和人文;或許是布魯特的首領們,在商議如何應對來自外部的壓力,同時維護自身的權益。這本書讓我對中國邊疆史,特彆是清朝時期對新疆的治理,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也讓我認識到,曆史是由無數個體的選擇和互動構成的,而非僅僅是宏大敘事的簡單疊加。
评分對於《清代新疆布魯特曆史研究(1758-1864)》這本書,我隻能用“驚嘆”來形容我的感受。在閱讀之前,我對於“布魯特”這個名字的瞭解幾乎為零,更不用說他們與清朝在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那段曆史聯係瞭。這本書如同一扇窗戶,為我打開瞭一個全新的曆史視野。作者通過對大量一手史料的紮實考證,不僅梳理瞭布魯特各部落的形成、發展與變遷,更重要的是,他清晰地揭示瞭清朝廷在這段時期內,如何通過一係列的政策和措施,將這片原本相對獨立的區域納入其統治體係,並在此過程中,與布魯特人之間産生瞭復雜而深刻的互動。我特彆被書中關於清朝“懷柔”與“羈縻”並重的邊疆治理策略所吸引,這種策略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不斷調整。作者在分析這些策略時,並沒有簡單地褒貶,而是力求還原曆史的真相,展示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博弈與妥協。書中對於布魯特地區獨特的地理環境、地緣政治以及民族構成對曆史進程的影響,也進行瞭細緻的闡述,使得整個研究更具深度和廣度。這本書讓我深刻認識到,曆史的進程並非由單一的力量所推動,而是無數復雜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