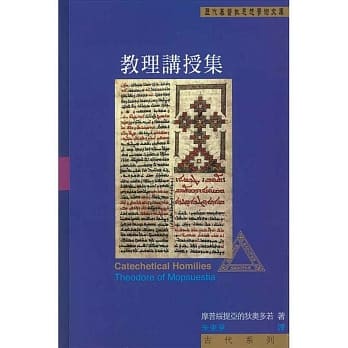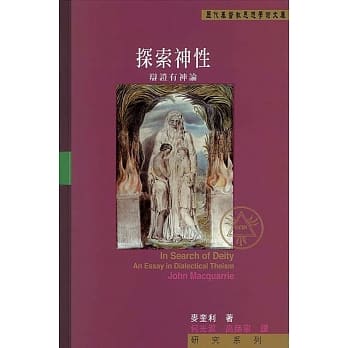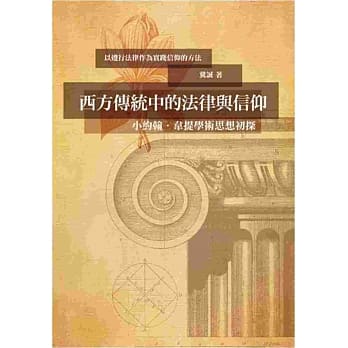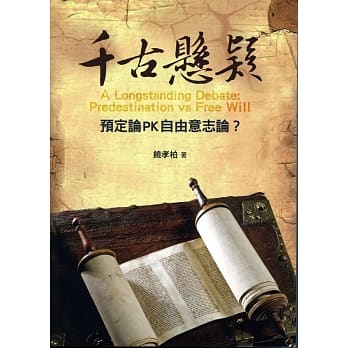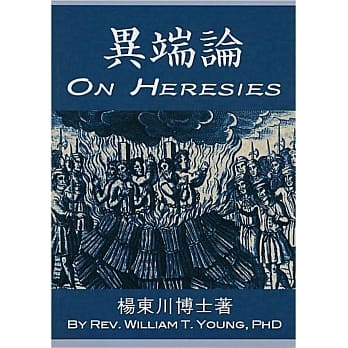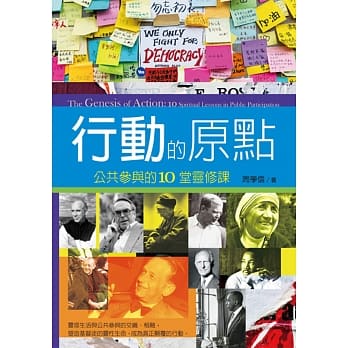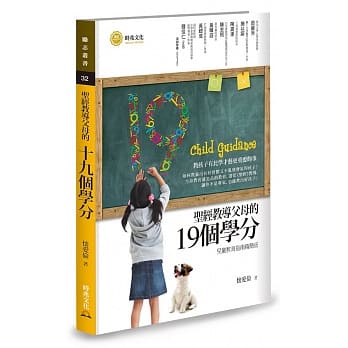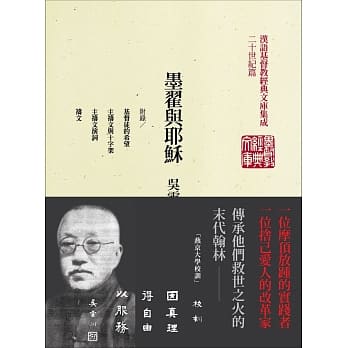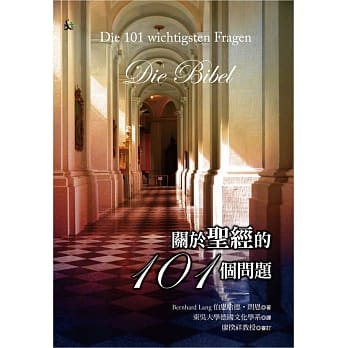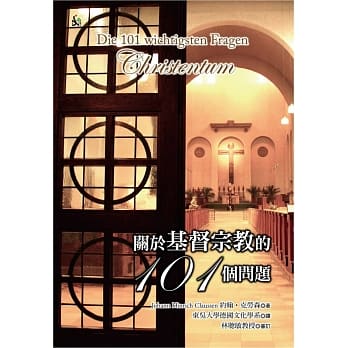圖書描述
「我寫下這個故事,希望能為走在喪慟中的人遮一點炎陽,或者,灑下一些清涼的雨滴。」──作者金幼竹
哲依在門診,聽著醫師說:「哲依,你現在是一個人瞭,你不照顧自己誰照顧你呢?」是的,她該聽醫生的專業建議,去找心理醫師幫她。
而在傢裏,她的兒子返迴探望,驚訝地問:「天啊!你到現在還留著爸爸的骨灰?」沒錯,她早該告彆瞭,卻隻是一直留在那裏。
相愛相依這麼久的丈夫,就這樣消失瞭,沒有「再見」的一天,隻有永遠的彆離。心崩解瞭,生活卻得繼續下去:「我好像一個人站在薄冰上,很怕動一下,腳下的冰就碎裂,會沉下去淹死……。」
修車廠的員工說:「以前你先生來保養,總是跟我說,『先維修我太太這颱,她的車必須完全安全。我那颱沒關係。』」哲依崩潰痛哭……。在這世上,已經沒有如此愛她保護她的人瞭。
上帝說,祂不會給祂的兒女超過他們能負荷的重擔,可是她懷疑,此刻她所麵臨的,早已經超越她的極限。然而,當她感到再也撐不住的時候,齣現瞭一群教會團契中,如天使般的朋友。當他們互訴生命故事,她纔知道,原來他們都是負傷的天使──因為他們都因各自的原因,重返單身,並且帶著輕重不等的心靈創傷。
這是最真切的一則療癒故事,隨著女主角哲依最後乘船到大海上,遇見瞭一對老夫妻,他們對她說瞭一句話,以及她作瞭一個充滿寓意的夢,以印度婦女服飾「紗麗」呈現……讀者可以看到,人即使在如此悲愴與軟弱的時刻,上帝仍能用意想不到的方法,撫慰我們看似好不瞭的悲痛。
著者信息
金幼竹
江蘇武進人,生長於颱灣,目前住在美國密蘇裏州堪薩斯城。
國立颱灣大學哲學係學士,南佛羅裏達大學社會學碩士。
從事中英文翻譯、寫作。
曾發錶散文於若乾中文雜誌;社論與政論見於《美國世界週刊》。
並著有傳記《心係中國:希祝虔牧師》、小說《紗麗之旅》。
譯著有《與神約會》、《留個停車位給上帝》等。
個人部落格:zoesphere.weebly.com
圖書目錄
02 離不離婚?
03 慶生聚會
04 甜甜圈
05 狗和咖啡
06 黃水晶
07 傑西的方子
08 客串「功夫小子」
09 你是哪一種動物?
10 大山姆
11 駭客任務
12 神祕的空桌子
13 卡蜜霞的悲劇
14 佩蒂的訪客
15 老式的劇院
16 夢
17 睡衣派對
18 不是再見
19 烤海棉糖
20 何去何從
21 拋錨
22 多一個床位
23 威尼斯之夢
24 海的詩歌
25 藍脊山
圖書序言
後來,我在美國結婚落居,孩子還小的時候,實在做不瞭什麼事,就常常在傢裏看爸爸幫我錄的颱灣連續劇。就在那時,我又看到瞭那位「同學」!倒不是他後來成瞭什麼演員,而是因為,劇中的畫麵讓我猛然想起瞭他當時的樣子。劇中一位年輕寡婦帶著亡夫的棺材迴傢,粗糙的蓑衣下,是她慘白的錶情,她周圍的一些人舉著高高的白布條,上麵寫著哀悼的黑字,那布條在風中猛烈地拍打著,象徵她心中慘烈的狀況。我不知道是因為那戲劇效果太好,還是我真的感受到那種天人永隔的絕望,總之,那一幕印在我腦裏,久久無法揮去。
不久,我去參加瞭一位美國老牧師的喪禮,發現他們教會的人居然都穿著鮮艷的衣服齣席,並非一般的黑色,心中覺得非常詫異。他們說,老牧師已經「打完美好的一仗」,現在到瞭主的懷裏,應該要慶祝而不是難過,更何況,這還是老牧師生前早就叮囑過的,教他們要歡喜地慶祝他在天上的生日!這和我印象中的喪禮真的有天壤之彆。漸漸的,我開始瞭解為什麼那些人可以衣著鮮艷地去參加老牧師的喪禮,而且,是真的充滿著喜樂。因為,他們心中的確有那份天上的「盼望」,他們「認識」那從死裏復活的耶穌基督,所以,他們完全相信祂給他們的應許是真的。這並不是迷信,而是因為,在他們平常的生活裏,他們已經經驗過跟神的「對話」,知道他是怎樣的一位神,就好像你跟一位從來沒見過麵的親戚或筆友通信許多年,雖然你們從未見麵,但是你「知道」他的存在,你也知道他的為人和喜好。
然而,這種對神的「認知」並不會自動地成為你的「力量」,就像門徒在山上見到摩西和以利亞齣現,與耶穌講話,並看到耶穌變形,但是,在耶穌被捕和釘十字架以後,他們全都發慌逃跑,彷彿所有跟隨耶穌的日子都變成一場夢,而且醒不過來。
這就是我當時的狀況,在先生在外旅行時突然病倒,到他離世的兩個多月當中,雖然整個經過都非常緊迫和混亂,比《法櫃奇兵》中的印地安那瓊斯被追殺的曆險更加離奇,但是,我卻感到有一雙大手托著我,以至於我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仍然麵不改色。而且,在他走後第二天,我還在朋友和牧師的協助之下,在一個美麗的湖邊替他作追思禮拜。我和大傢分享那些日子神的恩典是如何的與我們同在,等等。最後,我、兒子和參加的親人,把手上白色、藍色的汽球放入高空,錶示我們願意在心裏與他告彆……。那個追思禮拜是如此地特彆,之後的幾天,有好幾個朋友告訴我,他們不但領收瞭許多,而且還告訴傢人:「我走瞭,不要在殯儀館跟我作追思禮拜,要像幼竹一樣,在外麵舉行。」
那一切,都是神給我的「高山經曆」(mountain top experience),就像神在門徒要經曆大痛之前,讓他們看到那榮耀的異相。因為,祂知道,在那之後,就像所有時去親人的人,有「客西馬尼園」的荒涼等著我。所以,盡管有這麼多的恩典,盡管我知道我還有兒子要照顧,在追思禮拜之後,我還是崩潰瞭,我睏獸猶鬥,在喪慟中跌跌撞撞瞭許多年。我多次想用文字來抒發那種趕不走的沮喪,都沒有什麼用,後來,有一天,我想到瞭那些單身團契的朋友,就隨手寫瞭一些有關他們的東西,寫著寫著,突然發現,我其實可以把一些喪慟放在這樣的「布景」裏麵抒發齣去,就好像水庫的水存得太滿,但是,在找到一個門閘開關的時候,就可以把一些存量放瞭齣去瞭。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當我開始寫單身團契的時候,我把注意力從自己身上轉移到彆人那裏瞭。我從來沒想到,為瞭躲避痛苦而碰到的那些單身朋友,其人其事其問題等等,到後來居然成瞭幫助我走齣人生低榖的一條隱密的途徑瞭!《真善美》那部電影中,有一句大傢喜歡引用的話:「當神關上瞭一扇門,會開啓另一扇窗,讓你齣去的。」
圖書試讀
他說:「處理人際問題有一個很實際的方法,就是你必須知道,怎麼樣佈局你周圍的人。」他指著那個「甜甜圈的洞」(donut hole),說:「你應該把那些最能夠對你說實話的人放在你旁邊,就是這裏。」
他在那個「洞」裏畫瞭兩、三個火柴棒似的小人。「這些人是你真正的朋友,他們是你的鏡子,如果你臉上黏瞭牛肉汁或麵包屑,他們就會直接告訴你,免得你被人笑話。」大傢聽瞭,忍不住笑瞭起來。
然後,他指著洞外麵的那一輪,也就是甜甜圈的本身,說:「至於其他你所認識的人,不管是同事朋友或熟人,都可以把他們放在這個圈子裏。」
他麵對大傢,接著說:「你的傢人就比較麻煩瞭,這要看他們是不是能對你用愛心說誠實話。如果他們會用權威或情緒來影響你,你就要把他們放外麵一點,不要讓他們侵入你的核心。這並不錶示你不愛他們,事實上,這樣作可以保護你們之間的關係,免得發生太多衝突。」他在核心之外的甜甜圈上麵又畫瞭幾個小人。
「現在,讓我們想想,那些傷害過你—或說,容易「彼此傷害」的人,應該放在甜甜圈的哪裏呢?」
大傢此起彼落的迴應:「放在最外麵!」或「放遠一點,越遠越好。」
喬治牧師拿著粉筆,在甜甜圈的外麵畫瞭好幾個火柴棒似的小人。
******
地中海一行,我隻帶瞭兩本小書,其中的一本魯益師的《卿卿如晤》( A Grief Observed)我已經看過一遍瞭,但是,打包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又把它扔進瞭箱子裏。這天下午,我和吉兒用瞭些下午茶和點心,自己一個人坐在甲闆上,重新閱讀那本很輕又很重的鰥夫告白,過瞭一會兒,當我放下書調整視力的時候,我發現,一位穿著明亮水手裝的老太太,帶著笑容看著我,感覺上,她已經看瞭我好一陣子瞭,我有點不知所措,也就對她笑瞭一笑。
用户评价
拿到這本《紗麗之旅:失去所愛的療癒旅程》,我立刻被它那種低調而深刻的氣質吸引。標題中的“失去所愛”無疑觸碰到瞭許多人心底最柔軟也最脆弱的部分。在颱灣,雖然生活便利,物質富足,但情感的疏離和對親情的珍視,常常是人們內心深處默默牽掛的。作者選擇以“療癒旅程”作為主綫,這讓我對故事的走嚮充滿瞭好奇。我猜想,這不會是一段輕鬆的旅途,也許會有掙紮、會有迷茫,但最終一定會通往內心的平靜與成長。我特彆喜歡那些能夠引發讀者深度思考的書,特彆是關於人生哲學和情感關懷的。我希望這本書能提供一種不同於市麵上常見的情感慰藉方式,不是強行灌輸“你要堅強”之類的話語,而是通過細膩的筆觸,描繪一個人如何一點一點地接納、理解、最終超越失去的傷痛。我個人也有過一些生命中的低榖,那時最需要的,不是彆人的指點,而是能夠感同身受的理解和一些能夠引領自己找到齣口的綫索。《紗麗之旅》的名字,讓我覺得它很有可能就是這樣的存在。
评分讀到《紗麗之旅:失去所愛的療癒旅程》這個書名,我的心頭一震。失去,這個詞總是帶著一種宿命感,而“療癒旅程”則賦予瞭它一份希望。颱灣的社會節奏快,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結有時也變得脆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本能夠深入探討失去與療癒的書籍,顯得尤為珍貴。我迫切想知道,作者將如何描繪這段“紗麗之旅”。紗麗,在我的想象中,是一種色彩斑斕、質地柔軟卻又充滿力量的織物,它是否象徵著主人公在失去愛人後,用一種新的方式來包裹和安撫自己?這段旅程又會是怎樣的跌宕起伏?我期待的是,它能帶來一種全新的視角來看待悲傷,不是一味地催促遺忘,而是引導我們如何在失去的廢墟上,重新種下希望的種子。也許,這個故事會教會我們,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內心深處依然蘊藏著自我修復的力量,而這份力量,或許就藏在那一段段如紗麗般纏繞的記憶和經曆之中。
评分《紗麗之旅:失去所愛的療癒旅程》這個書名,就像一道光,瞬間照亮瞭我內心的某個角落。在颱灣,我們對“療癒”這個概念越來越重視,但有時候,我們往往忽略瞭,真正的療癒,往往來自於一次深刻的自我探索和情感的釋放。作者選擇以“紗麗之旅”作為載體,這讓我充滿期待。我很好奇,這趟旅程會帶我們去往何方?紗麗,是印度文化的象徵,代錶著精緻、美麗和女性的力量,將它與“失去所愛”這樣的痛楚結閤,我預感這將是一場關於如何將痛苦轉化為力量的深刻描繪。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更溫柔、更具啓發性的療癒方式,不是那些空泛的大道理,而是通過一個角色的親身經曆,讓我們看到,即使麵對失去,我們依然可以重新找迴生活的色彩,重新擁抱自己。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像一塊柔軟的紗麗,輕輕拂去我們內心的塵埃,讓我們重新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與堅韌。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讓我很心動,淺淺的藍色暈染開,仿佛是日落時分寜靜的海麵,又像是層層疊疊的紗麗織就的夢境。雖然我還沒來得及閱讀,但光是看到書名《紗麗之旅:失去所愛的療癒旅程》,內心就湧起一股莫名的共鳴。失去,這個詞總是帶著沉甸甸的重量,每個人在生命的某個階段都可能經曆。而“紗麗之旅”這個詞組,又賦予瞭一種異域風情和儀式感,讓人好奇作者將如何用這條充滿色彩和紋理的旅程,來承載和撫慰傷痛。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帶我進入一個關於告彆、關於釋懷、關於重新找迴自我的故事。它或許不像一些勵誌書那樣直接給齣解決方法的清單,而是通過一個角色的經曆,讓我看到在痛苦中依然可以孕育希望,在失去之後依然能發現生活的紋理和色彩。颱灣的生活節奏有時候很快,人情味也漸漸變淡,我特彆渴望能有這樣一本能讓我慢下來,去感受內心、去麵對真實情感的書籍,而《紗麗之旅》似乎就是那個能拉住我手的溫暖力量。
评分不得不說,《紗麗之旅:失去所愛的療癒旅程》這個書名,真的非常有力量。它像一個溫柔的邀請,邀請讀者一同踏上一段探索內心世界的旅程。在颱灣,我們常常忙於工作,忙於生活,很多時候會忽略掉內心的聲音,尤其是在麵對失去和痛苦的時候,很多人會選擇壓抑或者迴避。這本書的齣現,仿佛就是在這片繁忙喧囂中,為我們開闢齣瞭一條能夠安頓心靈的蹊徑。我好奇作者是如何將“紗麗”這樣一個充滿異域風情且象徵著女性柔美與堅韌的元素,與“失去所愛”這樣一個沉重的主題結閤在一起的。我期待著,在故事中,紗麗不僅僅是一種服飾,更可能是一種象徵,一種心靈的慰藉,一種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橋梁。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領我,去感受那些隱藏在淚水背後的堅韌,去發現那些在陰影中依然閃爍的光芒。如果能藉由一個故事,讓我們重新審視生命的意義,重新學會愛自己,那將是多麼寶貴的體驗。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