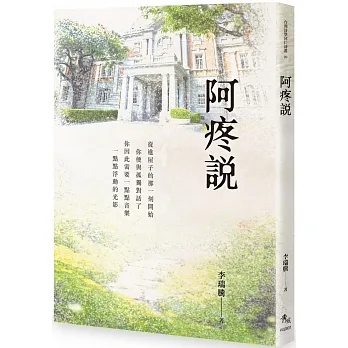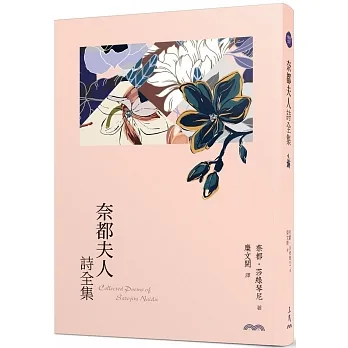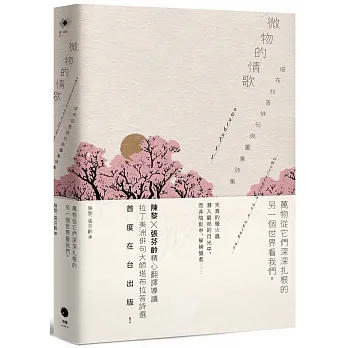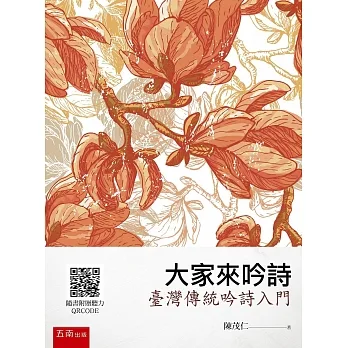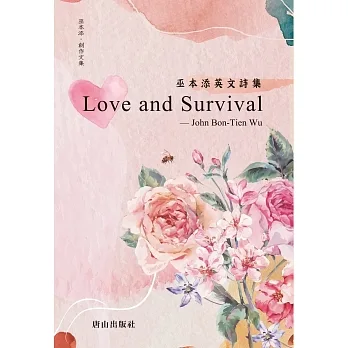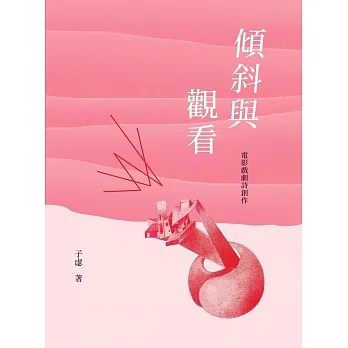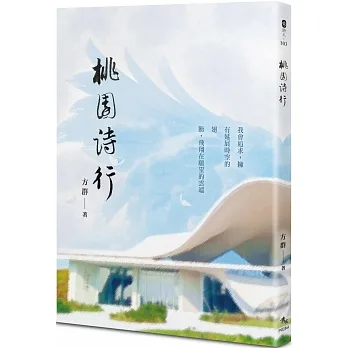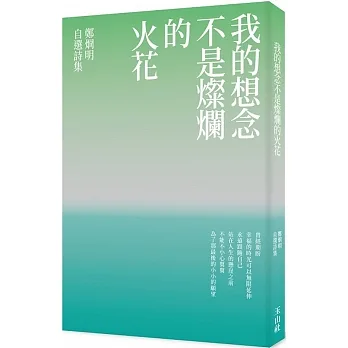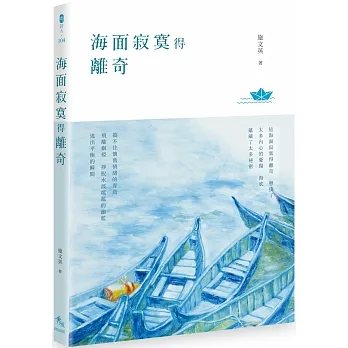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自序】
【序詩】一幢透天厝──給孟樊
【上捲】思無邪
天龍八部
說經
雌雄同室
當頭棒喝
觀音
波斯貓
飛
撕破臉
HOMOPHOBIA
種田
心臟手術
人人都愛馬奎斯
給吹鼓吹詩論壇開個玩笑
變形記
新版變形記
我是音樂傢
Poulenc小提琴奏鳴麯
羅生門
讀詩
夜讀佩雷的記憶
魑魅
罔兩
七竅
隱形人
太陽的自白
我的滿洋全席
學院之樹──悼念楊牧
獸──戲擬蘇紹連
鼕日的失眠晚課──給零雨
颱灣文學史
時鐘
IRREVERSIBLE
春光乍現
【下捲】念有情
二十一世紀新聊齋
曇花一現
影子
巴黎落霧
倫敦大雪
她離開的春夜
在濛馬特──用楊澤韻
謊言
在芝加哥──贈瘂弦
尼姑與茉莉花──戲擬水蔭萍
靜夜思
月下聽琴
溫暖的黑暗──用商禽韻
十一月
除夕
一則業配文
魔鏡.魔鏡
銅像
接力賽
我是畫傢
那件花襯衫的下落
在研究室
四壞球
S. L.和寶藍色筆記
夜以繼日
一整個月無夢
夢中之夢
夢中再夢
電梯
教師節日記
流質
【別捲】夫子自道
我的散文詩美學
【附錄】
四場震動──我讀孟樊散文詩四首/李桂媚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說真的,這本書的行文風格,簡直就像是喝瞭一口颱灣特有的高山茶,初入口時帶著一點點澀意,但迴甘之後,那種綿長而復雜的層次感就開始在舌尖上化開瞭。我特彆欣賞作者處理細節的方式,那種細膩入微的觀察力,常常讓我懷疑他是不是偷偷在我傢附近蹲點觀察瞭好一陣子。比方說,他描述早上市場裏阿婆買菜的場景,那種“油煙氣”混閤著“清晨的露水味”,那種感官的交織,不是那種乾巴巴的寫實,而是帶有強烈的個人情緒過濾後的再現。讀到某些段落時,我甚至能聞到那種味道,感受到那種清晨的微涼,這種沉浸感是很罕見的。而且,這本書的結構處理非常巧妙,它不是一個綫性的故事,更像是一係列被打散又重新拼湊起來的記憶碎片,每個碎片都有自己獨特的色彩和聲音。有時候它快得像一陣疾風,一下子把你的思緒捲走;有時候又慢得像老電影的慢鏡頭,讓你細細品味每一個停頓和呼吸。這種節奏的急緩變化,讓閱讀體驗充滿瞭動態的美感,讓人在翻頁之間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心率,非常考驗讀者的專注力,但也因此獲得瞭極大的滿足感。
评分如果讓我來形容這本書的“氣質”,我會用“遊走在秩序與失序的邊緣”來形容。它在內容上似乎很自由散漫,似乎是隨手拈來的生活感悟,但當你把所有的篇章串聯起來看時,會發現背後有一套非常嚴謹的內在邏輯在支撐著這一切。作者似乎非常著迷於捕捉那些“瞬間的崩塌”與“瞬間的重建”,無論是自然景觀的突變,還是人際關係中的一個微小誤會,他都能精準地捕捉到那個轉摺點。這種對“變化”的敏感度,讓整本書讀起來充滿瞭張力,就像是在看一場精彩的即興演奏,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音符會落在哪裏,但你知道它必然會落在最閤適的位置上。這種結構上的韌性,讓我聯想到我們颱灣社會那種看似鬆散,但骨子裏卻有著強大韌性的文化特質。讀完後,我有一種強烈的衝動,想把書裏的某些句子抄下來,貼在我的工作桌前,提醒自己,生活中的每一個“不完美”,都可能是一個更深層“完美”的綫索。這本書,絕對值得細細品味,反復閱讀。
评分這本書給我的整體感受,是一種非常“接地氣”的哲學思辨。它沒有那些高高在上的、教條式的說教,而是通過日常生活中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片段——比如一碗熱騰騰的鹵肉飯,或者捷運車廂裏陌生人的一個眼神——來探討人與時間、人與空間的關係。這種將宏大議題融入微小敘事的技巧,真的非常高明。我記得有一篇關於“等待”的文章,作者沒有去探討等待的意義是什麼,而是細緻地描繪瞭“等待發生時”身體的細微反應:指尖的輕敲、目光的遊移、以及心裏那種莫名的焦躁與平靜的拉鋸戰。這種描寫,簡直是抓住瞭所有“等待者”的共同體驗,讓人讀完後會忍不住停下來,默默地審視自己生命中那些被“等待”占據的時刻。它不像一本工具書,提供明確的答案,更像是一麵鏡子,讓你在幽默和自嘲中,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邏輯。這種不費力氣的深刻,纔是真正厲害的地方,它不跟你講道理,它隻展示給你看,你自己的生活本來就蘊含著如此豐富的況味。
评分哇,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很有意思耶,那種帶著一點點懷舊感又有點現代感的排版,一下子就抓住我的目光瞭。拿到手的時候,那種紙張的觸感也蠻特彆的,不是那種光滑到不行的印刷紙,而是帶點紋理的,拿在手裏沉甸甸的,感覺作者在裝幀上也花瞭不少心思。光是書脊上的那個小小的標識,都設計得很有巧思,好像在暗示著裏麵內容的某種節奏感。我記得我是在一個周末的下午,陽光正好灑進咖啡館的角落,翻開這本書的,第一頁的引言就讓我有點愣住瞭,那種文字的排列方式,仿佛真的在空氣中跳躍著,不是那種平鋪直敘的敘事,而是充滿瞭呼吸感。我以前很少看到有作者能把文字的“形”和“意”結閤得這麼緊密,讓人在閱讀的時候,不隻是在接收信息,更像是在參與一場無聲的音樂會。特彆是那些章節的標題,沒有用那種傳統的大字報式標題,而是用一些很生活化的短句,卻能精準地捕捉到某種情緒的起伏,這點真的非常觸動我,讓我迫不及待想知道,作者到底是如何用這些看似隨意的文字,搭建起一個完整的世界觀的。這不隻是一本書,更像是一個邀請函,邀請讀者進入一個充滿韻律感和想象力的空間裏,去感受文字本身的生命力。
评分坦白說,這本書的語言風格對我來說,是相當“清爽”的。在現今充斥著各種復雜詞藻和刻意雕琢的文學作品中,作者的文字顯得異常乾淨利落,卻又在簡潔中蘊含瞭巨大的張力。我特彆喜歡那些短句的運用,它們就像是精確切割的幾何圖形,排列在一起,構成瞭一種新的秩序感。這種行文的“疏密有緻”,讓讀者的大腦得到瞭充分的休息,不會被過多的形容詞和復雜的從句所拖纍。閱讀的過程中,我感覺自己仿佛站在一個開闊的陽颱上,微風吹過,視野非常開闊。作者很擅長使用一些非常生活化、甚至有點“土味”的詞匯,但經過他的重組和放置,這些詞語立刻煥發齣一種嶄新的、充滿生命力的光澤。這是一種非常颱灣式的幽默感和剋製力的結閤,既不失親切,又不落俗套。每讀完一個自然段,都會有一種“原來可以這樣寫啊”的驚嘆感,它在潛移默化中,提升瞭你對語言的審美標準,讓人不禁想拿起筆來,試著用更純粹的方式去記錄生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