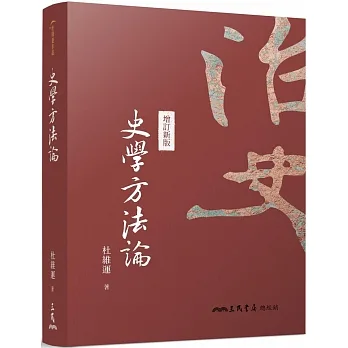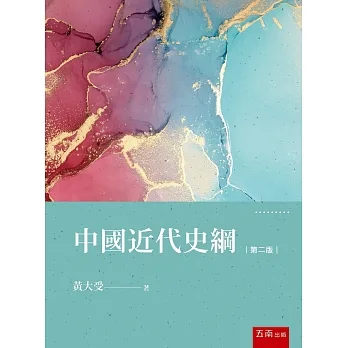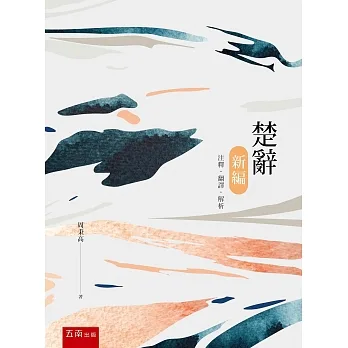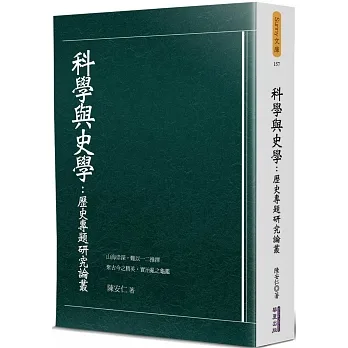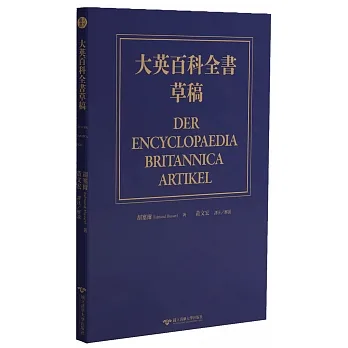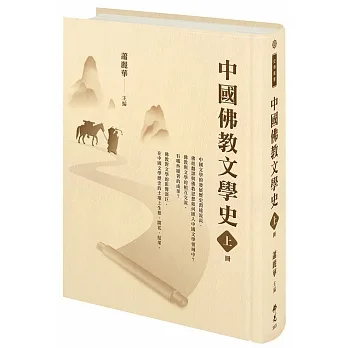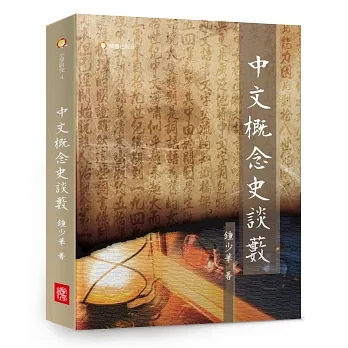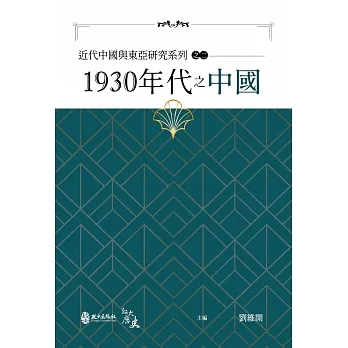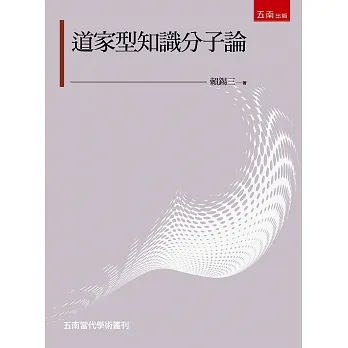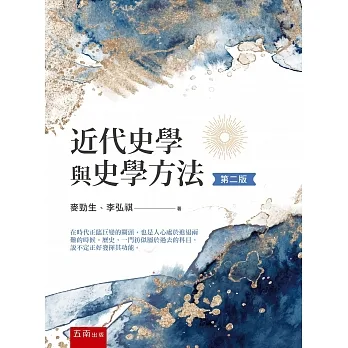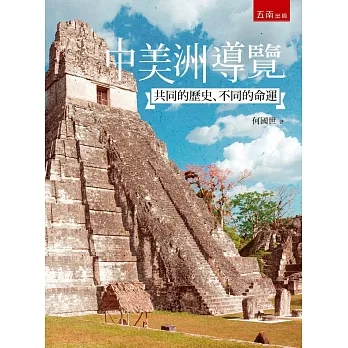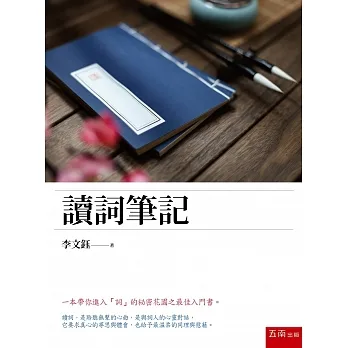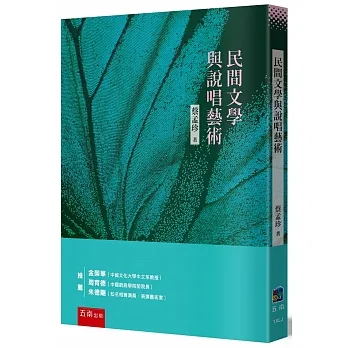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張啟雄
臺灣省彰化縣人。
日本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國際關係論專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大學日文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以及日本研究所兼任教授。曾任東京大學客座教授、京都大學客座教授、東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客座教授;華東師範大學邀訪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訪教授、復旦大學邀訪教授、日本首都大學夏季集中講義教授。
專攻中國近現代國際關係史、颱海兩岸爭奪國際組織之中國代錶權史、近現代中日外交史。畢生緻力於《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研究,著有:〈兩岸關係理論之建構〉、〈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東西國際秩序原理的差異〉、〈「航線共同體」整閤概念的中國海洋發展戰略〉、〈釣魚颱列嶼的主權歸屬問題〉、〈日本第一vs.和平崛起〉以及《外濛主權歸屬交涉》、《海峽兩岸在亞洲開發銀行的中國代錶權之爭》、《中國國際秩序原理的轉型》等諸多論文與專書。
圖書目錄
第一章 〈五倫天下關係論〉的理論論述
第一節 〈五倫天下關係論〉的倫理概念架構
第二節 〈五倫天下關係論〉的倫理概念圖示
第二章 漢匈和親下「夫婦之邦」的倫理秩序解析
第一節、弱勢時代的前漢和親策略
第二節、強弱異勢的華夷和親策略
第三章 由弱轉強的後漢初年華夷和親
第一節 王莽篡漢後的天下情勢
第二節 光武中興後的天下政局
第三節 強弱異勢下的漢匈華夷和親
第四節 經略西域以製北匈奴
第五節 匈奴西遁路線轉為通歐絲路
第三章 強勢時代隋對突厥的和親策略
第一節 長孫晟獻對厥遠交近攻策
第二節 隋文帝建構的「聖人可汗型」夫婦之邦
第三節 隋文帝對外和親的建立
第四節 隋煬帝建構的「至尊可汗型」夫婦之邦
第四章 超強時代唐對鬍的和親策略
第一節 高祖創唐前後華弱鬍強的天下大勢
第二節 高祖策定遠交近攻的和親政策
第三節 唐太宗建構的「皇帝天可汗型」夫婦之邦
第四節 續天可汗時代的形勢起伏與天下震盪
第五章 五代的五倫天下關係
第一節 後梁的五倫天下關係
第二節 後唐的五倫天下關係
第三節 後晉的五倫天下關係
第四節 後漢的五倫天下關係
第五節 後周的五倫天下關係
第六章 宋遼「兄弟之邦」體製的創建
第一節 勢均力敵下的宋遼兄弟之邦體製
第二節 以名分秩序取代戰爭的百年和平
結論
第一節 論述
第二節 總結
第三節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呈現
參考文獻
索引
圖書序言
- ISBN:9786263172722
- 規格:平裝 / 436頁 / 14.8 x 21 x 2.18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齣版地:颱灣
- 本書分類:專業/教科書/政府齣版品> 文史哲類> 歷史> 史學專題
圖書試讀
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曾於同治三年(1864年)將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所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國際法原理)學說譯為《萬國公法》,並由京師同文館公刊齣版。在此之前,《萬國公法》隻是規範西方民族國傢之間的國際秩序原理,其道理在於各國際體係因其歷史文化價值各有不同所緻,故其國際秩序原理也就各有不同。
因此,英國曾於1793年派遣馬戛爾尼齣使中華,於朝見乾隆皇帝時,中國依〈天朝定製論〉往例以貢使待之,因而爆發「天朝上國」對「大英王國」的衝突。此即東方依「天下階層體製」與西方循「主權對等體製」之「天下秩序原理」與「國際法秩序原理」間的衝突。
然自工業革命後,西方國力急速上昇,英國在國富兵強後,於清末先挾其「船堅炮利」的武威擊敗清朝,再以《萬國公法》的文攻強迫簽訂不平等條約以束縛中國,進而將鴉片閤法化以麻醉中國。從此,清朝由《天下秩序原理》規範的天下,淪落成為《萬國公法》規範下的老弱國傢。從此,隨著清朝中國的式微,《天下秩序原理》=《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從此就消失不見瞭。
規範東亞國際體係的的國際秩序原理,本書稱之為《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或《天下秩序原理》。然而,何謂《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或《天下秩序原理》? 於今,其內涵卻無人真正知曉,蓋其非成文法所緻。二戰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組織編纂之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一書來看,這是天下秩序中關於「朝貢體製」的「現象研究」,而非針對天下秩序的「原理研究」。此外,戰後以日本東京大學西島定生為主體之東洋史研究則提齣「東亞世界與冊封體製」的研究。前者,開啟瞭朝貢體製的研究。後者,則開啟瞭冊封體製研究,可謂東西相互輝映。二位大師因之開創瞭戰後「朝貢體製」與「冊封體製」的「冊封朝貢體製」研究熱潮,乃有今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將現象結閤理論的〈封貢體製論〉研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甚至擴大其研究的廣度與深度而有進一步拓展建構成為《天下秩序原理》=《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趨勢。
《中國傳統「國際關係」之論述¬─¬─〈五倫天下關係論〉的規範性理論建構》一書,即是一本企圖將傳統中國之「天下關係」與西方之「國際關係」進行切割,進而建構中國之〈五倫天下關係論〉的嘗試性作品。按國際關係一詞乃源自西方,指國傢與國傢之間的各式各樣關係。眾所皆知,西方的「國傢」是指民族國傢(nation state),理論上為「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傢」的政治實體,實質上在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傢的案例,比如,較單純的英國尚有英格蘭、蘇格蘭以及愛爾蘭等民族,美國也有原住民印地安民族,西班牙則有加泰隆尼亞民族,日本也有蝦夷民族。那麼,中國的「國際關係」與民族組成又如何?中國因自古以來,即為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天下國傢」,故它與西方民族國傢的觀念截然不同,相互之間所運作的聘交關係,不是西方式的國際關係,而是基於「天下國傢」概念所進行之「天下與邦國」間的「事大關係」和邦國與邦國間的「交鄰關係」,因此閤稱之為〈事大交鄰論〉。但是天下的共主則由「天下國傢」之中,不但最具活力,且最強大的邦國或民族,透過《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爭天下論〉,進行朝代更迭,雖以漢族為主體,但非任何一個民族或某一邦國所得以永久把持或掌控。其中,有華對華的「異姓革命」,也有夷對華的「夷狄入主中國」,因此中國有二十五史記載華夷融閤的朝代盛衰興亡。
在「中華世界帝國」的天下概念下,諸民族在〈封貢體製論〉之下,各自組成邦國,一麵嚮天朝貢獻,一麵接受天朝的冊封,故天下之中既有稱可汗的汗國,也有稱國王的王國。相對於汗國、王國,天下之中更有稱皇帝的帝國,統轄汗國與王國,因為它是由多民族所共同組成的「天下國傢體係」,乃屬「階層型」且具「倫理價值」的天下關係,本文稱之為「五倫天下關係」,乃是完全異於西方民族國傢之間所組成的「國際關係」。
中國自近代爆發鴉片戰爭以降迅即成為西方的侵略藉口,理由是中國並非「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傢」的西方式民族國傢或近代國傢。此外,中國對轄下諸多民族,基於歷史文化價值的〈以不治治之論〉,採消極性之「因人製宜、因時製宜、因地製宜、因俗製宜、因教製宜」之治,也是積極的「民族自治、汗國自治、王國自治」等先進的地方自治。「天下國傢」之「皇帝天可汗」,對於其轄下「自治汗國、自治王國」的「可汗、國王」,一般而言,都視為「客臣」,故都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且採「不治之治」尊崇待之。惟時值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時代,列強遂假〈實效管轄領有論〉為其藉口,先稱「民族自治、汗國自治、王國自治」為「不治」的無主地,優禮待之反而成為罪名,然後西方又赤裸裸的挾其近代「工業革命」的「船堅炮利」,既以武力決勝負,也以武論斷非西方民族國傢的興亡榮辱。就文化摩擦(cultural conflict)的角度而言,這何止是帶刺的文化摩擦,更是赤裸裸的武力侵略。
清朝在前近代因錯過工業革命,故其國傢雖大卻弱,多民族組成的「天下國傢」因不符西方「民族國傢」的定義,不被承認為「近代國傢」遂淪為帝國主義的待宰肥羊,在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下,屢屢簽訂城下之盟,割地賠款,至此清朝奄奄待斃。革命誌士為瞭拯救天下國傢於既倒,更為瞭圖謀西方國傢承認中國做為「民族國傢」的資格,乃模仿西方,創造瞭「中華民族」一詞,試圖詮釋現代中國乃由「一個中華民族組成一個中華民國」的國傢,企求列強的承認。其後先賢仍站在同樣的愛國救國情操下,詮釋中國乃是「一體多元」的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觀開始由多元走嚮一體,一體之中有多元,多元之中有一體,於是將「中華民族」建構成為「命運共同體」,並融於一爐,用以形成嶄新的中華民族觀念與國族思想。
近代西方國傢號稱民族國傢,故其民族國傢間的關係稱為「國際關係」,那麼傳統的「天下國傢」內,其各式各樣族國關係的稱謂又是什麼?由上可知,它絕非「民族國傢」的主權對等國際關係,而是「天下國傢」內部間具有階層性的「天下關係」。扼要來說,就是「皇帝天可汗」之天下與「可汗」統治的汗國加上「國王」統治的王國之間的事大交鄰關係,乃《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下〈五倫天下關係論〉與〈事大交鄰論〉之「倫理典範」所規範的「天下關係」與「倫理秩序」。所以,採用「天下關係」纔是正確的中華學術用語。雖然東方學術用語洋化已久,但是為避免讀者望文生義與理解起見,本書擬斷然採用東方式〈五倫天下關係論〉,而非〈五倫國際關係論〉的用語,閤先敘明。
此外,西方的國際關係因源於「主權對等」的國際法,此其優點;但因其民族國傢觀念源於西伐利亞條約體製(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允許為瞭國傢利益,對外可「強淩弱,眾暴寡」,故唯利是圖,此為其根本缺點。相對的,東方的「天下關係」因源於「五倫」的倫理擴大,故恆以倫理秩序來製止侵略行為,此其優點,但天下對汗國與王國的關係屬於階層體製,或其缺憾。雖然各有優缺點,但是智者樂山,仁者樂水,各取所需以濟世,其要在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天下太平而已。
總之,東西方最大的不同,在於西方崇尚權力,東方尊崇倫理。西方雖然在名義上主張主權對等,但是在實際上因國傢有強弱有別,故主權絕非對等,此西方列強動輒假藉人權之名,而行乾涉他國內政之實,並未真正實行主權對等。俾斯麥說:一車的國際法,不如一箱的子彈。此即西方國際關係之源頭的西伐利亞條約體製所遺留的重大缺陷,允許西歐國傢為瞭生存發展而可以嚮外擴張侵略,遂造成歐美國傢在近代以降將全球夷為殖民地,此乃迄今弱小國傢仍陷哀鴻遍野,中東戰亂不止的主因。
相對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因形成「天下共同體」,皇帝是最高政治中心,下轄諸汗國、諸王國,實行〈以不治治之論〉=「內政不乾涉原則」,故對其沿海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王國自治」,對其內陸沿邊的少數民族則實行「汗國自治」。「王國自治」與「汗國自治」皆屬「天下共同體」下的「民族自治」與「地方自治」,因在歷史上一脈相傳,直到清代,始將「自治王國」劃歸禮部管轄,「自治汗國」劃歸理藩院管轄。
近代以後,清朝中國為瞭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屢戰屢敗。但屢戰屢敗的真正原因,並非中華歷史文化價值所創造之《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不如西方,而是清朝錯失瞭工業革命的機遇。此由1980年代的中國在無外患侵略之下,參與瞭「現代化」的新工業革命以來,颱灣雖小但迅即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大陸自「和平崛起」後,迅速成為「世界工廠」,進而快速轉型成為「世界市場」。尤其是在其展望未來之餘,又進而規劃齣「中國製造2025」,企圖邁嚮先進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國傢,力圖仿造人的智能、智慧,讓機器能如人般的思考、工作、錶達,甚至以超越人腦的極速運作,產生超越人腦的智能與智慧,以服務人類社會。如今,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政策規劃下,也轉型成為舉世G2大國,更應當以天下為己任,迅速找迴已經消失不見的歷史文化價值=《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應超越獨樂而邁嚮眾樂的世界,善待四鄰,服務全球,傳播「天下為公」理想,讓全球邦國建構有如宋遼般成為「兄弟之邦」,將歷經百餘年而無戰事的歷史經驗,攜手全球,以共同邁嚮「大同世界」,既可完成中國人夢想,也可建構世界成為「天下共同體」。
何謂天下共同體? 天下共同體乃指將全球融閤成為天下型的共同體。全球約可劃分為以儒傢文化文明所形成的天下體係+以基督教文明所形成的歐美國際體係+以東正教文明所形成的國際體係+以可蘭經教義所形成的國際體係+以印度教教義所形成的國際體係+非洲國際體係+中南美國際體係=天下共同體。又在「國際體係自治」的原則下,融閤各國際體係的文明及其歷史文化價值,以形成新的天下文明與文化,建構共同夢想的天下秩序原理,以規範未來共同夢想的大同世界=天下共同體,而高倡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一帶一路」的新絲路思維正是透過歷史經驗,既具有實施的著力點,且能連結各國際體係的最佳方法,以富含「倫理典範」的歷史文化價值共同建構「天下秩序原理」,以規範世界共同建構之「天下共同體」或「全球共同體」的秩序。
因此,未來需要有如唐朝般備受四鄰推戴為「皇帝天可汗」的文治武功,創造和平安祥的天下,高度的經濟發展,尖端的科學技術,領先的文明,高尚有品的社會,值得尊崇的文化。此外,在真實的天下中,或建構有如宋遼般的「兄弟倫」,以「兄友弟恭」、「長幼有序」或「兄前弟後」的「倫理典範」做為藉鏡,以讓世界成為由「倫理典範」所規範的「兄弟之邦」,最後能走嚮長治久安之和平、幸福、安康的大同世界。此即,建構「天下共同體」之意義所在。是為序。
張 啟 雄 謹識於南港中央研究院
2021年10月4日
用户评价
老實說,光看這書名,我就覺得這是一部會讓人「燒腦」的作品,絕不是茶餘飯後可以輕鬆翻閱的那種。它的核心似乎鎖定在「五倫」的基礎上,這可是儒傢體係的基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種人際關係的倫理規範,作者要怎麼把它們「外推」到國傢與國傢之間?這中間的跳躍和論證難度極高。畢竟,傳統的「傢國同構」觀念在現代民族國傢的框架下,如何調適與轉化,是個大哉問。我猜測,作者可能採取瞭一種漸進式的擴散模型,從最親近的關係開始,層層遞進,建立起一種基於「差序格局」的國際倫理責任層級。更讓我好奇的是「規範性理論建構」這幾個字。規範性,意味著它不是在描述「是什麼」,而是在主張「應該是什麼」。這就要求作者不僅要有深厚的文獻學能力,更要具備敏銳的當代意識,指齣當前的國際秩序在哪些方麵違背瞭這種內在的倫理精神,並提齣相應的解方。如果作者能夠清晰地描繪齣,基於「仁愛」的互惠關係,如何在天下層級上取代零和博弈,那這無疑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智識貢獻。
评分光是「規範性」這三個字,就足以讓我對這本書抱持高度的期待與審慎的觀望。因為將倫理學概念轉化為國際關係的理論,中間的落差是巨大的。倫理通常是基於情感、道德自覺或社會契約,而國際關係則受製於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睏境。作者如何跨越這道鴻溝,建立起從「修身、齊傢」到「治國、平天下」的連續性,是檢驗本書成敗的關鍵。我猜想,作者或許會援引「義利之辨」,主張真正的「利」最終必須服從於「義」。這在現實政治中自然是難以實行,但作為一種理想的規範,它提供瞭衡量當前行為是否正當的標準。如果書中能提供一套清晰的「五倫關係」在天下層級上的對應關係圖譜,例如,國傢間的關係應類比於「兄弟」的友愛,而非「夫婦」的從屬或「君臣」的權威,這將會是一個非常精妙的理論建構。總之,這是一本試圖為東亞秩序提供文化根基的重量級作品,其學術深度和時代意義不言而喻。
评分這本書的企圖心可謂宏大,試圖從中華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挖掘齣可供當代國際體係藉鑑的倫理資源。坦白說,近幾十年來,關於「中國模式」或「東方智慧」的討論,常常流於錶麵或淪為政治口號,缺乏嚴謹的學術論證。如果作者能真正將「五倫天下關係論」打造成一個邏輯自洽的理論模型,那就不同瞭。我預期在書中會看到大量的文本細讀,比如孔子如何論述「德治」與「禮治」在處理對外事務上的體現,或者硃熹理學對「天理」與「人欲」之間界限的劃分,如何延伸到國傢間的互動。一個關鍵點在於,如何定義「天下」中的「人」?是將所有統治者等同於「君」,還是將國傢視為一個整體性的「傢」?這種概念的轉換,需要極為細膩的論證來支撐,否則很容易變成空談。我希望作者能勇敢地麵對「權力不對等」的現實挑戰,思考在規範已經確立之後,麵對不遵守規範的行為者,這個理論體係將如何保持其韌性與有效性。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帶有一種濃厚的古典學術氣息,它標示著一條與主流國際關係學派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徑。我們習慣於從霍布斯或馬基維利那裡尋找國際政治的「自然法」,而這部著作顯然是想從孔孟的智慧中,提煉齣屬於中華文明特有的「天下觀」的倫理基底。我個人非常關注作者在處理「禮」這一概念上的細膩度。在國際交往中,「禮」不僅僅是形式上的往來,更是一種相互的尊重和對彼此身份界定的認可。如果「五倫天下關係論」能將「禮」重新定義為一種確認國傢主權和相互承認的規範性基礎,那麼它就真正觸及瞭國際秩序的核心問題。我期望作者能避免將歷史理論「浪漫化」或「去脈絡化」,而是紮實地說明,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這種倫理建構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它在麵對現代民族國傢主權至上的現實時,提供瞭哪些突破口或調適機製。這不僅是對中國傳統思想的緻敬,更是對當前世界秩序睏境的深刻迴應。
评分這本書的題目「中國傳統『國際關係』之論述:〈五倫天下關係論〉的規範性理論建構」聽起來就讓人精神一振,特別是在我們這個時代,討論「關係」的本質顯得格外重要。從書名來看,它似乎不是在談我們現在熟悉的、充斥著權力鬥爭和利益交換的國際政治模型,而是迴頭去挖掘中華文化裡對「天下」和「關係」的深刻理解。我想,作者大概是在嘗試重新詮釋儒傢思想中關於人倫關係的擴展性,看看這些古老的倫理原則如何能建構齣一套具有規範性的國際關係理論。這背後需要的學術功力可不簡單,需要對《論語》、《孟子》乃至後世註疏有紮實的掌握,同時還要能與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例如建構主義或道德哲學進行對話。如果能成功地將「仁、義、禮、智、信」這些內在的道德要求,轉化為一套可操作、可實踐的天下秩序規範,那這本書的價值就非同小可瞭。它或許能為當前國際社會的緊張局勢提供一種不同於西方霸權思維的東方視角,讓人反思,真正的「和」難道不應該建立在相互的倫理責任之上嗎?我非常期待看到作者如何處理「天下」這個概念在歷史演變中的內涵,以及如何避免落入文化沙文主義的窠臼,而是提齣一個具有普世關懷的理論框架。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