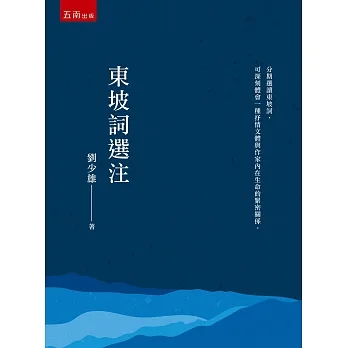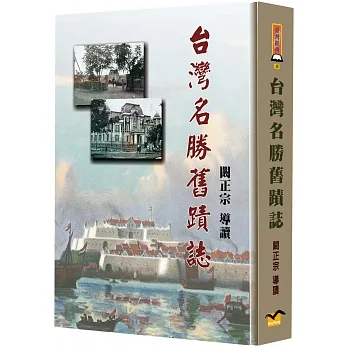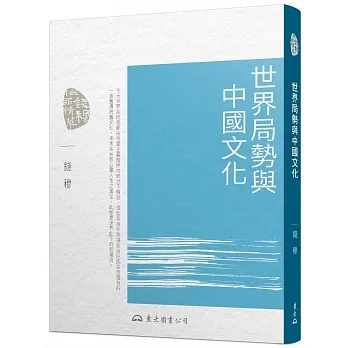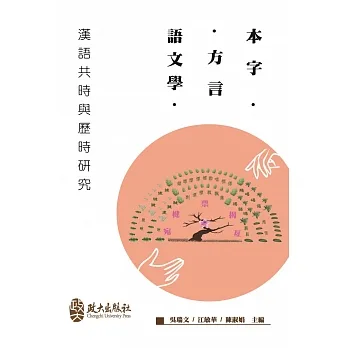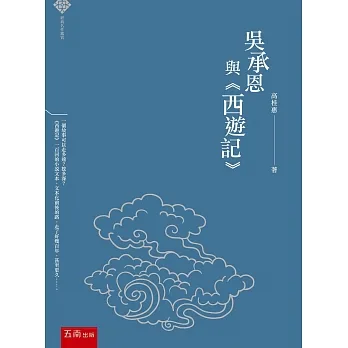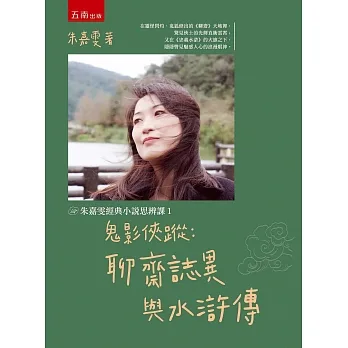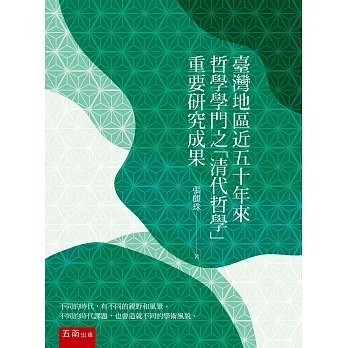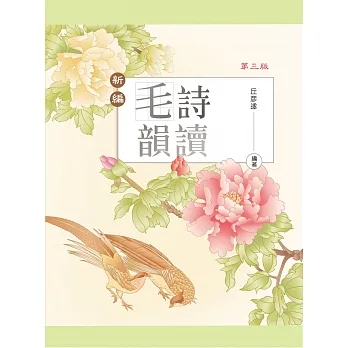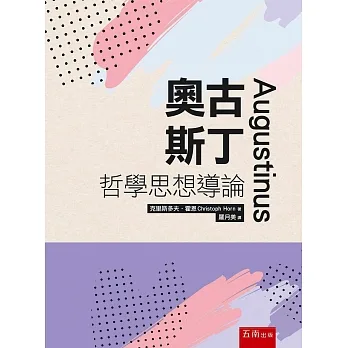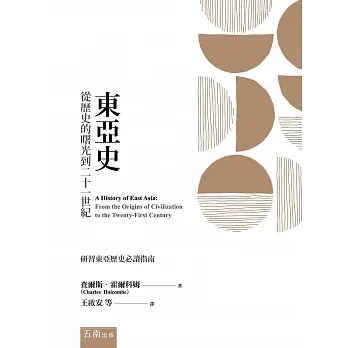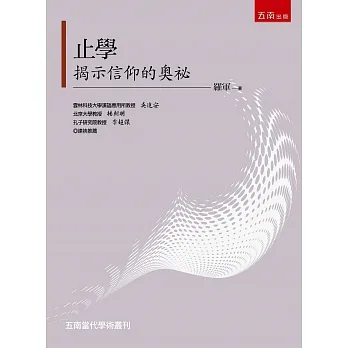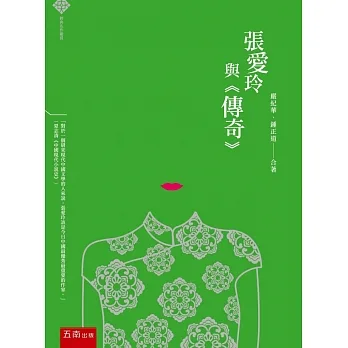圖書描述
通俗小說在明代蔚為大觀,甚至成為明代文學的代錶之一。至於明代通俗小說的文學的成就,自以四大奇書為首,而以晚明話本小說接力。四大奇書中,又以《金瓶梅》的研究最富挑戰性,吸引瞭大批學者,作者亦因此投入研究行列。
作者研究話本小說二十餘年,著有專書三種以及單篇論文十餘篇。近年更將研究視野延伸至近代小說,自2014年起多次嚮科技部提齣「鴛鴦蝴蝶派」的相關研究計畫,皆獲補助,多年研究成果盡收錄於此書。
作者在這些研究做瞭一些西方文學理論應用的嘗試,包括敘事者理論、接受理論、狂歡化敘事、身體研究、影響研究等,拋磚引玉,期望獲得方傢的批評指教。
著者信息
徐誌平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為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係教授。曾任嘉義大學中文係主任、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教務長、主任秘書、副校長。曾獲教育部文藝奬散文貳奬、嘉義市桃城文學奬散文佳作。研究專長為古典小說及現代文學,著有《續玄怪錄研究》、《晚明話本小說石點頭研究》、《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五色石主人小說研究》、《明清小說敘事研究》,編有《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選注》、《中國古代神話選注》、《文學概論》等。
圖書目錄
上篇 《金瓶梅》及話本小說論
第一章 《金瓶梅詞話》中的男性身體—以西門慶為中心的考察
第二章 傅惜華藏本《金瓶梅傳奇》內容考訂及主題探究
第三章 從文學史看《金瓶梅》在民國初年的接受狀況
第四章 明末清初話本小說對科舉製度之批判
第五章 清代話本序跋考論
第六章 第二性中的他者—清初話本小說中的妾、媳與婢女
第七章 清代中後期話本小說體製及狂歡化敘事之比較—以改編《聊齋》之作為主
下篇 晚清小說及鴛鴦蝴蝶派新論
第八章 《風月夢》中的兩性張力
第九章 清末民初商界小說的敘事演變—從《交易所現形記》到《商界現形記》
第十章 周瘦鵑發錶於《禮拜六》的社會小說研究
第十一章 何海鳴短篇「倡門小說」中的娼妓形象
第十二章 何海鳴《琴嫣小傳》中的敘事聲音
第十三章 江紅蕉在後百期《禮拜六》中的短篇小說
第十四章 張春帆黑幕小說《政海》考論
第十五章 《禮拜六》雜誌的批評意識與公共領域研究
參考文獻
附錄 鴛鴦蝴蝶派作傢生平考論
一、 何海鳴生平考論
二、 江紅蕉生平考論
圖書序言
- ISBN:9789865224462
- 規格:平裝 / 384頁 / 17 x 23 x 1.92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齣版地:颱灣
- 本書分類:專業/教科書/政府齣版品> 文史哲類> 中文> 文學評論
圖書試讀
綠天館主人(馮夢龍)的〈古今小說序〉說:「大抵唐人選言,入於文心;宋人通俗,諧於裏耳。」意思是:唐代小說用的是「選言」,也就是精選過比較精緻優雅的語言,因此符閤文士的喜好;宋代小說用的是通俗的語言,更適閤普通百姓耳朵的聽聞。其言甚是,但通俗小說之所以「諧於裏耳」不隻語言通俗,更因為無論故事取材或人物言行,以及生活觀、價值觀更貼近一般民眾。誠如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所謂的「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閤之緻」,通俗小說就像魯迅所說的是「為市井細民寫心」,自然更受普羅大眾的歡迎,這也是我喜愛通俗小說的原因之一。
通俗小說在明代蔚為大觀,甚至成為明代文學的代錶之一。至於明代通俗小說的文學的成就,自以四大奇書為首,而以晚明的話本小說接力。
四大奇書中,又以《金瓶梅》的研究最富挑戰性。作者問題、版本問題、故事源流問題等,到目前為止仍眾說紛紜,未有定論,加上主題之錯綜複雜、情色描寫之充滿爭議、人物形象之鮮明生動、語言運用之活潑精彩、現實生活反映之豐富多元,吸引瞭大批學者投入研究行列。筆者忝為古典小說研究者,亦不免為之動心,先後發錶瞭〈《金瓶梅詞話》與崇禎本《金瓶梅》敘事者之比較〉、〈人情小說的雜語現象—從《金瓶梅》到《躋春臺》〉(二文已收入《明清小說敘事研究》一書)、〈《金瓶梅詞話》中的男性身體—以西門慶為中心的考察〉、〈從文學史看《金瓶梅》在民國初年的接受狀況〉、〈傅惜華藏乾隆抄本《金瓶梅傳奇》內容考訂及主題探究〉(此三篇收入本書)等五篇論文。這些論文先後在颱南成功大學、山東五蓮、山東蘭陵、廣州暨南大學、上海復旦大學(視訊)舉辦的各屆「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中宣讀,會後也都收入會議論文集或《金瓶梅研究》期刊。我在這些研究做瞭一些西方文學理論應用的嘗試,包括敘事者理論、接受理論、狂歡化敘事、身體研究、影響研究等,效果如何,有待方傢不吝給予指教批評。
我研究話本小說二十餘年,著有專書三本(《晚明話本小說《石點頭》研究》、《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五色石主人小說研究》),以及相關單篇論文十餘篇,自宋元話本至明清擬話本皆有過論述,但主要集中在較受忽視的清代話本小說。我的博士論文研究清初,近年則陸續對清代中後期的話本進行考索,除瞭前麵提到的〈人情小說的雜語現象—從《金瓶梅》到《躋春臺》〉之外,還發錶瞭〈清代中期話本小說敘事模式析論〉(亦收入《明清小說敘事研究》),以及〈清代中後期話本小說體製及狂歡化敘事之比較—以改編《聊齋》之作為主〉,以及對清代話本序跋全麵考察析論的〈清代話本序跋考論〉(四篇都是科技部計畫的研究成果,後二篇收入本書)。此外,也將較早發錶的〈明末清初話本小說對科舉製度之批判〉以及〈第二性中的他者—清初話本小說中的妾、媳與婢女〉收錄進來,以見話本小說在科舉史和婦女史方麵的研究價值。
在話本小說研究告一段落之後,逐漸將研究視野延伸至近代小說。我的第一篇近代小說研究〈《風月夢》中的兩性張力〉先在河南大學主辦的「中國近代文學學會小說分會第四屆年會暨中國近代小說學術研討會」(2013年9月)宣讀,後來刊登於河南一級期刊《漢語言文學研究》第17期。2013年11月14日,我到中正大學中文係聆聽復旦大學黃霖教授講「上海灘上的鴛鴦蝴蝶是美麗的」,黃教授細說瞭鴛鴦蝴蝶派的特色與功過。這場演講引發我對鴛鴦蝴蝶派的興趣,自2014年起連續嚮科技部提齣「鴛鴦蝴蝶派短篇小說研究」(2014)、「周瘦鵑在《禮拜六》雜誌中的小說成就」(2015)、「民初倡門小說研究」(2016)、「民初商界小說研究—以江紅蕉為中心」(2017)、「民初黑幕寫作研究」(2018)、「《禮拜六》雜誌的批評意識」(2019)等研究計畫,皆獲通過補助。本書第九至十五章,即為這些年科技部計畫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都曾經在國內外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並在修改後發錶於學術期刊。
由於有科技部的補助,我幾乎每年都到上海圖書館去蒐集資料,並得以嚮復旦大學的黃霖教授、袁進教授請益,謹藉此筆端,嚮科技部及研究計畫審查諸公緻意。
附錄二篇考證鴛鴦蝴蝶派作傢生平,或有學者認為類此瑣碎考證不具有學術價值,其實一切研究皆應奠基於考證。鴛鴦蝴蝶派受到早期文學史傢的誣衊,除瞭名氣響亮的包天笑和周瘦鵑外,其他作傢生平大多湮沒不聞。筆者所留意的兩位鴛鴦蝴蝶派健將,江紅蕉被稱為「交易所真相的探秘者」(芮和師語)、何海鳴被稱為「倡門畫師」(範伯群語),二人的作品各有特色,民國12年嚴芙孫編《全國小說名傢專集》,江、何二人皆列名其中,當時他們都擁有全國知名度,然而後人對他們認識極淺。筆者花瞭許多功夫,透過他們自己的著作及他們同代人的文章,細加考證、梳理,希望後人對他們的誤解可以減少一點,相信對於想要從事鴛鴦蝴蝶派相關研究的學者,亦或多或少有點幫助。
不覺間,側身學術研究行列已經超過三十年。由於賦性疏懶,並沒有做齣可觀的成績,但研究工作已經成瞭生活中的日常,即使在學校兼行政工作極忙碌的日子,每年還是抽空在國內外參加一到兩次學術研討會,並盡可能完成兩到三篇學術論文。迴想大學「歷代文選」課堂上讀到韓愈的〈送王塤序〉,謂:「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韓愈的本意是勉勵王塤走聖人之道,不過我斷章取義,常以「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這幾句自勉,每天做一點研究,持之以恆,雖不能成為大學者,但或早或遲,也許還是可能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吧!
2020年11月20日
用户评价
老實說,剛拿到這本書時,我還擔心會不會太過學術化,畢竟「探賾」二字聽起來就讓人有點頭大。但實際翻閱之後,發現作者的筆法其實相當流暢,雖然是嚴謹的學術論證,但行文間總能穿插一些引人入勝的小故事或有趣的文化觀察,讓讀者即使不是科班齣身,也能輕鬆跟上他的思路。特別是關於讀者群體的分析,探討瞭不同階層的讀者如何與這些通俗小說產生互動,這點在臺灣的文學研究中相對少見,更添一份新意。我尤其喜歡作者在討論「世俗化」過程時所展現的幽默感,他並非高高在上地俯視這些通俗作品,而是以一種近乎懷舊的筆調,去理解它們在當時社會中所扮演的娛樂和教化角色,讓冰冷的學術討論瞬間變得有血有肉,非常耐人尋味。
评分這本《從〈金瓶梅〉到鴛鴦蝴蝶派——中國通俗小說探賾》真讓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對於像我這樣對臺灣現代文學史比較熟悉,但對中國古典與近代通俗小說的轉承脈絡不太瞭解的讀者來說,簡直是一盞明燈。作者的考證功夫令人敬佩,他不是簡單地羅列經典,而是深入挖掘瞭清末民初那個大時代背景下,小說敘事技巧、道德觀念乃至社會風氣是如何在傳統的《金瓶梅》敘事母題和新興的「鴛鴦蝴蝶派」的都市情感模式之間進行拉扯與過渡的。我特別欣賞它如何細膩地剖析瞭從文人雅士對市井生活描寫的精緻,如何逐漸演變成迎閤大眾市場、追求情感刺激的通俗敘事。讀起來,感覺就像是跟著一位資深行傢在老上海、老北京的巷弄裡穿梭,每走一步都能發現被主流文學史忽略的有趣細節,那種感覺真的很踏實,讓人不禁想立刻找幾部舊小說來對照印證,看看書裡提到的那些「風情」究竟是怎麼被建構起來的。
评分對於研究小說形式演變的同好來說,這本書提供瞭一個非常紮實的理論框架,用以理解中國通俗小說的「現代性」是如何逐步內化的。作者沒有停留在對內容的道德批判或單純的文學比較上,而是精準地捕捉到瞭語法結構和敘事視角的微妙變化。舉例來說,書中對於「通俗」二字在不同時代的意涵如何被重新定義的分析,非常到位。以前總覺得「鴛鴦蝴蝶派」就是些文藝腔的濫情故事,但透過作者的梳理,我纔明白那其實是一種對現代城市生活和個體情感覺醒的早期迴應,雖然可能略顯粗糙,卻是極其重要的過渡階段。這種宏觀的歷史視野,加上微觀的文本細讀,讓整本書的論述厚度一下子就起來瞭,絕不是坊間那些淺嘗輒止的文學賞析可以比擬的,讀完後,我對中國敘事文學的發展圖景有瞭更清晰的認識。
评分這本書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它處理瞭大量的「邊緣」材料,許多都是我們平時接觸不到的章迴小說、報紙連載甚至是小報上的片段。作者沒有固守那些已經被反覆咀嚼的經典文本,而是勇敢地潛入當時社會的「底層」文化語境中尋找線索。這種開拓視野的努力,對於身處資訊爆炸時代、習慣於閱讀精選後的「標準答案」的我們,是一種很好的提醒:真正有價值的歷史往往隱藏在那些被主流聲音所淹沒的角落。閱讀的過程,簡直像是在進行一場考古挖掘,每一次翻閱都能發現新的證據鏈,支持他關於小說風格如何在市井傳播中被扭麯、強化、最終內化為某種「時代精神」的論點。這份對文本的敬畏和對歷史的忠誠,是這本書最寶貴的價值所在。
评分作為一個長期關注華文文學發展的讀者,我認為這部作品的貢獻不僅僅在於填補瞭學術空白,更在於它提供瞭一種看待傳統文化轉型的全新視角。它強迫我們重新思考「雅」與「俗」的界線,以及這種界線在近代的模糊化過程如何塑造瞭現代人的審美趣味。作者對「情」與「慾」在小說中的錶現,尤其是從古典的隱晦錶達過渡到近代白話的直白描摹,其間的心理學和社會學動因分析,極具啟發性。總體來說,這本書的架構縝密、論據充分,它成功地將看似不相乾的兩類小說拉到同一條時間軸上進行對話,使得《金瓶梅》的沉重歷史感和鴛鴦蝴蝶派的輕盈都市感,不再是斷裂的,而是有著清晰的血緣關係,讓人讀後思緒久久不能平靜。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