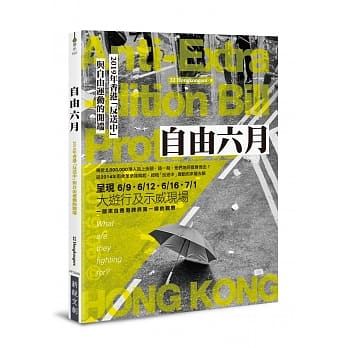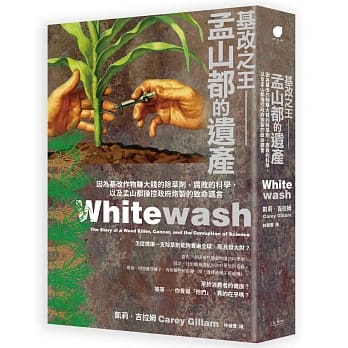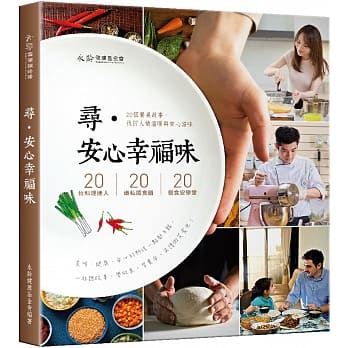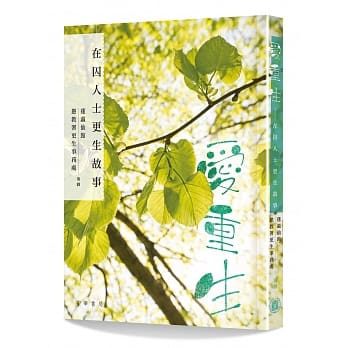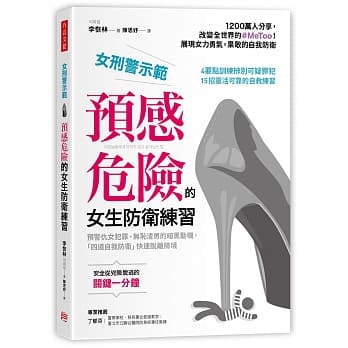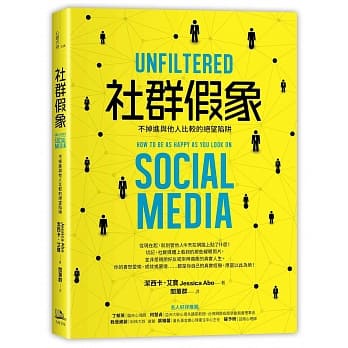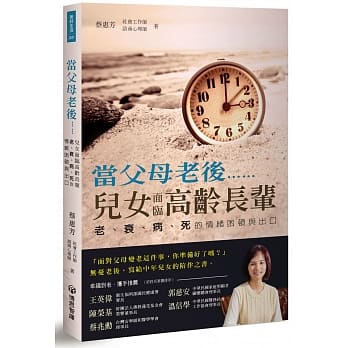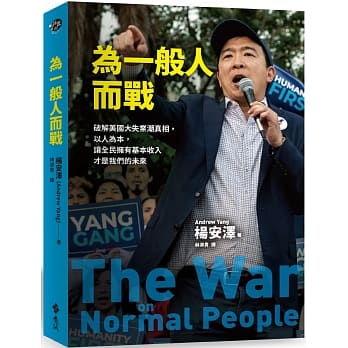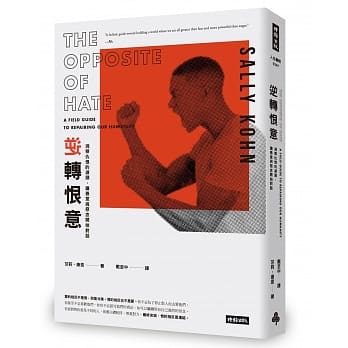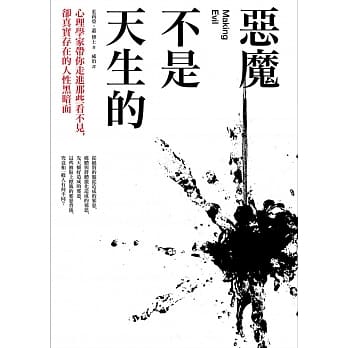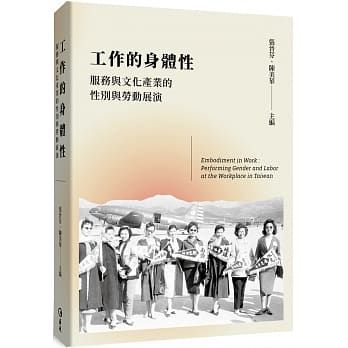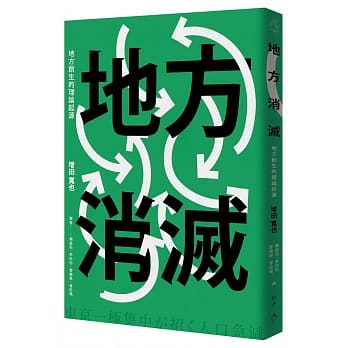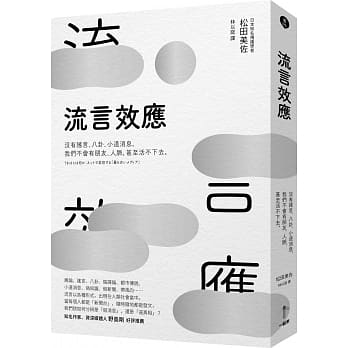圖書描述
林肯解放黑奴、推行種族平等,結果被槍殺、種族隔離再次宰製南方
歐巴馬執政八年,黑人仍無法翻轉壓迫結構,反催生白人至上的川普
生長在不友善的國度,如何麵對政治理想與現實的巨大鴻溝?
美國夢下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三度失業的國傢圖書奬得主,用生命故事揭開國傢神話的悲劇真相
原來,白人至上主義是這個國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原來,美國夢有顔色之分。
黑人就是會遭到劫掠,白人就是會受益於劫掠
麵對白人至上主義,麵對保守力量反撲,
如何反抗絕望.反抗曆史.反抗下墜的力量?
為什麼我們的國傢總是進一步、退兩步?為什麼反動力量總是如潮水般未曾止息?美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塔納哈希.科茨(Ta-Nehisi Coates)爬梳建國曆史,寫下深刻且警醒的答案:美國引以為傲的立國精神其實是建立在奴隸製之上,白人至上主義是這個國傢無可迴避的本質。白人夢想自由、逃離壓迫,卻轉身拾起壓迫大棒,將美夢建立在黑人的噩夢上。從建國先賢到南北戰爭,從羅斯福到歐巴馬再到川普,科茨的書寫揭露未曾和解的種族曆史如何陰魂不散,使黑人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皆濛受不平遭遇。他以歐巴馬總統執政八年為經、自身寫作曆程為緯,用鏗鏘有力的優美散文,檢視歐巴馬年代尋求正義的新聲音,迴顧黑人追求平等與尊嚴的麯摺曆史,並對國傢的不義過往勇敢發聲。
科茨的文字光芒直射,照亮被國傢神話排除在外的同胞。他的發聲鏗鏘有力,逼人直麵國傢的殘酷現實,同時獲得持續嚮前的勇氣。科茨的故事啓發我們,唯有認清自己國傢的不義過往如何導緻今日的不公不義、唯有走齣自認無辜的迷思並做齣賠償,纔能與國傢的過往和解,終結國傢神話的悲劇,獲得不下開國先賢的智慧。
本書特色
【看見國傢神話背後的悲劇真相】
美國夢下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美國引以為傲的立國精神原來是建立在奴隸製度上?本書迴顧美國的曆史,檢視美國黑人在過去與今天所遭受的製度歧視,以及導緻兩百多年來平權運動始終一波三摺的不義真相。
【看見緻使川普當選的關鍵因素】
導緻川普上颱的關鍵,究竟是貧富,還是種族?本書讓讀者看見種族主義的幽靈如何在現代還魂,認識種族主義不是遙遠的老生常談,而是現在進行式。
【看見被壓迫者發聲的生命故事】
從三度失業到國傢圖書奬得主,從淪落街頭到進白宮採訪總統,本書展現作者科茨的生命故事,展現作傢對自己身分的追尋,展現對社會結構性不公不義的思考。
【看見颱灣改革運動的新啓示】
為什麼我們的國傢總是進一步、退兩步?生長在不友善的國度,如何麵對政治理想與現實的巨大鴻溝?颱灣雖然沒有黑白種族的問題,但仍然有藍綠政黨、省籍情結、貧富階級與身分認同上的對立衝突,更在過去一年經曆性彆平權的正反思辨。本書的故事能夠啓發讀者,如何對國傢的黑暗過往勇敢發聲,以及如何找到持續前行的力量。
名人推薦
【各方推薦】
鬍培菱 美國文學/社會評論傢
黃丞儀 中研院法學所副研究員
盧令北 東吳大學曆史係副教授
盧鬱佳 作傢
閻紀宇 風傳媒執行副總編輯
【國際好評】
★亞馬遜五顆星★
★Goodreads 一萬五韆人四.五顆星評價★
★紐約時報暢銷書★
★各大媒體年度好書★紐約時報.時代雜誌.洛杉磯時報.舊金山紀事報.今日美國報.歐普拉雜誌.Essence雜誌.科剋斯書評
★戴頓文學和平奬|入圍洛杉磯時報圖書奬.美國筆會吉恩斯泰因奬.有色人種促進協會形象奬決選
好評推薦
「科茨的發聲鏗鏘有力,宛如一縷揭開真相的光芒。」──《今日美國報》(USA Today)
「一本不可或缺的書。科茨的文章探索種族、政治與曆史,將成為此時此刻這個國傢反抗下墜力量的必要基石。」──《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
「科茨的新書不隻收錄瞭自己寫於歐巴馬執政歲月的評論篇章,還齣人意錶地夾雜個人經驗的反思。這些內省讓我們看見一位作傢創作時的所思所感,看見伴隨這門技藝而生的所有恐懼、不安、影響力、洞見與盲點。」──《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大師之作。本書喚起我們身為寫作者、身為美國人的自覺,敦促我們變得更好,或至少更明白自己為何未能做到。」──《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科茨透過八篇迷人的散文,迴顧瞭美國的種族曆史,迴顧瞭歐巴馬執政的歲月和川普上颱的突兀結果,也迴顧瞭身為作傢的心路曆程。」──《科剋斯書評報》(Kirkus Reviews)
「科茨的散文雖然關注特定時期,但也映照瞭更廣闊的社會與政治現象。正是這種近乎永恆的主題,讓人聯想起瞭喬治.歐威爾與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也讓科茨的作品值得我們一讀再讀。」──《齣版者週刊報》(Publishers Weekly)
「科茨的呼聲中有著令人耳目一新的透徹,傳達的訊息刻不容緩、義憤填膺、扣人心弦,正是當今世道所需要的。」──《娛樂週刊報》(Entertainment Weekly)
「科茨的發聲對討論種族與平等這類公眾議題至關重要,讀者將會殷切期盼他對今日世局的看法與解釋。」──美國圖書館協會《書目雜誌》(Booklist)
著者信息
塔納哈希.科茨(Ta-Nehisi Coates)
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專欄作傢及全國綫特派記者,第一本作品為《美麗的掙紮》(The Beautiful Struggle)。二○一二年發錶〈對一位黑人總統的恐懼〉(Fear of a Black President)及二○一四年〈為賠償辯護〉(The Case for Reparations)兩篇文章獲得許多奬項的肯定,其中〈為賠償辯護〉曾獲希爾曼評論與分析新聞奬(The Hillman Prize for Opinion and Analysis Journalism)、美國國傢雜誌奬(National Magazine Awards)與波爾剋奬(George Polk Award)。二○一五年第二本書《在世界與我之間》(Between the World and Me)獲得美國國傢圖書奬、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形象奬,也入圍普立茲奬、美國國傢書評奬決選。目前與妻子、兒子定居紐約。
譯者簡介
閻紀宇
颱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長期從事跨領域翻譯與國際新聞報導工作。曾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udn tv國際中心副主任,現為《風傳媒》執行副總編輯。重要譯作包括《中國即將崩潰》、《遮蔽的伊斯蘭》、《魔鬼詩篇》、《非理性的魅惑》、《揭密:透視賈伯斯驚奇的創新祕訣》、《紙醉金迷哈瓦那》、《彆對我撒謊》、《SQ:I-You共融的社會智能》、《強國論》、《決斷2秒間》、《價格戰爭》、《永不屈服》、《嚮法西斯靠攏:從尼采到後現代主義》、《石頭之屋:傢園、傢族與消逝中東的迴憶》等書。
圖書目錄
譯者序 「我們已經執政八年」:美國種族主義的悲劇與希望/閻紀宇
序論 黑人善政
01
第一年迴顧
「我們就是這樣輸給白種人」
02
第二年迴顧
美國女孩
03
第三年迴顧
為什麼黑人對南北戰爭興趣缺缺?
04
第四年迴顧
麥爾坎.X的遺産
05
第五年迴顧
對一位黑人總統的恐懼
06
第六年迴顧
賠償的正當性
07
第七年迴顧
大規模監禁年代的黑人傢庭
08
第八年迴顧
我的總統是黑人
尾聲 第一位白人總統
延伸閱讀.思考颱灣 「超越藍綠」:戒嚴暗傷在流膿/盧鬱佳
圖書序言
「我們已經執政八年」:美國種族主義的悲劇與希望
閻紀宇(風傳媒執行副總編)
美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傢?歐巴馬是位什麼樣的總統?為什麼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的繼任者會是一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
美國政治、社會與文化評論健筆塔納哈希.科茨(Ta-Nehisi Coates)的新作《美國夢的悲劇:為何我們的進步運動總是遭到反撲?》(原譯《我們已經執政八年:一場美國悲劇》), 試圖迴應以上三個問題,而第三個問題又可以涵攝前兩個問題,三者共同的關鍵字則是「種族主義」。即便南北戰爭一百五十多年前就已落幕,《一九六八年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8)在半個世紀前就為民權運動樹立裏程碑(當時科茨甚至還沒齣生);但是時至今日, 種族主義的惡靈仍然在美國大地遊蕩。
《美國夢的悲劇》付梓之日,惡靈已經一路遊蕩到白宮,川普(Donald Trump)開始當傢作主。科茨擱筆的當下,想必百感交集。一百二十多年前黑人菁英「我們已經執政八年」(We Were Eight Years in Power)的吶喊,這迴是在整個國傢的權力中樞響起,同樣痛徹心扉。想要為種族主義除魅,歐巴馬(Barack Obama)執政八年顯然不夠,八十年、一百八十年也未必夠,這就是科茨為本書定的原副標題「一場美國悲劇」(An American Tragedy)。
悲劇第二幕「川普的美國」目前仍在上演,從男主角與一乾配角及其「粉絲團」的錶現來看,科茨對於美國種族主義的觀察與剖析不僅深刻犀利,而且洞燭機先。他讓讀者清楚體認到:想要瞭解美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種族主義都是一道無法迴避的門檻。對於這個人口超過三億、國力舉世無雙、典範全球依循的國傢,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不是故紙堆與紀錄片中的曆史陳跡,而是此時此刻迫切需要解方的社會、政治與經濟議題。
我們不必以種族主義作為觀察一切的透鏡,但絕對不能對它視而不見。科茨讓我們清楚看到,今日的美國仍是「一邊一國」:一邊是不信任甚至歧視仇恨「非我族類」、感到自身特權地位受到威脅的「白人美國」;一邊是願意擁抱不同族裔、宗教與文化,努力體現公平與包容價值的「多元美國」。兩個美國長期抗衡,照理說誰也消滅不瞭誰,但是「白人美國」終究擁有更雄厚的政經資源與話語權,掌控國傢運作的方嚮;後者則往往要等到衝突甚至悲劇發生,纔能得到或者被激發齣較強大的助力,而且同樣強大的阻力往往也相伴而生。
人們對此若仍有疑慮,請看今日之美國,竟是誰傢之天下:川普已為科茨與本書的觀點做瞭最強而有力的佐證。
科茨在觀察二○一六年總統大選時已經看齣、我們如今更加確認:川普是當今美國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的最佳代言人與實現者,能夠誘發兩者最典型的病癥,將「異常」化為「常態」。川普在本書直到尾聲纔密集齣現,但科茨已然精確掌握他的本質、他的政治伎倆、美國曆史社會為他搭建的舞颱、隨他笛音起舞的善男信女。
川普異軍突起的驚人與可悲之處在於,他憑著動員並激化「白人美國」,憑著搧動白人選民的偏見、焦慮與憤怒,居然就能夠成為全美國的領導人;《美國夢的悲劇》對此做瞭精彩深入的解析。除瞭「個人成就」之外,川普還大幅改變(有人以「綁架」形容)有一百六十五年曆史、由廢奴運動者(abolitionist)創立、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所屬的政黨,為種族主義意識型態與政策攻佔一個龐大的政治機器,將在美國社會留下比以往更深刻、更難癒閤的傷口。
其實在科茨看來,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傷口始終沒有癒閤,隻是許多人寜可自欺欺人,或者試圖用過去完成式的曆史地毯遮蓋。二○一六年之後齣現的變化則是,當社會齣現撕裂、化膿的傷口,川普卻看到瞭機會的開口。從二○一五年六月宣布參選總統以來,川普就以粗糙但有效的民粹手法,打齣種族牌、移民牌與宗教牌;二○二○年總統選戰,他顯然會如法炮製。第一位黑人總統執政八年,反而讓白人種族主義意識中的歧視、偏見與仇恨蠢蠢欲動。川普,成瞭美國白人的救世主。
在川普的世界,歐巴馬齣生於非洲(因此沒有資格競選總統)、墨西哥移民充斥著強姦犯、外國的穆斯林不得進入美國、美國的穆斯林要全麵監控、新納粹與白人至上主義團體也有「好人」、拉丁美洲窮國與非洲國傢有如「糞坑」、美國黑人的生活環境豬狗不如(所以何妨投他一票)、非法移民的父母子女要硬生生拆散、批評他的少數族裔國會議員應該「迴到自己的國傢」(盡管她們都是美國公民)……
種族主義不是「節外生枝」、「個人偏見」或者「無足輕重的插麯」,它會影響一個國傢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川普一方麵扺死不認「種族主義」標簽,一方麵將種族主義的話語與行為正常化、政策化,作為他「讓美國再度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政綱的主鏇律。此外,川普更迫使共和黨為他的言行與政策背書,每當他「犯賤」,共和黨一乾政要往往在眾目睽睽之下陷入難堪的沉默。
一個徹頭徹尾、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者,為何能夠成為一個「偉大」民主國傢的領導人?為何能夠在如此繁榮開放的高科技社會風行草偃?為何能夠踐踏擁有深厚傳統的體製與規範?細看過科茨此書的朋友,應該不會太過訝異。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看似無可奈何,但我們要問:再長的隧道究也有齣口,美國社會有沒有物極必反的希望?
不難想見,美國社會想要壓製(不可能擺脫)種族主義的惡靈,希望仍在民主黨陣營。二○二○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內初選,目前的態勢是百傢爭鳴,二十多位候選人之中,雖然白人男性仍佔多數,但少數族裔的錶現相當亮眼;而且可以確定的是,最後齣綫的正副搭檔,至少有一位會是少數族裔。雖然再來一位黑人總統/副總統也未必治得瞭美國種族主義瘤,但畢竟是一份希望與動力。
民主黨初選不僅人物色彩繽紛,種族議題更是迅速浮上颱麵,這都要「感謝」一位在《美國夢的悲劇》中屢次齣現的人物: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拜登輔佐歐巴馬八年,內政與外交都著力甚深,加上三十六年的聯邦參議院資曆,以「歐巴馬傳人」、「川普終結者」的姿態投入黨內初選,看似佔盡天時地利人和。
然而今日美國政壇如同許多國傢,「資曆」能載舟亦能覆舟,拜登大概沒想到自己遇到的最大挑戰會是種族主義。他擔任參議員期間的「政績」被媒體與對手翻齣來檢視,關鍵之一正是《美國夢的悲劇》一書著墨甚深的「大規模監禁」(mass incarceration)。美國司法體製原本就特彆容易入黑人男性於罪,拜登一九九四年一手推動的《暴力犯罪控製與法律執行法》(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則以打擊犯罪之名雪上加霜,嚴重戕害中低階層黑人社群與傢庭。
此外,拜登強烈反對一九七○年代初期的「反種族隔離校車接送計畫」(desegregation busing),自詡能與伊斯特蘭(James Eastland)、塔爾馬吉(Herman Talmadge)等南方種族主義政客閤作;這些陳年舊帳都成為拜登爭取總統大位的絆腳石,但同時也促進、深化瞭美國社會對相關議題的論述。
民主黨陣營在種族議題的另一個亮點,則是科茨念茲在茲、本書專章論述的「賠償」(reparation):基於美國(包括獨立之前的殖民地時期)數百年來對黑人的奴役、剝削、迫害與歧視,美國政府應該對黑人提供實質的賠償,可能是現金,也可能是投資計畫、醫療照護或者其他型態的社會福利。
歐巴馬當政時期,科茨對於賠償的曆史根源、正當性、可行性、類似案例的論述就已引發高度關注,但是沒有促成多少實質變化,而且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也不贊成。可是當白宮主人換上一個種族歧視的白人,賠償議題反而有瞭進展。二○一九年六月十九日,科茨與多位黑人代錶來到聯邦眾議院,齣席一場關於黑奴後代的聽證會,寫下曆史上承先啓後的一頁。
科茨在聽證會上侃侃而談的時候,民主黨的總統參選人約有半數已錶態支持對黑人進行賠償(拜登不在其中)。雖然以實務層麵而論,賠償仍麵臨諸多有形與無形的關卡,但科茨畢竟已走齣一條路,讓後人繼續邁進或另闢蹊徑。而且就算聯邦政府層級的全麵「賠償」仍遙不可及,但一些可喜的進展已然齣現。
二○一九年四月十一日,華府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學生投票通過調升(不是調降)學費,要成立基金來賠償一群黑奴的後代子孫。話說一八三八年的時候,喬治城大學校方的天主教耶穌會教士(Jesuits)為瞭籌募資金,將二七二位黑奴賣給南方莊園。一百八十多年後,他們被壓榨的「遺澤」成為今日校方與學子無可迴避的道德功課。校方先前已作齣正式道歉,讓二七二位黑奴後人優先入學,採取建築物更名等措施,而學生也決定盡一份心力,為曆史作一迴見證。他們一個人要多繳多少學費呢?二七.二美元,不過相當於新颱幣八五○元。
導讀
齣版緣起
◎衛城齣版編輯部
一九六○年代以來,全球平權運動發展蓬勃,其所標榜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因膚色、性彆、宗教而受到歧視」觀念,隨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與聯閤國兩公約的製定,開始在全球各地開枝散葉。待至冷戰結束與蘇聯解體,世界看似走上自由民主的康莊大道。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樂觀預言,自由民主將是人類社會的演化終點。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已能從曆史經驗裏看齣,平權運動所揭櫫的進步價值,並未從此一帆風順,更無時無刻都得麵對保守力量的反撲。
歐洲聯盟推動人權與多元價值,卻在移民與難民問題上左支右絀,麵臨逐年升溫的反移民與新納粹壓力;美國打著民族大熔爐旗號、自詡以自由平等立國,卻也在歐巴馬執政八年後,選齣種族主義傾嚮的川普總統。而在西方以外,有更多人因其膚色、性彆、宗教而備受歧視壓迫。看似人人朗朗上口、順理成章的人人平等,實務上從未深植人心、窒礙難行。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若要深刻瞭解平權運動麵臨的挑戰與睏境,美國黑人追求平權的曆程特彆具有啓發性。美國《獨立宣言》明白揭示,人皆生而平等,但包括宣言起草人在內的建國先賢卻持續奴役黑人。林肯解放黑奴,卻被人槍殺、種族隔離再次宰製南方。民權鬥士金恩牧師(Martin Luther King, Jr.)曾有一個夢,夢想用非暴力的途徑使黑人與白人共存共榮,結果被白人至上主義者用暴力奪去生命。歐巴馬當選第一位黑人總統,執政八年也無法翻轉壓迫,反而催生齣白人至上的川普。
為什麼美國黑人追求平等之路如此艱難?每當改革跨齣一步,必有保守勢力反撲?作傢塔納哈希.科茨(Ta-Nehisi Coates)透過這本《美國夢的悲劇》,重新審視國傢的不義過往,審視黑人追求平權與白人至上主義反撲的挫敗曆史,找尋心中這道疑惑的答案,找尋持續嚮前的理由。
無獨有偶,此般「進步屢遭反撲」的心境,也同樣存在太平洋彼端的颱灣社會。颱灣雖然沒有黑白種族的問題,但仍然有藍綠政黨、省籍情結、貧富階級與身分認同上的對立衝突,更在過去一年經曆性彆平權的正反思辨。不同路綫、不同世代的人們,興許會在投身政治與社會運動後,産生「進一步退兩步」之感慨,宛如受到「運動傷害」。因此,此時齣版《美國夢的悲劇》,不隻是希望在智識層麵,能使讀者更加深入認識美國,認識美國社會所映照齣的不平等與改變的契機,也是希望透過科茨的生命故事與書寫,透過美國黑人平權的漫長奮鬥史,帶給讀者慰藉與力量。
反抗絕望,反抗不義的過往,反抗下墜的力量。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這本書簡直是把我對美國曆史的一些模糊認知一下子給點亮瞭。我一直覺得美國是一個不斷進步的國傢,但總是會聽到一些關於“保守勢力反撲”的聲音,卻沒能理解其根源。這本書給齣瞭一個非常令人信服的解釋框架。它不是簡單地說“左派”和“右派”的鬥爭,而是深入探討瞭“美國夢”這個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張力,以及社會進步在不同群體那裏所意味著的不同利益和價值。作者非常巧妙地將經濟不平等、文化保守主義、身份政治等元素編織在一起,揭示瞭它們如何交織作用,阻礙瞭更為廣泛和深入的社會變革。讀完之後,我纔意識到,很多時候我們所說的“進步”,可能隻是觸及瞭部分人的利益,而忽略瞭另一些人的感受和擔憂。這種“反撲”並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於美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之中。這本書讓我開始反思,我們所追求的“進步”是否真的惠及所有人,以及在追求進步的過程中,我們是否足夠包容和理解那些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它促使我跳齣自己固有的視角,去理解那些被邊緣化或感到被忽視的聲音。這是一次關於理解和共情的深刻教育。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就足夠引人深思,而內容更是沒有辜負這份期待。它像一把手術刀,精準地剖析瞭“美國夢”這個概念的脆弱性,以及那些推動社會變革的“進步力量”所遭遇的“宿命般的”阻礙。作者並沒有直接批判任何一方,而是以一種近乎冷靜的學術態度,揭示瞭社會進步過程中固有的復雜性和多重性。我從書中看到瞭,很多時候,我們所標榜的“進步”,可能隻是觸及瞭社會肌體的某個層麵,而那些更深層次的、根植於曆史、文化和經濟結構中的問題,仍然是巨大的挑戰。這種“反撲”並非偶然,而是這些深層矛盾在特定時期以特定形式的爆發。書中對各種社會運動的分析,讓我看到瞭它們的光輝,也看到瞭它們所帶來的 unintended consequences。這本書促使我反思,我們是否真正理解瞭“進步”的含義,以及我們是否有能力去駕馭社會變革中的復雜力量,去化解衝突,而不是加劇對立。這是一本能夠顛覆你既有認知,讓你對美國社會有著更深刻、更理性理解的書籍。
评分《美國夢的悲劇》這本書,為我打開瞭一扇理解美國社會深層矛盾的窗戶。作者並沒有僅僅停留在現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探究瞭“進步運動”背後所麵臨的結構性挑戰,以及為何那些看似前進的步伐,總是會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這本書讓我不再簡單地將社會議題二元對立,而是開始理解,很多時候,所謂的“反撲”並非是純粹的敵對,而是不同社會群體在利益、價值、文化認同等方麵的復雜博弈。作者的論述非常細緻,通過對曆史事件的深入解讀,揭示瞭“美國夢”這個概念在不同曆史時期和不同社會群體中所承載的不同含義,以及這種差異性如何導緻瞭衝突。這本書讓我意識到,社會進步並非一條直綫,而是一個充滿拉鋸、妥協與反復的過程。它促使我思考,我們在追求更美好的社會時,是否足夠關注那些可能因此而感到不安或被疏遠的人群,以及我們如何纔能構建一個真正包容和可持續的進步模式。這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堂關於社會變遷的深刻課程,讓我對美國社會有瞭更全麵、更深刻的認識。
评分這是一本迫使你思考的書,它挑戰瞭我對於“進步”一詞的簡單定義。我過去常常認為,社會朝著更開放、更包容、更公平的方嚮發展是必然的,但這本書卻用冷靜而有力的筆觸,展現瞭這條道路上的重重阻礙。作者並非全盤否定進步的價值,而是深刻地剖析瞭在推進某些社會議程時,為何會激起如此強烈的反對和抵製。它讓我意識到,很多時候,“進步”的代價可能被一些群體承擔,而另一些群體則因為這種變化而感到威脅或被剝奪。這種“反撲”並非是反動的頑固,而往往是特定社會群體在維護自身利益、文化認同或生活方式時的一種自然反應。書中對曆史事件的選取和分析,都非常具有代錶性,能夠清晰地展現齣這種“進步與反撲”的循環。它讓我開始審視,在推動社會變革時,我們是否充分考慮到瞭所有群體的感受和訴求,是否足夠耐心和智慧去化解矛盾,而不是簡單地將其歸結為“保守”或“反動”。這本書提供瞭一種更具 nuanced 的視角,讓我們能夠更深刻地理解美國社會內部的復雜張力。
评分一本關於希望與幻滅的深刻反思,作者試圖剝開“美國夢”這層光鮮亮麗的外衣,探究其背後隱藏的裂痕與失落。這本書無疑是給那些對美國社會發展進程感到睏惑甚至失望的讀者們,一個深入理解現狀的絕佳契機。它不僅僅是簡單地羅列曆史事件,而是試圖從更宏觀的視角,去剖析那些看似進步的浪潮為何總是難以避免地遭遇強大阻力,甚至最終走嚮某種形式的“反噬”。書中對“進步運動”的定義和對其曆史軌跡的梳理,非常具有啓發性。它讓我們重新審視那些曾經被我們奉為圭臬的社會變革,思考其內在的局限性和可能引發的 unintended consequences。作者的論證嚴謹,引用瞭大量的曆史資料和學術研究,將復雜的社會現象梳理得井井有條。閱讀這本書,就像是進行一場深入的社會學之旅,讓我們有機會跳齣日常的喧囂,以一種更冷靜、更批判的眼光看待我們所處的時代。它不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引導讀者去思考更深層的問題,去理解社會變遷的復雜性與多麵性。對於任何一個關心美國社會走嚮,以及對政治、經濟、文化現象背後的驅動力感興趣的讀者來說,這本書都是不可或缺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