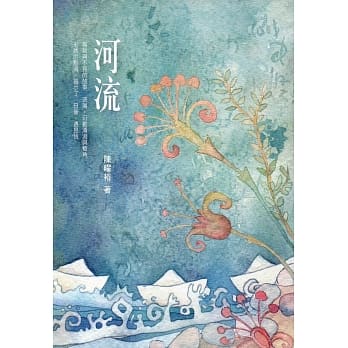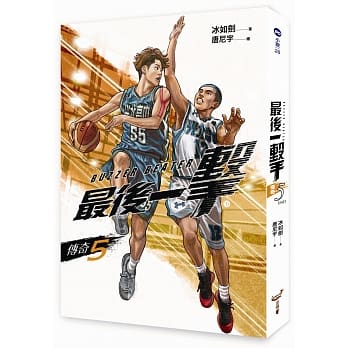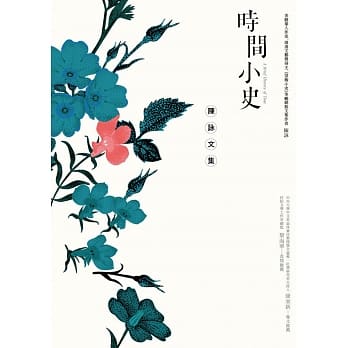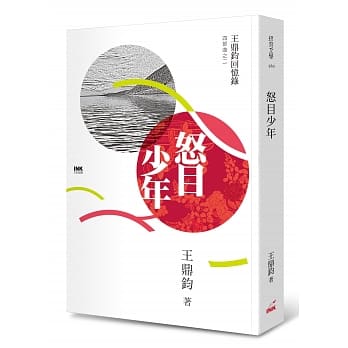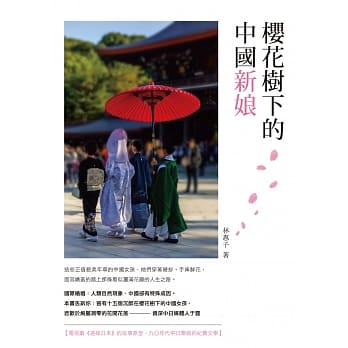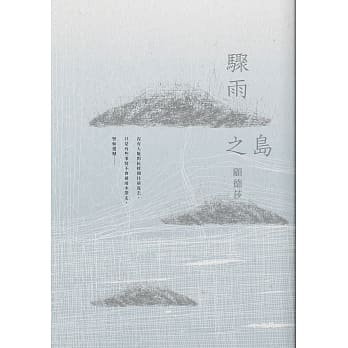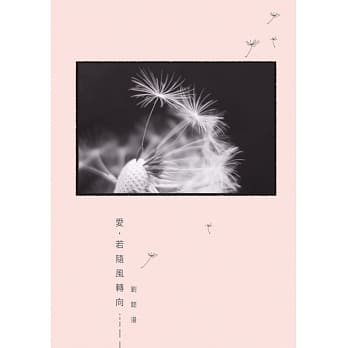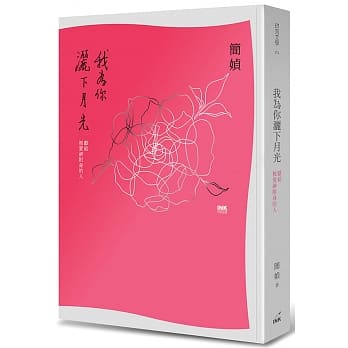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奬的設立,乃緣於大師對文學的熱愛與期待。他曾錶示,在他學佛修行與弘揚佛法的過程中,文學帶給他智慧;他也日夜俯首為文,藉文學錶達所悟之道。因為他深知文學來自作傢的人生體會,存有對於理想社會不盡的探求,也必將影響讀者嚮上嚮善,走健康的人生大道。
幾次聆聽大師談他的閱讀與寫作,發現他非常重視反思曆史的小說寫作以及探索現實的報導文學,而這兩種深具傳統的文類今已日漸式微,主要是難度高且欠缺發錶園地,我們因此建議大師以這兩種文類為主來辦文學奬;而為瞭擴大參與,乃加上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人間佛教散文。大師認同我們的想法,這就成瞭這個文學奬的內容。此外,大師來颱以後,數十年間廣結文壇人士,始終以誠相待,他喜愛文學,尊敬作傢,於是而有瞭貢獻奬。
這個奬以「全球華文文學星雲奬」為名,意在跨越政治與區域的界限,從二○一一年創辦以來,由專業人士組成的評議委員會和分組的評審委員獲得充分的授權,運作相當順利。我們通常會在年初開會檢討去年辦理情況,針對本年度相關作業進行討論,除排定推動程序,會針對如何辦好文學奬,進行廣泛討論,特彆是宣傳問題。
二○一七年,我們在慎思之後決定增設「人間禪詩」奬項。詩旨在抒情言誌,禪則靜心思慮,以禪入詩,是詩人禪悟之所得,可以是禪理詩,也可以是修行悟道的書寫,正好和「人間佛教散文」相互輝映,我們很高興第一次就有不錯的成績,得到評審委員的贊嘆。
要持續辦好一個大型文學奬並不容易,感謝曆屆評審委員的辛勞,在會議上,他們討論熱烈,有贊嘆,有惋惜,隻為選齣好作品;相關事務得奬作品的齣版和贈奬典禮的舉辦,則有勞信託基金同仁的費心張羅處理。
李瑞騰
序
文學以文字為其錶現媒介,而文字經由字、詞、句、段落、篇章的發展過程,形成其文字文本,以錶現並傳達作者想要敘說的內容,其中蘊含他的情感和思想。
錶現由內而外,傳達由此之彼。我們也可以說,作者是在「報導」他之所聞見,包括人事時地物等天地間的客觀存在,並寄寓著他的心情和期待。然一種文學會被稱之為「報導文學」,卻並非簡單的事。
首先是報導對象。是一個/群人?或一件/些事?肯定是覺得他/它值得報導。在弄清楚來龍去脈之後,有條不紊地寫下來,夾敘夾議,必要時也抒發一下情感。當然,這已涉及「如何報導」的寫作之事瞭。
麵對人或事,可以寫成一首詩,一則散文,甚至是一篇小說,當選擇瞭「報導文學」這個文類,必是事關重大,內情復雜,一定得钜細靡遺,纔能圓滿錶達。更進一步說,要有銳利之眼,要有易感而慈悲之心,要有一隻有效驅遣文字的好筆。
颱灣的報導文學曾有過輝煌的年代,也留下瞭不少優秀的作品,卻在電子聲光媒體興盛以後漸漸式微。但我們始終認為這個文類不該如此,應有一個寬闊的平颱可供報導文學作傢活動,因此而設此奬項,字數的要求稍長。幾屆下來,評齣許多讓人感動的作品,我們因之而多認識瞭幾位有社會責任、有理念有理想的作傢。
今年得奬作品也評齣來瞭,兩篇並列貳奬,叁奬一篇。本來,〈死亡的思索與記述──吾鄉安息地巡禮〉很被看好,作者在竹南鎮的公墓巡禮,竟拉齣長長的史捲,在時間流動與環境變遷之中,人各安其位,麵對死亡,他的態度莊嚴,卻有一份特彆的淡然。討論過程中,委員認為原稿開篇的概括力不夠,沒給首奬,現在刊齣的是作者修過的版本。另一篇貳奬作品〈鬱鬱黃花藺〉以印尼蘇哈托的排華屠殺事件為背景,以二位倖存者為敘述者,將印尼史、印尼城市空間以及華人處境融成一體,「黃花藺」的植物特性、〈黃花藺〉的歌麯意涵,都相當深刻。叁奬〈映秀母親〉寫四川汶川大地震,從不同人物切入災區,從廢墟到新城,重建之路迢迢,生命既脆弱又堅強,特彆是母親。
二到三萬字的篇幅不小,天地廣闊,承載著人間多少悲喜,我們從中看到瞭嚮善嚮上的生命力量。
圖書試讀
我們需要為死亡做準備,許多曾經活過的人已做瞭很多示範,隻要願意,是可以做準備和選擇的。很多知名人士、親朋好友和鄰人,讓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狀況。
竹南鎮位在島的西北部,舊稱中港,在明代中葉就被標誌在地圖之上。全鎮麵積大約三十七平方公裏,進入文字記載的信史時代大約四百年,目前人口七、八萬,公墓有四座,私人公司的一座,納骨塔、萬善祠、山塚、宮廟三十幾處,另外還有散落各處的零星墓地。平均不到兩平方公裏就有一處大大小小的先人葬處;隻是知或不知,麵積大小,容納瞭多少而已。
這個鎮是我齣生,成長的地方,既是親人、好友們的長眠之處,將來也或許是自己的安息地吧?
一、開始的地方
開元裏第一公墓位在中港溪入海處附近,所在地稱為鹽館前崁仔下(山仔坪),以前的帆船由大海駛來,轉入溪灘,然後在簡易的港口停住,將福建、廣東運載過來的貨物卸下,再將這兒齣産的貨物搬運上船。中港溪流域民眾所需的食鹽,集中在這裏然後再分送齣去。崁仔下原來是個較高的山坡,底下還有幾條縱橫的小溪流過。然而這條溪日漸淤積,砂石填塞,鹽館移走,小溪剩下一些涓流。根據民國八十八年(一九九九年)重修百姓公廟的碑記上麵記載,傳說在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這裏發生瞭「山仔坪之役」,當時「屍骨遍野」,不忍的人們在此建瞭一個草寮,收納屍骨。之後這裏成為最早的塚區,纍積去世的人,沒有停止過。曆經三百多年,十數次改建,纔有今日麵貌。然而康熙元年是鄭成功渡颱驅走荷蘭人的第二年,當年此地發生瞭什麼事嗎?是鄭軍驅荷後北上,徵討不肯降伏此地的中港社平埔族嗎?當時社人和距離不遠、同一種族的新港社人,確實是臣服於荷蘭人之下的,嚮他們繳稅納糧。還是敗逃的荷軍曾和中港社發生戰鬥?曆史幾乎是沒有記載的,碑記的說法有無錯誤,難以確知。
百姓公廟後麵有一個陽塔式的墓厝,裏麵收集瞭許多遺骨,農曆七月底照例會舉行簡單的法會,主事者會提供祭品,請道士誦經、燒紙,安慰孤魂。
用户评价
手捧著《巡禮‧思索‧人生: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四)》,一股莫名的期待感便油然而生。在颱灣,我們對文學的追求,往往不隻是追求形式上的美感,更看重其內容是否能引發我們對周遭世界的關懷與反思。這次星雲獎將目光聚焦在「報導文學」,這對我來說,無疑是一場及時雨。報導文學的精髓,在於它如何在既定的真實框架下,發揮文學的筆力,將冰冷的事實,轉化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溫度的人物故事。我非常好奇,作者們將如何捕捉社會中的細微觀察,如何挖掘那些隱藏在日常之下的深刻議題,又將如何透過文字,引導讀者進入一個真實而又引人入勝的世界。這本書,我預期它能帶給我的,不隻是一次閱讀的饗宴,更是一場心靈的洗禮。我渴望在這裡找到那些能夠觸動我內心深處的故事,那些讓我重新審視自己、審視社會、審視人生的篇章。這場文學的巡禮,我已準備好,踏上思索人生的旅程。
评分當我看到《巡禮‧思索‧人生: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四)》這本書名時,腦中立刻浮現齣許多對颱灣文學的記憶與期待。星雲獎的得獎作品,對我們來說,往往代錶著一股新銳的創作力量,而這次聚焦在「報導文學」,更是讓我感到無比的興奮。報導文學的魅力,在於它能將新聞的真實性,與文學的深刻情感、細膩描寫融閤在一起,創造齣既有知識性又有藝術性的作品。我迫不及待地想在書中尋找那些能觸動我內心、讓我重新審視周遭世界的篇章。或許是關於社會變遷下的個人命運,或許是關於被遺忘的歷史片段,又或許是關於那些默默奉獻的普通人。我相信,透過這些得獎作品,我將會展開一場深刻的人生巡禮,並從中獲得對生命的更多思考與啟發。
评分這本《巡禮‧思索‧人生: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四)》,光是書名就充滿瞭文學的深度與人文關懷。在颱灣,我們對文學作品的期待,除瞭美學的追求,更重視其能否引發我們對周遭社會、對人生百態的關懷與思考。報導文學,正是這樣一種能夠兼顧真實與藝術的文學形式。它讓冰冷的社會現象,透過作者的筆觸,變得有血有肉,讓被遺忘的角落,重現光彩。我特別期待在這本書裡,能讀到一些關於颱灣在地議題,或是華人社會共同經驗的報導文學。我想知道,作者們是如何深入採訪,如何捕捉那些不為人知的細節,如何將複雜的社會議題,轉化為引人入勝的故事。這不僅僅是一次閱讀,更像是一場心靈的洗禮,一次對人生意義的探索,一次對真實世界的深刻巡禮。
评分手握著「巡禮‧思索‧人生: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四)」,我彷彿接過瞭一份來自華文世界深處的邀請函。在颱灣,我們對文學的期盼,總是在於它能否觸及真實,能否引發共鳴,能否拓展我們的視野。而「報導文學」這個類別,恰恰最能滿足這樣的期待。它將新聞的客觀求證,與文學的細膩描寫、深刻洞察結閤,所呈現齣來的作品,往往既有事實的重量,又有情感的溫度。我迫切想知道,在這本書裡,我們將會遇見哪些真實而動人的故事?是關於那些在時代洪流中默默奮鬥的身影?是關於被忽略的角落裡,那些獨特的生命經驗?還是關於歷史事件背後,那些不為人知的真相?我預期這是一場兼具知性與感性的閱讀旅程,它將帶領我們走進真實的世界,去感受、去理解、去反思,並在每一個故事中,找到與自己生命對話的可能。這絕對是一本值得細細品味的文學瑰寶。
评分收到這本「巡禮‧思索‧人生: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四)」,我立刻就被它的厚度與質感吸引。身為一個長期關注颱灣文學發展的讀者,星雲獎對我而言,早已不僅僅是一個獎項,更代錶著一種對華文世界文學創作的肯定與引導。這次特別聚焦在「報導文學」,更讓我感到一絲興奮。報導文學的魅力在於它將新聞的真實性與文學的藝術性完美結閤,它不是冰冷的數據堆砌,也不是虛構的綺麗想像,而是透過嚴謹的調查、深入的採訪,將真實事件、真實人物,用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呈現齣來,讓讀者在閱讀時,彷彿親臨現場,感受人物的喜怒哀樂,體會事件的複雜與深刻。我尤其期待在這本書裡,能夠看到一些觸及颱灣社會脈動、歷史記憶,或是華人世界裡那些令人感動、令人深思的故事。報導文學的文字,往往具有一種穿透人心的力量,它能讓我們看到那些被淹沒在洪流中的聲音,能讓我們理解那些我們可能從未接觸過的生活,並在這些真實的故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與反思。這本書,絕對是一場文學的巡禮,也是一場心靈的思索之旅。
评分當我看到《巡禮‧思索‧人生: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四)》這本書名時,腦中立刻浮現齣許多畫麵。在颱灣,我們見證瞭文學的多元發展,而報導文學,更是其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它結閤瞭記者敏銳的觀察力、深入的採訪功力,以及作傢細膩的情感筆觸,將真實世界的點點滴滴,編織成一篇篇動人心弦的文學作品。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我穿越時空的藩籬,去觸碰那些真實存在的生命故事。或許是關於被遺忘的角落,或許是關於默默付齣的身影,又或許是關於社會變遷下的個人軌跡。報導文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能讓我們在閱讀的同時,深刻感受到現實的重量,並從中引發對人生的思考。這是一場文學的巡禮,也是一次對人生的探索。我深信,這本書中的每一個字句,都蘊含著作者對世界的觀察與感悟,也將成為我個人思索人生的重要養分。
评分這本《巡禮‧思索‧人生: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四)》光是書名,就充滿瞭深度與廣度。對於身處颱灣的我們來說,星雲獎一直是華文文學界的重要指標,而這次聚焦在「報導文學」,更是引發瞭我極大的興趣。報導文學的魅力,在於它能夠將我們日常生活中可能忽略的真實事件,透過文學的筆觸,變得生動而引人入勝。它不是虛構的小說,卻比一般的報導更有溫度、更有深度;它也不是枯燥的論文,卻比學術著作更加貼近人心。我期待在這本書裡,能夠看到作者們如何深入社會的肌理,如何捕捉時代的脈動,如何用文字描繪齣那些真實的人物故事。我希望能讀到一些關於颱灣在地發展、社會變遷,或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掙紮與希望的作品。這場文學的巡禮,不僅僅是對傑齣作品的欣賞,更是一次對自我生命觀的沉澱與反思,我迫不及待想要一探究竟。
评分哇!光是看到「巡禮‧思索‧人生:全球華文文學星雲奬報導文學得奬作品集(四)」這個書名,就覺得沉甸甸的,充滿瞭故事和智慧的重量。身為一個在颱灣成長、看著中文文學一路演變的讀者,對於星雲獎這塊金字招牌,心裡總是充滿一份期待與敬意。尤其「報導文學」這個標籤,更點燃瞭我對內容的好奇。報導文學不像小說那樣可以天馬行空,但它紮根於真實,又需要提煉齣文學的溫度與深度,這其中的平衡之道,絕對是考驗作者功力的。翻開這本書,我預期會看到一篇篇以真實為基底,卻又閃耀著人性光輝、社會關懷,甚至歷史省思的動人篇章。我對那些能夠將採訪、調查、紀錄等新聞採訪的嚴謹,巧妙融入敘事結構,並且能夠觸動人心、引發讀者共鳴的作品,總是讚譽有加。期待在這本書裡,能讀到作者們如何用文字描繪世界,如何挖掘被忽略的角落,如何呈現那些我們可能錯過的生命風景。這不隻是一本得獎作品的集閤,更像是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不同角落、不同生命、不同議題的真實麵貌,並且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地進行自我巡禮與人生思索,這本身就是一種極為豐富的體驗。
评分僅僅是看到「巡禮‧思索‧人生: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四)」這個書名,就讓我在颱灣的書市中,感受到一股不同凡響的文學能量。星雲獎在華人文學界早已是品質保證的象徵,而這次將重點放在「報導文學」,更讓我眼睛為之一亮。報導文學的迷人之處,在於它能夠將新聞事件的真實性,昇華為具有藝術感染力的文學敘事。它不隻是報導,更是深刻的挖掘,不隻是記錄,更是情感的傳遞。我非常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讀到那些觸動人心、引人深思的真實故事。無論是關於歷史的沉思,社會的觀察,還是人性的探索,我都相信這些得獎作品,能夠帶給我耳目一新的閱讀體驗。這不僅僅是一次對文學的欣賞,更是一場對自身生命的巡禮與反思,我渴望在這本書中,找到更多理解世界與人生的角度。
评分這本《巡禮‧思索‧人生: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四)》一書名,就勾起瞭我強烈的好奇心。在颱灣,我們對於文學的追求,總希望它能紮根於真實,又能開齣藝術的花朵。報導文學,正巧是這樣的一種文學形式,它透過嚴謹的採訪與調查,將真實世界的事件與人物,用富有文學性的筆觸呈現,給予讀者深刻的啟發與感動。我非常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看到不同角度、不同議題的報導文學佳作。或許是關於社會底層的聲音,或許是關於歷史洪流中的個人命運,又或許是關於文化衝突下的生命掙紮。我相信,每一篇得獎作品,都是作者用心血與智慧澆灌而成,它們不僅是文學的傑作,更是對人生、對社會、對時代的深刻映照。這場由文字編織的巡禮,勢必將引領我進入一場深刻的人生思索之旅,我迫不及待地想展開閱讀。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