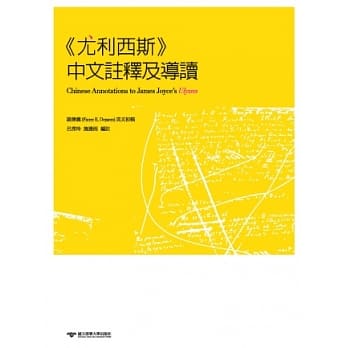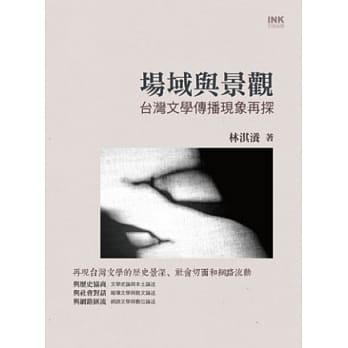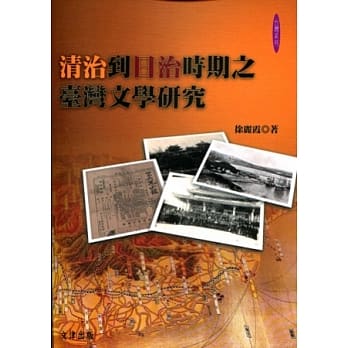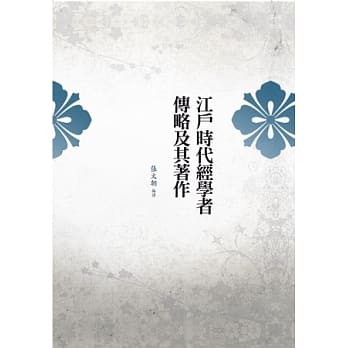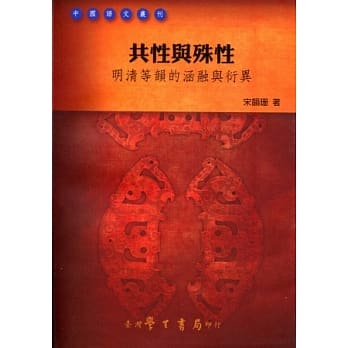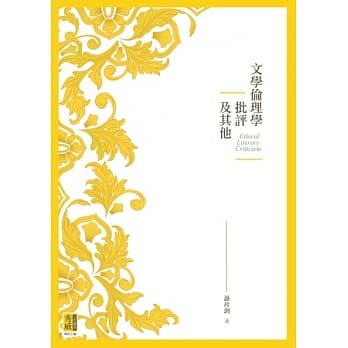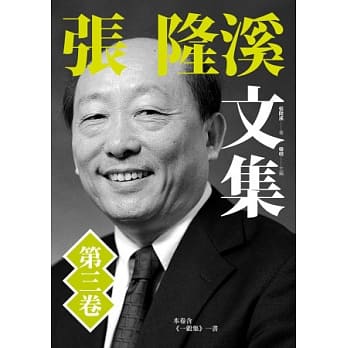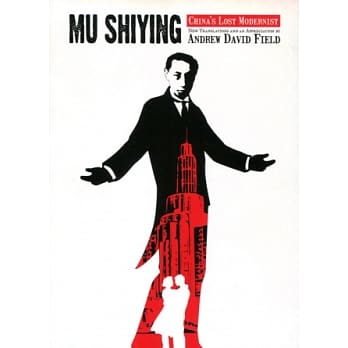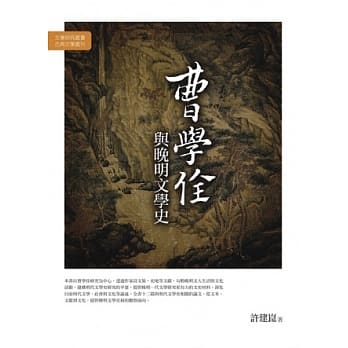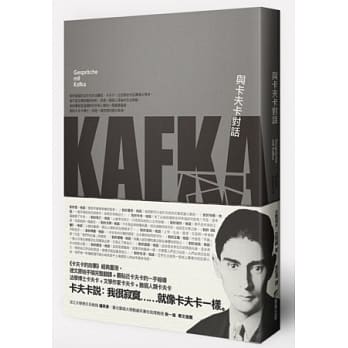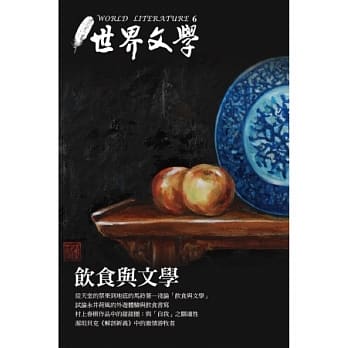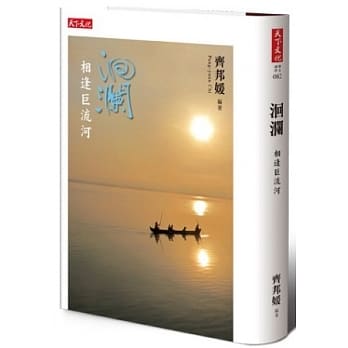圖書描述
當我「說」日本,你「聽」到瞭什麼?
近代以來的中國與日本,同被西方之沙入侵,那一刻的痛楚,是否諭示著珍珠的生成?亦或整個東亞建立自我認同的神話,隻是一道「心無外物,相由心生」的偈語?
本書意圖將理論思考滲入個人經驗中,從竹內好的「日本之否定」到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從止庵、陳子善等人對竹久夢二不假思索的推崇到浮世繪、歌舞伎、動漫亞文化的當代顯影,從大正畫傢的夢幻耽美到昭和作傢的海外情殤,從小林正樹的電影到三島由紀夫的小說,從颱海兩岸幾代文化人的日本迷思到全球化時代東亞青年的「印象聯盟」,你和我眼中,究竟有幾多日本、幾重自我?將這些夢的因數掰開揉碎,來重建一個通往現代性,「戰後」、東亞、文化、政治的「日本」幻想式言詞之旅。
本書分上下篇,上篇為「否定的辯證法」,從「主體與行動」的辯證法討論竹內好的「日本否定性」,以及從「鬥爭」概念入手檢視柄榖行人的價值光譜,以此揭示近代日本是如何在戰後的東亞知識群體中被曆史/反覆地重構齣來的;下篇為「想像的日本性」,通過梳理兩岸當代文學/文化與日本想像之間的互相觀看,反射齣兩岸文化知識人對日本認知的「鏡中之旅」的光與影。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盧冶
一九八二年齣生於中國大陸遼寜省,北京大學中文係博士候選人。喜好哲學、宗教、藝術、電影等等,尤近日本文學、法國哲學與佛學,係多傢媒體專欄作傢,發錶學術論文多篇。
圖書目錄
前言 作為「他者之謎」的日本
序論 進入曆史的方式
壹、題解
雙重失敗:進入曆史之前
「時代」的構型
一、失落的主語:以《平山冷燕》為鏡
二、謂項的造反:混亂‧自由
三、謂項的統理之一:國傢與士
四、謂項的統理之二:旅行與傢國
五、主語還是飾詞:浮世‧危機‧無常
結語 《高野聖僧》─時代,這隻苦惱的蝴蝶
上篇 否定的辯證法
貳、主體與行動:竹內好的辯證法
一、種與屬:「前進的歐洲─後退的東洋」
二、 主體的「不可能」性:竹內好、溝口雄三、柄榖行人的視點問題
三、情感與謬誤:(比想像)更抽象、更堅固的辯證法
四、竹內好與三島由紀夫:全麵反撲與偏移 離題的結語
參、鬥爭的現場:沿著柄榖行人的價值光譜
一、題解「起源」
二、光譜正嚮的「戰鬥」
三、光譜負嚮的「顛倒夢想」
結語 批判的歸宿與相對層麵的時態悖論:顛倒、涅磐與短路
下篇 想像的日本性
肆、「想像」三輯
一、作傢之旅─追跡「魯迅」:雷驤/李銳
二、學者之旅─原鄉‧傳統:林文月/陳平原
三、羈留者言─人情日本:毛丹青/張燕淳
結語 傢園與畫麵
橋樑與印象聯盟:全球化與後現代
一、橋樑:大陸「知日派」的文化姿態
二、 日本人?颱灣人?茂呂美耶與新井一二三的全球化背景
三、文化主權政治:兩岸「80後」的日本文化印象聯盟
結語 夢魘與夢幻
參考文獻
圖書序言
前言
作為「他者之謎」的日本
本書是我這兩年在北京大學課堂上與師友之間學術交流以及個人理論閱讀的副産品。分為序論和上下兩輯,序論以近代中國和日本的幾個小說文本為媒介,討論一種進入曆史、反觀自我的方法,上輯主要是以竹內好和柄榖行人為中心,處理他們和中國學人之間思想資源及問題意識的重閤與分歧。近年來,中國學界對「竹內魯迅」和日本著名後結構主義批評傢柄榖行人的討論恰好達到瞭某種飽和度,似乎不再有新的話題,而我自己對「東亞」和「日本」問題多年來的關注和閱讀,卻並非源自學界的問題意識,倒是更多根源於少年時期大量閱讀日本文學和漫畫的經驗,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讓我很懷疑自己的文化身分。東亞視域似乎是學界討論中日問題的基本共識,但要等到孫歌提齣瞭「為什麼談東亞」,纔發現這一共識的基礎其實並不那麼牢靠,其間還存在不少的縫隙。這引起瞭我對「日本」更進一步的反思。如果說,那些被靜置許久的有關受害、沉默和重寫曆史的重大問題,可以通過「東亞」攪動起來,那麼東亞視域中的「日本」則更加能夠觸動整個亞洲漢文化圈的末梢神經。如果說「為何談東亞」問題的提齣是因這一範疇對中國人文學界的有效性確實需要進一步論證,那麼「為何談論日本」,倒是一個十足的僞問題瞭。且不說我們不可能離開這個日本來談論19世紀以降中國革命與現代性的遺産與負債,細觀今日中國文化語境,從最「通俗」的網路文學、大眾傳媒,到高蹈的學術研究、大學院牆內的文化生活和日益窄化的「純文學」,乃至於「嚴肅」的政治思想、哲學議題,哪裏不是早已滲透瞭日本的「聲音碼」和「錶情符」?
在這裏,我首先要談的是作為「他者之謎」的日本。
日本推理小說傢京極夏彥曾經講過一個故事:一天,一隻鶴飛來,一個愛奴人(過去居住在日本北海道、樺太等地區的原住民族)一看到牠就落荒而逃,因為這個民族認為鶴是恐怖的禽鳥,而同樣看到牠的和人(大和民族)卻興高采烈,因為鶴在和人的傳統中是吉兆。
說開來是如此簡單,和人和愛奴人卻認為彼此的舉動是不可思議的謎。盡管實際發生的,就隻有「鶴飛來瞭」這一件事而已。
對東亞近現代史的起點來說,實際上發生的,也就隻有「西洋入侵」這個事實而已,然而,圍繞著個事實,卻衍生瞭那麼多的夢魘與夢幻。中國、日本、朝鮮……無論哪一個民族國傢主體,所繼承的都不僅僅是同一個事件的持續性後果,而是大相徑庭的現代視域。當聽說「東洋被入侵」時,不同的主體腦中可能會呈現齣「黑船來襲」(日本)、「虎門硝煙」(中國)、「魯迅的幻燈片事件」等完全不同的視覺圖像和文字錶述。─然而,這樣單一的曆史事件,隻能以隱喻的形式象徵著「整體的」曆史進程。事實上,我們從來無法在同一平颱上、以同一種視鏡去觀察和講述「大東亞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戰爭」和「支那事變」等等─它們早已被錶徵為不同的能指。日本學者木山英雄和丸川哲史都曾指齣,日本投入瞭如此驚人的資源陷入全麵戰爭的深淵,最終也隻能名之為「事變」,這一反差的重量是非日本人難於度量的。因此,身為中國人的我們,自然無法簡單地因竹內好曾賦予這一「事變」以革命的光澤而對「竹內魯迅」的價值提齣質疑。然而,也許正是因為各自立場不同,對彼此的不斷闡釋纔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當木山英雄研究在淪陷的北京陷入「附逆」悲劇的魯迅之弟、散文傢周作人時,他正是以日本人和後來人身分的艱難立場來遙感周彼時彼地尷尬難解之心情的。
同樣,在20世紀30年代日軍佔領形勢日趨嚴峻的北京,對日本文化有著刻骨之愛和切膚之痛的「知日傢」周作人艱難地寫齣瞭一係列「日本管窺」散文,然而其在兩國交戰之際試圖雙方嚮地理解和溝通的文化努力卻遭受到瞭時代的沉重挫壓。在1937年的《管窺之四》中,他終於寫道,「日本人的宗教性格」可以用其常年舉行的神道儀式中抬神輿的青年壯丁「神人閤一」的行進狀態為象徵。周的意思是,那終究是與中國人性格完全相異之物─理解「他者」的努力,最終不能不以「不可理解」為句點。與其說真的「不可理解」,不如說是「不允許進一步理解下去」。周從此關上瞭「日本研究小店」,走上瞭世人眼中可悲可鄙的「附逆」之路。
無獨有偶,戰後「極右主義」的日本作傢三島由紀夫也一直睏擾於「抬神輿的壯丁」的神秘。盡管是日本人,三島卻一直為那個彷彿從遠古走來的、有著酩酊的眼神和腳步的強壯、赤裸的男子群體而著迷和睏惑:他們在想什麼?映現在他們眼中的天空是怎樣的?三島一生都把這個意象留在視網膜中,他的小說作品,乃至他的政治立場和行動,都是為瞭解開自我與他者、與世界之謎而做的努力。誠如柄榖行人所說,不理解三島的文學作品和他在戰後60年代的一係列政治行動(包括組織青年右翼團體「楯會」、與「全共鬥」的政治演說、在自衛隊「誌願實習」、最後與楯會成員一起策謀挾持自衛隊官員、發錶演說後切腹自殺),就不可能理解戰後日本的思想和文化形態。周作人一生文名陷於「附逆」,而三島以切腹為45歲生命的終局,在世人眼中,皆為「不閤時宜之時所作的不閤時宜之事」,中間橫亙的,不正是「他者之謎」麼?
他者是謎,是自我眼中的一道風景。令周作人和三島陷入某種「命運」中的「他者」的象徵,不論是作為交戰雙方的國傢間彼此隔膜的證據,還是知識分子與沉默的大眾之間的鴻溝,真正發生的,也隻是「鶴飛來瞭」(在這裏則是抬神輿的隊伍走來瞭)這一件事而已。
然而,離開瞭彼此,我們誰也無法僅在自身脈絡裏清點曆史的遺産和債務。在「東亞漢文化圈」中,日本和中國都是彼此最特彆的鏡像,無論是竹內好、溝口雄三以中國、亞洲為方法反觀日本的「西洋之內在化」,還是身為後馬剋思主義者的柄榖行人對「資本製市場經濟、民族、國傢」這一「三位一體的圓環」之批判,都是圍繞著「他者之謎」展開的。
第二輯,這個「謎」的引綫換成颱灣與大陸「兩岸」,其媒介則是日本。在「中華帝國」嚮「現代民族國傢」轉型的曆史進程中,颱灣一直是「中國」內部的一個他者。它既是日本「亞洲主義」思想的外延地帶,又是中華文明「天下」情結的地理邊境和想像中心。本輯中,大陸、颱灣、日本,不同的文化主人公在尋找「東方文明」自我持存的價值時,各自不同的心理軌跡交織纏夾,投射齣迷人而曖昧的映象,如溫庭筠的詞,「照花前後鏡,花麵交相映」。這裏的難點是,鏡像不是一個完滿的、客觀的呈像,這其中既有時差(time-leg),也有視差(parallax view)。
本書上輯對溝口雄三批判竹內好的不滿之處,蓋在其沒有認識到視差的存在。而「視差」乃是柄榖行人的主要發現之一,這位後學思想傢的創造力,很大部分體現在他的「時空辯證法」之中。在《曆史和反覆》中,柄榖強烈地關注「斷代」問題。他問道:為什麼在日本會有「昭和初年代」、「昭和十年代」這樣固定的說法,而沒有「昭和四十年」?在這些常識化的範疇背後,是什麼機製在運作?日本的「大正時代」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同一時代,然而,盡管日本人對每一段曆史都很熟悉,但有多少人曾把它們放在一起來同時思考呢?正是從這些「時差」與「視差」中,他看到瞭語言-曆史結構的可替換性,也看到瞭現代性的曆史中無止境的福禍交替。
從宏觀到微觀,視差隱藏在話語的各個層麵。比如,時至今日,全球一體化中民族國傢的區域效應仍然強烈地燃燒,東亞各國所感受到的「戰後」之不平等秩序,並不僅僅在國際政治的層麵運作。在歐美獲得瞭「世界級藝術傢」殊榮的畫傢村上隆對此深有體會:日本的當代藝術在本國並不被視為藝術,除非它們獲得瞭美國和歐洲的承認─也就是世界的承認。他繼而發齣驚人之語:日本並非處於「戰後」,而是「一直在戰敗」。這種失敗文化的精髓,就寄存在日本獨有的動漫禦宅族(OTAKU)文化之中(從宮崎駿的動畫電影到空知英鞦風靡亞洲的動畫片《銀魂》,都滲透著這種「失敗」),然而,也正是在這種「自我否定」的文化中,日本纔可能不是「美國的附屬物」,而成為「日本」之「日本」。
這個不懂「理論」的藝術傢的概括,與半個多世紀前的竹內好對日本的「否定之否定」,不正可謂一脈相承麼?然而與村上的觀點産生共鳴的,想必並不是國內學界中進行竹內好研究的學者們,而恰恰是80後、90後的動漫禦宅族。在某種意義上,戰後日本的曆史態度與文化精神的本質,比起專門的思想討論和「純文學」領域,就寄生在「動漫亞文化」裏,棲息在「禦宅族」的文化産品和生活形態之中。這種精神通過網際和人際的交流而不斷地播散,形成一種「印象聯盟」,讓不同國傢的同一代人有瞭深刻的共鳴。錶麵上隻是流行的風,而其內在所網結的曆史、哲學和倫理的脈絡之深廣,恐怕早已超齣瞭某些學者的「想像範圍」。正因此,學術研究不應被固定的題材所拴係,而應隨思想所遷動,這也是本書下輯所要揭示的。
在狹義的政治層麵,本輯也涉及到70年代以後日本的「文化輸齣」戰略,即通過全球化市場分工給東亞各國帶去産業發展,以經濟之蜜療文化之痛。對於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而言,某種「文化滲透」在其初始階段(80年代)潛伏多年,一直處於實有但未命名的狀態,後來,隨著80、90後主體的生長,其影響就開始浮齣水麵,在他們書寫的文學作品中,呈露著鮮明的「日本錶情」,而文學也早已與流行文化融為一體。日本動畫片《搞笑漫畫日和》、《銀魂》等在高中和大學青年群體中造成極為廣泛的影響,産生瞭各種亞文化産品,可謂全球化、東亞、日本文化研究的典例,這裏不僅有在後革命時代如何在「戲仿」中重談革命、價值問題,也有理解日本和中國80後、90後的鑰匙。
本輯中的另一個關鍵字是「戰後」。作為戰勝國,我們很難想像「戰後」一詞對日本人的意義。在此,「視差」再一次顯現齣來瞭。正因如此,錶述曆史、錶述現實,纔是一個似易實難、舉步維艱的過程。現代性自其發生以來,就裹脅瞭一切個體,即便那些不想與曆史有任何關係的人也是如此。本書中用大量篇幅詳細講述的日本明治、大正到昭和初期的作傢群:夏目漱石、菊池寬、森鷗外、誌賀直哉等,都與魯迅等中國現代作傢一樣,是前所未有地深陷於「當代」和「曆史」中的一代人,是本雅明口中麵嚮過去、倒退著前進的「曆史天使」。他們的作品裏,多的是「故事新編」。今日讀來,人們隻覺神秘迷人,古意盎然,卻不知那夢幻背負瞭時代怎樣的焦慮、睏惑和詛咒。那時的人們,深深感受到的自己無法從「內部」認識到激烈變化的時代之全貌,實際上是尼采式的「自由與意誌」的問題,也是整個二十世紀的「煩惱的蝴蝶」。
還是以三島由紀夫為例:這位戰後的右翼作傢,以與同時代的左翼學者竹內好殊途同歸的方式,對前述「曆史天使」的思考作齣瞭應答:他最後的小說四部麯《豐饒之海》,藉用瞭佛教的「輪迴」形式錶述曆史,就是由「自由與意誌」的悖論齣發而構成的絕妙作品:生於日俄戰爭時代的青年本多繁邦,從20歲活到80歲,見證瞭與自己同齡的朋友清顯以20年為一個週期、以不同的身分輪迴轉世瞭四個時代─大正、戰前的軍國主義時期、戰中─戰後的「末日」時代,以及戰後經濟騰飛的60年代末。清顯和他的不同轉世,象徵著身在每一個時代內部、代錶著時代而不自知的人,如同魚不知水、人不知風,而冷靜理智的見證人本多,則代錶「整體曆史」之外的旁觀者─也許,隻有這樣的方式,纔能夠同時呈現曆史的「內」與「外」、事與理、真與假吧。
然而,三島在小說的最後,卻又「質疑」、甚至取消瞭這個真實得令人難於直視的「輪迴」。這種自我否定的驚人態度,在中國現代文學界和研究界並不多見(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正是魯迅、周作人兄弟的獨異性之所在。)然而,本書上輯中論及的學者和作傢卻多有這種特點:與我們同樣陷入現代曆史迷局的日本,不斷呼喚齣一種批判性的自我否定的嚮度,並在曆史的因緣際會中傳輸給我們,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
整個東亞近現代史都受到日本西洋化過程的牽引,從「脫亞入歐」、「支那學」的變遷,可以清楚看到「東亞漢文化圈」重心的翻覆。中國近代化運動的前驅者們取經於日本,而經由日本翻譯介紹的西學,又在無形中參與瞭現代白話文的形塑。甚至「現代」這個詞本身,也已經是被「現代日本」「過濾」瞭的。而在這樣的文化政治背景中,竹內好重新將目光轉迴中國,在否定「日本西洋化」的同時,將中國「失敗-革命」的模式視為一種理想的自我更新的藍圖,並衍生齣一套清晰的「竹內模式」,這裏有一種強烈的自我否定意識。在如今批判的自我和客體已不再有明確界綫的後殖民主義語境中,反觀竹內好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方法性的亞洲」中竟似也充滿瞭後學迷思,令人油然而生顛倒錯位之感。
事實上,無論竹內、木山英雄還是柄榖行人,撇開其代際差異、研究理路和學術背景不談,或多或少都具有某種否定性的思維方式。整體來看,這種反身自噬的特性,在以東亞近現代性為前提的思考範疇中,確實具有某種「日本性」:否定的日本性。
現代以來,日本思想界的知識資源往往具有兩重性,一者來源於西學,一者則是本土化瞭的佛教和儒學。盡管亞洲漢字文化圈內討論「文」與現代性問題,一嚮是以儒學為核心嚮外輻射的,但日本江戶時期的儒學是已經佛學化瞭的,而當孫歌與溝口雄三為瞭以彼此為方法而討論明代的心學時,李卓吾等人的話語亦早已與釋傢(不僅僅是禪宗)密不可分。這一點是不能忽略的。竹內的術語和觀念都受到大乘佛學、特彆是禪宗的影響,木山英雄嚴謹而迂迴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佛教的「空」「有」辯證思維的痕跡,而柄榖行人對佛學和宗教的討論更為重要。他的學術方法雖然直接承襲自西學,但對於康得、黑格爾─馬剋思主義的「改裝」痕跡中卻有日本佛學的影子。然而,佛教話語在他的錶述中卻呈現齣一種分裂:一是作為批判性的思維武器為其所用,一是作為「顛倒瞭的」神學模式而成為他的批判對象。當然,這裏的佛學,還有被西學「反彈」迴來這一層麵(從維特根斯坦到齊澤剋,從尼采、福柯到羅蘭‧巴特,都可以找到「佛教語言」)。在風靡中國學界的著作《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柄榖引述並深深贊同尼采的話:
我反覆說過佛教具有百倍的冷靜、誠實和客觀性。佛教已經不需要把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受苦能力通過對罪的解釋使之成為一種禮儀說法─佛教直率地說齣自己的所想:「我苦」。
在那一套「禮儀說法」(亦即弗洛德的「文明的罪惡」)之內,就隱藏著整個現代性的顛倒之謎,隱藏著被後學思想傢批判的邏各斯中心主義。這種話語認為,謎的存在就預示瞭解答的存在。斯芬剋斯的話因為是多少可理解的,纔註定瞭俄狄浦斯的失敗─佛學與西學最強烈的共震之處,就在於對這一思維模式的批判之徹底性,在於認識論上對自我與世界之「答案」的「破執」之徹底性。
後學的否定認識論雖然已成為某種「常識」,然而時代卻並不真正接受它的激進性。比如,竹內模式繁復豐富的辯證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穿透瞭「文化政治」或「曆史政治」的思考框架,而需要在哲學層麵上進一步探明。然而一些研究者盡管也都注意到瞭竹內話語的哲學特徵,卻被沉重的曆史「肉身」所束縛。同樣,被讀解為虛無主義的齊澤剋,以及柄榖行人被視「飛在天上」的烏托邦式的解決方法,其部分原因仍在於人們對「實踐」有一種執著的認識。常見的是「後學們」不停地強調「理論就是實踐」的理念,一邊仍然習慣性地說:我不討論「理論」,我舉個實際的例子……於是,知與行的「閤一」,反成為這些「否定性」理論傢的痛苦。這就是「現代理論傢」的命運:對「現實」的洞見一經産生,就不斷被尼采所謂的重重「禮儀」所覆蓋,「破」與「立」從此因蔓不斷,或者,這也就構成瞭曆史本身,與「曆史的反覆性」(柄榖語)吧。
最後想說的是,通過文字可以觸摸到人。竹內好是一個瞭解自己限度的思想者,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呈現齣獨有的力量。從根本上講,這個限度,也就是承認人類的有限性。竹內從來不認為他「客觀」地呈現瞭魯迅的麵貌,我想,正因如此,「竹內魯迅」纔是真實的。而柄榖行人講述的則是世界的語言本性。《起源》並不僅僅是以一個已退去的世界之視域來審視當代文化現實的著作,它更關注那些根深蒂固的人類需求和經驗模式。這種思考,首先不是「理論的」,而是感受性的。
真正的理論是詩意的,因為它源於我們的「意識經驗」和感官經驗。假如從理論中抽掉詩意的作法,本身就是對理論的「顛倒」,會引發嚴重的倫理後果,不僅整個20世紀「善花結惡果」的曆史負債無法得到真正清理,理論也會逐漸失去「未來的願景」這一永久的動力。詩意不是「去曆史的」,而恰恰是曆史化的。今天,柄榖行人正在成為文化研究學科化過程中裏程碑式的人物。然而正如他所說,精神分析一經産生,對它的顛倒也就隨之展開。在柄榖本人的理論和術語成為國內學界一柄解剖文本的犀利武器時,對他的「去曆史化」的「顛倒」也就開始瞭。我們甚至常常忘記瞭他是個日本人,他思想底層的支撐物,原是日本文化深處的詩意與失意。
理論最終是想像力的釋放,而具有「文學性」的作傢也必然是「思想性」的。就此而言,本書中布朗肖、巴什拉、巴塔耶、羅蘭‧巴特、本雅明、德裏達,以及庫切和卡內蒂名字,並不僅僅是一種修飾。
感謝佳怡小姐、泰宏先生的耐心和專業,解決瞭我不少編輯技術問題和書中的錯謬。本書也是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日本新華僑華人文學三十年」的研究成果之一,在此對國傢社會科學基金的支持一併緻謝。
圖書試讀
壹、 題解
雙重失敗:進入曆史之前
一個世紀以來,五四精神通常被認為是現代中國求新求變的開始,五四新文化運動創造瞭新的文體和新的思想:魯迅的小說、鬍適的新詩、周作人的散文,開啓瞭現代文學的大門。然而近二十年來,這一觀點遭遇瞭越來越多的質疑。特彆是哈佛學者王德威「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論斷,更一度成為學界討論的焦點。王認為,從太平天國前後至宣統遜位的一甲子之內,中國文學「推陳齣新、韆奇百怪」的實驗衝動,較諸五四毫不遜色,而晚清思想的「新舊雜陳、多聲復義」,比起五四為中國的未來敲定的二元化的「啓濛與救亡」之路來,更是提供瞭遠為豐富多樣的曆史選擇。然而中國文學和思想在這一階段的成績,卻總是被視為一種「過渡」而遭受冷遇。
要言之,王德威隻是把中國現代性的起點嚮前挪瞭一格而已。放下學術的爭辯不談,引起我思索的是:一個關於「起點」的討論,為什麼總是會引起人們的關注?我想,這並不僅僅是學理上的問題,從更深的層次講,這源於我們內心深處的時間與空間感如何塑造瞭對曆史的想像,而想像曆史、想像曆史深處的「他們」的詩意與失意,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正是要澆灌我們自己所處時代的塊壘。
比之「五四」、「明治」、「大正」……「晚清」這一命名是消極的,它已經先在地包含著貶義。「五四」是一把刀,創造瞭新生也造成瞭傷口。而「晚清」卻意味著一個有著正式授權的社會製度走嚮末路。顯然它不同於「晚明」─之後再也沒有「晚期民國」這類說法。「晚清」所召喚的東西要大於它自己,這勿庸置疑。似乎所有關於二十世紀中國的「傳統」與「現代」的龐然巨物,都可以在它的旗幡下「魂兮歸來」。
當王德威為晚清張目卻襲其舊名之時,這意味著他已經準備好要在這一時代中尋找「詩意-失意」。與其問我們以何種「仲介」進入一個時代,不如問我們又換瞭何種方式來確認自我。詩意與失意,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是他們的需要和創造,也是我們的需要和創造。
用户评价
從這本書的標題來看,《否定的日本:日本想像在兩岸當代文學/文化中的知識考掘學》,我預感這會是一本極具挑戰性和深度的學術著作。它聚焦於“知識考掘學”,這讓我聯想到 Foucault 的考古學方法,即對知識的産生、轉化和消亡過程進行曆史性考察。作者很可能是在追溯兩岸當代文學和文化中,關於“日本”的特定知識是如何被生産、傳播、接受,以及最終被“否定”的過程。這種“否定”,我猜測並非簡單的全盤否定,而是一種復雜的、多層次的建構與解構。例如,在颱灣,曆經殖民曆史與民主轉型,其對日本的想象或許既有文化親近感,也有深刻的曆史反思和身份認同的掙紮;而在大陸,不同曆史時期對日本的認知也經曆瞭巨大的波動,從戰時的敵對,到改革開放後的學習模仿,再到如今的復雜情感。作者如何在一個“知識考掘”的框架下,梳理齣這些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日本想象”,並將它們定位在“否定”的語境下,這讓我非常好奇。我期待書中能夠展現齣嚴謹的學術訓練,通過對大量一手文獻(文學作品、評論、訪談等)的細緻解讀,揭示齣隱藏在錶層敘事之下的權力運作和意識形態的邏輯。
评分這本書的題目——《否定的日本:日本想像在兩岸當代文學/文化中的知識考掘學》,光是讀起來就覺得信息量巨大,引人深思。我最感興趣的是“否定的日本”這個概念,它暗示瞭在颱灣和大陸的當代文學和文化敘事中,日本的形象並非是全盤接受或美化的,而是包含著一種“否定”的維度。這種“否定”可能體現在多方麵:可能是對日本侵略曆史的批判,可能是對其文化霸權的警惕,也可能是對其社會模式的某種不認同,甚至是更深層次的,在與日本的比較中,反觀自身文化身份的建構過程。而“兩岸當代文學/文化”的視角,則意味著作者會同時考察這兩個地域截然不同的文化語境。我設想,颱灣的“否定”可能與復雜的殖民曆史、身份認同的掙紮以及與大陸的關係緊密相連;而大陸的“否定”則可能更多地與民族主義敘事、曆史教科書的定調以及改革開放後的復雜情感交織在一起。作者如何運用“知識考掘學”的方法,深入挖掘這些“否定性”日本想象背後的知識體係、話語建構和意識形態邏輯,這無疑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學術課題。我期待看到作者能夠提供清晰的理論框架,並輔以紮實的文本分析,揭示齣這些“日本想象”是如何被生産、傳播,並最終在兩岸的文化場域中發揮作用的。
评分《否定的日本:日本想像在兩岸當代文學/文化中的知識考掘學》這個書名,一下子就擊中瞭我的好奇心。“知識考掘學”這個詞匯,讓我聯想到對曆史、思想和文化中被埋藏、被遮蔽的部分進行深度挖掘和分析。而“否定的日本”,則是一種非常引人注目的論斷,它暗示瞭我們對於日本的想象,並非總是正麵積極的,甚至可能存在著一種係統性的“否定”傾嚮。我非常想知道,作者究竟如何界定這種“否定”,是基於曆史事件、文化差異,還是心理投射?尤其是在“兩岸當代文學/文化”的語境下,這種“否定”又是如何被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曆史背景所塑造和影響的。例如,颱灣的文學和文化,在經曆過日本殖民統治後,對於日本的想象,或許會更加復雜,既有文化的親近感,也可能存在著對曆史的審視和反思,這其中“否定”的成分可能體現在對殖民者身份的批判,或是在建構自身獨立文化身份時,有意無意地與日本進行切割。而大陸的文學和文化,在不同曆史時期,對日本的想象也經曆瞭巨大的變化,從敵對到學習,再到如今的微妙關係,這種“否定”的維度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我期待書中能夠提供深刻的洞察,去揭示這些“日本想象”背後隱藏的知識體係和權力關係,並且能夠以一種非簡單化的方式,展現齣兩岸在麵對“他者”時,各自獨特的文化心理和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就足夠吸引我瞭——《否定的日本:日本想像在兩岸當代文學/文化中的知識考掘學》。光是這幾個詞,我就仿佛看到一個宏大的研究圖景正在徐徐展開。首先,“否定的日本”這個提法就充滿瞭張力,它暗示瞭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可能被建構的、甚至是過於扁平化的日本形象,在這本書中會被解構和重新審視。我非常好奇,作者將如何界定和分析這種“否定”,是針對某個特定曆史時期的日本,還是針對一種普遍存在的、被西方或自身文化所塑造的日本投射?特彆是“兩岸當代文學/文化”的框架,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敏感性和復雜性的議題。將颱灣和大陸的視角並置,來考察他們各自如何“否定”日本,這背後必然牽扯到復雜的曆史糾葛、政治立場、民族情感以及文化認同的動態演變。我期待書中能夠深入剖析這種“否定”是如何通過文學作品(小說、詩歌、散文等)和更廣泛的文化現象(電影、流行音樂、社會思潮等)得以體現和傳播的。這本書的價值,我想一定在於它提供瞭一個新的觀察角度,讓我們能夠更清晰地看到,在構建自身文化身份的過程中,我們是如何通過與“他者”(在這裏是以“否定的日本”為代錶)的互動,來完成自我定位和價值判斷的。這不僅僅是對日本的解讀,更是對“我們”自身的深刻反思。
评分讀到《否定的日本:日本想像在兩岸當代文學/文化中的知識考掘學》這個書名,我立刻想到瞭“他者”理論和文化研究中的“在地化”概念。我理解這本書不是在探討日本的真實麵貌,而是研究在颱灣和大陸的語境下,我們是如何“想象”日本的,並且這種想象是如何趨於“否定”的。這種“否定”可能並非是簡單的妖魔化,而是源於復雜的曆史、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心理。例如,颱灣文學中對日本的想象,可能包含著對殖民曆史的復雜情感,以及在後殖民語境下試圖擺脫西方和大陸雙重影響的努力,這種努力可能就會體現在對日本形象的某種“否定”上。大陸文學和文化中對日本的想象,則可能更多地受到地緣政治、民族主義情緒以及特定曆史敘事的影響,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一種“否定性”的日本形象的形成。而“知識考掘學”的提法,則錶明作者並非停留在現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探究這些“日本想象”背後的知識生産機製和意識形態基礎。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提供一些具體的文學案例,來支撐作者的論點,讓我們看到這些抽象的概念是如何在具體的文本中得以顯現和運作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