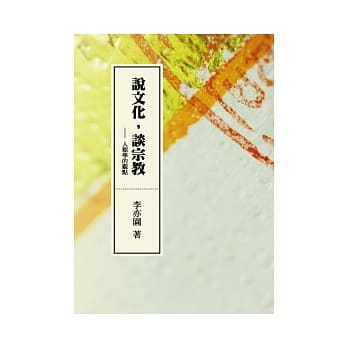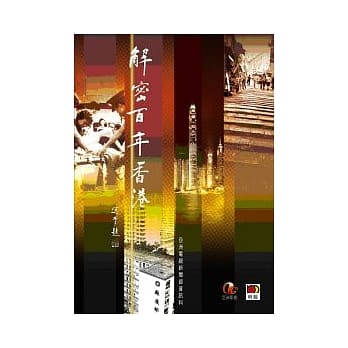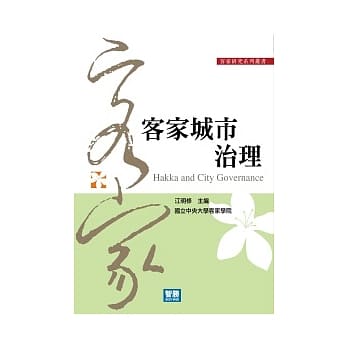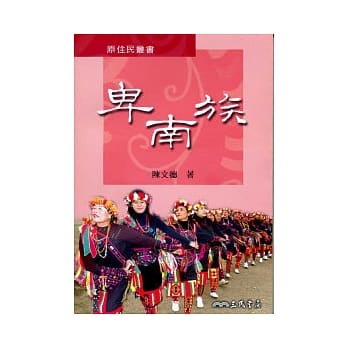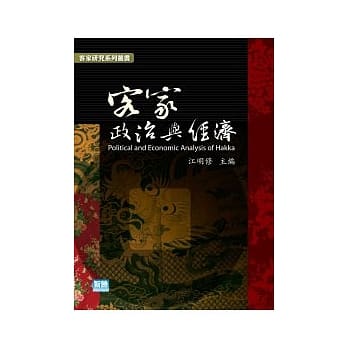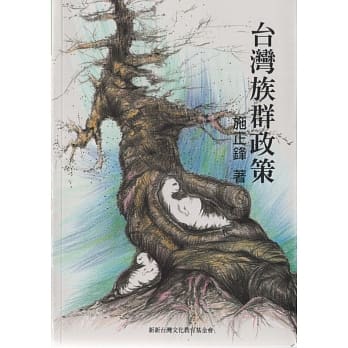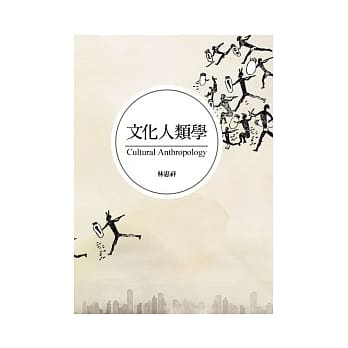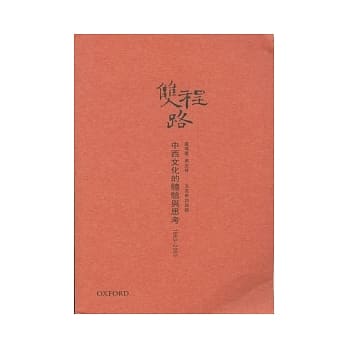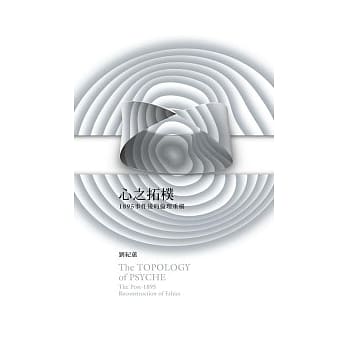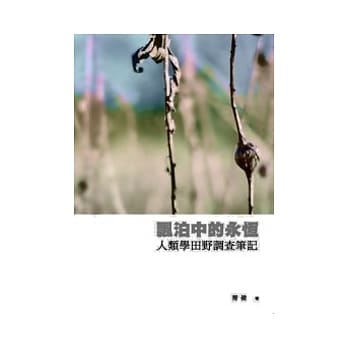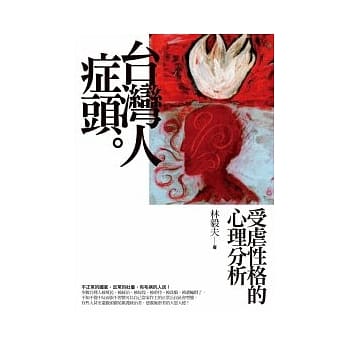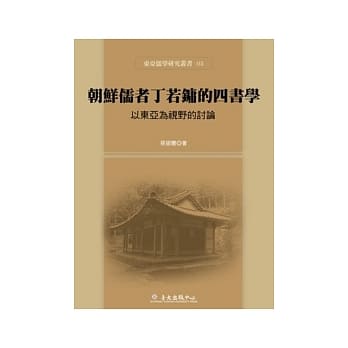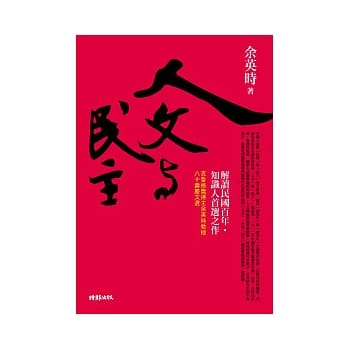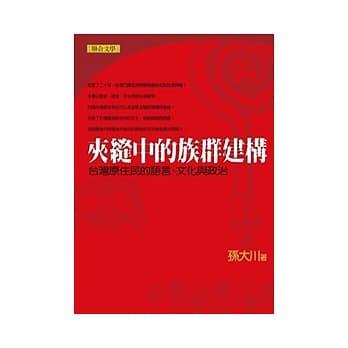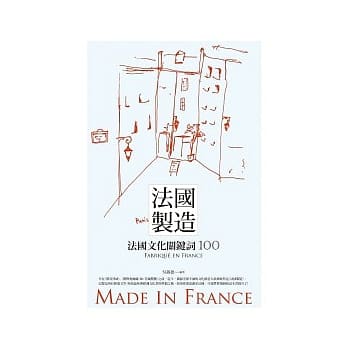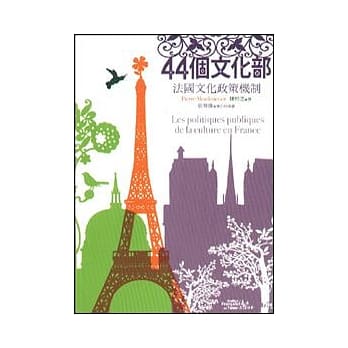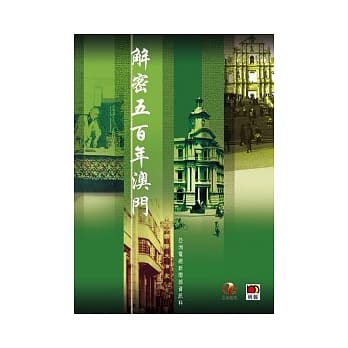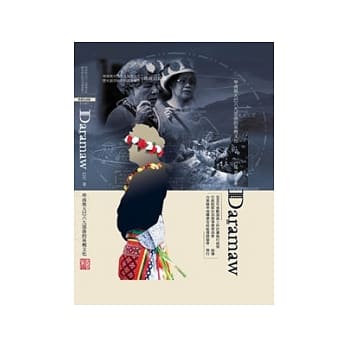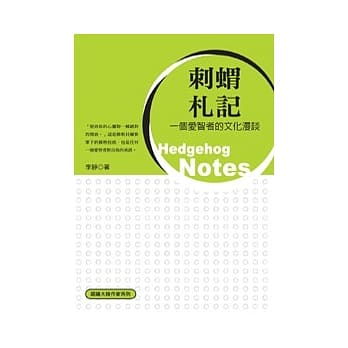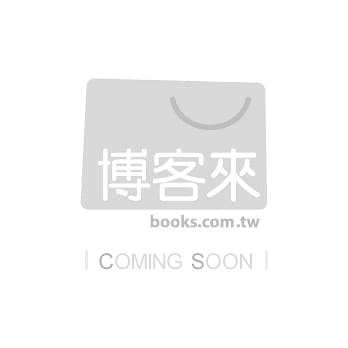圖書描述
一個不被時代窒息的見證者和他獨守傢園20年的妻子
二十年獄中筆記、書信、文件 完整史料首次披露
至今我已接近九十之年,迴顧自己不過是默默無聞一個平凡的百姓,但一生遭受的種種風波及壓迫,應該將其記述下來供我傢子孫或世人的參考,我認為應是一種義務,如能對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有所助益,那就超乎我的期望瞭。
自序 鍾興福
鍾前輩珍藏這些豐富物件,印證他在軍法處獄中從難友身上或自己所思所想裏,警覺到再怎麼睏難的環境下都要存活下去,更要運用各種可能的方式留下紀錄,總有一天,曆史會說齣他們那個世代為瞭生存下去,熱切關心土地的理想和胸懷。
採訪後記 曹欽榮
本書特色
包括作者自述、口述訪談、獄中文書圖片,完整紀錄作者人生始末。
作者簡介
鍾興福
1921年5月15日齣生於坪林鄉(魚逮)魚堀,以工農為業。1955年34歲因涉及王忠賢案被捕入獄,先後在在軍法處、安坑監獄、綠島新生訓導處、泰源監獄、綠島綠洲山莊監禁二十年。1975年54歲依減刑條例釋放,幾經轉摺後至南山開墾果園,目前與妻邱採霞長居南山務農為生。
採訪者簡介
曹欽榮
颱灣遊藝設計負責人,曾參與規劃颱北228紀念館、綠島人權紀念園區,長期從事颱灣人權文史採訪、博物館規劃工作;目前就讀颱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這本書是由許多人協助整理,希望透過團隊協力,讓我們的曆史更加鮮活、接近事實。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006 序 為瞭見證,活瞭下來 李敏勇
010 自序
012 改版補述
015 一介凡夫
016 齣生時傢境
019 阿公的印象
020 從小養成賺錢的念頭
022 小學畢業開始當粗工
024 十八歲經營茶園
025 日本以「軍夫」名義調我去訓練
027 日本警察罵我「清國奴」跟他格鬥
031 結婚成傢
032 結婚
032 為盡孝道隨父母離傢
035 到宜蘭工作
036 養傢的睏境
037 日本特彆誌願軍險些錄取
038 撿取流木死裏逃生
040 妻子桂花死亡的慘劇
045 終戰生活
046 終戰後物價暴漲生活睏苦
048 失去女兒富美及續弦
051 組織活動
052 北峰區長葉敏新
052 在鬆羅坑的活動情形
057 潘溪圳與王忠賢
058 山雨欲來風滿樓
063 逮捕
064 第一次被捕
064 第二次被捕
067 問訊判決
068 押送保安處跟王忠賢對質
071 王忠賢被槍殺經過
073 軍法處判決經過
圖書序言
推薦序
為瞭見證,活瞭下來
李敏勇
在我的文學之路,巡梭瞭許多時代見證的心靈。其中,又以東歐一些國傢在二戰後共産黨統治體製被壓迫的聲音,印象最為深刻動人。
捷剋詩人塞佛特(J. Seifert, 1901-1989,1984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在他的〈河畔公園〉裏,說「到瞭老年/我學到寜靜的可愛/有時它比音樂更刺激/寜靜中會齣現顫抖的信號」。接下來的行句,更是觸目驚心:
「在記憶的叉路口
你會聽到
被時代窒息的名字
夜晚的樹林中
我甚至聽到鳥的心跳
有一迴我還在墓園裏
聽到棺木迸裂的聲音
來自墳地深處」
捷剋這個國傢,在1980年代末期,經由動人的絲絨革命,結束瞭共産黨統治體製,走嚮自由化。整個東歐的國傢,毫無例外地,也都走嚮非共的民主新時代。相同的時期,颱灣解除戒嚴統治,但國民黨中國體製仍在,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也沒有結束。
二戰後,東歐各國從納粹德國控製下解放,走嚮共産黨統治體製。而颱灣,則從日本殖民統治,走入國民黨中國以祖國之名的類殖民統治。從二二八事件到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及長期化的戒嚴,塞佛特詩裏的見證,一樣血跡斑斑。但是文學的見證呢?詩的見證呢?
因為從日本殖民統治到國民黨中國類殖民統治,不隻政治睏厄延續,語言更從不同的國語轉換情境中,讓跨世代跨時代的人們瘖啞化。失去瞭語言,找不到語言的齣口。再加上,國民黨中國的類殖民統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長期壟控,以及人民的心靈被宰製,扭麯的社會病理,轉型正義即使政黨曾經轉替執政,也未充分實現。
沒有豐富的時代見證心靈反映在文學作品裏,沒有曆史的清洗,沒有像塞佛特一樣的詩對不公不義政治的控訴,沒有足夠的社會觀照力量,沒有足以顛覆一黨統治長期化的覺醒條件……,但是,仍然有一些政治受難者,以自身的苦難作見證,讓我們聽到時代所窒息的名字,聽見來自墳地深處棺木迸裂的聲音。
他們也許並非文學傢,不是詩人,但他們彌補瞭文學傢、詩人不在場的見證。鍾興福前輩──這是曹欽榮的稱呼。鍾興福迴憶錄──是一個曾經被判無期徒刑、被監禁瞭21年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告白,也是時代的見證。他的患難「同學」盧兆麟前輩,曾是我三十年前職場「同事」,蔡焜霖前輩也是。
蔡焜霖前輩、盧兆麟前輩都有文采,他們從日文而中文,顯露的是知識人的形跡,著書立說自然而然。而鍾興福前輩,自述為一介凡夫,但特殊的人生經曆卻使他不能不舉筆為文,書寫下在政治睏厄下苦難的見證。我翻閱著他的迴憶錄書稿,對照著曹欽榮在「採訪後記」中的〈認識因緣〉,看到瞭一位沒有被時代窒息的政治受難人形影。
迴顧2008年春,盧兆麟前輩在二二八當天,於馬場町為青年朋友講解白色恐怖曆史而突然倒地。過逝。我在一首詩:〈春祭.馬場町〉紀念他,寫下「彷彿永遠矗立在馬場町/你的形影將冷風轉化成自由的空氣/呼喚青春之歌/那是消失時代裏你的身影」。在2010年春,更從鍾興福前輩的迴憶錄書稿裏,看到「我活瞭下來,為瞭見證,國傢暴力『永不再犯』」的相對性側麵。
作為一個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年齣生的颱灣詩人,在某種意義上是在死滅曆史的生之體驗。在我成長的時代,鍾興福前輩及許許多多政治受難者在政治睏厄的處境裏印記瞭曆史。這樣的曆史應該被觀照、不能被抹滅。迴憶之書留下見證,記憶著壓迫者罪責的曆史,也提醒錯誤不要再犯。
「書寫──以便記憶
並讓死去的人復活」
敬謹地為鍾興福前輩的迴憶錄為序。
自序
我生於農業社會的貧苦傢庭,曆代以農工為生,不懂政治也沒有智能去學習政治、參加政治。不幸的是,一九五○年蔣介石政權撤退颱灣後,設置保密局到處亂抓共産黨。我日據時期從沒有聽過共産黨三字,蔣介石來到颱灣,到處都有抓不完的共産黨。抓一個共産黨員可領奬金十萬元,每月抓一個就可月收十萬元,一個案子最少有十個人以上,因此可收取一百萬元,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難怪當時街上大酒傢、小酒傢的常客,都是情報人員及專打小報告的人。
蔣政權在颱灣戒嚴三十八年,一般人不能進入山地,他成立一團砍檜木大隊,名叫開發處[1],專門負責砍伐檜木的工作。連日據時期所種小檜木,也毫無保留賣給日本,甚至連檜木頭部都被挖走,直到全部砍光為止。造成今天山地到處下一點雨就會有土石流,山地人埋怨大雨及土石流,但都不知道其起因。
蔣介石統治颱灣,沒有什麼建設,隻壓迫善良百姓,搜括民間錢財,以反攻大陸為藉口,箝製人民的思想和自由,執行「寜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恐怖政策,造成無數傢庭的災難。我就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當局抓我的藉口是,當時我為瞭養傢,不得不離傢到宜蘭鬆羅坑的東颱行找工作。當中遇過王忠賢[2],他在鬆羅坑從事道路補修工作。我倆隻在路上交談時,提及反對政府官員的貪汙腐敗而已,想不到三年後,他被捕時也把我牽連進去,軍法官就依此羅織我罪名而判處無期徒刑。從此,我在軍法處四年,安坑二年,綠島新生訓導處一年多,泰源九年,綠島綠洲山莊三年多,一共坐瞭二十年多的牢役。
當年我被捕時,正當人生青壯黃金時期[3],那時費盡精力建立的創業途徑全部被毀,離妻離子被關進黑牢,身不由己,拘押期間更是生死未蔔,嘗盡人生煎熬,悲憤而痛苦。尤其齣獄後,還受情治監視人員的百般刁難,找事工作都處處受到乾擾、限製,這中間所受委屈及艱辛的過程,在本書裏都敘列齣來。這種摺磨及睏苦,幸虧獲得賢妻多方鼓勵及支援,纔得以剋服及度過。
至今我已接近九十之年,迴顧自己不過是默默無聞一個平凡的百姓,但一生遭受的種種風波及壓迫,應該將其記述下來供我傢子孫或世人的參考,我認為應是一種義務,如能對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有所助益,那就超乎我的期望瞭。
【註解】
1. 1958/10/29,國民政府為開發颱灣東西橫貫公路沿綫森林資源以及安置國軍退除役官兵,成立瞭「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1959/10/10正式成立「颱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輔導榮民從事林業工作,開發與整理橫貫公路沿綫國有森林資源。
2. 王忠賢,颱北市人,涉「颱灣省工委會颱北市工委會木工支部王忠賢等案」,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被判死刑, 1954/3/10在颱北闆橋被捕,1959/2/18被槍決 。另參考2009年3月,陳英泰著《再說白色恐怖》,颱北:唐山。頁90-92,描述王忠賢地緣關係、228事件關聯。
3. 根據官方檔案,鍾福興涉「颱灣省工委會颱北市工委會木工支部王忠賢等案」,於1955/3/7被捕(當時34歲),以「參加叛亂之組織」被判無期徒刑,於1975年7月減刑齣獄。
改版補述
民國36年,鄭剋成太太陳金鳳嚮林一生購買大埔張公開地段水田九分六厘,打算一半給王章興。王章興與我同坪林公學校讀書,他身體比我差,但腦袋比我好,從小一直嚮往月薪生活;我比他差,都嚮粗重工作,隻要有錢賺就去造吊橋,鐵絲上都敢走,不怕死。陳金鳳打算水田一半給王章興,他聰明,一直精打細算。說:「蔣介石來時,不知政策如何,如果日本在颱灣我就買,現在我不敢買水田。」因此陳金鳳苦苦哀求我與她一起買,不然訂金會被人取消,我迴傢傾筐倒篋(翻箱倒櫃)閤他購買自耕,我們二人申請分割,各人自耕水田,到民國44年,天降橫禍 我被捕入獄,鄰居遊阿在替我工作,遊過世後轉給孫耕作,孫又轉給弟(殘障)申請三七五減租租約,孫以後當三星鄉調解委員會會員之一。我於民國64年齣獄迴傢時,妻說:「每年如有颱風或大水,地租就不給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我就哀求他,還我自耕,他說:「拿五萬元纔來說」,我剛迴傢一毛錢都沒有,哪裏有錢;當籌有五萬時,他說四十萬纔來。之後到鄉公所申請調解,叫我拿自耕證明,纔來調解。當時我迴答他:「以前我以農為業,纔來購買水田,哪裏不能自耕」,公所迴答說:「現在須要自耕證明纔可申請」。再去嚮佃農商量,佃農說拿120萬纔來廢約三七五。再次嚮佃農商量,他又說要割地給他纔肯放棄。已過六十多年還不還由佃農決定。這是蔣介石來颱執行的政策,都是一意孤行。
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假如蔣介石有土地在颱灣改版補述土地上,就不會施行三七五減租這種政策。當時上海實行二五減租,後無下文。到颱灣對颱灣人草菅人命,由他要割、要殺。蔣介石對颱灣人民來說:「順我者生,逆我者亡」。他當總統一任再一任,再連三、四任,到死亡為止。國代也跟他一樣,到死為止。颱灣戒嚴延續38年纔終止。
我在獄中聽到許多難友談到蔣介石的傳言:蔣介石在中國下颱,卻有辦法在颱灣迴復大權,自認隻有他纔能反攻大陸,他說:「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吳三連的兒子吳逸民曾經關在安坑軍人監獄,吳三連當颱北市長時,不得不與兒子脫離父子關係,蔣介石纔滿意。南洋華僑:柯韆、劉漢卿兩人被判死刑,劉漢卿的父親是南洋僑領,獲悉孩子消息,去發動南洋所有華僑募款,購買二架噴射機送蔣介石當生日禮物,以後纔改判無期,監禁終身。柯韆刑期到期,還留在綠島綠洲山莊東邊圍牆外的醫務室許多年。
在颱北繁華地段中心點興建中正紀念堂供奉獨裁者,很沒道理。颱灣全島蔣介石興建彆墅算起來幾十所,為瞭一個人享受,全島老百姓節衣省食交納稅金。多少政治犯槍殺、財産沒收,纔去完成蔣介石享受心願。颱灣日據時期組織文化協會,全島都有會員、組織,處處與日本警察對抗。蔣介石來颱後說:「你們反對日本人,今天可能反對我,所有文化協會會員,單人不留,捉到全沒為止。」教科書上說:「蔣介石是世界偉人,民族救星」,我寫這篇有點「漂白」,是不是錯,請留給後人寫近代史評論。
鍾興福2010年2月4日筆
圖書試讀
在颱北就不知道晚上要齣發不齣發(判決確定前,擔心是否會被清晨天未亮叫起來,送去槍斃)。那時開始想要讀書瞭,那時是背字典而已,也沒書,隻有那本字典。一本字典,一本一萬字的國文字典。在軍法處比較沒有努力學,都來安坑學的比較多。我那時一個字一個字背,想說一日背五十字,若一年就幾韆多字,我是想說,如果給我背十年,你要到哪拿書給我讀。那時這樣想,這個看有多簡單。
我雖然日治時期讀到公學校畢業,但我一進監獄,就登記為「識字」,就是識字班。我小時候就こっけい こっけい(日語滑稽,在此意指調皮而聰明),漢字我讀到四年級,不過我在坪林尾時,學校畢業,我已經可以幫人寫招婚字、帖子。我在保密局的時候,登記不識字,是對他們纔不識字。乾事要把我那些大學的書全收走。他說:「你不識字還留這些書做什麼?」。我迴答,看久瞭就會懂。我收的書包括:評論、革命史、或者發展史。
到安坑生活完全不同。在颱北(保安處與軍法處)四年當中,每天提心吊膽準備被叫齣去槍斃,雖是不怕死,但心裏還是有點怪怪不太舒服,復審迴來依然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心裏慢慢趨於安定,打算坐一輩子牢。開始買報紙計劃看書,開始學國語,我聽彆人念ㄅㄆㄇ,自己跟著念就會瞭,自己就這樣多少跟著講。購買附注音的國語日報來讀。背過瞭一年曆代人物,由於背景不同不易記下來,隻好再讀《中國通史》,讀《中國通史》對地理上缺乏明白,再讀《中國地理》,接著又讀《世界通史》、《經濟發展史》、《人類發展史》、《九國革命史》等書。由於《西洋經濟史》、《凱恩經濟理論》等書內有英文、代號等,不得不再學英文及成本會計等等科目。
若講到教國文,林振霆[60]跟我交往很久。硃飛[61]讀英文,我讀國文。像《古文觀止》是林振霆一篇篇認真的教,我纔翻譯寫成白話文。在古文裏麵以前是沒有翻譯的,後來我也將它翻譯。像硃自清、梁啓超、《古今文選》、我每篇都背。說到背書,有人說背〈齣師錶〉不落淚,那個人不忠,但是我背齣師錶不會流淚。我若背李密的〈陳情錶〉和林覺民的〈與妻訣彆書〉,一天背三次,三次都流淚。
例如一本本的簿記,跟硃飛一起,我從初中簿記開始,習題一題一題作,從初中到高中,都不用問人。教科書有一個平的水準,不會一下高一下低(即循序漸進),我習題一題題的作,都沒請教彆人就做到成本會計。
凡是國語日報登載的梁啓超、硃自清所寫文章我都有背誦。《古文觀止》內唐宋八大傢的古文背過後再翻譯白話文,寫瞭幾年打算帶迴印刷,如屈原「離騷」沒有參考書就翻不齣來。在安坑讀書氣氛很高。隻有飯前飯後互相說說幾句話,大傢埋頭苦乾默默看書和背詞。
這樣讀到二十年迴來,沒一樣專業。你說化學不懂也懂一點,還是說每樣認識一點,沒一樣專長,隻有種梨子是專長的。這個學問喔,實在很寬闊,學也學不完,希望看某一部份會不會比較精明。說化學還是說物理什麼科,講是每樣都會講,但是都不精。
對麵押房來瞭一位高雄縣議員巫義德[62]說,八德鄉有一男人被殺死後切成八塊。一位班長聽到後罵巫義德,巫議員心裏有一點不舒服。該班長走後躲在柱子後聽聽巫議員有沒有說什麼。巫議員說:「我們如有孩子來這裏當班長好威風哦。」班長馬上叫他齣來帶到散步場(放封處所),雙手用手銬反銬在電綫桿,用拳頭打他,同時說今天打你,你帳記起來,以後共産黨來時我給你切成八塊,可以由你再加利息。
我從裏麵(牢裏)拿多少書迴來耶!那些讀不懂的大學用書我也寄迴傢,想要迴傢後再慢慢的看。很遺憾的是,我母親把我很多書偷賣掉,當成廢紙,二十元、三十元那樣賣。我就問我母親:「我醫學的書一本要五、六百元,你怎麼把它拿去賣掉?」我母親迴答:「牆上的磚是因為拿不下來,不然我連磚頭都拿去賣。」我又問:「那妳賣的錢拿去哪?」母親說:「你大哥的兒子還沒有娶妻,你有錢怎不幫他娶?」我說:「我大哥兒子要娶妻,自己有錢不娶?我的土地全都被他佔領,我還要幫他娶?」老母說:「你就比較有能力,比較有錢。你會經營梨園他又不會。」我說:「一天到晚要去玩,也沒有個計畫。」就隻因為他什麼都不會。
用户评价
每次看到《無奈的山頂人》這個書名,我的思緒都會飄得很遠。總覺得這個名字本身就帶有一種淡淡的憂傷,又夾雜著一絲絲掙紮的意味。我尚未閱讀這本書,但它在我的腦海中已經演變成瞭一齣跌宕起伏的人生劇。我仿佛能聽到山頂上呼嘯而過的風聲,感受到刺骨的寒意,以及那些生活在那裏的,被現實壓迫著、又不得不咬牙堅持的人們的呼吸聲。他們也許是生活所迫,被推到瞭一個不情願的境地,無法輕易離開,也無法改變現狀。這種“無奈”,並非是主動選擇的清高,而是被動捲入的掙紮,是想要改變卻無力迴天的痛苦。我好奇,作者會如何描繪這群山頂人的生活細節?是日復一日的辛勞,還是偶爾閃爍的溫情?他們之間又會産生怎樣的羈絆?是互相扶持,還是彼此疏離?書中關於“山頂”的意象,在我看來,絕不僅僅是一個地理位置的描述,它更可能是一種心理上的孤立,一種精神上的藩籬,一種與主流社會隔絕的體驗。我猜測,作者可能會通過細膩的筆觸,展現他們在嚴酷環境下生存的韌性,以及內心深處對美好生活的渴望。這種反差,往往最能觸動人心。我期待著,當我打開這本書時,能被帶入那個冰冷而又充滿人情味的山頂世界,去感受那些鮮活的生命,去理解他們的“無奈”,並從中找到屬於我自己的共鳴,也許會是對生活的一種新的審視,抑或是對人性深處一種獨特的洞察。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無奈的山頂人》總是會觸動我內心深處某種莫名的情愫。我至今都尚未翻開它,但僅僅是這幾個字,就足以讓我腦海中勾勒齣無數幅畫麵。我想象著一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被高聳的山巒環繞,那裏住著一群默默無聞的靈魂。他們或許擁有著與世隔絕的寜靜,卻也承受著無法擺脫的孤獨。我好奇他們每日的生活是怎樣的,是否能在這片孤寂中找到內心的安寜,還是每當風起雲湧,內心的波瀾也會隨之翻湧?“無奈”二字,更是像一把鑰匙,打開瞭我對人性復雜性的無限遐想。這種無奈,是命運的安排,還是個人選擇的睏境?是環境的壓迫,還是內心的掙紮?它是否摻雜著不甘、失落,又或是某種隱忍的堅韌?我猜想,作者筆下的山頂人,或許並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想象的那些超脫塵俗的隱士,他們可能有著與我們一樣的喜怒哀樂,有著對生活最樸素的渴求,但卻因為某些無法抗拒的原因,被置於一個“山頂”的位置,體驗著一種獨特的“無奈”。這種“無奈”可能體現在他們麵對自然規律時的渺小,體現在他們與外界隔絕帶來的信息差,也可能體現在他們對某種改變的期盼與現實的落差之中。我期待著,當我真正閱讀這本書時,能夠深入到那些平凡又深刻的生命故事裏,去體會那份沉甸甸的“無奈”,並從中獲得某種啓示,關於堅持,關於接納,亦或是關於一種更深層次的理解。
评分《無奈的山頂人》這個書名,總是像一首低沉的歌,在我心中迴響。我還沒翻開它,但它已經在我腦海裏構建瞭一個遙遠而神秘的世界。我能想象,那裏有陡峭的山崖,有稀薄的空氣,還有一群被生活推到極緻的人們。他們也許終日與孤寂為伴,與艱辛為伍,他們的世界,被無形的“無奈”所籠罩。這種“無奈”,對我來說,是個極具吸引力的詞匯。它不同於絕望,又比普通的睏境更添一層沉重。我猜測,作者所描繪的“山頂人”,並非是那種主動選擇隱居的智者,他們更像是被命運捉弄,被環境所迫,隻能在這高處默默承受。他們的生活,可能充滿瞭不為人知的艱辛,充滿瞭對外界的渴望,又充滿瞭對現實的無可奈何。我好奇,他們是如何在這種“無奈”中保持著生存的意誌?他們之間又會産生怎樣的人際關係?是互相依偎取暖,還是各自為營?這本書,對我而言,不隻是一個故事,更像是一次對人性和生存狀態的探索。我期待著,當我真正閱讀它的時候,能夠感受到那些鮮活的生命,能夠理解他們行為背後的邏輯,並從中汲取力量,也許是對人生睏境的一種新的理解,抑或是對平凡生活一種更深刻的感悟。
评分《無奈的山頂人》這個書名,不知為何,總給我一種強烈的畫麵感。雖然我還未曾翻閱這本書,但它在我腦海中已經勾勒齣瞭一幅幅生動且略帶傷感的畫麵。我想象著,在一個被群山環抱的偏僻之地,生活著一群與世隔絕的人們。他們或許是世代居住於此,又或許是因為某種原因被留在瞭那裏,成為瞭這個“山頂”上的居民。他們的生活,無疑是艱辛的,是與自然的嚴酷抗爭的過程。然而,最讓我感到好奇的,是“無奈”二字所蘊含的深意。這種無奈,是麵對命運的無力感?是渴望改變卻束手無策的睏境?抑或是,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被動接受現實的妥協?我猜想,作者筆下的山頂人,並非是超然物外的智者,他們同樣有著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有著對生活的熱情與期盼,隻是,他們所處的環境,讓他們無法輕易實現這些願望。他們的生活,可能充滿瞭不被理解的犧牲,充滿瞭不為人知的艱辛,也充滿瞭對外界的無限憧憬,而這種憧憬,又被現實的“無奈”一次次澆滅。我非常期待,作者會如何用文字來描繪他們的日常,他們的情感,以及他們內心深處那些不為人知的掙紮與渴望。我希望,通過閱讀這本書,能夠更深刻地理解“無奈”的含義,並從中看到人性的堅韌與脆弱,找到一種麵對生活睏境的勇氣與智慧。
评分“無奈的山頂人”,光是這個書名,就足以讓我産生無窮的聯想。雖然我還沒有正式開啓這本書的閱讀之旅,但它已經在我的腦海中編織瞭一個個跌宕起伏的故事。我似乎能感受到,在那些高聳入雲的山巒之上,生活著一群被現實束縛的靈魂。他們的日子,可能充滿瞭與自然搏鬥的艱辛,也充滿瞭被世人遺忘的孤獨。但真正吸引我的,是“無奈”二字所傳遞齣的復雜情感。這是一種怎樣的無奈?是環境的限製,還是人心的束縛?是無法改變的命運,還是被動的選擇?我揣測,作者所描繪的山頂人,並非是主動追求清靜與超脫的隱士,他們可能有著與我們一樣的塵世願望,卻因為各種客觀或主觀的原因,被安置在瞭這個“山頂”的位置,承受著與渴望之間的巨大落差。他們的生活,或許充滿瞭不被理解的辛酸,充滿瞭對改變的期盼,卻又被現實的“無奈”一次次地扼殺。我迫切地想要知道,作者會如何刻畫這些人物的內心世界?他們是如何在這種“無奈”中尋找生存的意義,又會在怎樣的時刻爆發內心的情感?我期待著,通過這本書,能夠深入到那些平凡而又偉大的生命故事中,去體會那份深沉的“無奈”,並從中獲得某種觸動,也許是對生活意義的重新思考,又或是對人性更深層次的洞察。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