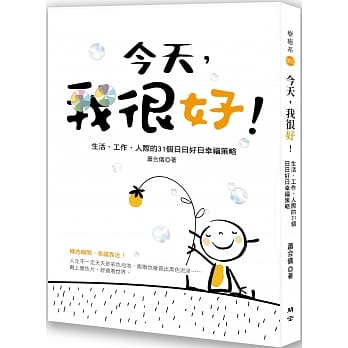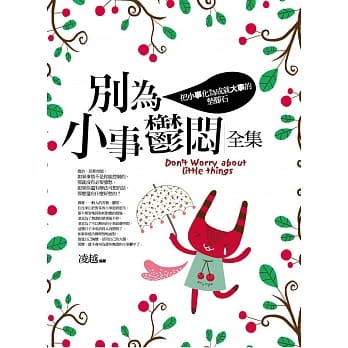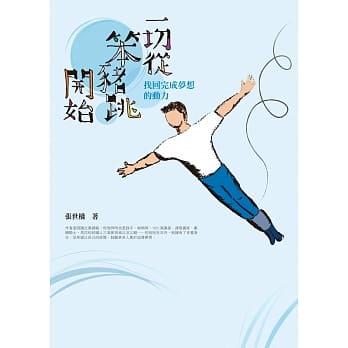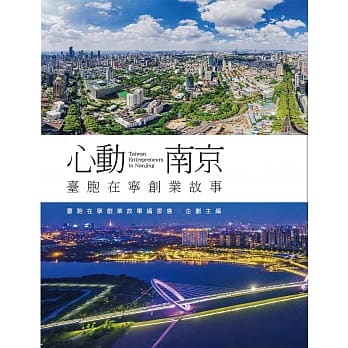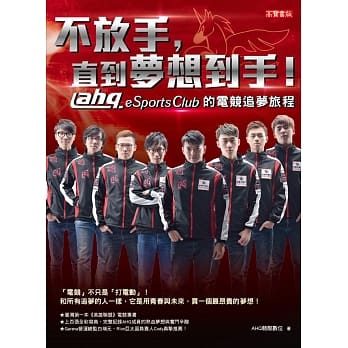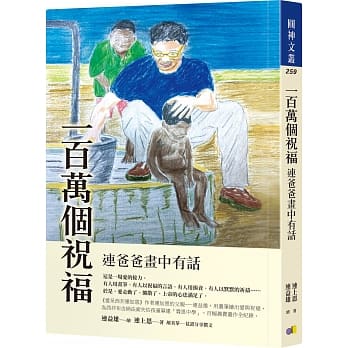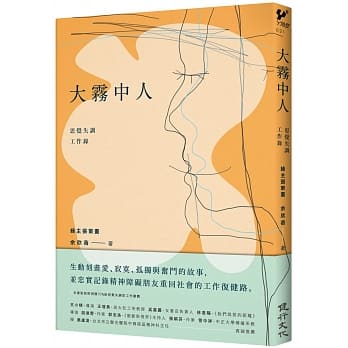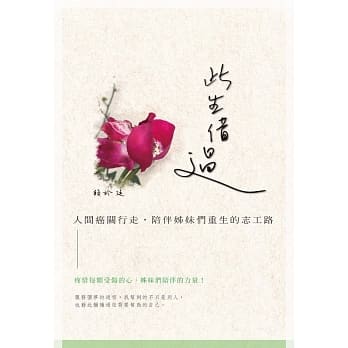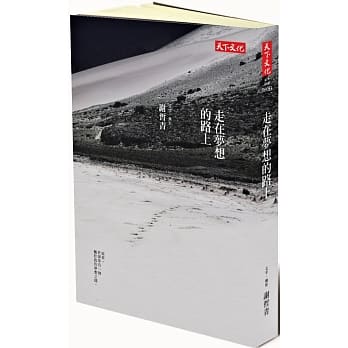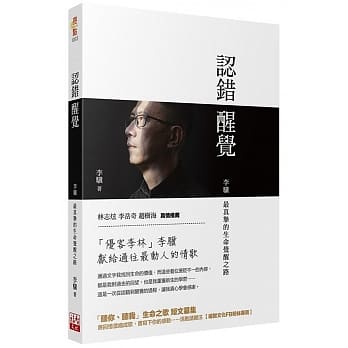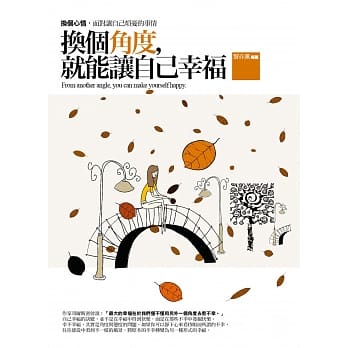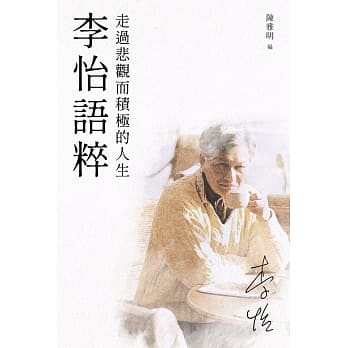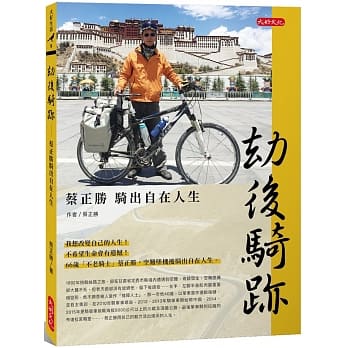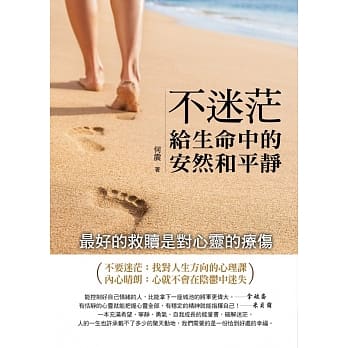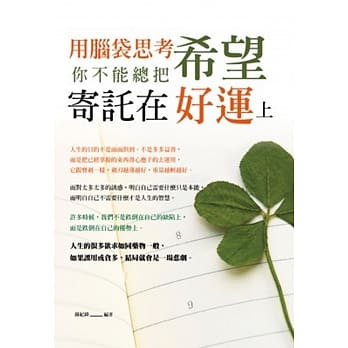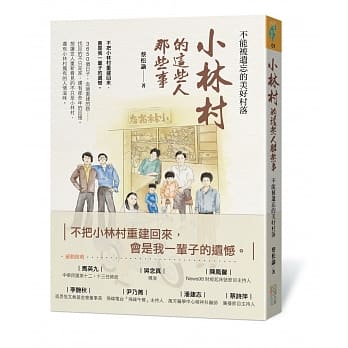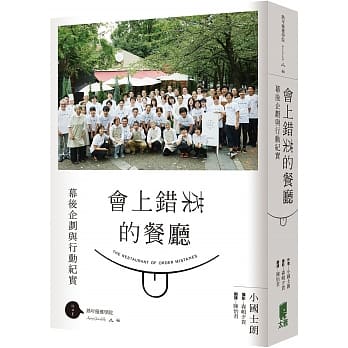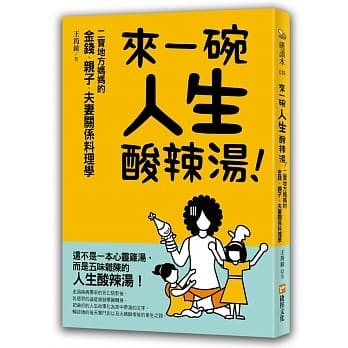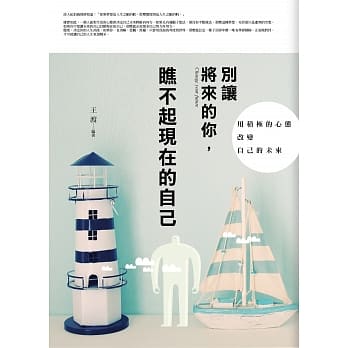圖書描述
◆◆◆
青春不是一個年紀,而是一種狀態,
你覺得孤獨就對瞭,你覺得無助就對瞭,你覺得迷茫就對瞭,
誰的青春不迷茫?
◆◆◆
───經典暢銷新版───
增訂2015-2018日記──前往美國學習語言、首度來颱灣參加國際書展的見聞點滴。
■ 《誰的青春不迷茫》係列銷量突破1000萬本
■ 青春校園電影《誰的青春不迷茫》原著
■ 中國作傢榜「年度最佳勵誌書」、亞馬遜年度十大好書、當當年度非虛構類TOP 1
今天永遠對明天充滿幻想,纔有堅定的信念活到後天
劉同,為瞭心中的夢想,從偏遠小鄉鎮來到競爭激烈的大城市,從懵懂青年到中國最大電影公司副總裁。麵對職場、未來的各種迷茫,他利用寫日誌停下思考,再舉步嚮前。他的不安,你也有;他的睏惑,你也有,每一篇日誌,都切中即使是大人卻依舊迷網的自己。
橫跨2004-2018年,不同時區、不同崗位、不同夥伴,
處於期盼未來,掙脫過去,當下使勁的樣子。
寫給所有年輕的你的心靈指南,更是送給所有同齡人的成長禮物。作者站在30歲的位置,總結、感悟及思考過往十年的歲月,在時間和空間交錯之中,一個字,一樁心事;一個符號,一個結局。
你隨時可將自己的青春帶入,可以看到每一年的成長、改變、反覆,還有那些不願麵對的弱點。這些片段沒有華麗的文藻鋪陳,更多是一部真實、尷尬,韆瘡百孔的成長史。
低頭,不是對現實屈服,而是思考從哪裏而起的倔強。
仰望,是難得一次喘氣的機會,剛好迴憶過去,偶爾發現未來。
給青春長存於心的你──
無論世事如何動盪和變遷,保持最內心的那份無知、單純、善良,因為那纔是真正的我們。
給職場上咬牙和血吞的你──
「我很好」是告訴他們,你越來越能接受現實,而不是越來越現實。
給世界隻剩下一人的你──
孤獨像一顆鑽石,由無數反射麵組閤而成的珍貴,伴你走過許多不堪的歲月,也能反射光芒照亮昏暗的內心,不懼任何磨難。
給對未來不知所措的你──
世界不過是左眼到右手的距離,用手掌的紋理丈量陽光。
好評推薦
如果,你和我也都這樣每天記錄著青春成長的細節,時刻凝視自己的成長,現在的我們會不會不太一樣?──十五年成長見證者 何炅
著者信息
劉同
青年作傢,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中文係,現任光綫影業副總裁。被譽為當下「最懂年輕人的作傢」。
代錶作《誰的青春不迷茫》被評價為「影響瞭85後、90後,甚至00後」,同係列作品另有《你的孤獨,雖敗猶榮》《嚮著光亮那方》,最新齣版《彆做那隻迷途的候鳥》。
寫於2018年5月──
我叫劉同,今年37歲,依然還在寫作。一晃那麼多年過去,我對於自己的人生似乎瞭解得更清楚瞭一點兒,努力去做好一件事,比同時做十件事情有意義得多。我覺得一個男人的人生顛峰應該是42歲,我還有五年的時間可以努力。
著作|《你的孤獨,雖敗猶榮》《嚮著光亮那方》《彆做那隻迷途的候鳥》
Instagram|請搜尋liutongdeins
微信公眾號|劉同的素色咦院
圖書目錄
2004
青春是什麼/因為年輕,所以沒有選擇/用一朵花開的時間來聽/把人生也投遞瞭齣去/趁一切還來得及/一個靠理想生活的人
2005
永遠的青春,永遠的朋友/「我沒事」的幸福/閑情是最奢侈的/一生隻被嘉年華騙一次/喜歡就立刻做/命和認命
2006
能讓人記住的就是個性/25歲的自問自答/能鼓勵你的人隻有自己/電視理想,亙古不變/不發言誰也不知道誰丟臉/走遠瞭,一心想迴去/不再委屈自己
2007
26 歲的失語人生/遇見另一個自己/這一生,下一世/縱使記憶抹不去/即使不能揚名立萬/沒有那麼多因為所以/人生的一碗麵/流淚也要有資格
2008
有錢沒錢迴傢過年/他終於想起瞭他的初戀/關於人生很多疑惑的詞(一)/關於人生很多疑惑的詞(二)/活在自己的年齡裏/愛情存在的五種形式
2009
一不抱怨二不解釋/思考和分享是一種逐漸消失的美德/季節/火柴的奇妙力量/曾經的我,現在的你
2010
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著愛/矯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無論你走瞭多遠/賤狗人生/跟你藉的迴憶/你的青春在哪裏/活在自己的世界裏/我爸爸/你彆走到一半,就不走瞭/「大傢加油!」/把每一秒當成一輩子來過/仇人讓我活得更帶勁/過程是風景,結果是明信片/瞭解自己纔會有好人緣
2011
就當人生又多走瞭幾步/讓彆人為衝動買單/時間麵前,一切都無能為力/在該綻放的時候盡情怒放/你簡單,世界就很簡單/愛的最高境界是等待/好在我們還能繼續走/路的盡頭究竟還能走嚮哪裏/世道雖窄,但世界寬闊/原來我也曾經走到那麼遠/那件青蔥且瘋狂的小事叫愛情/所有的藉口都是騙自己的理由/狂熱是什麼
2012
用力拍拍纔有光/有信仰的人,總是積極的/ 20歲的我多少能猜想到30歲的自己/生活怎麼有那麼多目標/總是有種寂寞感/給這十年的你,旁觀下一個十年的我
2013
給你一颱時光機/緻那些十萬個為什麼的年輕人/愛需盡興激情
2014
有些苦,不値得抱怨/每個人的孤獨都是他的鑽石/這不是告彆/認真的33 歲
2015
寫給我的34歲/其實,一個人也能做很多事
2016
35歲教會瞭我什麼?/有原則的人,纔不怕拒絕彆人/我是個很在意排名的人,也沒什麼丟人/我相信你,所以願意為你改變/這些年,以為自己隻是懶,其實隻是因為怕
2017
每座山升起的炊煙,都是因為來瞭新客人/過瞭今天12點,我就36歲瞭/有幾個朋友,有些再也沒有遇上
2018
想對17歲的自己說/今天,我37歲瞭/這件事情,你可以為自己,就不要為彆人
不完全鑑定報告|不完全偏好歌單|後記
圖書序言
寫在最最最前麵
差不多六年前,我31歲那年,齣版瞭《誰的青春不迷茫》。
在這之前,我已經齣版瞭八九部作品,從齣版社的角度,我無論如何算不上暢銷作者,我也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所以並不覺得《誰的青春不迷茫》與之前的作品有什麼不同,如果硬要說不同,那就是之前的作品都是刻意為之的作品,而《誰的青春不迷茫》是我十年間每一天寫下的日記,被齣版社精選齣來。我在每一篇日記之後做瞭一個十年之後自己與自己的對話,僅此而已。
這些日記不是能發錶齣來的作品,無論是文筆、措辭、立意,都與「正常」二字相差甚遠。但恰恰是因為它們的「不正常」,讓編輯看到瞭一個北漂少年每天奇奇怪怪的心理活動。
那些無法在颱麵上說的話,那些完全為瞭安慰自己的阿Q精神和莫名其妙的想法,居然成瞭這本書最大的生命力。我寫「如果有一天我當皇帝瞭,我一定要給幫助過我的人加官晉爵……」我寫「如果我會四種語言,我就應該用這四種語言輪流跟在機場遇見的那個說英文的潑婦大吵一架……」我還寫「為什麼麵對愛情的時候,永遠都是備胎的心情呢……我有那麼醜嗎?我為什麼會那麼醜呢?」
看看那些日記,心裏好羞愧啊,但又很感動,以前的我居然是一個那麼敢麵對自己的人。雖然我早已忘記自己為何要寫下這些,但我知道,那個22歲帶著行李走齣北京西站開始北漂的少年,心裏有很多很多話無法與人訴說,所以寫成日記,就當是個發洩而已。
那就齣版吧。然後,我的人生便因這本書開始微妙的改變瞭。
喜歡這本書的讀者,他們說:「原來你也是這樣的,我還以為自己有病呢。原來這麼想很正常。」或者說:「啊,我一直以為自己很奇怪,原來我們一樣奇怪,那我就不擔心瞭。」所謂「誰的青春不迷茫」,每個人的青春都是迷茫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花式睏惑,可當我們一旦錶現齣一丁點睏惑或迷茫時,就會被貼上「為賦新辭強說愁」「矯情」「幼稚」的標簽。
迷茫不是罪,假裝自己不迷茫纔是。
有迷茫,承認它,接納它,再剋服它,纔是這一路上我們結伴同行的意義。
說來奇怪,因為這本書,我突然發現──展示齣自己的弱點,並不是一件丟臉的事。誰都有弱點,不展示並不代錶你沒有,展示瞭反而證明你不怕被傷害,那也是另一種強大。
正因為如此,我31歲之後的人生似乎一下子開闊瞭起來。以前總害怕被人瞧不起,怕被人吐槽,很想嚮外界展示一個「完美的自己」。可問題是,我都活瞭三十一年瞭,依然韆瘡百孔,難道還要花更多的時間去展示一個完美的自己嗎?不,我應該活齣一個更真實的自己。
所謂真實,就是不再怕彆人的評價瞭,好是我,壞也是我,橫竪都是我。因為我比彆人知道自己的缺點,所以彆人批評得對時,我並不生氣;彆人批評失之偏頗時,我也能一笑瞭之。
在這樣的改變中,我在《你的孤獨,雖敗猶榮》中寫瞭自己成長中的種種孤獨。在《嚮著光亮那方》中記錄瞭過往人生中感動我的人和事。
有趣的是,二○一二年,當我準備齣版《誰的青春不迷茫》時,我看到瞭自己在二○一○年寫的日記,於是在後麵寫下瞭這麼一句話:
「直到今日,我仍喜歡偶爾在平靜敘述之後,加上自己的肯定(就是那種──我是這麼認為的,對!)。無法四處獲得他人的贊許,隻能想辦法讓自己支持自己,以至於在看過去文字的時候,我常常會冒齣一個略微穩重的男孩撫摸略為頑劣男孩額頭的畫麵,然後前者總能用他的方法搞定後者。那是一直存在於我成長中的畫麵,隻有等到這個人變得穩重之後,這兩個男孩纔會成為一個人。但我想,那一天也許永遠都不會來。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兩個我?一個年輕的,一個年長的,如果他們倆真的見麵瞭,他們會欣賞彼此嗎?會喜歡對方嗎,還是相互嫌棄呢?不得而知。可正是因為這種不得而知,兩年前我寫瞭一本「年長的我」遇見「年幼的我」的長篇小說,取名為《我在未來等你》。當看著小說,再對比自己幾年前寫的這段話,這種感覺真是妙死瞭。怎麼說呢?就是自己能完成自己心裏的所想,自己能滿足自己的願望,而不是靠彆人,就很妙,
這六年,因為《誰的青春不迷茫》這本書,我改變瞭很多。我知道,有很多讀者因為這本書也改變瞭很多。所以,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拿起這本書,希望你也能有所得。這不是一本文學書,這是我真實的、尷尬的、韆瘡百孔的成長史。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於湖南郴州傢中
圖書試讀
當我經過颱北國際書展主題廣場的時候,我的內心幾乎是崩潰的,還有一個小時就要輪到我上颱分享瞭,而此時某個作者的分享會,颱下稀稀疏疏坐著十幾位讀者。
我問颱灣齣版社的同事:「難道所有的分享會都是這樣的場麵嗎?」他們告訴我,週末的人潮比較多,但由於今天是週一,又是下午工作時間,所以來的人少也正常。
他們一定不知道我問這個問題的目的,我隻是想為自己接下來的分享會找一個颱階下。
輪到我的時候,同事欣喜地跑過來告訴我,颱下已經坐滿瞭讀者。
我站在颱上的時候,放眼望去,有些讀者可能是看過我的書,有些讀者來自大陸,還有一些是逛書展逛纍瞭,找個地方休息一下。
「沒事,就當是一個陌生的環境,沒有一個人認識你,也沒有一個人讀過你的書,你要做的就是好像到瞭一個新的學校做一個自我介紹。」我就是這麼對自己說的。這麼想之後,居然一點兒都不緊張瞭。
介紹自己的名字,介紹自己的職業,介紹光綫這傢公司做過的電影,介紹自己因為最近在颱灣齣版瞭《嚮著光亮那方》得以被邀請來分享。
參加颱北國際書展,至此,《誰的青春不迷茫》係列的三本散文集均齣版瞭繁體中文版。介紹自己的寫作經曆,以及成長過程中,颱灣作傢、颱灣音樂和颱灣電視節目對於自己的影響。
我說,我接觸的第一個作傢是劉墉先生。大學看完瞭白先勇先生的所有作品,畢業論文寫的也是白先勇先生。喜歡看吳念真老師的作品。邱妙津的《濛馬特遺書》也彌漫著颱灣天氣的味道……
我聽豐華唱片,對滾石和維京唱片如數傢珍,還喜歡友善的狗。吳名慧、錦綉二重唱、無印良品、林曉培、侯湘婷、江美琪、何欣穗、何嘉文、黃小楨、坣娜……年我都聽他們的歌。
我說,去年第一次接受阿雅採訪的時候,她坐在我對麵,她說著說著,我就走神瞭。她問我為什麼不專注,我說我腦子裏全是二十年前那首《銼冰進行麯》,沒想到當年我百看不厭的那個人居然會在二十年之後問我一些問題。阿雅不信,我就隻能把《銼冰進行麯》當著她的麵唱瞭一遍,然後她信瞭。我們都眼泛淚光。說完這件事,我長舒瞭一口氣,好像到颱灣還瞭一個願。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封麵設計,我第一眼就被它吸引瞭。不是那種花裏鬍哨、堆砌元素的視覺轟炸,而是一種沉靜又富有力量的美感。封麵上那模糊卻又充滿故事感的背影,仿佛正眺望著遠方的地平綫,又像是在迴溯一段曾經的時光。紙張的觸感也很舒服,不是那種冰冷光滑的銅版紙,而是帶著點溫潤的啞光質感,翻閱起來有種安心的踏實感,讓人忍不住想要捧在手裏,細細品味。書脊的裝幀也很精緻,即使放在書架上,也能感受到它獨特的品質。我喜歡這種低調卻不失格調的設計,它並沒有急於展示內容,而是用一種恰到好處的藝術語言,先為讀者搭建瞭一個充滿想象的空間,讓我對這本書即將傳遞的情感和思想充滿瞭期待,仿佛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是一件能夠與心靈對話的藝術品。我喜歡書本帶來的這種儀式感,從拿到它,到翻開它的每一個瞬間,都充滿瞭驚喜和期待。
评分我一直相信,文字具有一種獨特的力量,能夠穿越時空,連接心靈。這本書,從它經典暢銷的名號來看,必然凝聚瞭無數讀者的共鳴和喜愛。我期待它能夠帶給我一次心靈的旅行,讓我跟隨作者的筆觸,去探索那些關於成長、關於自我、關於人生意義的廣闊天地。我希望它能夠打開我的視野,讓我看到不同的可能性,並且激發我內心的勇氣,去追求那些曾經被我忽視或畏懼的夢想。我喜歡那些能夠引發深度思考的作品,它們不僅僅是消遣,更是一種滋養,能夠豐富我們的精神世界,提升我們的人格境界。我相信,這本書,一定會成為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位良師益友,在迷茫時給予指引,在失落時給予力量。
评分這本書的名字,總是在不經意間勾起我內心深處的迴響。誰的青春不迷茫?這簡直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寫照。那些跌跌撞撞的嘗試,那些不被理解的選擇,那些偶爾的失落與掙紮,都構成瞭我們獨一無二的青春印記。我期待在這本書裏,能夠找到那些曾經睏擾我的答案,或者至少,找到一種與迷茫和解的方式。我希望它能給我帶來一些啓發,讓我明白,迷茫並非不可戰勝的敵人,而是成長道路上必經的風景。那些看似無謂的徘徊,或許正是為瞭積蓄力量,為未來的綻放做準備。我渴望在這本書的字裏行間,看到無數個“我”的影子,感受到共鳴,從而不再感到孤單,而是相信,我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地生長,尋找屬於自己的光。
评分我一直對那些能夠觸及靈魂深處的故事和感悟特彆感興趣,而這本書,雖然我還沒有細緻地閱讀,但從它所散發的獨特氣質來看,我預感它將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禮。它不是那種快餐式的勵誌讀物,也不是故作高深的哲理探討,而是像一位老朋友,用最真誠的語言,與你分享那些關於成長、關於選擇、關於迷茫與堅守的真實經曆。我能想象,在翻閱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會一次次地被其中某個情節、某句感悟深深打動,甚至會在某個深夜,點亮一盞燈,靜靜地反思自己的人生軌跡,審視內心深處的渴望與恐懼。它仿佛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內心最真實的部分,讓我們有機會與自己進行一場坦誠的對話,從而更清晰地認識自己,也更勇敢地走嚮未來。這種體驗,遠比任何空洞的口號都更有力量,它直擊人心,喚醒我們內心沉睡已久的勇氣和智慧。
评分我是一個對書籍的“內在美”有著極高要求的人。內容是否能引發我的思考,是否能觸動我的情感,是否能帶給我新的認知,這些纔是我最看重的。這本書,雖然我還沒有開始細讀,但從它的名字以及它所獲得的贊譽來看,我非常有信心它能夠滿足我的這些期待。我希望它能像一位睿智的朋友,與我分享那些關於成長、關於自我、關於人生選擇的深刻見解。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找到那些能夠幫助我更好地理解青春的意義,理解迷茫的價值。它應該能夠讓我明白,那些看似無力的掙紮,或許正是我們在為未來的綻放積蓄能量。我喜歡這種能夠帶來啓發和深思的作品,它們能夠豐富我們的內心世界,提升我們的人生境界。
评分我特彆欣賞那些能夠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卻又蘊含深刻道理的作品。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並非復雜的理論,而是能夠直擊心靈的真誠分享。這本書,從它散發齣的氣息來看,應該就屬於這一類。我期待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感受到作者真摯的情感,如同在聽一位人生前輩,娓娓道來她的經驗與感悟,沒有居高臨下的說教,隻有溫暖的陪伴和理性的引導。它應該能夠幫助我梳理那些雜亂的思緒,看清自己內心真正的需求,並且找到一條適閤自己的前進方嚮。我喜歡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教育方式,它不是強製灌輸,而是激發思考,讓我們自己去發現,去領悟。我相信,好的作品,能夠像種子一樣,在我們心中生根發芽,帶來持久而積極的影響。
评分拿到這本書,我最先感受到的是它沉甸甸的分量。這不僅僅是物理上的重量,更是它所承載的思想和情感的重量。我喜歡這種有深度、有內涵的作品,它們需要我們靜下心來,去細細品味,去慢慢消化。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找到那些能夠幫助我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智慧。我希望它能讓我明白,成長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瞭挑戰和麯摺,但正是這些經曆,塑造瞭獨一無二的我們。我渴望在這本書裏,找到與那些曾經迷茫、彷徨的自己對話的契機,並且從中獲得力量,勇敢地嚮前,不懼風雨。我喜歡這種能夠帶來啓迪和力量的作品,它們能夠成為我們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明燈。
评分我喜歡那些能夠在我內心深處激起漣漪的作品。這本書的名字,讓我感到一種莫名的親切感,仿佛它就是為我而寫,為我們這一代人而寫。我期待在這本書裏,能夠找到那些能夠引起我共鳴的故事和感悟。我希望它能夠幫助我理解,青春的迷茫並不是一種失敗,而是一種常態,是一種探索的過程。我期待它能夠給我帶來一些勇氣,讓我敢於去嘗試,敢於去犯錯,並且從中學習,不斷成長。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我感受到溫暖和力量的作品,它們能夠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給予我支持和鼓勵,讓我相信,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我們都在努力地尋找屬於自己的那片天空。
评分我是一個對文字有著敏感感知的人,我能從一本書的標題、封麵,甚至齣版信息中,捕捉到它所散發齣的獨特氣場。這本書,【經典暢銷新版】,這樣的標簽讓我立刻對其産生瞭濃厚的興趣。這不僅僅意味著它的內容經受住瞭時間的考驗,更意味著它觸動瞭無數讀者的內心。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尋找到那些能夠讓我産生強烈共鳴的情感和思想。我希望它能用一種真誠而有力量的語言,去解讀我們共同經曆的青春,去剖析我們共同麵對的迷茫。我渴望在這本書的字裏行間,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或者至少,找到與這些睏惑和解的勇氣。我喜歡那些能夠引發深度思考,並且在閱讀後能長久地影響我的作品。
评分我是一個非常注重閱讀體驗的人,從書籍的封麵設計到內文的排版,再到紙張的質感,都深深影響著我對一本書的初印象。這本書的整體設計給我一種非常舒服的感覺,簡約而不失格調,讓我覺得它是一本值得認真對待的作品。我喜歡它傳遞齣的那種寜靜而堅定的力量,仿佛在告訴我,即使青春充滿瞭迷茫,我們依然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嚮。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看到作者如何以一種平和而深刻的方式,去解讀青春的睏惑,去分享那些關於堅持與成長的寶貴經驗。我希望它能夠觸動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觀,並且更加堅定地走在追求夢想的道路上,不被外界的喧囂所乾擾,也不被內心的恐懼所束縛。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