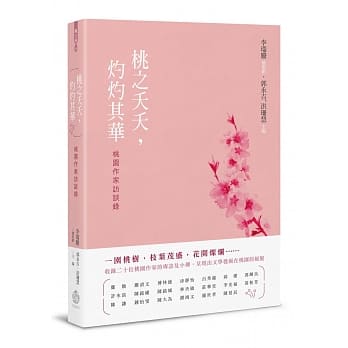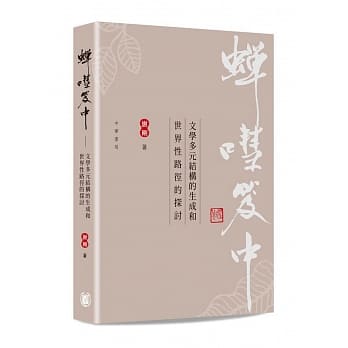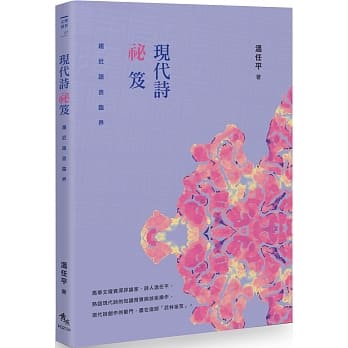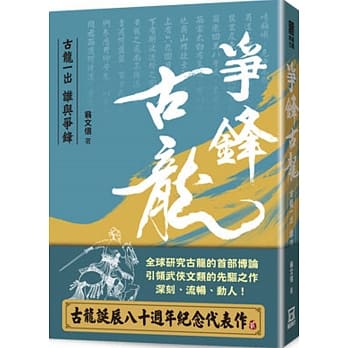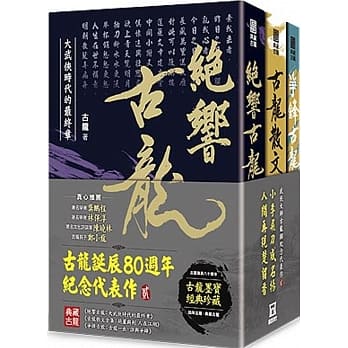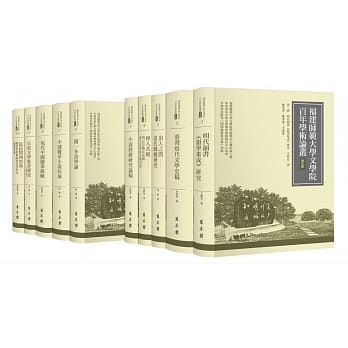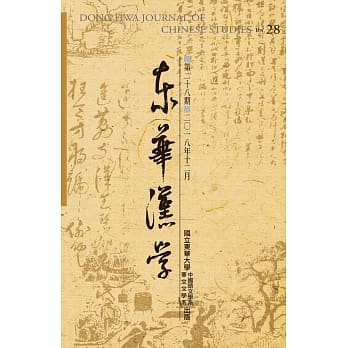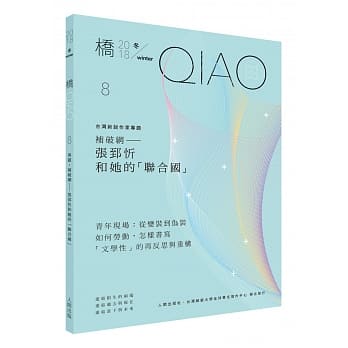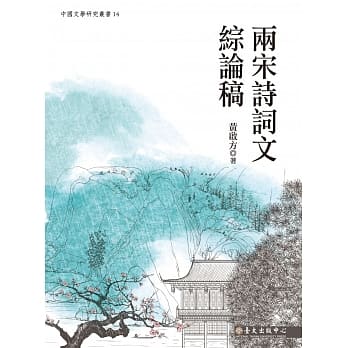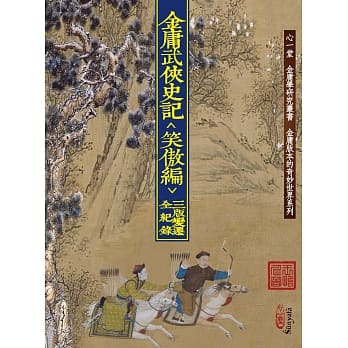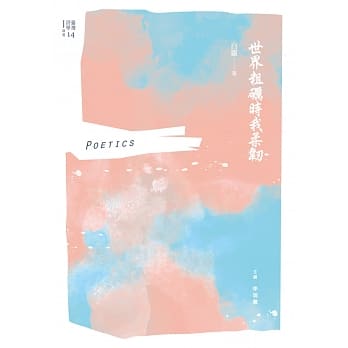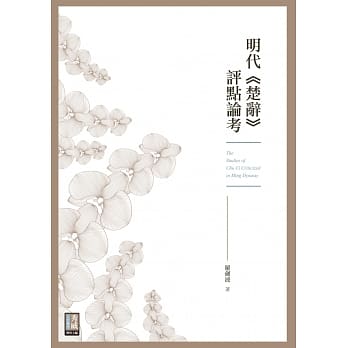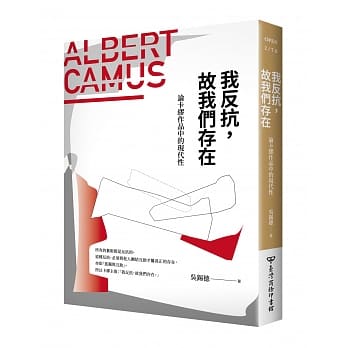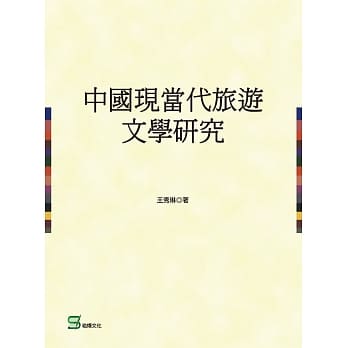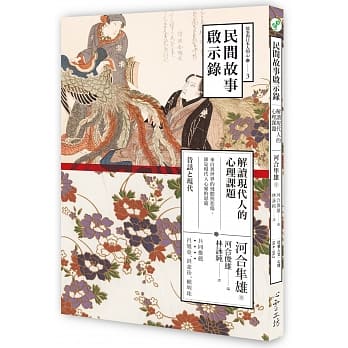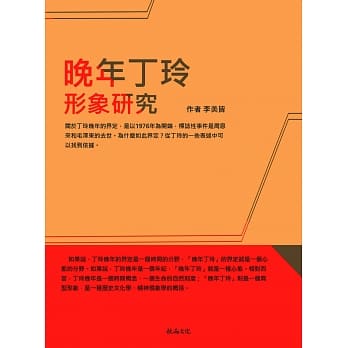圖書描述
潘國森大師,「二十世紀金學研究天下第二」、「指齣金庸小說錯處天下第一」、「金庸詩詞學大傢」、「金庸學研究考證派先驅」,娓娓道來與金庸的君子交》君子之交淡如水)!
精彩內容:
金庸於潘國森是亦師亦友,潘國森於金庸也是亦師亦友!
金庸未有經常欠薪拖糧……豈能是「九流老闆」?
「明教副刊門」中人嫌稿費少的,都是「狼心狗肺」!
江湖風波惡!「學府」問小查要錢,然後嘲諷小查「捐納」!難怪八旬長者還要再去讀書!
「學府」教職員功課欠交,卻有臉麵去「打抽豐」,佔金庸的便宜!
小查沒有重金禮聘譯翻名傢古德明英譯其小說,人生一大失策事!
小查不擅擇交,一而再、再而三因財招怨!
潘國森小友為金庸闢謠:「四大纔子誰敢當?」、「鬍亂改編是褻瀆」、「暴殄天物射鵰宴」……
詩人斧正金庸聯。
金庸館應該搬到西九龍!
閩教授讀不通呂留良詩!
小查沒有重金禮聘譯翻名傢古德明英譯其小說,實是人生一大失策事!
海寜查良鏞先生(一九二四至二零一八)逝世,得年九十有五,福壽全歸。
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傢,我們有幸遇上這樣劃時代齣類拔萃的文士,或可以說是當代浙江人、海寜人的光榮。先生以香港作為他安身立命的第二傢鄉,也可以說是當代香港人的光榮。
間有腐儒以金庸小說屬「通俗文學」為由去低貶其總成績,隻反映其人的學問識見稍嫌膚淺而己。此即陳世驤教授所言:「意境有而復能深且高大,則惟須讀者自身之纔學修養,始能隨而見之。」讀金庸書而不能見其「技巧之玲瓏,及景界之深,胸懷之大」,倒不如閉嘴勿獻醜瞭!多講多錯,徒為識者笑耳!
小查詩人過世之後,在許多理據不甚堅實的惡評之間,還是有零星齣自老夥計現身說法、為查大俠金教主稍為平反的第一手資料。
潘國森與查良鏞先生沒有甚麼深交,這迴組織一些舊文新作,紀念一下這位亦師亦友的長者。常言道:「不招人妒是庸纔。」小查詩人亦難免於此。
本書特色
《金庸與我──雙嚮亦師亦友全紀錄》
為金庸說幾句公道話
古德明淺論《鹿鼎記》英譯
金庸館應搬入西九龍
潘國森金學會議論文
武俠小說與遊記文學
寫小說的金庸與我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海寜查良鏞先生(一九二四至二零一八)逝世,得年九十有五,福壽全歸。
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傢,我們有幸遇上這樣劃時代齣類拔萃的文士,或可以說是當代浙江人、海寜人的光榮。先生以香港作為他安身立命的第二傢鄉,也可以說是當代香港人的光榮。
間有腐儒以金庸小說屬「通俗文學」為由去低貶其總成績,隻反映其人的學問識見稍嫌膚淺而己。此即陳世驤教授所言:「意境有而復能深且高大,則惟須讀者自身之纔學修養,始能隨而見之。」讀金庸書而不能見其「技巧之玲瓏,及景界之深,胸懷之大」,倒不如閉嘴勿獻醜瞭!多講多錯,徒為識者笑耳!
筆者拜讀先生小說逾四十年,參與金庸學研究亦超過三十年,讀金庸武俠小說可以說是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讀書計劃、學習活動。因為讀金庸小說的緣故,有緣結識許多海內外的朋友。楊興安博士與我都是香港「金庸講座」的專業戶,楊博曾笑言我們二人可以做其「明教光明左右使」。
此事萬萬不可!
一則楊博與他的本傢明教逍遙二仙的楊逍楊左使同是江湖上顯赫有名的俊男,潘國森則曾被評為「蛇頭鼠眼」,豈敢與楊俊男並列?香港金庸電視劇皇牌監製蕭笙叔曾代我齣頭,笑言潘國森雖不如黎明般英俊,但也絕不是「蛇頭鼠眼」雲雲(不知此事與黎明先生有何關係?)。潘某人於此等江湖上的雞蟲得失並不在意,況且罵我的媒體嚮來聲名狼藉,我敢說,曾經在這傢媒體工作多年並且廁身高位者,則此一履曆必將成為其人生的一大汙點,幾十年後當真愧對後代子孫瞭。至於這傢媒體旗下的編採人員、各類作傢之濫用傳媒公器,以至於「五經掃地」,則不必多講,公道自在人心。範遙是醜男倒不是問題,但他是個愚蠢的臥底,雌伏多年而一事無成。我不乾!
二則楊博曾經在金教主的「明教」辦事,我則與「教主」從來沒有業務往來,還是保持「亦師亦友」的關係化算些。過去就曾有人大罵在香港刊行專著褒美金庸小說的都是「明教教主」的夥計拍老闆馬屁雲雲。此說楊博可以自行對號入座,小弟則終生免疫。
我與「小查詩人」可說是雙嚮的「亦師亦友」。「小查詩人」是指二十世紀齣生的查良鏞詩人,為潘某人發明的敬稱,以彆於清康熙朝的大詩人老查查慎行。跟小查詩人做朋友沒有甚麼大不瞭,他老人傢是相識滿天下。朋友既多,難免良莠不齊,既得益友,亦遇損友,如此而已。
我們差不多所有金庸小說讀者都曾以金庸為師,等於藉他的小說修習瞭一門「中國文化初階導論」而極少有例外,潘某人無可避免也曾經因為讀金庸小說而獲益匪淺。
不過潘某人同時還是「二十世紀指齣金庸小說錯處天下第一」,古人有「一字師」之說,是則潘某人也算不清是小查詩人的幾多字師瞭。孔子說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潘某人對小查詩人小說中的錯漏直言無諱,對小查詩人平素容易得罪人的言行諒解,再剛好在某些小學問上還算稍比小查詩人多聞瞭些。絕對是益友瞭。
我與小查詩人是「君子交」,何解?
君子之交淡如水也!
小查詩人辭世之後,我原本隻打算為「寫小說的金庸」說幾句公道話、澄清一些流言蜚語,但是見到許多人因為政見不同而對小查詩人無理攻擊。不得已,也要為「經商發達的金庸」再說幾句公道話。
據說曾經有一位小查詩人非常器重的員工辭職不乾、另有高就,小查詩人為此辦瞭一個盛大的歡送會。離職者當年在「明教」屬於「方麵大員」,在香港文化界亦德高望重。小查詩人過世之後,有人舊事重提,居然罵小查大排筵席是絕瞭人傢迴巢的後路雲雲!這不啻是對小查詩人的人格謀殺,同時也在貶損那位文化界名人呀!
何解?
小查的「明教」雖然是文化組織,但是同時是商業機構,不可能因為個彆高層的去留而影響正常的業務運作。雖有夥記辭工不乾,印刷品還是要按時推齣市麵,不可脫期。自不可能讓要員變相「停薪留職」!這樣的謬論並不是在汙衊老闆,其實是汙衊瞭員工!這樣德纔兼備的一位文士,既然認為新崗位的發揮空間會比留在「明教」大得多,他又不是很看重金錢物質讀書人,當時決定與小查詩人分手,肯定有他的崇高理由。後來事態的發展,大傢都認為他沒有看透新老闆的底細,這迴轉工可能真的是失策瞭。但是我們看見這位先生此後仍然長期將精神心力都專注在文化事業上,他對香港社會的貢獻,並不見得就一定低過仍然在「明教」效力呀!
成年人在個人事業上麵臨重大抉擇,風險當然要自己承擔,又不是小孩子兒戲!假如是年青人初齣茅蘆,希望到外麵闖天下,結果是碰壁之後有意「吃迴頭草」,能夠重新迴到起點當然是人生的幸運際遇,但是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位老闆都能夠這樣「虛位以待」。如果小查不辦隆重的歡送會,癡癡地等舊人迴頭,則心裏把後來的繼任人當成甚麼?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備胎」嗎?
對小查詩人經營的細節如此苛評,與某些人對小查詩人小說的苛評都是同樣的不閤常情常理。
最荒唐的,莫過於社會上流播小查詩人是「九流老闆」之說!
如果說到事分「九流」,我們正常人的理解,就隻有第一流到第九流,第九流之外,更是壞到不入流瞭。如果小查詩人是一個「九流老闆」,是不是在說他正正是近年鬍鬧政客經常掛在口邊的「無良雇主」?
我雖然沒有入過「明教」,不過長居香港逾半世紀,此間的社會現狀還是略知一二。我倒要問一問:「明教金教主」是否經常欠薪不發,陷夥計於經濟睏境?
如果沒有,該可以升一流,算他「八流」吧?
還要再問,「明教金教主」有沒有試過因為員工遲到、早退或請假要扣工資?
如果沒有,又可以再升一流,算他「七流」可以嗎?
有人說「明教金教主」給的稿酬太低,不過我卻聽說過其副刊專欄作傢有雙糧可領!
何謂「雙糧」?
這是香港職場慣例,不知何時開始。因為香港華洋雜處,每年的農曆年關誰都開支多。這年關有時在公曆一月,有時在公曆二月,年年不同。於是許多所謂「寫字樓」的白領工,都有每年發第十三個月薪水的習慣,有些更白紙黑字寫在雇傭閤約上。所謂「雙糧」,即是大概農曆年前發放等於一個月薪金的花紅,約略等同老闆代員工儲蓄,在年關前纔給員工,這樣就不怕無錢過年瞭。
此事我隻是聽來的,如果「明教金教主」給專欄作傢發雙糧,是不是還可以再升他一流,算他「六流」呢?
此所以,「明教」教眾也不是人人有資格罵金教主,當中「副刊門」的「雜文供應商」就沒有這個資格瞭!如果曾經每年支雙糧,還有膽罵金教主「九流」,那真是「狼心狗肺」、「枉讀詩書」瞭!
至於說金教主的明教工資特低,那麼自以為可以在外麵領更高工資的人纔,又是為瞭甚麼原因仍要讓「九流老闆」長期剝削呢?
有報界前輩說,那個年代在報館工作其實很清閑!許多人隻花三四小時就完成瞭每天的工作。當然,有突發大事又當彆論,這就可能要大量加班而沒有特彆加班費,不過這種情況可能一年也沒有幾次。
報館員工除非是活在老闆的眼皮底下,工作桌在老闆十呎之內,否則在報館上班的時間在辦公事還是辦私事倒是不容易界定的清楚。我們隻知道有畫傢在上班時畫自己私人賺外快的漫畫;有作傢在上班時寫自己私人的小說、詩歌,或為彆傢報紙供稿;有記者在上班時給競爭對手寫新聞報導;還有上進心強的夥計在上班的邊角空閑時間自修,務求考取更高學曆,期待將來事業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些都不是甚麼秘密。
還有人說小查詩人曾經暗地理齣資,辦一份性質相近的報紙去分薄他旗下報紙的市場佔有率雲雲。
難道真的:「壞人衣食,猶如殺人父母」?
怪哉!
此君不是長年纍月都在謳歌自由市場經濟嗎?
當年仍是九七香港迴歸前的英殖時代,難道港英政府有發過「專買執照」給他嗎?
有法例不準其他人加入這個市場做買賣嗎?
此君認為香港不應該奉行所謂「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嗎?
這也可以成為惡評小查詩人的理由嗎?
可見,「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真能反映先哲聖賢的智慧!
再有某學府教師,曾撰文譏諷小查詩人齣錢捐一個名譽學位。據說當年小查詩人一度要以誹謗罪興訟,後來又作罷。於是又有人以小查詩人不再追究作為落實「捐學位」一事的實證,剛好在小查離世後,將這一段陳年舊事翻齣來。
不過我們老香港都知道在香港告人誹謗,是很容易「原告變被告」而得不償失的。因為香港法律費用高昂,而且從往績研判,告誹謗嚮來難入罪,而得值亦罕有多判賠償,一般人很難經法律途徑討得甚麼公道。
此類事件「本縣曾經此苦」,有一迴我有感於受瞭一傢大機構的員工濫用公器狂罵,屬於疑似誹謗,於是搜集證據,看看可以怎樣迴應。結果是讀過法律而沒有執業的朋友看過所有資料之後說官司有得打;直正執業的大律師和律師學長,卻看也不看便直斥我不要興訟!
一個說:「這類案件若對方委託我處理,你未見官就要破産瞭!」行內的潛規則很難三言兩語講得清,老行尊既然一錘定音,此事實在不必再深究瞭!
一個說:「當你是兄弟纔勸你,這遊戲不是你能玩的!」
法治雲乎哉?
小查詩人的學位與捐款是甚麼關係,雙方手頭上的物證是那邊的強,今天我都無資料去評論。
不過以常理推斷,學府頒名譽學位給社會上各行各業的公眾人士,當中受者有富有貧。富的少不免請他隨緣樂助;貧的則學府無攤大手闆要錢之理。以小查詩人的事功而論,不管是他的文學作品、社評政論,還是辦報營商、企業管理等等,當然每一項都夠資格領這些甚麼榮譽學位,隻不過剛巧他同時是個富商,學府高層當然會乘機勸捐。如果每一傢學府的高層教職員都可以這樣隨心所欲去挑剔獲頒榮譽學位的人,去追究是先捐款後領學位還是先領學位後捐款,以後還有社會賢達肯捐錢給這學府並領其學位?按廣府人的說法,這學府也太過「無衣食」瞭!
原來說穿瞭,是有學府教師因為政見分歧的問題,便藉捐款與頒學位兩事之間的關係大造文章而已。據說這位學府教師掌握瞭不少會議紀錄,可以證實小查詩人是捐學位的。
問題是,你大學高層指責捐款人捐學位,我們局外人便要問,是誰先開口要「玉成」這件「好事」?
如果是小查詩人先去問那學府的高層,可否用錢捐個學位;結果錢捐瞭,學位也頒瞭;這樣還可以說得通。如果隻是小查要捐錢,卻沒有說要得甚麼好處,然後是學府「良心發現」給個學位,那就不能說是小查要用錢捐學位瞭!而且一隻手掌拍不響。有人肯捐錢換學位,亦要有人肯收錢派學位呀!
如果是學府的高層先主動問小查要錢,待小查捐瞭之後卻嫌少,還不顧臉麵的要小查多捐一個「零」(江湖傳聞如此)。然後不知怎的要頒小查一個學位,這也可以算是小查齣錢捐一個學位嗎?
當這位學府高層伸齣一根食指指責小查的時候,會不會有三根手指(中指、無名指和小指)都在指著自己?此所以今天潘某人指罵該罵的人,都是食指、中指和無名指併攏來指,就不怕惹人閑話瞭。
即使退一萬步來說,小查詩人與這傢學府的高層真的有捐錢換學位的默契瞭。但是怎麼可以在高層會議紀錄入麵,居然有人討論讓社會上那些「不該」拿榮譽學位的人捐學位?究竟是開會的人斯文掃地,還是被指捐學位的慷慨捐款人丟臉呢?
高層收瞭錢「貨銀無訖」,卻縱容「下麵的人」到江湖上散播惡言,這一乾相關人等還算是個人嗎?
如果這位學府教師是這樣的清高絕俗、白璧無瑕,我們局外人是否可以請學府以後將捐款和頒榮譽學位兩事完全切割。捐款的勿頒學位,頒學位的絕不收捐款,可以嗎?
這樣日後就不會再有人捐瞭錢然後被羞辱瞭!
這傢學府的儇薄無行,還不止於此。
小查詩人既是作傢、也是商人。那傢學府隻看上瞭小查詩人的錢,全體教師沒有人有興趣或能力參加「金庸學研究」,亦不認同小查作為一個報人、政論傢和企業傢的成就,為甚麼要頒學位?難道這傢學府的榮譽學位就是明碼實價,真的可以任由社會上的張三李四陳五黃六拿錢去捐迴來的嗎?
這學府的教職員在「金庸學研究」上麵交瞭白捲也算瞭,研究唐詩宋詞的教師,不見得一定要拜讀小查的大作,不過自稱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而沒有讀好金庸小說,就未免太過疏懶瞭!還有臉麵去問小查詩人要錢?
後來,這裏小貓三四隻教職員,自稱要「研究小查」,還弄瞭個「世界性」的組織。這幾位先生,倒有點似嚮問天譏諷嶽不群那樣,練瞭「鐵麵罩」、「金臉皮」的功夫。他們手中拿書給傳媒拍照留念,看官一望,竟然都是小查的小說,卻不是這幾位先生的個人著作!
以這學府教職員的輕佻,難怪學府的名聲江河日下瞭!
小查詩人過世之後,在許多理據不甚堅實的惡評之間,還是有零星齣自老夥計現身說法、為查大俠金教主稍為平反的第一手資料。
潘國森與查良鏞先生沒有甚麼深交,這迴組織一些舊文新作,紀念一下這位亦師亦友的長者。常言道:「不招人妒是庸纔。」小查詩人亦難免於此。
本書題為《金庸與我──雙嚮亦師亦友全紀錄》,收錄瞭我在小查詩人過世之後寫的一係列專欄文字(發錶在香港《文匯報》的〈琴颱客聚〉),放在第一章。第二章是過去幾次金庸小說研討會的論文,都是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急急完成的。
附錄有古德明先生幾篇談論《鹿鼎記》英譯的短文。我在《總論金庸》有一章談及翻譯金庸小說的難處。後來在《武論金庸》提齣應該請德明兄負責《金庸作品集》英譯的工作,德明兄曾任《明報月刊》總編輯。小查詩人沒有重金禮聘德明兄主理此事,實為一生人一大失策之事。
我與小查詩人並無深交,多年來見麵不過十次。不過能夠與這樣一位偉大的作傢處於相同的時代,還有過一些有趣的交集,亦是很奇特的因緣。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閱讀這本書的過程,是一次意外的驚喜,也是一次心靈的洗禮。我曾以為,像金庸先生這樣的文學巨匠,與普通讀者的距離是遙不可及的,仿佛高高在上,隻存在於筆下的文字世界。然而,這本書徹底打破瞭我的固有認知。它讓我看到瞭一個更加接地氣、更加有人情味的金庸。作者以一種近乎朝聖的姿態,記錄瞭他與金庸先生之間非同尋常的師友關係。那些關於創作的交流,關於人生哲學的探討,甚至是一些生活中的瑣事,都被細膩地描繪齣來。我仿佛能聽到金庸先生爽朗的笑聲,感受到他睿智的眼神,體會到他身上那股不減當年、睥睨天下的俠者風範。而作者的視角,則如同一把鑰匙,為我們打開瞭通往金庸先生內心世界的大門。我從中學習到的,不僅僅是寫作技巧,更是如何做一個有情有義、有擔當的人。金庸先生對於文學的熱愛,對於民族文化的傳承,對於俠義精神的弘揚,都深深地影響著我。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關於金庸的書,更是一本關於如何成為一個更好自己的指南。它讓我重新審視瞭自己的人生,思考瞭自己肩負的責任。
评分這本書帶來的震撼,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我一直以來都將金庸先生視為我人生路上的精神燈塔,他的作品給予我無數的啓迪和力量。而這本書,則讓我有機會走近這位我心中永遠的“大俠”,看到他生活中不為人知的一麵,感受到他作為一位智者、一位長者,與後輩之間建立的深厚情誼。作者的文字樸實而真摯,字裏行間流露齣的,是對金庸先生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以及對這段師友關係的珍視。我讀到瞭他們之間關於文學創作的探討,關於人生道路的選擇,關於對社會的觀察與思考。這些交流,對我而言,如同一場場醍醐灌頂的講座,讓我受益匪淺。我看到瞭金庸先生的博學多纔,他的幽默風趣,以及他對後輩的耐心教導。更讓我感動的是,金庸先生並非高高在上,而是將作者視為平等的朋友,給予他真誠的建議和鼓勵。這種亦師亦友的關係,是多麼的難能可貴!這本書不僅僅是記錄瞭一段師友情誼,更是展現瞭一種傳承,一種精神的傳遞。它讓我更加深刻地理解瞭金庸先生作品中所蘊含的俠義精神,以及他對於民族文化的熱愛。
评分這本書就像是一扇窗,透過它,我得以窺見金庸先生內心深處不為人知的另一麵。那些武俠世界中的英雄豪傑,在現實生活中,也曾是我的良師益友,給我指引方嚮,在我迷茫時給予力量。我一直以為自己對金庸先生的瞭解已足夠深,讀瞭他的無數作品,揣摩他字裏行間的深意,甚至模仿他的筆法,試圖捕捉那種江湖的豪情與俠骨。然而,當我翻開這本書,纔發現自己之前的認知不過是冰山一角。作者以極其真摯的情感,娓娓道來他與金庸先生從相識到相知的點點滴滴。字裏行間流淌的,不僅僅是文字的力量,更是情感的溫度。我仿佛置身於那個充滿魅力的時代,與他們一同品茗論道,一同感受人生百味。那些關於創作的睏惑,關於人生的感悟,關於對世事的洞察,都如同涓涓細流,滋養著我的心靈。我從中看到瞭一個更加立體、更加鮮活的金庸先生,一個充滿智慧、幽默,同時又有著深刻人生體驗的長者。而作者本人,也如同一麵鏡子,映照齣金庸先生對後輩的關懷與指導,也映照齣作者對恩師的敬重與感激。這種雙嚮的情感連接,讓我深深感動。
评分翻開這本書,我仿佛穿越瞭時空,迴到瞭那個金庸先生還活躍在我們身邊的年代。我一直深信,偉大的作傢,他們的作品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他們人生閱曆、思想境界的結晶。而這本書,恰恰為我們提供瞭一個絕佳的窗口,讓我們得以窺見金庸先生的創作源泉,以及他作為一個人,是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如何與這個世界互動的。作者的敘述,充滿瞭真情實感,字裏行間都飽含著他對金庸先生的崇敬與愛戴。我被他們之間那些充滿智慧的對話深深吸引,也被他們之間那種超越年齡、超越名利的真摯友誼所感動。我看到瞭金庸先生在創作上的嚴謹與執著,也看到瞭他在生活中的豁達與幽默。而作者,則在這段關係中,不斷成長,不斷蛻變,成為瞭一個更加成熟、更加有擔當的人。這本書讓我明白,真正的師長,不僅僅是傳授知識,更是以身作則,以人格魅力影響學生。金庸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導師,他用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他的品格,為我們樹立瞭榜樣。這本書,讓我更加熱愛金庸先生,也讓我更加熱愛生活。
评分這本書是一本令人驚艷的“解密”之作,它不僅僅是關於一位偉大的文學傢,更是關於一份溫暖而深厚的師友情誼。我一直以為,金庸先生的形象,更多地存在於他的武俠世界裏,高大、威嚴、充滿瞭江湖的傳奇色彩。然而,當我捧起這本書,我看到瞭一個更加真實、更加生動、也更加有人情味的金庸。作者以其細膩的筆觸,將自己與金庸先生之間非比尋常的交往點滴,娓娓道來。那些關於文學創作的切磋,關於人生哲學的探討,關於對社會萬象的觀察,都如同珍珠一般,散落在字裏行間,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我從中感受到瞭金庸先生的淵博學識,他的睿智幽默,以及他對後輩無私的關懷和指導。這種亦師亦友的關係,讓我看到瞭一個更加立體、更加有血有肉的金庸。作者的敘述,並非是簡單的崇拜,而是充滿瞭平等的交流和真誠的請教。他用自己的成長曆程,印證瞭金庸先生的教誨是多麼的寶貴。這本書讓我明白瞭,真正的傳承,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精神的共鳴,是人格的熏陶。它讓我對金庸先生這位偉大的作傢,又多瞭一份敬意和熱愛。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