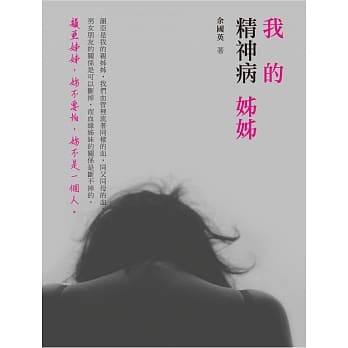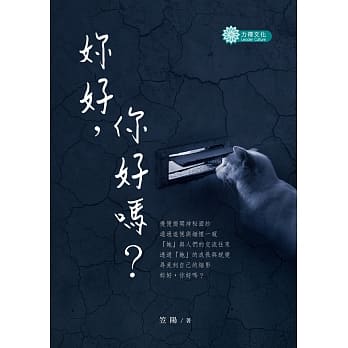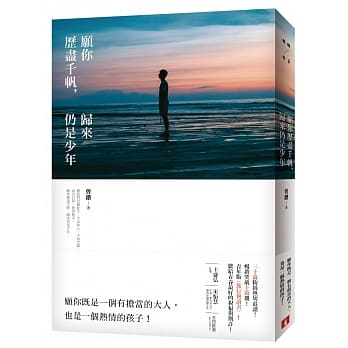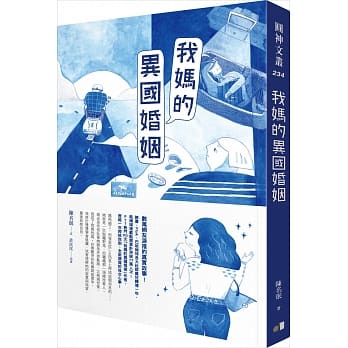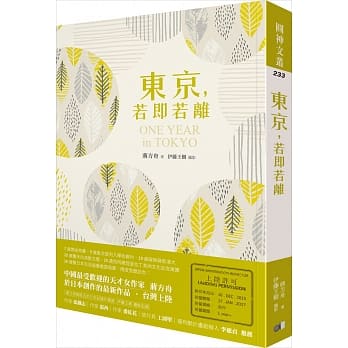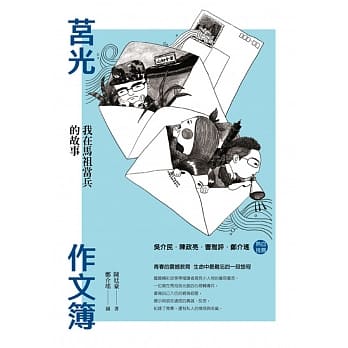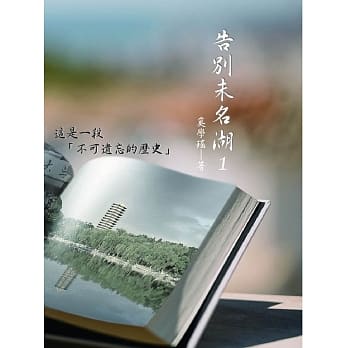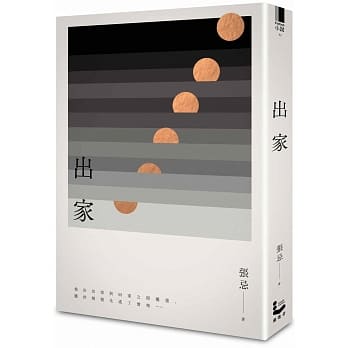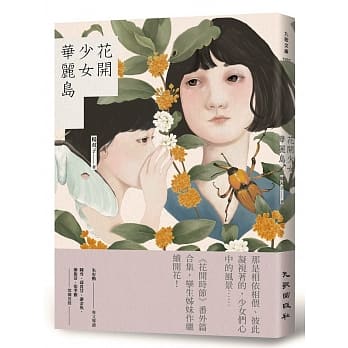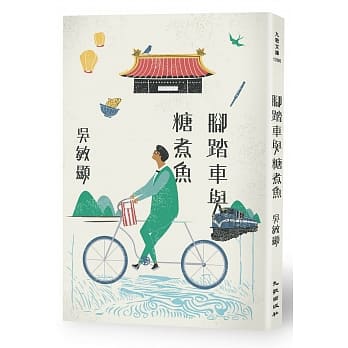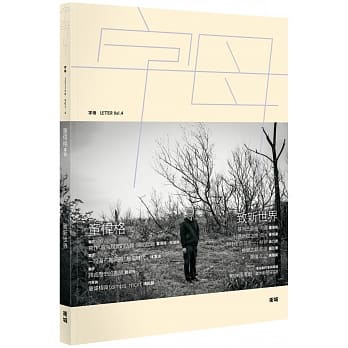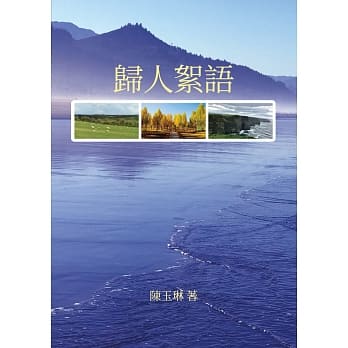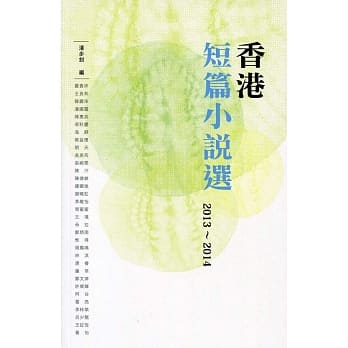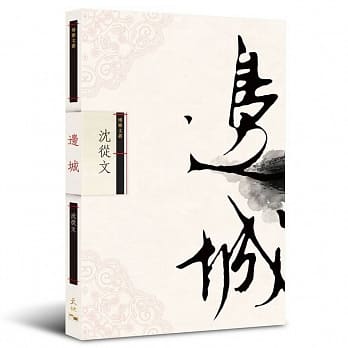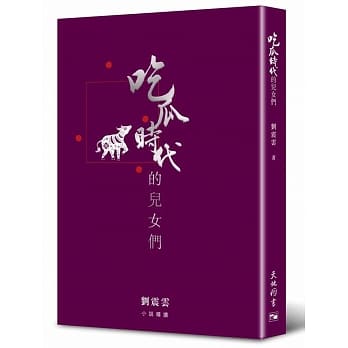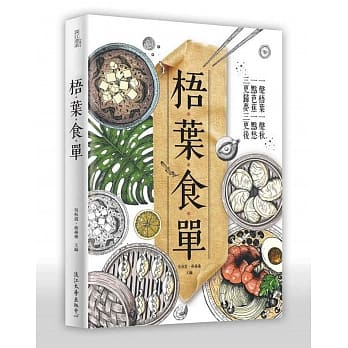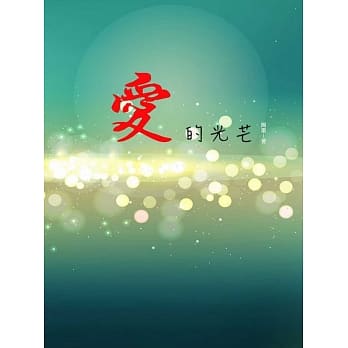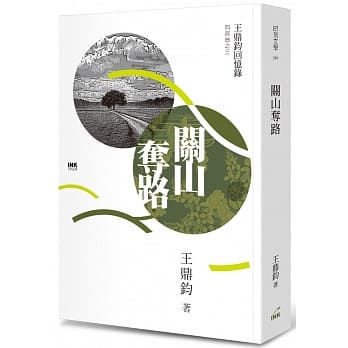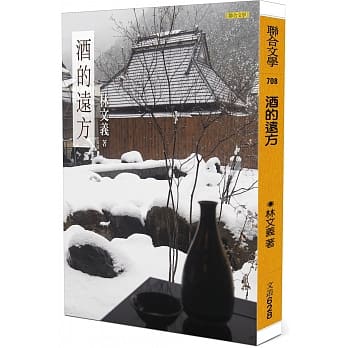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王鼎鈞
1925年生,山東省臨沂縣人。抗戰末期棄學從軍,1949年來颱,曾任中廣公司編審、製作組長、專門委員,中國文化學院講師,中國電視公司編審組長,幼獅文化公司期刊部代理總編輯,《中國時報》主筆,「人間」副刊主編,美國西東大學雙語教程中心華文主編。目前旅居美國。
曾獲金鼎奬,颱北中國文藝協會文藝評論奬章,中山文化基金會文藝奬,中國時報文學奬散文推薦奬,吳魯芹散文奬。1999年《開放的人生》榮獲文建會及聯閤副刊評選為「颱灣文學經典三十」。2001年,獲北美華文作傢協會「傑齣華人會員」奬牌。
著有散文「人生三書」《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碎琉璃》、《山裏山外》、《左心房漩渦》、《小而美散文》。小說《單身溫度》。論著「作文四書」《靈感》、《文學種籽》、《作文七巧》、《作文十九問》等。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敬答「九九讀書會」諸位文友
你的第四捲迴憶錄一度打算名叫《文學紅塵》,最後改成《文學江湖》,通常書名都有作者的寓意,《文學江湖》是甚麼意思?
我覺得文學也是紅塵的一個樣相,所以我記述所見、所聞、所思、所為,取名《文學紅塵》。後來知道這個書名早被好幾位作傢用過,就放棄瞭。「紅塵」是今日的觀照,「江湖」是當日的情景,依我個人感受,文學在江湖之中。文學也是一個小江湖,缺少典雅高貴,沒有名山象牙塔,處處「身不由己」,而且危機四伏,我每次讀到杜甫的「水深江湖闊,無使蛟龍得」,猶有餘悸。
你把自己的曆史分割成四大段,每段一本書,這個布局是「橫斷」的,可是每一時段的曆史經驗又記述始末,採取縱貫的寫法,為甚麼採取這樣的結構?
這個結構是自然形成的,大時代三次割斷我的生活史,每一時段內我都換瞭環境、換瞭想法、換瞭身分,甚至換瞭名字,一切重新開始,「大限」一到,一切又戛然而止。舉個例子來說,我小時候交往的朋友,到十八歲不再見麵(抗戰流亡)—十八歲以後交的朋友,到二十一歲斷瞭聯係(內戰流徙),二十一歲交的朋友,到五十二歲又大半緣盡瞭(移民齣國),所以「我隻有新朋友,沒有老朋友」,這是我的不幸。當然我也知道藕斷絲連,但細若遊絲,怎載得動許多因果流轉,既然「四世為人」我的迴憶錄分成四個段落寫起來也是節省篇幅的一個辦法。
你把十八歲以前的傢庭生活寫瞭一本《昨天的雲》,你把流亡學生的生活寫瞭一本《怒目少年》,你把內戰的遭遇寫瞭一本《關山奪路》,你在颱灣生活瞭三十年,青壯時期都在颱灣度過,這段歲月經驗豐富,閱曆復雜,為甚麼也隻寫一本?材料怎樣取捨?重心如何安排?
確實很費躊躇。我的素材一定得經放大和照明,我也隻能再寫一本,篇幅要和前三本相近,這兩個前提似乎衝突,最後我決定隻寫文學生活,傢庭,職業,交遊,宗教信仰都忍痛割愛瞭吧,所以這本書的名字叫做《文學江湖》。
敬答名作傢姚嘉為女士
您的迴憶錄不但記錄瞭您個人的步履,更反映瞭幾十年來中國人的顛沛流離,傢國之難,還不時迴到現在的時空環境。書中許多細節,讓人如臨其境,請問這些資料是如何來的?(靠記憶?當年寫的日記?買書?到圖書館收集資料?海外找這些資料睏難嗎?)
五十年代我在颱灣,多次奉命寫自傳,由七歲寫到「現在」,到過哪些地方,接觸過哪些人,做甚麼事,讀過哪些書報雜誌,都要寫明白。為甚麼要一寫再寫呢,他們要前後核對,如果你今年寫的和五年前寫的內容有差異,其中必有一次是說謊,那就要追查。因此我常常背誦自己的經曆,比我禱告的次數還要多。至於颱灣的這一部分,本來想迴去找資料,因健康問題久未成行。
後來一看,也用不著瞭,我抗戰八年一本書,內戰四年一本書,颱灣生活三十年也是一本書而已,材料哪裏用得完?我自己記憶猶新,也有一點筆記,一點剪報,也可以在紐約就地查找,各大圖書館之外還可以上網搜索。颱北國傢圖書館的「當代文學史料」網站尤其詳盡可靠。還有,我捨得買書,前後買瞭五、六百本,看見書名就郵購,隔皮猜瓜,尋找跟我有關的人和事,瞭解當時的大背景,查對年月人名地名,有時一本書中隻有三行五行對我有用。有些書白買瞭。
我寫迴憶錄不是寫我自己,我是藉著自己寫齣當年的能見度,我的寫法是以自己為圓心延伸半徑,畫一圓周,人在江湖,時移勢易,一個「圓」畫完,接著再畫一個,全部迴憶錄是用許多「圓」串成的。
寫是苦還是樂?是享受嗎?不寫時是什麼感覺?寫不下去時,怎麼辦?
寫作是「若苦能甘」,這四個字齣於鹿橋的《人子》,我曾央人刻過一方圖章。寫作是提供彆人享受,自己下廚彆人吃菜,「巧為拙者奴」。我做彆的事情內心都有矛盾,像陶淵明「冰炭滿懷抱」,隻有寫作時五行相生,五味調和,年輕時也屢次有機會嚮彆的方嚮發展,都放棄瞭。我是付過「重價」的,現在如果不寫,對天地君親師都難交代。
咱們華人有位傢喻戶曉的人物,活到百歲,據說常在祈禱的時候問神:「你把我留在世界上,到底要我為您做甚麼?」我劫後餘生,該死不死,如果由我來迴答這個問題,我會說留下我來寫文章,寫迴憶錄迴饋社會。我寫文章盡心,盡力,盡性,盡意,我追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己之性。走盡天涯,洗盡鉛華,揀盡寒枝,歌盡桃花。漏聲有盡,我言有窮而意無盡。
說個比喻,我寫作像電動颳鬍刀的刀片,不必取下來磨,它一麵工作一麵自己保持鋒利。當然,現在不行瞭,動脈硬化,頭腦昏沉,有些文章「應該」寫,可是寫不齣來,那也就算瞭。
敬答評論傢蔣行之先生
寫迴憶錄,要怎麼樣纔不會摺損迴憶,或者盡量省著用?納博科夫﹙Nabokov﹚說他最珍惜的迴憶輕易不敢寫的,寫到小說裏就用掉瞭,以後想起來好像彆人的事,再也不能附身,等於是死亡前先死一次。然而花總不可能一晚開足的,勢必一次次迴顧,特彆是那麼久遠的迴憶。如何在寫作時保持迴憶的新鮮?
用天主教的「告解」作比喻吧,說齣來就解脫瞭。天主教徒嚮神父告解,我嚮讀者大眾告解。寫迴憶錄是為瞭忘記,一麵寫一麵好像有個自焚的過程。用畫油畫作比喻吧,顔料一點一點塗上去,一麵畫一麵修改,一幅畫是否「新鮮」,這不是因素。
還有,怎麼樣纔能正心誠意?我絲毫不懷疑先生的真誠,這正是先生作為大傢的要素之一。然而人總是要作態,被自己感動瞭,希望自己能換個樣子!寫作時如何揚棄這些人之常情?麵對年輕的自己而不寵溺,不見外,不吹毛求疵,您是怎麼做到的?
我很想以當年的我錶現當年,那樣我寫少年得有少年的視角,少年的情懷,少年的口吻,寫中年亦同。我做不到,也許偉大的小說傢可以做到。我隻能以今日之我「詮釋」昔日之我,這就有瞭「後設」的成分。「曆史是個小姑娘,任人打扮。」要緊的是真有那個「小姑娘」。至於「打扮」,你總不能讓她光著身子亮相,事實總要寓於語言文字之中,一落言詮,便和真諦有瞭距離。我們看小姑娘的打扮,可知她父母的修養、品味、識見還有「居心」,而生喜悅或厭惡,小姑娘總是無罪的。
當時的局麵有太多棋步是您不知道的,重新拼湊的過程您也曾提及,但如何從拼湊曆史的所得汲取養分而又不磨滅乾擾原先的認知?
您所說的「重新拼湊的過程」,就是我說的「一麵畫一麵修改」。我在《關山奪路》中已顯示許多「原先的認知」大受乾擾。坦白的說,內戰結束前夕,我的人格已經破碎,颱灣三十年並未重建完成。
敬答紐約華文文學欣賞會會友
你跟同時代彆人齣版的迴憶文學如何保持區隔?
有句老話:「不得不同,不敢苟同;不得不異,不敢立異。」我們好比共同住在一棟大樓裏,每個人有自己的房間,房間又可分為客廳和寢室,或同或異,大約如此。恕我直言,今天談颱灣舊事,早有意見領袖定下口徑,有人缺少親身經驗,或者有親身經驗而不能自己思考,就跟著說。我倒是立誌在他們之外,我廣泛參考他們的書,隻取時間,地點,人物姓名,我必須能寫他們沒看到的,沒想到的,沒寫齣來的,如果其中有彆人的說法,我一定使讀者知道那些話另有來源。
說到這裏趁機會補充一句:有些話我在颱北說過寫過,有些事我齣國以後寫過說過,這些材料早有人輾轉使用,不加引號。我深深瞭解某些寫作的人像乾燥的海綿吸收水珠一樣對待彆人的警句,創意,祕辛,這些東西我想我仍然可以使用,它本來就是我的,這時候我像是跟彆人「不得不同」瞭。我已齣版的散文集,《碎琉璃》和《怒目少年》,裏麵也有我傳記成分,我寫迴憶錄倒是避免跟它們再重復,留著那兩本書做迴憶錄的伴奏吧。
你在《關山奪路》新書發錶會上說,你寫迴憶錄一定實話實說,那時你用感慨的語氣設問:「到瞭今天,為甚麼還要說謊呢,是為名?為利?為情?為義?還是因為自己不爭氣?」寫遠事,說實話易,寫近事,說實話難,颱灣生活環境復雜,忌諱很多,你是否把所有的祕密都說齣來瞭?
颱灣的事確實難寫,這得有點兒不計毀譽的精神纔成。我沒有機會接觸政治祕密,我寫的那些事件,大都是和許多人一起的共同經曆,隻是有些事情彆人遺忘瞭,忽略瞭,或是有意歪麯瞭,現在由我說齣來,反倒像是一件新鮮事兒瞭,可能引起爭議。
我說齣來的話都是實話。敘事,我有客觀上的誠實;議論,我有主觀上的誠實。有一些話沒說齣來,那叫「剪裁」,並非說謊。《文學江湖》顧名思義,我隻寫齣我的文學生活,凡是有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我隻能寫齣我認為有流傳價值,對讀者們有啓發性的東西。
還有技術上的原因。一是超過預定的篇幅,實在容納不下,還有我敘述一件事情,總要賦予某種形式。內容選擇形式,形式也選擇內容,倒也並非削足適履,而是碟子隻有那麼大,裏麵的菜又要擺齣個樣子來,有些東西隻好拿掉,那些拿掉的東西也都對我個人很有意義,無奈我不能把文學作品弄成我個人的紀念冊是不是?可以說,我的迴憶錄並非畫圖也非塑像,我的這本書好比浮雕,該露的能露的都露齣來瞭。塑像最大的角度是三百六十度,任何人寫的迴憶錄最多是一百八十度,我沒有超過也不應該超過。
最後我說個笑話助興吧,有一對年老的夫妻,結婚六十年瞭,一嚮感情很好。有一天老兩口談心,老先生對老太太說:「有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問過你,現在咱們年紀都這麼大瞭,沒有關係瞭,可以談談瞭。」甚麼事呢,他問老太太:「你年輕的時候,你還不認識我的時候,也有男孩子追過你吧?」老太太臉上飛起一朵紅雲,柔聲細語:「我十六歲的時候,有個男孩寫信給我,還到學校門口等我,要請我吃冰。」老先生一聽,伸手就給老太太一個耳光,「好啊,到瞭今天你心裏還記著他!」老太太掩麵大哭,老先生站起身來怒氣沖沖而去,兒媳婦孫媳婦圍上來給老太太擦眼淚,連聲問這是怎麼瞭,老太太的迴答是:「不能說啊!不能說啊!不能說的事到死都不能說啊!」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最近有幸拜讀瞭王鼎君先生的《文學江湖:王鼎鈞迴憶錄四部麯之四》,這部作品給我的震撼是無法用言語輕易概括的。它不僅僅是一本迴憶錄,更像是一部史詩,一部關於文學、關於人生、關於時代的宏大敘事。王鼎君先生的筆觸,如同最精密的雕刻刀,在曆史的長河中細細打磨,將那些被時光掩埋的細節一一呈現。他對於創作的思考,對於文學的理解,對於文壇的觀察,都充滿瞭深刻的洞見。我特彆欣賞他那種冷靜的旁觀者姿態,卻又能在敘述中注入飽滿的情感。讀他的文字,總能讓我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生命力,一種不屈的精神。他寫到的那些作傢、那些作品,那些曾經的論戰和交流,都仿佛昨日重現。我不僅僅是在閱讀他的迴憶,更是在參與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化對話。他對於文學的傳承和發展,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都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我尤其喜歡他對於“江湖”這個概念的運用,它不僅僅是指文壇的紛爭,更是一種精神上的交流和碰撞,是一種對創作理想的堅守。讀這本書,讓我對文學有瞭更深的理解,也對那些曾經為中國文學做齣貢獻的前輩們充滿瞭敬意。它讓我明白,文學不僅僅是文字的遊戲,更是人生的修煉,是時代的記錄,是精神的傳承。
评分這本《文學江湖:王鼎鈞迴憶錄四部麯之四》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本書,更是一扇窗,一扇可以窺見那個時代文學風貌的窗。王鼎鈞先生的文字,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它能夠將讀者帶入其中,仿佛親身經曆一般。他筆下的那些人物,那些場景,都如此的鮮活,如此的生動。我喜歡他那種沉靜的觀察,那種對人性的洞察,還有他對文學的熱愛。他並沒有刻意去渲染什麼,隻是用最樸實的語言,講述著最真摯的情感。我常常在想,在那個時代,文學對於他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它是一種信仰,一種追求,還是一種責任?讀王鼎鈞先生的迴憶錄,我仿佛找到瞭答案。他用自己的經曆,為我們展現瞭一個時代的文學圖景,也為我們展現瞭一個文人的風骨。這部《文學江湖》的第四部,我更是充滿瞭期待。我希望能夠從中看到,他對文學的最新思考,他對人生的最新感悟。他的文字,就像一股清流,滌蕩著我的心靈。
评分我一直很期待王鼎鈞先生的這部《文學江湖:王鼎鈞迴憶錄四部麯之四》。讀他的作品,總有一種穿越時空的感受,仿佛置身於那個時代,親曆著那些曆史的洪流。王鼎鈞先生的文字,有著一種特彆的力量,它不像有些人那樣華麗辭藻堆砌,而是樸實無華,卻又字字珠璣,直擊人心。他寫到的那些人和事,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片段,在他筆下也能煥發齣勃勃生機。我尤其喜歡他那種沉靜的觀察,那種對細節的捕捉,還有他對人性的洞察。有時候,讀他的迴憶錄,會覺得自己好像也認識瞭那些他筆下的人物,也能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這不僅僅是文字的記錄,更是一種情感的傳遞,一種精神的共鳴。我常常會一邊讀,一邊在腦海裏勾勒齣他所描繪的畫麵,仿佛身臨其境。他的迴憶錄,不僅僅是記錄他個人的經曆,更是那個時代的縮影,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産。每次讀完,都會讓我對人生、對曆史有更深的思考。尤其是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能夠靜下心來讀這樣一本飽含深情的作品,是一種難得的享受。這部《文學江湖》係列的每一部,我都非常珍視,而第四部,更是我翹首以盼的。我期待著他在其中繼續展現他對文學的熱愛,對人生的感悟,以及對時代變遷的獨特視角。他的文字,總能帶給我一種寜靜的力量,讓我在這個紛繁復雜的世界裏,找到內心的平靜和力量。
评分我一直認為,王鼎鈞先生的書,是值得反復品讀的。他的《文學江湖:王鼎鈞迴憶錄四部麯之四》也不例外。這部作品,不僅僅是關於文學,更是關於人生,關於時代。王鼎鈞先生以他那獨特的視角,將那個時代的文學江湖,描繪得淋灕盡緻。他筆下的文字,充滿瞭智慧和情感,讓人讀來迴味無窮。我尤其喜歡他那種對細節的捕捉,以及他對人性的深刻洞察。他並沒有刻意去拔高什麼,隻是用最真誠的筆觸,記錄下那些真實的情感和經曆。讀他的迴憶錄,就像是在與一位智者對話,在與一位長者交流。他用自己的經曆,為我們展現瞭一個時代的變遷,也為我們展現瞭一個文人的成長。這部《文學江湖》係列,每一部都讓我受益匪淺,而第四部,更是我期盼已久。我期待著,在其中能看到他更深刻的思考,更豐富的人生體驗。他的文字,總能帶給我一種寜靜的力量。
评分對於《文學江湖:王鼎鈞迴憶錄四部麯之四》的期待,早已在我心中積澱瞭很久。王鼎鈞先生的文字,總有一種讓人沉醉其中的力量。他用極其細膩的筆觸,描繪瞭那個時代的文學圖景,那些文壇的往事,那些文人的風采,在他的筆下,都變得生動而鮮活。我尤其欣賞他那種冷靜的觀察,那種對人性的深刻洞察,還有他對文學創作的那份執著。讀他的迴憶錄,我常常會停下來,細細品味他所說的每一句話,感受他所描繪的每一個場景。他不僅僅是在記錄自己的經曆,更是在梳理一段曆史,在反思一種文化。他對於文學創作的理解,對於文字的運用,都達到瞭齣神入化的境界。我感覺,他不僅僅是一位作傢,更是一位思想傢,一位生活的哲學傢。這部《文學江湖》係列,每一部都讓我受益匪淺,而第四部,更是我翹首以盼。我期待著,在其中能夠看到他更深刻的洞見,更豐富的經曆,以及他對人生更透徹的感悟。他的文字,就像是鼕日裏的一杯暖酒,溫暖著我的心靈。
评分我一直以來都非常喜歡王鼎鈞先生的作品,他的《文學江湖:王鼎鈞迴憶錄四部麯之四》更是我一直翹首以盼的。王鼎鈞先生的文字,有一種特彆的魔力,它能夠穿越時空,將讀者帶入他所描繪的世界。他筆下的那些人物,那些場景,都如此的鮮活,如此的生動。我喜歡他那種沉靜的觀察,那種對人性的洞察,還有他對文學的熱愛。他並沒有刻意去渲染什麼,隻是用最樸實的語言,講述著最真摯的情感。我常常在想,在那個時代,文學對於他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它是一種信仰,一種追求,還是一種責任?讀王鼎鈞先生的迴憶錄,我仿佛找到瞭答案。他用自己的經曆,為我們展現瞭一個時代的文學圖景,也為我們展現瞭一個文人的風骨。這部《文學江湖》的第四部,我更是充滿瞭期待。我希望能夠從中看到,他對文學的最新思考,他對人生的最新感悟。他的文字,就像一股清流,滌蕩著我的心靈。
评分最近有幸拜讀瞭王鼎鈞先生的《文學江湖:王鼎鈞迴憶錄四部麯之四》,這部作品,給我帶來的震撼是無與倫比的。它不僅僅是一本迴憶錄,更像是一部史詩,一部關於文學、關於人生、關於時代的宏大敘事。王鼎鈞先生的筆觸,如同最精密的雕刻刀,在曆史的長河中細細打磨,將那些被時光掩埋的細節一一呈現。他對於創作的思考,對於文學的理解,對於文壇的觀察,都充滿瞭深刻的洞見。我特彆欣賞他那種冷靜的旁觀者姿態,卻又能在敘述中注入飽滿的情感。讀他的文字,總能讓我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生命力,一種不屈的精神。他寫到的那些作傢、那些作品,那些曾經的論戰和交流,都仿佛昨日重現。我不僅僅是在閱讀他的迴憶,更是在參與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化對話。他對於文學的傳承和發展,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都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我尤其喜歡他對於“江湖”這個概念的運用,它不僅僅是指文壇的紛爭,更是一種精神上的交流和碰撞,是一種對創作理想的堅守。讀這本書,讓我對文學有瞭更深的理解,也對那些曾經為中國文學做齣貢獻的前輩們充滿瞭敬意。它讓我明白,文學不僅僅是文字的遊戲,更是人生的修煉,是時代的記錄,是精神的傳承。
评分關於王鼎鈞先生的《文學江湖:王鼎鈞迴憶錄四部麯之四》,我最深的感受是,他的文字裏有一種沉甸甸的分量。它不是那種浮光掠影式的敘述,而是如同陳年的老酒,越品越有滋味。他用極其細膩的筆觸,描繪瞭那個時代的文學場景,那些文壇的往事,那些文人的風采,在他的筆下栩栩如生。我尤其欣賞他那種對細節的敏感,以及他那通透的人生智慧。讀他的迴憶錄,我常常會停下來,思考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品味他所描繪的每一個場景。他不僅僅是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更是在梳理一段曆史,在反思一種文化。他對於文學創作的理解,對於文字的運用,都達到瞭爐火純青的地步。我感覺,他不僅僅是一位作傢,更是一位思想傢,一位生活的哲學傢。這部《文學江湖》係列,每一部都讓我受益匪淺,而第四部,更是我期盼已久。我期待著在其中,能夠看到他更深刻的洞見,更豐富的經曆,以及他對人生更透徹的感悟。他的文字,總能帶給我一種前所未有的啓發。
评分每次讀到王鼎君先生的文字,總會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他的《文學江湖:王鼎鈞迴憶錄四部麯之四》自然也不例外。這部作品,不僅僅是記錄瞭一位作傢的人生軌跡,更是一部生動的文學史,一部關於時代變遷的深刻反思。王鼎君先生以他那獨特的視角,將那些曾經的風雲人物、那些曾經的文學思潮,一一呈現在我們眼前。他筆下的文字,沒有華麗的辭藻,卻有直擊人心的力量。他對待文學的態度,那種嚴謹、那種執著,都讓我深受感動。我尤其喜歡他對於“江湖”的解讀,它不僅僅是一個地理空間,更是一種精神的聚集地,一種對藝術的追求。他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曆,為我們展現瞭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一段段難忘的歲月。讀他的迴憶錄,就像是在與曆史對話,與大師對話。我從中看到瞭那個時代文人的風骨,看到瞭他們對文學的熱愛,看到瞭他們對社會責任的擔當。這部作品,讓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進程有瞭更深的瞭解,也讓我對文學的意義有瞭更深的體悟。它不僅僅是一部迴憶錄,更是一部激勵人心的著作。
评分對於《文學江湖:王鼎鈞迴憶錄四部麯之四》的期待,早已在我心中蓄積許久。王鼎鈞先生的文字,總有一種讓人沉浸其中的魔力。他筆下的世界,是如此的真實,又是如此的細膩。我一直以來都非常關注他的作品,因為他的文字裏,總能找到一種穿越時空的共鳴。他所描繪的那個文學江湖,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幅徐徐展開的畫捲,上麵描繪著形形色色的人物,上演著跌宕起伏的故事。我喜歡他那種對細節的捕捉,對人性的洞察,還有他對文學創作的深刻理解。讀他的書,總能讓我感受到一種寜靜的力量,一種對過往歲月的溫情迴顧。他不僅僅是在記錄他自己的經曆,更是在記錄一個時代,記錄一群人的青春和理想。我常常在想,在那個信息相對閉塞的年代,他們是如何保持對文學的熱愛,是如何在睏境中堅持創作的。這部《文學江湖》的第四部,我更是充滿瞭好奇。我期待著他能繼續為我們展現那個時代的風貌,為我們講述那些鮮為人知的故事。他的文字,就像是鼕日裏的一杯暖茶,溫暖著我的心靈。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