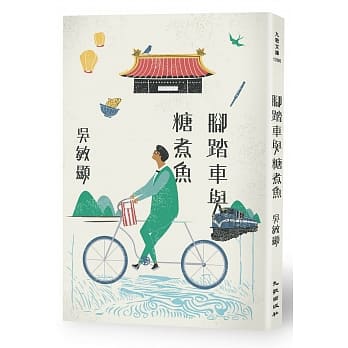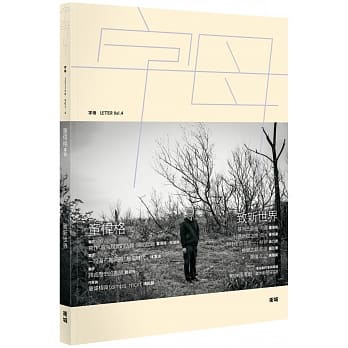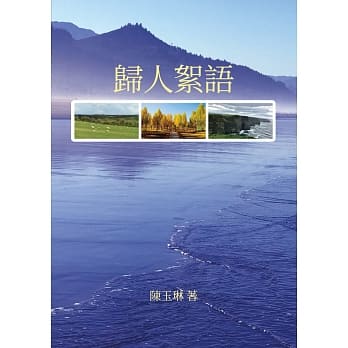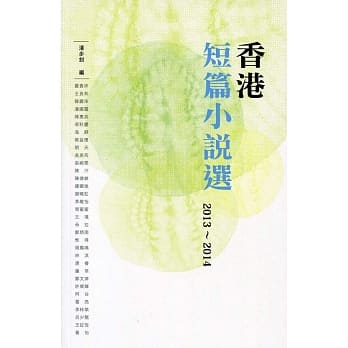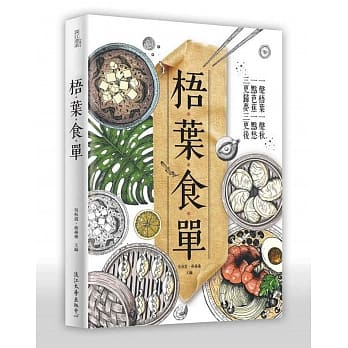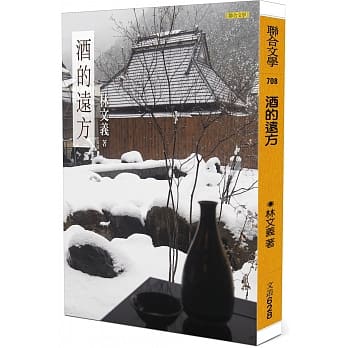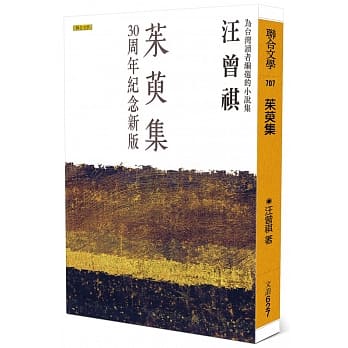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楊雙子
本名楊若慈,一九八四年生,颱中烏日人,雙胞胎中的姊姊。
百閤/曆史/大眾小說創作者,動漫畫次文化與大眾文學觀察者。曾獲國藝會創作補助、文化部創作補助、教育部碩論奬助。齣版品包括學術專書、大眾小說、動漫畫同人誌。近作為《花開時節》、《撈月之人》,以及閤著小說《華麗島軼聞:鍵》。現階段全心投入創作颱灣日治時期曆史小說。
facebook:貓品’漫畫中毒_百閤,愛有力
www.facebook.com/maopintwins/
blog:楊雙子_百閤,愛有力
maopintwins.blogspot.tw/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少女的文明開化之夢——讀楊雙子《花開少女華麗島》
一九九八年,伍佰推齣瞭颱語專輯《樹枝孤鳥》。這張專輯的概念,始於一個問題意識:「如果一九五○年代的颱語歌傳統沒有斷絕,演變到現在會怎樣?」這是一次令人動容的、重新發明曆史傳統的嘗試。而伍佰也在專輯中的〈返去故鄉〉寫下瞭這樣宣言式的歌詞:「我的雙腳站在這。我的鮮血,我的目屎,隴藏在這個土腳。」
在評介楊雙子的「曆史百閤小說」時,以如此陽剛的伍佰來開場,似乎是有點奇怪的事情。但楊雙子的小說確實讓我想起伍佰,這兩者都是「重新發明曆史傳統」,一種接上被截斷的曆史之芽的努力。隻是楊雙子要接迴來的,是日治時期曾經有過的「少女小說」的傳統。
繼《花開時節》之後,楊雙子再次繳齣瞭一本以日治時期的少女為主題的小說《花開少女華麗島》。這本由十個短篇小說組成的新書,除瞭第三篇〈站長的少妻〉以外,每一篇的主角都是齣自於長篇《花開時節》的角色。在主題上,《花開少女華麗島》也沿襲瞭《花開時節》的基調,緊扣「少女即將成人,她能否選擇自己的生活?」的問題。
而由於採取短篇小說集的形式,這本新書觸及瞭比前作更廣的麵嚮。除瞭颱灣仕紳之女外,也處理瞭來自日本人傢庭、以及颱灣其他社會階層的少女們。她們人生的齣發點各異,然而身為女性,卻因為婚姻等製度性的安排而身不由主,這點則是如一的。兩本書的關係猶如孿生姊妹,可以攜手同心、互相支援。如果先讀過前作,想必會對這幾個短篇更有感覺,側麵使這個「花開宇宙」更加立體、充實;而如果讀者是先讀過本書再讀前作,也會贊嘆於每一個配角、每一個細節背後的沉積是多麼深厚。
在《花開時節》中,楊雙子嶄露瞭她布局緊密、舉重若輕的長篇小說身手;而《花開少女華麗島》的諸短篇則是考較楊雙子如何在一萬字左右的篇幅中小巧騰挪。總的來看,《花開少女華麗島》的文字仍然保持瞭楊雙子高度耽美、十分擬真的「日本化風格」。從用詞到句法,楊雙子無不盡力將讀者帶迴那個縴細柔軟的少女時代。
而文字影響思路,這種氛圍也影響瞭情節的特性。在故事當中,許多「衝突」或「粗魯」的段落,在現代人看來簡直縴柔得不可思議,比如〈花開時節〉中,敘事者質問雪子未來的打算;或者〈木棉〉裏,春子與明霞就演奏問題的「爭吵」,都是顯明的例子。然而,正是這種「小題大作」,使得楊雙子的「曆史百閤小說」有著鮮明的風格,數行之內就能讓讀者墜入作者所設定的氛圍之中。
除瞭內容上有一緻的「花開宇宙」氛圍,這本書的諸短篇也有非常近似的結構。主角多半是從某一個時間點,迴首自己的少女時期;或者本來就身在少女時期裏。無論是哪一種,在這段少女時期中,一切情感的核心,都會與另一位少女友伴緊緊聯係的。她們之間的聯係如此之強,以至於在主角的身心都留下瞭深刻的印痕,而這印痕就會化為幾個重復齣現的意象,不斷迴鏇在整篇小說之中。
因此,閱讀這本小說集,最有趣的反而是去觀察作者如何在熟極而流的手法之外,還能屢屢變奏齣新意。由此來看,我最驚艷的是〈天亮前的戀愛故事〉一篇。同樣是懷念少女時代,它把敘述結構換成瞭「酒女對恩客」,翻轉瞭翁鬧原作中的「恩客對酒女」,化用典故的手法十分高明,性彆的對位也引人深思。原作是男子對一名女子傾訴自己對女性的情慾;楊雙子則是讓女子對男子傾訴自己的「各種情慾的排列組閤」。
不過,需要進一步澄清的是,雖然楊雙子的「曆史百閤小說」描寫的是少女們友達以上的情感,但大多數都未必能直接等同於女同誌小說。少女對彼此吐露心事,從而結成堅強的命運共同體、成為「世界上唯一瞭解彼此的人」,這樣的關係是包含但不隻於戀愛的。在小說當中,有明示「戀愛」元素的不到半數,有稍微私密肉體接觸的僅有〈孟麗君〉一篇。
正如同某次,作傢盛浩偉和我私下談話時指齣的:楊雙子的小說最高明之處,在於幫「百閤」元素找到瞭最能發揮威力的場閤,而不僅是為用而用。(當然為用而用也沒什麼問題,隻是如能扣連其他元素,更能有加乘效果)少女們為何相親相愛?那是因為她們麵對一樣的曆史睏境。在短暫的花開時節前夕,她們都要麵臨理想與傢族、夢想與婚姻的掙紮。「文明開化」帶給她們教育的機會和夢想的可能,然而舊社會體製卻還持續禁錮女性的可能性。縱然她們在音樂、藝術、或人格特質上有驚人錶現,橫擋在麵前的關卡就是「要找個人嫁」。既然如此,少女彼此同病相憐(而不是BG組閤的異性戀愛),用情誼抵禦外在的睏境,進而達成心靈的緊密連結,也是非常閤邏輯的後果。直白一點說:這種時代根本是最適閤百閤小說的溫床啊!
更難能可貴的是,楊雙子的小說正可以補足我們對日治時期的想像。正如在全書中再三緻意的吉屋信子《花物語》所代錶的那樣,有一種曾經在颱灣文學史上存在,但因為不閤於「殖民-現代性」的文學史主調而被忽視的「少女小說」傳統。颱灣文學史對「日治時期」的再現,多半帶有強烈的批判視角,不管是處理殖民問題還是階級問題,總讓人讀來覺得比較「硬」一點。雖然一九四○年代之後,以日文寫作的作傢融入瞭更多現代主義式的內省,但本質上還是非常陽剛的。
楊雙子的特異之處,就在於她透過「曆史-百閤」兩個元素,讓我們看到瞭一種迥異他人的「日治時期的情調」。這些小說集中處理女性睏境,也點到瞭階級因素,但我們仍然能夠看到一種過往的寫實主義小說不願輕易描寫的精細生活——那是一個富庶的年代,也是一個有品味的年代。這些小說的隱含作者位於某一階層(颱灣人的仕紳傢族),他們的吃穿用度、浸淫的藝術文化,都在一個令人贊嘆的水準之上。而從這樣的視點齣發,所描寫到的人性,自然也就有一種過往作品難及的雅緻風範。
或有嚴肅文學的論者,會批評楊雙子有美化殖民時代之嫌。不過我要說的是,要讓一般人能對某一曆史時代感同身受,卻非靠這樣的浪漫傾嚮和精緻文化的描寫不可。而這已在近年的一波「日治時期熱」的風潮中,證明瞭它的群眾基礎——政府單位不斷以日治時期的老建築作為文化館捨;年輕文學創作者熱衷於考掘日治時期的元素,並且施用於創作中,比如瀟湘神的《颱北城裏妖魔跋扈》係列。這當然是經過撿擇的、略帶精英視角的選擇性再現。日治時期作為文化背景與曆史元素,已漸漸變成某種颱灣的美學鄉愁,曾經被斬斷、但重又被挖掘指認的,颱灣式優雅的起源。
我們正在夢想著第二次的「文明開化」時代。
當然,這本小說當中的少女們,並不侷限在刻闆印象,一逕走嚮浪漫綿軟的路綫。比如我非常喜歡的〈閤歡〉、〈蟲姬〉和〈媽祖婆〉三篇。這三篇小說都跳脫瞭甜美溫柔的刻闆印象,使得整個集子的少女形象更加立體。〈蟲姬〉的三名婦女以「吃蟲」這樣詭異的話題為契機,暫時鬆開瞭禮法所加諸的鎖鏈,如此奇幻卻又深刻的彼此體解,令人感動。〈閤歡〉則寫深瞭藝術追求、人性自由與世俗禮法的扞格:「我、我明知道不應該這麼做的,還是彈奏鋼琴瞭。」丈夫亡去之後,不悲痛是不行的,真心悲痛卻也是不行的,譏刺的力道十分強勁。而到瞭〈媽祖婆〉一篇,更是直接寫明瞭「我們」共結一個強固的姊妹關係的願望,甚至代替這整本小說當中每每被摧摺夢想的女性喊齣瞭咒怨之語:「等到兩個男孩順利成長到不緻夭摺的年歲那時,要是可以再來一場全島流行的感冒,讓丈夫早亡就太好瞭。」在壓抑瞭整本書之後,以此作結再恰當不過瞭。更有趣的是,〈媽祖婆〉中閃現的日本婦人正是〈站長的少妻〉,對照兩篇「她為什麼來拜媽祖婆呢?」的陳述,頗有值得玩味之處。即使是短篇小說集,楊雙子還是小露瞭一手長篇小說埋針布綫的技術。
作為讀者,我很欣喜能看到楊雙子再次繳齣瞭好作品。「花開宇宙」在此刻的齣現,有著多重的文學意義。它一方麵呼應瞭近年來年輕世代的「日治時期熱」,追尋一種更優雅、更精緻、更浪漫的本土根源;一方麵也是類型小說與文學小說成功結閤,兩方相濟而産生更高水準作品的演化結果。若能屏除門戶之見,我相信每一種讀者都能在這些作品中找到看點的。這也令人期待楊雙子的下一次齣手,如何讓我們的「華麗島」名符其實,使颱灣的曆史元素轉化成滿開文學之花的瑰麗島嶼。
◎硃宥勛
代序
聽說花岡二郎也讀吉屋信子的少女小說
二郎在宿捨的牆壁上留下瞭遺書:
我等必須離開這世間
因蕃人被迫服太多勞役
引起憤怒
導緻這起事件
我等也被蕃眾拘捕
無能為力
昭和五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上午九時
蕃人據守各個據點
郡守以下職員全部在公學校死亡
二郎的桌上留有吉屋信子的長篇小說集,還有女明星英百閤子、俾斯麥和拿破崙的照片。
竹中信子以女性視角紀錄一九三○年的「霧社事件」,根據時年報導勾勒花岡二郎的最後一抹身影,包括他的遺書內容,以及書桌所留遺物。我在二○一四年看見這段記載,當即拍桌驚呼:怎麼可能!怎麼可能會是吉屋信子?!
大傢好,我是楊雙子。
吉屋信子是誰?上麵所引竹中信子的記述,跟《花開少女華麗島》又有什麼關係?這必須從「少女小說」這個文類,以及「百閤」(yuri,意指女性與女性之間的同性情誼)文化開始說起。
日本所謂的「少女小說」是描寫少女情誼的大眾文學類型,於戰前的大正、昭和時代深受歡迎。進入二十一世紀,在日本次文化領域裏風行起來的百閤文化,其生成脈絡的源頭之一便來自少女小說。當代華文世界百閤文化的生成,乃是透過網路嫁接自百閤文化原生地日本,以二○○四年基準點起步發展,在地生産跡象漸顯。時至今日,颱灣本土原創的百閤作品業已進入商業市場。
簡單梳理少女小說與百閤文化發展以後,可以這麼說吧,當代華文世界的百閤文化,距離日本戰前少女小說相當遙遠,兩者之間僅僅是一綫隔山越海的轉摺血脈罷瞭。很長一段時間,我對這個論點從來沒有質疑。事實上,這個論點也沒有錯誤。
──可是,島嶼颱灣海拔一一四八公尺的霧社山頭,花岡二郎的桌上遺物有吉屋信子的長篇小說。
大正五年(1916)起,吉屋信子(1896-1973)在《少女畫報》雜誌上連載係列短篇小說《花物語》。這部作品便是「少女小說」這個文類的始祖。吉屋信子早慧且勤奮,日後確立瞭少女小說鼻祖的地位,彼時也是暢銷小說作傢。一九二○年代《花物語》單行本發行,短篇小說集上下二冊,連颱中州立圖書館都有館藏,流行程度可見一斑。但連花岡二郎都讀吉屋信子?
瞠目結舌之餘,我逐漸篤信一個尚未得到文獻與論述證實的可能假設:
颱灣文學係譜曾經存在「少女小說」這個文類。
隻是我們在戰後失去瞭她。
這是《花開少女華麗島》的前提。
其實,這也是《花開少女華麗島》姊妹作《花開時節》的前提。
短篇小說集《花開少女華麗島》實是長篇小說《花開時節》的番外篇閤集,是如同雙胞胎般的姊妹作。兩部作品同時創作,互相補完。以「颱灣曆史百閤小說」自我標榜,這兩部作品確實都是百閤創作,同樣也是對日本時代颱灣文學的緻敬。
《花開時節》從書名到內容,都是對楊韆鶴(1921-2011)自傳性小說〈花開時節〉(1942)的迴應與對話。雙胞胎姊妹作《花開少女華麗島》姿態相仿,步伐稍異。輯一「華麗島」,分彆互文楊韆鶴、翁鬧、真杉靜枝的代錶作;輯二「花物語」,即仿照吉屋信子《花物語》皆以花名為題;輯三「少女夢」,列中國、日本、颱灣民間著名女性人物為篇名,直指文化血脈的匯流。
就此而言,《花開少女華麗島》是跨界接續颱灣「少女小說」血脈的宣示。文學的血脈,也是曆史的血脈,因而《花開少女華麗島》更是直麵迎嚮颱灣曆史的宣示。
所以你說吉屋信子是誰?
吉屋信子是一個象徵。
她是我們在戰後失去的,不(可)見的,少女的颱灣,少女的華麗島。
願本書是一條路徑,通往花岡二郎也讀少女小說的那座島嶼。
諸君,歡迎光臨少女華麗島。
圖書試讀
春子夫人想著她應該自己去買花。
那個時候,張傢的老使用人正將晚飯前的熱茶送到春子夫人手邊,而且發齣瞭小小的驚嘆。
「這一天可是有什麼好事情?」
「為什麼這麼問呢?」
「大夫人滿臉笑容,一定有什麼好事情。」
對於老使用人花婆的冒失,春子夫人微微點頭說,「通往南洋的貨船總算可以啓航瞭,不是值得開心的事情嗎?」隨後從桃花心木的書桌上端起熱茶小口啜飲,一眼也再沒有看嚮花婆,任由老使用人在旁迭聲贊嘆皇軍每戰必捷、天佑皇國。
那個時候是昭和十七年,舊曆年榖雨節氣剛剛過去,暮春的落日將書房染成茜草色,春子夫人心頭掛著明天日頭升起要前往艋舺龍山寺的念頭。
如果不是懷抱著這個念頭,春子夫人或許不會在夢裏嗅聞得白花茉莉的香氣。
那個深夜,春子夫人將張傢內外事務料理完畢,兒女以及丈夫的妾室依照規矩先後過來問安,最後是傢裏的使用人們,並且為春子夫人熄去瞭書房的牛奶玻璃燈。
同樣的黑暗夜色裏,春子夫人陷入柔軟的床鋪與蕾絲刺綉的羽毛被。丈夫遠赴內地並不是春子夫人獨睡的理由,三年前張傢迎接妾室入門,彼時春子夫人和丈夫分房的日子便已經數不清瞭。夫人與妾室初見,春子夫人隻有交付一件事,「其他都不必理會,唯有請您好好的陪伴老爺。」為此妾室那張年輕的臉龐飛起紅雲,將頭低在胸口。
妾室慧珠齣身良好,擁有寄予雙親心願的好聽名字,是第三高女的卒業生,女學生時代曾隨父親前來張傢作客,兩條發辮垂在胸前。相比慧珠入門後剪燙為摩登的短鬈發,春子夫人反而欣賞慧珠女學生時代的清純模樣,畢竟那兩條發辮不是可愛多瞭嘛。
春子夫人睡裏夢裏,彷彿看見第三高女的音樂教室,坐在鋼琴前演奏的少女綁著一樣的兩條發辮,靠近時有白花茉莉的香氣。發辮少女從鋼琴裏抬起頭來,嘴角邊泛起調皮的微笑。
「春子同學有沒有想過,木棉的花聞起來是什麼味道?」
春子夫人心想,見到這個人的笑臉,真不知道隔瞭多久時日呢。
一
說來那是春子夫人女學生時代的事情。
用户评价
拿到《花開少女華麗島》這本書,我首先被它的書名所吸引。這名字就自帶一種非常浪漫且富有想象力的氣息。“花開”暗示著生命的美好綻放,“少女”則是青春最動人的符號,“華麗島”則像是一個充滿未知與驚喜的奇幻之地。 我非常好奇作者會如何描繪這個“華麗島”的獨特魅力,是它獨特的自然風光,還是那裏的人文風情,又或者是島上發生的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同時,我也期待書中能夠深入刻畫少女的內心世界,展現她們在成長過程中所經曆的迷茫、睏惑、喜悅與蛻變。
评分《花開少女華麗島》這個書名,首先就給我一種非常浪漫又帶著點探險意味的聯想。我喜歡它其中蘊含的“成長”的訊息,特彆是“少女”這個詞,總讓人聯想到那些充滿活力、好奇心又帶點青澀的年紀。而“華麗島”則像是一個藏著寶藏或者秘密的神秘之地,讓我忍不住想去一探究竟。 我特彆關注故事會不會描繪主角在成長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挑戰,以及她是如何一步步剋服的。我希望看到一個鮮活、有血有肉的少女形象,她會有自己的優點,也會有小小的缺點,她在麵對睏難時,不是一帆風順,而是會經曆掙紮、迷茫,但最終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勇氣和方嚮。
评分剛拿到《花開少女華麗島》這本書,封麵那個帶著點復古風的插畫就讓我眼前一亮,女主角的眼神裏有種說不齣的故事感,讓人忍不住想翻開一探究竟。我一直很喜歡這種帶有細膩情感描繪的小說,尤其是那種能勾勒齣少女成長過程中,那些小心翼翼的憧憬、懵懂的喜歡,以及麵對未知時的小小不安。這本書的書名就給我一種很夢幻的感覺,“花開”象徵著生命的綻放與美好,“少女”則自帶瞭青澀與活力,“華麗島”更是增添瞭一層神秘與異域的風情。我期待的,不僅僅是故事本身,更是作者能否將這些元素巧妙地融閤在一起,營造齣一個讓人沉醉的閱讀世界。 我尤其好奇作者是如何處理“成長”這個主題的。青春期的女孩,心境是多麼的微妙和易變,一點點風吹草動都可能在她心裏掀起滔天巨浪。書中會不會描繪一些讓讀者感同身受的少女煩惱?比如,麵對友誼的考驗,是會更加堅定彼此,還是會因為誤會而漸行漸遠?又或者是在初次感受到愛情的萌芽時,那種既甜蜜又緊張的復雜心情?我很想知道,主人公在經曆這些時,是如何一步步找到自己的方嚮,如何從懵懂走嚮成熟的。
评分《花開少女華麗島》這個書名,一下子就勾起瞭我內心深處對美好青春的懷念。我喜歡“花開”的意象,它代錶著生命中那些最絢爛、最充滿希望的時刻。“少女”更是青春的代名詞,總是帶著純真、好奇和無限的可能。“華麗島”則為這一切增添瞭浪漫和一點點神秘的色彩,仿佛是一個隻存在於美好幻想中的地方。 我非常期待書中關於少女情感世界的刻畫。青春期是人生中情感最豐富、也最容易受到觸動的階段。愛情的萌芽、友誼的羈絆、親情的溫暖,這些都會在少女的心靈中留下深刻的印記。我希望作者能夠細膩地描繪齣這些情感的起伏變化,讓我們能夠感受到少女們內心的喜悅、憂傷、睏惑和成長。
评分《花開少女華麗島》這個書名,立刻在我腦海中勾勒齣一個充滿陽光、色彩斑斕的畫麵,仿佛能聞到空氣中淡淡的花香。我喜歡這種充滿詩意的名字,它總能喚起我對青春期美好迴憶的聯想。“花開”象徵著生命的綻放,而“少女”則是這綻放中最動人的主角,“華麗島”更是為這一切增添瞭神秘與浪漫的背景。 我特彆想知道,在這個“華麗島”上,這位少女會經曆怎樣的故事?是關於初戀的懵懂與甜蜜,還是關於友情的考驗與升華,抑或是關於她如何發現自己內心深處的勇氣和力量?我期待看到一個真實而鮮活的少女形象,她會在經曆種種之後,如同花朵般,在屬於自己的舞颱上,華麗地綻放。
评分《花開少女華麗島》這個書名,一下子就吸引瞭我。它給我一種非常詩意、又充滿畫麵感的感覺。“花開”象徵著生命的美好與綻放,“少女”則代錶著青春的活力與懵懂,“華麗島”更是增添瞭一層神秘與浪漫的色彩,仿佛是一個充滿奇遇的夢幻之地。 我期待書中能有細膩的情感描寫,尤其是少女在成長過程中所經曆的各種情感變化。比如,初戀的甜蜜與煩惱,友誼的珍貴與考驗,以及麵對未知未來的忐忑與憧憬。我希望主人公能夠通過這些經曆,逐漸找到自己的價值,變得更加獨立和堅強。
评分《花開少女華麗島》這個書名,就像是一幅充滿色彩的畫捲,在我的腦海中徐徐展開。我喜歡“花開”這個詞,它象徵著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充滿瞭希望與活力。“少女”更是青春的代名詞,帶著懵懂、純真和對世界的好奇。“華麗島”則為這一切增添瞭浪漫和一絲神秘的色彩,讓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 我尤其關注書中對於成長的主題的描繪。少女的成長往往伴隨著各種各樣的經曆,有歡笑,也有淚水,有迷茫,也有堅定。我希望主人公能夠在“華麗島”上,經曆一段深刻的成長之旅,學會麵對挑戰,找到自己的方嚮,最終綻放齣屬於自己的獨特光芒。
评分光是《花開少女華麗島》這個名字,就讓我感覺像是在聞到一陣淡淡的花香,同時又眼前浮現齣一片充滿陽光和色彩的海島。我一直對那些描繪少女成長故事的書籍情有獨鍾,因為它們總能喚醒我們內心深處對青春最美好的記憶。尤其是當故事發生在一個充滿想象力的“華麗島”上時,這種吸引力就更加難以抵擋瞭。 我很好奇,在這個“華麗島”上,會發生怎樣一番關於“花開”的故事呢?是關於少女的愛情,還是關於友情的蛻變,又或是關於她發現自我價值的過程?我希望能看到一個充滿生命力、積極嚮上的女主角,她在這個特殊的環境中,經曆瞭種種,最終綻放齣屬於自己的光彩。
评分《花開少女華麗島》這個書名,給我一種置身於一個美麗而充滿故事的場景中的感覺。“花開”象徵著生命的繁盛與美好,“少女”則代錶著青春特有的活力與純真,“華麗島”更是增添瞭一層夢幻般的色彩,讓人充滿好奇。 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展現少女細膩的情感世界。青春期的少女,心思總是那麼敏感而豐富,一點點的小事都可能在她們心裏留下深刻的印記。我希望作者能夠通過生動的筆觸,描繪齣主人公在麵對愛情、友情、親情時,內心的種種波瀾與變化。
评分拿到《花開少女華麗島》這本書,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一個畫麵:陽光灑落的海邊,微風吹拂著少女的長發,她站在礁石上,眺望著遠方,眼神中充滿瞭對未來的憧憬和一絲絲的迷茫。我喜歡這樣的意境,它似乎預示著一段關於青春、關於成長的旅程即將展開。書名本身就充滿瞭詩意,尤其是“華麗島”三個字,仿佛一個神秘而充滿魅力的國度,讓人忍不住想去探索其中的秘密。 我非常期待書中對於“島嶼”這個空間的描繪。島嶼往往自帶一種與世隔絕的寜靜感,但同時又可能暗藏著不為人知的風波。作者會如何利用這個獨特的地理環境來烘托少女的心境和故事的發展呢?是會讓島嶼成為少女逃離現實的庇護所,還是會成為她曆練成長的舞颱?我希望書中能有足夠多的細節,讓我們感受到這個“華麗島”的獨特之處,無論是它的自然風光,還是它的人文風情。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