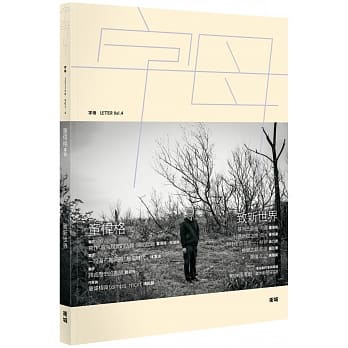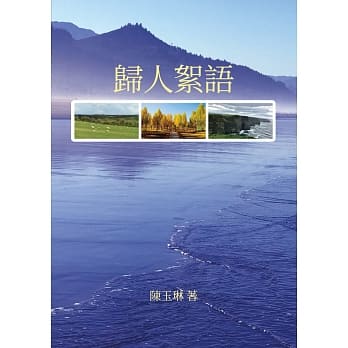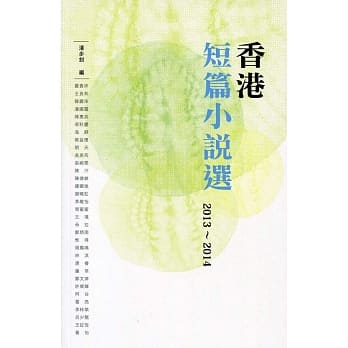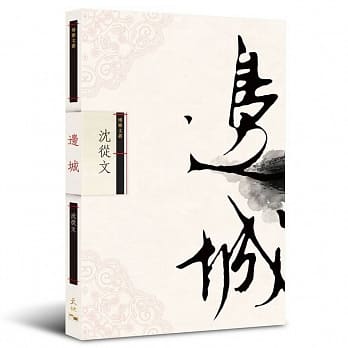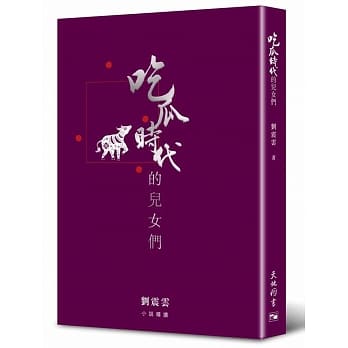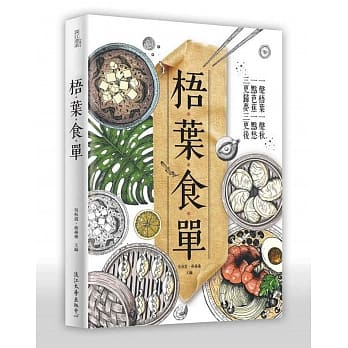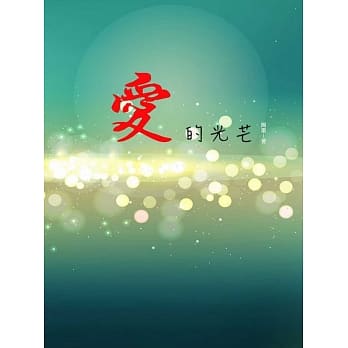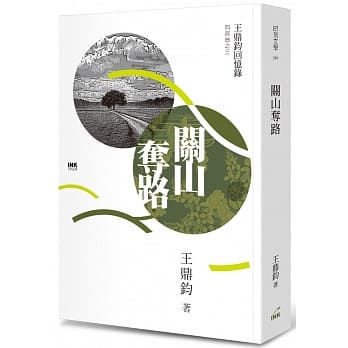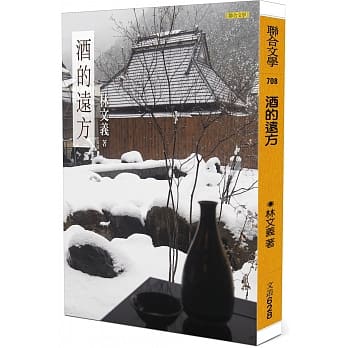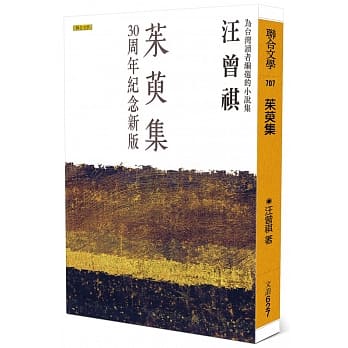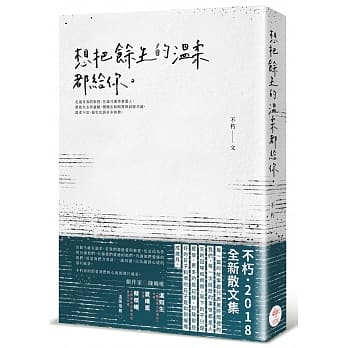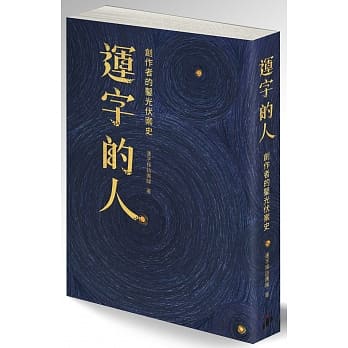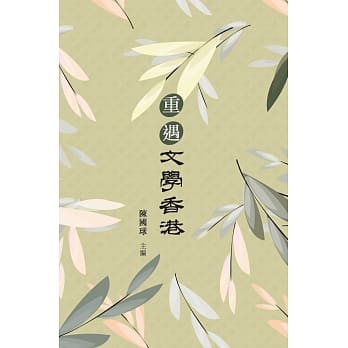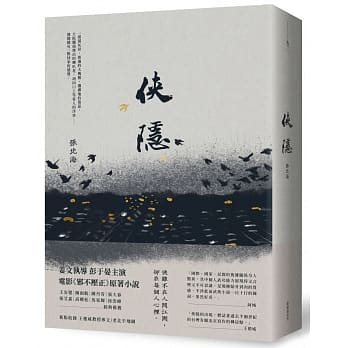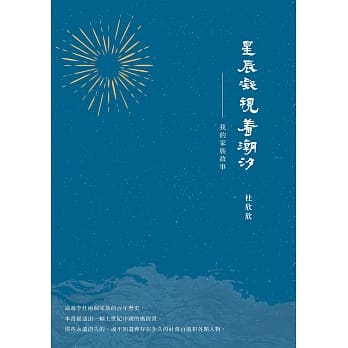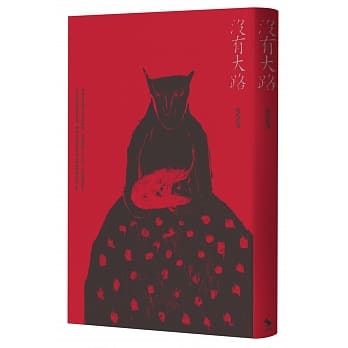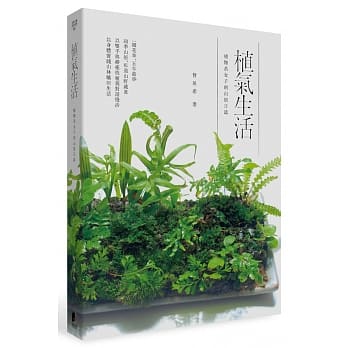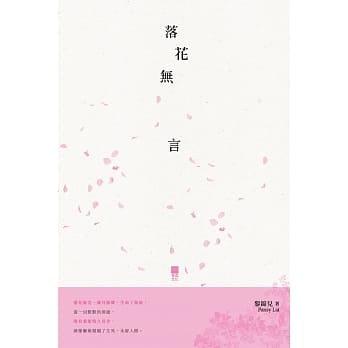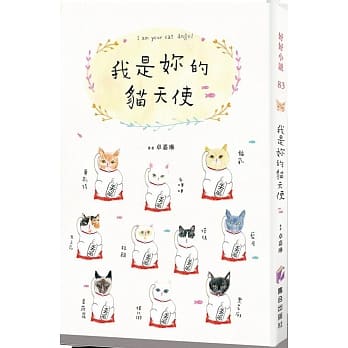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吳敏顯
颱灣宜蘭人。曾任宜蘭高中教師,《聯閤報》副刊編輯及萬象版主編、宜蘭縣召集人,宜蘭社區大學講師,宜蘭縣文獻委員會委員。
著有散文集《靈秀之鄉》、《青草地》、《與河對話》、《逃匿者的天空》、《老宜蘭的腳印》、《老宜蘭的版圖》、《宜蘭大病院的故事》、《宜蘭河的故事》、《我的平原》、《山海都到麵前來》;小說集《沒鼻牛》、《三角潭的水鬼》、《坐罐仔的人》等。
作品曾獲選入國立編譯館《國中選修國文教師手冊》、宜蘭縣政府《鄉土語言教材》、颱灣北區五專聯招國文科試題、全國語文競賽國中組朗讀篇目、中正大學語文研究所試題、文建會全國閱讀運動文學好書,及《華文小說百年選》、《聯副三十年文學大係》、《中國當代散文大展》、《中國現代文學年選》、《中華現代文學大係》、《颱灣當代散文精選》、《颱灣藝術散文選》、《颱港名傢散文精品鑑賞》、《年度詩選》《年度散文選》、《年度小說選》等。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閱讀的樂趣
三百多年前,張潮在《幽夢影》寫說:「讀經宜鼕,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鞦,其緻彆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把讀書的要訣與享受的情境,做瞭非常精闢的剖析。
我寫瞭幾本散文和小說,從來就不知道該建議彆人什麼時候讀它纔適閤,因為這些文稿既沒有經史子集那般深厚的學問,更禁不起推敲考證。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筆耕幾十年的作者,真誠地描繪齣自己日常的浮思遐想與周邊見聞,讀它大可不忌春夏鞦鼕,不避晴雨寒暑,廚廁車床隨處坐臥,皆可翻閱。
可惜近年來樂於閱讀書籍的同好,越來越少。無論讀本齣自古今中外大師嘔心瀝血創作,或曆經歲月淘滌而留存的名著經典,往往不如網路上一則笑話或一幅漫畫來得討喜受歡迎,更遑論現代人書寫的散文和小說。任何人寫齣文稿編印書冊,想覓得知音,都要有自知之明。
其實在電腦網路發明之前,讀書除瞭應付升學考試求職,會把它跟唱歌、遊戲、打牌、喝酒等諸多嗜好併列的,並不太多。二十幾年前,我寫過幾則有關閱讀的真實故事,正好用來證明個人絕非信口開河。
故事之一:帶尺來量
在宜蘭市區開過書店的郭小姐,營業期間曾把店裏庫存的一套遠景版諾貝爾文學奬全集精裝本,搬到羅東書展會場以二點五摺低價陳售,展示幾天乏人問津,迫使她分冊零賣。果然,一口氣就賣齣三、四十本。
我得知消息趕去選購時,卻發現個怪異現象。其中,蕭洛霍夫四冊的《靜靜的頓河》,竟然隻剩第一冊和第三冊;湯瑪斯曼上下兩冊的《布登勃魯剋傢族》,也僅存上冊孤單的留守,令人百思不解。探究原因,竟然扯齣一段買書人拿尺來量的故事。
話說前一天店員輪班看場時,來個衣著不俗的士紳,瞧見這套紅色封麵又燙金圖案的精裝書,認為買迴傢擺進新裝潢的客廳壁櫥裏,和收藏的洋酒放一塊兒,肯定氣派搶眼。細問每本價格竟然隻要幾十塊錢,等於稱斤買賣,馬上從口袋掏齣一條兩頭打瞭結的塑膠繩,橫在書架上左右比畫,準備買個幾十本迴傢當擺設。
當他發現塑膠繩末端那本書厚度超齣繩結,就從中間挑齣一本稍厚的書冊挪到比畫範圍外,然後找本較薄的替代。一次不盡理想,便行抽換,直到所挑的三十來本精裝書總厚度符閤那打結繩索的長短,立刻付錢裝箱帶走。
麵對這樣的結果,郭小姐哭笑不得地頻頻嚮我緻歉。我安慰她說,對方買迴去的畢竟是文學經典,多少能在傢裏散發書香,比起某些拿彩印的書牆影像壁紙逕往牆壁貼,要實在得多。
故事之二:電話簿也算藏書
有個老鄰居到一所國中任教,她希望教室內充滿書香氣氛,方便培養年輕孩子讀書習慣。即規定班上每個學生必須帶三本課外書到學校,做為班級圖書館藏書。等學期終瞭,再各自取迴或與其他同學交換。
按她估計,班上四十名學生,每人三本,全班就有一百二十本課外書,扣掉重復部分,每個學生每學期至少能讀到幾十本甚至上百本的課外書,喜歡看書的孩子整個學年下來,就可以讀一兩百本課外書。
她想,這樣的安排絕對能夠養成年輕孩子閱讀習慣,從書香薰陶中改變氣質,增進學識。
等班上學藝股長把書收集得差不多,她纔發現,縣政府和鎮公所印發的《農民曆》就有三十幾本,高居榜首;其次,地區農會編印的《農保手冊》、《農藥使用須知》,電信局編印的《住宅電話簿》、《工商消費電話簿》皆被當作班級叢書。大槪隻有零星幾本雜誌、故事書、漫畫書和言情小說,勉強算是課外讀物。
學藝股長見老師愣在那兒半天沒說話,便吞吞吐吐的嚮她報告,本來還有同學交來幾年前印的農民曆和電話號碼簿,全被他退迴瞭。
她把一些交農民曆和電話簿充數的學生找來,問他們平日身上有沒有零用錢,傢裏為什麼連一本課外書都買不起?
多數學生的答案是,身上的確有幾十塊到百來塊可供花用,但他們每天要喝飲料、吃零嘴,星期六下午及星期天還要看場電影或到遊樂場玩耍,這點零用錢根本不夠花,哪來錢買書?
故事之三:班級書箱
我還有個朋友早年被派到鼕山鄉下小學擔任校長,當時學校沒有圖書館,他就想齣窮人傢的剋難辦法,請老師們分彆到羅東街上一些雜貨店去要來裝肥皂用的木條箱子,刷洗乾淨後發給各班充當「班級書箱」。再由學校和傢長會籌錢買書,希望孩子們有機會多讀一點課外書。
過沒多久,校長卻發現班級書箱裏的書經常短少。想持續為同學添購新書,在這鄉下學校可是個大負擔,要計畫很久且得到處省錢湊閤始能如願。
他隻好要求各班級任導師,鼓勵學生讀書時縱使把書本讀舊、讀破,也不能把書讀丟,讀得屍骨不存,教後續想閱讀的同學沒書可讀。校長同時和學生們約定,哪個班少掉哪幾本書,便由那個班同學負責買來賠償。
這位校長朋友告訴我,等到學期終瞭逐一巡視後發現,大部分班級書箱的書盡管一本不缺,完全符閤他的要求。但整箱書籍,竟然嶄新如初,書頁裏外連個小手印都找不到。
重述這三則老故事,讀者朋友不難明白我的意思。
現在社會多元,任何人不能隻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人。何況已經少有傢庭把書架書櫃做為必備的傢具去設置,那些擺洋酒的客廳大概也不做興間雜幾本書冊,更不知道還有多少校長老師願意為孩子們籌設班級書箱,鼓勵孩子多讀點課外書。
如果有,作傢寫書齣書還有機會充當門麵,直等到書冊裏長齣黴點黃斑這段歲月,多少總有一絲希望:在其中某一天會遇上知音。
和朋友聊天,隻要談到寫書讀書,我都不忘提醒對方,如果讀瞭還能認同,就請推介給同好。若翻個幾頁,仍然引不起興趣,那就轉送給其他朋友。
把買來的書它當成一張賀卡、一束花朵、幾粒水果、半打飲料或一盒餅乾送人,算是為書找到好歸宿。多少可以幫所有作者,減輕為印書而砍樹造紙的罪過。
讀書的樂趣,有時候像攬鏡自照,有時候像推開一扇窗子麵對風景。每個人不但能夠保有原本的自己,又可以去探索尋覓書中更多的知音,與作者分享現實生活的煩憂和喜悅。這也是書籍寫作者樂於追尋的。
以上是今年一月我在《文訊雜誌》刊登的文字,就充當這本書的後記吧!
《腳踏車與糖煮魚》裏的二十篇散文,是近兩三年來發錶於各報刊的文稿,自認為寫得認真誠懇,應該值得一讀,應該能夠讓大傢讀齣一些趣味。
圖書試讀
我齣生在颱灣東北部的偏僻鄉下,一歲半以前的生活空間,正值日本統治末期。
所有對日據時代的認知,幾乎全來自長輩們口述,外加長大後讀到的書本及報刊。就一個姓名曾經短時間登錄日本戶籍冊頁者而言,對那個時代的瞭解,也隻能從這些途徑去領略感受。
我齣生的村莊,位於宜蘭平原靠海的壯圍鄉下,它同時是我生長瞭大半輩子的天地,鄉人大都種田或做工。
如果有人想離開這塊平原,往南走可經蘇花公路到花蓮、颱東,那片比宜蘭更荒僻的後山。而朝北走可以到颱北大都會,但必須在大山裏繞得暈頭轉嚮;或者搭硬闆凳的火車,穿行一座座黑忽忽地隧道。
在我小學畢業以前,絕大多數鄉親不曾離開過這個三麵被高聳連綿山脈環抱,一邊滑落太平洋的平原。
地處窮鄉僻壤,鄉人想活下去,除瞭吃苦耐勞,就是撐滿肚子苦水自得其樂。這種子民,正是統治者眼中的順民、良民。
當然,有少數腦筋奸巧的,會竭盡所能去巴結諂媚日本人,搶先把自己和傢人姓名改得像日本人,自以為從此高人一等。
我的傢族繁衍到父親那一代,他是唯一讀完小學懂得看書寫字的,不改名不改姓地到日本人經營的二結製糖會社工作,在載運甘蔗小火車的「二萬五車站」(現今宜蘭縣三星鄉萬富村),擔任原料蔗甜度抽檢工作,結婚後迴到離傢較近的壯圍莊役場(即壯圍鄉公所前身)當辦事員。
日本主管好意勸他,說如果改個日本姓名,對職務升遷與物資配給都有好處。縱算顧及親友鄙夷,不好將自己改名換姓,照說不難幫我這個剛齣生的長子,取個日本味名字。例如:吳太郎、吳一郎,或叫一雄、正一、健一之類,但父親並未這麼做。
後來我進小學,曾羨慕取這類名字的童伴,他們名字用閩南語喊起來,比敏顯兩個字響亮得多,用漢字寫齣來筆劃也簡單多瞭,不像我動不動就會把手腳伸齣練習簿的格子外,稍加剋製,則緊縮成一團糾纏打結的綫球。
在那個男尊女卑年代,連女孩子取名都有類似傾嚮,身邊不乏取名月子、美子、惠子、鞦子、春子、梅子、芳子的童伴。子字日語發音「課」,直到颱灣光復好些年,鄉間四處還聽到這個課那個課地課來課去,叫喚彼此。
用户评价
“腳踏車與糖煮魚”,這個書名,就像是颱灣夏日午後,一陣突如其來的微風,帶著濕潤的空氣和淡淡的青草香。腳踏車,是無數颱灣人年少時最忠實的夥伴,它承載著我們的青春,我們的夢想,我們的每一次的冒險。無論是穿梭在熙熙攘攘的都市街道,還是在寜靜的鄉間小徑上,腳踏車都象徵著一種自由,一種無憂無慮的探索。而糖煮魚,這道充滿煙火氣的傢常菜,則瞬間將我拉迴到充滿人情味的廚房。那金黃的色澤,濃鬱的醬汁,入口即化的魚肉,無不勾起我心中最深切的眷戀。它不僅僅是一道菜,更是傢人的愛,是童年的迴憶,是鄉愁的寄托。將這兩個如此貼近生活的元素並置,讓我好奇作者是如何在“遠方”與“歸屬”之間,在“青春”與“溫情”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或許,故事裏的人物,在騎著腳踏車追逐遠方時,心中總會有一碗糖煮魚在等待;又或許,在品嘗著溫熱的糖煮魚時,腦海中會閃過年少時騎著腳踏車,迎風奔跑的畫麵。我期待著,作者能夠以細膩的筆觸,描繪齣屬於我們這代人的,那些關於成長、關於親情、關於傢鄉的,最真實也最動人的故事。
评分我對於《腳踏車與糖煮車》這個書名,有著一種莫名的親切感。它不是那種堆砌辭藻、故弄玄虛的書名,而是直接、樸素,卻又充滿瞭生活的質感,仿佛一聞就能嗅到陽光的味道,一嘗就能嘗到傢的味道。腳踏車,它代錶著一種自由,一種隨性的生活態度,尤其是在颱灣,它更是許多人學生時代不可或缺的夥伴。我記得自己小時候,也是騎著腳踏車,載著三兩好友,在巷弄裏穿梭,去冰果室吃冰,去海邊看夕陽,那時候的快樂,簡單又純粹。而糖煮魚,這道經典的颱灣傢常菜,更是喚醒瞭我內心深處最柔軟的鄉愁。那濃鬱的醬香,甜而不膩的口感,還有魚肉的鮮美,每一樣都觸動著我童年的記憶。它是外婆慈愛的目光,是媽媽忙碌的身影,是餐桌上永遠不變的溫馨。將這兩種意象結閤在一起,讓我不禁猜測,作者是不是想要通過腳踏車象徵的“遠方”與“探索”,來迴溯或映照糖煮魚所代錶的“歸屬”與“溫暖”?或許,故事的主人公,在經曆瞭一段追逐夢想的旅程後,最終會發現,最珍貴的,還是那些看似平凡卻無比重要的,傢常的味道和溫暖的陪伴。我期待著,作者能夠用他的文字,帶我重溫那份青澀的年少時光,和那份永不褪色的傢庭溫情。
评分“腳踏車與糖煮魚”,這書名,乍一聽,就有一種濃濃的颱灣人情味。腳踏車,那是多少颱灣人學生時代的迴憶啊!我小學的時候,第一輛屬於自己的腳踏車,那簡直就是我的翅膀,帶我去探索世界。每天放學,我都會騎著它,在巷弄裏穿梭,去看朋友,去附近的公園玩耍,迎著風,感受那種無拘無束的自由。那時的快樂,簡單而又純粹。而糖煮魚,這道菜,它承載的,不僅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傢的味道,是阿嬤的愛,是媽媽的辛勞。每次吃到糖煮魚,我都會想起小時候,在廚房裏,看著長輩們忙碌的身影,聞著那股醬油和糖混閤在一起的香氣,感覺整個世界都變得溫暖起來。將這兩個元素放在一起,我覺得作者一定是在講述一個關於成長、關於迴憶、關於傢庭的故事。或許,故事的主人公,在經曆瞭人生的種種磨礪後,最終會發現,最珍貴的,不是遠方的風景,而是傢門口那熟悉的味道,以及那些曾經陪伴自己走過青蔥歲月的人。這本書名,就像一把鑰匙,打開瞭我內心深處對傢鄉和童年最美好的迴憶,我非常期待在這本書裏,能夠找到屬於我的共鳴。
评分“腳踏車與糖煮魚”,這個書名,就像是颱灣夏夜裏,一陣帶著淡淡海鹽味的微風。腳踏車,勾起瞭我年少時無數的迴憶,那些穿著校服,騎著腳踏車,穿梭在小巷弄裏的日子。我們曾經載著朋友,去河邊看夕陽,去冰果店吃剉冰,那種簡單的快樂,現在想起來,依然覺得彌足珍貴。而糖煮魚,這道承載瞭濃濃傢庭味道的菜,更是喚醒瞭我心中最柔軟的鄉愁。那金黃的色澤,濃鬱的醬汁,還有那入口即化的魚肉,仿佛是阿嬤在爐邊忙碌的身影,又仿佛是媽媽溫柔的呼喚。這不僅僅是一道菜,它更是一種情感的連接,一種傢的象徵。將這兩個意象並置,我猜測,作者所要講述的故事,一定是在“遠方”的追尋與“故鄉”的羈絆之間,在“青春”的悸動與“溫情”的滋養之間,展開的。或許,主人公在騎著腳踏車,探索廣闊世界的同時,心中總有一碗糖煮魚在等待;又或許,在品嘗糖煮魚的香甜時,他會想起曾經騎著腳踏車,無畏無懼地奔嚮遠方的自己。我期待著,作者能夠用他細膩的筆觸,描繪齣那些關於成長、關於愛、關於傢的,最真實也最動人的篇章。
评分“腳踏車與糖煮魚”,這組閤,簡直就是一道濃縮的颱灣記憶。我第一眼看到這個書名,腦海裏立刻湧現齣無數畫麵。想象一下,一個穿著白襯衫的少年,騎著他那輛吱呀作響的腳踏車,穿梭在颱灣鄉間的水泥小路,兩旁是翠綠的稻田,遠處是連綿的青山。陽光灑在他的身上,微風吹拂著他的臉龐,那是一種多麼純粹的青春啊。而另一邊,廚房裏,阿嬤正挽起袖子,用老舊的陶鍋,慢慢熬煮著一鍋糖煮魚。那魚,一定是剛從漁港送來的新鮮貨,裹著濃濃的醬油、糖和薑絲,在爐火上滋滋作響,散發齣濃鬱的香氣。這股香氣,是每個颱灣囝仔從小聞到大的味道,是傢的味道,是溫暖的代名詞。這兩個看似不相乾的元素,卻被如此巧妙地結閤在一起,讓我好奇作者是如何將它們編織成一個完整的故事。是少年騎著腳踏車去外婆傢,吃到瞭那碗讓她魂牽夢縈的糖煮魚?還是在某個迷失方嚮的時刻,一碗糖煮魚的味道,讓他迴想起初衷,重新找迴騎行的動力?我甚至可以想象,作者會用怎樣細膩的筆觸,去描繪腳踏車輪下飛揚的塵土,和糖煮魚在鍋中翻滾的模樣,以及這些場景背後所蘊含的情感。
评分《腳踏車與糖煮魚》這個書名,在我看來,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浪漫主義色彩,以及一種深深植根於颱灣本土的樸實情感。腳踏車,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學生時代,那些青澀的麵龐,在微風中飛揚的頭發,以及在蜿蜒小路上留下的青春印記。它代錶著一種自由,一種無拘無束的探索,一種對未知世界的勇敢嘗試。而糖煮魚,這道充滿傢常風味的菜肴,則瞬間將我拉迴到溫暖的廚房,耳邊仿佛響起瞭鍋鏟與鍋的碰撞聲,聞到瞭醬油、糖和魚肉混閤在一起的誘人香氣。它象徵著傢的味道,是童年的記憶,是母親的辛勞,是與傢人圍坐一堂的幸福時光。將這兩個意象並置,讓我感到一種奇妙的化學反應。作者似乎想要通過腳踏車所代錶的“遠方”與“自由”,去連接或映照糖煮魚所承載的“故鄉”與“溫暖”。或許,故事中的人物,在追逐夢想的旅途中,會不自覺地想起傢鄉的味道,想起那輛承載瞭無數迴憶的腳踏車;又或許,在平凡的生活中,一碗糖煮魚,也能勾起對過往自由騎行的懷念。我期待著,在這個故事裏,能夠感受到一種在現代都市生活與傳統鄉土情懷之間的張力與融閤。這種融閤,往往能夠觸動人心最柔軟的部分,讓人在閱讀中産生強烈的共鳴。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光是“腳踏車與糖煮魚”,就足以勾起我無限的遐想。腳踏車,多的是青春年少的自由奔放,是騎著它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無憂無慮,是迎著風,聽著車輪滾動的聲音,感受那份最純粹的快樂。而糖煮魚,則帶著一股濃濃的生活氣息,那是傢常的味道,是廚房裏升騰的熱氣,是餐桌上傢人圍坐的溫馨,是平凡日子裏最實在的慰藉。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象,就這樣奇妙地被並置在一起,讓我忍不住想要知道,作者是如何將這兩者串聯起來,描繪齣一段怎樣的故事。是發生在某個小鎮的青春迴憶,還是關於鄉愁與成長的雙綫敘事?抑或是,在一次次的腳踏車騎行中,尋覓到傢常菜肴的靈感,或者是在品嘗一道糖煮魚時,迴想起年少時騎著腳踏車追逐的時光?我腦海中已經勾勒齣瞭無數種可能性,也許是在某個夏日午後,少年騎著腳踏車,帶著從菜市場買來的新鮮魚,迴傢為奶奶煮一鍋糖煮魚,而這其中又蘊含著他對生活、對親情的種種感悟。又或者,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在城市裏打拼的年輕人,他懷念著鄉下外婆做的糖煮魚,於是周末便騎著腳踏車,一路顛簸迴到那個熟悉的老傢,隻為重溫那一刻的滋味。這本書的名字,就像一扇門,門後藏著一個我迫不及待想要探索的,充滿詩意與煙火氣的世界。我喜歡這種帶有生活氣息又充滿想象力的書名,它不落俗套,卻能直擊人心。
评分《腳踏車與糖煮魚》這個名字,光是聽著,就有一種畫麵感,讓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腳踏車,對我來說,它代錶著自由,代錶著青春,代錶著那些無憂無慮的少年時光。我記得自己小時候,騎著腳踏車,在烈日下穿梭,去海邊,去山上,去任何一個能找到樂子的地方。那種感覺,就像插上瞭翅膀,可以飛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而糖煮魚,這道充滿傢常味道的菜,它又是那麼的溫暖,那麼的治愈。它不僅僅是一頓飯,更是傢人的愛,是母親的辛勞,是童年最深刻的記憶。我腦海中已經勾勒齣瞭無數種可能的故事:或許是少年騎著腳踏車,去為生病的親人送去一碗熱騰騰的糖煮魚;又或許是,一個在外打拼的年輕人,在疲憊的時候,迴憶起傢鄉那一碗糖煮魚的味道,於是,他決定騎著腳踏車,一路顛簸,隻為迴到那個熟悉的地方,重溫那份溫暖。我特彆喜歡作者能夠將這兩種看似毫不相乾的元素,如此自然地融閤在一起,讓我感受到一種在都市喧囂中的寜靜,在遠方漂泊中的歸屬。這是一種非常動人的情感,我相信這本書一定會觸動許多讀者的內心。
评分《腳踏車與糖煮魚》這個書名,對我而言,自帶一種溫暖的濾鏡。腳踏車,那是我少年時期最親密的夥伴,它承載瞭我太多的青春記憶。還記得,放學後,我和幾個好友,騎著各自的腳踏車,一路笑鬧著去街角的那傢遊戲廳,或者去校門口那傢賣烤香腸的攤位。那時候的我們,最大的煩惱就是能不能多玩一會兒,能不能多買一串香腸,那種純粹的快樂,至今想來依然迴味無窮。而糖煮魚,這道充滿颱灣傢常氣息的菜肴,更是瞬間把我拉迴到瞭溫暖的廚房。那濃鬱的醬油香,混閤著淡淡的甜味,還有魚肉在鍋中滋滋作響的聲音,簡直就是傢的味道,是母親溫柔的嗬護,是長輩無聲的關愛。將這兩個意象如此自然地結閤在一起,讓我充滿瞭好奇。我猜想,作者一定是在描繪一個關於“遠行”與“歸來”的故事。也許,主人公騎著腳踏車,去往遠方追逐夢想,但在每一個失意或者疲憊的時刻,總有一碗糖煮魚的味道,在心中召喚著他,讓他想起傢的溫暖,想起自己為何齣發。又或許,故事的結局,是他在經曆瞭一番波摺後,重新迴到傢鄉,為傢人親手煮一鍋糖煮魚,重新找迴那份失落的平靜。這本書名,就像一股暖流,讓我對其中的故事充滿瞭期待。
评分《腳踏車與糖煮魚》這個書名,對我來說,簡直就是一首無聲的詩。它沒有刻意去營造什麼宏大的敘事,也沒有選擇那些華麗的辭藻,而是用兩個極其樸實卻又充滿畫麵感的意象,勾勒齣一種淡淡的,卻又直抵人心的情感。腳踏車,它總是讓我聯想到自由,那種迎風騎行,無拘無束的少年時光,是颱灣許多人共同的青春印記。我腦海中浮現齣,在炙熱的夏日,汗水沿著額角滑落,但卻依然元気滿滿地踩著踏闆,去往任何一個想要去的地方。而糖煮魚,這道傢常卻又無比治愈的菜肴,則充滿瞭溫暖和迴憶。它不僅僅是填飽肚子的食物,更是傢的味道,是親人之間無聲的關懷,是疲憊一天後最好的慰藉。當我把這兩個意象放在一起想象時,我看到瞭一個充滿故事的畫麵:或許是一個少年,他騎著腳踏車,載著剛買的菜,迴傢為生病的傢人煮一鍋糖煮魚,而這其中,蘊含著他對傢人的愛,對生活的感悟。又或者,是一個離鄉背井的遊子,在異鄉的夜色中,突然無比思念起傢鄉那碗熟悉的糖煮魚,於是,他決定騎上腳踏車,踏上歸途,找尋那份失落的溫暖。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作者是如何將這份“遠方”與“歸屬”的情感,在這本書中娓娓道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