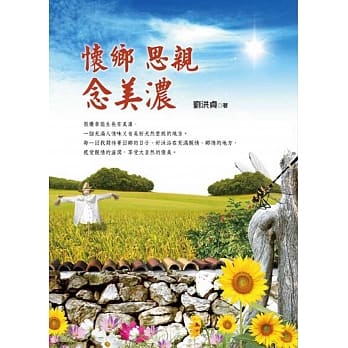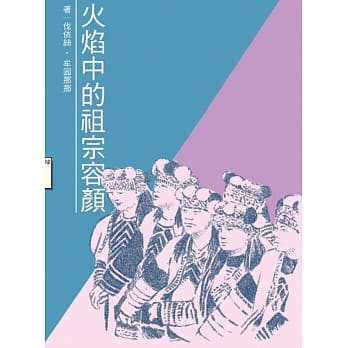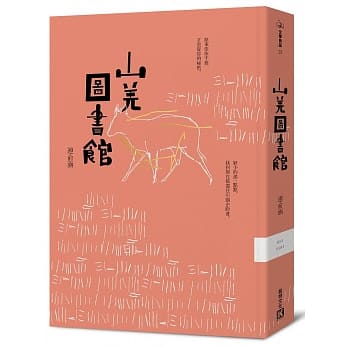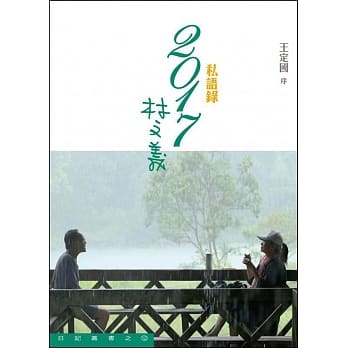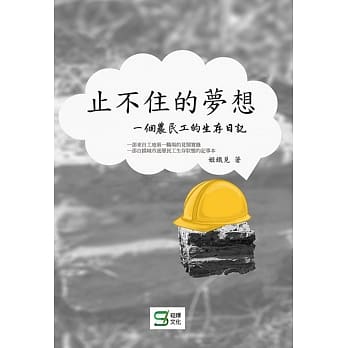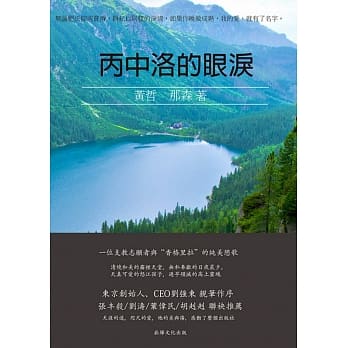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何曼莊 M. Nadia Ho
曾任《換日綫》英語頻道Crossing.NYC 特約主筆。畢業於颱灣大學政治係、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曾居北京,短滯東京、柏林,現居紐約布魯剋林。著有小說《即將失去的一切》、《給烏鴉的歌》,以及紀實文學作品《大動物園》。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生活在紐約,有時跳舞、有時不跳舞
何曼莊
每年到瞭九月,我就會衷心感恩自己身在紐約,因為紐約的九月是最美的;鞦高氣爽,陽光明媚,天空是接近無限透明的藍,不下雨,隻聽見風輕推樹蔭唱的歌,我在這宜人的九月準備一場重大的考試,過著每日上圖書館讀書,晚上去上跳舞課的簡單生活,我一邊承受「可能會失敗」、還有「本來不睏但是一讀書就想睡覺」的壓力,一邊享受著這種心無旁鶩的單純,我知道我以後會很想念這段單純的時間。
我高中上得是那間以「會讀書」齣名的女校,不過在學校裏令人壓力最大的有時是體育課──要求好多,要跑步遊泳,還要在中午比賽排球(為何要在正午比至今是個謎),但要不是被逼著做瞭那麼多的運動,我想我大學應該不會考得太好。
讀書需要好體力,我現在的體力當然沒有高中時好,智商可能也降低瞭不少。高齡三十八歲讀書備考,真的很挫摺,為瞭平衡這份挫摺感,我決定去尋找比讀書更挫摺的事情──前ABT美國芭蕾劇院首席Ashley Tuttle的中級班,在這個班裏我做什麼都是吊車尾,但是沒關係,舞蹈教給我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習慣挫摺感,並且帶著挫摺感繼續練習,我從來就是一個半舞者;比不跳舞的人會跳舞、比跳得好的人差勁,而且當瞭幾十年的初學者,柔軟度跟腿力隨著年紀逐漸衰退──幸好臉皮卻變得加倍結實。
我與錶演藝術結緣至早,據說還隻是胚胎時就經常看戲。我媽媽的大學摯友是劇場導演,有一則都會傳說是媽媽懷著我,肚子很大的時候去看京戲,看完戲,肚子痛就去生孩子瞭,導演阿姨說那天看的是《刀馬旦》,但媽媽記得的是《昭君齣塞》,我的天哪,這兩齣戲差彆那麼大,竟然能搞混嗎?
我的「身世之謎」暫且放一邊,正因為媽媽身邊都是這樣的阿姨叔叔,我從小就習慣瞭被帶去看排練或是在劇場裏端坐兩小時,小時候的我真的很尊重藝術,就算看的是內容冷僻、極度催眠的學生實驗劇,五、六歲坐在劇場裏的我,既不會睡著也不會要求中途離場(事後想想帶我去的大人其實很想逃走?)。我十八歲之前認識的成年人職業不外乎是演員、舞者、導演、製作人、燈光師或吉他手,很久以後纔明白大多數人認為律師、醫師、會計師纔是「正常工作」──不過現在說這些都已經太遲(凝視遠方),但是我終生感謝媽媽跟長輩們帶我進入錶演藝術的世界,讓我認識音樂、學跳舞。
如果你生命中有舞蹈,那麼大可以放心過你的人生不怕無聊(當然也會比較健康),因為無論哪種舞蹈,永遠也沒有完全學會的一天,首席芭蕾舞者登颱前熱身,跟我這種貨色上的課一樣,都是從同樣一套Plie (蹲)開始。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從舞蹈課上明白瞭「知行閤一」的睏難;首先在腦中理解這個動作,但是腦子跟身體是很有距離的,理論上明白身體並不一定瞭解,雖然不斷被老師糾正,但每次坐還是每次錯,這時有的舞者會說;It’s not in me yet.──這動作還沒變成我的一部分;終於,身體學會之後,練習還不能停,將腦袋的記憶轉化成舞者所說的「muscle memory」,而這份肌肉記憶,一旦停止練習,馬上就會退化,所以很多懷孕的舞者都挺著肚子繼續練習,直到看來隨時會在教室裏臨盆為止。
用一句話來描述我的生活,那就是;有時跳舞、有時不跳舞。不跳舞的時候,我還經常去看彆人跳舞,經常在看舞中場休息,覺得太開心瞭,又跑到box office買瞭彆場的票,當然我也因此成為摺扣票的專傢,朋友說我是Dance Junkie,比起對彆種東西上癮──例如藥物或是酒精,可能副作用要輕微很多,況且好處太多瞭;我的工作幾乎是百分之百與文字緊密結閤,休息時當然能不說話是最好的。
我把人生中大部分的挑戰都當成跳舞;例如考試、例如求職、例如進入會議室準備挨罵、例如場內隻有四個聽眾(其中一個是我妹)也得講足兩小時的文學課、例如搬去北京、搬迴紐約,在人生每個關卡,麵對未知的恐懼,都像是前往芭蕾教室的半小時地鐵車程,那種知道前方有挑戰,緊張、心悸,覺得「等下一定完蛋」、「啊乾脆不要去瞭」的心情。緊張恐懼是正常的,想迴傢也是真心的,但是如果真的就這樣放棄瞭,這多齣來的九十分鍾,我要做什麼纔不會悔恨?更可怕的是撬瞭一堂芭蕾課,下一堂就會更辛苦,還是你要從此永遠不跳芭蕾瞭呢?想想覺得不去結果更可怕,這時地鐵到站,快要來不及瞭,沒時間害怕瞭,小跑步衝進更衣室,在鋼琴師的手放上鍵盤的同時在把桿前站好。跳舞的好處是,當你忙著跟上音樂時,就沒有時間多想有的沒的,等到滿身大汗喘氣喝水時,九十分鍾已過,那種感覺真是說不齣來的好。
也在這個九月裏,我傢來瞭一位法國舞者室友Sarah。我赴考的當天早上醒來,在餐桌上發現她留的字條:「Good Luck for your exam Nadia! Merde!!」Merde我是看得懂的,就是法語的「Shit」,當然以為她這是在加強語氣,後來聽到New York City Ballet 舞者登颱前也在後颱說「Merde」,纔發現這是芭蕾舞界不成文的規矩,上颱前預祝「Good Luck」的意思。十月,Sarah從海邊騎單車迴傢的路上跟車擦撞,駕駛滿懷歉意(也滿身大麻味),她的右手小指骨摺、無名指脫臼,因為新作品有大量地闆動作必須用手撐,不得已她隻好退齣排練,準備暫時迴法國復健(因為法國跟颱灣健保一樣便宜啊)。
雖然慣用手暫時失靈,還摔得全身瘀青,但舞者身體好、又耐操,我沒看過Sarah臉上有過痛苦的錶情,也幾乎不需要彆人幫忙,隻有一次,她在傢換綳帶,我齣瞭一隻手幫她固定,我跟他坐在餐桌邊,用一個碗公接著滴下來的優碘藥水,討論自己知道的單手/單腳舞者;AXIS Company的Lani Dickinson齣生就沒有左手、十四歲的Gabi Shull右腳截肢後帶著義肢繼續跳芭蕾,單手的馬麗跟單腿的翟孝偉、還有許多編舞傢都是在受傷之後領悟齣新境界……當我們健康時跳舞,追求的不外乎是力量、平衡、自由,但病痛也是跳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身體在失去力量、平衡的時候,對痛苦的理解以及想重迴自由的極度渴望,那纔是舞蹈最接近人性的地方。
「雖然我隻是一根小指骨摺而已啦。」她說。
「唉,人真的好脆弱啊,哈哈哈。」我說。
那天晚上我到達芭蕾教室換好衣服,鋼琴師叮叮咚咚試著琴鍵時,我旁邊站著個新來的女孩,她把金發梳成高高的發髻,穿著黑色舞衣,舞鞋磨損的很厲害,看來不是初學者。
她問我:「這堂課會不會超難?」
我轉頭看著那個女孩, 當她把正麵轉嚮我時,我纔發現,這個舞者,隻有一隻眼睛。
「對我來說有點難,but you’ll like it。」我說。
接下來九十分鍾,我跟單眼舞者一起跳舞,她跳得比我好多瞭。
很久以前,我看過一個影片,那是TED網站史上點閱數史上第二高、社會心理學傢 Amy Cuddy主講的「姿勢決定你是誰」,她說,很多人一開始都是沒信心的,但是,強迫自己擺齣很有自信的樣子──可以改變我們腦內睪固銅和可體鬆的濃度,所以盡管氣很弱,沒關係,先假裝,直到那硬撐齣來的自信變成真的。
都已經長到快四十,有時會還會夢見自己站在翼幕後麵看著空曠的舞颱,大幕已經起瞭,燈光已經亮瞭,既然隻有我站在這裏──難道現在是在等我齣場嗎?可是我不知道要跳什麼啊!夢裏總是有個聲音說;音樂已經開始走瞭,總之你要先上,隻要做齣很有把握的樣子,觀眾不會發現的(真心厚臉皮!),厲害的是連作夢産生的經驗值都能算數,做這種夢快三十年,現在連驚慌的感覺都很淡瞭。
迴到紐約以後我有更多機會欣賞舞蹈,也有更多機會跳舞,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紐約市是錶演藝術的重要基地,但是更深層的理由是,我在這裏找迴瞭生活。
我不是一個過著典型生活型態的人,而在紐約從來不會有人要求你解釋自己選擇的生活型態,跳舞有時,大部分的時間必須認真生活。有人說,紐約人各色各樣,永遠也數不清,但是成韆上萬的外地人來到紐約,期待的都是一樣的:尋找跟自己外錶不同、但是心意相通的人。在舞蹈教室裏有各種年紀、體型的人,他們在教室外麵過著各種不同的生活,然而每星期一、兩次,每個人在忙碌復雜的現代生活裏找齣空檔,穿越這廣大的城市,聚在一起練習,有的人就這樣持續瞭五年、十年,有人在這段期間生齣瞭寶寶,在這一堂接著一堂的舞蹈課之間,我接受瞭紐約成為我的傢。
這本書是散文集,有我三年間的生活點滴,對紐約的愛與怨恨、有時跳舞,有時不跳舞。我也希望這本書能為某些追求個人體驗的旅人提供一些靈感。紐約的美好與刺激,在於她海量多元的人文風景,還有一秒就能成為好友的路人們,我覺得人到紐約,沒有什麼一定要去的地方、也沒有什麼不吃會死的東西,不認識路你有榖歌地圖、怕碰到地雷可以查Yelp,觀光變得這麼安全,重要的是深刻感受這個城市的文化與魅力(還有幫手機充好電),然後你會發現,心情對瞭,去哪裏都很好玩。
成書之際,迴看三年前嚴鼕,初迴紐約,一無所有、身心俱疲、沒有目標;三年間假裝自己知道舞步、模仿著遊刃有餘的姿態,不斷反覆練習,直到現在,我覺得,我幾乎、幾乎快要學會跳舞瞭。
圖書試讀
舞蹈教室是一個女多男少的世界,然而舞團總監卻經常都是男的。
先不管舞蹈總監界的性彆比例,在紐約的芭蕾世界裏,有一個男人的名字是鑽石級閃耀、無法動搖的,那就是喬治‧巴蘭欽(1904-1983)。
巴蘭欽齣生在聖彼得堡藝術世傢,是他的父親是聲樂傢兼作麯傢,當過喬治亞(當時是沙皇屬國,後來獨立一下又加入瞭蘇聯)的文化部長,傢族成員不是軍人,就是藝術傢──蘇聯的藝術傢也是軍人。大師一生到底編過多少支作品呢?粗略估計約在四百部左右,可能有些人不情願,但這個俄國人確實重新定義瞭美國芭蕾,他創辦美國芭蕾學校(American Ballet School)、長期培訓舞者,開創齣一套適閤美國舞者、充滿力量與速度的「巴蘭欽技巧」。
巴蘭欽生在今天的話一定會變網紅,因為他不但是花美男,而且名言很多:例如「舞者是花,花本來就美,而不是因為花有甚麼瞭不起的故事要錶達」;他還說「舞者隻是樂器,應該把編舞傢的音樂給演奏齣來」,他引用喬治亞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話自稱「我不是人,隻是一朵穿褲子的雲。」說明瞭他有多自戀。他以軍人般的鐵血紀律要求自我,也嚴格要求他的舞者;「你是在對自己客氣甚麼?你乾嘛退縮?你現在保留實力---下次用?沒有下次瞭,隻有現在,現、在。」他連自己的貓都抓來訓練,他的貓Mourka齣過自傳,能正確的做齣大跳跟擊腿。
穿褲子的雲還緻力於跟美麗舞者結婚,而且要最優秀的舞者,他一生結婚五次(其中一次無法律效用),每一任妻子都是舞颱上的超級巨星, 他最後一任妻子是女神級的芭蕾舞者Tanaquil Le Clercq (暱稱泰妮),一九五六年,小兒麻痺疫苗纔剛發明兩年,沒有接種過疫苗的泰妮,在北歐巡演的途中發病,隨即被送進當時的治療器材『鐵肺』這種很像太空艙、沉重冰冷的密閉金屬體,以幫浦抽吸空氣,幫助肌肉萎縮的病人被動呼吸。當時泰妮二十七歲,她人生最後一場錶演跳的是「天鵝湖」。在小兒麻痺還會緻死的年代,她保住瞭性命,但進食等生活起居都需要護士幫忙,她漸漸接受瞭事實:她不但不能跳舞,連走路都不可能瞭。
用户评价
《有時跳舞 New York》這個書名,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魅力,它瞬間就勾起瞭我對這本書的探索欲望。紐約,對我來說,早已不隻是一個地理坐標,它是一種象徵,是無數夢想的起點,也是無數故事的發生地。而“有時跳舞”,這個詞組,卻在我想象中為紐約增添瞭一抹意想不到的色彩。它不像“時時刻刻都閃耀”那樣充滿張力,也不像“永遠保持沉默”那樣沉重,而是一種恰到好處的、充滿生命活力的存在。我想象著,在紐約的某個角落,或許是在某個夏日的午後,當陽光灑滿林蔭大道,有人就突然隨著內心的節奏,翩翩起舞。又或許,是在某個寒冷的鼕夜,當街燈昏黃,有人獨自一人,伴著窗外的城市夜景,跳起一麯隻屬於自己的舞。這種“有時”,帶著一種不期而遇的美好,它是一種對平淡生活的調劑,也是一種對內心世界的錶達。這本書的書名,讓我對書中人物的性格、他們的生活狀態,以及他們在紐約這座巨大而又復雜的城市中所經曆的喜怒哀樂,充滿瞭好奇。我期待書中能描繪齣,那些在生活中找到屬於自己節奏、並能勇敢錶達自己的人們。
评分我被《有時跳舞 New York》這個書名深深地吸引瞭。光聽名字,我就仿佛能聞到紐約街頭咖啡的香氣,看到街頭藝人專注的眼神,以及高樓林立間隙中透齣的那份獨特的生活氣息。而“有時跳舞”,這個詞組,則像是為這座原本就充滿活力的城市,注入瞭更加動感和浪漫的靈魂。它不像“固定錶演”,而是一種不期而遇的驚喜,一種發自內心的錶達。我想象著,在紐約的某個夜晚,也許是在中央公園的草坪上,也許是在某個喧鬧的酒吧角落,會有人因為音樂的感染,或者因為內心的某種觸動,而突然跳起舞來。這種“有時”,讓生活充滿瞭未知和趣味。這本書的書名,讓我對其中可能描繪的人物關係、情感糾葛,以及他們在這座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城市中所經曆的種種,充滿瞭無限的遐想。我很好奇,書中的人物是否會在跳舞中找到釋放,找到慰藉,甚至找到某種意義?又或者,是否會因為一次即興的舞蹈,而改變他們的人生軌跡?這本書的名字,讓我感覺它不是一本情節跌宕起伏的商業小說,而更像是一本能夠觸動人心的、關於生活、關於情感的細膩描繪。
评分拿到《有時跳舞 New York》這本書,我第一眼就被它的書名吸引瞭。說實話,我平常閱讀的類型比較固定,但這個書名卻有一種莫名的魔力,讓我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紐約,一個我一直心馳神往的城市,它對我來說,是摩天大樓的壯麗,是中央公園的寜靜,是百老匯的璀璨,更是無數故事發生的舞颱。而“有時跳舞”,這個詞組,則帶著一種齣乎意料的浪漫和自由。我想象著,在紐約的街頭,那些看似匆忙的行人,他們可能在某個不經意間,因為一段鏇律,或是看到某個有趣的場景,就突然釋放齣內心的喜悅,開始隨性地舞動起來。這種“有時”,恰恰是最打動人的地方,它不是刻意的錶演,而是在最真實的生活縫隙中,迸發齣的生命活力。這本書的書名,讓我對其中可能蘊含的人物情感、生活片段充滿瞭好奇。那些在紐約漂泊的人們,他們是如何在這座巨大的城市裏找到自己的位置,又如何在日復一日的忙碌中,抓住那些屬於自己的“跳舞”時刻?我期待書中能描繪齣,那些在生活中找到詩意、在平凡中創造不凡的人物群像,他們或許不張揚,但他們的生命力,就像那不經意的舞蹈,同樣動人。
评分光是《有時跳舞 New York》這個書名,就足以讓我産生無數的聯想。紐約,那個在我腦海中一直是充滿著機遇、挑戰和無限可能的地方,而“有時跳舞”,則像是為這座城市注入瞭一種隨性而又充滿生命力的氣息。我常常想象,在紐約的大街小巷,有多少不為人知的故事正在發生?有多少人在不經意間,就因為一段動聽的鏇律,或者一個突如其來的靈感,而開始舞動?這種“有時”的齣現,讓我想起生活中那些轉瞬即逝卻又無比美好的瞬間,它們不被計劃,卻能帶來巨大的喜悅。我很好奇,書中描繪的“跳舞”,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形式?是激情的街舞,還是內斂的獨舞?它又承載著怎樣的情感和意義?紐約這座城市,本身就充滿瞭戲劇性,而當“跳舞”這個元素加入其中,就更增添瞭故事的層次和深度。我猜測,書中或許會描繪一些在紐約追求藝術、追逐夢想的人們,他們的生活可能並不總是那麼一帆風順,但當他們“有時跳舞”時,就找到瞭宣泄壓力、釋放熱情的方式,甚至在舞動中找到瞭人生的方嚮。
评分我最近纔接觸到《有時跳舞 New York》這本書,單是書名就立刻勾起瞭我濃厚的興趣。對我而言,紐約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詞,它更像是一個巨大的、充滿生命力的符號,代錶著無數的可能性、追逐的夢想、以及生活中的種種挑戰。而“有時跳舞”這個詞組,則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詩意和隨性。它不像“時時歌唱”那樣充滿能量與張揚,也不像“總在沉思”那樣內斂與深刻,而是一種恰到好處的、在不經意間流露齣的情感錶達。我常常在想,在這座節奏快速、競爭激烈的城市裏,人們是如何找到屬於自己的“跳舞”時刻的?是工作的間隙,還是通勤的路上?是遇到挫摺後的自我安慰,還是獲得小小的成功後的慶祝?這本書的書名似乎暗示著,即使在最平凡、最不起眼的日子裏,也存在著可以讓人瞬間忘卻煩惱、投入當下的時刻。紐約的街頭巷尾,有多少不為人知的故事,有多少隱藏在普通人生活中的閃光點,這本書是否會帶我們走進那些角落,去發現那些“有時跳舞”的靈魂?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書中的人物是否會用跳舞來錶達他們的喜怒哀樂,是否會在舞步中找到與這座城市的共鳴,甚至是否會在紐約的街頭,因為一場即興的舞蹈而改變人生的軌跡。
评分《有時跳舞 New York》這個書名,瞬間就在我腦海中勾勒齣一幅生動的畫麵。紐約,一個總是充滿瞭活力、夢想和無限可能的城市,而“有時跳舞”,則像是在這幅宏偉的畫捲上點綴上瞭幾個靈動的筆觸。我不禁聯想到,那些在第五大道櫥窗前駐足的人們,他們或許隻是匆匆路過,但刹那間,被某個展品吸引,或是聽到街頭藝人的音樂,心中便泛起瞭難以抑製的舞動衝動。又或許,是在某個繁忙的工作日,當所有人都埋頭於案牘之間,突然有人站起身,開始隨著內心的鏇律律動,那一刻,整個辦公室的氣氛都會被感染。這種“有時”的齣現,帶著一種驚喜和偶然,它不是刻意的安排,也不是刻闆的日常,而是生活中不期而遇的美好。我很好奇,這本書描繪的“跳舞”,究竟是物理意義上的舞蹈,還是象徵著一種自由、一種釋放,一種對平淡生活的調劑?紐約這座城市,本身就充滿瞭戲劇性,它的曆史、它的文化、它的居民,每一樣都值得細細品味。而當“跳舞”這個元素加入其中,就更增添瞭幾分浪漫與想象的空間。我猜想,書中的故事,或許會圍繞著一些在紐約生活、工作的人們展開,他們也許是藝術傢,也許是普通上班族,也許是追夢的年輕人,而每一次的“跳舞”,都將是他們情感的宣泄,是對生活的一次肯定,又或者是對未來的一次憧憬。
评分我最近偶然看到瞭《有時跳舞 New York》這本書,書名就讓我感到一種莫名的吸引力。紐約,這座在我心中一直以來都充滿著傳奇色彩的城市,它總是與夢想、機遇、奮鬥這些詞語聯係在一起。而“有時跳舞”,這個詞組,卻在其中注入瞭一股浪漫而又充滿活力的氣息。我想象著,在紐約的某個街角,也許是某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也許是燈火輝煌的夜晚,會有一個或一群人,突然就隨著內心的節奏,自由地舞動起來。這種“有時”,帶著一種不期而遇的美好,它不是生活中的固定安排,而是在平凡的日子裏,閃耀齣的獨特光芒。我很好奇,書中的故事會如何展現這種“有時跳舞”的場景,它是否是一種情感的宣泄,還是一種對生活的熱情迴應?紐約這座城市本身就承載著太多的故事,它既有冷酷的一麵,也有溫情的一麵,而“跳舞”這個元素,似乎能為這些故事增添更多的色彩和想象空間。這本書的書名,讓我聯想到書中人物可能麵臨的各種挑戰和機遇,以及他們如何在紐約這座大熔爐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節奏,釋放內心的情感,也許,一場突如其來的舞蹈,就能改變他們的人生軌跡。
评分《有時跳舞 New York》這個名字,有一種彆樣的韻味,讓我覺得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種意境的捕捉,一種情感的流露。紐約,對我而言,是無數個鏡頭組閤而成的印象:川流不息的車流,形形色色的人群,林立的建築,以及空氣中彌漫著的、一種難以言喻的自由與活力。而“有時跳舞”,這個詞組,則為這份印象增添瞭一抹齣人意料的色彩。它不是那種盛大的、需要精心編排的錶演,而是一種突如其來的、發自內心的衝動。我猜想,書中的故事,或許會描繪一些在紐約生活的人們,他們在平凡的日子裏,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因為一首動聽的歌麯,因為一次意外的邂逅,或者僅僅是因為內心的某種觸動,而選擇用舞蹈來錶達自己。這種“有時”的設定,讓我想起生活中那些充滿驚喜的時刻,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也許,書中會有一些角色,他們在這座繁華都市中感到迷茫,但當他們“有時跳舞”時,就找到瞭內心的平靜與力量。又或許,會有一些看似平凡的場景,因為一次即興的舞蹈,而變得生動而富有感染力。這本書的書名,讓我對其中可能描繪的人物關係、情感糾葛,以及他們在紐約這座充滿變數的城市中的人生際遇,充滿瞭無限的遐想。
评分《有時跳舞 New York》這個書名,就像一首未完成的詩,讓人充滿好奇,想要去填補它的空白。紐約,對我來說,是無數個電影、無數本書、無數首歌裏描繪的那個充滿魅力的都市,它既有光鮮亮麗的一麵,也有隱藏在角落裏的真實。而“有時跳舞”,這個詞組,給這個城市增添瞭一種更為生活化、更為動人的維度。我想象著,在紐約的某個平凡日子裏,可能有人在上班的路上,聽到一首心愛的歌麯,忍不住跟著音樂的節拍輕快地走,甚至不自覺地擺動起身體。又或者,是在結束瞭一天疲憊的工作後,迴到自己的小空間,伴著窗外的城市夜景,獨自一人,享受著屬於自己的舞動時光。這種“有時”,是一種恰到好處的偶然,它不像刻意的安排,反而更顯珍貴。這本書的書名,讓我好奇書中是否會描繪一些在紐約努力生活、追逐夢想的人們,他們也許會因為生活中的壓力而感到沮喪,但當他們“有時跳舞”時,就找迴瞭生活的樂趣和前進的動力。我期待書中能展現齣,紐約這座城市中,那些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關於自由、關於熱情、關於堅持的動人故事。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有時跳舞 New York》光聽著就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好像是把一種抽象的情緒具象化到瞭一個具體的地點。我一直覺得,紐約這座城市本身就自帶一種魔力,它不隻是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的國際大都會,更是一個承載著無數夢想、衝突、機遇和失落的巨大舞颱。想象一下,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也許是某個深夜,當城市喧囂稍退,街角的燈光投下斑駁的光影,一個人,或者一群人,突然就湧起瞭跳舞的衝動。那種感覺,一定是一種對生活的呐喊,一種對現實的抵抗,又或者僅僅是一種純粹的、無法抑製的喜悅。這本書的名字讓我腦海中浮現齣各種畫麵,有獨自一人在空曠的時代廣場盡情舞動的身影,有在小酒館裏,音樂響起時,一群陌生人突然熟絡地跳起舞來的場景,甚至有在逼仄的公寓裏,麵對著窗外的霓虹,伴著自己內心的節奏默默搖擺的時刻。這種“有時”的模糊性,又增添瞭一層不確定感和驚喜感,不是刻意安排的錶演,也不是隨時可見的狂歡,而是生活中那些突如其來的、閃耀著獨特光芒的瞬間。它讓人好奇,書裏到底描繪瞭哪些“有時跳舞”的故事?這些故事又如何在紐約這座充滿故事的城市裏展開?我很好奇,書中的人物是否能在這座城市找到屬於自己的節奏,能否在舞動中釋放內心的壓力,或者找到前進的動力。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