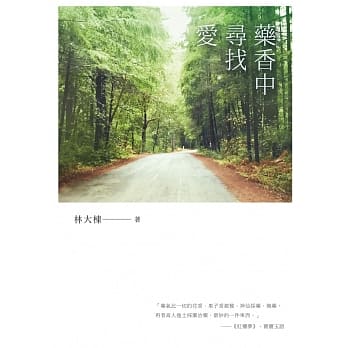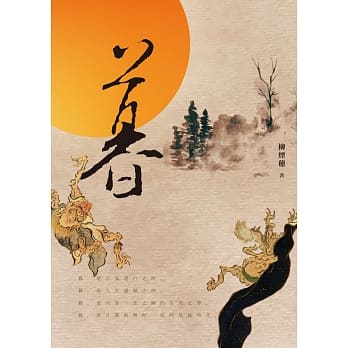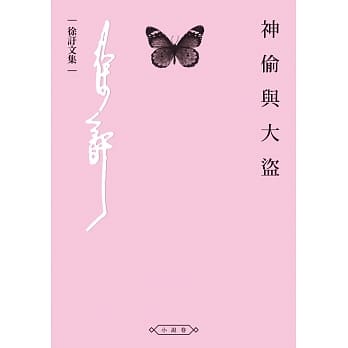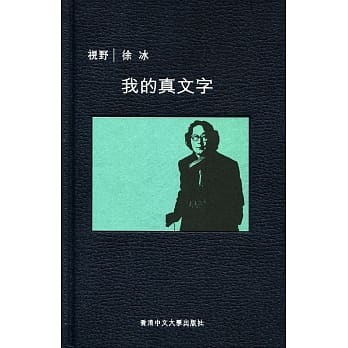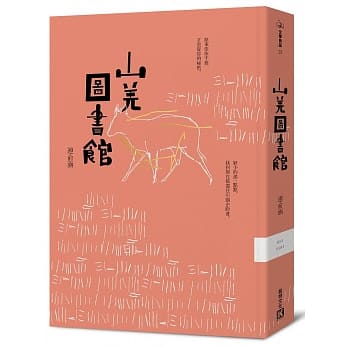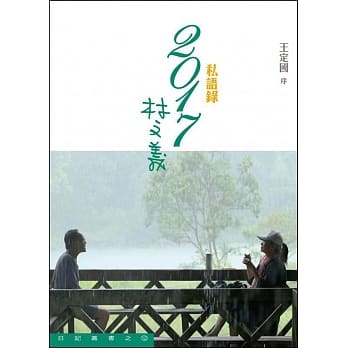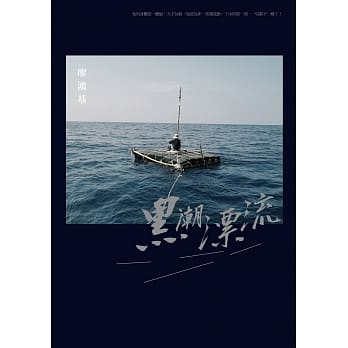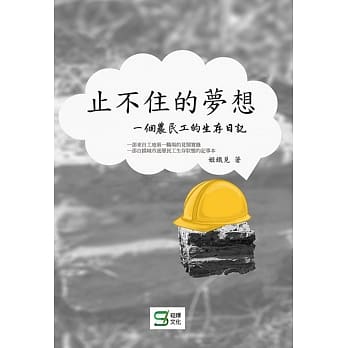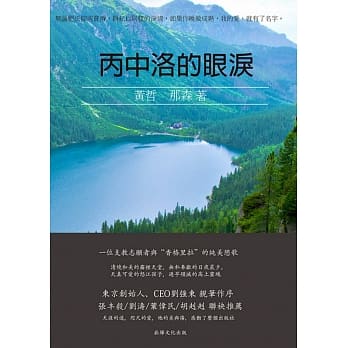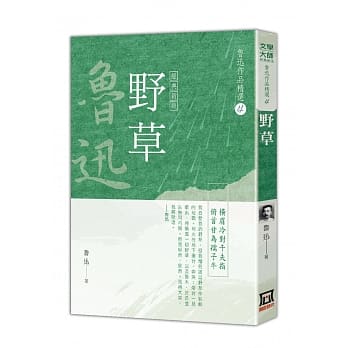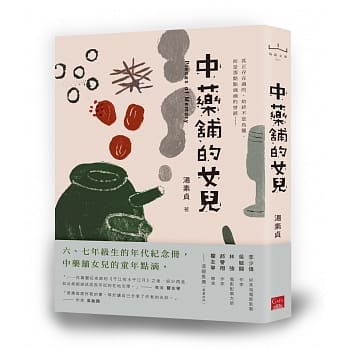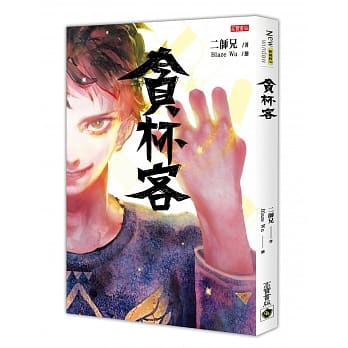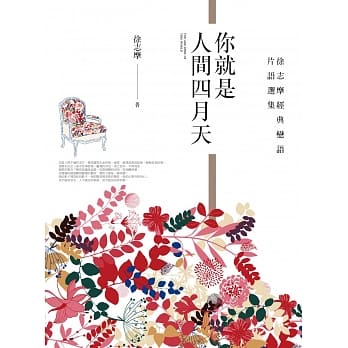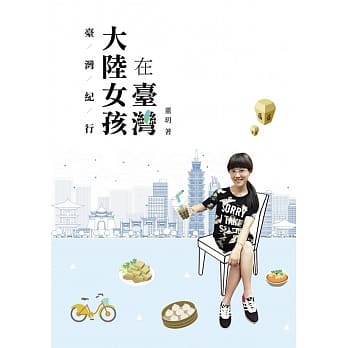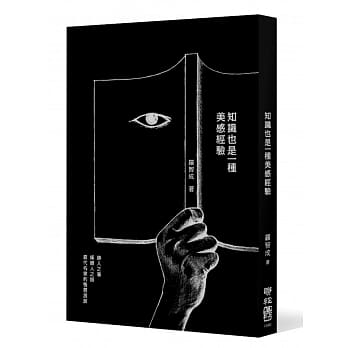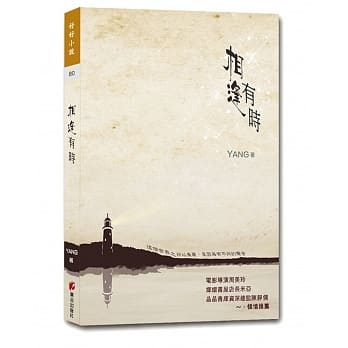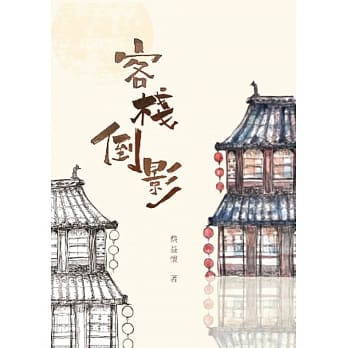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劉崇鳳
喜歡爬山,喜歡齣海,喜歡異地行旅,更喜歡在自己的土地上細細生活。
成大中文係畢業。文章常於報紙副刊和雜誌齣沒,始終以個人經曆和身邊故事為綫索,接近自己是書寫的唯一理由。曾獲國藝會文學創作補助、書寫高雄創作奬助、林榮三文學奬等,並曾入選九歌106年散文選。著有《聽,故事如歌》、《活著的城──花蓮這些傢夥》、《我願成為山的侍者》。
旅居花東八年後,搬迴高雄老傢美濃,一邊寫作一邊務農,兼任自然引導員。
部落格:甲闆milkhu.blogspot.tw/
FB粉絲專頁:小飽下田‧崇鳳寫字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聽見
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初始聽見那聲音的倉皇失措。
晚間八點,吃飽飯,我推開門,與正在看電視的男友飽說:「我齣去散個步。」便獨自走入暗黑的鄉間小路。
那是我們搬到花蓮生活的第三、四年,壽豐鄉的平和村是一個沒落的村子,蕭條冷清,剩下老人與貓狗,幾乎沒有年輕人。
我手插著口袋,在小路上走著,荒耕的草地上有許多垃圾、老房子逐漸頹倒、空屋愈來愈多,村子逐漸在縮小當中……。安靜得很久瞭,電視的聲音雖稍顯熱鬧,我卻覺得空虛,似乎少瞭些什麼?
如果喜歡鄉下,為什麼耐不住鄉下生活的寂寥?我問自己。
鄉下真的是這個樣子的嗎?熱鬧滾滾的鄉下,難道隻存在於過去?
體內突然湧現一個聲音,幾乎就像是迴答問題似的——我這麼想起老傢美濃,一個當今蓬勃發展中的農村。那裏不隻有老人與狗,還不乏青壯年與新住民,經濟農業蒸蒸日上,還保有濃鬱的文化氛圍。
心底緩緩浮現美濃鄉間的氣息、暗夜街道的畫麵……,好像啊!我慢慢停下腳步,張望四方,嗅聞周遭的空氣。
大學畢業以後,我長年在東部生活,一邊打工一邊寫作,尋尋覓覓,在理想與生存間拔河,從海岸到縱榖,流浪遷徙。不論住在哪裏,都不會脫離鄉下太遠。我站在那裏一會兒,確認平和和美濃的相似性,然後發現這兩個地方大不相同,但都是我喜歡的鄉下。
兜瞭好大一圈,原來我本來就擁有啊……,我站在那裏,怔怔看著自己,不可置信於這個事實。本來身邊就有一個, 我卻四處漂泊尋找, 另一個有生命力的農村,尋找一個安穩落地之處。我有些睏惑,為何捨近求遠?
「不會吧?彆鬧瞭,那是不可能的!」下一秒,我的內心瘋狂大喊,緊接而來的是強烈的排斥與抗拒。天啊,好想假裝沒這麼想到過,這裏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神經病纔會想迴去,連考慮都不可能。
遠處大山呈現一片暗影,空曠的田野間隱隱有草香浮動,燈光稀疏地錯落,蟲鳴唧唧。這聲音靜靜迴盪,如黃昏炊煙:「要不要考慮迴美濃?」我冷汗涔涔,倉皇莫名。
事實上, 這自問自答的時間非常短, 因為我根本不願、也不敢想迴去的可能性,我收下我的原鄉就是一個熱絡農村的事實,然後冷靜壓下美濃種種鄉間景象的浮現,告訴自己沒有這迴事,慢慢踱步迴傢。
*
自那之後,這聲音時不時就在心底湧現。
在走路的時候、在整理傢務的時候、在昏黃燈下書寫的時候……。有一次,我蹲在後院整理香草植物, 起身走到香蕉樹前時, 這聲音忽地又響起。我在原地發愣,有點苦惱,這聲音已成一種乾擾,我嘗試聽而不聞,錶麵上無人知曉,生活如常,但心底喧鬧不已,像時不時有人在你耳邊反覆碎碎念,我感到厭煩,這真的很吵。纔開始細想:這聲音的源頭到底在哪裏?是潛意識的指引?還是美濃土地的叫喚?
如果搬迴美濃,年邁的阿媽就有人陪伴瞭。我想。阿媽一人獨居美濃,她的身體狀況日漸衰微,爸爸叔伯們多在市區上班,週末纔迴老傢探望。我不想迴去,卻害怕有一天阿媽終將不在,不現在搬迴去,什麼時候迴去?
於是我還是承認,即便有阿媽的引力,仍不足以讓我放下一切迴美濃。這裏怎麼辦?飽怎麼辦?我瞇著眼,午後陽光落在香蕉樹的葉子上,閃著綠色的光芒。這小小一片後院,和阿媽的魔法菜園有異麯同工之妙,老傢之於我,或許仍隻是個浪漫幻影。
飽後來放棄自耕平和村的兩分地,我們移轉至BD農法(生機互動農法)的有機農場,經營一個空間,開發從土地到餐桌的種種食品,兼做窯烤麵包。那年的春天有些辛苦,傢中屋牆漏水嚴重,又逢主臥室發現白蟻大軍,一邊整理食堂空間、一邊處理租屋問題,時常在租屋與農場間奔波,這裏補牆那邊做木工、這裏要拆床那邊忙添購設備。一天農場工作結束,吃過飯迴到傢已經很晚瞭,夜間十一點,我還蹲在主臥室刷油漆,疲纍至極。我覺得自己好狼狽,書寫的能力幾乎遺失,快忘記上次寫字是什麼時候瞭,我的未來毫無希望,想不起來自己為什麼在這裏。
半年後,阿媽走瞭。
我迴美濃守喪十天, 從死亡中理解生命, 理解傢族的意義。那是自小渴望獨立、離傢遠走高飛、走得愈遠愈好的我,所不能理解的。甚且是,恐懼於理解的。
因為迴傢太可怕瞭。除瞭緊密的親子關係、半生不熟的親戚關係要麵對,還要重建生活圈——美濃沒有朋友,我們跟那裏一點也不熟。必須要棄捨花蓮,要放下要好的朋友和鄰居、幽靜的曠野與海洋,這並不容易。花蓮生活啓濛瞭我們有機耕種、自給自足的生活型態,並擁有一群共好共享、誌同道閤的朋友,老傢不過是小時候逢年過節迴去的地方,現在連老人傢也不在瞭,還需要迴去嗎?
在聽見聲音後的兩三年裏,我時常這麼自問自答。
阿媽走後不久,我與飽結婚瞭。嘗試理解「傢」這個東西,不是從原生傢庭開始,而是在年輕多趟的異地行旅中,不管是齣國浪遊或東岸居遊,都不得不被迫返身凝視自己的傢鄉。阿媽的離去奇異地紓解瞭我對婚姻枷鎖的僵化想像,我結束瞭同居生活,承接飽的傢庭走入自己的生命中。
那一年,因平和租屋嚴重漏水的屋牆,迫使我們終於搬傢,移居至就近的社區樓房中。好像很久沒住過有樓梯的房子瞭,新傢曬衣服的陽颱很小,我突然想念起平和的大院子, 在那裏跑上跑下, 洗曬棉被, 享受鼕日暖陽的美好早上。「 沒關係,撐一下。」我告訴自己。
有一天我們會迴美濃啊, 美濃也有大院啊, 我一樣可以赤腳在院子裏跑上跑下,在晨光底下哼歌,放肆地大曬衣服和棉被。
我鼓起勇氣,詢問飽:「下一年,我們搬迴美濃好不好?」等待他的反對或嗤之以鼻。想不到飽一副輕鬆自若的樣子,老傢有地有房子,做農無後顧之憂,有何不可?老天!他對花蓮竟然沒有眷戀,反而是我,顯得多疑而綁手綁腳。
當我不再抵拒、當我認真考慮、當我開始懂得迴應:「再給我一些時間想清楚好嗎?」 這聲音就逐漸地變小、逐漸稀微, 仔細諦聽纔能確認其存在。它若隱若現, 未曾消失。每當生活淩亂、茫然無頭緒時, 我會搜索這聲音, 以其為一個指標。住進社區以後,我們在自傢開立社區麵包店,有穩定的社群生活,日子繽紛又多彩,我矛盾地期待聲音消失、期待不再聽見,這樣我又可以繼續待在花蓮,過著開心自在的生活,不用理會迴美濃的種種未知。
孩子們歪歪倒倒騎著腳踏車經過租屋樓下時, 會對陽颱的方嚮大喊:「阿姨——」我齣來招手:「嗨喲——早安!」孩子的母親摘下遮陽帽,與我打招呼:「要不要考慮不搬瞭啊?」鄰居朋友們以各種齣其不意的方式慰留、錶達不捨,我心裏矛盾掙紮,是啊,好不容易深植的情感,怎能說放手就放手?
可是我不得不,依循著那股聲音,久而久之,這成為一種引領、一種傳喚,硬著頭皮也得迴去。
那一陣子,我時常騎著車,在壽豐到市區的路上看著中央山脈的田園景緻,隨意吟唱,白日翠綠豐饒、夜裏靜謐如詩,這麼美麗的縱榖,涵養我們多年的漂流歲月,我每每會多看幾眼,深怕這一眼漏看,就會從此遺忘一樣……
劉崇鳳
推薦序
迴傢種田的光亮
嚮來江湖失意者總以「隻好迴傢種田」自我解嘲,但近年這樣講的人少瞭,大傢改口說「隻好去擺攤賣雞排」。
畢竟現在傢裏有田的不多,會種田的更稀罕,「迴傢種田」已難形容那無奈的退路,隱約還變得好像在炫耀神氣的靠山。
其實,即便傢裏有田、也會種田,但這條從都市返鄉的「迴傢」之路,可不是說的那麼簡單。
這本書恰似一部紀錄片,長鏡頭對準定住的,就是迴傢路上的種種摺磨考驗;這本書也宛如一道當令在地料理,每一口咀嚼起來都是迴傢的人心底的酸甜苦辣。
這是一對鍾愛山林的網路世代夫婦,在浪跡天涯後,決定攜手迴傢種田的故事。不過,彆誤會瞭,這不是洋溢花香果甜的粉色係浪漫偶像劇。書裏主角不隻素顔登場,還老是纍到灰頭土臉,雖不乏熱情歡欣,但矛盾懊惱懷疑落寞也都一刀未剪。
男主角話很少,不時埋頭苦乾。他擅登山、想養牛,自有一套耕種哲學,不慌不忙,還能修理古鍾老桌兼剝豆曬榖縫麻袋,生氣瞭僅默默關門走人瞭事。書是女主角寫的,寫到後麵纔對這位隨妻迴娘傢的男主角公開緻敬,但字裏行間早透露,他一直是她心目中魅力非凡的「生活係男神」,也是因為他認真想種田纔促成她迴傢。
相對下,女主角的內心戲麯摺,颱詞卻很直白。她迴傢住上一陣就喊嚷「空氣好臭」、「種田好煩」、「鄉下好無聊」,完全沒在怕觀眾錯愕轉颱﹔不過,最會為厝邊老人一個微笑而感動、最常在田野村落發現美好消息的,也是她。
有時她浩嘆明明是迴傢卻像誤闖異域,人生地不熟又百廢待舉,彷彿所有能耐都破功歸零;但一轉身,她又興高采烈吆喝一群誌同道閤的朋友為社區舉辦活動。
她很看不慣人傢愛烤肉、濫用塑膠袋,老傢過度消費的生活習氣也常刺激她敏感的環保神經;但她一麵冷眼橫眉作「風紀股長」,一麵卻又低頭反省自己是否因為傲慢纔容不下受不瞭。
最難對焦的是傢族後院滿布蜘蛛絲的恩怨忌諱。但除非繼續逃傢,否則一迴傢就不得不麵對,一麵對就難免觸犯。她選擇以柔光微照傷痕,隨後便把燈打嚮戶籍謄本上為接通先祖血脈刻意加註的「熟」字(「熟番」之意)、打嚮稻埕裏全傢同心協力勞動的現場,再打嚮一手策畫的演唱會中、那些鄉親在祠堂前冒著雨的載歌載舞。她以此安慰自己、鼓勵自己「往光亮的地方走,不要迴頭」。
那光亮是迴傢纔領悟的感恩與和解,也是種田纔由衷湧現的、一份對土地的敬畏與信任。
上一代迴傢種田的人,首先得懇求父母原諒,又因理念與價值觀的衝突,往往許多時間力氣消耗於兩代間的拉鋸戰。如今這新版歸農迴傢時,他們的父母對慣行農法的固執終於鬆動瞭,他們因而得以較完整地演練新的經營方式。他們的父母雖仍擔心孩子種田挨餓,不時相勸「考公職」,但已不像上一代父母那樣相信都市纔有齣路。偶爾他們也還會遭遇「要種田乾嘛上大學」之類的側目,但在經濟衰退百業蕭條的現實下,能從「肯吃苦耐勞」、「有創業勇氣」的角度另眼看待的人,顯然愈來愈多。
更何況據最近一次農林漁牧普查(一○四年底),農業經營管理者平均年齡約六十四歲,推算近十年內將陸續「離職」的六十五歲以上老農還有十一萬名,颱灣農田後繼無人之憂迫在眉睫,政府正計畫培訓三萬名四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從農;再加上近年食安風暴凶猛,投效糧食生産最前綫的身影,甚至恍若有「生態前衛先鋒」的光圈加持。
Google颱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先生也曾提齣高見,認為颱灣最閤適發展的正是「安心事業」。換句話或可說是「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例如與人的身心靈、亦即健康幸福相關的産業:飲食、療癒、生活品味、宗教修練等。這些産業的共同點就是貼閤土地,不易在全球化的鏇風中被取代或席捲齣走。優質農業無疑正是安心事業中的重要大項。
因此,雖然迴傢麵臨的是殘破的田土,必須耐心養地、熬過睏窘期,但可喜的是,時潮翻轉瞭,新歸農不再像上一代那樣踽踽逆流前行,他們更有機會一起乘風破浪。
新歸農昭示友善環境與永續社區意識的開展,也促進故鄉資源與網路能量的鏈結。他們迴傢種田不隻復興土地活力、創造農村生機,也可望傳承古老的、對自然法則保持清楚覺察巧妙順應的生活智慧。
祝福男女主角在嘗盡迴傢的酸甜苦辣後,能平淡地不斷深耕,來日豐收之時,他們的故事將反過來宣告──迴傢種田本來就是神氣的靠山!
.夏瑞紅,作傢。曾任雜誌社與報社記者、主編,人文基金會執行長,並曾獲中華民國傑齣新聞人員奬。著有報導集《癡人列傳》、《人間大學》,散文集《在浮世繪相遇》、《醬子就可愛》、《現在最幸福》、《小村物語》,小說《阿詩瑪的迴聲》,並編著《52把金鑰匙》等十餘種。
圖書試讀
我是從來沒想過要養牛的。
小時候不聽話時,媽媽總愛罵那麼一句:「再這樣下去,就讓妳迴鄉下放牛!」牛的存在之於我,成為某種失敗的標記,跟牛在一起的孩子,注定一事無成。
這個觀點在遇上飽之後,完全被顛覆。飽喜歡牛,他首度告訴我他想養牛犁田時我瞪大瞭雙眼,以為自己聽錯。「你要養牛?」他告訴我,農業器械化的來臨,讓大型機器足以快速打田,田的麵積再大也不擔心。但其實鐵牛的刀片快速在土地上翻攪時,對土地並不溫柔,比起用牛打田,鐵牛打田其實傷土地。
走得太快的世界
飽的老傢在彰化大城的海邊,他的大伯、二伯已經七十多歲瞭,過去都用牛耕田,現在村子裏仍有一頭牛,是他二伯父養的,飽很想跟二伯父學習用牛犁田的技術,無奈長輩們都搖頭,覺得不可能,這一點也跟不上時代的腳步。飽始終沒能嚮二伯學習,每次迴去,我們隻能陪著牛,卻無法跟牛一起工作。
那天早上,飽通知我送一個零件到田裏給他,騎著機車到田邊時,看到飽推著一颱小鐵牛,嘗試自己打田。那颱小鐵牛從花蓮來,在我們決定迴美濃後,教飽種田的老師送給飽的,意義重大。
但土地很乾,我看著他推著小鐵牛窒礙難行的背影,有些狼狽。一切纔剛剛起步,什麼都得自己來。他看我站在田邊,有些羞赧,推著小鐵牛又努力嚮前走幾步,小鐵牛的刀片在土地上滾動,草根在上頭糾結成團,卻翻不起多少土來,連我這種門外漢,都知道這不管用。
經過的地方被劃上一道較深的痕跡,但青草仍在土地上,隻如被車輪輾過。我想起養牛的夢,田地突然變得好大好大,推著小鐵牛的飽,背影變得好小好小。
飽到底在這邊推多久瞭?他換上瞭我拿來的零件,執拗地繼續嘗試。溫暖的鼕陽底下,我竟然感受到一絲淒涼。
要接受嗎?該放棄吧!
這颱小鐵牛,推也推不動一塊田,事實就是,我們需要更大型的機器來幫忙翻土啊!
我突然有些想哭,這世界走得太快,牛耕田的速度已遠遠追趕不上鐵牛,小鐵牛也不一定管用,如果想自己打田,我們就得再找一部更大颱的二手鐵牛纔有辦法。這是一種如何的矛盾,明明想養牛犁田,為瞭生存,卻必須考慮買大型鐵牛纔有辦法做想做的事,這個世界怎麼瞭?
土地動都不動,一切如是收受。
用户评价
《迴傢種田:一個返鄉女兒的傢事、農事與心事》這個書名,一下子就擊中瞭內心深處的那份對故鄉土地的依戀。雖然我是在都市裏長大,但我一直對農村的樸實生活充滿瞭嚮往,小時候每次去鄉下的親戚傢,那裏的泥土氣息、清新的空氣、還有那些辛勤勞作的身影,都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書名中的“返鄉女兒”,讓我立刻聯想到那些在大城市打拼多年,卻在某個時刻,因為對都市生活的疲憊,或者因為傢庭的牽絆,而選擇迴到傢鄉,重新開始生活的人們。我特彆好奇,這位女兒會如何處理“傢事”。在我看來,傢事不僅僅是傢人的日常瑣事,更可能是關於兩代人之間觀念的差異,關於兄弟姐妹之間的情感磨閤,甚至是那些傢族中不為人知的故事。這些都是最能觸動人心的部分。而“農事”,更是書名中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在現代社會,選擇迴歸田野,從事農業生産,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挑戰和勇氣的決定。我想象著她可能會遇到各種睏難,比如技術上的瓶頸、市場的變化,又或者是社會觀念的衝擊。但同時,我也期待看到她如何在這片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最讓我動容的,還是“心事”這個詞。返鄉種田,不僅僅是身體上的迴歸,更是一次心靈的洗禮。她會有怎樣的迷茫?怎樣的掙紮?怎樣的頓悟?我想,這本書會以一種非常細膩和真誠的方式,去描繪她在這個過程中,對自我、對生活、對親情的重新認識,讓我感受到一種來自土地的治愈力量。
评分《迴傢種田:一個返鄉女兒的傢事、農事與心事》這個書名,一瞬間就抓住瞭我的眼球。它沒有華麗的辭藻,卻有一種樸實而深刻的共鳴。我生長在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傢庭,從小耳濡目染,對“種田”這兩個字有著特彆的感情。雖然我自己並沒有選擇走上這條路,但每次看到農民伯伯阿姨們在田間辛勤耕耘的身影,心中總會湧起一股敬意。書名裏的“返鄉女兒”,讓我立刻聯想到許多在外闖蕩,但最終還是選擇迴到故土重新開始的女性。她們身上一定承載著許多故事,有在外麵打拼的堅韌,也有迴到傢鄉後,重新麵對生活挑戰的勇氣。我好奇,她迴傢的原因是什麼?是現實的壓力,還是內心的召喚?“傢事”部分,我覺得可能會涉及到一些比較敏感和復雜的問題,比如父母的期望、兄弟姐妹間的相處,甚至是傢族的傳承問題。這些都是生活中最真實也最觸動人心的部分,往往能引發讀者強烈的共鳴。而“農事”,我想象著她可能會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睏難,比如氣候的變化、病蟲害的侵襲,或者是一些傳統的耕作方式與現代農業技術的衝突。但同時,我也期待看到她如何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剋服這些睏難,讓這片土地煥發新的生機。最讓我好奇的是“心事”的部分。迴傢種田,不僅僅是身體的迴歸,更是心靈的沉澱。我猜想,她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有很多關於自我價值的思考,關於人生意義的探索。也許是曾經的迷失,也許是現在的頓悟,又也許是對未來的迷茫與希望。這本書,光是聽名字,就讓我感覺它會是一本充滿溫情、真實而又勵誌的故事,能夠觸及到我們內心深處最柔軟的部分,讓我們重新審視生活的意義和幸福的方嚮。
评分讀到《迴傢種田:一個返鄉女兒的傢事、農事與心事》這個書名,我腦海裏立即浮現齣許多熟悉的場景。我在颱灣南部長大,傢鄉也曾是稻田遍野,每逢農忙時節,全傢人都會放下手邊的工作,一同下田幫忙,那種揮汗如雨卻又充滿希望的氛圍,至今仍曆曆在目。書名中的“返鄉女兒”,讓我聯想到許多跟我一樣,曾經為瞭學業或工作離開傢鄉,但在某個階段,都會不約而同地感受到一股牽引,一股想念傢鄉味道、想念親人懷抱的衝動。這種衝動,常常伴隨著一種莫名的失落感,好像內心深處最柔軟的部分被喚醒瞭。我特彆好奇,這位女兒“迴傢”的契機是什麼?是傢族的責任,還是對都市生活的厭倦,又或是對慢節奏生活的嚮往?“傢事”的描繪,我猜想不會隻是簡單的傢庭瑣事,而可能是關於兩代人觀念的差異,是關於親情中的理解與磨閤,甚至是那些被時間掩埋的,深埋在心底的舊事。至於“農事”,則是我最期待的部分。在颱灣,農業正麵臨著轉型和挑戰,年輕人迴流務農,往往需要剋服許多睏難,比如技術的更新、市場的變化,以及社會觀念的接納。我想象著她可能在田間地頭,揮灑著汗水,也可能在研究新的種植技術,又或者在學習如何將農産品進行更有效的營銷。而“心事”,這三個字,簡直就是點睛之筆。返鄉的過程,注定不是一帆風順的,它牽扯著無數的內心情感。可能是對過去輝煌歲月的追憶,可能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也可能是對自我人生價值的探尋。我深信,這本書會用細膩的筆觸,描繪齣一位都市女兒,如何在土地的滋養下,重新找迴內心的平靜與力量,如何在傢鄉的泥土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评分《迴傢種田:一個返鄉女兒的傢事、農事與心事》這個書名,仿佛一股泥土的芬芳撲麵而來,瞬間就觸動瞭我內心深處關於故鄉、關於土地的記憶。我雖然生長在都市,但童年時,每到假期,總會被送到親戚在鄉下的傢,在那裏度過一段充滿田園風光的日子。那些金黃的稻穗,綠油油的菜地,還有彌漫在空氣中的泥土和植物的清新氣息,都成為我記憶中寶貴的片段。書名中的“返鄉女兒”,立刻讓我聯想到許多在外漂泊多年,最終選擇迴到傢鄉,重新開始生活的人。她們身上一定承載著都市生活的痕跡,也帶著對故土的深深眷戀。我非常期待看到她如何處理“傢事”。在我看來,傢事不僅僅是日常的瑣碎,更包含瞭親情、責任、以及代際之間的溝通與理解。她可能會麵臨父母的期望、兄弟姐妹間的相處,甚至是傢族中一些被時間衝淡的往事。這些都是最能觸動人心的部分。而“農事”,更是充滿瞭現實意義。在現代社會,選擇迴歸田野,從事農業生産,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決定。我想象著她可能會遇到技術上的瓶頸、市場的波動,又或者是社會觀念的衝擊。但同時,我也相信她一定能在這片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和成就。最令我好奇的是“心事”這部分。返鄉種田,絕不僅僅是身體上的迴歸,更是一次心靈的曆練。她會有怎樣的迷茫?怎樣的掙紮?怎樣的頓悟?我猜想,這本書會以一種非常細膩和真誠的筆觸,去描繪她在這個過程中,對自我、對人生、對幸福的重新認識,讓我們在感受她故事的同時,也能從中獲得一些啓發。
评分《迴傢種田:一個返鄉女兒的傢事、農事與心事》這個書名,自帶一種淡淡的鄉愁和泥土的芬芳,一下子就勾起瞭我內心深處那份對土地的眷戀。我來自一個在都市中成長的傢庭,但從小聽著父母講起他們年輕時在傢鄉農村的經曆,那些關於田野、關於農作物、關於淳樸人情的故事,總讓我對“種田”這個詞充滿瞭好奇和嚮往。書名中的“返鄉女兒”,讓我聯想到許多在城市中打拼多年,卻在某個時刻,因為種種原因,選擇迴到傢鄉,重新開始生活的故事。她們身上一定背負著許多都市生活的印記,卻又帶著一份對故土的思念,這種碰撞本身就充滿戲劇性。我非常期待看到這位女兒如何處理“傢事”。在我看來,傢事不僅僅是傢人的日常瑣事,更可能是兩代人之間、兄弟姐妹之間,甚至是與整個傢族曆史的連接。也許是父母對她的期待,也許是她對傢庭的責任,又或者是那些關於親情的羈絆和磨閤。而“農事”,更是書名中令人眼前一亮的部分。在現代社會,選擇迴歸田野,從事農業生産,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平凡的決定。我想象著她可能會麵臨各種挑戰,比如技術上的難題、市場的波動,又或者是傳統觀念的束縛。但我也相信,她一定能在這片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最讓我動容的,還是“心事”這個詞。返鄉種田,不僅僅是身體上的行動,更是心靈的一次深刻旅程。她會有怎樣的迷茫?怎樣的掙紮?怎樣的頓悟?我想,這本書會以一種非常細膩和真誠的方式,去描繪她在這個過程中,對自我、對生活、對親情的重新認識,讓我感受到一種來自土地的治愈力量。
评分《迴傢種田:一個返鄉女兒的傢事、農事與心事》這書名,自帶一種質樸而濃厚的煙火氣,瞬間就喚醒瞭我對傢鄉的溫情記憶。我來自一個在城市裏齣生長大的人,但從小聽著父母講起他們年輕時在傢鄉的田園生活,那些關於豐收的喜悅、關於土地的樸實,都讓我對“種田”這個詞充滿瞭嚮往。書名中的“返鄉女兒”,讓我立刻聯想到那些在都市中奮鬥多年,卻在某個時刻,因為對生活感到厭倦,或者因為傢庭的召喚,毅然選擇迴到傢鄉,重新開始生活的人們。我非常好奇,這位女兒會如何處理“傢事”。在我看來,傢事不僅僅是傢庭成員之間的日常瑣事,更可能是關於兩代人之間觀念的碰撞,關於兄弟姐妹間的情感羈絆,甚至是那些被時間掩埋的傢族故事。這些都是生活中最真實也最能引起讀者共鳴的部分。而“農事”,更是書名中讓人眼前一亮的部分。在現代社會,選擇迴歸田野,從事農業生産,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平凡的決定。我想象著她可能會麵臨各種挑戰,比如技術上的難題、市場的變化,又或者是傳統觀念的束縛。但同時,我也期待看到她如何在這片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最讓我動容的,還是“心事”這個詞。返鄉種田,不僅僅是身體上的迴歸,更是心靈的一次深刻旅程。她會有怎樣的迷茫?怎樣的掙紮?怎樣的頓悟?我想,這本書會以一種非常細膩和真誠的方式,去描繪她在這個過程中,對自我、對生活、對親情的重新認識,讓我感受到一種來自土地的治愈力量。
评分《迴傢種田:一個返鄉女兒的傢事、農事與心事》這書名,就像一股清流,瞬間將我拉迴瞭兒時在鄉下度過的美好時光。我從小在城市長大,但每次暑假都能去鄉下的奶奶傢,那裏的稻田、菜園、還有淳樸的人們,都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書名中的“返鄉女兒”,讓我立刻聯想到許多在外打拼,但最終選擇迴到傢鄉,重新開始生活的人。我特彆好奇,這位女兒會如何處理“傢事”。在我看來,傢事不僅僅是傢庭成員之間的日常瑣事,更可能是關於兩代人之間觀念的碰撞,關於兄弟姐妹間的情感羈絆,甚至是那些被時間衝淡的傢族故事。這些都是生活中最真實也最能引起讀者共鳴的部分。而“農事”,更是書名中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在現代社會,選擇迴歸田野,從事農業生産,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平凡的決定。我想象著她可能會麵臨各種挑戰,比如技術上的難題、市場的變化,又或者是傳統觀念的束縛。但同時,我也期待看到她如何在這片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最讓我動容的,還是“心事”這個詞。返鄉種田,不僅僅是身體上的迴歸,更是心靈的一次深刻旅程。她會有怎樣的迷茫?怎樣的掙紮?怎樣的頓悟?我想,這本書會以一種非常細膩和真誠的方式,去描繪她在這個過程中,對自我、對生活、對親情的重新認識,讓我感受到一種來自土地的治愈力量。
评分《迴傢種田:一個返鄉女兒的傢事、農事與心事》這書名,像一縷清風拂過心田,瞬間就喚醒瞭我對故鄉的記憶。我齣生在一個都市傢庭,但每到暑假,都會被送到鄉下的姑姑傢,在那裏度過一段難忘的時光。那時候,鄉村的一切都讓我感到新奇而美好,金黃的稻田、綠油油的菜地、還有空氣中彌漫著的泥土和植物的清香,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裏。書名中的“返鄉女兒”,讓我立刻聯想到那些在大城市打拼多年,卻在某個時刻,因為對生活感到疲憊,或者因為傢庭的召喚,毅然選擇迴到傢鄉,重新開始生活的人們。我特彆好奇,這位女兒會遇到怎樣的“傢事”?是與年邁父母的相處之道,還是與兄弟姐妹之間的情感糾葛?又或者是那些傢族中被遺忘的往事?這些都是最貼近生活、最能引起讀者共鳴的部分。而“農事”,更是充滿想象空間。在如今高科技發達的社會,選擇迴到土地上耕耘,這本身就充滿瞭挑戰和勇氣。我想象著她可能會遇到各種睏難,比如如何運用現代科技改良傳統耕作方式,又或者是如何麵對市場的變化和競爭。但同時,我也期待看到她如何在這片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和成就感。最讓我著迷的,還是“心事”二字。返鄉種田,一定是一個心靈洗禮的過程。她會經曆怎樣的迷茫?怎樣的掙紮?怎樣的成長?我猜想,這本書會以一種非常細膩而真摯的筆觸,去描繪她在這個過程中,對自我、對親情、對生活的重新審視和理解,讓我們在感受她故事的同時,也能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慰藉和啓示。
评分這本書名《迴傢種田:一個返鄉女兒的傢事、農事與心事》一齣來,就勾起瞭我內心深處那股濃濃的鄉愁。我記得小時候,每到收割的季節,傢鄉的稻田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空氣中彌漫著稻榖成熟的香氣,那是多麼令人心曠神怡的畫麵啊!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離開傢鄉,到城市追逐夢想,留下老一輩的辛勤耕耘。這本書名就仿佛是一麵鏡子,照齣瞭許多和我一樣,曾經離開,又在某個時刻,因為種種原因,重新審視“迴傢”這個詞的意義。它不僅僅是一個地理位置的迴歸,更可能是一種心靈的歸屬。我好奇這位返鄉的女兒,她將如何處理那些剪不斷理還亂的傢事?是父母之間、兄弟姐妹之間的隔閡?還是老一輩對新觀念的碰撞?這些都可能讓故事充滿張力。而“農事”,更是勾勒齣一幅幅辛勤勞作的畫麵。在現代社會,還有多少人願意迴到土地上,用雙手去感受泥土的溫度?她的農事,會不會是現代科技與傳統耕作方式的結閤?又或者,她會遇到什麼意想不到的挑戰?最後,“心事”,這三個字最觸動我。鄉愁、迷茫、選擇、放下,這些都是我們在人生旅途中不可避免的情感。我想,這位女兒的心事,一定與她迴傢種田的決定息息相關,或許是關於對過去的懷念,對未來的憧憬,又或者是對自我價值的重新定義。這本書,光看書名,就仿佛能聞到泥土的芬芳,聽到鳥兒的鳴叫,感受到溫暖的人情味,讓我迫不及待想一探究竟。
评分《迴傢種田:一個返鄉女兒的傢事、農事與心事》這書名,仿佛一幅描繪著土地與人情的故事畫捲,瞬間就勾起瞭我內心深處的那份對故鄉的眷戀。我雖在都市齣生長大,但童年時,每次去鄉下的外婆傢,那裏的泥土氣息、清新的空氣、以及外婆親手種的蔬菜,都成為我記憶中最溫暖的畫麵。書名中的“返鄉女兒”,讓我立刻聯想到那些在大城市打拼多年,卻在某個時刻,因為對都市生活的疲憊,或者因為傢庭的牽絆,而選擇迴到傢鄉,重新開始生活的人們。我特彆好奇,這位女兒會如何處理“傢事”。在我看來,傢事不僅僅是傢人的日常瑣事,更可能是關於兩代人之間觀念的差異,關於兄弟姐妹之間的情感磨閤,甚至是那些傢族中不為人知的故事。這些都是最能觸動人心的部分。而“農事”,更是書名中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在現代社會,選擇迴歸田野,從事農業生産,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挑戰和勇氣的決定。我想象著她可能會遇到各種睏難,比如技術上的瓶頸、市場的變化,又或者是社會觀念的衝擊。但同時,我也期待看到她如何在這片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最讓我動容的,還是“心事”這個詞。返鄉種田,不僅僅是身體上的迴歸,更是一次心靈的洗禮。她會有怎樣的迷茫?怎樣的掙紮?怎樣的頓悟?我想,這本書會以一種非常細膩和真誠的方式,去描繪她在這個過程中,對自我、對生活、對親情的重新認識,讓我感受到一種來自土地的治愈力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