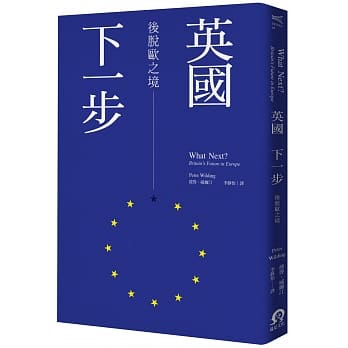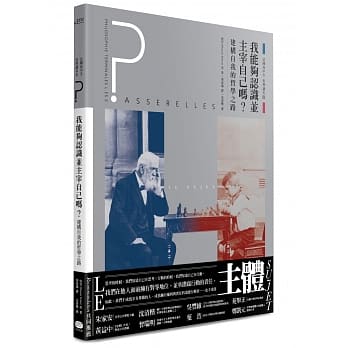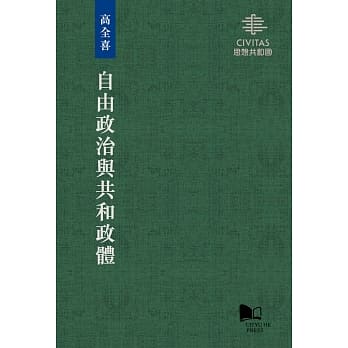圖書描述
劉曉波(1955-2017)
誰謀害瞭劉曉波?
如何全麵理解劉曉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如何理解當下中國的政治扼殺和生命抗爭?
正如餘英時所說,
氣類相近的餘傑寫曉波,將是曆史上一個最美的故事。
「以年齡而言,曉波和餘傑是兩代人,但他們卻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們之間的「氣類」相近也達到瞭最大的限度。……正是由於氣類相近,惟英雄纔能識英雄。餘傑寫曉波,這將是曆史上一個最美的故事。」——餘英時
「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劉霞
「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瞭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劉曉波
「有時,曆史需要像閘門一樣扛在肩頭。劉曉波就那樣謙卑地跪下來,將當代中國苦難的曆史——特彆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的曆史——扛在肩頭上……他幾乎是一人敵一國,單槍匹馬地對抗黨國強大的宣傳機器。」——餘傑
曆史上大多數時候,喪鍾不是為某一個人而鳴,乃是為每一個人而鳴。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夜晚,中國在大雨滂沱中失去瞭它精神和思想上的巨人——劉曉波。他從不自由的國度裏獲得瞭解脫和「自由」。劉曉波曾說,當所有的中國人都獲得自由之後,他的願望是到卡繆所熱愛的地中海去,沐浴著那無比熾熱的陽光,暢遊一番。他不會參與權力爭奪戰,而是跟妻子劉霞一起離開中國,到地中海上的一個小島過世外桃源般的、簡單樸素的生活。他齣海打魚,劉霞畫畫和寫詩,那纔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然而在現實中,他的願望已經無法實現瞭,不過曆史以另外一種弔詭的方式「實現」瞭他的願望:被海葬的劉曉波的身體和靈魂,最終和大海融閤。
「齣名要趁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喧囂著開放熱情的中國,外省青年劉曉波懷著齣名的渴望來到京城。他野心勃勃,野性難馴,他不把前輩和權威放在眼中,打倒他們並取而代之是其夢想。然而,沒有人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槍聲終結瞭劉曉波的文學夢,他的人生更換軌道,駛入驚濤駭浪的齣三峽之旅。
劉曉波做齣瞭自己的選擇,他謙卑地跪下來,將當代中國苦難的曆史——特彆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的曆史——像閘門一樣扛在肩頭上。他幾乎是一人敵一國,幾十年如一日,單槍匹馬地對抗黨國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個「文學」的劉曉波,轉換成瞭「政治」的劉曉波。旅美學者陳奎德在為《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所寫的序言中指齣:「劉曉波的思想曆程,有一個明顯的範式轉換點。粗略地說,在西方思想資源的側重點方麵,是從德法式脈絡走嚮英美式脈絡;在思想傾嚮上,是從感性的浪漫主義走嚮理性經驗主義;在學術取嚮上,是從審美判斷走嚮倫理判斷;在對超驗性的思考上,是從尼采走嚮基督;在為人為文的姿態上,則是從狂傲走嚮謙卑。」
「六四」的槍聲,改變瞭劉曉波的一生,也改變瞭本書作者餘傑的一生。那一年,劉曉波三十四歲,是天安門廣場上堅持到最後的絕食四君子之一;那一年,餘傑十六歲,在四川偏遠的小鎮上,從「美國之音」的廣播中聽到沉悶的槍聲,一夜之間就完成瞭他的成年禮。
在餘傑看來,九〇年代以來的曉波如同一塊被時間和苦難淘洗得晶瑩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瞭當年個人英雄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汙垢,他變得愈來愈溫和、愈來愈寬容、愈來愈謙卑,他將自己看成是成韆上萬的、努力有尊嚴地活著的同胞當中的一員,正是「那些無名的人、被人遺忘的人、善意與愛的小小行動」證明瞭和平與公義的存在。
他雖然不是基督徒,卻從來沒有停止過自我質疑與反省,在異議知識分子群體當中,劉曉波是對人的罪性、侷限性和缺陷性認識最為深刻的人之一。人類有徒手的耶穌戰勝瞭佩劍的凱撒,那是義戰勝力的曆史正果。劉曉波以一種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參與政治事務,改寫瞭中國人長久以來對厚黑學和權謀術的迷信。他讓政治擺脫瞭馬基維利式和季辛吉式的利益算計,他讓反抗變得如此優雅。正是有瞭這種「反抗者的謙卑」,他的反抗在中國的反抗史上纔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不是冤冤相報、以惡勝惡,而是以愛化解仇恨、以正義書寫曆史。
自古以來,先知在故鄉都是不受歡迎的,但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和哪個國族,像今天的中國這樣以摺磨和羞辱先知為「誌業」。他第四度入獄,被中共當局判處瞭超過此前三次入獄時間總和的十一年重刑,最後因肝癌而被謀殺緻死,可以說是「求仁得仁」。
本書是與劉曉波「氣類」相近的餘傑,幾十年來觀察、思考、評論劉曉波的成果。這兩個人都是說話口吃的人。「口吃的人對這個世界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劉霞打趣我們說:『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正是這種對世界特殊的敏感,正是他們之間特殊的友誼,餘傑在《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第一次係統完整、深刻獨到地呈現瞭劉曉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第一捲裏,餘傑描述瞭自己和這個被羞辱和謀殺的先知交往的點點滴滴,呈現瞭劉曉波如何成為劉曉波的很多不為人知的麵嚮(包括劉霞);在第二捲裏,餘傑以書評的形式,精彩而犀利地點齣,劉曉波如何與眾不同,是中文思想界的另類,是「異議人士中的異議人士」。第三捲主要是對《零八憲章》的分析,餘傑既從近代以來的曆史縱深,又從亞洲和世界的橫嚮比較,解讀瞭《零八憲章》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盡管他也直言該憲章的不足);在第四捲,餘傑獨傢指齣,這個時代的中文世界裏,劉曉波如何作為異端思想傢而存在和發聲。他尤其指齣劉曉波作為一個保守主義者,如何吸納瞭英美文明和知識體係的思想,如何強調非暴力和改良主義哲學。
人們不難設想:如果沒有哈維爾,捷剋會怎樣;如果沒有曼德拉和圖圖大主教,南非會怎樣;如果沒有翁山蘇姬,緬甸會怎樣。愛因斯坦在悼念居裏夫人時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曆史進程的意義,其道德方麵,也許比單純的纔智成就方麵還要大。」這句話也可用在劉曉波身上。在「我沒有敵人」的宣告背後,是劉曉波長期思索的一個問題,即「寬恕與正義如何獲得平衡」。
是的,他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但這個國傢充滿瞭敵人和仇恨。他生在世界上唯一一個囚禁諾貝爾和平奬的國傢,也最終被這個國傢所謀殺。
「親愛的,該起身瞭,通往深淵的橋就要坍塌。」
「讓我的頭再一次 高貴地昂起,直到 最黑的時刻降臨。」
這不僅僅是情詩,也是命運的預言。最黑的時刻降臨瞭,但劉曉波和劉霞在黑暗中仍然發光。世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囚禁曉波的心靈,他沒有翅膀,卻可以像鳥一樣飛翔;在不自由的國度裏,他們是最自由的人。
著者信息
餘傑
旅美華裔獨立作傢。一九七三年生於四川成都,北京大學文學碩士。先後齣版四十多本著作,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奬」、「公民勇氣奬」等奬項。
二〇〇四年,餘傑與劉曉波等共同起草「中國年度人權報告」,遭警方拘押。二〇一〇年十月,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奬」之後,作為劉曉波親密友人的餘傑被非法軟禁數月,進而遭到黑頭套綁架、酷刑摺磨至昏死。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攜妻兒齣走美國,定居華盛頓郊區,創辦「亞太宗教自由與民主化研究所」,緻力於民主人權、公民社會與宗教信仰自由等議題的研究。
著有《1927民國之死》、《我無罪:劉曉波傳》、《在那明亮的地方:颱灣民主地圖》、《我也走你的路:颱灣民主地圖第二捲》、《人是被光照的微塵:基督與生命係列訪談錄》、《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颱灣同行》、《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50本書》等作品。
圖書目錄
劉仲敬序
盧斯達序
葉浩序
作者自序
第一捲 被謀害的先知
愛與黑暗的故事——劉曉波的文學與人生
看哪,那個口吃的人——我與劉曉波交往的點點滴滴
在橫眉與俯首之間——為劉曉波五十三歲生日而作
探望劉霞受阻記
劉霞也成為一座孤島
將陽光和自由歸還給劉曉波——緻共産黨最高決策者的公開信
誰謀害瞭劉曉波?
第二捲 異議人士中的異議人士
文字收功日,中國民主時——《大國沉淪:劉曉波政論集》編輯手記
為什麼說愛國主義是一個巫術詞?——讀《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
反抗的高度——讀《劉曉波文集》
讓中國解體,讓人民自由——序《統一就是奴役》
非毛化是中國邁嚮現代化的第一步——序《混世魔王毛澤東》
從「持不同政見者」到「持自己政見者」——讀《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
劉曉波從未幻想中共啓動政改——讀《追尋自由:劉曉波文選》
從「中國的劉曉波」到「東亞的劉曉波」——《劉曉波傳》日文版序
第三捲 劉曉波與《零八憲章》
我們唯有勇氣和謙卑——我為何在《零八憲章》上簽名?
在一封公開信上簽名究竟有什麼價值?
與國保警察談《零八憲章》
中共為何拒絕《零八憲章》這根救命的稻草?
從《零八憲章》看一百年前的立憲運動——為劉曉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立憲與革命——從康有為與章太炎的論爭看《零八憲章》的改良主義
我們共同的人性尊嚴——《零八憲章》與《亞洲人權憲章》之比較
不是公車上書,而是公民宣言——與曹長青商榷
第四捲 這個時代的異端思想傢
曆史的選擇——諾貝爾和平奬為何頒給劉曉波?
「我們是美國人」及「支持伊戰」——作為古典自由主義者的「右派」劉曉波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如何理解劉曉波的「無敵論」?
非暴力是走嚮自由中國的唯一道路——劉曉波為何既反對政府暴力,又反對民間以暴易暴?
從罪人到聖人的漫漫長路——劉曉波與曼德拉之比較
附錄
《零八憲章》
我沒有敵人(劉曉波的法庭最後答辯詞及諾貝爾和平奬缺席演講稿)
劉曉波年譜簡編
圖書序言
圖書試讀
《愛和黑暗的故事》是以色列作傢阿摩斯.奧茲(Amos Oz)帶有自傳體色彩的長篇小說,也是我這幾年來讀到的最偉大的小說之一。我很少用「偉大」這個形容詞來定位一本小說——而《愛與黑暗的故事》是當之無愧的,它既是一部傢族史,也是一部民族史與國傢史。那裏麵,有愛,也有仇恨;有黑暗,也有光明;有絕望,更有救贖。
「我在樓房最底層一套狹小低矮的居室裏齣生,長大」,小說從這個句子開始瞭長達五百多頁的講述。這不是一個絢麗而驚艷的開頭,但絕對是順暢而清澈的,如同大河的源頭,而且必然具有一種平靜的氣質。一部作品能稱為偉大,絕不會因為它的控訴、憤怒與無助,就像作者的祖母曾經對他說的:「當你哭到眼淚都乾瞭,這就是你應該開始笑的時候瞭。」
阿摩斯.奧茲說過:「你可以迴避曆史,曆史不會迴避你。你可以逃離,或者轉過身來迴顧以往,但是你不能消除他們……我們不可以成為曆史的奴隸,但是在歐洲這片土地,人們必須跪下,將曆史扛上肩頭。隻有這樣,我們纔能去我們想去的地方。」在承受苦難、珍惜記憶、捍衛曆史的維度上,華人跟猶太人非常相似。有時,曆史需要像閘門一樣扛在肩頭。劉曉波就那樣謙卑地跪下來,將當代中國苦難的曆史——特彆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的曆史——扛在肩頭上。我在寫作《劉曉波傳》的時候,恍然覺得自己也是在寫一個關於愛與黑暗的故事,描述劉曉波的文學與人生,沒有比這更為妥帖的說法瞭。
二〇〇五年,法國具有領袖地位的知識分子索爾孟(Guy Sorman)訪問中國,走遍大江南北,訪問各個階層的中國人,寫齣瞭《謊言帝國》一書。索爾孟為西方讀者描述瞭一個被謊言重重包裹的中國,也錶彰瞭若乾與謊言戰鬥的、值得尊敬的中國人,其中就有劉曉波夫婦。有意思的是,這位目光敏銳的知識分子,在採訪劉曉波夫婦之後,並沒有將劉曉波作為「傳主」,偏偏將劉曉波的妻子劉霞選為「傳主」。
劉霞在作為猶太人的索爾孟麵前,將自己形容為「中國的猶太人」。索爾孟認同這一嚴重而真誠的比喻,並以此作為書中這個章節的題目。經過兩韆年的顛沛流離和二十世紀納粹屠猶的慘劇,「猶太人」的身分不再是作為上帝選民的榮耀,而是隱喻著必然經曆無邊苦難與羞辱的「賤民」。
用户评价
我對《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可以用“震撼”來形容,但這種震撼並非來自情節的跌宕起伏,而是來自一種深刻的、持久的思想共鳴和情感觸動。作者以一種近乎悲憫的情懷,將劉曉波先生近乎傳奇的一生,以及他那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融為一體,呈現給讀者。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那些敏感的曆史事件時所展現齣的剋製與冷靜。他並沒有煽動情緒,而是用紮實的史料和嚴謹的邏輯,去呈現事實的原貌,去解讀那些復雜的社會背景和政治環境。 書中對於劉曉波先生在“八九事件”後的處境,以及他所遭受的打壓和迫害的詳細記述,讓我對那個時代的殘酷有瞭更深刻的認識。我看到瞭一個曾經充滿理想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在現實的洪流中,一步步被推嚮瞭風口浪尖,又如何在一次次的磨難中,愈發堅定自己的信念。作者對他所撰寫的“零八憲章”的解讀,以及因此而引發的巨大爭議和後果,都進行瞭詳盡的梳理。這讓我得以理解,為什麼這樣一份宣言,會在當時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又為什麼它會被視為對國傢體製的一種深刻挑戰。這本書讓我意識到,劉曉波先生的思想,並非空中樓閣,而是深深植根於中國現實的土壤之中,他的每一個論斷,都是在對中國社會的病癥進行切實的診斷,並試圖開齣藥方。
评分《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這本書,給我帶來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增長,更是一種精神的洗禮。作者在書中對劉曉波先生的思想演變過程的梳理,讓我看到瞭一個思想傢是如何在時代的洪流中,不斷反思、成長,並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思想體係。我尤其被書中關於劉曉波先生對“啓濛”的理解所吸引。他認為,中國的啓濛並非僅僅是知識的傳播,更是對國民性改造的深刻呼喚。 作者在書中對劉曉波先生所經曆的每一次審判和監禁,都進行瞭詳盡的描述。我看到瞭一個在法庭上據理力爭的知識分子,也看到瞭一個在獄中依然保持著樂觀和幽默的鬥士。那種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在黑暗中點燃火炬的精神,深深地打動瞭我。書中對劉曉波先生最後的日子,以及他生命的最後時刻的描繪,更是讓人心碎。在病榻上,他依然沒有放棄對自由的追求,依然在用盡最後一絲力氣,呼喚著中國的民主和進步。這本書讓我深刻地認識到,劉曉波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關於勇氣、尊嚴和自由的史詩。他的生命,如同一顆劃過夜空的流星,雖然短暫,卻照亮瞭無數黑暗的角落。
评分這部厚重的著作,在我拿到它的時候,就感受到瞭一種沉甸甸的分量,不僅僅是紙張的堆疊,更是它所承載的關於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人的生命重量。我自認算是個對中國當代曆史和社會問題有一定關注的讀者,但翻開《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的扉頁,我依然被一種巨大的、撲麵而來的信息量和情感衝擊所震撼。作者沒有選擇用簡單的敘事拼湊,而是以一種極為精細的解剖刀,深入到劉曉波先生個人生命軌跡的每一個細微之處,將他從一個普通的學者,一步步走嚮“自由鬥士”的曆程,用一種近乎考古學般嚴謹的態度,抽絲剝繭地呈現齣來。 書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於劉曉波早期思想的梳理。那段時期,彼時的中國正經曆著劇烈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動蕩,而年輕的劉曉波,以其驚人的敏銳和深刻的洞察力,在那個洪流中留下瞭深刻的印記。作者詳盡地引用瞭大量的文獻資料,包括他發錶的論文、演講稿,甚至是當時的一些私人信件,讓我得以窺見一個思想傢是如何在時代的激蕩中形成自己的觀點,又如何在現實的睏境中不斷修正和深化。那種對“中國病”的診斷,對國民性改造的呼喚,以及對啓濛精神的執著追求,在書中被描繪得淋灕盡緻。我尤其被作者對劉曉波早期那些帶著些許激進和理想主義的論述的解讀所吸引,他並沒有迴避那些可能引起爭議的觀點,反而通過深入的分析,展現瞭這些思想背後所蘊含的真誠和勇氣。這種還原,讓我覺得不再是隔著一層麵紗去理解一位偉大的思想傢,而是仿佛置身於他思想形成的關鍵時刻,與他一同經曆那份痛苦的探索和求索。
评分當我翻開《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這本書時,我內心深處感受到的是一種沉甸甸的責任感。作者以極其細緻和富有洞察力的筆觸,為我們勾勒齣劉曉波先生波瀾壯闊的一生。我特彆欣賞作者在分析劉曉波先生的思想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宏觀視野和微觀考量相結閤的能力。他並沒有將劉曉波先生的思想孤立起來,而是將其置於中國近現代曆史的大背景下,去審視其産生的土壤,去分析其傳播的影響。 書中關於劉曉波先生對中國政治體製的批判,以及他對憲政民主的倡導,都進行瞭深入的闡述。我看到瞭他對於中國社會弊病的深刻洞察,也看到瞭他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嚮的深切憂慮。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對劉曉波先生的觀點進行蓋棺論定,而是力求客觀地呈現其思想的邏輯和內涵。我尤其被書中關於劉曉波先生在海外所受到的關注和支持的描寫所感動。這讓我看到瞭,即使在被剝奪瞭自由的情況下,他的聲音依然能夠跨越國界,引起世界的共鳴。這本書讓我深刻地理解瞭,劉曉波先生之所以被視為“中國的曼德拉”,並非偶然,而是他用一生踐行瞭對自由和正義的承諾。
评分我一直認為,理解一個人的思想,必須先理解他的生命。而《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恰恰做到瞭這一點。這本書的偉大之處在於,它並沒有將劉曉波先生簡單地標簽化,而是用一種極其人性化、極其細膩的筆觸,描繪瞭一個鮮活的、有血有肉的個體。從他童年時期的生活經曆,到他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所經曆的愛恨情仇,再到他與傢人、朋友之間的復雜關係,作者都毫不避諱地展現齣來。我尤其為書中關於他與妻子劉霞女士之間深沉而又充滿犧牲的愛情的描繪所感動。那種在極端環境下,兩人之間相互扶持、相互慰藉的感情,其力量足以穿透最堅固的牢籠。它讓我看到瞭,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刻,人性的光輝依然能夠閃耀,愛與希望依然能夠成為支撐個體前行的強大動力。 作者在書中對於劉曉波先生個人性格特質的刻畫也十分到位。他既有知識分子的傲骨和堅持,也有普通人的脆弱和無奈。在一次次被囚禁、被壓迫的過程中,他所展現齣的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智慧,都讓我肅然起敬。書中記錄瞭他在獄中寫下的那些詩句,那些充滿力量和哲思的文字,仿佛是他對抗黑暗的武器,是他對自由最真摯的呼喚。我常常在閱讀這些片段時,會不自覺地紅瞭眼眶。因為我能感受到,那不僅僅是一個人的痛苦,更是無數在不自由國度裏,渴望自由的靈魂的共鳴。這本書讓我深刻體會到,劉曉波先生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部最偉大的詩篇,一部用鮮血和淚水書寫的關於勇氣和尊嚴的史詩。
评分讀完《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們有幸能夠通過這本書,近距離地“認識”一位如此偉大的人物。作者用一種極其詳盡和深入的方式,為我們展現瞭劉曉波先生的思想世界。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梳理劉曉波先生思想脈絡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嚴謹和條理。他能夠將劉曉波先生在不同時期、不同場閤所發錶的觀點,有機地聯係起來,形成一個完整而 coherent 的思想體係。 書中對於劉曉波先生對中國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他對中國前途的憂慮,都進行瞭詳細的闡述。我看到瞭他對於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麵臨的種種挑戰的深刻理解。作者在書中對劉曉波先生所經曆的流亡、監禁、迫害,都進行瞭客觀而細緻的記錄。我看到瞭一個在逆境中不斷成長和升華的靈魂。這本書讓我深刻地理解瞭,劉曉波先生之所以被稱為“中國的良心”,是因為他用自己的生命,詮釋瞭何為真正的自由和尊嚴。
评分《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這本書,為我打開瞭一個全新的視角,去理解劉曉波先生以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作者以一種極其深刻和富有穿透力的筆觸,為我們展現瞭劉曉波先生的生命軌跡和思想世界。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劉曉波先生對“公民社會”的構想,以及他對個體權利的強調。這些思想,在當時極具前瞻性。 作者在書中對劉曉波先生所承受的巨大壓力和孤立,都進行瞭詳盡的描述。我看到瞭一個在孤軍奮戰中,依然堅持自己信念的鬥士。書中也記錄瞭他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深刻思考,以及他對中國人民的殷切期盼。這本書讓我深刻地認識到,劉曉波先生的生命,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那個時代無數追求自由者的縮影。他的聲音,雖然被壓製,但他的思想,卻如同種子一般,在悄然地生根發芽。
评分在我閱讀《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的過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作者以一種極其深情和富有力量的筆觸,為我們展現瞭劉曉波先生非凡的一生。我尤其欣賞作者在對劉曉波先生思想進行解讀時,所展現齣的那種深刻的哲學關懷。他能夠將劉曉波先生的每一個論斷,都上升到對人類生存境況的普遍性追問。 書中對於劉曉波先生在獄中對“自由”的理解,以及他對“希望”的定義,都進行瞭詳盡的闡述。我看到瞭一個在黑暗中依然能夠保持光明的靈魂。作者在書中對劉曉波先生所經曆的每一個重大事件,以及他所付齣的巨大代價,都進行瞭客觀而真摯的記錄。我看到瞭一個用生命踐行理想的英雄。這本書讓我深刻地理解瞭,劉曉波先生的價值,不僅僅在於他提齣瞭多少深刻的理論,更在於他用自己的一生,為我們樹立瞭一個關於勇氣、尊嚴和自由的生命榜樣。
评分《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這本書,對我而言,是一次思想的啓迪,更是一次心靈的震撼。作者以一種近乎虔誠的態度,為我們展現瞭劉曉波先生在漫長人生中所經曆的種種磨難,以及他在這過程中所展現齣的不屈精神。我尤其對書中關於劉曉波先生在獄中對文學、對藝術的思考感到敬佩。即使身處絕境,他依然沒有放棄對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追求。 作者在書中對劉曉波先生的“絕食抗爭”的描寫,讓我看到瞭他為瞭信念,可以付齣生命的代價。那種視死如歸的精神,讓人動容。書中也記錄瞭他與傢人之間的深情厚誼,以及他對朋友的真摯情誼。這些細節,讓劉曉波先生的形象更加立體和豐滿。我看到瞭一個偉大的思想傢,也看到瞭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這本書讓我深刻地體會到,追求自由的道路,從來都不是輕鬆的,它需要巨大的勇氣和堅定的信念。劉曉波先生的生命,就是對這種信念最生動的詮釋。
评分作為一名普通的讀者,在閱讀《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的過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這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次與一位偉大靈魂的深刻對話。作者用一種極其真誠和充滿敬意的筆觸,為我們展現瞭劉曉波先生不平凡的一生。我非常喜歡書中關於劉曉波先生對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反思,以及他對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堅持。這些思想,在那個年代,是何等的稀缺,又是何等的寶貴。 作者在書中對劉曉波先生的“沉默”的解讀,尤其讓我印象深刻。在漫長的牢獄生涯中,他選擇瞭用沉默來對抗壓迫,用一種超然的態度來麵對苦難。這種沉默,並非軟弱,而是一種更強大的精神力量。它讓我看到瞭,即使在最無力的境地,個體依然可以通過精神的堅守,來保持自己的尊嚴和獨立。書中對於劉曉波先生在獲得諾貝爾和平奬後的處境的描寫,更是讓人心痛。他無法親自領奬,他的名字在那一刻,成為瞭一個被禁忌的符號。作者用一種平實的語言,記錄下瞭這一切,但字裏<bos>的悲涼和無奈,卻如同潮水般湧來,讓人無法呼吸。這本書讓我深刻認識到,追求自由的道路,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充滿瞭荊棘和犧牲。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