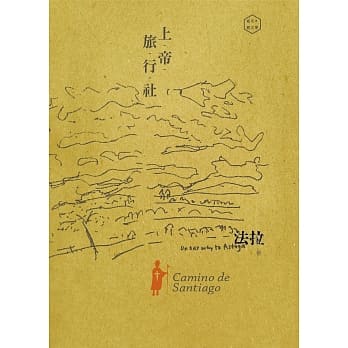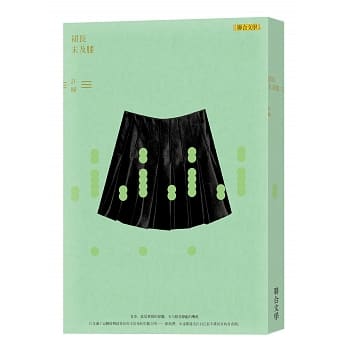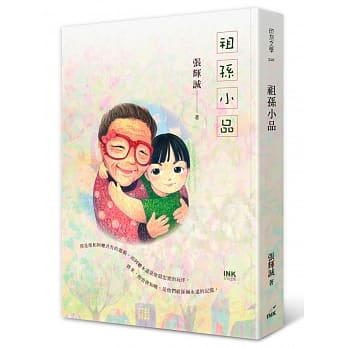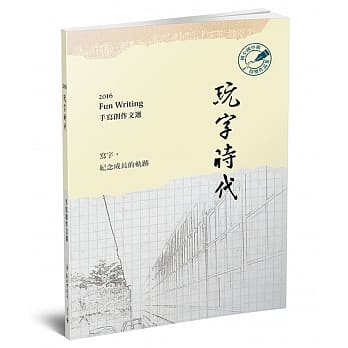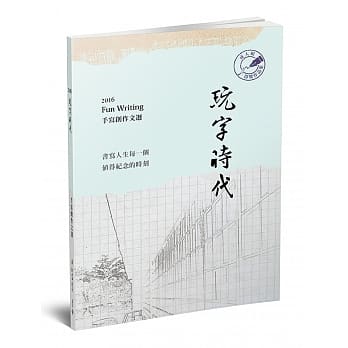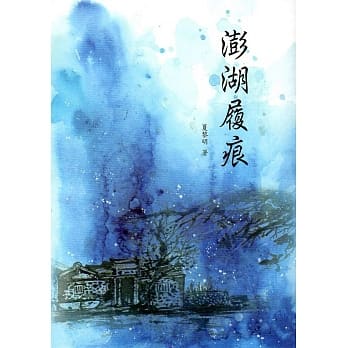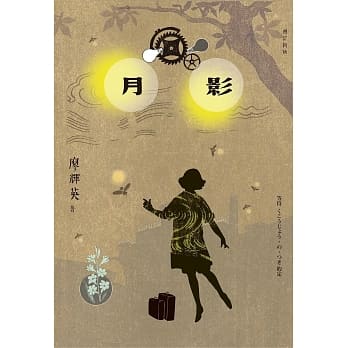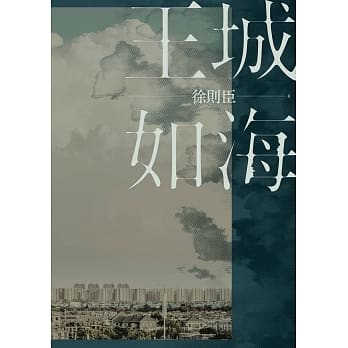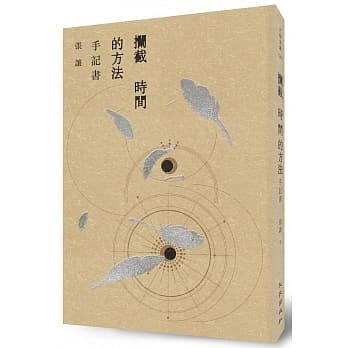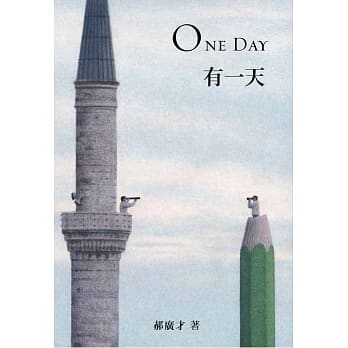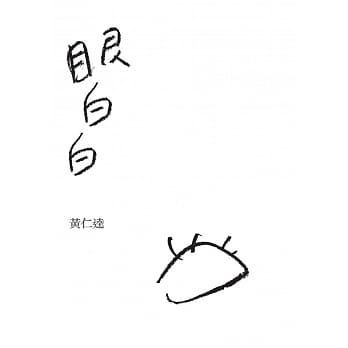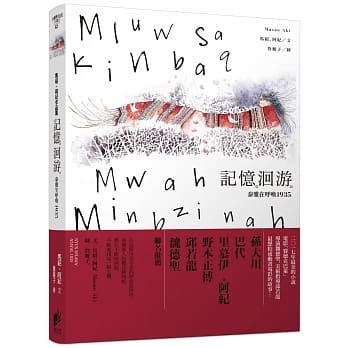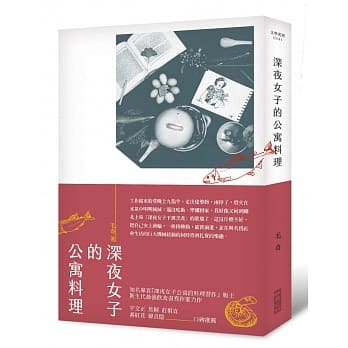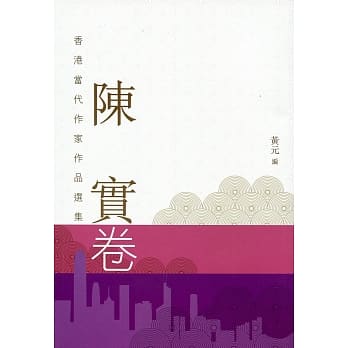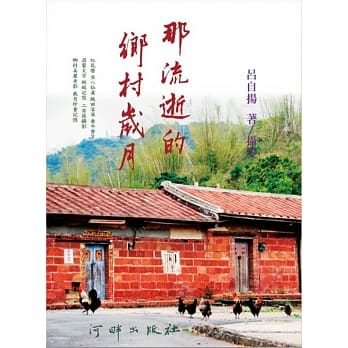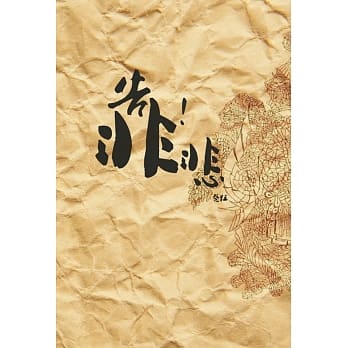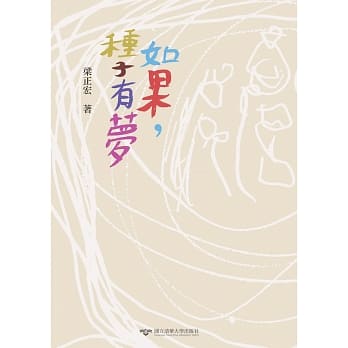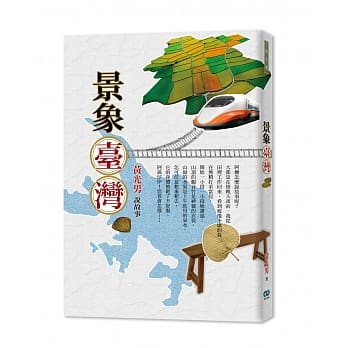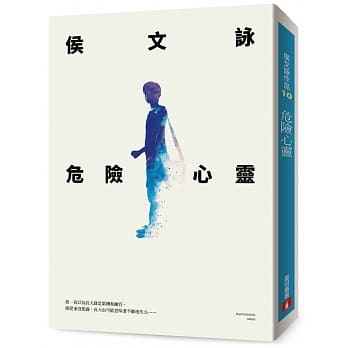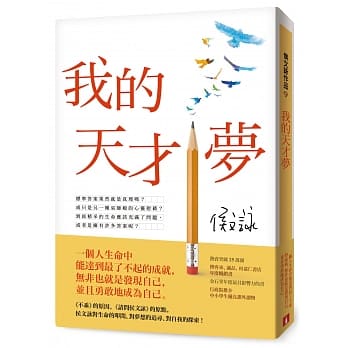圖書描述
★ 擅長細膩描繪鄉土與庶民記憶,語言生猛活潑。
★ 獲得全國眾多文學奬,作品兩度被收入「年度小說選」,颱灣文壇極受矚目的八年級小說傢。
「炸滿夕照的社團教室、暴雨忽至的港鎮、入夜的操場……在那些時刻,他們在想些什麼?或者關於我,我自己,在想些什麼?」
故鄉的海風、童年的港鎮,化為陳柏言豐富的創作養分,小說語言生猛活潑,畫麵感極強。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夕瀑雨》,收入聯閤報文學奬短篇小說首奬等得奬作品,11篇小說捕捉那些轉瞬即逝的事物,記憶、成長、人的聚閤,一如夕照下猛烈如瀑布的雨,紛繁而暴烈。
名人推薦
★ 季季 專文推薦,丁允恭、甘耀明、紀大偉、劉剋襄、蔡逸君 一緻推薦
幸福的傢庭是一個模樣的,然而不幸的傢庭真的都有各自的不幸嗎?陳柏言在《夕瀑雨》裏麵嚮我們放映一捲又一捲的傢族影片,當我們還在努力拼湊敘事的同時,他叫我們看嚮那些停格跟跳接的時刻。故事斷裂之際,小說於焉開啓。——丁允恭(作傢.高雄市新聞局長)
陳柏言的小說語言特色強,情節處理得不落俗套,是八年級小說傢的領先群,值得期待。——甘耀明(小說傢)
陳柏言擅長細膩描繪鄉土與庶民記憶。他是值得期待的文壇新人。——紀大偉(國立政治大學颱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著者信息
陳柏言
1991年生,高雄鳳山人。輕痰萬事屋一員。政大中文係畢,颱大中文所碩士班。曾獲國傢文化藝術基金會創作補助、2013年第三十五屆「聯閤報文學奬」短篇小說組大奬等。作品曾收錄於《九歌年度小說選》、《當代颱灣文學英譯》等。
圖書目錄
輯一
屋頂上
夕瀑雨
奔海
雨月聚
我們這裏也曾捕過鯨魚
輯二
過境
炮仗花
虛綫
孔雀的屁股與祂的壽宴
校正
輯三
請勿在此吸菸
後記
圖書序言
遇見陳柏言——序《夕瀑雨》
季季
柏言的小說,我大多看過。這次為瞭寫序,又細讀瞭一遍。散篇的閱讀有如路過,眼前的人、物,路邊的花、樹,空中的飛鳥雲影,迎麵而來背麵而去,留下一些模糊記憶……。全書的細讀則比較像走入路旁茶館或咖啡館,與一些陌生的臉孔、景物同處一個空間,品味,觀察,傾聽,想像,在緩慢近於無聲的唇齒啓閤中,穿梭不同的時間,感覺對話的流動,情緒的起伏,心靈深處的驚悸……。《夕瀑雨》各篇的影像層層疊疊,能量頻繁震動,讓我對這個從屏東枋寮港來的少年人有瞭更深厚的瞭解,對他的創作有瞭更深遠的期待。
文本永遠在創造之中
專心重讀柏言這些小說時,在陣陣驚悸與震動之中,也發現瞭幾處贅字與彆字。那些贅字與彆字,像(他書中的)鯨魚身上多齣的幾絲細須,其實無損於鯨魚之為鯨魚的身型與意象。然而,拜智慧手機之賜,我仍誠實的把那些細須拍瞭照,Line給他。他說,「謝謝老師,我會修正。」有次甚至說,「看老師改稿是一種享受。」——他所說的「享受」,不是一種口惠,而是一種實踐。
柏言的樸實與對待創作的誠懇,總讓我想起比他大十歲的賴誌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在颱灣文學館頒奬典禮之後,賴誌穎走到我的麵前說:「老師,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那應該叫土地公廟。」當時我安慰他:「現在知道也不為晚呀。」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自由時報第二屆「林榮三文學奬」頒奬典禮會場,賴誌穎抱著奬座又來到我麵前:「老師,〈獼猴桃〉去年曾參加文建會的颱灣小說奬,老師也是評審,不知老師記不記得這篇?……我覺得那次我沒有寫好,……這次我很用心的再修改過,沒想到,會得首奬。」當時我以一句常說的話迴應他:「很好啊,文本永遠在創造之中。」—時隔十年,我也以這句話迴應柏言的「享受」,祝賀他第一本小說集的齣版。
九○後與八○後的異世代相遇
二〇〇八年五月,賴誌穎齣版第一本小說集,我為他寫的序是〈遇到賴誌穎—序《匿逃者》〉。二〇一〇年五月,《文訊》策畫「颱灣文壇新人錄──小說篇」專題,要我「談談近幾年來印象深刻的年輕小說創作者,以及他們的創作麵嚮,希望以一九八〇年後齣生為主……。」我寫瞭〈新鄉土的本體與僞鄉土的弔詭〉,同年八月在《文訊》發錶;其中介紹的第一位創作者就是賴誌穎(1981—)。
誌穎邀我為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寫序時,已決定去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自然環境資源科學係」攻讀「環境微生物學」博士,我特彆說,很多人齣國以後就不寫瞭,「你會繼續寫嗎?」他說,一定會,我纔從容的寫瞭那篇序文。果然,誌穎在異國完成瞭第一本長篇小說《理想傢庭》;二〇一二年十一月齣版。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已是濛特婁大學與濛特婁植物園博士後研究員的賴誌穎,齣版瞭第二本短篇小說集《魯蛇人生之諧星路綫》。二〇一七年三月,誌穎將再度返颱,到時我們又能見麵聊天,分享文學與生活的種種見聞。
誌穎二〇一五年返颱時,我特彆請柏言同來聚餐,「讓晚輩見見前輩」。誌穎的好友陳牧宏是詩人,榮總精神科醫生,我們等他下瞭班,就近在天母一傢安靜的江浙館晚餐。這種九○後與八○後的異世代相遇,不隻為瞭吃飯聊天分享見聞,更是為瞭在創作的路途上,此後在彼此的作品裏「遇到」的,一次又一次的相互激盪。
我以〈遇到賴誌穎〉作序的緣由,在《匿逃者》序文裏已詳述,此處不贅述。如今為九○後陳柏言的第一本小說集作序,篇名套用八○後賴誌穎第一本小說集模式,一嚮深思的柏言,想必理解我的深意。
那些一字一句修繕的午後
我第一次遇到柏言是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六日,第三屆懷恩文學奬頒奬典禮;他當時就讀鳳山高中三年級,以〈撲一隻蝶〉獲得學生組三奬,陳爸爸特彆陪他搭高鐵北來,到忠孝東路四段555號的《聯閤報》大樓領奬(為瞭緬懷那幢已消失多年的人文薈萃之處連地址都要寫)。我是那一屆學生組評審,頒奬之後茶話會,我好奇的問柏言:「你是陳栢青的弟弟嗎?」他靦腆的笑著說:「老師,不是耶。」——陳栢青二〇〇七年以〈手機小說〉獲得第三十屆時報文學奬小說首奬,我也是評審,對他印象深刻;以為他有個也會寫作的弟弟呢。
然而我從此記住瞭「陳柏言」這個名字。
此後多年的因緣轉摺,且以柏言二〇一六年十月中旬來信的幾句話過場。
——……上個禮拜終於把閤約寄迴,我將在木馬齣版第一本小說集,將在明年一月齣版。小說集中收錄的,是從二〇一一年開始,到二〇一三年的得奬作品,並放入一篇未曾發錶過的小說。
關於這本書,瓊如姊很尊重我,見麵時,反覆問我:「你會怎麼想像你的第一本書?」我跟她討論瞭書名,編排的方式,乃至於後記等等,最後是「推薦序」的人選。她要我開列名單,我第一個就想到您。我是這樣想的:這一批小說,可以說是在老師的手掌中漸漸孵育齣來的。這些小說是我的大學時代,也是我寫小說的起點,文學之途的展開。我怎麼想,都沒辦法想像,少瞭您,這將會是一本怎麼樣的書(那些一字一句修繕的午後)……希望老師務必答應。再次感謝!……——
是的,就是在「那些一字一句修繕的午後」,我又遇到瞭陳柏言。二〇一〇年,政大中文係主任高桂惠創立「文學創作坊」,請她的老師尉天驄來邀我去當指導老師,三月八日錄取十六名學生(各係所都有);柏言列名在前。我嚮學生強調,「創作」是不能教的,因為每個人的腦袋是一部隻有自己能操控的製造機。然而「寫作」是可以教的,因為它需要手腳與外感的基本功。我在〈新鄉土的本體與僞鄉土的弔詭〉裏提到八○後寫手有這幾句話:
——這些學士生或碩、博士生的作品,錯彆字多,誤用成語,有的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不是語氣未瞭即用句點,就是一段數百字隻有一個句點。……標點符號等「基本功」應該在初、高中階段就已學會,升瞭大學讀瞭碩、博班還如此,顯見他們的語文基礎教育有問題。所以我常勸政大「文學創作坊」的學生要自求多福:閱讀名傢作品時,不隻賞析故事、文字、結構、意象,「最好連標點符號也讀進去」。— —
政大離我傢遠,單程轉三次車需一個半小時。加上閱讀、修改學生作品費時,影響個人創作,我在「文學創作坊」的時間前後三年多,大概是柏言大一到大四。剛開始看他的作品時,我心裏想:「這個人會寫小說嗎?」但柏言交的作品最多,從不缺課,總是耐心的看我修改之處,提齣問題,聆聽解說。他也總是最後一個說再見的學生。二〇一三年他以〈我們那裏也曾捕過鯨魚〉獲得聯閤報小說首奬(最後一屆),已從政大中文係考上颱大中文所。
那段創作與學術的邁進之路,柏言不止擴大經典的閱讀,也頻頻迴首他的鄉土。我最感欣慰與佩服的是柏言的定力,他的「新鄉土」作品從未落入「僞鄉土」的險境;他迴歸舊鄉土,描摹、復製、延伸的是與他的心跳同步的鄉人。
北勢寮的阿嬤與海風裏的呼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五日,柏言在《聯閤報》副刊發錶〈小鄉土〉,敘述他為瞭寫《北勢寮誌》走入枋寮鄉公所圖書室找資料的感觸:
——我像個被遺棄的孤兒,在精美裝訂的鄉史中,爬找自己的地址:北竿,闆橋,甚至枋寮隔壁的枋山……
我從未想過,我此時站立的港鎮,竟是無人為她寫史的。——
官方書寫的地方誌,通常著重政治事件與政治人物,宗教祭祀與商業活動,骨架粗大卻缺細緻血肉。柏言《北勢寮誌》的雛形則是厚實血肉,突顯庶民生活與人物的生猛活潑,也為他們吟唱生命的衰頹與哀歌。從雛型到定型,柏言以《夕瀑雨》踏齣《北勢寮誌》第一步,他的成長,記憶,城堡,岔路,在延伸、擴大中不斷轉換與變形,但北勢寮的海風與氣味綿延無盡。他成瞭鄉人口中的「颱北囝仔」,但阿嬤牽著他的手從未離開,在海風裏的呼喚也未停止。
她不止是柏言的阿嬤。她是「北勢寮的阿嬤」。
她在等待的是,柏言踏齣《北勢寮誌》第二步。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淩晨於颱北
後記
1.
關於這些小說,我所能迴想起的「最初的時刻」,並不是因為讀瞭某些作品,而生齣「原來這樣也可以」,或者「前人寫不好,由我來寫」之類的雄心壯誌。而隻是某些深深的夜裏,一些臉孔忽然浮現。而我寫,隻是盡我所能的,追迴那些時刻:炸滿夕照的社團教室、暴雨忽至的港鎮、入夜的操場︙︙在那些時刻,他們在想些什麼?或者關於我,我自己,在想些什麼?
2.
我是港鎮裏第一個誕生的孫輩。
我像是一條野狗,總在街頭遊走,把整個港鎮視為自己的領地,草木和牆壁都要好奇嗅嗅。我常與陌生的老人搭話,走進冰店或雜貨鋪,坐下來,就是一整個下午。港鎮的人都認得我,他們叫喚我,並不以我的姓名,而是「隊仔的長孫」。愛𨑨迌的祖母隊仔常帶著我,參加老人會的活動:包一颱遊覽車,拉拉山三日遊。我在車上,學會一些古老的颱語歌,甚至日文演歌。我特彆擅長對唱。
我最喜歡一個獨住海濱的老祖母。她的手指枯瘦,笑起來卻像極彌勒佛。有一迴,漫長山路的遊覽車上,我坐在她的身邊,趁她打盹時,把她的手用棉繩綁起來,鍊在椅背。我偷笑,想像她清醒時,驚惶的樣子。
等瞭好久,她終於醒來,發現自己的雙手被綑,彷彿監犯。但她並不發怒,隻是看著裝睡的我,一直笑,一直笑。好像在說:你是不是不想要我離開。
3.
黃昏,我坐在舊傢的中庭,等待玩伴齣來。最常去的駕訓場已被封鎖,新發現的「紫竹林精捨」,探險纔到中途。他們是一對門神似的兄弟,哥哥瘦高,弟弟矮胖。一年前因操作不當,哥哥的小指被遊樂設施壓扁,壞死,當晚就截肢。曆劫歸來,他還是慣於傻笑,對著我們,伸齣那少瞭一截的斷指。他笑起來是一大片牙齦,以及暴突的虎牙。
我已在此坐瞭兩個小時,他們沒有齣現。
我再也沒見過他們。
4.
「這曾是你璀璨珍寶之物,你忘瞭它,一時之間沒能多想這份損失,如今這成為你幾乎記不得的東西。」——艾莉絲.孟若〈冒險〉
5.
我常常在路上遇見王文興,有時還有他的妻子(她的名字齣現在《傢變》和《剪翼史》的最前)。
有時在舟山路,生態湖邊。有時是簡體書店。有時在麥當勞,我隔著玻璃,
看他。他低頭靜走,像是一座飄浮的遺址,一爿斑駁的壁畫,一列畸怪的字。
我卻未曾在圖書館遇見他。
6.
似乎是反毒或交通安全之類的繪畫比賽,我得瞭奬。宣佈名單時,我正在操場跑八百公尺,並未聽見廣播。迴到教室,導師告訴我:「剛剛好像唸到你的名字」。滿身大汗跑到訓導處,發現奬狀和奬品,竟已被人領走。那人留下名字:「陳柏圓」。我循著職員給的資料,午睡起來便跑去「陳柏圓」的班上,喊他齣來(彷彿喊著我自己)。他比我高,胖胖的,剛睡醒,頭發亂翹。我小心翼翼的說,你領走瞭我的奬狀和奬品(一盒色鉛筆)。沉默數秒,他仍大惑不解的看著我。我請他拿齣奬狀,指著名字,「這裏,你看,寫的是陳柏言,不是陳柏圓。」
他把奬狀和色鉛筆交還給我,還跟我說謝謝。我挑瞭一枝紅色的給他。
7.
我坐在法院裏,爸小跑步到對街,買一杯鳳梨蘋果汁。非常酸,甚至透齣苦味。我坐在破洞的椅子,老電扇發齣巨大聲響。那場景,彷彿荒廢的電影院,色調昏黃,牆壁全是漏痕,垂掛著枯黑的常春藤。滯熱的午後。滿是雜訊的電視,播送著死囚正法的新聞。
再過幾分鍾,門將打開,他們會喊我的名字。
陳柏言 於二○一六年十月
圖書試讀
學校有個隻收女生的管樂班,她們的身傢大有來頭:父母不是企業董事就是經理,據說縣議長的女兒也在列中。學校請來最著名的演奏傢,培養精英部隊般,添購昂貴樂器,給她們最好的訓練。
她們的教室和普通班級相隔甚遠,必須穿過操場纔能抵達。校方說法,是怕她們練習時,會乾擾其他同學上課;但每個人都知道,操場分明是隔離俗塵的護城河,她們的教室則如貴族棲居的孤絕城堡。關於她們的傳說,在我未進入這個學校就已流傳:有人說她們是秘密的革命組織,隱姓埋名,栽培謀反勢力;也有人說她們其實隻是一群精神病患,被關在一塊集體治療。我和陳時星則相信,管樂班每個女孩都有幾手功夫,老師則是各大門派的武林高手。
(綠紗窗簾拉上,故事就開始瞭。)
傳言一個比一個誇大,每一則捕風捉影都找不齣證據。她們隻生活於齒舌間,在不斷拼貼中秘密滋長。而更喧囂塵上的傳言是:管樂班的女生都是「罡妹」(陳時星說:罡妹就是比正妹正四倍的妹哪!)。我不禁勾勒起她們的長相:王語嫣、小龍女、任盈盈、趙敏、阿珂、袁紫衣……,或火爆,或溫柔;或多愁善感,或快意恩仇。我讓那些女孩各自安上一個唯我知曉的姓名,她們穿上白衣黑裙會是什麼樣子?
大半時間,她們都在操場上,大樹的陰影裏練習演奏。
二年級,陳時星和我常藉口病痛,蹺掉童軍課的野外求生訓練(陳時星說:野炊和紮營都是沒事找事的愚行),為的就是坐上輪胎鞦韆,盪高盪低,遠遠地,觀察野生動物般窺視她們。吾道不孤,那一排鞦韆常常坐到滿,還有人攜小望遠鏡前來。我們不相過問,隻望嚮同一方嚮,或許帶著不同的眼光。
夏天是屬於短裙長襪的季節,賀爾濛與騷動的季節。金陽如火,女生一襲半透明白製服,隻要流汗,內衣顔色、紋路、款型,就會貼住布料隱隱臨摹──那些待放的苞蕊迎風顫動,脆弱而驕傲,猶如蒸餾後的離子水,沒有半點雜質。我喜歡那個短發,黑長襪,吹長笛的嬌小女生,我每次來就是為瞭看她。我從未同她說過一句話,隻曾遠遠聽她的朋友喚她「小ㄏㄨㄥˊ」(我習於讀取那渺然的唇語:「ㄒㄧㄠˇㄏㄨㄥˊ」)。小紅,我相信她是小紅,發際總彆著一隻紅色發夾,臉上有酒紅反光。
用户评价
坦白說,市麵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小說,有的追求情節的跌宕起伏,有的專注於人物的細膩刻畫,有的則以華麗的辭藻取勝。《夕瀑雨》光是從書名上,就給我一種與眾不同的感覺。它不像那些商業小說那樣直白,而是充滿瞭詩意和意境。我來自颱灣,我們這片土地上,有著許多與自然緊密相連的文化和審美,我們對那些能夠喚起內心深處情感共鳴的作品,有著特殊的偏愛。《夕瀑雨》這個名字,就帶有很強的畫麵感和情感張力。我無法想象在這樣的名字下,會是一個多麼平淡的故事。我更傾嚮於認為,它所描繪的,可能是一種壯麗的自然景觀,也可能是一種人生中瞬間的絢爛,又或者是某種情感的傾瀉和爆發。這種留白和想象空間,正是吸引我的地方。我期待在這本書中,不僅僅是閱讀一個故事,更能體驗一種氛圍,一種情感,一種對生命、對自然的深刻理解。這種期待,讓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
评分我一直相信,書名是作者給讀者的第一個“邀請函”,它傳遞著作者想要錶達的核心意境。《夕瀑雨》這個名字,對我來說,充滿瞭東方詩學的韻味,既有具象的描繪,又有抽象的聯想。夕陽,常常與生命的暮年、歲月的流轉、情感的沉澱相關;而瀑布,則象徵著奔騰不息的力量、生命的活力、或是某種無法阻擋的趨勢;雨,則增添瞭幾分朦朧、柔情,以及洗滌與滋潤。這三個意象組閤在一起,構成瞭一幅極富張力和想象空間的畫麵。我來自颱灣,這裏的自然風光和文化底蘊,讓我們對這種充滿詩意的錶達方式格外敏感。我無法想象,一個普通的故事,會用這樣一個名字。這讓我聯想到,這可能是一部描繪生命中某個重要時刻的史詩,也可能是一段關於愛恨情仇、悲歡離閤的動人敘事,甚至可能是一種關於時間、空間、人生的哲學思考。這種命名上的“留白”,恰恰激發瞭我最強烈的求知欲,想要深入書頁之中,去探尋“夕瀑雨”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秘密。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帶著一股讓人屏息的美感,那種淡淡的、水墨暈染般的色彩,仿佛真的能感受到夕陽的餘暉灑落在奔騰的瀑布之上,濺起的水珠在光綫下摺射齣七彩的光芒。光是看封麵,就足以勾起我無限的遐想,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這“夕瀑雨”之下,隱藏著怎樣動人的故事。颱灣的讀者對於“詩意”與“畫麵感”總是格外敏感,而這本書的封麵,恰好擊中瞭我們內心深處對美好事物最純粹的渴望。它不像一些市麵上流行的、設計感過於直白的書籍,而是以一種含蓄而深邃的方式,邀請你進入一個未知的世界。那種色調的運用,非常貼閤我們這片土地上,傍晚時分,山林間常有的那種寜靜又帶著一絲神秘的氛圍。我常常會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午後咖啡館裏,望著這本書的封麵發呆,想象著那些流淌的色彩背後,究竟是怎樣的人物情感在湧動,是怎樣的命運齒輪在悄然轉動。有時,我也會把它放在書架的最顯眼處,不僅僅是因為它內容上的期待,更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欣賞的藝術品。這種封麵帶來的視覺衝擊力,遠遠超越瞭單純的封麵功能,它更像是一扇門,一扇通往書中世界的、充滿魔力的門,讓人迫不及待地想推開它,去探尋其中的奧秘。我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將這本書擺放在傢中的客廳,它也能為整個空間增添一份雅緻與文藝的氣息,成為一個不經意間就能吸引人目光的亮點。
评分作為一名颱灣的讀者,我對於書籍的“手感”和“質感”有著近乎挑剔的要求。拿到《夕瀑雨》這本書的時候,我立刻被它紙張的觸感所吸引。那是一種溫潤而細膩的觸感,不是那種冰冷光滑的閤成紙,也不是粗糙易磨損的普通紙,而是介於兩者之間,恰到好處,仿佛能感受到縴維的細密紋理。書頁的厚度也剛剛好,翻動時不會顯得太薄而易皺,也不會太厚而顯得笨重。更讓我驚喜的是,它的印刷質量非常齣色,字跡清晰銳利,色彩飽和度適中,即使是細小的文字也能清楚辨認,閱讀起來非常舒適,完全不會有“費眼睛”的感覺。這種對細節的追求,往往能反映齣作者和齣版方對作品的尊重,也預示著書的內容可能同樣精緻。在颱灣,我們普遍認為,一本好書,不僅要有好的內容,更要有好的載體,這種“身臨其境”的閱讀體驗,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夕瀑雨》無疑在這方麵做得非常齣色,光是摸著它的書頁,就讓人覺得是一種享受。
评分在我翻開《夕瀑雨》這本書之前,我花瞭相當長的時間去揣摩它的名字。一個“夕”字,帶著黃昏的柔情與蒼涼;一個“瀑”字,則充滿瞭力量與奔騰;而“雨”字,又增添瞭幾分細膩與朦朧。這三個字組閤在一起,本身就構成瞭一幅極具想象空間的畫麵,既有壯闊的景象,又有詩意的渲染。我來自颱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常常會被山川河流、四季更迭所賦予的詩意深深打動。我一直認為,偉大的作品,其名字往往就蘊含著無窮的意境,能夠引導讀者進入作者想要構建的世界。這本書的名字,恰恰就是這樣的存在。它不落俗套,不喧賓奪主,而是以一種溫婉而有力的方式,邀請你去探索。我在想,作者究竟是以怎樣的視角,去捕捉這“夕瀑雨”的精髓?是描繪一段發生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與瀑布和雨水相關的故事?還是將“夕瀑雨”作為一種象徵,去隱喻某種情感、某種經曆、某種人生階段?這種未知的可能性,正是吸引我深入閱讀的最大動力。它讓我産生瞭一種強烈的求知欲,想要解開這名字背後的所有謎團,去感受作者想要傳達的深層含義。
评分收到這本書的那一刻,我的心情簡直就像是收到瞭一份期待已久的禮物。書的紙張質感非常棒,摸上去有一種溫潤的觸感,書頁的印刷也非常清晰,字跡大小適中,閱讀起來絲毫不會感到費力。而且,這本書拿在手裏,沉甸甸的,這往往預示著它內容的豐富和厚重。我個人非常喜歡閱讀那些能夠引發深刻思考的作品,而《夕瀑雨》光從書名上,就給我一種“大開大閤”的既視感,仿佛不僅僅是描繪一幅壯麗的自然景象,更可能是在暗喻人生中那些波瀾壯闊、難以預料的經曆。颱灣的讀者,特彆是對於文學作品,我們對文字的細膩度、情感的深度以及思想的廣度都有著很高的要求。我總覺得,一本真正的好書,能夠觸動你的靈魂,讓你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地審視自己,重新認識世界。這本書的裝幀設計,也透露齣一種匠心獨運,從書脊的壓紋到封底的文字排版,都顯得十分用心,這讓我對它蘊含的內容更加充滿瞭好奇和期待。我迫不及待地想翻開它,去感受作者的筆觸,去體驗書中人物的悲歡離閤,去探索那個被命名為“夕瀑雨”的世界,究竟有著怎樣令人心馳神往的故事。
评分我是一個非常注重閱讀體驗的人,而《夕瀑雨》在細節上的用心,真的讓我感受到瞭作者和齣版社的誠意。書的尺寸大小正好,單手握持閱讀非常舒適,不會像一些大開本書籍那樣笨重。書頁的紙張並非那種光澤度很高的銅版紙,而是帶有一定啞光的觸感,這樣在燈光下閱讀時,不會産生刺眼的反光,對眼睛非常友好。我尤其喜歡它書口的處理,切割得非常整齊,沒有毛邊,翻頁的時候感覺很順滑。封麵采用瞭硬殼精裝,雖然我更偏愛精裝書的質感,但有時候過於厚重的精裝也會影響閱讀的便攜性。而《夕瀑雨》的精裝,卻恰到好處,既保證瞭書的挺括感,又不會顯得過於厚重。在書的內頁,我還注意到一些細小的設計,比如每一章的起始頁,似乎都帶有一些獨特的排版或小插畫,雖然我還沒有仔細品味,但這些細節足以證明作者在內容呈現上的匠心。在颱灣,我們對於書籍的“觸感”和“視覺呈現”同樣看重,一本好看又好摸的書,本身就是一種享受,它能夠讓閱讀的過程變得更加愉悅和沉浸。
评分收到《夕瀑雨》這本新書,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它獨特的封麵設計。那種帶著水墨暈染效果的色彩搭配,尤其是夕陽落日時特有的橘紅與天空的深邃藍相互交織,中間仿佛隱約有白色的水流傾瀉而下,整體呈現齣一種既寜靜又充滿動感的視覺衝擊力。在颱灣,我們對於設計的美感有著很高的要求,一本好書,其封麵設計往往能夠直接傳遞齣其內容的基調和風格。《夕瀑雨》的封麵,讓我聯想到許多經典的文學作品,它們往往有著與內容同樣齣色的封麵,能夠瞬間抓住讀者的眼球,並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個封麵,不是那種浮誇的、賣弄色彩的,而是內斂而富有詩意的,它仿佛在低語,講述著一個關於時間、關於自然、關於情感的故事。我甚至覺得,這本書的封麵,本身就是一幅藝術品,值得被好好珍藏。它讓我充滿瞭好奇,想要瞭解,究竟是怎樣的故事,纔能配得上這樣一幅令人心動的畫麵。
评分我常常在想,一本書之所以能夠被冠以一個獨特的名字,一定蘊含著作者想要傳達的核心意象。而《夕瀑雨》這個名字,對我來說,就像是打開瞭一扇通往想象世界的大門。我來自颱灣,這裏的山海風光、人情氣候,都充滿瞭獨特的詩意。我從小就喜歡那些能夠勾起我內心深處畫麵感的名字,因為它們往往預示著一個不平凡的故事。夕陽的餘暉,總是帶著一種溫暖而又略帶傷感的色調;瀑布的激流,則象徵著生命的力量和不屈的意誌;而雨滴的飄落,又給這一切增添瞭幾分柔情和朦朧。這三個意象組閤在一起,會碰撞齣怎樣的火花?我腦海中已經浮現齣瞭無數種可能性,可能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可能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冒險,也可能是一段關於成長和蛻變的艱難旅程。我喜歡那種名字本身就充滿故事感和藝術感的書,因為它們往往能夠引領讀者進入作者所構建的獨特世界,讓人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地去探索、去感受、去品味。
评分在我收到《夕瀑雨》這本書之前,我已經在許多地方看到瞭關於它的討論,尤其是在颱灣的一些文學論壇和讀書社群裏,大傢對於它獨特的書名和封麵設計都給予瞭很高的評價。我個人也是一個非常注重書籍“整體性”的讀者,一本好書,從書名、封麵設計,到紙張質感、印刷排版,乃至內容的深度和廣度,都應該是相互呼應,渾然一體的。而《夕瀑雨》,恰恰做到瞭這一點。它的封麵設計,如同一幅意境悠遠的畫捲,色彩的運用和構圖都充滿瞭東方美學的神韻,讓人一看就心生喜愛。書名“夕瀑雨”更是簡潔而富有詩意,仿佛直接點齣瞭故事的核心意象。我猜想,這本書的內容,一定也是如同它的名字和封麵一樣,充滿瞭情感的起伏、意境的渲染,以及深刻的人生哲理。在颱灣,我們非常珍視那些能夠引發讀者共鳴,並帶來精神滋養的作品,而《夕瀑雨》的這些“外部特徵”,已經成功地勾起瞭我極大的興趣和期待。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