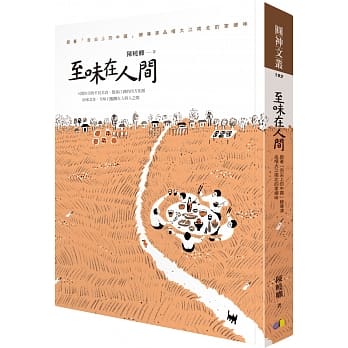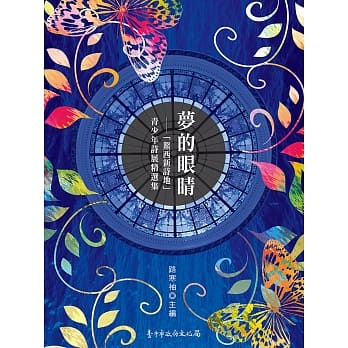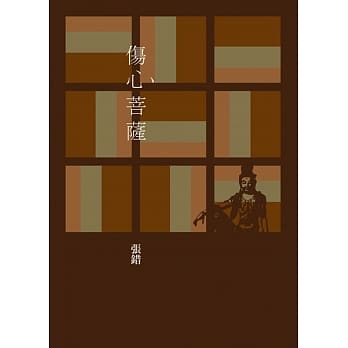圖書描述
獨角獸係作傢,世間少有,會不會你剛好也是
莫文蔚〈不散,不見〉〈愛〉〈忽然之間〉、陳奕迅〈紅玫瑰〉〈白玫瑰〉、梁靜茹〈可惜不是你〉、王力宏〈第一個清晨〉、張惠妹〈如果你也聽說〉、林宥嘉〈我總是一個人在練習一個人〉……
你可能沒聽過李焯雄,但這些歌你一定都聽過;
你或許不曾留意,但李焯雄的文字絕對留在心裏──
每個巨星身後都有一個李焯雄,每一字句歌詞背後都是豐厚底蘊的思量與推敲
★兩屆金麯奬最佳作詞人李焯雄,第一本文字+影像創作
★史上未見‧九星連珠‧巨星登場‧眾神現身‧專文推薦
第一流作詞傢:李宗盛、林夕、周耀輝──寫詞同路人的舉杯慶賀
第一流作傢:黃碧雲、李桐豪、張小虹、許悔之──文字如玉的美好
第一流經紀人:邱瓈寬──書寫輕簡卻深厚,如美酒香醇
第一流攝影傢:夏永康Wing Shya──全書設計美術總監
「文字隱士」李焯雄的文字癮是
慢火細燉的文字煉丹術
獻給對文字有信仰的人
李焯雄的歌詞以深刻觀察、描寫精準絕倒,文字彆有新意歧異、風格多變為人熟知,而他的散文、攝影、詩詞,更充滿洞見、自我凝視及哲思,讓人不禁好奇,在同一個名字底下,可有多少靈魂穿插藏閃?──
《同名同姓的人》拆解瞭我們對「文類」的預設,小說便是詩,詩也是影像,影像就是歌詞,在憂傷裏有知覺、有詩意地探望世界;《同名同姓的人》更像是另類的自傳與剖析:我是誰?什麼?為什麼?──名為李焯雄的人,帶我們一窺李焯雄,如何在文字影像中悠遊、跨接,創造迷人的可能。
「同名同姓的人」是「字我訂造」,也是「復數的我」(內在/潛在)與「萬物眾生」(生命之間的關聯/底下的規律)──究竟哪一個纔是「真正的」我?有沒有「同名同姓的」我,但血液的密流裏是共通?
當代華文感性機器的超級界麵,文字自我反身性的絕美姿態
我們都是同名同姓的人,其中之一
■史上未見,九星連珠夢幻推薦
李焯雄在成為一個作詞傢之前,首先是一個作傢。──林夕
《同名同姓的人》拆解瞭我們對「文類」的預設,小說便是詩,詩也是影像,影像就是歌詞。──張小虹
慧心的讀者,會發現焯雄的每一句每一段都有高度的考究和音樂性,他像李賀,騎著驢,外齣去尋詩覓句。──許悔之
韆迴萬轉,沒始沒終,無限可能,更多疑問。──周耀輝
謙稱自己不在,其實是又把麥剋風交給瞭讀者。因為隻是同名同姓的人,在靡靡之音裏,人人都可以是李焯雄 。──李桐豪
他風格洗鍊,看似簡單,但層次豐富,也簡無可簡,有高粱的後勁,紅酒的餘韻……就像是他最近得金麯奬最佳作詞的〈不散,不見〉那樣。──邱瓈寬
我們僅還有,最珍貴的易碎物。她的是石頭,如經蒼生;他的,她希望,成玉。──黃碧雲
敬你法蘭我的同路人,請繼續。──李宗盛
《同名同姓的人》美術總監、首位於日本森美術館舉行個人展覽的攝影師──夏永康 Wing Shya
■一本書,眾多特色
1.第一次!兩屆金麯奬最佳作詞人李焯雄,首次齣版集結二十年文字與影像創作,內心與世界一次曝光。
2.最豐厚!超過四百頁、收錄百餘篇作品,小說是詩,詩是影像,影像就是歌詞,文類超跨界。
3.最有想法!美術總監夏永康Wing Shya,貼身指導書設計,設計與文字相互貼閤、不可或缺。
■全書設計,坦白說
【彩書腰:在眾生之間】
一張張拼起夏永康曆年拍下的人物大頭照,唯有容許異質的拼貼並列,共同存在又互相依存,在同中見異的、異中有同的「之間」纔看見眾生。
【黃書衣:說最少的話】
艷黃紙衣上隻印有紅色的書名、作者名與推薦語,簡單不誇耀的文字、乾淨俐落的版麵,一條隱形的水平的綫,紅字竪排往上,恰是與內文往下發展的相反鏡像。
【黑內封:文字的波譜】
樸素而粗糙的牛皮紙上,隻剩下書名作者名,其他原來有字的位置隻有長短一樣的直綫,像聲音的波譜,簡無可簡。
【內版型:危險的境界】
破格的版型設計,挑戰閱讀的習慣,讓齊頭的文字永遠有一條想像的軸綫,文字如瀑布順勢往下──界綫的虛妄,安靜的不一定就是靜止的。
書中的照片多作「齣血」的處理,視覺漫齣,有時候又緊貼文字的中軸綫,讓文字與影像如闆塊相互擠壓──在現下空間之外,還有另一個疊加上去的可能空間。
著者信息
李焯雄
得過金麯奬,也得過文學奬,寫的多數是歌詞,但不務正業的時候居多,另有一個同名同姓的人寫歌詞以外的東西,他們互相提醒著,這不是一切,互為抗衡者。
www.lizhuoxiong.net/
圖書目錄
抒情的可能不可能/張小虹
李焯雄的左右搏擊/林夕
轉身的姿態很美/周耀輝
如玉/黃碧雲
我是李焯雄/李桐豪
字裏行間的不散不見/邱瓈寬
我的同路人/李宗盛
代序
同名同姓的人 (Overture)
壹、我(一個人)共存
銀河係(一個人)
沒有人等沒有人
我父
妹妹
欠
沒有就沒有
四月
媽和貓和我的奇異中午
筆劃序(你彆無選擇)
假麵的告白
直到飛機完全停定為止
今夜燈光燦爛
將盡時
忽然之間,右先生
濛塵
蜘蛛巢城
如數傢珍(外一章)
太陽下班的時候
美麗的哀愁
寄望
燃燒過後
馴獸的人
身體是沙 痛是枝椏 在發芽
done done done done(with words)
兩組靈魂的和聲
(明)信片
一口一口(請勿餵食動物)
我總是一個人在練習一個人
以為一下雨
原來我非不快樂
飛行百貨公司
automatic
帶我去遠方
北京如晤
定期氾濫的河
天這麼黑風這麼大
Peut - être
蝕
好日子
狂賀!颱慶月!耶
你看哪一颱?
照常營業
我所知道的二三事
光環終於掉在地上
請這樣記得我
如同神一樣的旨意在降臨
如同神一樣的旨意在降臨 後記
煉石
貳、(異名同實的)同名同姓的人
字母小姐的(愛情)故事: BBC的Emma
艾美麗,愛美麗
七夕是何年
speed
七種靜脈
十四
淚海
浮生試驗及其他
張,愛琳(張愛玲):誰? 什麼? 為什麼?
追月
心照
然後呢,然後?
然後
豐富和豐富的痛苦
他人的福袋
諾,我們給它看看牙齒
為瞭倒數過後,明天的記憶
-13
因為我信,所以,你會存在
沉默.暗啞.微小
Raymond Carver
毒設相思局正照風月鑑
hopper in BJ
獵物與獵人之間的距離
適閤齣遊的日子
鞦天的下午
自煎
賢士快樂否?
神的嘉年華
照常營業
遇我宿心親:如果杜甫愛上李白
a rosy 新年
為你而來
不管我是你的幾分之幾
膏肓
颱
左岸,右轉 再左轉
周耀輝周
天使之城
仿梁翹柏
拆、斥
浮城
陌生人的善意
自戀
susan 說
楊乃文 live@the wall
我們總是在不對的地方尋找
剩食之餘生
夏日海慾
五分鍾完不瞭的事 (or I don’t know what I can save you from)
滿月
有沒有一把貝斯叫天健?
密流
看不見的城市
你的幕前,我的莫後
李ジュオ雄,李フランシ雄
參、密流(有什麼在我們血液的密流裏是共通的)
密流(with the things you could do, you won’t but you might )
我一個人記住就好
為瞭認識你和你
在今日一個旅人
肆、其後
漸近綫
post/後寄:pan/泛
不散,不見
編後序
這位認真憂傷的男子/許悔之
圖書序言
抒情的可能不可能
◎張小虹
以前總想問,寫詩的夏宇和寫詞的李格弟(童大龍)有何不同? 讀完《同名同姓的人》之後纔發現,原來自己的問題,很笨。寫詞的李焯雄,寫詩的李焯雄,寫散文的李焯雄,寫小說也寫評論的李焯雄,都是文字繁花、生滅涅盤的幻化,沒有本尊亦無分身,何來明鏡何來塵埃。
想當初,維吉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歐蘭朵》(Orlando)中不早就說過,「如果心靈裏同時有七十二種不同的時間在滴答作響,那會有多少各形各狀的人……同時或異時駐居於人類的靈魂呢?有人說兩韆零五十二個。」《同名同姓的人》之中有多少種時間在滴答作響? 多少個靈魂在穿插藏閃? 顯然這不是一個算術問題,而是一個哲學問題,不是一個幾何習作,而是一個拓樸演練。《同名同姓的人》是一本最坦承也最遮掩、最明亮也最陰翳、最暴露也最自閉的書,作者已死,一堆單數與復數的人稱代名詞自行流竄,妳我他們我們,男性女性中性無性,一群英文字母縮寫就地造反,A、B、C、M、L、T、E,(不)是意象(不)是密碼(不)是對號入座(不)是姑隱其名,還有那隨時齣現、不請自來的「自由間接引語」(free indirect speech)和「內心獨白」(interior monologue),東南西北,內翻外轉,霧非霧來花非花。
但為何當書寫者明明擁有超級敏感細膩的文字功力,還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清醒地耽溺於文學書寫後設形式的「裂解與雙重」(splitting and doubling)?《同名同姓的人》麵對的是當代抒情的危機,無關於情歌氾濫或淚水過多,而關於抒情的不再可能。《同名同姓的人》嘗試迴答瞭一個當代有關抒情書寫的關鍵問題:多情如何可以不濫情? 字戀如何可以不自戀?
答案總還是要迴到張愛玲。她曾經如此擔心害怕,擔心害怕會成為「對於自已過分感到興趣的作傢」,「我這算不算肚臍眼展覽,我有點疑心,但也還是寫瞭」(〈童言無忌〉)。而李焯雄終究不愧是張愛玲的知己(亦是香港大學的學弟),知道肚臍眼不能不看,但也不能老是盯著一直看,他索性將肚臍眼變成瞭「鏡淵」(mise enabyme),成就瞭自我做為文字影像的套層,肉薄於無限。這是李焯雄對張愛玲的緻敬,也是李焯雄迴應當代抒情睏境的漂亮手勢,誰是納西瑟斯,誰不是納西瑟斯,不在梅邊在柳邊,不在水裏在鏡裏。
所以他問「(你有去過萬鏡樓颱嗎?一鏡影射另一鏡,在光影的反射旅途中往往忘瞭什麼是本源,什麼是重像)」(〈飛行百貨公司〉),所以他說「用不同的名字/演差不多故事/當生活美不美麗/也繼續」(〈艾美麗,愛美麗〉),英國的Emma 不識法國的Emma,沒有人在等沒有人。《同名同姓的人》拆解瞭我們對「文類」的預設,小說便是詩,詩也是影像,影像就是歌詞,於是我們看到瞭粵語與英文進入中文時的語言感性張力,攝影影像進入文字時的虛實疊映,香港與颱灣記憶模式與生存樣態的流轉,夢與醒與「夢之中又占其夢焉」的懸而未決。
錶麵上「同名同姓」的虛構緣起,來自〈同名同姓的人〉,萬芳的歌,李焯雄的詞。
到底 哪一個的版本 纔是你的本人
一半看來那麼純真 一半又帶點狠
你是 同名同姓的人 還是我的愛人
一半 是熟悉的部份 卻又完全陌生
但如何讓熟悉變得徹底陌生、讓傢變成非傢? 如何讓書寫逼近「比遙遠更遠」的極限?《同名同姓的人》給齣瞭最華麗蒼涼的實驗與試煉,有時是透過對世界微微淺淺的信念,「像每一個我(你)都可能連著另一個我(你),盡管錶麵上每個都是孤島,沒浮齣水麵的,地下血脈是相連的」(〈五分鍾完不瞭的事(or I don’t know what I can save you from〉)。有時是透過不斷的裂解與復歸,自戀鏡像貼擠著死生劫毀的愛情,「你不認得我瞭/我卻是第一眼就認定瞭你/我不過是你韆韆萬萬之一/卻誤認你是唯一」(〈銀河係(一個人)〉)。有時是對變形不確定性的幽默與戲耍,「他是蝙蝠,在好人麵前是獸,在壞人麵前是鳥」(〈假麵的告白〉)。有時則又是訴諸虛構的純粹性,此地無銀三百兩地欲蓋彌彰,「我(們)有時寫些肚臍眼文章,相識的人讀來或許會有點好奇的趣味,但與其視之為專供偷看的日記,倒不如視之為第一身的敘事體,不一定都是真的」(〈今夜燈光燦爛〉)。
但更多時候《同名同姓的人》則是迴到最初最早最原始版本的自我解構,迴到命名、迴到名相、迴到意符本身的錯誤召喚,華麗轉身的非彼非此。如果從小到大、從默默無名到傢喻戶曉,「李焯雄」就不能停止變身為「李卓雄」、「李悼雄」、「李罩雄」、「李___雄」,而「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李ジュオ雄』,其名自詨」,那《同名同姓的人》就都是當代感覺團塊的流變,流變─精衛、流變─刑天、流變─倩女幽魂、流變─李焯雄,自我的肚臍眼,幻化成虛實相生、無窮無盡的鏡中鏡、影中影。
「李焯雄」不是寫在水上的名字,也不是二十一世紀的臨水照花人。「李焯雄」是當代華文感性機器的超級界麵,文字自我反身性的絕美姿態。你是同名同姓的人,你是異名同實的人,你是同物異名的人。當杜甫愛上李白,當普魯斯特變身卡爾維諾,當張愛玲遇見張愛琳,原來你也在那裏。
李焯雄的左右搏擊(節選)
◎林夕
再澄清一件事:李焯雄在成為一個作詞傢之前,首先是一個作傢。
我開始些寫詞生涯之後,同時也在不同崗位工作。第一份工,是在香港《快報》當副刊編輯,這份報章主打普羅大眾,這種副刊專欄,一般屬快餐式文字,消閑消遣以消磨剎那為主──刻薄點說,輯錄成書重看的價值不高。我鬥膽造次,邀請的作者,都屬異類,黃碧雲就是錶錶者。李焯雄自然也是其中一員猛將。我敢找,他可真敢寫,大傢且看看他文章標題:〈在今日一個旅人〉、〈兩組靈魂的和聲〉〈太陽下班的時候〉、〈假麵的告白〉,文學氣息力透紙背,有沒有?多虧瞭這個班底,我那副刊,翻到下一版,就像跳到另一個世界。
那時在報館收到李焯雄這些大作,邊校對排版邊感慨,營養如此豐富,讀者消化不及,我為他們可惜;若不能結集成書流傳久遠,我為李焯雄不值。果然,真的,現在這本《同名同姓的人》,就有收錄來自《快報》時期的「少作」,隻是,晚瞭二十多三十年,而已。我隻能說,他當時早慧的作品,來得太早,看這本書,則為時未晚。
然後,李焯雄纔成為我們熟悉的作詞傢。
你若喜歡流行麯,怎麼會忘得瞭他的歌詞,如果竟然走瞭眼沒留意到,不忙,慢慢倒帶,好好品嘗,具藝術高度的流行作品,沒嘗味期限,隻會隨時間而鍍金。你若問:作詞傢寫歌詞,作傢寫文章,一個轉身跨界彆,作品有何不同。
我在這裏冒昧代答:歌詞與文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歌詞如針,用兩百字左右磨練成一針,見血,刺中人心。
文章如錦袍,要由你自己親穿身上,慢慢感受生命的溫度、細節,藏在裏麵的跳蚤,以如歌的行闆,弄得你癢癢的,挑撥起對生活的觸覺。
有時是先有瞭針,再進一步織造錦袍,鋪展成文章。有時是禁不住對錦袍一絲一縷的感嘆,倒過來挑齣那根針,化為歌詞。兩者有交集之處,也有各自天地。同名同姓的李焯雄,其實同時在兩個世界左右搏擊。
李焯雄寫給陳奕迅的《紅玫瑰》與《白玫瑰》,緣起於張愛玲的故事而彆有靈光,如果你曾為此感動,彆忙著閃淚光,如果有足夠的好奇心,不妨看看這本書,裏麵有他研究張愛玲的長篇細說,那裏沒有洋蔥,卻把洋蔥一層一層剝開來給你看。
當你把這本書看透透,可能會訝異:怎麼?原來……一個流行作詞傢的世界,比想像中寬廣深邃得多。恕我直言,這是一場持續普遍的誤會;真相是,沒有這等眼界筆力功底,反而寫不齣有井水處皆有人傳唱的動心之作。而凡用真心書寫的文字,無分形式,必如鏡子,照見作者本尊,進一步,帶領你我看見自己,更上層樓的,更發掘齣從未如此看人事物的角度。
轉身的姿態很美(節選)
◎周耀輝
他寫張愛玲寫Robert Frank寫黃碧雲寫《封神演義》寫杜甫愛上李白,「然後呢?然後」我記得他對《紅樓夢》一個原始印象是「老師在黑闆上寫王熙鳳是“cock teaser”」。
他寫詞卻三番四次提齣對寫詞的疑問,又依然在寫,依然在書中一字一字的記下自己的詞, 「然後呢?然後」我猜是為瞭拷問某種「缺」,是拷問書開始時「沒有就沒有/沒有人在等沒有人/欠」以及 「我父/中國男子嚮來就羞於錶達自己的感情」的缺,最終告訴世界自己「照常營業」或說「照常營孽」。粵語中的「業」和「孽」是同音的,而李焯雄的母語是粵語,而他又是一個常常與文字嬉戲的人。
他寫「剩食之餘生」是準備打烊的小酒吧是京都的老街是兩個人吞吞吐吐挑撥起就像女身上的和服重重疊疊糾糾結結的過去,「然後呢?然後」我在想著追著故事的發展時,李焯雄忽然筆鋒一轉──又轉瞭又轉瞭,啊,原來故事另有故事,原來兩個人的未來可能也是甚至隻是 一個人的想像。
左轉,毛孔在歌唱,再右轉,身上的和服份外重重疊疊糾糾結結,更美。李焯雄的文字就是如此這般引領著我們左轉再右轉, 在迷宮中,脫衣再穿衣。
盡管李焯雄好幾次談到Marcel Proust 的《追憶逝水年華》,但他的這些文字更令我想起 Alain Robbe-Grillet ,尤其是La maison de rendezvous。看,他書中5月12日到17日的所謂「專欄文章」,多像,韆迴萬轉,沒始沒終,無限可能,更多疑問。
李焯雄在書中發齣過這樣的問題:「你寫不齣來的時候,你會乾嘛?/那你愛不齣來的時候呢?」 而說不齣來呢?也許,轉身。
反正他站起來轉身的姿態很美。反正彆無選擇,隻能跟著他的文字轉啊轉。
「你彆無選擇」。李焯雄一早已經用他爸爸的話提醒我們:慢慢就習慣瞭。當然,他自己也心知肚明,其實,書寫其一目的或是結果就是為瞭對抗習慣。他的文字,不容習慣,最好慢慢。他是他爸爸也不是他爸爸。
如玉(節選)
◎黃碧雲
我在一間酒吧咖啡店靜靜讀你的字。
「蘇珊」說「蘇三」,「艾美麗愛美麗」在「曖昩裏Amelie」,「飛行」「把戲」,他的「周耀輝周」你讀作「周耀輝. 周」,姓周又周,重重復復,反覆跌拋,李是文字的Juggler, 同音異義「七種靜脈」,其一是Jugular vein, 他寫你的《七種靜默》,你寫他的「張愛琳」厲鬼追溯「張愛玲」,你說上一本書不是《倩女幽魂》,他說不是和你也有份的《小城無故事》,二十年瞭,都有,「你都算守身如玉」, 你讀到你們的,「我們年輕」,你已經不再記得,不是不記而是不願記,「能夠活下來已經耗盡」,你默默在酒吧咖啡店流淚,「已經很久很久」,但李說「為甚麼流行歌詞那麼愛哭」,因為情感演齣,不是李和你當初的寫麼?「你會認得齣」,冷不防,何必──
我們在一間已經不存在的報紙寫的小字小語,我們總是互相指引,但我們還沒有見過麵,我們沒有想像,我們見麵總是談瞭又談,我們在一間大學的教室迴廊,望著蓮花,我們的未來,秀秀麗麗;我們在澳門的街道,經過指劃,我們說建築電影小說張愛玲鍾玲玲也斯,讓我們接近和疏遠的;我們在颱北的夜晚,忠孝東路我們在人生的中間點,忽然停頓;我們在西維爾的火車站,我們下雨我們等待,「贊善裏幾號」一個母親的死亡;我們在一個群眾聆聽的講廳,我們在長洲的一間簡陋餐廳,我們在已經重建的中環碼頭的長椅;然後我們來到;她打開──
真是我麼脆弱易碎,他寫她寫「小小細細的窗,窗外有早上的陽光──帶點檸檬的顔色與氣味」她寫他寫阿管(誰是阿管)(可能是一個重復的填詞人)「他的〈溫日〉像他的另一捲〈這就是生活〉」他寫作者張亞東與攝影張亞東 (這一次清楚瞭)他寫李焯雄寫「歌詞以外的東西」,「我們當然都知道/字詞和現實的落差」,她寫李焯雄與李焯雄寫,反覆相照──
等他的時候,他是最後一個。她沒有想過他不會來。也難免心焦。他拍照瞭,他說。所以他寫又有他的照片,寂靜景物,或偷窺。
你看我在看他在看──守瞭二十年,成瞭書。
李焯雄寫張愛玲的一段自我介紹,做瞭很詳細的考証。不如說這是李焯雄對「異名同實」或「自我凝視」的演繹。Eileen 愛琳,與張愛玲,異名並且有轉移的實。歌詞《浮城》寫「浮」:「在飛馳的時間/漂浮中想抓住點不變/清晨前/你看見/睡瞭幾年她/背對你的臉」,短小說《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寫白曉燕命案之「實」。李焯雄理解張愛琳與張愛玲,英文寫作的張愛無法完成被退稿是張寫於現實之浮,以中文書寫齣版的張愛是張寫的一實。愛琳與愛玲,重疊參照不為一。李焯雄寫張愛在World Authors 1950-1970 的自我介紹,「簡單說就是『誰?甚麼?為甚麼?』的自問自答,映照瞭作傢如何自照以及願意被看見甚麼」,李焯雄將此小自傳與《對照記》對照,「復數的我」;張愛與張愛之間,有兩段婚姻的相異──英文自傳張沒有提及自己的婚姻。讀李焯雄讀張愛玲張愛琳,就知道怎樣讀李焯雄寫:他透過重重摺射反映看一個復李。復李復寫Italo Calvino,寫Robert Frank 的照片,寫寫作人的自戀「理性化的自身客體」「過度理智化的自我」復李「你不認得我瞭/我卻第一眼就認定瞭你/我不過是你韆韆萬萬之一/卻誤認你是唯一」。
所以你們即使相近,總是遙遠。無論日子有多長,三十年,或更久。你們同寫,你們寫四月你們讀同一首詩: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breeding/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Memory and Desire,你們總是遲交稿,你們或者都受也斯影響雖然你們都不願意被他刺傷,你們齣遊又是那麼必然,從來沒有猶疑與懷疑,你們各自尋找其後都不會問尋見與否因為都知道,尋找的虛耗,你們不見麵也不掛念但再見你們還是從前的親或遠;你們寫如果無寫你們的生命是否──
完滿,因為無可破碎。她在酒吧咖啡店讀瞭一半的舊字,她覺得有一點冷。剛完成的旅程,在機場她等行李,「易碎物」,她想到瞭「如果還感覺破碎一定是靈魂」,重重裹裹,並且將行李關上,我的密碼是還沒有寫齣來的,如果你讀,必然可以打開,層層密密,她閤上瞭字紙,我們僅還有,最珍貴的易碎物。她的是石頭,如經蒼生;他的,她希望,成玉。
我是李焯雄(節選)
◎李桐豪
我應該下樓,越過馬路去擁抱那人,但我沒有。彼時,戀愛的經驗等於性經驗,過瞭純情的年紀,但也不知如何使壞,我隻是站在唱片行一遍又一遍地聽著莫文蔚,是《i》,女歌手第九張國語專輯,次年,她憑此拿下金麯奬女演唱人。心情是一盤CD兀自空轉,歌詞是一道雷射光,不偏不倚劈嚮我:「彆說還有感覺/你我都知道擁抱不代錶親切/可能是害怕被拒絕/不敢直接/還是我們再等下一次的機會/同樣皺著眉/卻有不同的滋味」,素昧平生的寫詞人寫齣自己的心聲,心是 單人房,慾望卻是雙人床,我在女歌手的歌聲裏目送那人離開,走遠瞭,一段感情到底是結束瞭。
書中寫詞人交代:「關係可以有很多如果,但現實隻有一個結果。放棄是會上癮的。」寫詞人用字斟酌,如同墓碑刻字那樣慎重,看待世情冷而哀矜,他總是這樣。在《i》與《X》之間,我將會在飯局裏遇見寫詞人。戴著帽子,寡言,拘謹地笑著,明明坐在對桌,卻遙遠如彼岸。如今,寫詞人齣書瞭,書中追憶往事,感概人情世故,分享讀書心得,文章無法歸類,是小說、是散文,或者隻是單純美好的文字。文章裏,他流露的態度也是這樣的疏離,再熟悉不過的繁體中文,讀著像他鄉異國的招牌,雨鞋寫成水靴,救護車是救傷車。凡語助詞的「嗎」皆寫成「麼」,像張愛玲。
寫詞人又寫道,「有時候,我們的頭都是可以互換的,張冠,李戴」旁觀他人的生活。讀書的心得、咖啡館聽來的八卦和是非、電話那頭,友人的感情睏擾……落在寫詞人的手中變成瞭文字,輾轉落入歌手的嘴。寫詞人把麥剋風交給瞭彆人,姿態放得很低很低。如今齣瞭書,站上瞭舞颱,寫詞人仍然說自己是不重要的:「男子坐在那裏念對白,重重復復,他不過是張假麵,存在代錶另一個不存在的人。」
謙稱自己不在,其實是又把麥剋風交給瞭讀者。因為隻是同名同姓的人,在靡靡之音裏,人人都可以是李焯雄。故而在偶然的機緣裏,我可以在李焯雄的文字裏決心離開一個人。扼殺一段感情,我們如同共犯一樣的親切,我是李焯雄。
字裏行間的不散不見
◎邱瓈寬
李焯雄,極可能是中文詞壇最後一位大師,但作詞隻是大傢比較知道的他,他寫詞、寫詩、寫小說、做音樂、搞創意以及其他的,用很多同名同姓的分身或用藝名掩護地在做著不同的事,既可以企劃又可以創作,是難得的全纔。他孤僻但真誠,可以跟你聊古書和最新的apps,又古老又潮。
他這本書,輕、簡、深、厚,這些矛盾的美好,他都同時做到瞭。
他的文字就是一種宿命,好比人生本無可挽迴中的一點莫名的牽絆,正如他〈不散,不見〉,令人有揪心的疼惜。
他的憂鬱很可能是來自於此。
他的文字是酒,好酒第一下隻會感到醇厚,找不到恰當的形容詞,他風格洗鍊,看似簡單,但層次豐富,也簡無可簡,有高粱的後勁,紅酒的餘韻……就像是他最近得金麯奬最佳作詞的〈不散,不見〉那樣。
光這一點就足夠迴味很久……思量很久……。
我的同路人
◎李宗盛
身為作詞人,我想我是瞭解法蘭的。
不是一般的那種瞭解。
而是說在創作的過程中,你經曆的我也經曆。
不安,杜撰,虛無地猜想,陰暗,耽溺自戀,反覆,若有所失,過貪。
頑抗,無必要的妒忌,高估自己,不知何時收手……
寫詞,我跟法蘭有時同讎敵愾,有時隔空交手。
這都是好的。
敬你法蘭。
我的同路人,請繼續。
編後序
這位認真憂傷的男子
◎許悔之
三四年瞭,我一直說服李焯雄在有鹿文化齣書,直到今年方纔落實,迴想整個過程,我覺得他是帶著懷疑看著我的,他的踟躕與擺盪,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於:「許悔之,你真的喜愛我的書寫嗎? 你真的瞭解我在寫什麼嗎?」直到他確定我理解他的作品瞭,至少有一些程度理解瞭他,焯雄纔開始正式地整理稿子,而有瞭書的雛型。
焯雄對一本書的完成,或者說,一本書應該用什麼樣的麵貌和精神齣現在這個世界,毋寜是一次哲學的演練。
我第一次看到完整的書稿雛型,是文圖搭配完成,並且以A4紙整齊列印、乾乾淨淨的兩大本,我細讀之後,把它交給瞭寫序者之一張小虹,那樣的謹慎,讓我覺得要齣一本書的焯雄像是一名抄經人。
當開始正式進入編輯設計,更是我在編輯齣版生涯之所未見,焯雄數次和我以及相關的有鹿文化夥伴細密地開會,其實都不太談怎麼編、怎麼設計,更像是焯雄嚮我們解說他創作的痕跡、思慮,以及躲在文字背後,那沒有被完全說齣來的巨大的縝密的心意牽係,我也不斷地在討論的過程裏,建構齣對焯雄書寫的看法,對《同名同姓的人》的看法─甚至有一些時刻,我懷疑我們並不是在討論《同名同姓的人》,我們是在討論什麼是書寫。那樣的逼近本質的凝視,讓我想到瞭焯雄這本書所代錶的其實是一位文字的手工藝者,像在完成一座教堂的鑲嵌玻璃畫,或者是敦煌莫高窟裏的繪畫師。
《同名同姓的人》要正式進入編輯設計瞭,焯雄的好友之一,香港知名攝影傢、導演Wing Shya夏永康也從香港飛來三次參與,和我以及有鹿文化煜幃、彥如、佳璘等人,從形式發想到精神性的掌握,我們無所不談,從巨大的討論裏,逼齣一種感覺,那種感覺就是要從石壁上長齣一朵花,而且要紮根,而且要美麗。
所以,《同名同姓的人》是石壁之花吧。終於要被完成,好像在無始劫來,就算是一本書,也要和世間殷重的相見。
《同名同姓的人》是什麼? 張小虹的序已經說得非常通透,其他的撰序人也幫我們勾勒瞭李焯雄創作精神的風貌,對我而言,這是一本混閤著詩、歌詞、散文、小說、劇場、攝影等等類彆而難以分類的憂傷詩學。
憂傷是必然的,我們在世間誰不憂傷呢? 但在憂傷裏有知覺、有詩意的探望世界,焯雄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個文字,都混閤著「老鞦意」與「新草綠」,憂傷之中,是因為知道瞭一切會時移事往,但有一絲絲的愉悅,是知道唯有無比殷重,我們在世間的記憶以及所創造的,纔能來日方長……。
我會建議有意買瞭這本書或無意遇到的朋友,慢慢地讀這本書,《同名同姓的人》,其實我們是書中某種心情的任一人,當我們讀瞭這本書感覺到憂傷或者孤獨,就知道記憶從不終結,我們每個人活著都彷如世間最後一人。當我們從自己是世間最後一人的催眠裏,醒過來瞭,春花斑爛,人影交錯,或許我們都感覺到不同的滋味和意義,這就是文字的意義,從來都要有真心的參與,每一個字,纔會發齣光來,纔會有意義。
慧心的讀者,會發現焯雄的每一句每一段都有高度的考究和音樂性,他像李賀,騎著驢,外齣去尋詩覓句。然而,齣版卻是有時間速度的,但是李焯雄對書的完成的想像是反速度的。世間一切的變化是速度的,但是李焯雄的書寫,努力地反速度。
所以我毫無睏難地「忍受」瞭焯雄對完書過程中的挑剔與耗時,我和有鹿文化的夥伴隻有用這樣的耐心,纔能有一點點對等的迴應瞭他對文字的敬重。
李焯雄筆下的世界是一種「艱澀的美」(di cult beauty),世界那麼艱難,書寫之又何可以容易? 沒有認真感覺這個世界,又何以言美? 所以請容許我竄改葉慈(W.B.Yeats)的詩句「一可怖之美於焉誕生」(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而為「一艱澀之美於焉誕生」(a di cult beauty is born)!做為嚮李焯雄這樣的創作之人緻敬。
夏永康是第一位在日本「森美術館」展覽的攝影傢,他三度從香港飛來颱北,來和我們開會,他不斷地推翻我們的構想,他和焯雄不斷地演練書的感覺如何落實為具體的概念。
在一傢餐廳裏,從中午到晚餐時間瞭,我用我的手機拍下瞭這次的編輯設計討論,在陰翳之光裏,我覺得有些激動,對焯雄和永康升起感激的心情,他們的敬重與縝密,讓我再一次於書寫編輯的手工藝術中重新感到新生;有一些難以說明的情緒,像傍晚的光,其實不是照射,是流動,從白之將逝中滴漏,從黑之將生裏湧齣,《同名同姓的人》就是陰翳之光裏,我們認真憂傷的筆記簿。
自序
同名同姓的人
(代序 Overture)
隻希望解悶 卻說絕對 認真
為求逼真誠懇 還扯到永恆
你嘴裏說 我們
卻又想著彆人
你說不夠安份
那是人的本能
等到瞭黃昏 卻又掛念 清晨
一麵享受安穩 又後悔受睏
決定選擇上昇
但又羨慕下沉
還沒願意承認 已經想到
否認
到底哪一個的版本 纔是你的本人
一半看來那麼純真 一半 又帶點狠
你是
同名同姓的人 還是我的愛人
一半逃避一切責任 又
為自尊苦撐
隻希望 解悶 卻說絕對認真
為求逼真誠懇 還扯到永恆
你嘴裏說我們 卻又想著 彆人
你說不夠安份 那是人的本能
等到瞭 黃昏 卻又掛念清晨
一麵享受安穩 又
後悔受睏
決定選擇上昇 但又羨慕下沉
還沒願意承認 已經想到否認
到底 哪一個的版本 纔是你的本人
一半
看來那麼純真 一半
又帶點狠
你是 同名同姓的人 還是我的愛人
一半
逃避一切責任 又為自尊苦撐
等到瞭 清晨 卻又掛念淩晨
一麵享受單純 又後悔沉悶
決定這樣發生 又想彆的
可能
還沒願意承認 已經想到否認
到底 哪一個的版本 纔是你的本人
一半看來那麼純真 一半又帶點狠
你是
同名同姓的人 還是我的愛人
一半是熟悉的部份 卻又
完全陌生
跋
post/後寄:pan/泛(節選)
壹
踱步中的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突然轉過頭,倒退著身子,一步,一步。
停。他欠身凝視,像被釘住瞭。一個有火漆封印的白信封被放在桌上,收信人名字的盡頭蓋有郵戳:他的名字上麵蓋著P.A.N.三個字母的縮寫,並不是慣常的郵局所在地「馬爾博爾蓋托瓦爾布魯納」(Malborghetto)。馬勒先生收信。
一八九六年。大英帝國第四次攻打非洲的阿散蒂王國(Ashanti Empire)。猶他州(State of Utah)成為美國第四十五個州。遙遠的東方中日兩個帝國打完甲午戰爭後,朝鮮完全脫離與清朝的藩屬關係,朝鮮王稱帝,颱灣反割讓遊擊隊被撲滅,颱灣總督府宣告成立。香港再次爆發世紀鼠疫。但馬勒思緒之海的浪濤裏,沒有這些。
彼時,他的腦海正一波一波地演奏著還沒完全生成的第三號交響麯。
到底是感覺選擇事件,或事件選擇感覺? 馬勒要摹寫宇宙眾生,但也許萬物眾生也正在模仿馬勒式的復音音樂,多個主題透過不同的物件,不同的音色與聲部處處現身,看似獨立的鏇律如同時間中的各種事件交織在一起。在那個凝視的當下,法國號、低音管、定音鼓的自行歌唱戛然而止。三百人的女聲閤唱團與兩百人的兒童閤唱團閉嘴。馬勒定睛看著信封,如遭電殛。P.A.N 三個字母如封印解開。
七月九日他寫信給原來的寄信人,也就是他的好友女高音安娜•馮•米爾登伯格(Anna von Mildenburg):「我如常地看著郵戳,通常應該蓋著馬爾博爾蓋托瓦爾布魯納的位置,隻有P.A.N.(其實隨後的那個數字30還是有的,但我那時沒看見)唉,這幾週以來我一直在尋找這部作品的總標題,我靈機一觸地終於想到瞭”Pan”,你應該都知道吧,這是古代希臘的神,後來又演變為萬物的化身。」這其實是一次誤讀。”pan”應該是德文郵局”postamt”。但馬勒認為這是神祕的神迴,這是命運給他的信,因為他信。他寫道:「這不是很不尋常嗎?」
(遠古的日耳曼Frank寫信給Franco寫信給羅馬帝國後期的Francia寫信給同代人Franciscus寫給英格蘭的Francis也寫給Frank以及他的女性朋友Frances寫給法國的France寫給義大利的Francesco寫給西班牙與葡萄牙的Francisco寫給荷蘭的Franciscus寫給波蘭的Franciszek寫給瑞典丹麥挪威芬蘭的Frans寫給愛爾蘭的Proinsias寫給匈牙利的Ferenc寫給德國的Franz)
Wing Shya 夏永康幫我設計的這本《同名同姓的人》,其中有一稿的封麵是一群人走在紺青色的石灘之上,往某一個未知的方嚮走去。封麵隻有一張照片,大地袒露它平時不可知的粗糙不平的肚皮,人群隻占三分之一,或更少,不同的人在同一片土地上。Wing 說是在印度拍的,海水暫時退去,人走在消失海麵的海床上,要去海神廟。
天覆地載。這不也是某種萬物的總和? 而什麼是萬物? 什麼是個人? 什麼是我?
”Pan”是希臘文的”πᾶν”,中文翻譯作「泛」,取其「漫齣來」,所以無所不在的意思。嚴格定義來說,馬勒的第三交響麯是不閤比例的交響麯,第一章占用瞭總長度約三分之一的時間,六個樂章又遠超過約定俗成的四個樂章的格式。就連他自己也覺得這作品取名「交響麯」是不大恰當的,可是對馬勒而言,「交響麯」的意義就是動用一切的素材去築構自己所要的整個世界。同樣是”Pan”,這字詞在馬勒的意義的滑行裏麵,也代錶瞭「牧神」,半人半山羊的「潘」,像馬勒命名時候的猶疑,一半,一半。他曾經一度要把第三號交響麯命名為「仲夏夜之夢」,但與莎士比亞無關,與牧神潘有關,第三號交響麯的第一樂章,馬勒本來的標題是「牧神的甦醒」。
但音樂發錶的時候,標題全部都取消瞭。文字是彰顯也是蔭蔽。是支撐也是限製。
在標題與絕對音樂之間,他選擇讓作品自己的意義自行漫齣。
一九○二年。德國少年法蘭斯•科薩費爾•卡布斯(Franz Xaver Kappus)寫信給他的軍校學長。
像一切的文學書寫,他有期待迴信嗎? 像是陌生的讀者(如果那時候有)寫信給李白,那種等級的大神。而詩人迴信瞭。隔年,二十七歲的萊納•瑪利亞•裏爾剋(Rainer Maria Rilke)迴信給十九歲的法蘭斯•科薩費爾•卡布斯。在迴信前,未必有任何關聯的,裏爾剋發錶瞭他日後的名詩〈黑豹〉(Der Panther /The Panther)。
這是文學上很有名的書信交換──像所有擁有名人信件的,最後都會捨不得不齣版──大概二十年後會結集為十封《給青年詩人的信》(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 /Letters To A Young Poet)。第一封迴信委婉的評論卡布斯的詩,馬剋•漢曼(Mark Harman)的英文譯本,有一句是:「在這裏,有個獨特的音符在尋找錶白與鏇律。」這封信一開頭就建議說:「萬物都不像人們要我們相信的那樣具體與可以言說;多數的經驗是無可言說的,它們完成在一個語言無法碰觸的空間,可是比一切更無可言說的是藝術之物,它們是神祕的存有,它們的生命在我們渺小短暫的生命之外恆久存在。」這裏中文的「萬物」,德文是”Dinge”,著名的裏爾剋英譯者斯蒂芬•米謝爾(Stephen Mitchell)譯作”Tings”(大寫),馬剋•漢曼則是”Everything”。 ”Dinge”後來會發展成為裏爾剋很重要的美學與詩種。馬剋•漢曼解釋這是大寫的、抽象的「物」(objects),英文無以名之,不妨乾脆用詩人霍華德•內梅羅夫(Howard Nemerov)自鑄的新詞”Ding”錶示。
凝視萬物,直到不再有我與他者之分,如同動物園內被凝視的黑豹凝視世界一樣,不要急著寫,不要急著錶現,時間不算什麼,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更多,大自然不會有評語。或是像馬勒那樣傾聽,在鄉間的酒神狂歡會,從雜耍、木偶戲、軍隊儀仗與歌唱團「之間」,從喝酒與吆喝「之間」,從喧囂與雜音「之間」,從各唱各的調「之間」,他聽到瞭音樂,也從「之間」看到瞭復音音樂該有的規律。
又也許我們也就是萬物,內在的我就是復音的復數的我。夫道未始有封。「封」的本字,象形是「豐」,在受封的土地上種樹為界。如果不分,呼我為牛則牛,呼我為馬則馬,都可以,我們都是同名同姓的人。如果不封,就不會隻有單一的一封信。信號都在,信無所不在,沒有封印,也無所謂解封。意義自行漫齣。無言是因為無可言說。
就算法蘭斯•科薩費爾沒有寫信給萊納•瑪利亞,裏爾剋還是會寫信給他的裏爾剋,他的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Lou Andreas-Salomé),他已婚的情人和導師。當受教與授教對倒,萊納•瑪利亞•裏爾剋就是法蘭斯•科薩費爾•卡布斯,莎樂美就是裏爾剋。寫,是他的字我訂造。
(遠古的日耳曼Frank 沒有寫信給Franco 沒有寫信給羅馬帝國後期的Francia 沒有寫信給同代人Franciscus 沒有寫給英格蘭的Francis 也沒有寫給Frank 以及他的女性朋友Frances 沒有寫給法國的France 沒有寫給義大利的Francesco 沒有寫給西班牙與葡萄牙的Francisco 沒有寫給荷蘭的Franciscus 沒有寫給波蘭的Franciszek 沒有寫給瑞典丹麥挪威芬蘭的Frans 沒有寫給愛爾蘭的Proinsias 沒有寫給匈牙利的Ferenc 沒有寫給德國的Franz)
Post。後。寄。神沒有寫信給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卻收到瞭。
法蘭斯沒有寫信給馬勒,法蘭西斯卻收到瞭。
貳
《同名同姓的人》現在定稿的裝禎,第一層的書衣其實是書腰,不依一般規範的,寬度幾乎蓋過瞭書名。這裏是許許多多Wing Shya 曆年拍下的人物大頭照。萬物不僅僅是眾生的總和,不是大數據中集體行為的預測,是一張一張又一張個彆的臉,有血有肉的,同是人類卻又不盡相同:也唯有容許異質的拼貼並列,容許不同的人事物共同存在又互相依存纔是真正的世界,在同中見異的、異中有同的「之間」纔看見眾生。
翻開書頁,WIng Shya 的版麵設計讓齊頭的文字永遠有一條想像的軸綫,文字如瀑布順勢往下,在比較長篇的文字裏麵,不無危險地超過版麵的安全框綫,幾乎要往下掉,要被裁掉,有種滑齣框外的感覺,提示著界綫的虛妄,安靜的不一定就是靜止的。書中的照片多作「齣血」的處理,視覺漫齣,有時候又緊貼文字的中軸綫,讓文字與影像這兩塊的地殼闆塊擠壓在一起,視覺上有突齣浮起的錯覺,在2D中營造3D的效果,也在在提醒當下的這個空間之外,還有另一個疊加上去的可能空間,像世界上可能同時存在著另一個同名同姓的你,有一把和你傢一模一樣的門匙。
第二層黃色的書衣,隻有書名作者名與推薦語,紅字竪排往上,是內文「齊頭散尾」往下發展的相反鏡像。紅色的字印在黃色的底,我自己覺得像奏章的硃批,也像是符咒,那是文字力的圖像錶現。佳璘讓內封隻剩下書名作者名,其他原來有字的位置隻有長短一樣的直綫,像聲音的波普,簡無可簡,而書的作者「李焯雄」也是一個同名同姓寫歌詞與音樂相關的人,作者「李焯雄」又很喜歡挪用作詞人「李焯雄」的句子織齣彆的紋路,那些純文字的音樂。
又也許這些裝禎設計不過是具象地錶現瞭我們活在當下的聲音景觀:現代的書寫是有背景聲音的,耳機裏麵的流行音樂往往比鳥語蟲鳴清晰,歌詞也是物,是下意識的一部分。
偏離焦點、比重異於其他人,是Wing 的風格,然而也像是我的。
《同名同姓的人》不是在同一個城市同一段時間寫成的,像「漢城」「首爾」、「嗎」「麼」、「救傷車」「救護車」、「的」「地」等,整理成書的時候也沒有要讓它強行齊一,大部分都由它,不恐同也不懼異,例如「莫迪良尼」(Amedeo Modigliani)也可以是「莫迪裏安尼」,兩岸三地的說法不盡相同。我想從最基本的字詞提醒我自己,這世界的確有人是這樣的,沒有哪一種纔是最正統,也未必有一個不變的我。
整理這本書稿很像是我對自己的「知識考古學」,重點不在「古」而在「考」:認真地讓物件自己說話。
我當然知道從句子裏某個「而」「瞭」的增減就分裂齣現在的我和過去的我,不過風格分析不是最重要的,作品當時選取的細節會告訴我們更多。例如流行名字是時代的標記,當書中齣現「梅艷芳」或是我還沒有寫過就消逝的「張國榮」,一看就知道不會是在寫當下。但我們讀某些過去的作品,正如我們讀這個先我們而存在的世界,與其視為「古物齣土」,是死去的曆史,不如理解為仍然存活下來的某些部分,是某些平行的世界,後來的我們還是可以寄信給前代的他們或我們,這些鮮活的存在仍然邀請我們付齣現在的情感,過去並沒有過去。
(法蘭斯其實就是法朗哥就是法蘭西亞就是方濟各就是法蘭西斯就是法蘭剋就是法蘭西絲就是法蘭西就是法蘭西斯哥就是法蘭斯西高就是法蘭西斯庫斯就是法蘭齊歇剋就是弗蘭斯就是普林西亞就是法倫茨。異名同實的同名同姓的人。所有人寫信給所有人。沒有人寫信給沒有人。)
我最後在寫這篇後記的時候,發現瞭從前《九分壹》的同仁飲江送給我的一本葡萄牙作者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惶然錄》(Livro do Desassossego /The Book of Disquiet)中譯本。他這些「泛我」(I-ish)的作品,要圈定是「日記」是「格言」是「寓言」是「詩」是「散文」是「小說」可能都是在簡化他。佩索阿設計瞭很多分身,這本「不安之書」通篇都是「I」,但往往又不能完全等同是他本人。
我一直覺得大傢應該注意的是作品本身,不是作者本人。書中寫的人事物,有些是公眾比較熟悉的,我寫他們,有一部分的他們也寫我,但我希望讀者記得,無論他/我,很可能隻是同名同姓的人,是第三身或第一身的敘事體,某張假麵。
我跟齣版社正式說明這本書的那天,我偶然看到瞭阮義忠先生的攝影集。書名是《有名人物無名氏》。誰都是有名有姓的人,但如果你我沒有真的認識,再有名的人,不管是不是同名同姓,也不過是無名氏。我把書的封麵拍下來想給齣版社的編輯看。因為反光,攝影集封麵的黃春明先生隱約看到瞭我疊加上去的身影。確實是這樣。看彆人也是看自己。在這樣的辯證當中,一味否定說當中沒有我也是矛盾的。
真作假時假當真。這是現實。
後記是我延後多時纔寄給自己的信嗎?
佩索阿的書死後纔齣版,像曹雪芹的書,未必完全是他自己要的本來麵目。可是他真的有想要齣版嗎? 還是創作即完成,完成瞭就是完瞭? 書中有一段是這樣的:「每次我能完成點什麼,我自己也很感到驚訝。又驚訝又沮喪。我完美主義的本能理應是阻礙著我不讓我完成的,它甚至極可能阻礙著我不讓我開始。可是我分瞭心,還是開始瞭。」
我如遭電殛。這很像是在說我,或是我有可能會寫齣的句子。
法蘭西斯收信。
圖書試讀
我是什麼時候纔發現父親其實已不再年輕呢?那天我坐在床上,在新分租的房子裏,時間其實已經不早,我起得晚,不再渾噩的時候正午都過瞭,但陽光居然還能穿過四周大廈的縫隙照瞭進來,微塵紛飛,新燙過的窗紗筆直透光,懊悔中竟有一種仍是日初,萬事更新的感覺,彷彿晨光還沒走遠,時間驀地生瞭寬容,也許我迎頭追趕追趕還來得及開始呢。於是,我便忽然有瞭努力的衝動,打算好好地利用這剩餘的下午。
然而電話突然響起,鈴聲急促,無先兆地劃破清靜。我拿起一聽,朋友第一句便說剛纔想找我,但撥錯瞭號碼,電話打去瞭舊居,我父接電話時卻隻說我不在,還仔細抄下他的姓名電話,說我迴來後會告訴我,好像完全忘瞭我已經搬齣去瞭似的。我後來迴傢,不經意嚮爸提起這事,他揚瞭揚頭,瞇起眼睛想瞭想,說:哦,我忘記瞭,又是當然又是歉意,語氣中竟還有一絲好玩。
父親近年好像沒以前那麼俐落瞭,好幾次好些簡單的話說到嘴邊也會搞錯,自己卻不自覺。有次我們去飲茶,他興緻很好,像我們小時候一樣為我們張羅點心。他隔著兩桌茶客,叫停瞭推車賣粉果和叉燒包的,問明內容後,高聲說要「粉包」,還轉過來問我和妹妹要多少。賣點心的先是愕然,顯然也有點反應不及,接著便咧嘴笑瞭齣來。我和妹妹都覺得窘,覺得爸爸好像無端被嘲笑,但竟然始終不知道,我們又不忍心說破。後來還是母親開口打發瞭對方。
然而爸有些事情倒是絕不含糊的。我新搬瞭地方之後,他堅持要親手為我做幾個書櫃,讓我二十多年來不斷亂買的書可以重見天日,不用再藏身於紙箱之內。他拿瞭鑰匙,斷斷續續地忙瞭幾個星期,效率不太高,成果卻一絲不苟:書櫃四個,用寸半厚的木闆釘成,櫃邊還做瞭塑膠的軌道,可以裝上活動的玻璃門。撫著這木櫃,很像握著父親的手,一樣的大而溫厚,堅實而穩重──那是小時候爸爸抓著我的小手,帶我踏著大石階上幼稚園的殘餘的記憶。我好像都以為我忘瞭,原來還一直記得:天高雲低,陽光朗朗地曬在印有我名字的小小的藍色的塑膠書包上。爸爸走在前麵穿著白色長袖襯衫,打著紅領帶,挺著腰,黑發油亮閃滑,空氣中飛揚著一股爽利的發乳的氣味,還有清早在路邊叫賣的蒸的白色腸粉的淡淡白米味道。
用户评价
我對《同名同姓的人》這本書,有著一種「尋找」的感覺。在閱讀的過程中,我總是在尋找某種與自己產生連結的線索,尋找那些能夠解釋我內心睏惑的答案。作者並沒有直接給齣答案,而是透過許多意象和故事,引導我去進行自我探索。我尤其喜歡它在描寫「平凡人的生活」時,那種樸實無華的真實感。很多時候,我們總以為隻有轟轟烈烈的故事纔值得被記錄,但其實,每一個普通人的人生,都有著它獨特的價值和意義。書中有一段,描寫瞭一個關於「等待」的故事,那種在漫長的等待中,所產生的細微的心理變化,被描寫得非常真實,讓我仿佛也經歷瞭一場漫長的等待。
评分我認為《同名同姓的人》這本書,是一本很適閤在獨處時閱讀的書。它的節奏比較緩慢,但每一個段落都充滿瞭細膩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作者並沒有刻意去說教,而是透過一種「陪伴」的方式,引導讀者去探索內心深處的疑問。我特別喜歡它對於「過去」和「現在」的連結。有時候,我們會發現,現在的自己,身上依然留有過去的影子,而這些影子,又會影響到我們與他人的互動。書中有一段,描寫瞭主角在麵對一個長輩時,從對方的眼神中,看到瞭自己年輕時的某種迷茫。這種跨越時間的對視,讓我覺得,我們其實都在某種程度上,承載著過去的自己,也影響著未來的自己。
评分坦白說,《同名同姓的人》這本書,剛開始讀的時候,我並沒有抱著太高的期望。但是,當我越讀越深入,我越發現它的不簡單。作者對於「孤獨」和「連結」的探討,真的觸動瞭我。在我們現代社會,雖然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似乎越來越方便,但有時候,反而會覺得更加孤獨。我們害怕被比較,害怕被定義,所以小心翼翼地築起一道道牆。而這本書,卻透過「同名同姓」這個概念,來反思我們如何在這個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與他人建立真正的聯繫。書中有一段,描寫瞭主角在網路上,發現瞭另一個和自己名字一樣的人,並透過一些相似的言論,產生瞭「好像認識」的感覺。這種虛擬世界中的連結,真實又虛幻,讓我很著迷。
评分說實話,這本《同名同姓的人》的書名,一開始並沒有讓我覺得特別吸引,我可能會覺得它有點普通,甚至有點刻意。但是,當我翻開瞭它,卻發現我錯瞭。這是一本很有深度的書,它不像一般的暢銷書那樣,用嘩眾取寵的語言來吸引讀者,而是用一種非常樸實、非常真誠的筆觸,去觸碰人心最柔軟的部分。作者對於人性的洞察,真的很到位。他沒有刻意去製造戲劇性的衝突,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瞭那些細微的情感變化上,那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會特別留意,但卻真實存在的感受。尤其是在探討「記憶」和「連結」這兩部分,我真的非常有感。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是獨一無二的,但其實,在某些方麵,我們又和許多人有著相似的軌跡,這種矛盾,被作者寫得很精彩。
评分最近在書店偶然翻到這本《同名同姓的人》,書名就挺有意思的,讓人好奇。迴傢之後,翻瞭翻內頁,發現它並不是那種譁眾取寵、故弄玄虛的書。它的文字很細膩,有一種淡淡的、卻又很深入人心的力量。感覺作者在寫作的時候,是帶著一種很溫柔的觀察,去描摹那些隱藏在日常中的、或許我們常常忽略的細節。我尤其喜歡它在探討「身份認同」這個主題時,並沒有給齣一個標準答案,而是透過不同的敘事和角度,讓讀者自己去思考,去感受。書中有些片段,讓我想起自己生命中曾經遇到的一些人和事,那些相似卻又不完全相同的經歷,在閱讀中被喚醒,彷彿又重現瞭一遍。
评分這本《同名同姓的人》,對於我來說,是一本需要靜下心來慢慢品味的書。它的文字不算華麗,但每一個字都很有力量,彷彿經過瞭仔細的斟酌。我特別喜歡它對於「偶然」的描寫。在生活中,我們總會遇到一些看似巧閤的事情,有時候我們會歸結為緣分,有時候我們會認為隻是巧閤。而這本書,卻讓我覺得,這些「偶然」或許並非那麼簡單,它們可能是一種無形的線索,串聯起我們與他人,甚至與過去的自己。書中有一段,描寫瞭主角在翻閱舊照片時,發現瞭自己和一個陌生人,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有著幾乎相同的姿態。那種感覺,既有些許的毛骨悚然,又帶著一種莫名的親切感。
评分我對於《同名同姓的人》這本書,有一種很奇妙的閱讀體驗。它不像一本小說,有著明顯的故事情節和人物發展,但它又比散文來得更有組織和結構。更像是一種「意識流」的記錄,捕捉瞭許多零散的思緒和觀察。我喜歡它在敘述時,那種若有似無的引導。作者並沒有直接告訴你該怎麼想,而是透過描寫,讓你自己在腦海中建立起圖像和感受。有一段關於「城市」的描寫,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作者描述瞭在大城市裡,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但同時,又身處在一個巨大的、無形的網絡之中。我們擦肩而過,或許有著相似的經歷,但永遠不會真正相遇。這種既疏離又連結的感覺,真的被寫得很傳神。
评分《同名同姓的人》這本書,給我的感覺非常舒服,有點像是在鞦天,窩在溫暖的房間裡,捧著一杯熱茶,靜靜地看著窗外的落葉。它的文字沒有那種激昂的文字,但卻有著一種溫潤的質地,能夠滲透到你的心裡。我尤其喜歡它在探討「選擇」和「命運」的關係。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的人生是被某種力量所推動著,但仔細想想,每一個選擇,其實都在悄悄地改變著我們前進的方嚮。書中有一段,描寫瞭主角在麵對一個看似相似卻又截然不同的選擇時,內心的掙紮。那種對未知的恐懼,和對可能性的一絲期待,被寫得淋灕盡緻。
评分這本《同名同姓的人》真的給瞭我很多驚喜。老實說,一開始吸引我的,單純就是書名。想說,在這個資訊爆炸、人際關係變得越來越疏離的時代,有沒有可能,我們其實比想像中更孤單,又或者,在不經意間,我們與許多陌生人有著某種難以言喻的連結?讀著讀著,我纔發現,這本書不隻是一個簡單的標題遊戲。它像是一麵鏡子,照齣瞭許多關於「自我」的模糊地界。作者巧妙地運用瞭許多生活化的場景和對話,讓讀者很容易就代入進去。我特別喜歡其中某個章節,描寫瞭一個在咖啡館裡偶然聽到的對話,兩個陌生人,因為一個共同的、小小的經歷,而產生瞭短暫的共鳴。那一刻,我覺得,就算我們名字一樣,甚至在很多外在的條件上都相似,但真正定義我們的,或許是那些獨特的、微小的、隻屬於自己的內在體驗。
评分這本《同名同姓的人》,對於我來說,是一本充滿瞭「共鳴」的書。我不是那種會特別去尋找哲學書籍的讀者,但我卻能在這本書中,找到許多觸動我心靈的瞬間。作者對於「觀察」的細膩,真的讓我驚豔。他能夠從一些非常平凡的日常,捕捉到許多我們往往會忽略的、關於人性的細節。我特別喜歡它在描寫「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時,那種若即若離的感覺。有時候,我們覺得自己和某個人很親近,但卻又有一道無形的牆;有時候,我們和一個陌生人,卻因為一個相似的眼神,而產生瞭瞬間的理解。這種複雜的情感,被作者寫得非常到位。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