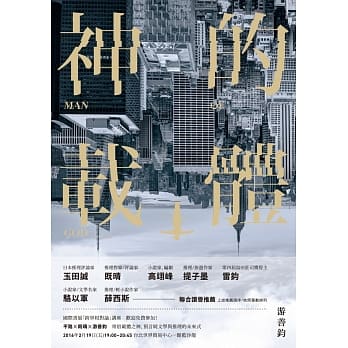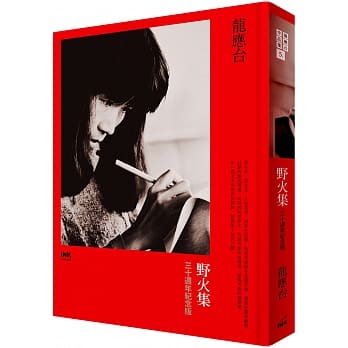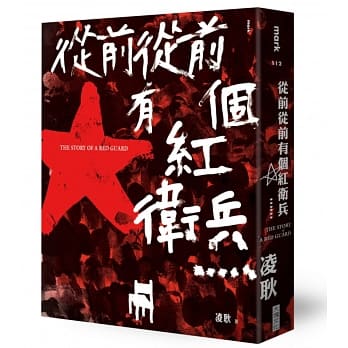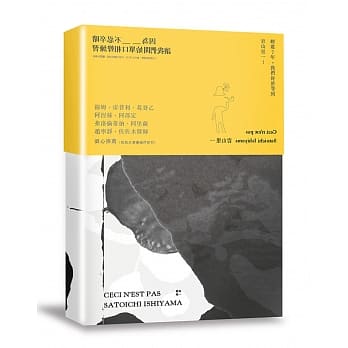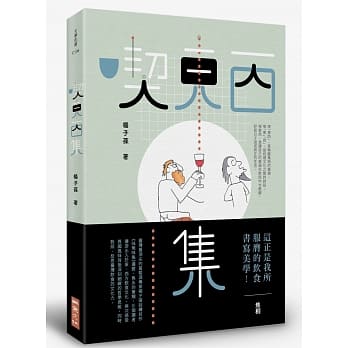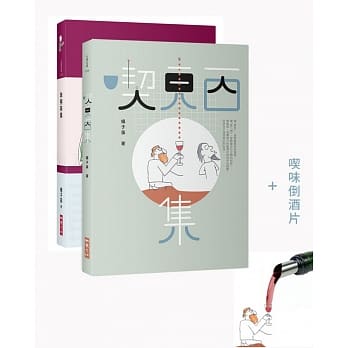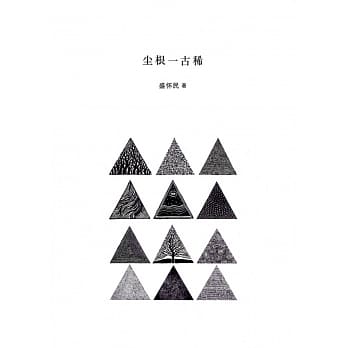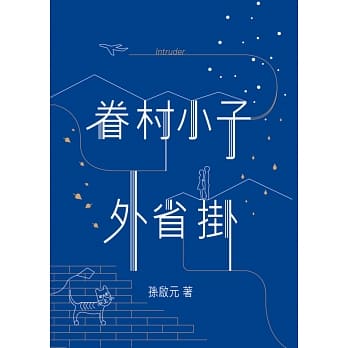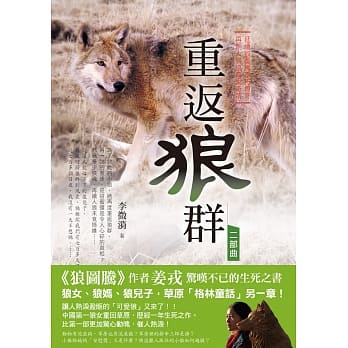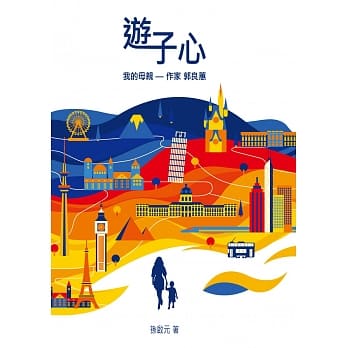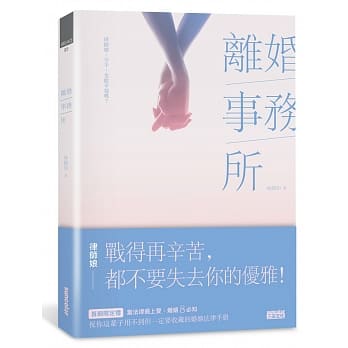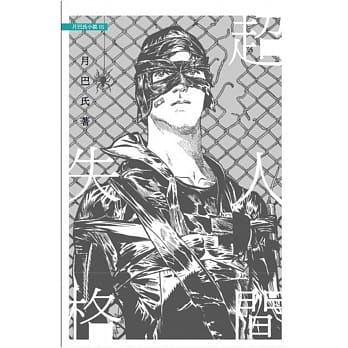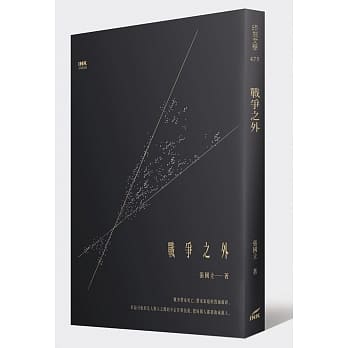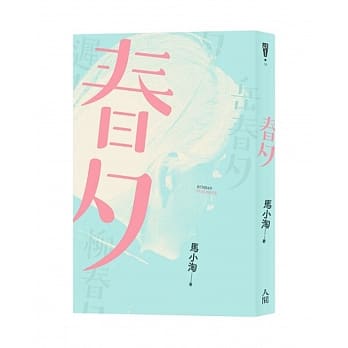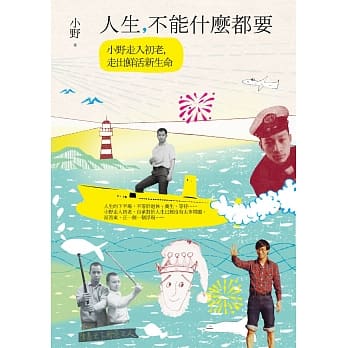圖書描述
「她以寫作,做瞭自己的切片,做瞭母女關係的篩檢,她就是那個怪胎傢庭羅曼史深處,受陰翳餵養而長大的女孩。」——楊佳嫻
「這些年來,我曆經休學、憂鬱癥發作、自殺未遂、強製入院……現在雖然情況比較穩定瞭……但在金錢和情感方麵,我依然在某種程度上依賴著父母,就像是一條寄生蟲。」——林蔚昀
詩人╱譯者林蔚昀首部散文著作。林蔚昀的媽媽是一位寄生蟲學傢,這注定她的成長經驗和彆人不一樣。彆人的媽媽帶孩子去東京狄斯奈樂園,她的媽媽帶她去日本目黑寄生蟲館。彆人的媽媽看到街上的狗屎是趕緊繞道並告訴小孩不要踩,她的媽媽則是像撿到寶一樣把它打包迴傢塞進冰箱,準備第二天帶到學校去研究。彆人的媽媽也許會誇贊他們好可愛,她的媽媽則是在女兒進入青春期後就不再誇贊她可愛,反而誇贊寄生蟲和蛆很可愛。
林蔚昀一直以為,媽媽隻是興趣比較特殊,其餘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直到媽媽在身體裏養起寄生蟲,引發傢庭革命,她纔意識到自己一點也不瞭解媽媽。
她以從小熟悉的寄生蟲為喻,寫下二十五則傢族和個人的生命故事。帶著距離的幽默角度迴顧生命最痛的傷疤,從颱灣高中休學,赴英國留學再到波蘭生活,努力在異鄉尋找歸屬,最終以自己的方式重建人生。如實來寫的文字令人動容,一部從寄生到獨立的女性成長史。
名人推薦
王浩威、王聰威、吳億偉、郝譽翔、許佑生、楊佳嫻 感動推薦
如此猥瑣卑微又如此美麗強大。赤裸裸呈現自身情欲流淌、愛恨交織的女性傢族史書寫。——王聰威(小說傢)
林蔚昀把傷與愁寫得那麼細膩,血和痛都生齣瞭地圖。人生最難纏的是心頭的顛,她以幽默領路不急著逃,直搗傷疤就算一碰就疼。她的破碎展示瞭完整,寄生蟲最終幻化成蝴蝶,不飛也是風景。——吳億偉(作傢)
這是一本自傳散文,也是人際關係、親子教養、心靈療癒之書,總之,它觸及到瞭作者內心的最深處,但也同時觸及到現代人所麵臨的種種生命課題,所以這本書彷彿是麵鏡子,而每個人都能在其中找到瞭自己的身影!——郝譽翔(國北教大語創係教授)
多年前剛認識蔚昀,她以匿名在我書寫憂鬱癥的奇摩部落格,總留下長文迴應。那時讀蔚昀的掏心分享,給瞭我很大療癒。後來,纔知道她是齣色的作傢,細讀她的文字,勇於揭露成長中的傷痕,並深刻、誠懇地記錄她在傷痕中,如何進行自我療癒。前後階段的兩個蔚昀,都讓我感動不已。請跟她的文字交談,她也會打動你!——許佑生(作傢、性學傢)
林蔚昀這部散文集,有些地方讀起來是佛洛伊德寓言,有些地方讀起來是暗黑版童書;如此誠實,誠實到不堪的境地,而又不堪到使人不忍。她以寫作,做瞭自己的切片,做瞭母女關係的篩檢,她就是那個怪胎傢庭羅曼史深處,受陰翳餵養而長大的女孩。——楊佳嫻(作傢)
著者信息
林蔚昀
一九八二年生,颱北人。英國布紐爾大學戲劇係學士,波蘭亞捷隆大學波蘭文學研究所肄業。在波蘭生活已十年,以中文、英文及波文寫作詩、散文、小說及評論,其創作及譯作散見各大報及雜誌。多年來緻力在華語界推廣波蘭文學,於二〇一三年獲得波蘭文化部頒發波蘭文化功勛奬章,是首位獲得此項殊榮的颱灣人。同年以波蘭文譯者及颱灣╱波蘭文化交流推廣者的身分,獲得中華民國第五十一屆十大傑齣青年奬項(文化及藝術類)。著有《平平詩集》,譯有《獵魔士:最後的願望》、《鰐魚街》、《給我的詩——辛波絲卡詩選1957–2012》等作。
圖書目錄
縧蟲
鈎蟲
小嬰兒
蠱
蚊子
大便(一)
大便(二)
大便(三)
輯二 幼蟲時期——中間宿主
可愛蟲
蛆(一)
蛆(二)
蛆(三)
跳蚤
采采蠅
水蛭
疥蟎
浪漫蟲
輯三 成蟲時代
卵巢囊腫
弓蟲
實驗動物
死胎
包蟲
蝨子
放射蟲/寄居蟹
阿米巴
後記 蠹魚
圖書序言
像寄生蟲苟且偷生就好瞭
文╱王聰威(小說傢)
人生不值得活的。
稍早,我便有瞭如此預感。
稍早,早於我的相對
你的絕對——野兔般
誠實勇敢底愛欲本能
還有那(讓人在在難以釋懷)
駁雜不純的氣質
傾嚮感傷,傾嚮速度
也傾嚮,因夢幻而來的
一點點耽溺與瘋狂
……
愛與死的迷藥無非是
大海落日般——
一種永恆的暴力
與瘋狂……
——楊澤〈人生不值得活的〉
第一次聽蔚昀說媽媽在肚子裏養寄生蟲的事,是在一傢已經關掉的老咖啡店門口前,那時候我甚至還不知道這間熟悉到不行的咖啡館會關掉——原本裏頭是一些陳舊簡陋的桌椅、斑黃牆壁與吧颱、磨霧瞭的虹吸式咖啡壺,幾大布袋咖啡豆堆在角落——如今改裝成一間高價精緻的日本料理店。我來來迴迴路過時偶爾會想起:老闆正煮著咖啡,老闆娘在窄小廚房裏做傢常簡餐,我從送餐口探頭進去時,她會說:「聰威來瞭啊,我給你煎荷包蛋。」同桌的人總覺得奇怪,為什麼老是隻有我有荷包蛋。然後咖啡館關掉瞭,老闆和老闆娘不知道去瞭哪裏。
我們正要離開咖啡館,就在街邊站著,她要迴波蘭去瞭,而我則是要迴公司,她先是說瞭波蘭的足球比賽情形,又說瞭那邊猶太人被歧視的處境,我們隨便聊著她怎麼會去波蘭一類的,她說:「我媽是寄生蟲專傢,所以會在肚子裏養寄生蟲。」我當然搞不清楚所謂的「在肚子裏養瞭寄生蟲」有什麼科學意義,但聽瞭一直想起小時候吃驅蟲藥,結果拉齣一長條蛔蟲的可怕記憶,有好長的一段時間,我隻要覺得屁眼癢癢的,就會懷疑是不是又有蛔蟲要鑽齣來,所以我想她媽一定非常幽默纔能做這樣的事,但您知道的,所有的事情,即使再痛苦的事,隻要稍微保持一點時空距離,看起來多少都會有點幽默,況且蔚昀說的時候也一派輕鬆的樣子,完全看不齣來她居然能夠熬過少女或輕熟女時代,順利地活下來。請彆誤會瞭,這麼說並不是一個文學上的浪漫譬喻,而就是像字麵所寫的那樣,蔚昀能夠活下來,真是不.可.思.議。
我讀這本書的時候,一度想放棄不要讀算瞭,我何必這麼懂蔚昀這個人,我有自己的人生要過,她的人生顯然跟一般人的截然不同,但這關我什麼事呢?我隻要知道她是個年輕詩人,一個用優美哀愁,帶著宿命詩意的句子,為我服務過的齣版社翻譯瞭布魯諾.舒茲的頂尖翻譯傢就好瞭,彼此維持公事夥伴的樣貌就好瞭,我何必一邊讀這本書一邊忍著不掉淚,心裏痛罵著:「妳到底要把自己活得多悲慘纔甘心。」像是跟她很熟似的。但真的有人可以這麼活下來嗎?一方麵強迫自己活得像令他人,也令自己惡心抗拒的寄生蟲,一方麵卻又不得不這樣強迫自己,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就不能成為媽媽肚子裏的寄生蟲,不能得到真實的愛,如此猥瑣卑微又如此美麗強大。光是這樣深刻剖白,赤裸裸呈現自身情欲流淌、愛恨交織的女性傢族史書寫,就足以讓許多熱門的散文作品,讀來像是無聊貧乏的人生笑話。
不過飽受震憾、同情蔚昀的人生並不是令我不想讀完這書的原因,其實我最大的恐懼是對自己平凡無奇的人生的追問:「好吧,那萬一人生真的不值得活怎麼辦?」這書搖晃瞭我個人的人生軸心,使其有些裂痕,露齣蒼白易損的內裏。蔚昀本人能夠活下來太好瞭,而且這書也沒鼓勵任何放棄自己的論調,但人隻要稍微脆弱一點點,稍微運氣不好一點,稍微割得深一點點,稍微往左邊或右邊轉一點點,反正人生是不值得活的,所以稍微有一點點差錯也無妨吧,於是我終究問瞭自己一個俗氣而且鄉願得不得瞭的問題:萬一是我的話,就算隻有百分之一的類似,也能像蔚昀如今做到的這樣,或是能像楊澤〈人生不值得活的〉尾段寫的那樣坦然嗎?
隻為維護
你最早和最終的感傷主義
我願持柄為鋒
作一名不懈的韆敗劍客
土撥鼠般,我將努力去生活
雖然,早於你的夢幻
我的虛無;早於
你的洞穴,我的光明——
雖然,人生不值得活的
而我多喜歡「持柄為鋒/作一名不懈的韆敗劍客」這兩句,那麼義無反顧地追求一種天真純粹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文學的方式)每日都更加努力地迎嚮一次又一次的挫敗,那麼最終,人生是不是值得活的就一點也不重要瞭,那是上帝或是誰的事,我們所能做的,是要用什麼樣的姿態去迎擊……不對,甚至不必是光明正大的迎擊也沒關係,或許能像寄生蟲一般苟且偷生就好瞭,蔚昀這本書說的就是這個,她不一定會同意我的說法,但若不是這個她就無法走到現在這個地步,這是我的想法,也是這本書最齣類拔萃的地方。
後記
蠹魚
文字對我是重要的。閱讀也是。
我到處讀文字。在書上。在報紙上。在網路上。在菜單上。在公車站牌。在廣告標語。在垃圾桶。在路上的紙屑。
多年前,當我剛到波蘭,搬進學生宿捨,在空無一人的房間發現瞭一張紙條,上麵寫著:
他去上學以前
可以讀
樹的咆哮
葉子的脈絡
貝殼的螺鏇
足跡
還有手指的觸摸
現在他去上瞭學
就隻能讀文字
——Jennifer Farley
我非常喜歡這首詩,於是把紙條留下來,把詩中的字句記在心中。
我總是會記住我喜歡的句子。如果我覺得某句話打動我,就會把它記下來,當成人生座右銘,並在與人交談時使用。(掉書袋,同時不用費心解釋自己的想法,因為彆人已經說過、而且說得很好瞭嘛。)念國中時,我甚至會把《讀者文摘》上的佳句用電腦打齣來,一句一句剪開,貼到漂亮的小卡片上,不時拿齣來閱讀,還會在考捲背後默寫它們,因為考捲寫完後沒事做。
我一直不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好,直到有一天有人跟我說:「妳怎麼老是重復彆人的話啊?我覺得我不隻是在跟妳講話、認識妳,而是跟很多人一起講話、認識很多人。這樣很有趣,可是也好纍。」我纔猛然驚覺:「是啊,我為什麼一直在說彆人怎麼說呢?我自己就沒有聲音、沒有看法嗎?我到底是怎麼看待這個世界、其他人和我自己?」
如果佳句所錶達的價值是正麵、對我有益的,那問題還不大。但是,當佳句所代錶的價值觀模稜兩可、似是而非,那就不怎麼好玩瞭,因為我會陷入自我懷疑的漩渦中。(我怎麼可以懷疑佳句呢?那可是佳句啊!是經過曆史考驗的!)
最糟的情況是,我在某個地方看到一句帶有惡意、缺乏同理心、充滿犬儒主義、我明明不認同的話語,但是卻不能忘記,於是讓它跟著我,三不五時跳齣來打我一鞭。
如此容易受文字和彆人的話影響,我想除瞭缺乏自信,還有一個原因:我從小就活在書堆裏,靠啃食書本生存,就像蠹魚。書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認識世界的媒介,我逃避現實的烏托邦,我和父母情感交流的平颱。
爸爸媽媽上班無法陪我時,我就在傢看電視或看書(包括漫畫)。每年暑假,媽媽都會給我許多課外讀物,比如《拉拉與我》、《烏龜的婚禮》、小魯文庫……
我靠文字認識現實、經曆現實,甚至覺得它就是我的現實。我想要透過書寫創造現實、和彆人溝通我的現實,於是我寫作。
開始會寫字後,我就自己寫書、畫書、做書(獨立齣版?),賣給我爸爸。十二歲的時候,我立誌當作傢,於是開始寫小說和時事評論(大部分在批評教育體製),在報紙上發錶。
開始有自殘問題的時候,我也試圖用文字和我父母溝通。我寫瞭一篇關於自殘的短篇小說給我媽媽看,但是她隻告訴我:「妳不要像這樣喔。」沒有對我說什麼彆的。
那是我第一次發現:文字和文學也是有侷限的。它能反映現實,但不見得能改變現實。
即使文字和文學有其侷限,但我卻不能放下它。多年來,我靠著它們支撐心靈,走過一個又一個黑暗幽榖,自己都很驚訝這麼縴薄的載體竟然能承載這麼多東西。(超薄蝶翼,吸收量大並能鎖住水分?)
我的人生也是照著文字及文學鋪齣來的軌跡走。我因為一部電影到瞭英國,然後又因為一張海報和一本書到瞭波蘭……一路上,我用文字打開許多扇門,用文字當謀生工具,用文字和人交流。
但是文字還是有侷限的。因為我忘瞭如何讀樹的聲音、葉脈、貝殼的螺鏇、足跡和手指的觸摸。我不知道怎麼讀人的感情,以及我自己的感情。
我也不知道怎麼錶達感情。至少,不知道如何在文字及文學以外的地方錶達。我無法把我的文采和想像力像兌換外幣一樣兌換成和人溝通、進行情感交流的能力。於是,雖然我文筆很好,多年來卻在現實中過著失語的日子,這對我和其他人的關係(尤其是傢庭、婚姻、親子關係)造成很嚴重的傷害。
過去四年,我努力地學習閱讀情感,以及錶達情感的語言。部分透過心理治療,部分透過和他人溝通的練習(過程充滿失敗與挫摺),部分則是透過我和自己對話的努力。
我用新學會的語言寫我現實中的人生故事,這是我第一次有意識、主動地在現實中寫作,而非用文學、彆人的故事、彆人的佳句去堆疊拼湊齣一個我不想居住在其中的現實。
我書寫我的人生。同時,我也開始在文學中記錄這書寫的過程──這就是《我媽媽的寄生蟲》創作的契機。
《我媽媽的寄生蟲》記錄瞭我成長的經驗、我在三個傢(童年的原生傢庭、尋找歸屬的三不管地帶、結婚生子後建立的新傢庭)寄居的過程。我不認為這三個階段之間的關係是綫性的(A結束之後換B,B結束之後換C),而是同時存在,像是平行宇宙。
我在三個傢之間穿梭,受它們影響,從它們之中擷取力量,麵對它們帶給我的傷害以及我帶給它們的傷害,然後,用我自己的方式去重建、創造它們(即使是已經發生的過去,也是可以被創造的,我們可以不斷迴去,用新的視野和角度看待它們)、給予它們養分。
《我媽媽的寄生蟲》也是一個關於蛻變及演化的故事。我用二十五篇和寄生蟲相關的故事訴說我的生命經曆,同時也是把自己變化為這些動物,鑽到他們皮膚下體驗當一隻蟲的滋味,看看自己或自己內在的情緒是否和他們有相似之處。
和前段提到的三個階段類似,這「二十五變」也是流動的過程。我有時候是阿米巴蟲,有時候是浪漫蟲,有時候什麼蟲都不是,隻是一個試圖適應現實、與環境共生共榮、在獨立及與人互相扶持之間取得平衡(不一定經常成功)的人。
雖然書裏寫的是真實發生的事件,但它還是一部用文學手法寫下的文學作品。既然是文學,必定或多或少有誇張、為瞭敘事需要或戲劇性而虛構、剪裁的部分,也有隱蔽沒說的部份。我並不覺得這些故事就因此而變得不真實。這些故事所描寫的情感依然是真實的,隻是換瞭一種方式呈現,蛻變為隱喻,就像這本書中的寄生蟲也是一個隱喻。
寫作《我媽媽的寄生蟲》的目的是什麼?我想一個理由是為瞭和我父母溝通、試圖瞭解他們和我自己(就像他們以前透過書本和我溝通、透圖瞭解我)。另一個理由是我想從彆人的敘事(書本、網路文章、專傢說法、名人觀點、鄉民爆料……)中掙脫,開始擁有我自己的敘事,並且想透過這個行動告訴讀者: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敘事。每個人都有權利以自己的方式去訴說自己的故事,不管他或她的故事在彆人眼中是成功還是失敗、值不值得說、說得好還是說得不好。
我不覺得我的敘事一定是對的,也並不想「隻」活在自己的敘事中,聽不見彆人的聲音、看不見彆人的觀點。但是,我必須有我自己的敘事,必須用我自己的眼光注視自己。不然,我就等同於不存在。因為如果沒有自己的想法,我就隻是一個寄生在彆人頭腦中的寄生蟲,或是反過來,讓彆人的思想寄生在我的腦袋。
我不想要再寄生瞭。不管是在經濟、思想、還是情感的層麵。我想要走嚮獨立,並且正在這條路上走著。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走到一個令我滿意的終點,但是我知道我必須自己去定義終點的位置,並且自己決定在哪些地方可以停下來休息(一定要達到終點纔可以休息?還是中途也可以停下來休息?遺憾的是,我目前還無法做到允許自己休息這件事),而不是等彆人來定義它。我也必須自己決定「獨立」、「依賴」、「接受幫助」之間的分界。
我曾經認為,「獨立」就是完全不接受彆人的幫助、完全不依賴彆人,但是我現在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也不需要這麼做。這些年來,我接受瞭來自父母、丈夫、孩子、治療師、朋友的幫助,並且也盡瞭自己的努力,纔能從睏境中走齣來、並且尋找屬於我的路(我不認為「走齣來」就是結束,而是一個一直往前的過程)。對於給我幫助的人,我由衷地感謝,並且希望我能夠盡我的力量,在人生道路上也給予他們幫助──不是迴報,而是互相扶持──及歡樂。
我希望,這本書也可以給某個我不認識的陌生讀者扶持,甚至是歡樂。我無法決定事情是否會如此,但是如果真的發生瞭,那我會很高興並感激。
圖書試讀
我小時候經常和朋友一起去河邊釣魚,那些魚都有縧蟲,我們把蟲從魚肚子裏扯齣來,把它們埋在土裏(因為怕狗去挖),然後把魚烤來吃。有一次,在我們埋完蟲後,有一個小孩跑來附近玩。他在地上東挖西挖,也不知道在挖什麼。後來他的爸媽來找他,他驕傲地轉嚮他們,手裏拿著我們的縧蟲,大喊:「哈哈哈!你們看我找到什麼?鞋帶!」──我的波蘭朋友E和我說的故事
我印象最深刻的童年迴憶之一,是一隻在東京「目黑寄生蟲館」看到的縧蟲。
那是人的縧蟲。牠到底有多大我已經忘瞭,隻記得很大很大,像輓聯或那種用來上吊的白布條一樣掛在牆上,比當時的我高齣好幾倍,而且還繞瞭好幾圈。想來應該有十公尺吧。也許,牠並沒有這麼大,隻是在我孩童的眼光看來,牠簡直大到不可思議。
我會看到這隻縧蟲,是因為我媽媽。她當時在颱灣知名學府T大的寄生蟲學科工作,是那裏的副教授。當彆人問起她的職業,她總是曖昧地笑著說:「我在教寄生蟲。」言下之意,學生也是寄生蟲。所以那些學寄生蟲的研究生為瞭避嫌,都說他們是「微研所」的學生,而非「寄生蟲學組」學生。
從我有記憶開始,寄生蟲就存在於我生命中,和我常相左右,像是童年最好的玩伴或最棒的玩具(雖然,牠不能陪我玩也不能讓我拿來玩),或甚至,一個隱形的手足。
在我開始學英文,認識ABC並且會說第一句英語「How are you?」之前,我就記住瞭一個非常難並且拗口的英文單字──Parasitology(寄生蟲學)。我媽媽指著電梯前的樓層標示嚮我解釋這個字,當時小小年紀的我發下宏願,要把旁邊其他的英文單字如Anatomy(解剖學)、Pharmacology(藥理學)、Biochemistry(生物化學)、Public Health(公共衛生)……都背下來。
我有沒有想過要和爸媽一樣,成為一個具有博士頭銜的生物學傢?答案是有,也沒有。我小時候第一個誌願是當動物園園長(因為父母都是學生物的),後來是當發明傢(這是因為看瞭小叮當),之後是當小學老師(我父母、我外婆和我曾外祖父都是老師),十二歲的時候我立誌當作傢(這是因為看瞭張係國的小說《棋王》),然後念國中時我突然說,我要去研究水母(因為在帛琉看到的水母很漂亮,而且我想試試看被水母螫到是什麼滋味)。
用户评价
這本《我媽媽的寄生蟲》絕對是我近期閱讀體驗中最具顛覆性的一部作品。老實說,一開始吸引我的是那個充滿獵奇感和些微驚悚的名字,但讀完之後,我發現它遠不止於此。作者在敘事上展現齣瞭非凡的技巧,他/她沒有直接拋齣那些可能令人不安的元素,而是層層鋪墊,用一種近乎詩意的筆觸,描繪瞭主人公與母親之間那段復雜而又糾纏的關係。我特彆欣賞的是,書中對“寄生”這個概念的理解,它並沒有停留在生物學的層麵,而是將其延展到情感、心理乃至於生活方式的各個維度。讀到某些情節時,我仿佛能感受到那股無形的壓力,那種被某種東西附著、被慢慢侵蝕的無力感,但作者處理得非常剋製,沒有濫用煽情,而是讓讀者自行體會其中的深意。 母親這個角色,在書中被刻畫得立體而又多麵。她不是一個標簽化的形象,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反派。我反而看到瞭她身上那種令人心疼的脆弱,以及她試圖通過某種方式去“連接”或“控製”女兒時所錶現齣的,那種扭麯的愛。這種愛,如同寄生蟲般,雖然可能帶著毀滅性,但其根源卻可能源自深切的依賴和對失去的恐懼。作者巧妙地運用瞭大量的生活化細節,比如餐桌上的對話,衣物上的氣味,甚至窗外搖曳的樹影,都充滿瞭象徵意義,讓整個故事的氛圍顯得格外凝重,卻又不失日常的真實感。我常常在閱讀過程中停下來,思考作者是如何捕捉到這些細微的情感流動的,是如何將一種抽象的心理狀態具象化的。 “寄生蟲”這個隱喻,在書中反復齣現,卻又在不同的語境下呈現齣不同的解讀。它既可以是對母親某種病態行為的直接指代,也可以是對主人公自身內心某種陰影的投射。我甚至覺得,有時候,“寄生”更像是一種相互依存的極端形態,一種無法擺脫又無法割捨的羈絆。作者在這一點上處理得非常高明,沒有給讀者一個明確的答案,而是留下瞭廣闊的想象空間。每一次重讀,我都能從中發現新的層次,新的理解。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一個傢庭的故事,它更像是在探討人與人之間,特彆是親子之間,最深層的聯結與疏離。那種在看似平靜的生活錶麵下湧動的暗流,以及那些不為人知的,足以改變一切的秘密,都讓這本書充滿瞭引人入勝的力量。我強烈推薦給所有對人性、傢庭關係有深入思考的讀者。
评分《我媽媽的寄生蟲》,這個書名,光是聽起來就足以讓人産生無限的想象,那種有點令人不安卻又充滿好奇的吸引力,讓我毫不猶豫地拿起瞭這本書。但真正讀進去後,我纔發現,它所展現的內容,遠遠超齣瞭我最初的想象。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寄生”的故事,更是一次對親子關係,特彆是母女之間那種既是血脈相連又可能彼此消耗的復雜情感的深刻剖析。作者的敘事風格非常獨特,她沒有采取直白的講述,而是像一位技藝精湛的雕塑傢,一點一點地雕琢齣人物的內心世界,以及她們之間那張力十足的關係。 母親這個角色,可以說是全書的靈魂人物,也是最能引發讀者復雜情感的角色。她並非一個臉譜化的反派,而是一個混閤瞭母性光輝和一種近乎病態的控製欲的矛盾體。我常常在閱讀時,試圖去理解這位母親內心的孤獨與恐懼,她對女兒的“寄生”,或許是她試圖抓住某種確定性的唯一方式。作者在刻畫這個角色時,非常細膩,沒有給她簡單的標簽,而是讓她在矛盾與掙紮中,展現齣人性的多麵性。這種處理方式,反而讓人物更加真實,也更具衝擊力。 “寄生”這個概念,在書中被賦予瞭多重解讀的可能性。它不僅僅是生物意義上的侵占,更是一種情感上的依附,心理上的捆綁,甚至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固化。主人公試圖擺脫母親的“寄生”,但這份關係又如此根深蒂固,如同藤蔓一般纏繞著她,讓她難以呼吸。作者在描寫這種糾纏時,非常擅長運用象徵性的意象,將抽象的情感具象化。讀到某些情節時,我仿佛能感受到那股無形的壓力,那種被緊緊束縛,想要掙脫卻又無能為力的窒息感。 這本書讓我對“傢”這個概念有瞭更深的思考。它不僅僅是一個物理空間,更是情感的容器,是身份認同的源頭。主人公在書中,不僅是在與母親的“寄生”對抗,更是在尋找一個獨立自主的自我。這個過程充滿瞭痛苦和掙紮,但也因此顯得尤為珍貴。作者的筆觸冷靜而富有力量,她沒有給齣廉價的答案,而是留給瞭讀者廣闊的思考空間。這本書的深度和細膩,絕對值得反復品讀,每一次閱讀,都能從中發掘齣新的感悟。
评分《我媽媽的寄生蟲》,這個書名,絕對是我在書店裏一眼就會被吸引住的類型。它充滿瞭神秘感,又帶著一絲絲令人不安的預兆。但當我捧起這本書,真正走進作者構建的那個世界後,我纔發現,它所探討的,遠不止於一個獵奇的故事。這本書更像是一次對現代傢庭關係,特彆是母女之間那微妙而又充滿張力的聯結的深刻解剖。作者的敘事方式,不是那種直白的陳述,而是像一位高明的畫傢,用點、綫、麵,一點點地勾勒齣人物的內心世界和她們之間錯綜復雜的關係。 母親這個角色,在書中被刻畫得極其飽滿,她並非一個簡單的反派,而是一個集愛與控製、溫暖與壓抑於一身的復雜體。我常常在閱讀時,試圖去理解這位母親內心的掙紮,她對女兒的“寄生”,或許源於她自身生命中無法填補的空虛和恐懼。作者在處理這個角色時,非常細膩,沒有給她任何簡單的標簽,而是讓她在矛盾中展現齣人性的多麵性。這種處理方式,反而讓人物更加真實,也更具衝擊力。 “寄生”這個概念,在書中被賦予瞭多重含義。它不僅僅是生物意義上的侵占,更是一種情感的依附,心理的捆綁,甚至是一種生活模式的固化。主人公試圖擺脫母親的“寄生”,但這份關係又如此根深蒂固,如同藤蔓一般纏繞著她,讓她難以呼吸。作者在描寫這種糾纏時,非常擅長運用象徵性的意象,將抽象的情感具象化。讀到某些情節時,我仿佛能感受到那股無形的壓力,那種被緊緊束縛,想要掙脫卻又無能為力的窒息感。 這本書讓我對“傢”這個概念有瞭更深的思考。它不僅僅是一個物理空間,更是情感的容器,是身份認同的源頭。主人公在書中,不僅是在與母親的“寄生”對抗,更是在尋找一個獨立自主的自我。這個過程充滿瞭痛苦和掙紮,但也因此顯得尤為珍貴。作者的筆觸冷靜而富有力量,她沒有給齣廉價的答案,而是留給瞭讀者廣闊的思考空間。這本書的深度和細膩,絕對值得反復品讀,每一次閱讀,都能從中發掘齣新的感悟。
评分《我媽媽的寄生蟲》,這個書名一開始就足夠讓人好奇,但讀完之後,我發現它比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故事的展開方式非常有意思,作者並沒有急著去解釋“寄生蟲”到底是什麼,而是通過主人公的視角,一點一點地揭開她與母親之間那些不尋常的日常。這種敘事手法,就像是在一層層剝洋蔥,每一次剝開,都會露齣新的、更深層的味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對細節的捕捉能力。書中描繪的那些生活場景,無論是廚房裏升騰的水汽,還是客廳裏斑駁的光影,都帶著一種難以言說的,令人不安的美感。 母親這個角色,在我看來,是全書的靈魂人物。她不是那種扁平化的反派,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受害者。她身上混閤著母性的光輝和一種近乎病態的控製欲,這種矛盾的特質,反而讓人物更加真實,也更加令人著迷。我常常在想,是什麼樣的經曆,讓一個女人變得如此?書中並沒有直接給齣答案,而是通過一些零碎的對話和迴憶,讓讀者自己去拼湊。這種“留白”的處理方式,我個人非常喜歡,它給瞭我很多思考的空間。 “寄生”這個概念,在書中被運用得非常巧妙。它不僅僅是字麵上的意義,更是一種情感上的依附,一種精神上的捆綁。主人公試圖擺脫這種“寄生”狀態,但又在某種程度上被這種關係所定義。我讀到的一些情節,讓我感到非常壓抑,仿佛能感受到那種被無形的力量所束縛的窒息感。但作者的處理又很細膩,沒有讓這種壓抑變得濫俗。相反,它營造齣一種獨屬於這本書的,一種淡淡的憂傷和無奈。 這本書讓我重新審視瞭“親密關係”的定義。有時候,最親近的人,反而會帶來最深的傷害。而“傷害”本身,也可能是一種扭麯的愛。作者通過這本書,探討瞭這種復雜的親子關係,以及個體在傢庭環境中所經曆的掙紮與成長。我喜歡這種不提供廉價答案的書,它讓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迴味。這種閱讀體驗,是很多作品無法給予的。它更像是一種精神上的洗禮,讓我對一些習以為常的事物有瞭新的看法。
评分《我媽媽的寄生蟲》,這書名本身就帶著一股子詭異又迷人的氣息,很容易就讓人産生好奇。不過,當我真正開始讀的時候,我發現它並不是那種簡單的恐怖故事。作者非常擅長用一種“軟”的方式來鋪陳,把那種“寄生”的感覺,一點點地滲透到故事的肌理裏。整個故事的基調,不是那種轟轟烈烈的衝突,而是像潮水一樣,緩慢但有力地湧上來,把人慢慢地包裹進去。 我最想提的就是母親這個角色,簡直太復雜瞭。她身上有那種為人母的溫柔,但同時又有一種讓人喘不過氣來的控製欲。我總覺得,她並不是故意要傷害女兒,而是她自己的人生也充滿瞭太多無法言說的東西,所以她隻能用這種方式來抓住些什麼,抓住女兒,抓住她所認為的“正常”。作者對這個母親的描繪,非常立體,沒有把她臉譜化,而是讓你看到瞭她背後那種深深的孤獨和恐懼。 “寄生”這個詞,在書中被用得非常巧妙。它不單單是字麵上的那種侵占,更是一種情感上的糾纏,一種精神上的依賴。主人公一直試圖掙脫,想要過自己的生活,但母親的“寄生”已經滲透到她的方方麵麵,讓她很難找到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空間。我讀到一些情節的時候,感覺自己也跟著主人公一起在窒息,那種被無形的力量纏繞的感覺,真的讓人很揪心。 作者在描寫這些復雜的情感時,運用瞭很多生活中的小細節,比如母親做的飯菜的味道,她說話的語氣,甚至是一個不經意的動作,都充滿瞭深意。這些細節,就像是給“寄生”這個概念,披上瞭一層層真實的外衣,讓它顯得更加可怕,但也更加引人入勝。這本書讓我重新思考瞭“愛”的邊界,以及我們該如何在親密關係中,既保持連接,又不失去自我。它不是那種讀完就忘的書,會一直留在腦海裏,讓人迴味。
评分《我媽媽的寄生蟲》這個書名,光是聽起來就足夠讓人心頭一震,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吸引力。然而,當我真正翻開書頁,沉浸其中時,我纔發現,它所呈現的遠不止於一個驚悚的標題那麼簡單。作者以一種極其細膩且深刻的筆觸,描繪瞭一段復雜到令人窒息的母女關係。故事並非直接切入高潮,而是通過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細節,慢慢地將讀者引入一個充滿張力的世界。每一個字句,每一段描繪,都仿佛帶有某種潛藏的能量,一點點滲透進讀者的內心。 母親這個角色,在書中被塑造得極其飽滿,充滿瞭矛盾與掙紮。她並非一個簡單的惡人,而是一個在愛與占有、保護與控製之間搖擺的個體。她的每一個舉動,每一次言語,都似乎在試圖維係某種平衡,但這種平衡卻脆弱得不堪一擊。我常常在想,作者是如何捕捉到這樣復雜的人性的?是如何將一個母親的愛,扭麯成一種令人難以承受的“寄生”?這種處理方式,讓我對“母愛”這個概念,有瞭全新的認識,甚至是顛覆性的理解。 “寄生”的概念,在書中被賦予瞭多重解讀的可能性。它既可以是對某種病態情感的象徵,也可以是對主人公自身精神狀態的隱喻。我感覺,有時候,所謂的“寄生”,也是一種在失去對方之後,自己也無法獨立存在的極端依賴。作者在敘事上,非常擅長運用象徵手法,將一些抽象的情感,通過具體的意象呈現齣來。讀到某些段落時,我仿佛能感受到那股無形的壓力,那種被緊緊纏繞,無法呼吸的窒息感。 這本書讓我思考良多,關於傢庭,關於愛,關於成長。它揭示瞭在看似平靜的傢庭錶麵之下,可能隱藏著怎樣的暗流湧動。主人公在試圖擺脫“寄生”狀態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地尋找自我,定義自我。這種掙紮,是如此的真實,又是如此的令人心疼。作者並沒有給齣一個圓滿的結局,而是留下瞭很多值得玩味的空間。我喜歡這種不強行喂給讀者答案的作品,它讓我自己去挖掘,去思考,去構建屬於自己的理解。
评分《我媽媽的寄生蟲》,光是書名就足以讓人産生無限的遐想,充滿瞭神秘和一絲絲不安。但深入閱讀後,我發現它遠遠超齣瞭我對一個“奇幻”或“驚悚”故事的預期。這本書更像是一麵鏡子,照見瞭人際關係中最幽微、最復雜的部分,特彆是母女之間那種既是血脈相連又可能彼此消耗的深層聯結。作者的敘事方式非常獨特,沒有采用直白的敘述,而是通過主人公的視角,一點一點地揭示那個籠罩著她們母女的“寄生”陰影。 母親這個角色,可以說是全書的焦點,也是一個極具爭議的存在。她身上混閤瞭母性的光輝和一種令人窒息的控製欲,這種矛盾的特質,反而讓她顯得異常真實,甚至帶著一種讓人心疼的悲劇色彩。我多次在閱讀中停下來,思考這位母親內心的孤獨與恐懼,以及她試圖通過某種方式來“抓住”女兒,從而填補自身空虛的心靈。這種“抓”的動作,既是愛,也是一種無意識的傷害,將女兒也拖入瞭“寄生”的泥沼。 “寄生”這個概念,在書中被運用得非常巧妙,它不僅僅指代生物學上的侵蝕,更是一種情感上的依附、心理上的捆綁,甚至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固化。主人公試圖掙脫,卻又在無形中被母親的“寄生”行為所塑造,這種糾纏不清的關係,讓我在閱讀時常常感到一種壓抑和無力。作者的筆觸非常細膩,她擅長通過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來展現這種深層的關係。比如,一段無意義的對話,一個不經意的眼神,都能透露齣潛藏的危機。 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人物心理上的深度。她沒有將人物簡單地臉譜化,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去挖掘她們的動機和掙紮。這種對人性的深刻洞察,讓這本書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更像是一次對情感和心理的探索。主人公在試圖擺脫“寄生”的過程中,也在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這種自我救贖的過程,充滿瞭艱難與痛苦,但也因此顯得尤為動人。這本書帶給我的思考,是關於我們如何定義愛,如何擺脫不健康的依附,以及如何在復雜的關係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
评分《我媽媽的寄生蟲》這個書名,絕對是那種一看就讓人眼睛一亮,好奇心瞬間被勾起的類型。但當我真正沉浸在這本書的故事裏後,我發現它遠比這個聽起來驚悚的名字要深刻得多。作者以一種非常“沉”的方式,鋪陳開來,不是那種快節奏的推進,而是像在品一杯需要慢慢咀嚼的茶,每一口都帶著不同的迴甘。故事圍繞著主人公和她母親之間那種復雜到令人窒息的關係展開,那種“寄生”的感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像溫水煮青蛙一樣,一點點地滲透進生活裏。 母親這個角色,是我讀這本書過程中最大的感受點。她不是一個簡單的反派,也不是一個全然的受害者。她身上背負著太多,她的愛,她的控製,她的絕望,都以一種扭麯的方式呈現齣來。我常常在想,她是不是也曾經是彆人“寄生”的對象?或者,她自己也深陷在一種無法擺脫的孤獨之中,所以纔拼命地想要抓住什麼?作者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繪,非常細膩,沒有直接給結論,而是通過大量的細節,讓讀者去體會。那種無聲的壓抑,比大聲的嘶吼更能讓人感到震撼。 “寄生”的概念,在書中被延展得非常廣闊。它不僅僅是字麵意義上的掠奪,更是一種情感上的糾纏,一種精神上的依附。主人公想要“斷捨離”,想要擁有自己的獨立空間,但卻發現,這份“寄生”已經滲透到瞭骨子裏。這種掙紮,讓我感同身受。有多少人,在親密關係中,也曾經有過類似的感受?想要離開,卻又被某種東西牢牢地牽絆住。作者的文字,就帶著這種魔力,讓你覺得,這不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而是就發生在我們身邊。 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對“傢庭”這個概念,有瞭更深的理解。它不是一個完美的烏托邦,也不是一個全然黑暗的煉獄。它是一個充滿著復雜情感交織的地方,有愛,也有傷害,有溫暖,也有窒息。主人公在書中,不僅僅是在對抗母親的“寄生”,更是在尋找一個獨立自我的過程。這個過程充滿瞭痛苦,但也因此顯得格外珍貴。我喜歡作者這種不迴避復雜性的寫作方式,它讓我們看到,人性本身就是如此的多麵和矛盾。
评分《我媽媽的寄生蟲》,這本書的名稱本身就帶著一種引人遐思的張力,讓我一度以為會是某種奇幻冒險或者驚悚懸疑。然而,當我真正翻開它,我發現這本書所觸及的,是更為深邃,也更為貼近人心的議題——關於親子關係,關於情感的依附,以及個體如何在錯綜復雜的關係中尋找自我。作者的敘事手法非常高明,她沒有直接扔齣“寄生蟲”這個具象的概念,而是通過主人公的視角,一點一滴地展現瞭母親身上那種令人不安的“寄生”特質。 母親這個角色,可以說是全書的核心,也最能引起讀者強烈的情感共鳴。她不是一個簡單的惡魔,也不是一個全然的受害者。她身上混閤瞭母性的溫存與一種近乎病態的占有欲,這種復雜的混閤體,讓人既感到憐憫,又感到畏懼。我經常在想,是什麼樣的經曆,讓一位母親,將愛扭麯成瞭一種“寄生”?作者在刻畫這個角色時,非常細膩,沒有給齣一個簡單的評判,而是讓讀者去體會她的掙紮,她的孤獨,以及她對“連接”的極度渴望。 “寄生”的概念,在書中被解讀得非常多層次。它不僅僅是生物意義上的侵蝕,更是情感上、心理上的依附與捆綁。主人公試圖擺脫這種“寄生”,但這份關係又如此根深蒂固,仿佛已經成為瞭她生命的一部分。作者在描寫這種糾纏時,使用瞭大量的日常細節,比如餐桌上的沉默,衣物上的氣味,甚至是窗外的風景,都帶著一種難以言說的,令人不安的象徵意義。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描寫方式,反而讓“寄生”的力量更加滲透,更加令人心悸。 這本書讓我對“親密關係”有瞭更深刻的反思。有時候,最親近的人,反而會帶來最深的傷害,而這種傷害,又常常披著愛的外衣。主人公在書中,不僅僅是在對抗母親的“寄生”,更是在對抗自己內心深處的某種陰影,在尋找一個獨立自主的自我。作者的筆觸冷靜而剋製,沒有濫用煽情,而是讓讀者在沉默中體會那種壓抑與掙紮。這本書就像一杯陳年的酒,需要慢慢品味,越品越能體會到其中的醇厚與深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