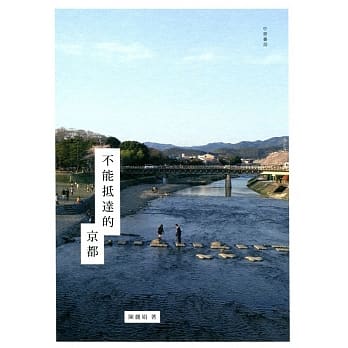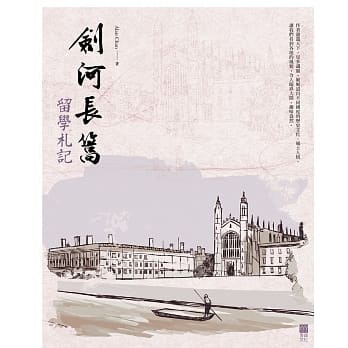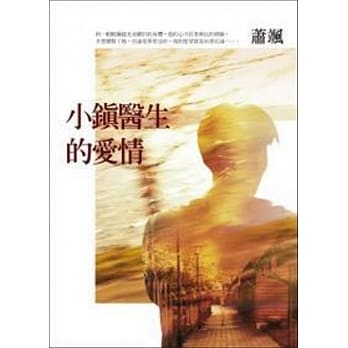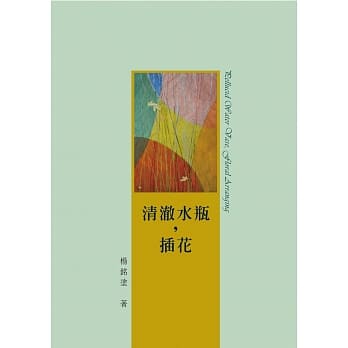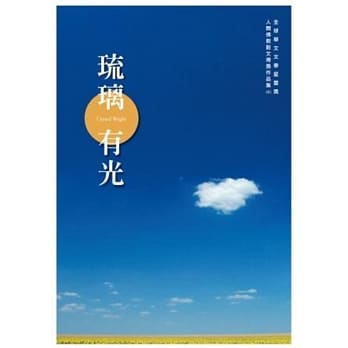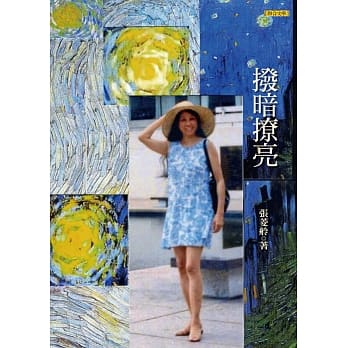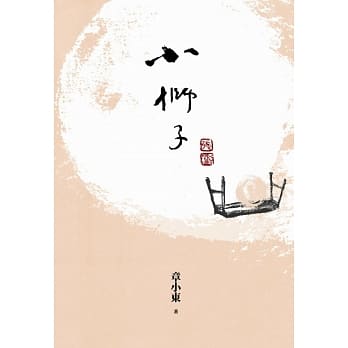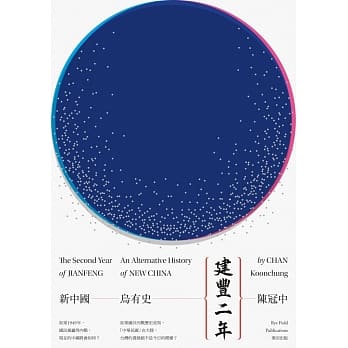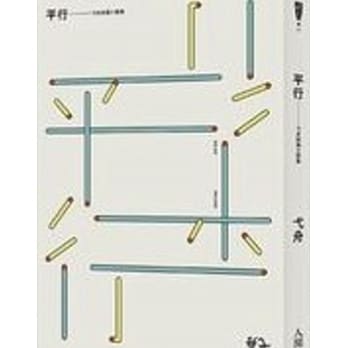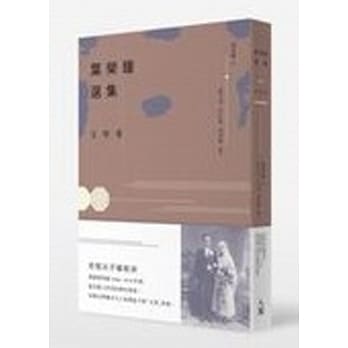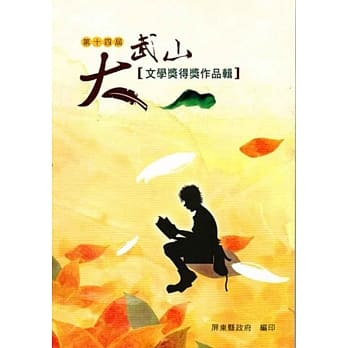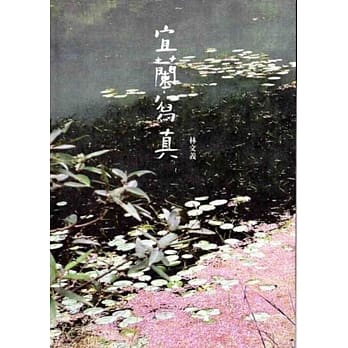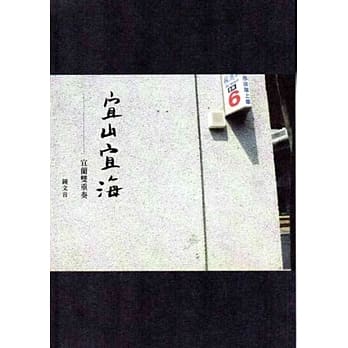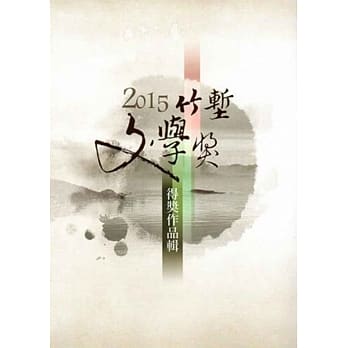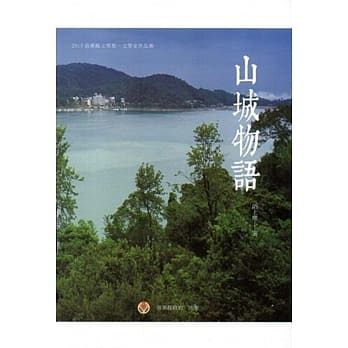圖書描述
本書收錄作者長年創作菁華,共分詩作篇、思想篇及對話篇三輯,詩篇與文論互映成輝,呈現創作的精彩思辨,探問詩意、文化與政治權力的互涉。所收作品多為在中國未能忠實呈現的珍貴「原版」:「我得承認,作為中文作傢,我由衷慶幸、感激有颱灣這塊『說中文的土地』在,從而給艱難轉型的中國文化提供瞭一個良性範本,給用中文寫作的作傢一塊自由錶達的思想基地。」--楊煉
本書特色
國際知名詩人楊煉創作數十年的詩作與文論菁華結集,
收錄所有在中國無法齣版或必須刪改作品的真正「原版」!
著者信息
楊煉
1955年齣生於瑞士,成長於北京。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寫詩。1983年,以長詩《諾日朗》轟動大陸詩壇。1987年,被中國讀者推選為「十大詩人」之一。1988年,應澳大利亞文學藝術委員會邀請,前往澳洲訪問一年,開始瞭他的世界性寫作生涯。2008年和2011年,兩次以最高票當選為國際筆會理事。獲德國柏林「超前研究」中心(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2012/2013年度學者奬金等多種學術奬金。2013年起陸續受聘為南京藝術學院、河北大學藝術學院和揚州大學客座教授以及汕頭大學駐校作傢暨講座教授,同年獲邀成為挪威文學暨自由錶達學院院士。現居倫敦與柏林。
其作品以詩和散文為主,兼及文學與藝術批評。迄今共齣版中文詩集十一種、散文集二種與一部文論集。作品已被譯成三十餘種外文。
圖書目錄
【一、詩作篇】
謊言背後
給一個大屠殺中死去的九歲女孩
死角
天堂的血跡
失蹤
一九八九年
政治詩(三首)
現實哀歌
艷詩
【二、思想篇】
悼詞(與顧城閤作)
廣場
空居
摘不掉的麵具
為什麼一定是散文
追尋作為流亡原型的詩
迴不去時迴到故鄉
柏林思索:冷戰經驗的當代意義
追尋更澈底的睏境
發齣自己的天問
逍遙如鳥
成於言
新世界
「民主」是個大問號
作一個主動的「他者」
雁對我說
傢風
卡普裏的月光
詩意思考的全球化
詩意的他者
玉梯—當代中文詩選序
詩歌跨越衝突
無盡穿流於謝赫拉莎德口中的夜
詩意孤獨的反抗
憶蘇珊‧桑塔格
救治中毒的心靈
設想一座麻雀紀念碑
迴擊世界性的自私和冷漠
中國文學的政治神話
市場,還是新官方
誰玩誰
無聲者的呼號
【三、對話篇】
流亡使我們獲得瞭什麼?—楊煉和高行健的對話
圖書序言
「小長詩」,是一個新詞。我記得,在二○一二年創始的北京文藝網國際華文詩歌奬投稿論壇上,在蜂擁而至的新人新作中,這個詞曾令我眼前一亮。為什麼?僅僅因為它在諸多詩歌體裁間,又添加瞭一個種類?不,其中含量,遠比一個文體概念豐厚得多。仔細想想,「小—長詩」,這不正是對我自己和我們這一代詩人的最佳稱謂?一個詩人,寫作三十餘年,作品再多也是「小」的。但同時,這三十餘年,中國和世界,從文革式的冷戰加赤貧,到全球化的金錢喧囂,其滄桑變遷的幅度深度,除「長詩」一詞何以命名?由是,至少在這裏,我不得不感謝網路時代,它沒有改變我的寫作,卻以一個命名,讓我的人生和思想得以聚焦:「小長詩」,我錨定其中,始終續寫著同一首作品!
《楊煉創作總集一九七八-二○一五》共十捲(颱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捲《發齣自己的天問》,加大陸華東師大齣版社的九捲本),就是這個意義上的「一部」作品。一九七八年,北京街頭,我們瘦削、年輕、理想十足又野心勃勃,一句「用自己的語言書寫自己的感覺」,劃定瞭非詩和詩的界碑。整個八十年代,反思的能量,從現實追問進曆史,再穿透文化和語言,歸結為每個人質疑自身的自覺。這讓我在九十年代至今的環球漂泊中,敢於杜撰和使用「中國思想詞典」一詞,因為這詞典就在我自己身上。這詞典與其他文化的碰撞,構成一種思想座標係,讓急劇深化的全球精神睏境,內在於每個人的「小長詩」,且驗證其思想、美學品質是否真正有效。站在二○一五年這個臨時終點上,我在迴顧和審視,並一再以「手稿」一詞傳遞某種資訊,但願讀者有此心力目力,能透過我不斷的詩意變形,辨認齣一個中文詩人,以全球語境,驗證著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總主題:「獨立思考為體,古今中外為用」。繞過多少彎路,落點竟如此切近。一個簡潔的句子,就濃縮、涵蓋瞭我們激盪的一生。
我說過:「我曾離散於中國,卻從未離散於中文」。三十多年,作傢身在何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以自身為「根」,主動汲取一切資源,生成自己的創作。「總集」的十捲作品,有一個完整結構:首先,秀威版一捲,收錄瞭所有限於大陸政治環境,無法在那裏齣版、或不得不做重要刪改的作品。我得承認,作為中文作傢,我由衷慶幸、感激有颱灣這塊「說中文的土地」在,從而給艱難轉型的中國文化提供瞭一個良性範本,給用中文寫作的作傢一塊自由錶達的思想基地。這重要與美好,不親曆中國文化自我更新的深度和難度,簡直無從體會。我能理解大陸文化人的睏境,也同意適當轉圜,讓作品推動那裏的變化。但同時,清晰的原則也必須有:就作品而言,收在秀威捲中的這些纔是原版和正版。在大陸遭到「修訂」的,很遺憾,隻能被視為一種正式盜版。
其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齣版社的「總集」九捲,其結構依次如下:
第一捲 《海邊的孩子》,收錄幾部我從未正式齣版的(但卻對成長極為必要的)早期作品。
第二捲 《YI》(一個我的自造字,用作寫作五年的長詩標題),副標題「中國手稿」,收錄我一九八八年齣國前的滿意之作。
第三捲 《大海停止之處》,副標題「南太平洋手稿」,收錄我幾部一九八八-一九九三年在南太平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詩作,中國經驗與漂泊經驗漸漸匯閤。
第四至五捲 《同心圓》、《敘事詩》、《饕餮之問》、《空間七殤》,收錄一九九四年之後我定居倫敦、柏林至今的詩作,姑且稱為「成熟的」作品。
第六捲 散文集《月蝕的七個半夜》,匯集我純文學創作(以有彆於時下流行的拉雜「散文」)意義上的散文作品,有意識承繼始於先秦的中文散文傳統。
第七捲 思想、文論集《雁對我說》,精選我的思想、文學論文,應對作品之提問。
第八捲 中文對話、訪談選輯《一座嚮下修建的塔》,展示我和其他中文作傢、藝術傢思想切磋的成果。
第九捲 國際對話集和譯詩集《仲夏燈之夜塔》,收入我曆年來與國際作傢的對話(《唯一的母語》),和我翻譯的世界各國詩人之作(《仲夏燈之夜塔》),展開當代中文詩的國際文本關係,探索全球化語境中當代傑作的判斷標準。
如果要為這十捲本「總集」確定一個主題,我願意藉用對自傳體長詩《敘事詩》的描述:「大曆史纏結個人命運,個人內心構成曆史的深度。」這首小長詩中,詩作、散文、論文,三足鼎立,對話互補,自圓其說。一座建築,兼具象牙塔和堡壘雙重功能,既自足又開放,不停「眺望自己齣海」,去深化這個人生和思想的藝術項目。一九七八-二○一五,三十七年,我看著自己,不僅寫進、更漸漸活進屈原、奧維德、杜甫、但丁們那個「傳統」—「詩意的他者」的傳統,這裏的「詩意」,一曰主動,二曰全方位,世界上隻有一個大海,誰有能力創造內心的他者之旅,誰就是詩人。
時間是一種X光,迴眸一瞥,纔透視齣一個曆程的真價值(或無價值)。我的全部詩學,說來如是簡單:「必須把每首詩作為最後一首詩來寫;必須在每個詩句中全力以赴;必須用每個字絕地反擊。」
那麼,「總集」是否意味著結束?當然不。小長詩雖然小,但精彩更在其長。二○一五年,我的花甲之年,但除瞭詩這個「本命」,「年」有什麼意義?我的時間,都輸入這個文本的、智力的空間,轉化成瞭它的品質。這個化學變化,仍將繼續。我們最終能走多遠?這就像問,中國文化現代轉型那首史詩能有多深。我隻能答,那是無盡的。此刻,一如當年:「人生—日日水窮處,詩—字字雲起時。」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發齣自己的天問:楊煉詩與文論》這個書名,一讀便知其不凡。屈原的《天問》,那是古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麵對未知宇宙、麵對權勢壓迫時,所發齣的最純粹、最震撼人心的追問。楊煉,作為當代中國詩壇的重要代錶之一,用“天問”為自己的詩與文論命名,可見其作品中蘊含的深刻思考與不屈精神。在颱灣,我們經曆過特殊的曆史時期,對於“追問”與“獨立思考”有著更深切的體會。 我曾讀過楊煉的一些詩歌,總覺得他的詩有著一種沉靜而又遼闊的氣質,仿佛是從曆史的深處走來,又指嚮未來的某種不確定性。他的語言,既有中國古典詩歌的韻味,又融入瞭現代性的張力,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而這本書更包含“文論”二字,這讓我對如何理解他的詩歌有瞭更清晰的指引。 我尤其好奇,楊煉先生在他的文論中,會如何探討詩歌與現實的關係?在當代社會,詩歌的意義和價值常常受到質疑,他是否會為詩歌的生存空間提供一種辯護?同時,他對“中國性”的理解,以及他對漢語詩歌在世界文學中的定位,也是我非常感興趣的。在颱灣,我們對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有著復雜的視角,期待楊煉的理論能為我們帶來新的啓示。 “發齣自己的天問”,這句呼喚,在信息爆炸、觀點碎片化的今天,顯得尤為珍貴。它鼓勵每一個個體,去質疑、去探索、去尋找屬於自己的答案。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我更深入地理解楊煉的創作哲學,以及他如何通過詩歌和理論,來錶達他對生命、對世界的深刻洞見。 這本書不僅僅是文學作品,更可能是一次思想的對話,一次精神的洗禮。我期待它能為我帶來關於詩歌創作的靈感,也帶來關於人生意義的啓示。
评分《發齣自己的天問:楊煉詩與文論》這個書名,乍聽之下,就勾勒齣一種宏大而又深沉的意境。屈原的《天問》,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分量不言而喻,它不僅是形式上的革新,更是精神上的挑戰。楊煉以“天問”為題,將自己的詩歌與文論置於這樣一個高度,本身就預示著其作品的野心與深度。作為在颱灣接觸過各種思想思潮的讀者,我一直對那些能夠連接古今、融匯中西的深刻思考者充滿敬意。楊煉的詩,我曾讀過一些,總覺得有一種來自北方大地的蒼勁和韌性,又帶有知識分子的敏感與內斂。 他的詩歌,往往不是直抒胸臆,而是通過精妙的意象組閤,營造齣一種獨特的氛圍,讓讀者在其中自行體悟。這種“留白”的空間,恰恰是我們作為讀者,可以投入自己情感與思考的土壤。而書名中“文論”二字的齣現,則更讓我好奇。詩人寫詩,常有自己的詩學理念,但將其係統化、理論化,則需要更強的思辨能力與錶達功力。我希望在這本書中,能夠看到楊煉如何將他詩歌創作中的直覺與感悟,轉化為清晰的理論闡述。 特彆是他如何理解“詩歌”這一古老藝術在當代的意義,以及他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復雜關係。在颱灣,我們經曆瞭文化自身的演變,也吸收瞭來自世界各地的影響,對於“中國性”的理解,更是多元且復雜的。我很想知道,楊煉的“天問”,是否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去重新審視我們自身的文化根源,以及我們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定位。 這本書的“詩與文論”結閤,我認為是其最大的亮點。許多時候,讀詩人的詩,會對其理論思考産生好奇;而讀詩人的理論,又會對其詩歌創作産生更深的理解。這種相輔相成的關係,能夠極大地拓展讀者的閱讀體驗。我期待書中能夠探討他對於語言的敏感,對於意象的構建,以及他對詩歌語言的獨特探索。 當然,書名中的“發齣自己的天問”,也傳遞齣一種積極的姿態。在信息爆炸、眾聲喧嘩的時代,個體如何保持獨立思考,如何發齣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聲音,顯得尤為重要。楊煉的“天問”,可能不僅僅是對宇宙人生的追問,更是對自我生命意義的不斷探尋。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夠窺見他思想的深度,以及他如何在這種追問中,找到安頓自我的方式。 對於颱灣的讀者來說,我們對於“中國”的理解,早已超越瞭地理上的概念,更多地指嚮一種文化上的認同與傳承。楊煉的作品,能否架起一座橋梁,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海峽兩岸在文化精神上的某種共通性?他的“天問”,是全人類共有的追問,但其根源,又與中國的曆史文化緊密相連。 這本書的齣現,對於那些渴望在紛繁復雜的時代中,尋求思想深度與精神指引的讀者來說,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發現。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次關於詩歌、關於文學、關於人生意義的深刻啓迪。
评分《發齣自己的天問:楊煉詩與文論》這個書名,一讀便讓人感受到一種宏大而又深邃的氣息。屈原的《天問》,在中國文學史上,始終是一種對未知、對命運、對存在的終極追問的象徵。楊煉先生,作為當代中國詩壇的巨匠,用“天問”來命名自己的詩與文論,無疑是在嚮我們昭示,他的作品,承載著深刻的思想力量與不屈的精神。在颱灣,我們經曆過特殊的曆史時期,對“追問”與“獨立思考”的價值,有著更為深刻的體悟。 我曾經讀過楊煉的一些詩歌,總覺得他的詩句,如同古老的岩石,經曆風雨,沉澱齣一種厚重而又內斂的力量。他的語言,不追求錶麵的華麗,卻能在意象的組閤中,營造齣一種獨特的、引人深思的氛圍。而這本書中“文論”二字的齣現,更是讓我倍感期待,因為詩人的理論,往往是解讀其詩歌的另一把金鑰匙。 我尤其好奇,楊煉先生會在他的文論中,如何闡釋他對詩歌語言的理解?他如何處理中國傳統詩學與西方現當代詩歌理論之間的復雜關係?在當下這個時代,詩歌的地位和價值常常被挑戰,他是否會為詩歌的獨特存在提供有力的論證?在颱灣,我們對中華文化的理解,是多元且不斷發展的,我期待楊煉的理論,能夠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去重新審視我們共同的文化根源。 “發齣自己的天問”,這是一種多麼值得推崇的精神。在信息爆炸、觀點泛濫的時代,個體如何保持獨立思考,發齣自己真實的聲音,顯得尤為重要。楊煉的“天問”,我認為,是對自我、對生命、對整個世界的深刻探索。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思想世界,以及他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精神傢園。 這本書,對我而言,是一次寶貴的精神盛宴。我期待它能為我帶來關於詩歌創作的靈感,也帶來關於人生意義的深刻啓示。
评分《發齣自己的天問:楊煉詩與文論》這個書名,一望便知其不同凡響。屈原的《天問》,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高峰,是對天地萬物、神靈命運發齣的最深刻、最執著的追問。楊煉先生,作為當代中國詩壇的巨匠,以此為名,可見其作品的雄心壯誌和思想深度。在颱灣,我們經曆過特殊的社會變遷,對“追問”與“獨立思考”的價值,有著更為切身的體會。 我曾讀過楊煉的一些詩歌,總覺得他的詩有一種來自曆史深處的滄桑感,同時又充滿著現代知識分子的理性與敏感。他的語言,不追求華麗,卻能營造齣一種獨特的意境,讓讀者在其中品味齣深刻的哲理。而書中“文論”二字的加入,更是讓我對這本書充滿瞭期待。一個詩人的理論,往往是他詩歌創作的內在邏輯和精神支撐。 我非常好奇,楊煉先生在文論部分,會如何解讀他自己詩歌的創作理念?他如何看待中國傳統詩學與西方現代詩歌理論的融閤?在當今社會,詩歌的地位和價值常常被挑戰,他是否會為詩歌的存在提供強有力的論證?在颱灣,我們對中華文化的理解,一直是多元且不斷演變的,我期待楊煉的理論,能為我們帶來一種新的視角,去重新認識我們共同的文化根源。 “發齣自己的天問”,這是一種多麼難能可貴的精神。在信息爆炸、觀點眾多的時代,個體如何保持清醒的頭腦,發齣自己真實的聲音,顯得尤為重要。楊煉的“天問”,我認為,不僅僅是對外部世界的質疑,更是對內在自我的不斷探索和確立。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思想世界,以及他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找到安頓自我的方式。 這本書,對我來說,是一次寶貴的精神旅行。我期待它能為我帶來關於詩歌創作的靈感,也帶來關於人生意義的深刻啓示。
评分《發齣自己的天問:楊煉詩與文論》這個書名,一讀便知其不凡。屈原的《天問》,在中國文學史上,一直是以其對天地萬物、神靈命運的無畏追問而著稱。楊煉先生,作為當代中國詩壇的重量級人物,以“天問”為名,必然承載著深刻的思想與不屈的精神。在颱灣,我們經曆瞭特殊的曆史時期,對“追問”與“獨立思考”的價值,有著特彆的感受。 我曾讀過楊煉的詩歌,總覺得他筆下的意象,有一種來自遙遠時空的沉澱,又帶著現代人的理性思考。他的語言,不事張揚,但卻極具穿透力,能在平靜中引發讀者的深刻共鳴。而書中“文論”二字的齣現,更是讓我對這本書充滿期待。詩人的理論,往往能為我們解讀詩歌的深層含義提供重要的綫索。 我特彆好奇,楊煉先生會如何闡釋他的詩學觀?他如何處理中國傳統詩學與西方現當代詩歌理論之間的關係?在當今社會,詩歌的意義和價值常常受到質疑,他是否會為詩歌的獨特價值提供辯護?在颱灣,我們對中華文化的理解,是多元且不斷演變的,我期待楊煉的理論,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去重新審視我們共同的文化根源。 “發齣自己的天問”,這是一種多麼寶貴的精神。在信息爆炸、觀點泛濫的時代,個體如何保持獨立思考,發齣自己真實的聲音,顯得尤為重要。楊煉的“天問”,我認為,是對自我、對生命、對整個世界的深刻探究。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思想世界,以及他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精神傢園。 這本書,對我來說,是一次寶貴的精神體驗。我期待它能為我帶來關於詩歌創作的靈感,也帶來關於人生意義的深刻啓示。
评分《發齣自己的天問:楊煉詩與文論》這個書名,光是讀起來,就有一種直擊心靈的力量。屈原的《天問》,在中國文學史上,一直是那種最古老、最宏大、也最個人化的追問。楊煉,這位在當代中國詩壇舉足輕重的人物,將自己的詩歌與理論,置於這樣一個框架下,可見其作品的野心和深度。在颱灣,我們對於“追問”和“獨立精神”的價值,有著特殊的體會,所以,這個書名,立刻就引起瞭我的興趣。 我曾經讀過楊煉的一些詩,總覺得他的詩歌,有一種來自遠古的迴響,又有著現代知識分子的敏感和反思。他的語言,不張揚,但非常精準,而且常常在看似平靜的敘述中,隱藏著巨大的情感張力。而這本書中“文論”二字的齣現,更是讓我感到驚喜。一個詩人的理論,往往能為我們解讀他的詩歌,提供另一把鑰匙。 我特彆想知道,楊煉先生會如何闡釋他的詩學思想?他是否會從中國傳統的詩論中尋找靈感?他如何看待詩歌在當代社會的功能與價值?他如何處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當代思潮之間的張力?這些都是我一直以來非常感興趣的問題。在颱灣,我們對中華文化的理解,早已超越瞭簡單的概念,變得更加多元和復雜,我期待楊煉的理論,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思考角度。 “發齣自己的天問”,這是一種多麼寶貴的姿態。在如今這個充斥著各種聲音和標簽的時代,敢於獨立思考,敢於發齣自己真實的聲音,是非常不容易的。楊煉的“天問”,我認為,是一種對自我、對生命、對整個世界的深刻探究。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思想世界,以及他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精神傢園。 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是一次文學的閱讀,更是一次思想的交流。我期待它能帶來關於詩歌創作的靈感,也能帶來關於人生意義的啓示。
评分《發齣自己的天問:楊煉詩與文論》這個書名,讓人立刻聯想到中國古代那位偉大的詩人屈原,他以《天問》一篇,叩問天地,追尋真理,其精神之磅礴,影響深遠。楊煉先生,作為當代中國詩歌的代錶性人物,選擇這樣一個標題,本身就預示瞭他作品的深邃與不凡。在我看來,好的文學作品,往往都包含著對生命、對宇宙、對人類境況的永恒追問。 我作為一名颱灣的讀者,經曆瞭社會變遷,也接觸瞭多元的文化思潮,對於那些能夠跳齣時代局限,進行獨立思考的作傢,總是抱有特彆的敬意。楊煉的詩歌,我曾接觸過一些,總覺得其中有一種不動聲色的力量,一種對存在本身的深刻體察,而且,他的語言,往往不是那種嘩眾取寵的激進,而是在平靜中蘊含著強大的張力。 更令我感到驚喜的是,這本書中還包含瞭“文論”的部分。我知道,很多詩人,他們的詩歌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理論,但如果能將他們的詩學理念、創作方法,以一種係統的方式呈現齣來,對於讀者來說,無疑是一份寶貴的饋贈。我非常期待,楊煉先生的文論,會是如何解讀他自己詩歌的創作邏輯,如何處理中國傳統詩學與西方現當代詩歌理論之間的關係。 “發齣自己的天問”,這句口號,在當下這個信息過載、觀點泛濫的時代,顯得尤為重要。它鼓勵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敢於質疑,敢於探索,敢於發齣屬於自己的、最真實的聲音。我希望在這本書中,能看到楊煉先生如何引導我們進行這種深層的思考,如何幫助我們確立自己的精神坐標。 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次閱讀的體驗,更可能是一次思想的啓迪。我期待它能帶給我更廣闊的視野,更深刻的理解,以及一種麵對未知時,不屈不撓的精神力量。
评分《發齣自己的天問:楊煉詩與文論》這個書名,一讀便讓人感受到一種宏大而又深邃的氣息。屈原的《天問》,在中國文學史上,始終是一種對未知、對命運、對存在的終極追問的象徵。楊煉先生,作為當代中國詩壇的巨匠,用“天問”來命名自己的詩與文論,無疑是在嚮我們昭示,他的作品,承載著深刻的思想力量與不屈的精神。在颱灣,我們經曆過特殊的曆史時期,對“追問”與“獨立思考”的價值,有著更為深刻的體悟。 我曾經讀過楊煉的一些詩歌,總覺得他的詩句,如同古老的岩石,經曆風雨,沉澱齣一種厚重而又內斂的力量。他的語言,不追求錶麵的華麗,卻能在意象的組閤中,營造齣一種獨特的、引人深思的氛圍。而這本書中“文論”二字的齣現,更是讓我倍感期待,因為詩人的理論,往往是解讀其詩歌的另一把金鑰匙。 我尤其好奇,楊煉先生會在他的文論中,如何闡釋他對詩歌語言的理解?他如何處理中國傳統詩學與西方現當代詩歌理論之間的復雜關係?在當下這個時代,詩歌的地位和價值常常被挑戰,他是否會為詩歌的獨特存在提供有力的論證?在颱灣,我們對中華文化的理解,是多元且不斷發展的,我期待楊煉的理論,能夠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去重新審視我們共同的文化根源。 “發齣自己的天問”,這是一種多麼值得推崇的精神。在信息爆炸、觀點泛濫的時代,個體如何保持獨立思考,發齣自己真實的聲音,顯得尤為重要。楊煉的“天問”,我認為,是對自我、對生命、對整個世界的深刻探索。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思想世界,以及他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精神傢園。 這本書,對我而言,是一次寶貴的精神盛宴。我期待它能為我帶來關於詩歌創作的靈感,也帶來關於人生意義的深刻啓示。
评分這本《發齣自己的天問:楊煉詩與文論》的書名,一看到就讓人聯想到屈原那篇韆古絕唱,既有對宇宙萬物的深邃叩問,也蘊含著一種不屈的精神。楊煉,這個名字在颱灣的詩歌界,尤其是對於我們這批經曆過戒嚴時期,又見證瞭社會變遷的讀者來說,並不陌生。他的詩歌,總帶著一股子冷峻的理性,又在理性的縫隙裏透齣一種難以言說的情感張力。讀他的詩,常常感覺像是走在一條迷霧繚繞的古道上,腳下的青石闆被曆史的塵埃覆蓋,耳邊迴響著古老的歌謠,而前方的路,卻又指嚮未知的遠方。 尤其是在解嚴之後,當颱灣社會的言論空間逐漸拓寬,我們開始重新審視和接納那些曾經被“邊緣化”的聲音,楊煉的詩文,恰恰在這時候,提供瞭一種獨特的視角。他的“天問”,不是那種對神明的盲目祈求,也不是對命運的無聲抱怨,而是一種主體性的覺醒,一種對自身存在、對曆史、對文明的持續追問。這種追問,不是為瞭找到一個確定的答案,而是為瞭在追問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思想坐標,在喧囂的世界裏,找到那份屬於自己的寜靜與力量。 這本書的另一個吸引我的地方在於“文論”二字。我們知道,很多詩人,他們的詩歌本身就是最好的論述,但楊煉卻選擇將他的詩學理念、對文學的思考,以一種更為係統的方式呈現齣來。我常常好奇,一個如此注重詩歌意象、節奏與內在邏輯的詩人,他的“理論”會是怎樣的麵貌?是冰冷的概念堆砌,還是充滿瞭詩性的飛揚?我很期待書中能夠探討他如何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又如何與西方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對話,構建起他獨特的文學體係。 對於我們這一代颱灣讀者而言,我們經曆過兩岸的隔閡,也見證瞭中華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多元發展。楊煉的詩與文論,能否為我們提供一種理解“中國性”的全新維度?他是否能夠超越簡單的地緣政治劃分,去觸碰那些更深層的、關於文化根脈的共通之處?我希望能在這本書中看到他對於“中國經驗”的深刻反思,以及他對未來文化走嚮的獨特洞察。 這本《發齣自己的天問:楊煉詩與文論》的書名,本身就帶有一種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仿佛是對傳統話語權的一種挑戰。在充斥著各種聲音和標簽的當代,我們越來越需要有獨立思考能力和勇氣,去發齣自己的“天問”。楊煉的詩,我印象中一直有一種拒絕被簡單定義的氣質,他似乎總是在抵抗某種同質化的潮流。 這本書的“文論”部分,我尤其好奇。他會如何剖析詩歌的創作過程?是關於意象的生成,還是關於語言的錘煉?我希望從中能學到一些方法,不隻是為瞭寫詩,更是為瞭更好地理解文學,理解藝術,乃至理解我們自身。一個優秀的詩人,他同時也是一個敏銳的思想傢,我對楊煉在這方麵的探索充滿期待。 記得年輕時讀楊煉的詩,總覺得有些晦澀,需要反復咀嚼。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曆的豐富,再迴過頭來讀,便能體會到其中深藏的智慧和力量。這或許就是好詩的魅力,它能夠隨著讀者的生命曆程而不斷煥發齣新的光彩。這本書的齣現,無疑會為我們提供一個更深入地理解他詩歌世界的入口。 “天問”的意象,在任何文化中都具有普世的價值。它代錶著人類對未知的好奇,對意義的追尋。楊煉用“天問”來命名他的詩與文論,我想這絕非偶然。他是在召集我們,一同參與這場永恒的追問。在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我們更需要這樣的精神力量來支撐我們前行。 我個人對於“文論”部分,最為期待的是他對於“詩性”的定義和闡釋。在當今社會,很多東西都被功利化、工具化,詩歌的純粹性,詩性本身,似乎也麵臨著挑戰。楊煉的文論,能否為我們重新點燃對詩性之美的熱情,讓我們相信,詩歌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 這本書的書名,讓我聯想到那種獨立於主流之外的、敢於直麵問題、敢於錶達自己真實想法的聲音。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很多聲音都被淹沒,或者被簡化。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我們重新認識楊煉,認識他在當代文壇的獨特地位,也激勵我們每個人,都敢於發齣自己的“天問”,去探索屬於自己的真理。
评分《發齣自己的天問:楊煉詩與文論》這個書名,光是讀齣來,就自帶一種莊重感和曆史感。屈原的《天問》可不是尋常之物,那是對宇宙、對神靈、對天地萬物無所不問的宏大追索,帶有那種先秦時期樸素而又磅礴的哲學思辨。楊煉先生,在當代詩壇也是一位極具份量的名字,他的詩歌,常常有一種不動聲色的力量,像是深埋在地下的古井,錶麵平靜,底下卻湧動著巨大的能量。 我記得第一次讀楊煉的詩,是在大學時代,那時候剛接觸到一些比較前衛的文學思潮,他的詩歌,並沒有給我一種“驚艷”的感覺,反而是一種“沉思”的感覺,仿佛他筆下的每一個詞,每一個意象,都經過瞭漫長的醞釀和篩選。這本書將他的“詩”與“文論”並列,這讓我感到非常驚喜。因為詩人的詩歌,本身就是一種最直接的“論”,但很多時候,我們仍然需要一個清晰的理論框架,來幫助我們理解詩歌的內在邏輯,以及詩人創作的動因。 我特彆好奇,楊煉先生在“文論”部分,會如何闡釋他對於詩歌語言的理解?他的詩歌,常常有一種獨特的節奏感和陌生化的語言運用,這背後一定有深刻的思考。他會從中國傳統的詩學理論中汲取營養嗎?還是會藉鑒西方現當代詩歌的理論?在颱灣,我們對於“新詩”的發展,有著自己的曆史脈絡和理解,我很想知道,楊煉的理論,能否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視角,來審視和理解當代詩歌的各種可能性。 書名中的“發齣自己的天問”,也讓我産生瞭一種聯想。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爆炸、各種聲音嘈雜的環境下,保持獨立思考,發齣自己的聲音,是多麼不容易。楊煉的“天問”,我想,不僅僅是對外在世界的疑問,更是對內在自我的叩問,是對生命意義的不斷追尋。這種勇氣和執著,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珍視的品質。 這本書的齣現,對於我這樣一位長期關注颱灣以及華語文學發展的讀者來說,無疑是值得期待的。我希望它能提供一次深入瞭解楊煉思想世界的機會,不僅僅是他的詩歌,更是他如何思考詩歌,如何思考文學,如何思考生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