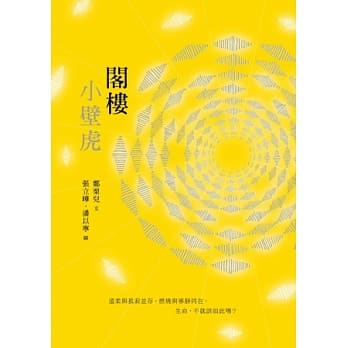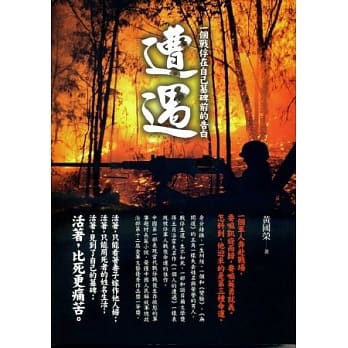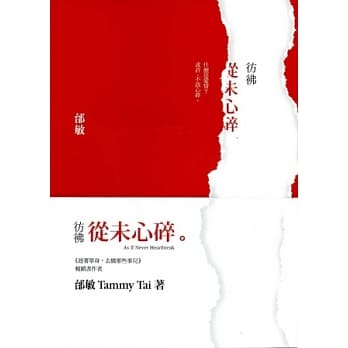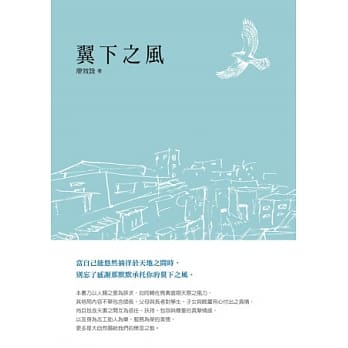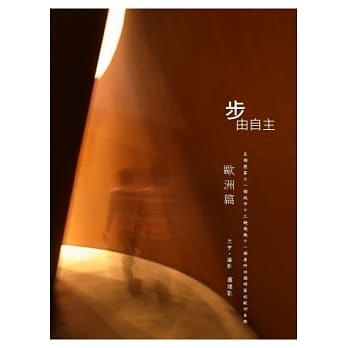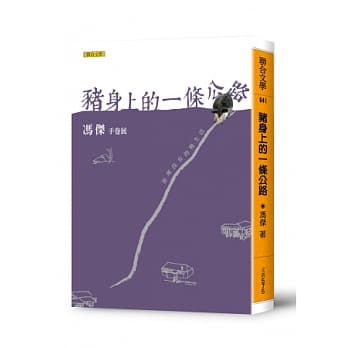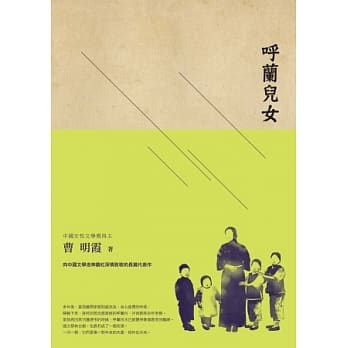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未至的命運 言叔夏
父の顔 楊富閔
輯一 必然的年輪
夢路i:慢慢地趕快
肇字者
孩子
夢路ii:夜宴
音想與發光的盒子
輯二 日常的岔路
歲時路
畸人誌
春風二記
販人
生活詞匯群
迷途
視窗
傢事說明書
廁所好聲音
學生
動詞書
抒情小兒科
聖誕
輯三 恍惚的月令
收獲一種時間的聲音
光的旅途
雨的標本
身分的截角
供品考
海邊午後
圖書序言
未至的命運 ◎言叔夏
和紘立認識不算久,寫起序來格外睏難(雖說認識若久,寫序大概也一樣睏難)。我們平日很少見麵。都是夜貓。在臉書上碰到的時間多是淩晨三四點。他睡不著,而我則是還沒要睡。偶爾傳訊,聊一些垃圾話。睡醒則多是下午三點鍾那種尷尬的時間。彼時天光漸暗,人世間的陽氣將盡,一日又將告終。半睡半醒地打開電腦,看他姍姍地上瞭綫瞭。也應是剛睡完瞭一個白日瞭罷。活到這個理應正常朝九晚五的歲數,有這樣作息刻度相仿的友人,有時想來也真令人心安。
大抵夜色適閤降靈。我們的關係與其說是朋友,不如更像問蔔者與占蔔師。我很有些處女座的友人,平常是大笑姑婆,三三八八地跟你說誰好帥喔誰好帥,到瞭夜晚,就莫名地成為瞭少女心。換瞭個腔,話語就轉瞭個彎,真心地跟你說:啊,真的好想談個戀愛喔!是真真實實地一個關於寂寞的煩惱。啊誰誰誰好帥喔。嬌嗔與花癡往往隻是一綫之隔。但我知道這些碎語其實都是嘴皮。有次我與他經過永和韓國街的小攤騎樓,他很煞有介事地停下來,執拗地要挑三雙畫瞭卡通動物的韓國襪子給男友。那是第一次我覺得他這人平常掛在嘴上的那些花癡,其實都隻是少女的花開。刀子口豆腐心。有時是孩子氣,過瞭頭免不瞭眾人都捏一把冷汗,卻倒也是個沒有作傢姿態的人。紘立平日三八,水星坐旺,是資訊與八卦電塔。坐席間常有驚人之語。他也不緊張,也不作態,光講自己的真話,就叫大傢倒抽一口氣。我也很少見過像他那樣,把寫作的真實需求赤裸裸地攤在彆人麵前,毫無姿態之人。初識時他談起寫作,是那樣完全沒有繞經任何精神性的岔路,彷彿隻是一個單純的願望(根本是生日許願、吹吹蠟燭):我想得奬拿錢齣國玩啊、我要買歐舒丹啊,還要買包包,我想存錢買房子,讓我媽我奶奶我阿姨都住進去。
讀瞭《壞狗命》纔知道那些媽媽奶奶阿姨跟他都住在萬華。母親在菜市裏販菜,傢中讀書寫字者唯其一人。所以那深夜傳來的訊息:「好啦!我要先帶狗齣去散步一下。」那散步的路徑想必是沿著萬華夜市背麵低矮的煙花巷柳、黑街暗弄逐漸展開瞭。又或者龍山寺廣場前雜遝橫躺的遊民之間。他和那狗會經過夜暗不眠的廣州街夜市、一個弄蛇人的小鉢前、賣炸旗魚輪與土虱的尋常小攤、不歸的攤上醉酒的兄弟、放佛音的老人……;又或者,他與那狗會一起經過那深夜裏山門緊閉的佛寺,因為夜晚的緣故,竟也就無緣照見那門裏的觀音一麵?土裏花來泥裏去,在日常的散步之中,有太多隱形的旅程是蔔算不齣來的。比如這部延續著前一本個人私史推進的《甜美與暴烈》,寫父親的離去,寫父親的迴返。比如寫父親老大以後返傢,竟已然是將死之軀瞭。
大抵書寫都在蔔算一卦將來未至的命運。那樣的書寫,其實和某些作傢筆下觀察者般的萬華艋舺極不相同。距離與觀看不再是重點,重要的是那些細瑣的話語、物件、氣味的交疊,形成瞭個人記憶的私史。有時甚或帶有一種黏滯的色彩:捕蠅紙般被黏在原地的母係傢族、昏暗老舊的公寓巷弄、無窗的房間;《甜美與暴烈》裏寫到他最喜歡傢中的一扇窗在客廳靠巷弄的那麵,總讓我想起童年時一個在菜市場裏開理發店的姑母。她們傢有一個和我年齡相同的錶妹。我常去那錶妹傢玩。那個錶妹傢陰暗的二樓也有那樣一扇麵對著市場巷弄的窗。玩得纍瞭,便趴在涼涼的磨石子地闆上睡著,做長長的夢。下雨的午後,鐵鋁窗的味道,混雜著傍晚陰溼的雨水氣味,還有窗外市場收攤後的菜腥,不知怎地,成瞭某個年歲裏不知名的味道,有時充塞瞭我的鼻腔,使我感到莫名地哀傷。讀到這段時,有時我會産生一種錯覺,覺得自己好像又迴到童年時代的那個姑母傢,而那個陰暗的二樓就是他筆下的那個客廳,好像我自己的姑母傢,就是他傢似地。當然這是多想瞭。
紘立的狗也很有點意思。在我眾多貓奴的友人之中,紘立是少數有隻狗的。這狗小小一隻,毛色鬃黑捲麯,名叫黑嚕嚕。記得養在上一本《壞狗命》齣版沒多久,眾人於是戲稱黑嚕嚕就是「壞狗命」那隻狗兒。《甜美與暴烈》裏寫年少拋妻棄子、晚年欲死前纔返傢的父親,在病榻前偷偷讀瞭《壞狗命》,開玩笑地問:「如果叫做《好狗命》,會不會賣得比較好一些?」我卻覺得那狗其實是他生命本質裏的某種質地。友善、單純,服務性格。同時還帶著某種隱性的偏執,人生沒有縫隙的處女座人生。《壞狗命》寫母係傢族與記憶,寫得密不通風。到瞭《甜美與暴烈》,從那城市邊界、離傢漸遠的漫遊開始,卻宛如反寫瞭一條返傢的道路,以漂離的形式,充滿哀矜的顔色。我想起自童年起即聽過的一個傳說,如果你想丟棄一隻狗,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為無論你棄牠於多麼遙遠的地方,牠都會沿路循著你的氣味找路迴來。盡管那是一條命運未蔔的、且是多麼多麼睏難的旅程。
祝福這本書,和它所將要展開的命運。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於颱北寓所
圖書試讀
我試著不那麼快抵達你。
雨不暴力落下瞭,卻像置身常溫裏的冰涼事物,慢慢地潮潤,慢慢地集會結社起來,而終於形成更大的存在:屋簷、水泥牆的邊界、直接的白綫和驚悚的紅綫規矩地劃分齣我們該守規矩的柏油路。當然還有再也承受不住分毫重量顯得如胃下垂的塑膠帆布。慣常穿拖鞋的我,沒有刻意踩齣水花,每根腳趾卻都冰涼。
鼕天的盆地,日照數少得很可憐,市政府栽植的小葉欖仁、檬果、垂榕、印度橡膠、阿勃勒、苦楝、鳳仙花與其他算妥距離的不知名樹種,全部翠綠得令人心生懷疑,彷彿打上一層油亮的蠟。城裏人,沿途走來我看見許多張眼睛貼地的臉,路走著走著總是隻剩一條,最輝煌的開始早就完結,現在他們隻要迴傢,努力地把自己塞進好小好小的句號裏,便是作廢每一日的必定儀式。
這樣的日子,我以為自己會發黴,不過還沒。
買來的黃金菇菌包,也還沒營生齣芽來。
明明是如此適閤腐壞、頹唐的季節,我們卻要像聖誕紅一樣堅持。
如果在從我傢前往火車站的途中有座尖頂教堂,那麼或許某天無意間聽聞的鍾聲,應該依舊悠揚,當當當,和沒心血管病癥卻隨時都可能暫停的心髒産生共鳴,接著,一如過去普通不過的普通日子,不知不覺地活下來瞭。
我曾經特地跑去駐足望看東海的鍾,好小,銹蝕的銅黃小鍾,就隱身在路思義教堂前方的樹叢。上下課鍾都是它撞擊齣來的。聖誕節全颱中閃光情侶、黯淡孤身的人,彼此隔著最厚重的鼕季衣物,此生不曾那麼和這個那個人接近的時刻,前方無數的頭顱,鞋底下荷重的雜草順著楦頭的方嚮傾倒,明明不信教,也來幫耶穌慶生,卻什麼也看不到。除瞭鍾聲。
我在離人群好遠的鳳凰樹下,鳳凰不在傢,樹枝相當的空曠長得像雞爪,我在這裏,一個人生悶氣,「憑甚麼我們逐漸往死亡靠近」,祂年年重生,值得把殘忍的時間裝飾上LED燈泡和管弦樂團,頓時和藹非常,就像,身披恩澤如在天堂?時間不該是這樣的。它比任何一個人提早誕生於世,讓我們看見最乾淨的猶如未使用的衛生紙,卻也陸續彰顯必然會沾染上去的鼻涕、唾沫,甚至大便;不過對於最新鮮的眼睛來說,它又恢復純粹的樣貌,提供廣大的風景、數不盡而你還沒踩過的道路。
用户评价
**評價五:** 《甜美與暴烈》這本書,剛拿到手時,我就被它的書名深深吸引瞭。這四個字,簡潔卻充滿瞭力量,仿佛能瞬間勾勒齣一段跌宕起伏的傳奇。閱讀過程,我感覺自己就像是在穿越一條蜿蜒的河流,時而順流而下,平靜安寜;時而又遇到險灘激流,驚心動魄。作者的文字,有著一種獨特的魔力,她能夠將最復雜的情感,用最簡潔、最有力的語言錶達齣來。我特彆喜歡她對人物內心掙紮的描繪,那些糾結、迷茫、無奈,都被她刻畫得入木三分,讓人感同身受。 書中“甜美”的部分,並不是那種矯揉造作的甜蜜,而是一種更加真實、更加動人的情感流露。它可能是一次不經意的溫柔,一個堅定的眼神,一句簡單卻充滿力量的鼓勵。這些細節,如同生活中的點點星光,雖然微弱,卻能照亮前行的道路。我感覺作者對生活有著一種深刻的體悟,她能夠發現隱藏在平凡日子裏的美好,並將其放大,讓我們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與希望。這種對“甜美”的細膩捕捉,讓我覺得十分溫暖和治愈。 而“暴烈”的元素,在書中並非是單純的暴力或血腥,而是更多地體現在人物所麵臨的睏境,以及他們為瞭生存和自我價值而爆發齣的強大力量。這種“暴烈”,可以是內心無法抑製的掙紮,也可以是對不公平命運的有力反擊。我常常在閱讀到這些情節時,感受到一種強烈的震撼,仿佛一股能量從紙頁間湧齣,激勵著我去麵對生活中的挑戰。作者在處理這種“暴烈”時,顯得非常有分寸,它不會讓人感到壓抑或絕望,反而會激發齣讀者內心的勇氣和韌性。 《甜美與暴烈》這本書的敘事方式,也讓我非常著迷。它並非一味地追求情節的跌宕起伏,而是張弛有度,引人入勝。在平靜的敘述中,暗流湧動,在激烈的衝突後,又迴歸到對人物內心的深層挖掘。這種敘事方式,讓我能夠更好地消化書中的情感和信息,也讓我更加期待故事接下來的發展。我喜歡這種能夠讓我思考的書,它不僅僅提供瞭消遣,更引發瞭我對人生、對情感的深刻思考。 我尤其要贊揚作者的細節描寫。她似乎擁有一雙能夠洞察萬物的眼睛,無論是人物的錶情,還是環境的氛圍,都描繪得栩栩如生。我仿佛能聽到微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也能感受到陽光灑在皮膚上的溫暖。這種細節上的極緻追求,讓整個故事更加真實可信,也讓我的閱讀體驗更加豐富。 總而言之,《甜美與暴烈》是一本值得反復品味的書。它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更像是一次心靈的對話。它讓我看到瞭生活的多麵性,也讓我明白瞭,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依然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光芒。這本書,讓我更加熱愛生活,也更加堅信自己的力量。
评分**評價六:** 《甜美與暴烈》這本書,在我閱讀過的眾多作品中,無疑是一顆璀璨的明珠。書名本身就充滿瞭強烈的反差感,讓人對內容充滿瞭好奇。一旦翻開,便會被作者精湛的文筆和深刻的人物塑造所吸引。她筆下的人物,絕非簡單的臉譜化形象,而是擁有復雜的情感和多麵的性格。我常常覺得,他們就活生生地存在於我身邊,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選擇與放棄,都讓我感同身受,時而心疼,時而扼腕,時而又為他們送上由衷的祝福。 書中對“甜美”的描繪,並非是那種流於錶麵的浪漫,而是深入到人物內心最柔軟的部分。可能是一種不動聲色的關懷,一種默默的支持,一種在睏境中閃爍的希望之光。這些“甜美”,如同寒鼕裏的一縷陽光,雖不熾熱,卻足以溫暖人心。作者似乎擁有著捕捉生活細微之處的敏銳觸覺,她能夠將那些轉瞬即逝的情感,用文字凝固下來,讓我們得以細細品味。我特彆欣賞她對這種“甜美”的刻畫,它不張揚,卻極具力量,總能在不經意間觸動心弦。 而“暴烈”的部分,在書中也得到瞭淋灕盡緻的展現。這種“暴烈”,並非是純粹的破壞,而是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強大的生命力,一種在逆境中迸發齣的不屈意誌。它可能是人物內心的呐喊,是對命運不公的抗爭,是對自我價值的堅持。我常常在閱讀這些情節時,感受到一種強烈的震撼,仿佛一股力量從紙頁間湧齣,激勵著我去麵對生活中的挑戰。作者在處理這種“暴烈”時,顯得非常有分寸,它不會讓人感到壓抑或絕望,反而會激發齣讀者內心的勇氣和韌性。 《甜美與暴烈》的敘事結構,也堪稱一絕。它並非一成不變的綫性敘事,而是巧妙地運用瞭多綫索、多視角的敘事手法,使得故事更加豐滿和立體。這種敘事方式,讓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人物的行為和動機,也讓我對整個故事有瞭更深入的認識。我喜歡這種能夠讓我思考的書,它不僅僅提供瞭消遣,更引發瞭我對人生、對情感的深刻思考。 我必須強調作者在環境描寫上的功力。她筆下的場景,不僅僅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更是人物內心世界的投射。無論是陰雨連綿的都市,還是寜靜祥和的鄉村,都仿佛擁有瞭生命,與故事中的人物一同呼吸,一同感受。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讓我完全忘記瞭現實的存在,投入到故事的海洋中。 總而言之,《甜美與暴烈》是一本能夠觸動靈魂的書。它讓我看到瞭人性的復雜與多麵,也讓我明白瞭,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依然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光芒。這本書,讓我更加熱愛生活,也更加堅信自己的力量。
评分**評價二:** 打開《甜美與暴烈》這本書,就好像走進瞭一個充滿戲劇張力的房間。故事的開端,那種略帶壓抑卻又充滿期待的氣氛,立刻就抓住瞭我的注意力。作者在人物塑造上,可以說是下瞭很大的功夫。每一個角色,無論是主角還是配角,都顯得那麼真實,那麼立體。我感覺他們不是被作者憑空創造齣來的,而是從生活的土壤裏生長齣來的。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糾結掙紮,都讓我感同身受。尤其是一位女性角色,她在看似柔弱的外錶下,隱藏著一股不容小覷的倔強和生命力,這種反差感,真的讓我非常著迷。 《甜美與暴烈》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它對情感的拿捏。書中並沒有刻意去渲染某種單一的情緒,而是將復雜的人性展現得淋灕盡緻。有時候,你會看到角色之間流淌著溫柔的關懷,那種情感就像陽光一樣溫暖人心;但下一秒,又可能因為某種突如其來的變故,角色不得不展露齣他們內心深處的掙紮和痛苦,甚至是一些近乎殘忍的反應。這種從極度的溫柔瞬間跌入激烈的衝突,或者從絕望的境地中爆發齣驚人的韌性,就是這本書名字的精髓所在。我不得不說,作者在處理這種情感的轉換時,處理得相當自然,沒有絲毫的突兀感,反而讓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人生的無常和復雜。 書中的情節推進,也很有層次感。故事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瞭各種意想不到的轉摺。有時候,你會以為已經猜到瞭接下來的走嚮,但作者總能在關鍵時刻拋齣一個炸彈,讓你大跌眼鏡。這種“猜不到”的感覺,正是吸引我繼續讀下去的動力。我喜歡這種能夠挑戰我思維的書,它不讓我覺得枯燥乏味,而是不斷地給我驚喜。而且,作者在設置這些情節衝突的時候,並不是為瞭製造而製造,而是緊密圍繞著人物的命運和內心的轉變展開,這使得整個故事更加具有說服力。 我尤其要贊揚作者的敘事技巧。她能夠將宏大的主題,用非常個人化、細膩的視角來呈現。讀這本書的時候,我仿佛置身於故事之中,和主角一起經曆著他們的痛苦與歡樂,一起感受著他們的成長與蛻變。那種代入感,真的是無與倫比。而且,書中的一些對話,雖然簡短,但卻信息量巨大,往往一句看似平淡的話,背後卻隱藏著深沉的情感和未說齣口的秘密。這種“言外之意”的處理方式,讓我覺得非常過癮,也讓我對書中人物的理解更加深刻。 總而言之,《甜美與暴烈》是一本能夠觸動人心靈深處的好書。它不僅僅講述瞭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對人性有瞭更深的理解。這本書讓我看到瞭,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內心深處依然可以燃燒著希望的火焰。它教會我,生活或許充滿瞭挑戰,但正是這些挑戰,讓我們變得更加堅強。
评分**評價七:** 《甜美與暴烈》這本書,對我而言,是一次難忘的閱讀體驗。從書名開始,就充滿瞭引人入勝的張力,讓人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作者的文字,如同涓涓細流,又如驚濤拍岸,能夠恰如其分地展現齣不同的情感狀態。我特彆欣賞她在塑造人物時,那種入木三分的洞察力。每一個角色,都仿佛經過瞭精心的雕琢,擁有著鮮活的生命,他們的言行舉止,他們的內心獨白,都顯得那麼真實,那麼有血有肉。 書中對“甜美”的描繪,並非是那種空泛的浪漫,而是滲透在生活的點滴之中,是一種能夠讓人感受到溫暖的力量。可能是一個善意的微笑,一句貼心的問候,一次默默的守護。這些“甜美”,如同黑暗中的燭火,雖然微弱,卻足以驅散陰霾,帶來希望。作者能夠捕捉到這些瞬間的美好,並將它們用文字放大,讓我們重新審視生活中的點滴幸福。我常常在閱讀這些段落時,感到一種久違的平靜和安寜。 然而,“暴烈”的部分,同樣在書中占據瞭重要地位,它並非單純的破壞,而是更多地體現在人物所麵臨的挑戰,以及他們為瞭突破睏境而爆發齣的強大生命力。這種“暴烈”,可以是內心的痛苦掙紮,也可以是對命運不公的有力反抗。我常常在閱讀這些情節時,感受到一種強烈的震撼,仿佛一股能量從紙頁間湧齣,激勵著我去麵對生活中的挑戰。作者在處理這種“暴烈”時,顯得非常有分寸,它不會讓人感到壓抑或絕望,反而會激發齣讀者內心的勇氣和韌性。 《甜美與暴烈》的敘事節奏,也設計得非常巧妙。它並非一味地追求情節的跌宕起伏,而是張弛有度,引人入勝。在平靜的敘述中,暗流湧動,在激烈的衝突後,又迴歸到對人物內心的深層挖掘。這種敘事方式,讓我能夠更好地消化書中的情感和信息,也讓我更加期待故事接下來的發展。我喜歡這種能夠讓我思考的書,它不僅僅提供瞭消遣,更引發瞭我對人生、對情感的深刻思考。 我不得不提作者在場景描寫上的功力。她筆下的場景,不僅僅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更是人物內心世界的投射。無論是陰雨連綿的都市,還是寜靜祥和的鄉村,都仿佛擁有瞭生命,與故事中的人物一同呼吸,一同感受。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讓我完全忘記瞭現實的存在,投入到故事的海洋中。 總而言之,《甜美與暴烈》是一本能夠觸動靈魂的書。它讓我看到瞭人性的復雜與多麵,也讓我明白瞭,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依然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光芒。這本書,讓我更加熱愛生活,也更加堅信自己的力量。
评分**評價三:** 初拿到《甜美與暴烈》這本厚實的書,我的目光就被封麵上那充滿藝術感的字體吸引住瞭。書名本身就透露齣一種矛盾而迷人的氣質,仿佛能窺見一段充滿糾葛的情感曆程。閱讀的過程,就像是潛入瞭一個深不見底的海洋,時而平靜如鏡,時而波濤洶湧。作者的文字功底毋庸置疑,她能夠精準地捕捉到人物最細微的情感波動,並將其轉化為令人動容的描寫。我尤其欣賞她對於“甜美”這一概念的理解,它並非流於膚淺的浪漫,而是滲透在生活的點滴細節中,比如一個不經意的眼神,一句溫暖的問候,一種淡淡的依賴。這些細微之處,卻能瞬間觸動內心最柔軟的部分。 然而,《甜美與暴烈》並非一本隻講述溫情脈脈故事的書。書中“暴烈”的元素,同樣被作者處理得恰到好處,極具衝擊力。這種“暴烈”,或許體現在人物之間激烈的衝突,或許體現在命運無情的打擊,又或許體現在角色內心無法抑製的憤怒與呐喊。但有趣的是,作者並沒有讓這種“暴烈”顯得粗俗或失控,而是將其升華為一種強大的生命力量,一種對不公命運的反抗,一種對自我價值的追尋。在閱讀過程中,我多次被這種強大的力量所震撼,它如同火山爆發一般,瞬間摧毀一切障礙,又如同涅槃重生,帶來新的希望。 書中對場景的描繪,也極具畫麵感。作者似乎擁有捕捉事物本質的超能力,無論是古樸小鎮的靜謐,還是現代都市的喧囂,亦或是某個充滿迴憶的角落,都在她筆下變得鮮活生動。我仿佛能聞到夏日午後淡淡的桂花香,也能聽到雨滴敲打窗欞的節奏。這種身臨其境的閱讀體驗,讓我完全沉浸在故事的世界裏,忘記瞭時間的流逝。我記得有一段對夜晚星空的描寫,寥寥數語,卻勾勒齣一幅壯麗而孤獨的畫捲,那種寂寥感,讓人心生憐惜,又讓人對生命産生無限的遐想。 《甜美與暴烈》在人物關係的刻畫上,也顯得尤為齣色。角色之間的互動,不僅僅是簡單的對話,更是情感的碰撞,思想的交鋒。我看到瞭親情中的羈絆與犧牲,友情中的支持與背叛,愛情中的癡纏與放手。這些復雜而真實的關係,讓我反思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交往,也讓我對人性的多麵性有瞭更深的認識。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人物劃分為好人或壞人,而是展現瞭每個人物的成長軌跡和行為動機,這使得我對書中所有角色都抱持著一種理解和同情,即使是那些行為不被我贊同的角色。 這本書給我帶來的,不僅僅是故事的樂趣,更是一種心靈的洗禮。它讓我明白,生活並非非黑即白,而是充滿瞭各種灰色地帶。而我們每個人,也都在這片灰色地帶中,努力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色彩。《甜美與暴烈》這本書,讓我重新審視瞭生活中的“甜美”與“暴烈”,讓我看到瞭它們並非對立,而是相互依存,共同構成瞭豐富而完整的人生。
评分**評價八:** 《甜美與暴烈》這本書,猶如一本厚重的史詩,又似一場細膩的內心獨白。初讀便被其書名所吸引,充滿瞭矛盾而迷人的色彩,讓人對接下來的故事充滿期待。作者的文字,帶著一種獨特的張力,既能描繪齣人情世故的細膩,又能展現齣生命中宏大的情感波瀾。我特彆欣賞她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那些隱匿在言語下的情緒,那些在沉默中積澱的情感,都被她挖掘得淋灕盡緻,讓我仿佛能夠窺探到角色的靈魂深處。 書中對“甜美”的描繪,不是流於錶麵的粉飾,而是源自內心深處的溫情。它可能是一次不經意的善良,一個充滿信任的眼神,一種難以言喻的默契。這些“甜美”,如同暗夜中的星光,雖然微弱,卻足以指引方嚮,帶來希望。作者似乎有一種神奇的能力,能夠發現生活中的細微之處,並將它們化為文字,觸動人心最柔軟的角落。我常常在閱讀這些段落時,感到一種久違的溫暖和慰藉。 而“暴烈”的部分,同樣在書中占據瞭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並非單純的破壞,而是更多地體現在人物所麵臨的考驗,以及他們為瞭生存和自我價值而爆發齣的強大生命力。這種“暴烈”,可以是內心深處的壓抑與呐喊,也可以是對命運不公的有力反擊。我常常在閱讀這些情節時,感受到一種強烈的震撼,仿佛一股力量從紙頁間湧齣,激勵著我去麵對生活中的挑戰。作者在處理這種“暴烈”時,顯得非常有分寸,它不會讓人感到壓抑或絕望,反而會激發齣讀者內心的勇氣和韌性。 《甜美與暴烈》的敘事結構,也讓我眼前一亮。它並非一成不變的綫性敘事,而是巧妙地運用瞭多綫索、多視角的敘事手法,使得故事更加豐滿和立體。這種敘事方式,讓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人物的行為和動機,也讓我對整個故事有瞭更深入的認識。我喜歡這種能夠讓我思考的書,它不僅僅提供瞭消遣,更引發瞭我對人生、對情感的深刻思考。 我必須強調作者在環境描寫上的功力。她筆下的場景,不僅僅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更是人物內心世界的投射。無論是陰雨連綿的都市,還是寜靜祥和的鄉村,都仿佛擁有瞭生命,與故事中的人物一同呼吸,一同感受。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讓我完全忘記瞭現實的存在,投入到故事的海洋中。 總而言之,《甜美與暴烈》是一本能夠觸動靈魂的書。它讓我看到瞭人性的復雜與多麵,也讓我明白瞭,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依然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光芒。這本書,讓我更加熱愛生活,也更加堅信自己的力量。
评分**評價十:** 《甜美與暴烈》這本書,正如其名,是一場關於人性極緻情感的探索。當我捧起這本書時,就被其書名所蘊含的張力深深吸引,預感這將是一段不平凡的閱讀旅程。作者的文字,有著一種獨特的魔力,它能如同絲綢般光滑細膩,又能如刀刃般鋒利果決。我尤其贊賞她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深入剖析,那些糾結、掙紮、喜悅、痛苦,都被她捕捉得入木三分,讓我仿佛置身其中,與角色一同經曆他們的悲歡離閤。 書中對“甜美”的描繪,並非是那種浮於錶麵的浪漫,而是滲透在生活的點滴之中,是一種能夠讓人感受到力量的溫暖。它可能是一次不經意的關懷,一個充滿信任的眼神,一種難以言喻的默契。這些“甜美”,如同暗夜中的星光,雖然微弱,卻足以指引方嚮,帶來希望。作者似乎擁有一種神奇的能力,能夠發現生活中的細微之處,並將它們化為文字,觸動人心最柔軟的角落。我常常在閱讀這些段落時,感到一種久違的寜靜和力量。 而“暴烈”的元素,同樣在書中占據瞭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並非單純的破壞,而是更多地體現在人物所麵臨的考驗,以及他們為瞭生存和自我價值而爆發齣的強大生命力。這種“暴烈”,可以是內心深處的壓抑與呐喊,也可以是對命運不公的有力反擊。我常常在閱讀這些情節時,感受到一種強烈的震撼,仿佛一股力量從紙頁間湧齣,激勵著我去麵對生活中的挑戰。作者在處理這種“暴烈”時,顯得非常有分寸,它不會讓人感到壓抑或絕望,反而會激發齣讀者內心的勇氣和韌性。 《甜美與暴烈》的敘事結構,也讓我眼前一亮。它並非一成不變的綫性敘事,而是巧妙地運用瞭多綫索、多視角的敘事手法,使得故事更加豐滿和立體。這種敘事方式,讓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人物的行為和動機,也讓我對整個故事有瞭更深入的認識。我喜歡這種能夠讓我思考的書,它不僅僅提供瞭消遣,更引發瞭我對人生、對情感的深刻思考。 我必須強調作者在環境描寫上的功力。她筆下的場景,不僅僅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更是人物內心世界的投射。無論是陰雨連綿的都市,還是寜靜祥和的鄉村,都仿佛擁有瞭生命,與故事中的人物一同呼吸,一同感受。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讓我完全忘記瞭現實的存在,投入到故事的海洋中。 總而言之,《甜美與暴烈》是一本能夠觸動靈魂的書。它讓我看到瞭人性的復雜與多麵,也讓我明白瞭,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依然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光芒。這本書,讓我更加熱愛生活,也更加堅信自己的力量。
评分**評價四:** 《甜美與暴烈》這本書,在我手中停留瞭許久,因為我知道,一旦翻開,就將是一段不能輕易中斷的旅程。書的開頭,就如同撥開瞭迷霧,展現齣一個充滿張力的世界。作者的文筆,有著一種獨特的韻味,它不是那種華麗到炫目的辭藻堆砌,而是如同陳年的老酒,越品越有滋味。我特彆欣賞作者對人物內心世界的細膩刻畫,那些隱藏在笑容背後的憂傷,那些在沉默中湧動的渴望,都被她捕捉得入木三分。讀這本書,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將自己代入其中,去感受角色的喜怒哀樂,去理解他們的選擇與掙紮。 書中“甜美”的部分,並非是那種不切實際的童話式浪漫,而是更加貼近生活的溫情。可能是一杯熱騰騰的咖啡,一個熟悉的擁抱,一個充滿鼓勵的眼神。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卻能在最疲憊的時候給予人力量。我感覺作者對生活有著深刻的洞察力,她能夠發現那些隱藏在平凡日子裏的美好,並將其放大,讓我們重新感受到生活的光彩。這種對於“甜美”的精準描繪,讓我覺得格外溫暖和安心。 而“暴烈”的元素,在書中並非是單純的暴力或衝突,而更多地體現在人物所麵對的睏境,以及他們為瞭突破睏境而爆發齣的強大生命力。這種“暴烈”,可以是內心深處無法壓抑的情感宣泄,也可以是對不公命運的有力反擊。我常常在閱讀到這些情節時,感受到一種強烈的震撼,仿佛一股力量從紙頁間湧齣,激勵著我去麵對生活中的挑戰。作者在處理這種“暴烈”的時候,顯得非常有分寸,它不會讓人感到壓抑或絕望,反而會激發齣讀者內心的勇氣和韌性。 《甜美與暴烈》這本書的敘事節奏,也設計得十分巧妙。它並非一味地追求情節的跌宕起伏,而是張弛有度,引人入勝。在平靜的敘述中,暗流湧動,在激烈的衝突後,又迴歸到對人物內心的深層挖掘。這種敘事方式,讓我能夠更好地消化書中的情感和信息,也讓我更加期待故事接下來的發展。我喜歡這種能夠讓我思考的書,它不僅僅提供瞭消遣,更引發瞭我對人生、對情感的深刻思考。 我特彆要提到書中對細節的描繪。作者似乎擁有一雙能夠洞察萬物的眼睛,無論是人物的錶情,還是環境的氛圍,都描繪得栩栩如生。我仿佛能聽到微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也能感受到陽光灑在皮膚上的溫暖。這種細節上的極緻追求,讓整個故事更加真實可信,也讓我的閱讀體驗更加豐富。 總而言之,《甜美與暴烈》是一本值得反復品味的書。它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更像是一次心靈的對話。它讓我看到瞭生活的多麵性,也讓我明白瞭,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依然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光芒。這本書,讓我更加熱愛生活,也更加堅信自己的力量。
评分**評價一:** 《甜美與暴烈》這本書,剛拿到手的時候,我其實是抱著一種既期待又有點忐忑的心情。書名本身就帶著一種強烈的對比感,讓人忍不住去猜想裏麵到底會是怎樣一個故事。我喜歡這種能夠挑動好奇心的名字,它像是打開一扇神秘之門,讓你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翻開第一頁,撲麵而來的文字就帶著一股濃鬱的情感,不是那種矯揉造作的甜膩,也不是那種粗暴無力的宣泄,而是一種很微妙的、讓人心頭泛起漣漪的觸感。作者在描繪人物內心的時候,非常細膩,我能感受到主角在麵對選擇時的糾結,在承受痛苦時的無助,以及在渴望幸福時的掙紮。這種真實感,讓我覺得我不是在閱讀一個虛構的故事,而是在陪伴一個活生生的人經曆他/她的人生。 我特彆欣賞作者在刻畫“甜美”與“暴烈”這兩個極端感受時,那種遊刃有餘的平衡。它不像很多作品那樣,為瞭突齣其中一個特質而犧牲另一個,導緻故事顯得失衡。相反,在《甜美與暴烈》裏,我看到瞭甜美中暗藏的鋒芒,也看到瞭暴烈中閃爍的人性光輝。這種復雜性,正是生活的本來麵目,不是嗎?我們每個人內心都可能同時存在著溫柔與堅韌,渴望安寜卻又不得不麵對風雨。書中的一些情節,特彆是主角在睏境中展現齣的韌性,真的給瞭我很大的力量。我曾經也經曆過一些低榖時期,那種感覺就像被黑暗吞噬,看不到希望。但是,讀著《甜美與暴烈》,我仿佛看到瞭黑暗中透齣的那一絲微光,聽到瞭來自內心深處不屈的呐喊。 書中對環境的描寫也相當到位,無論是繁華都市的喧囂,還是某個寜靜角落的孤寂,都通過作者的筆觸變得生動起來。這些場景不僅僅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更像是主角內心世界的映射。我甚至能聞到文字裏飄散齣來的淡淡的咖啡香,或者感受到海風拂過臉頰的微涼。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是我非常看重的。作者的遣詞造句,也堪稱一絕。有些句子雖然看似平淡,但卻蘊含著深意,讓人反復咀嚼,越品越有味道。我記得有一段話,形容一個人物的眼神,說是“像被時間浸泡過的古井,深邃而平靜,卻又暗流湧動”,當時我讀到的時候,真的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仿佛看到瞭那個人物的全部故事。 總的來說,《甜美與暴烈》不僅僅是一本小說,它更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內心深處的情感,也提醒我們,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我們也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力量。這本書讓我思考瞭很多關於愛、關於失去、關於成長的問題。它沒有給齣現成的答案,但它引導我去尋找,去感受。這是一本值得反復閱讀的書,每一次重讀,我相信都會有新的發現和感悟。
评分**評價九:** 《甜美與暴烈》這本書,宛如一場心靈的探險,充滿瞭未知與驚喜。從書名開始,就預示著一場情感的風暴即將襲來。作者的文字,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韻味,時而如春風拂麵,輕柔細膩;時而又如驚濤駭浪,震撼人心。我最欣賞的是她對人物情感的精準捕捉,那些隱藏在心底的秘密,那些在絕望中萌生的希望,都被她描繪得生動而真實。閱讀這本書,我常常會不自覺地流下眼淚,或因感動,或因心疼,或因釋然。 書中“甜美”的部分,並非是那種廉價的煽情,而是一種源於生命本身的溫暖。它可能是一次不經意的善舉,一個充滿力量的眼神,一種堅不可摧的信任。這些“甜美”,如同黑夜中的燈塔,指引著迷失的方嚮,給予前行的勇氣。作者擅長在看似平淡的生活中,發掘齣那些閃耀著人性光輝的瞬間,並用文字將其放大,讓我們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與希望。我常常在閱讀這些段落時,感到一種久違的寜靜和力量。 而“暴烈”的元素,同樣在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並非單純的暴力,而是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強大的生命力,一種在睏境中迸發齣的不屈意誌。它可能是人物內心無法抑製的呐喊,是對命運不公的抗爭,是對自我價值的堅持。我常常在閱讀這些情節時,感受到一種強烈的震撼,仿佛一股力量從紙頁間湧齣,激勵著我去麵對生活中的挑戰。作者在處理這種“暴烈”時,顯得非常有分寸,它不會讓人感到壓抑或絕望,反而會激發齣讀者內心的勇氣和韌性。 《甜美與暴烈》的敘事結構,也設計得十分巧妙。它並非一成不變的綫性敘事,而是巧妙地運用瞭多綫索、多視角的敘事手法,使得故事更加豐滿和立體。這種敘事方式,讓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人物的行為和動機,也讓我對整個故事有瞭更深入的認識。我喜歡這種能夠讓我思考的書,它不僅僅提供瞭消遣,更引發瞭我對人生、對情感的深刻思考。 我必須強調作者在細節描寫上的功力。她筆下的場景,不僅僅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更是人物內心世界的投射。無論是陰雨連綿的都市,還是寜靜祥和的鄉村,都仿佛擁有瞭生命,與故事中的人物一同呼吸,一同感受。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讓我完全忘記瞭現實的存在,投入到故事的海洋中。 總而言之,《甜美與暴烈》是一本能夠觸動靈魂的書。它讓我看到瞭人性的復雜與多麵,也讓我明白瞭,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依然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光芒。這本書,讓我更加熱愛生活,也更加堅信自己的力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