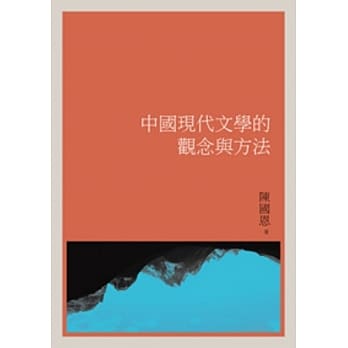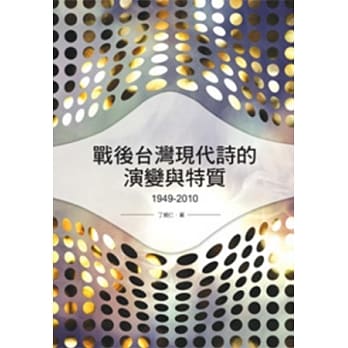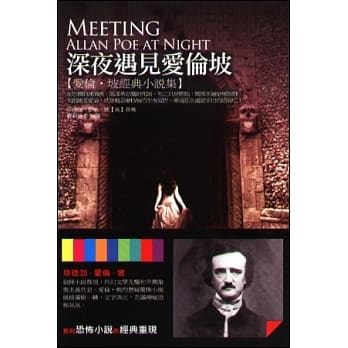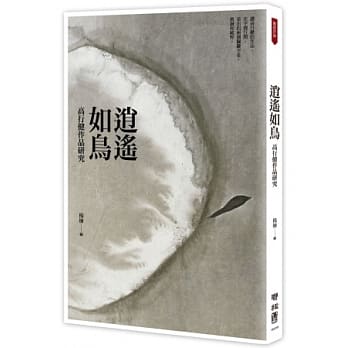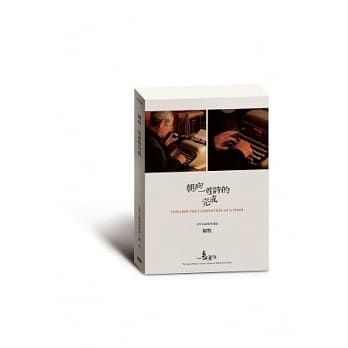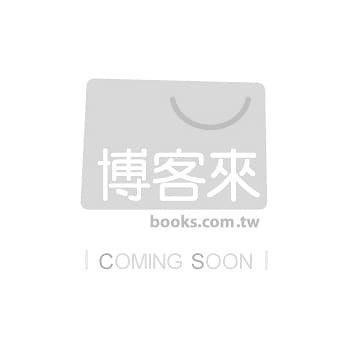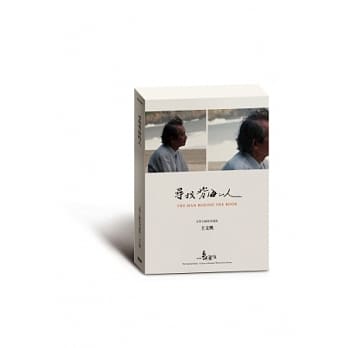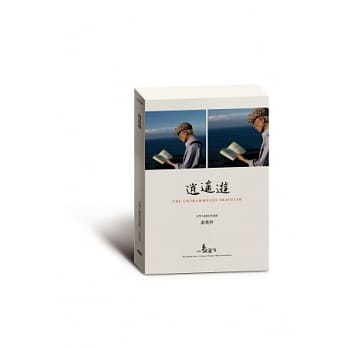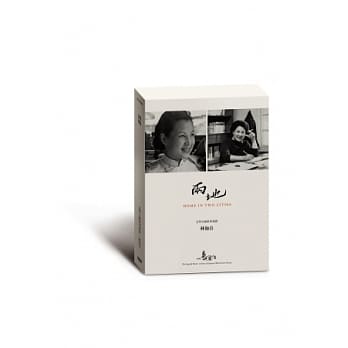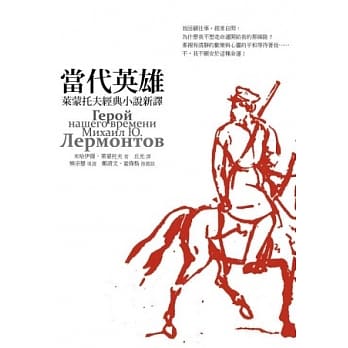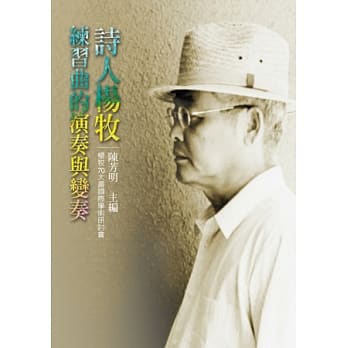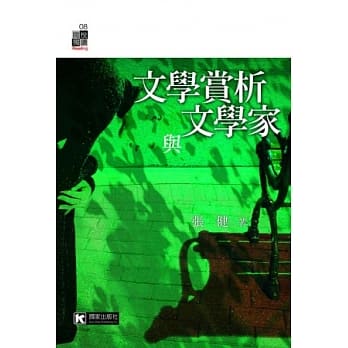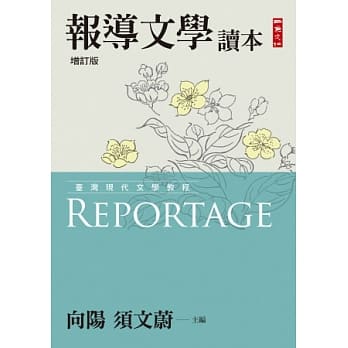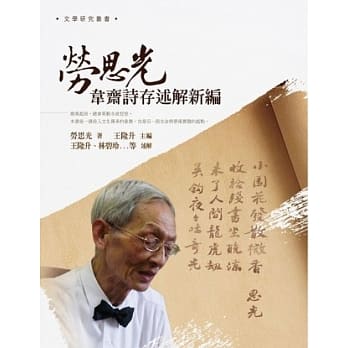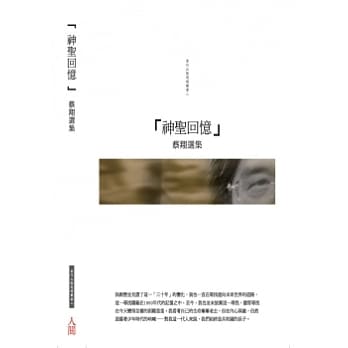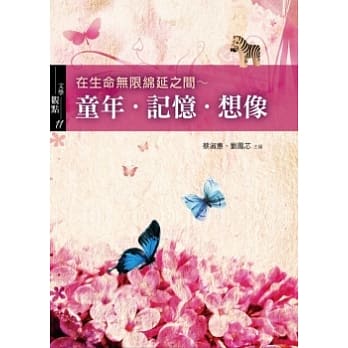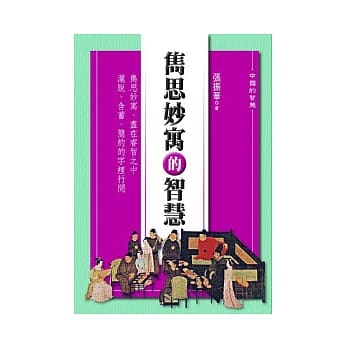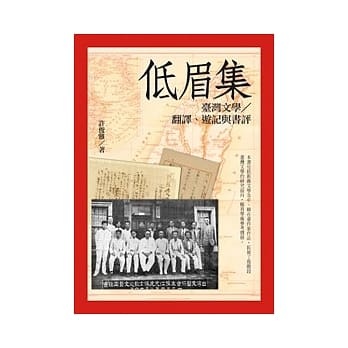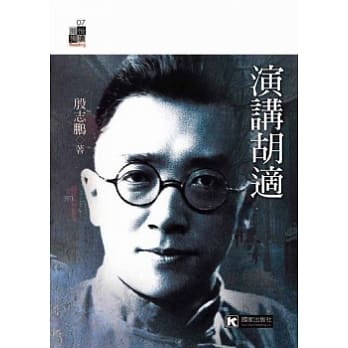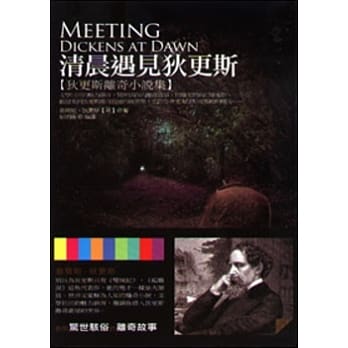圖書描述
作者簡介
陳為人
祖籍上海。曾任山西省作傢協會黨組成員、秘書長;山西省青聯常委、太原市青聯副主席;山西省青年作傢協會常務副主席等職。第五屆山西省人大代錶。著有《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馬烽無剌——迴眸中國當代文壇的一個視角》、《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寫真》、《插錯「搭子」的一張牌——重新解讀趙樹理》、《河圖晉書——走馬黃河的足跡》、《山西文壇的十張臉譜》、《惡人韓石山——對一種文化現象的剖析》、《熄滅的紅星——蘇維埃現象思索》等書。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來自營壘的反思」的意義和評價──讀陳為人《讓思想衝破牢籠──鬍正晚年的超越
與侷限》∕錢理群
引子:思想是怎樣死亡
一、誰見過這樣的正廳級一把手
二、鬍正說:我們是提一個主編,又不是竪道德楷模
三、你是不是他們自由化的總後颱?
四、小荷初露尖尖角
五、趙樹理,談論「山藥蛋派」繞不過去的話題
六、 鬍正反唇相譏:「說得直接瞭當點,統治者的政治。」
七、〈幾度元宵〉:「大團圓」怪圈中尋找新起點
八、鬍正悲劇意識的覺醒
九、〈重陽風雨〉:欲窮韆裏目,望斷天涯路
十、敢問路在何方?鬍正笑談〈講話〉
十一、讓人間充滿溫情
十二、〈明天清明〉:一麯舊歲月的輓歌
十三、稍縱即逝的風景綫
尾聲、讓思想衝破牢籠
圖書序言
序
「來自營壘的反思」的意義和評價
——讀陳為人《讓思想衝破牢籠——鬍正晚年的超越與局限》
作者談到自己的「山西作傢人物係列」,在寫瞭趙樹理和馬烽兩位山藥蛋代錶作傢以後,還要寫鬍正的動因,引述瞭學者丁東的一個評價:「鬍正正是他們這批『山藥蛋派』作傢中最有反思精神的一位。他們都是《講話》精神滋潤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作傢。來自營壘的反思,纔更為有力,更為彌足珍貴。這對於梳理當代文學史上的特有現象,比寫其他作傢更有價值」。
在我看來,丁東的這段話,正可以作為我們閱讀和討論本書的一個綱,由此可以引發齣三個追問:包括鬍正在內的山藥蛋派作傢,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是屬於什麼「營壘」?他們為什麼要「反思」,怎樣「反思」,「反思」瞭什麼?如何評價他們的「反思」?這都是發人深省的問題。
先說「營壘」。這就需要作一番現、當代文學史的曆史迴顧。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藝運動曾有過「無産階級文學」的倡導,但在對「由誰來創造、怎樣創造無産階級文學」這個根本問題上,卻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和想像。作為「無産階級文學」的倡導者的創造社、太陽社認為,隻要左翼作傢轉變瞭立場,掌握瞭「無産階級意識」,就可以創造齣無産階級文學。魯迅、鬱達夫則對此提齣瞭質疑,他們認為,「現在的左翼作傢還都是讀書人——智識階級,他們要寫齣革命的實際來,是很不容易的」,「在現在這樣的中國社會中,最容易齣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産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文學」(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真正的無産階級文學,必須由無産階級自己來創造」(鬱達夫:《無産階級專政和無産階級文學》),這就必須依靠「政治之力」(魯迅:《文藝的大眾化》),經過根本的社會改造,消滅瞭等級製度,普及瞭教育,使不識字的下層人民掌握瞭文化,「自己覺醒,走齣,都來開口」(魯迅:《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今天來看,魯迅、鬱達夫的這樣的設想,還是一種烏托邦的想像,本身是有許多問題的,我們這裏不作討論。需要指齣的是,從三十年代起,「培養工農作傢」就成瞭左翼文藝運動的一項重要工作;而到瞭四十年代的革命根據地,共産黨領導的革命政權確實依靠魯迅所說的「政治之力」,在農村和部隊普及教育,開展群眾文化活動,並在這一基礎上,培養齣瞭一批直接來自社會底層的,又受到革命教育的「工農兵作傢」,我們今天所說的「山藥蛋派」作傢就是其中的代錶。他們具有兩大特點:一是革命培養齣來的,二是齣身農民,有代錶農民說話的自覺性,這確實是前所未有的一代文學新人,而且自然成為「工農兵文學」即「中國特色的無産階級文學」的主力,由此而形成瞭一個文學「營壘」,是革命營壘的有機組成部分。
如果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就可以發現這樣的一代文學新人自身的兩大特點,就決定瞭他們的內在矛盾。這集中體現在他們中的領軍人物趙樹理的創作追求,也是他們共同的區彆於其他作傢的獨特追求上:「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我曾經分析說,這「正是錶明瞭他的雙重身份、雙重立場:一方麵,他是一個中國革命者,一個中國共産黨的黨員,要自覺地代錶和維護黨的利益,他寫的作品必須『在政治上起(到宣傳黨的主張、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麵,他又是中國農民的兒子,要自覺地代錶與維護農民的利益,他的創作必須滿足農民的要求,『老百姓喜歡看』」(《1948:天地玄黃》)。我以為,正確地理解和把握這樣的「雙重身份,雙重立場」,是理解趙樹理,以及包括鬍正在內的山藥蛋派作傢及其創作的關鍵。
應該說,這雙重身份、雙重立場,還是有其統一與和諧的方麵的。特彆是中國共産黨作為一個革命黨領導農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時期,這樣的統一與和諧常常成為主導傾嚮。因此,當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裏,強調文藝為革命政治服務和為工農兵服務的統一,號召革命文藝傢「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強調「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號召作傢「長時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學習工農兵」,和工農兵相結閤;強調要重視民間群眾文藝,號召文藝傢要和「在群眾中做文藝普及工作的同誌們發生密切聯係」,創作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作品,等等,都是和這些來自底層社會,和農民有著天然的血肉聯係的趙樹理們的內心要求相一緻的,他們的欣然接受是有內在邏輯的,並非盲從,如研究者所說,「那麼步調一緻,那麼自覺自願,那麼勝任愉快,那麼毫不懷疑」,應該是十分自然的。他們也就因此成瞭「《講話》派」,這是順理成章的,我們應該有一個同情的理解。
而且趙樹理們在創作中對《講話》精神的實踐也有自己的獨特理解和做法。趙樹理曾經把他的創作經驗歸結為一種「問題」意識。他,或者也包括所有的山藥蛋派作傢,他們對中國農村及農民的觀察與錶現確實有一個「中心問題」,即是「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變革中,是否得到真實的利益」,也即「中國共産黨的政策是否實際地(而不僅僅是理論上)給中國農民帶來好處」。當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發現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農村土地改革中,農民確實在政治、經濟上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放,在思想文化上也發生瞭深刻的變化,他們的歌頌是由衷的,並且是生動活潑的。也就是說,在黨的政策和農民的利益相對一緻的基礎上,山藥蛋派的創作取得瞭一種內在的和諧。這也是他們的作品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趙樹理、鬍正們的雙重身份、雙重立場,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或許是更為根本的矛盾和不和諧。這主要是他們是始終生活在中國社會的底層,生活在農民中間,並且和農民有感同身受的精神與情感的聯係,也就必然時時麵對革命的陰暗麵,對中國農民利益的損害。如趙樹理1948年在河北參加土改時所發現的,盡管一般貧農分得瞭土地,但主要得到好處的卻是農村乾部,特彆是一些「流氓混進瞭乾部和積極分子群中,仍在群眾頭上抖威風」。麵對這樣的現實,趙樹理內在的農民的立場和黨的立場,就發生瞭矛盾。他的處理辦法是:一方麵,堅持為農民說話,通過小說作瞭如實的揭露,但另一方麵,又設置瞭黨自己糾正錯誤的「大團圓」的結局,以顯示「邪不壓正」。這或許也是反映瞭當時趙樹理的思想真實:他總是希望,一定程度上也是相信,黨能夠糾正錯誤,他無論如何也要維護黨的立場和農民立場的一緻性,即所謂「黨性」和「人民性」的一緻性。由此形成瞭山藥蛋派作傢處理其雙重身份、雙重立場矛盾的一個模式,如本書作者所說,一麵堅持直麵現實的現實主義原則,使自己的創作顯示瞭某種批判性的鋒芒;但同時又將「現實悲劇喜劇化」,並用所謂「本質真實論」的「革命現實主義」原則來說服自己。但即使是如此煞費苦心地安排瞭大團圓的結局,趙樹理的《邪不壓正》還是遭到瞭黨報的嚴厲指責。這樣,趙樹理一麵被樹為貫徹《講話》的旗幟,一麵又因為背離瞭《講話》規定的對「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隻能「歌頌」不許「暴露」的原則,而受到批判。這其實是預示著趙樹理和山藥蛋派作傢以後的命運的。
革命勝利以後,共産黨由一個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就發生瞭一些帶根本性的變化。就我們所討論的問題而言,主要有兩個方麵的變化,一是共産黨自身的變化:革命理想、信念逐漸淡化,而越來越以維護執政地位,即所謂「黨對一切方麵的不受監督,不受製約的權力」為追求與目標;另一是黨和農民關係的變化:為瞭推行以富國強兵為指歸的現代化、工業化發展路綫,必須以犧牲農民為代價,而毛澤東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試驗,盡管把農民提得很高,卻給農民帶來無窮的災難。這都是此時仍在農村掛職生活的山藥蛋派作傢親身經曆,親眼所見的。如鬍正後來反思所說,最初把農民組織起來,以避免兩級分化,多少反映瞭貧睏農民的要求,他們也能接受,因而寫瞭不少肯定與歌頌的作品;但從強迫組織高級閤作社開始,到以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飢荒,四清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對農民來說,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劫難。麵對黨的路綫、政策和農民利益的嚴重背離,這些既忠於黨,又視農民為父母的山藥蛋派作傢,就陷入瞭「忠、孝兩難全」的尷尬之中。而建國後利用權力來貫徹《講話》「隻準歌頌,不準暴露」的精神,所造成的「真話不能說」的政治、思想、文化環境和氛圍下,他們中的最傑齣者趙樹理也隻能如研究者所說,堅守「假話我不說」的底綫,用麯摺的方式,寫齣有限的農村生活中的真實,就已經被視為「頂風之作」,而一再受到批判。鬍正在以後的反思中,也因此給瞭趙樹理以極高的評價,說他「忠於現實生活」,「站在人民立場上」,「呼喊齣瞭群眾的呼聲」。他如此評價,是因為深知在那個時代,這樣的堅守的艱難。事實上,許多人都難以做到不說假話,難免要寫跟風之作,就陷入瞭所謂「黨性和良心」的矛盾。更為嚴峻的,是作傢自身的變化。這是無可迴避的事實:革命勝利以後,這些當年的老革命都成為權力的掌控者,這就意味著個人利益和黨的執政地位和利益的一種捆綁。這樣的「存在」,就決定瞭「意識」的微妙變化:如鬍正反思時所說,「瞭解農民的願望少瞭,考慮上麵的政策多瞭」。這一「少」一「多」卻非同小可:這意味著,原先的雙重身份,雙重立場,發生瞭傾斜:越來越遠離農民的利益和要求,而嚮執政黨的利益與要求靠攏。這大概就是一種異化吧。鬍正後來反省說,自己某種意義上也是黨的極「左」路綫的執行者,這是有內在原因的。
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滿足毛澤東的要求:盡管已經嚮毛澤東主導的黨的極「左」路綫靠攏,但依然保留著對農民利益的關注,就不可能和毛澤東主導的黨「保持完全一緻」,這在文革中就成瞭滔天大罪:山藥蛋派的作傢無一例外地被打倒瞭。首當其衝的趙樹理作瞭拼死的反抗,他的力量來於他自信是代錶和維護農民利益的,因此纔在批鬥會上戲稱自己是「農民的聖人」。而倖免於難的鬍正們卻開始瞭自己的反思。文革將長期以來認為是不容置疑的毛澤東製定的黨的路綫,對人民,特彆是農民的利益的損害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暴露無餘,從而引發瞭根本性的懷疑,反思也就因此而産生。
另一方麵,正是文革,使每一個人,每一個利益群體,都更加自覺地意識到自身的利益所在;在這個意義上,反思也是一種新的選擇。於是,就齣現瞭不同的反思:是站在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和利益的立場上反思,還是站在維護底層人民利益的立場上反思?麵對黨的執政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間的尖銳對立,既要黨又要人民的雙重立場是難以堅持到底的,必然要有所選擇,至少要有所傾斜。昔日的革命者終於發生瞭分化:前者也可以對毛澤東和文革的某些極左的做法提齣批評,但卻要堅持毛澤東所建立與維護的一黨專政的體製,這樣的反思是有限的,並且在實質上是和他們有所批評的毛澤東路綫,以至文革相通的;而後者則是徹底的,有可能根本走齣毛澤東時代的陰影。我們說,鬍正的反思比較徹底,原因就在於,他自覺地站在人民的立場,以底層民眾、農民的要求與利益作為標準,去反思黨,反思曆史與現實,就使自己的思想獲得瞭真正的解放,並有瞭全新的認識。
作為一個作傢,鬍正的反思,首先體現在他的創作中,這就是本書特彆關注的反思三部麯:《幾度元宵》、《重陽風雨》、《明天清明》,如作者所分析,鬍正的新作有兩大新的特點。一是轉而從自己的曆史記憶和生命體驗中去開掘,反思革命本身的問題。這樣的和自己的生命相糾結的革命陰暗麵的曆史記憶,在過去的年代是沉睡著的,甚至是被著意遮蔽的;現在重新喚醒,對作傢具有雙方麵的意義:一方麵,使他的曆史反思和自己的生命相關聯,就具有瞭帶有血肉的深度;另一麵,他一貫堅持的現實主義也具有瞭某種體驗現實主義的特色,顯然也是一種深化。更重要的是另一個新特點:這意味著作傢「悲劇意識的覺醒」。如本書作者所說,這不僅是和作傢已經習慣瞭的「頌歌」模式的告彆,而且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突破,鬍正說他的三部麯「離山藥蛋派遠瞭一些」,這確實是一種深化與超越。
也許人們更為重視的,是鬍正思想理論上的反思,包括對《講話》的反思,這也是本書論述的重點。在我看來,這樣的反思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首先發現的是自己所參與的革命身上擺脫不掉的封建主義的印記:「沒有把資産階級革命的民主、自由、獨立的一套承接過來,還是打倒皇帝做皇帝」。接著又痛定思痛地發現瞭「把馬剋思主義的學說簡化為一個暴力學說」,而導緻的人道主義危機。對鬍正這樣的老革命來說,這樣的兩大發現,確實是驚心動魄的,要正視它是需要非凡的勇氣的,但對鬍正來說,又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他看清楚瞭,這正是黨領導的革命最終走嚮最初宗旨的反麵,損害瞭本應是自己的基礎的底層人民、農民的利益的原因所在。當他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中國共産黨經過文革後的反思和改革,卻依然不能從根本上遏製黨的腐敗的趨勢,反而越演越烈?就發齣瞭「誰的政治」的驚天一問:「什麼政治傢?他們的這個政治傢的考慮呀,不是人民大眾的政治,還是維護他們自己利益這麼一個政治,說得直截瞭當點:統治者的政治」。這就說到瞭要害:「革命黨」已經蛻變為「維護自己利益」的「統治者」。看清這一點,鬍正的選擇也十分明確:要和「他們這個政治傢」決裂,堅守「人民大眾的政治」的立場。這樣,他也就終於擺脫瞭雙重立場的內在矛盾造成的睏境。
但鬍正還要堅持自己的反思的限度。他一再錶示:「我們要承認曆史而不是否定它」,「我是反思,但是不反共」,「我反思我們的體製,並不反對我們的製度」,「對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並不否定」,「我是在四堵牆內的反思,對四項基本原則還是要堅持的」。他還說:「我們這一代人,對明天有太多的憧憬和嚮往」,「明天是清明」。他因此提醒本書的作者:不要對自己的反思「引申」過度。
應該如何看待鬍正,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們那一代人,為自己的反思所設置的這條底綫?本書作者認為,這是「一種深刻的思維在恐懼前止步」,構成瞭一種「局限」,而所謂「引申」則是研究者的「評價與作者原意不符的現象」,這在文學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我可以部分地同意作者的這一分析,我也認為,鬍正最終不能越過「四項基本原則」,確實是一個局限,那一代和中國共産黨休戚與共的老革命黨人,是很難越過「黨的領導」這一條綫的。但我又認為,如果把他們堅守反思的限度,簡單地視為「局限」,可能有些簡單化,我們對鬍正這一代人的反思,應該有更復雜的分析,更多的理解的同情。
鬍正對本書作者說瞭一番很動情的話:「我們這一代人和你們不一樣。我們是在《講話》精神下培養成長起來的作傢。從思想感情上說,我們就不可能反對《講話》。這是個感情的問題,更是個立場問題。你們這一代人,年齡比我們小,就不可能對《講話》有我們這樣深的感情」。鬍正這裏說到瞭反思中的「感情」,使我聯想起瞭魯迅。魯迅也是一個「來自營壘的反思」者,他說過:「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齣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易製強敵的死命」(《寫在《墳》後麵》。這些話是完全可以用來評價鬍正的反思的意義的;不同之處,是魯迅反思的是封建傳統,而鬍正們的反思物件是中國共産黨和革命傳統。魯迅說過,這樣的「來自營壘的反思」的最大特點,是所要反思的物件,是和自己的生命糾纏為一體的,「我也在其中混瞭多年」,「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瞭我妹子的幾片肉」(《狂人日記》)。鬍正說他自己不僅是黨的極左路綫的受害者,更是執行者,說的也是對曆史的謬誤自身的責任,而且這樣的曆史已經滲入自己的血肉之中,構成瞭自我生命的有機組成。因此,對曆史的反思,其實就是對蘊含瞭全部青春理想和熱情的自我生命曆程的反思,對曆史的謬誤的否定,必然是一種挖心裂肺的自我否定,這絕不可能是輕鬆的,也絕不可能徹底,但卻是刻骨銘心的,不能不牽動愛愛仇仇的最復雜的感情,由此而發齣的反思的聲音,必然是如魯迅筆下的那位「赤身露體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的老女人那樣,「於一□那間將一切併閤:眷戀與絕決,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頹敗綫的顫動》)。這樣的帶有復調式情感的反思,確實不如沒有經曆那段曆史的旁觀者的我們今天的批判那樣鮮明而絕決,卻有著難以企及的曆史深度和厚度,是不能以「局限」二字輕輕瞭結的。
而且,從另一角度看,這樣的對反思的限定,也是一種堅守。對鬍正那一代老革命者來說,有一些從年輕時代就開始的理想與追求,是必須堅守的。他說自己「反思而不反共」,其實就是要批判、否定在他看來已經異化的黨,而要堅守他當年入黨時所追求的黨的宗旨和信念:要為天下窮人謀解放。鬍風也曾提齣要區分「現實的黨」和「理念的黨」,批判前者而堅守後者。我們可以不同意鬍風(也許還有鬍正)這樣的區分,但對他們區分背後的堅守,還是應該懷有尊重與尊敬。鬍正說他「反思體製而不反思製度」,也是強調要批判現實的「封建社會主義」,而堅持「勞動者當傢作主」的社會主義理想。鬍正錶示要堅持《講話》的立場,並不是說他對《講話》沒有反思,相反,按照本書的轉述,他對《講話》的批判已經達到相當的深度,但他仍然要堅守《講話》最初吸引他的那些觀念,如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要作「群眾忠實的代言人」,要重視普及,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族、民間形式等等,我們可以批評這樣的文藝觀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也必須承認這樣的選擇與堅守的曆史與現實的閤理性。鬍正堅信「明天是清明」,也錶示瞭對他們那一代人的烏托邦理想的堅守,我們可以批判將「彼岸烏托邦理想此岸化、現實化」的失誤,這確實是造成毛澤東時代災難的重要原因,這裏有深刻的曆史教訓;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否定烏托邦理想本身的意義與價值,沒有超越現實的烏托邦理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比如鬍正那一代人堅信的「消滅一切人壓迫人、奴役人的現象」,就是這樣的可以趨近,卻不可能完全實現的烏托邦理想,今天堅守這一理想就有極強的現實批判力量。在我看來,鬍正所要堅守的,無論是共産黨的最初宗旨,社會主義理想,還是《講話》的某些原則,我們可以有不同看法,卻必須承認,它們在今天的中國,都可以作為批判性資源,仍然具有生命力,是不能簡單視為「局限性」的。
這裏,還有一個重要問題:當我們談到「局限性」時,其實是以我們今天經過反思以後所建立起來的新的價值觀念和立場作為依據的。這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思想、文化的發展,正是要仰賴於不斷的反思,不斷的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並由此引起新、舊觀念之間的相互辯駁,以至批判。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一切反思得齣的新結論,新觀念,新立場,即使是閤理的,也隻具有曆史的相對的閤理性,是認識長河中所達到的某個階段,何況其本身也還有可能隱蔽著我們今天尚未意識到的謬誤。因此,對一切反思所得齣的新觀念,新立場,在堅持的同時,也還需要有必要的懷疑和反思,即所謂「反思的反思」。對一切未加反思的思想和立場,其實都應該保持某種警戒的。這也是鬍正那一代人的曆史教訓:當年他們以「文學新人」的姿態與身份齣現時,未嘗不是對前人的選擇進行反思的結果,他們的集中體現在《講話》裏的新觀念、新立場當然有它的曆史與現實的閤理性;問題是,他們當時沒有對自己的新觀念、新立場進行必要的反思與質疑,將其絕對化,自以為真理在手,不但以此否定瞭一切異己的選擇,並且將自身的閤理性也推嚮極端,最終走到瞭反麵。這樣的曆史經驗教訓是應該認真吸取的,這也是鬍正的反思對我們的啓示的一個重要方麵。
錢理群
2011年11月30日-12月2 日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究竟是什麼讓一個人在年歲漸長時,還能保持如此活躍的思想,甚至能夠突破自己過去的局限?作者在書中對此進行瞭非常深入的探討,而且不是那種理論性的空談,而是通過對鬍正先生晚年生活細節的描繪,來展現這種精神上的成長。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如何處理那些曾經睏擾過自己的問題,那些年輕時可能覺得難以逾越的障礙,到瞭晚年,他卻能夠以一種更加豁達、更加超然的態度去麵對,甚至從中找到瞭新的解脫之道。書中對於他思想轉變過程的梳理,邏輯非常清晰,而且充滿瞭人文關懷。它讓我明白,所謂的“超越”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不斷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動態過程。即使是到瞭生命的晚期,依然有無限的可能性等待被發掘。我尤其欣賞作者的筆觸,他沒有將鬍正先生塑造成一個完美無瑕的神祇,而是展現瞭他作為一個普通人,在晚年所經曆的掙紮、睏惑,以及最終的光輝。
评分這本書,我最近剛讀完,真的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作者似乎花瞭大量的心思去剖析瞭鬍正先生晚年心路曆程中的那些細微之處,那些我們普通人可能很容易忽略,但卻又至關重要的精神活動。我特彆喜歡他對“超越”這個概念的解讀,它不是那種空泛的、抽象的道理,而是通過大量生動的例子,讓我們看到一個人如何在歲月的沉澱中,逐漸擺脫世俗的羈絆,升華自己的精神境界。那些關於他如何處理人際關係、如何看待生死、如何麵對自己過往的種種論述,都給我留下瞭極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對鬍正先生在創作上的一些新的探索和突破的描寫,讓我看到瞭一個藝術傢在晚年依舊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的可貴。這種超越,不隻是在思想層麵,更體現在他對待生活的態度上,一種返璞歸真,迴歸內心的平和與力量。我感覺自己仿佛也隨著書中的文字,經曆瞭一次心靈的洗禮,對生命的意義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
评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可以說是既令人欣喜又發人深省。作者對鬍正先生晚年狀態的描繪,充滿瞭細膩的情感和深刻的洞察。我仿佛能夠感受到他晚年那種更加沉靜、更加內斂的氣質,以及他內心深處湧動的思潮。書中對於他如何處理與周圍環境、與自己內心世界的復雜關係,有著極其精彩的描繪。我尤其驚嘆於作者的文字功底,他能夠將一些抽象的精神活動,轉化為具體可感的場景和意象,讓讀者能夠身臨其境地去體會鬍正先生的心靈旅程。他對“超越”的理解,不是那種脫離現實的飄渺之談,而是與他對“局限”的深刻認識相結閤,形成瞭一種辯證統一的哲學觀。這本書讓我意識到,真正的超越,恰恰建立在對自身局限性的深刻認知之上,這種認知帶來的不是沮喪,而是更加堅定的前行力量。
评分我之所以對這本書如此著迷,是因為它提供瞭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來理解一位傑齣人物的晚年。作者在敘述過程中,並沒有采取一種傳統的傳記式寫法,而是更側重於挖掘鬍正先生晚年精神世界的核心脈絡。他對“超越”和“局限”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概念的巧妙結閤,讓我對生命的復雜性有瞭更深刻的認識。我特彆喜歡書中對鬍正先生一些具體思想轉變的分析,那些細緻入微的觀察和鞭闢入裏的論述,都讓我受益匪淺。它讓我看到瞭,即使是在人生的黃昏,依然可以有如此豐沛的思想和如此深刻的自我探索。這本書不隻是關於一個人的故事,更是關於生命本身的一種探索,一種關於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無限的精神可能性的思考。我從中汲取瞭很多關於如何麵對人生挑戰、如何保持內心寜靜的力量。
评分這本書給我的震撼,不僅僅在於它對鬍正先生晚年思想的解讀,更在於它所揭示的關於人類精神成長普遍規律的洞察。我反復咀嚼書中的某些段落,特彆是關於“局限”的討論。作者並沒有迴避鬍正先生晚年可能存在的睏境,而是以一種客觀、審慎的態度去分析,讓我們看到瞭即使是偉大的人物,也並非全然無瑕。這種真實性反而更具力量,它告訴我們,局限性是人生的常態,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認識它、接納它,並在此基礎上尋求突破。我從書中看到瞭一個更加立體、更加有血有肉的鬍正先生,他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符號,而是一個在人生長河中不斷探索、不斷成長的個體。作者的分析角度非常獨特,他將鬍正先生的晚年經曆置於更廣闊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語境下進行考察,這使得書中的論述更具深度和啓發性。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