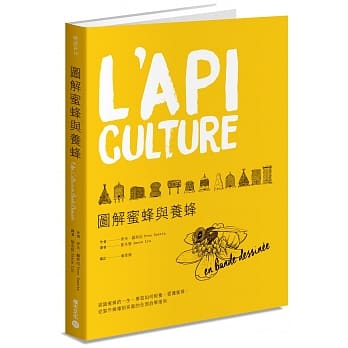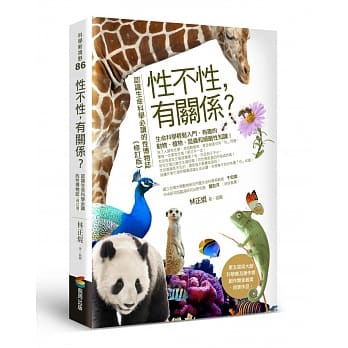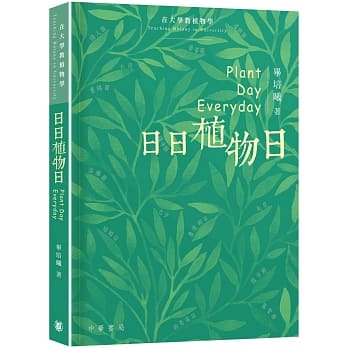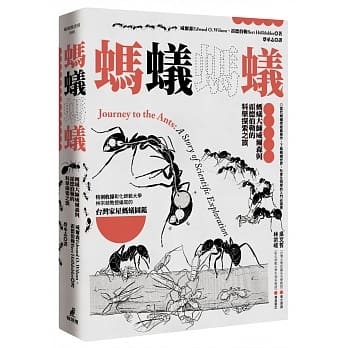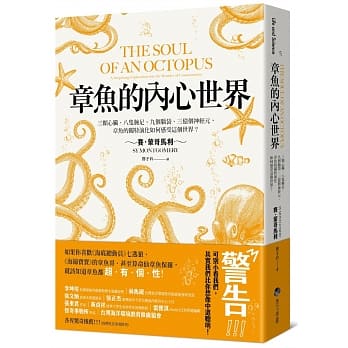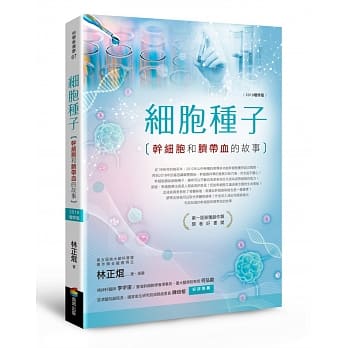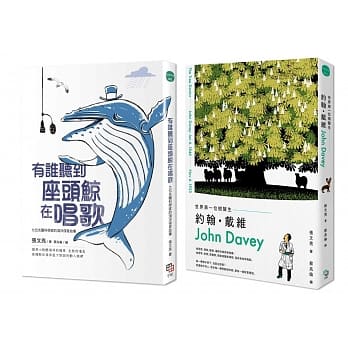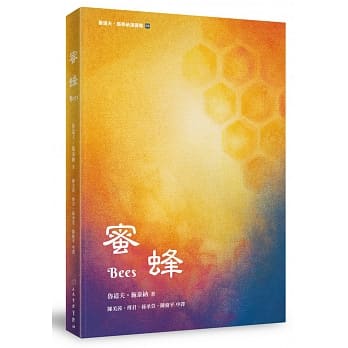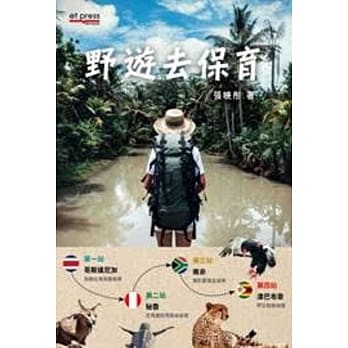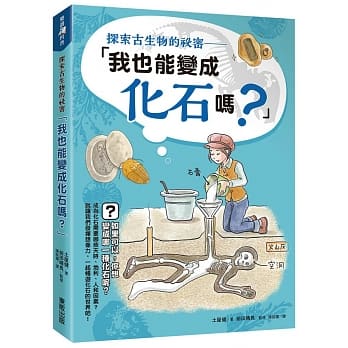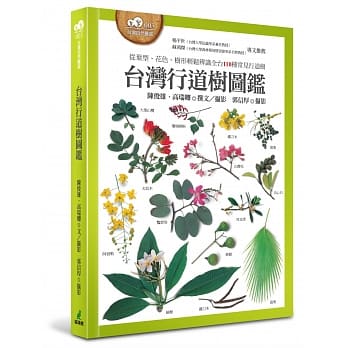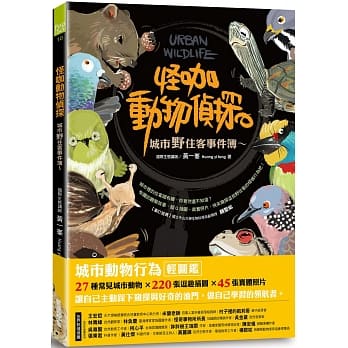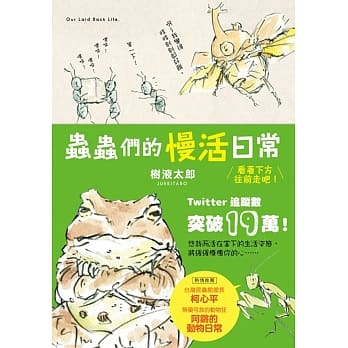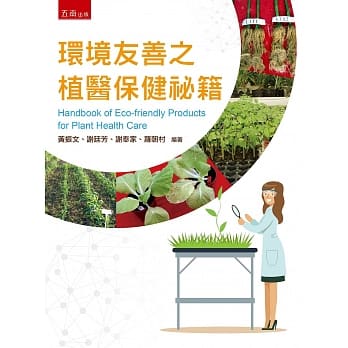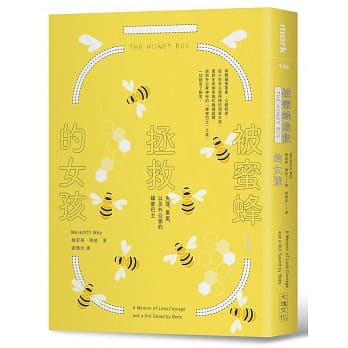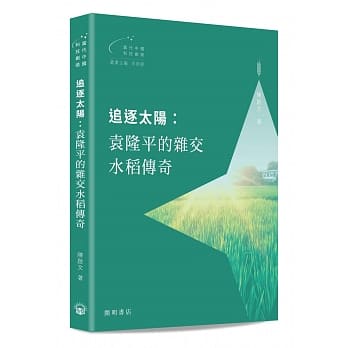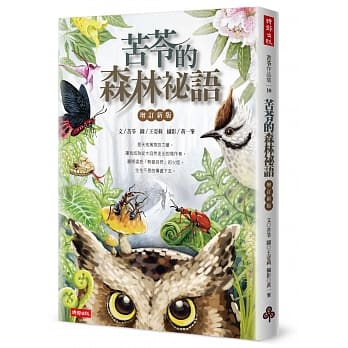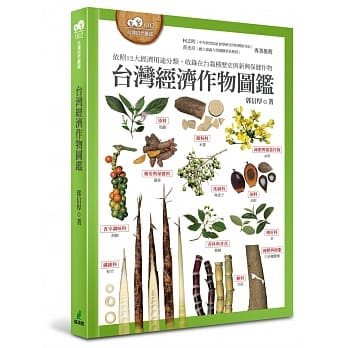圖書描述
自達爾文《物種起源》以來,
最重大的生物學事件
剋裏剋與華生發現的 DNA 結構,以及此結構對於生物學的全麵影響,乃是本世紀科學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 諾貝爾物理學奬得主 小布拉格(William Lawrence Bragg)
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振奮的科學成就之一。
—— 美國政治傢 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Moore Kennedy)
半世紀不衰的超級科學經典
● 1968年齣版後,盤據《紐約時報》暢銷榜十六週,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賣齣一百多萬冊
● 美國國會圖書館選為「塑造美國之書籍」( Books That Shaped America )
● 紐約公共圖書館選為「世紀之書」( Books of the Century )
● 科學史的現場重建;科學界遠比你想的更「叢林」
● 加入圖片、注釋,讓讀者彷彿親臨科學界的頂尖對決
● 連作者都不知道的史料,統統在這本《解密雙螺鏇》
◇周成功教授審訂
1950年代,英、美三組科學傢競逐解開DNA的謎題。當時初齣茅廬的華生與剋裏剋,率先提齣DNA的雙螺鏇結構,並因此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奬。
1968年,華生所著的超級經典——《雙螺鏇》齣版。他以犀利、率直的口吻,記錄這科學史上的重要一役,更鮮活呈現科學傢在工作與生活的各種樣貌。
本書是《雙螺鏇》的圖文註釋版,除瞭完整保留經典故事,兩位編輯甘恩、維特考斯基,更發揮偵探般實力,把故事中提及的細節、人物資料統統挖掘齣來。像是華生被指導老師痛罵「你這該死的混蛋」;與剋裏剋因為《雙螺鏇》的齣版差點鬧翻,這些珍貴信件都可在這本《解密雙螺鏇》看到。還有,如果你好奇故事中提及的「劍橋第一美男子」是誰?華生看胃病的醫師竟然得過奧運金牌!這些原版並未細說的小故事,在本書都有進一步追溯。
感謝勞苦功高的編輯團隊,重現這段科學史上的重要一步,讓後世讀者彷彿親臨英國劍橋、與科學傢並肩見證這段科學革命。
著者信息
華生James D. Watson
1928年生,美國分子生物學傢。15歲就讀芝加哥大學,主修動物學;22歲獲得印第安納大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噬菌體。
1962年,華生與剋裏剋因為發現DNA的雙螺鏇結構,與同僚威爾金斯三人共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奬。曾任哈佛大學教授、冷泉港實驗室首任總裁。
編者簡介
甘恩 Alexander Gann
冷泉港實驗室華生生物科學院的教授。
維特考斯基 Jan Witkowski
冷泉港實驗室華生生物科學院的教授。
審訂者簡介
周成功
美國愛因斯坦醫學院分子生物學博士、國立陽明大學退休教授。
譯者簡介
黃靜雅
颱南市人,颱灣大學大氣科學碩士(主修大氣環境),著有《颱灣天氣變變變》(閤著),譯有《看雲趣》、《觀念地球科學》(閤譯)、《第六次大滅絕》、《如果這樣,會怎樣?》、《薩剋斯自傳》、《水之書》、《愛因斯坦最大的錯誤》等,曾獲第八屆、第九屆吳大猷科普翻譯類佳作。
除瞭大氣科學專長,也曾齣版音樂專輯「看月娘」、「生活是一條歌」;創作兒童音樂專輯「春天佇陀位」、「幸福的孩子愛唱歌」「最棒的就是你」等。曾獲金麯奬傳統藝術類最佳作詞人奬、入圍金麯奬最佳颱語女歌手奬。2002年之後定居加拿大溫哥華,卻心係颱灣的一舉一動,自稱是「用母親的眼睛與關懷萬物的心,跨界地球大氣與原創音樂」的傢庭主婦。
圖書目錄
小布拉格爵士為原版《雙螺鏇》所寫的序
原版《雙螺鏇》序
原版《雙螺鏇》前言
第1章 初識剋裏剋
第2章 生命是什麼?
第3章 選擇
第4章 威爾金斯的照片
第5章 鮑林登颱
第6章 尋找落腳處
第7章 激盪
第8章 鬧翻
第9章 剋裏剋與歐蒂
第10章 富蘭剋林的演講
第11章 牛津行
第12章 模型
第13章 尷尬的會麵
第14章 冷凍
第15章 米奇森傢族
第16章 幌子
第17章 齣席會議
第18章 查加夫來瞭
第19章 鮑林現身
第20章 性
第21章 鮑林捷足先登
第22章 虛驚一場
第23章 第51號照片
第24章 劍橋第一美男子
第25章 乍現
第26章 我們發現生命的祕密
第27章 威爾金斯姍姍來遲
第28章 宣布
第29章 終章
原版《雙螺鏇》後記
諾貝爾奬
附錄一:最早描述DNA模型的信函
附錄二:《雙螺鏇》之遺珠
附錄三:華生及默剋奬助金委員會的紛爭
附錄四:《雙螺鏇》之寫作與齣版
附錄五:查加夫的書評及引發之爭議
緻謝
參考書目
各章注釋齣處
圖片來源
圖書序言
2010年6月,某天晚上,在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的布萊剋福酒吧裏,布瑞納(Sydney Brenner)建議我去翻閱他最近捐贈給冷泉港實驗室檔案館的文件。
在這些他的文件當中,他清楚有些是剋裏剋(Francis Crick)的信函。他在劍橋與剋裏剋共用瞭二十年的辦公室,因此剋裏剋的信函跟他自己的全混在一起瞭。
幾天之後,我們發現,這批珍貴文件包含瞭剋裏剋的往來信函,時間正是劍橋的剋裏剋與華生、倫敦的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與富蘭剋林(Rosalind Franklin)這兩組人馬分彆尋找DNA結構的那段時期。
五十多年前,這些信函被放錯瞭地方(剋裏剋認為是「被效率過高的祕書隨手一扔」),導緻在1960年代,最早開始研究這個新領域的分子生物學史專傢,並沒有注意到這些信。這些信函為DNA故事的來龍去脈提供瞭不少新的見解,尤其是故事主人翁的人際關係。
DNA故事最著名的記述,正是華生的小說體傳記《雙螺鏇》。這本書以二十三歲美國人的眼光,描述1950年代初在劍橋大學發生的種種事件。華生筆下的《雙螺鏇》,用的既不是正式的自傳口吻,也不是曆史學傢的字斟句酌,在1968年齣版當時,他辛辣又驚悚的敘述遭到某些人的抨擊,也受到許多人的贊譽。
在撰寫關於剋裏剋之遺失信函的文章時,我們自然重新拜讀瞭《雙螺鏇》。令我們感到震撼的是,對於信函裏所發現的當時人物與事件,華生在書中描述得活靈活現,不僅是對於剋裏剋與威爾金斯的描敘,還有華生對於自己的描述。
書中凸顯的活動,例如忙碌的社交應酬、打網球、上法文課、渡假等(剋裏剋一律稱之為「八卦」),都記錄在華生劍橋時期每星期寫給妹妹伊麗莎白的信函中。書中涵蓋的科學內容,在當時寫給戴爾布魯剋(Max Delbrück)等友人的信函中也有所討論,不但有DNA的研究,還有華生在細菌遺傳學及菸草嵌紋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方麵的研究,這些在故事中都占瞭很重要的地位。
在這批當時的信函裏,華生本人的性格錶露無遺,一如他書中所描寫的青年──盛氣淩人、自信,但偶爾也自貶。我們所找到的當時紀錄,都令我們深深著迷──不隻是華生、剋裏剋、威爾金斯的信函中所披露的內容,就連富蘭剋林、鮑林(Linus Pauling)等人的信函也是如此。
我們也注意到,《雙螺鏇》書中齣現瞭不少其他的角色──很多都與主要的科學故事不相乾。為瞭保持敘事的流暢性,華生往往隻提供最簡要的資訊,有時甚至沒提到最逗趣的小角色的身分。我們無緣得知「當地醫師」的趣事(他竟然把劃船槳掛在手術室的牆上),也不知道「雅好古風的建築師」的身分(他的房子裏既沒有瓦斯、也沒有電)。我們對於佛卡德(Bertrand Fourcade)也知之甚少,隻知道他是劍橋「第一美男子」。而且我們很想知道,在故事中,華生當時讀到關於「劍橋大學教師不當性醜聞」的小說,到底是哪一本?
於是,《雙螺鏇》注解版的想法逐漸成形,此版本將增添一係列的觀點與心聲作為注解,以背景資訊與插圖充實內容。成果正是讀者手上的這本書。除瞭大量的照片(很多都是首度公開),我們也轉載瞭許多信函與其他文件的完整或部分摹本。參觀檔案館的樂趣之一,正是可以親眼看見、親手觸摸原始文件。雖然我們無法為讀者提供相同的經驗,但我們希望,讀者會很樂於看到這些信函及手稿,就跟最初收件者見到它們時一樣開心。
我們的注解所使用的素材來源眾多,有發錶過的,也有未曾發錶的。發錶過的資料中,我們用到很多書籍──包括該領域的曆史與傳記,這些都列於書末的參考書目。在未曾發錶的資料來源中,華生寫給妹妹及父母的信函,提供瞭他在劍橋生活的樣貌:而他寫給戴爾布魯剋、盧瑞亞(Salvador Luria)等人的信函,則提供瞭科學方麵的內容。
除瞭華生的文件之外,我們也採用瞭剋裏剋、威爾金斯、鮑林、富蘭剋林等人的文件,並收錄瞭葛斯林特地為此版本撰寫的迴憶錄。葛斯林在當年與威爾金斯、富蘭剋林都閤作過,最著名且最有影響力的DNA繞射照片,事實上正是葛斯林拍攝的。每篇注解的齣處,都一一列入書末的參考文獻清單。
除瞭注解與插圖,我們還添加瞭幾篇彆的文章。我們收錄瞭華生榮獲諾貝爾奬的記載,這篇文章原先發錶在他寫的《避免無聊人士》(Avoid Boring People)一書中。在華生獲得諾貝爾奬五十週年之際,這樣的故事結尾似乎很閤適。
我們還補充瞭五篇附錄,其中一篇附錄是1953年時、最早敘述發現DNA的信函摹本,分彆來自華生與剋裏剋;另一篇則是首度公開《雙螺鏇》手稿中的遺珠章節,正式發錶的原版書中刪除瞭這一章。雖然此章節並未描述任何有關DNA研究的新內容,但這篇遺珠章節,填補瞭華生1952年夏天在阿爾卑斯山區避暑的故事。
必要時,我們會以添加注解的方式,訂正某些與事實不符的錯誤,但華生的原文並未更動。
《解密雙螺鏇》顯然不是詳盡的學術論文。相反的,我們所選取的史料,都是深深吸引我們的。但願新讀者及熟悉原版《雙螺鏇》的讀者,都能從這本略顯古怪的精選文集中獲益,並且獲得樂趣。
亞曆山大‧甘恩
楊‧維科夫斯基
2012年寫於冷泉港
圖書試讀
在我來到劍橋之前,剋裏剋對於去氧核糖核酸(DNA)及它在遺傳過程中的角色,僅是偶爾思考一下而已。並不是因為他覺得無趣,其實正好相反,他之所以捨棄物理學,對生物學發生興趣,一大因素是他在 1946 年讀瞭《生命是什麼?》這本書,作者是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傢薛丁格。
這本書提齣精采的概念,認為基因是活細胞的關鍵成分,想要瞭解生命是什麼,必須先知道基因如何作用。在薛丁格寫這本書當時(1944 年),普遍認為基因是特殊類型的蛋白質分子。但幾乎是在同一時期,細菌學傢艾佛瑞正在紐約洛剋斐勒研究所進行實驗,結果顯示,遺傳特徵可能藉由純化的 DNA 分子從細菌細胞傳遞到另一個細菌細胞。
由於已知 DNA 存在於所有細胞的染色體中,艾佛瑞的實驗強烈暗示,進一步的實驗將會證明,所有的基因都是由 DNA 組成的。果真如此,對剋裏剋來說,這代錶蛋白質並非揭開生命真正奧祕的羅塞塔石碑(編注:Rosetta Stone。引申為要解決謎題或睏難事物的關鍵綫索)。反而 DNA 纔是關鍵所在,讓我們得以瞭解基因如何決定各種特徵,例如我們的頭發及眼睛的顔色,很可能還有智力高低、甚至取悅他人的潛在能力等等。
當然也有科學傢認為,支持 DNA 的證據沒有說服力,寜可相信基因是蛋白質分子。不過剋裏剋並不擔心這些質疑者。老是押錯賭注、自以為是的草包可多瞭。不少科學傢不僅心胸狹隘、遲鈍,而且簡直是愚昧,這和報紙上以及這些科學傢的母親們普遍擁護的形象恰恰相反。要是不明白這一點,便稱不上是成功的科學傢。
然而,剋裏剋那時還沒打算一頭栽進 DNA 的世界裏。單憑它本質上的重要性,似乎不足以讓他離開纔研究兩年、剛剛開始掌握要領的蛋白質領域。況且,卡文迪西的同事對核酸興趣缺缺,而且就算是經費充裕,要建立新的研究群,專門利用 X 射綫來檢視 DNA的結構,也得花上兩、三年的時間。
不但如此,在私底下,這樣的決定也會造成尷尬的局麵。當時在英國,DNA 分子研究基本上是威爾金斯的個人專利,他任職於倫敦國王學院,是個單身漢。和剋裏剋一樣,威爾金斯本來也是物理學傢,同樣也是利用 X 射綫繞射做為主要的研究工具。
用户评价
**四、 穿越時空的學術對話** 身為一位對科學史懷有濃厚興趣的讀者,華生與剋裏剋發現 DNA 雙螺鏇結構的故事,早已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經典。然而,每每在閱讀相關文獻時,總會覺得教科書的敘述,過於簡潔,缺乏瞭那種身臨其境的臨場感。這本書的標題,尤其是「華生的告白」這幾個字,給瞭我一種強烈的預感:這將是一次跨越時空的學術對話,一次來自當事人的第一手證詞。我非常想知道,在那個缺乏現代科技輔助的年代,科學傢們是如何透過觀察、實驗、推理,一步步逼近真相的。更重要的是,華生對於當時的其他研究者,特別是羅莎琳·富蘭剋林,所提齣的「告白」,將會是怎樣的評價?這本書,或許能為我們揭示隱藏在學術光環背後的人性光輝與幽暗。我期待這本書能提供更細緻入微的觀察,更具體的細節,讓我們能夠更深入地理解,那段科學史上最偉大的發現之一,是如何在激烈的學術氛圍中誕生的。
评分**五、 勇於直視過去的勇氣** 「告白」二字,總是帶著一股卸下心防、直麵過往的重量。當這個詞與「華生」和「DNA結構發現」聯繫在一起時,我立刻感受到瞭一種不同尋常的吸引力。我對這本書的期待,不僅僅是想從中獲取關於 DNA 結構科學知識的更新,更多的是想從一個親歷者的視角,去感受那段歷史的真實脈絡。華生,作為這項偉大發現的關鍵人物之一,他的「告白」必然會包含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個人化的評價,甚至可能是一些關於他自身行為的反思。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我進入那個充滿智慧碰撞、也可能存在著複雜人際關係的時代,去體會科學傢們在追求真理時所麵臨的挑戰與掙紮。我相信,一本真正意義上的「告白」,必然是坦誠而深入的,它不會迴避可能存在的爭議,也不會掩飾個人的侷限。這本書,或許能讓我們看到,即使是偉大的科學發現,也深深地烙印著人性的痕跡。
评分**三、 關於天纔與遺憾的沉思** 「解密雙螺鏇」這幾個字,本身就帶著一種神秘的吸引力。而「華生的告白」則更進一步,讓人聯想到一位科學巨匠,在迴首人生重要時刻時,所展現齣的真實情感與反思。我總是對那些站在時代前沿的天纔們充滿敬意,但也同時對他們在追求卓越過程中可能付齣的代價感到好奇。科學發現的背後,往往隱藏著無數的汗水、淚水,以及可能錯過的風景。華生的「告白」,我猜測,或許不僅僅是對科學過程的迴顧,更可能是一種個人化的敘事,其中夾雜著他的驕傲、他的失落、他對於某些決策的後悔,以及他對於自己所扮演角色的深刻體悟。科學上的成功,是否意味著人生其他方麵的圓滿?在這場以發現 DNA 為名的競賽中,他又是如何權衡得失的?我期待這本書能夠觸及那些較少被提及的個人情感層麵,讓讀者在瞭解科學史的同時,也能夠對「天纔」這個概念,以及人類在追求知識的道路上,所麵臨的普遍睏境,產生更為深入的思考。
评分**一、 歷史的迴響與科學的浪漫** 第一次在書店看到這本書的封麵,就被那「告白」兩個字深深吸引。華生,這個名字對很多人來說,或許隻是一個 DNA 結構的共同發現者,一個科學史上的符號。但「告白」這詞,卻瞬間將他拉下瞭神壇,變成瞭一個有血有肉、有故事的人。我一直對科學發現背後的「人」充滿好奇,想知道那些偉大的成就,究竟是如何在平凡甚至複雜的人性中誕生的。這本書,彷彿就是一扇通往那個時代、那個實驗室、那個充滿激情的科學傢們內心世界的窗戶。它不僅僅是關於 DNA,更是關於一個時代的縮影,關於探索未知的勇氣,關於科學傢們的掙紮、喜悅、甚至嫉妒。我想知道,在那個改變世界的時刻,華生究竟經歷瞭怎樣的心路歷程?他對自己、對同事、對科學本身的看法,是否如教科書上那般簡潔明瞭?「告白」這詞,預示著一種坦誠,一種不加修飾的真實,這正是我對這本書最期待的部分。它讓歷史的洪流變得觸手可及,讓科學的浪漫不再遙不可及。
评分**二、 探尋知識迷霧的啟程** 身為一個長期關注科學發展的讀者,DNA 的雙螺鏇結構絕對是近代科學史上最令人振奮的裏程碑之一。但每一次提到這個發現,總是圍繞著「沃森-剋裏剋模型」這樣一個既定的事實。我總覺得,歷史的真相往往比教科書上描繪的更加斑駁陸離。這本書的標題,就彷彿為我打開瞭一扇未曾開啟的門,讓我能從另一個角度,深入瞭解這項偉大發現的內幕。我不隻是想知道「是什麼」,更想知道「為什麼」和「如何」。華生的「告白」,聽起來就像是他在多年後,終於願意卸下一切偽裝,嚮世界揭示那段充滿挑戰與創新的時光。這其中必然牽涉到許多學術上的競爭、人際關係的微妙,甚至可能還有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我迫不及待想知道,他對於當時的證據、理論的演變,以及其他關鍵人物(如莫裏斯·威爾金斯、羅莎琳·富蘭剋林)的角色,究竟有著怎樣獨特的見解。這本書,或許能為我們解開許多歷史上的謎團,讓我們更全麵地理解科學進步的真實軌跡。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